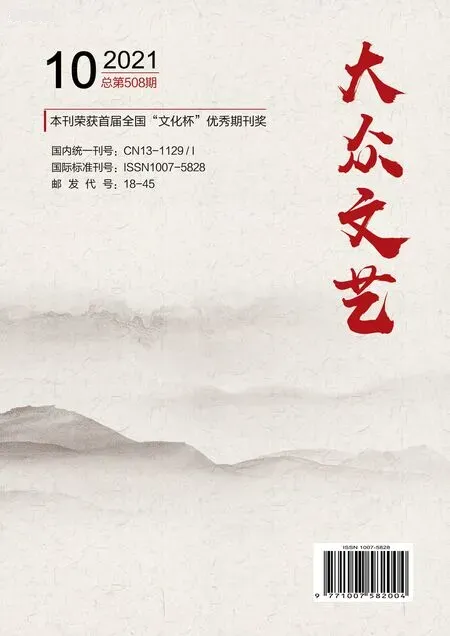透视悲剧与《悲剧心理学》的透视*
常晓茗
(南京艺术学院,江苏南京 210000;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江苏南京 210000)
《悲剧心理学》是朱光潜先生以在《悲剧的快感》一文的基础上,原英文撰写的博士论文,起初由斯特拉斯堡大学出版社出版,后来在国内印制单行本。“《悲剧心理学》是我国悲剧理论史上的一座重要里程碑”,朱光潜先生在具有高度的逻辑性的基础上,在历史维度、内容维度上,全面细致从西方主要悲剧理论的类比、对比中,通过不断螺旋式上升的思辨脉络,形成了具有融合东西方美学特色的思辨理论。
在朱光潜先生的《悲剧心理学》中对于主题的论述往往涉及众多研究,以悲剧心理作为始终环绕的中心形成循环往复、不断盘旋上升、相互独立又能合理链接的多个学术话题、相应的学术问题以及渗透于思辨本身的思维问题,因此《悲剧心理学》具有价值观意义、文献学意义以及方法论意义等多重的重要内涵。
一、透视悲剧——悲剧内核与自身
悲剧研究是一种独特的美学观。《悲剧心理学》的开篇破题即抛出了问题:“然而奇怪的是,人们固然憎恶苦难,却又喜欢看舞台上演出的悲惨事件。”这既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又具有难以解答的疑惑,通过专业的思考仍能发现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这个问题的重要研究价值被凸显出来。而对这个关键问题进行释惑,则展开了对悲剧内核的解读:“悲剧是最高的文学形式、悲剧快感能解决心理学的问题与难题、悲剧心理学的研究对美学也将是一大贡献、对文学批评具有革命性的鼓励、有益于舞台表演艺术、悲剧和宗教与哲学所要解决的终极问题密切相关。”
悲剧是一般审美经验中的一种审美体验,“审美观照区别于概念联想、审美态度区别于批评态度并动摇了享乐派美学基础、审美经验独立于伦理道德的考虑。”康德、席勒、斯宾塞支持审美经验与功利无关,审美超脱于功利与实用,是闲情逸致的产物;克罗齐的“艺术直觉论”强调艺术的非概念性,带着太多概念就将不再是艺术;柏格森、哈曼、闵斯特堡提出艺术的非关联性:“整个意识领域都被孤立的对象所独占。”以及叔本华主客体混为一体的审美合一性,都是一般审美经验的主要特点。
但是绝对的概念和绝对的独立对于审美来说又是行不通的,那么如何做到非概念性、非关联性的审美,其切题与破题的回应为——“心理距离说”,审美需要距离,包括空间距离、时间距离、关系距离,即通过采取不同的条件去制造距离、加入诸多条件形成陌生化效果,形成与自然条件不一样的审美状态。什么样的艺术才算得上是接近完美的?这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对于距离的把控。俗话说“距离产生美”,但是在艺术的鉴定欣赏和创作的过程中是需要掌握其中的尺度的,不要过度地去拉近与艺术的距离,要保持一定的距离感,过度的追求“距离之美”是理想主义的艺术追求者所具有的通病,距离过度往往会减少对作品鉴赏的趣味性和对作品理解的深度;而距离过近则又是那些无限追求自然主义者的通病,这种“近距离”的接触往往会使鉴赏者局限于日常现实主义的联想当中,没有办法超脱出来,难以体味艺术品本身所蕴含的超越表面的深层次的东西。所以,艺术的创作必须要把握距离的尺度感,在坚守形式感和反写现实主义的核心的基础上,来加入超越表面的深度内涵,而这些全部是悲剧当中距离的重要阐释依据。审美距离的源头是心理距离,所有审美来自审美距离及其分寸的把握。悲剧距离化的产生与塑造,可以通过实际生活的距离化、时间空间遥远化;通过任务、情境与情节的非常性质,例如超出日常的极其突出非常态情境、个性鲜明的强悍与过分执着所形成的性格-命运关系;通过艺术技巧与人为的形式的程式;通过抒情、超自然、舞台技巧和布景效果来实现。本质上这是一种人为设计框架并经过艺术化手段过滤,剩下美感快感,变成艺术而不是实际生活的一种规律与过程。“悲剧中可怖的东西必须用艺术的力量去加以克制,使之改观,使它只剩下美和壮丽。”
二、《悲剧心理学》的进路逻辑透视
对于观看悲剧,审美快感是否等同于“幸灾乐祸”的恶意这一最基本的判断和必须要回应的悲剧心理学基础性问题,朱光潜先生分析快感来源与恶意关系的基础性脉络,是以来自常识性经验、判断作为逻辑起点,采用对浅表简单的表达逐渐进行丰富的过程,通过审美态度与实际态度的区别、日常生活之线被戏票剪断的距离化过程、对法格理论缺陷的批判反驳观看悲剧是幸灾乐祸的恶意说。
特别是对法格的批判具有非常强有力的逻辑锐度。法格提出戏剧显然诉诸人类天性残忍,恶意中伤、诽谤与喜欢喜剧可以归入统一理论范畴,而悲剧与喜剧的区别只是程度的区别,因此悲剧具有与他所分析的喜剧相同的恶意要素。朱光潜先生的批判主要为两点:一是作为前提的喜剧恶意说没有得到共识和理论支点,二是悲剧与喜剧两种艺术形式之间的关系与区别的研究范畴甚至超越悲剧心理学所要开展的研究,因此采用法格的理论来支撑恶意说并不能够得到确立和认可。“不能归因于人性中根深蒂固的邪恶本能……”
“恶意说”的批判之后,与“恶意”这类带有残忍特性的心理状态相反的“同情”被紧密联系到分析之中,把逻辑关联最为密切的思维切口对准聚焦于博克的“怜悯说”。博克同情理论的基础得到了三个维度的总结,一是从现实中得到快乐是片面的真理,二是现实苦难比悲剧更加具有吸引力,三是生物学解释是不准确的臆测。博克所指向的同情具有道德伦理意义,道德同情消除了距离从而破坏了悲剧效果,道德同情与审美观照中“移情”现象下的审美同情的重要区别还在于,道德同情是主客体具有明确差异、具有利害得失的实际功利考量、针对客体能够引发实际结果和实际反应的人类心理活动;审美同情与其相反,它是主客体同一、脱离生活史背景的超功利活动以及与客体活动平行、并不引发实际结果的心理活动。
讨论同情之后,分析的相关思路已经推进至“怜悯和恐惧”。怜悯是复合情感,它包括爱或同情、惋惜、安全感、自我优越感,但它同时又是人类社会的普遍情感、一种审美同情。怜悯具有居高临下的感觉,而与其相反的,自上而下、具有压制特点的恐惧,又区分为生活恐惧与悲剧恐惧,生活恐惧并不等同于悲剧恐惧,生活恐惧只有可怖,悲剧恐惧既有恐惧与欣赏的叠加又有恐惧与鼓舞的叠加。
那么,悲剧心理本身的特质究竟为何?痛感中的快感正是具有这样的重要价值。人们并不总是逃避痛感,痛感和快感并不是相互绝不相容的,痛感与快感相互关联又同时具有各自特性,相互产生、共同存在,是两者之间以各种比例混合和调和的一种存在。痛感通过身体活动得到缓和,通过器官冲动得到宣泄,并通过艺术家创造性的想象得到克服和转化,通过艺术的距离化得到升华。朱光潜先生既尊重规律,又高度提升了对人作为主体的点赞,痛感与快感需要不断地混合并找到合适的黄金分割,共同激发出生命力的冲动、感动与冲击,生命力感是这些中和、平衡与混合的最终指向。“如果我们可以用数学方程式来表现已经得出的结果,那就可以说怜悯和恐惧中积极的快感加上形式美的快感,加上由于情绪的表现或缓和再将痛苦变为怜悯和恐惧而得到的快感,最后得出的总和。”
至此,朱光潜先生运用参照系进行比较性表达,形成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开展层次性强的逐层递进思辨,完成了悲剧心理的进路阐述,这是朱光潜先生在研究逻辑上第一重胜利。
三、《悲剧心理学》的思辨逻辑透视
黑格尔悲剧理论的大致轮廓是将“绝对理念”延伸到自己的悲剧理论中,强调通过“永恒正义”的干预达到和解。绝对理念是终极的统一,所有个别都在绝对理念中失去特殊性的一般,这种绝对理念可以被视为认知格局的无限性:对立与矛盾是泛在的,但是认知的延展在框取矛盾的时候,将一切对立、差异与矛盾消解,例如当认知范畴从渺观到微观再到中观,然后扩大至宏观并再次扩充到宇观,这种螺旋式上升的框取矛盾层次不同的扩展,使矛盾不断的“和解”。黑格尔认为悲剧结局要么同归于尽完全消解,要么放弃排他,无论是终结、归顺、还是妥协,总之归于和解;悲剧中的矛盾体并非命运的产物而是“永恒正义”的表现,悲剧快感在于看到“永恒正义”的胜利,广义的和解感构成了是悲剧快感的根源。但是,朱光潜提出黑格尔唯理主义悲剧观具有弱点——它是先验推演、以希腊悲剧的错误解释为基础、不适用于近代悲剧、忽略了悲剧受难以及在命运问题上存在矛盾、在根本上来说是悲观的,意味着冲突导致毁灭。黑格尔的“永恒正义”具有一种圆满哲学理念的特质,但是仅仅能够从自身进行逻辑自洽,事实上,悲剧并不是按照永恒正义所阐释的那样具有必然性,悲剧更多具有偶然性,黑格尔的悲剧理论具有哲学逻辑,但是缺乏悲剧逻辑、艺术逻辑与生活逻辑的有力支撑。
布拉德雷的悲剧观点尝试支持黑格尔理论并对其中的弱点进行重新阐释,但却脱离了黑格尔的原初立场,布拉德雷在继承中暴露了黑格尔的理念弱点。“布拉德雷教授给‘和解’一词加进来完全不是黑格尔派的意思,它不是永恒正义的证明,却是个人意志的胜利,也就是说,是黑格尔很不喜欢的‘主观性’和‘片面性’的表现。”布拉德雷认为决定悲剧冲突与结局的要素是命运而非正义,这与黑格尔的和解本意并不一致。朱光潜先生对于黑格尔批判的一个切口正是支持黑格尔悲剧理论的布拉德雷。
朱光潜先生的整体美学观,更倾向对叔本华与尼采的理论偏爱,更强调人作为主宰性的价值——人的生命力得到释放、所有悲剧都是意志悲剧,悲剧的产生在于人的本身,人类作为引以为豪的存在应当得到礼赞,人的力量愈发强大,主观主义愈发强大,人在有限生命中证明价值的存在。这与古典悲剧观所认为的,理性背后是人的主体性弱化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因此认为古典悲剧观并非真正接近悲剧本源。尼采用感性喷涌的酒神与理性静止的日神作为生命力的两端来尝试寻找悲剧快感的解释。叔本华与尼采的理念终极是悲观的,但仍能感到人的生命力的展现。这些理论的阐释是朱光潜对悲剧心理从客观转向主观的变化,也是由古典转向近现代的理论分析,更加深入的通过叔本华的意志本源论和尼采的酒神日神说,肯定生命意志,转向主观世界与内宇宙的探查,注重指向人类主体内在感受即生命力的感受。
四、《悲剧心理学》的目标逻辑透视
朱光潜对于目标阐释的锚定有着深刻的逻辑内线,这一内线是人类对世界的认知进程与人类戏剧观念变迁的双重路径相交织共同搭建而成。人类认识世界的进程是从浅显到深刻,从对大自然紧张畏惧到通过神话、传说、宗教想象再到对于命运的思索,尤其是对命运作为结果存在还是作为原因存在的讨论,是人类认知的关键转折之处,这也是人类从对想象世界的追寻、到现实世界的探询、再到人类内在世界的探索的过程。对于性格与命运之间关系的假设,使得人类的性格要素得到重视,从而进入正义作为社会力量的社会层面观念的讨论及思考,人类宇宙观形成了从自然到社会再到内心的由客观宇宙世界转向内宇宙的审视。
人类戏剧观念的变迁与人类认识世界的发展进程相伴随,古希腊悲剧往往以无法逃脱的命运作为悲剧的嵌入式内核,在古希腊后期,这一观念亦有所松动,关于人的主体性强化使得命运、性格、正义作为混合的悲剧构成模式进入到戏剧的呈现中来,莎士比亚将命运、性格、正义进行了充分的柔和形成了近代悲剧与古代悲剧之间的有效过渡,恰恰呈现出用以强化人性的丰富度和复杂性的悲剧作品,故而歌德曾说在《说不尽的莎士比亚》中提出莎士比亚“还是一个真正的现代作家,他与古人之间隔着一道鸿沟”;按歌德的归结,莎士比亚能以一种绝妙的方式把古今相结合起来,使主体的愿望与客在的天命在他的作品中达到平衡——二者相持不下时,愿望终究会处于劣势。而近现代的悲剧理念更是以性格为主导的阶段,以性格决定命运作为深刻的嵌入式核心。
回归到人类本身的探寻,生命力感是朱光潜《悲剧心理学》所要指向的最重要的核心议题,也是朱先生起笔阐释以来进行思辨的重要靶点,“引起我们快感的不是灾难,而是反抗。”早在对怜悯与恐惧的思辨中,朱光潜对生命力支持的态度就充分的蕴含其中,体现在对怜悯与恐惧分析章节的结论:怜悯与恐惧必须加入元素才能进入悲剧中,加入秀美与崇高力量形成激励和鼓励的积极情绪,用生命力揭开怜悯与恐惧的生命密码——激活、激发与内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