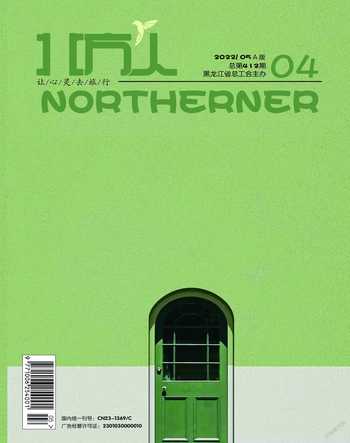四川大厨在美国
[英]扶霞·邓洛普

寒冷的秋夜,我们坐在露台上,沐浴在从窗户那边溢出的暖光之中。用“兴奋”来形容我此刻的心情都是轻描淡写了。我之所以怀着如此强烈的期待,一是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来“法国洗衣房”,这家餐厅位于加州的杨特维尔,是大厨托马斯·凯勒的高级料理殿堂,我迫不及待地想品鉴看看它是否不负盛名。
不过,还有更重要的原因:我今晚的“餐友”是三位杰出的大厨,肖见明、喻波、兰桂均,他们来自四川。这三人都是第一次来到西方国家,从前也没有真正接触过中国概念里的“西餐”,所以,我除了自己对这顿饭抱有期待之外,也很想看看他们的反应。
在驱车经过29号高速前往餐厅的路上,我想给客人们做点“餐前心理准备”,就随口一说:“你们很幸运哦,因为我们要去全世界最棒的餐厅之一。”
“全世界?”兰桂均表示质疑,“谁封的?”
这个疑问对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做出了清晰的预示。
就我个人而言,这顿饭是超出预期的——餐厅装修低调奢华,服务礼貌亲切,当然还有我为在座的大家点的“主厨亲点”菜单,一共十四道菜。像“牡蛎珍珠”这样的特点佳肴和我想象的一样精彩。油煎红鲷鱼片,搭配酸甜橙和“融化”菊苣,堪称琴瑟和鸣,实乃天作之合。这一盘盘食物中真真蕴含着诗意:崇高享受,引人入胜。
然而,在我自己渐入佳境地享受着这顿叫人完全心满意足的晚餐时,却不得不注意到“餐友”们与我的体验感受大相径庭。三人中最有冒险精神的喻波,下定决心要尽情品味每一口,并仔细研究这顿饭的排布和构成。他全神贯注,神情庄重。但另外两位只是在强撑。我崩溃而清晰地意识到,对他们每一位来说,这都是一次千困万难、十分陌生又极具挑战的经历。
我在这一餐品尝到了美食生涯中最完美的羊肉,但他们三人却觉得太生,生得令人震惊。一系列美味的甜点在他们看来有点“无事包金”(四川方言,意为“没事找事”),毕竟在他们的饮食文化中,甜食并没有那么重要。巨大的白色餐盘上只放了一人份的少量食物,这样的摆盘方式也叫他们困惑不已。这顿饭采用了“俄式上菜法”(即按照“头盘—汤—副菜—主菜—甜品”的顺序分别上菜,每次一道,随吃随撤),时间较长,也让他们觉得太过难挨,仿佛永无止境。
这顿饭让我颇感震撼的是,在某种抽象的层面上,托马斯·凯勒的菜竟与最精致的中餐有着很多共同之处,比如上等的食材原料,包含其中的非凡智慧与匠心独运,以及在微妙之处注重味道、口感与色彩的和谐共鸣。然而,这一切饮食理念的实体表达,也就是我们面前这一道道菜品,却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
“这个我该咋个吃呢?”喻波问道。那道叫我吃得欲仙欲死的红鲷鱼,却让他烦恼疑惑。他那摸不着头脑的样子,恰如一个西方人面对人生的第一碗鱼翅汤、第一盘海参或第一份炒鸭舌。我常在中国看到这样的情景,但这还是我第一次站在另一边的角度去见证刚好相反的情况。
三位大厨并没有很多西方人在中国那样的傲慢,死守着自己的偏见不放。兰桂均承认:“只是因为我们不懂,就像语言不通。”喻波甚至更为谦虚,“都很有趣,”他说,“但我就是说不出来到底是好是坏:我没有资格来评判。”
大厨们此行赴美,主要目的是在圣海伦娜的美国烹饪学院做展示。在学校吃午饭时,他们表现得很礼貌,往自己盘里装的是沙拉和做熟的肉类。去各家餐厅用餐时,他们最喜欢的西餐总是那些与中餐关系最密切的:烧烤猪排、烤鸡、南瓜泥。他们唯一吃了个光盘的一道菜,是意式海鲜调味饭:“很是吃得下。”这是他们的一致评价,但又觉得区区一碗汤饭竟然收这么贵的钱,实在太好笑了。
但也有一些我不曾预料到的大忌讳,最突出的就是他们对生食发自内心的厌恶。三位大厨看着端到面前的血淋淋的生肉惊骇不已。在学校吃了两天自助午餐之后,就连沙拉也让他们觉得厌倦:“我再吃生的东西,就要变成野人啦。”肖见明开了个玩笑,露出了一个顽皮的笑脸。
硬壳的酸酵种面包,他们觉得很硬,嚼不动,吃起来很不舒服。中国人喜欢那种滑溜溜的、软骨一样的口感(想想鸡爪、海蜇和鹅肠),而大部分西方人对此可谓深恶痛绝。而酸酵种面包独特的口感似乎一时半会儿在中餐里还找不到能与其对应的食物。大胆的喻波一直在品尝和分析一切,即便另外两位大厨已是意兴阑珊。我饶有兴味地观察着喻波咀嚼人生的第一口洋蓟心,品尝枫糖浆,深吸一口气,感受有史以來第一缕上乘红酒的酒香。
有个奇怪的文化态度镜像。西方人会抱怨在中餐馆用餐后一小时就又饿了,而这些中国游客在美国也经常性地面临“吃不饱”的问题。一天晚上,在一间餐厅以欧洲餐桌礼仪吃了几道菜之后,肖见明明确要求我去问问,能不能上一份简单的蛋炒饭。这要求在中国特别正常。(餐厅当然做不到了,因为他们根本没有现成能用的冷饭。)
我们在烹饪学院的第三天,他们宁愿选择一家风评并不好的中国餐馆,也不愿意再冒险尝试另一顿精美的西餐了。过完第四天,我们在学院的厨房找到了一个电饭煲,所以晚饭我们都吃了蒸米饭,配上简单的辣味韭菜。到美国以来,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三人吃得这么狼吞虎咽,看着是如此开心和放松。
西方人可能认为,中国人有着种类丰富到令人惊讶的食材、中国人爱吃“怪”食,而相比之下,西餐就很“安全”和“正常”。但这些大厨在这个国家的经历恰恰说明,美食方面的文化冲击是双向的。
他们在加州做出的种种反应,让我想起自己食在中国的早期回忆:我刚到目的地安顿下来的那天晚上,风尘仆仆、疲惫不堪,在一家重庆火锅店,面前是一桌子奇形怪状的橡胶一样的东西,我一个也不认识,更不知道该怎么吃;我与花椒第一次相遇时,它们被大量地撒在我点的每一道菜里(“真难吃,受不了”,我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朋友好心地夹了精挑细选的小块猪脑花放进我的米饭碗,我想尽办法不吃。招待我的中国朋友觉得他们是在给我“打牙祭”,特别优待,而我却要挣扎着才能把那些食物吃下去,一边还要强装出一副勇敢的样子,真是太难了。所以,我真的特别理解和同情这些中国朋友,他们在这条充满挑战的路上迈出了试探性的第一步,还得努力保持礼貌、努力去适应。
但初遇总是会带来震荡的,不管你的起点是四川还是加州。大厨们在美国匆匆一瞥,兴趣盎然;然而在美食方面,确实是过于新奇了,短时间内很难消化吸收。在旅程的尾声,肖见明和兰桂均已经归心似箭,要赶紧回四川喝一碗米粥、吃个红烧鸭、尝点儿豆瓣酱了。
尽职尽责地当完导游和翻译的我又做了什么呢?我在一家咖啡馆舒服地坐着,点了个汉堡,肉饼要五分熟,加一片奶酪和大量的生蔬菜沙拉。也许有人要说这是野蛮人才吃的东西,但是,天啊,真是太美味啦。
(摘自上海译文出版社《寻味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