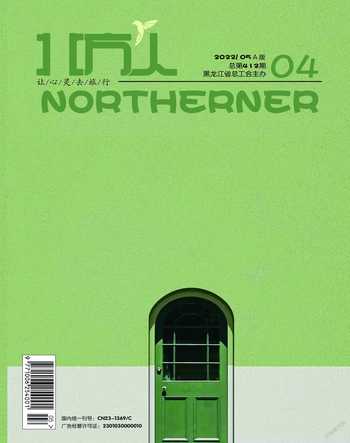黑白色的回忆
丁立梅
父亲在32岁上,照过一张小照。在上海城隍庙照的,二寸,黑白的。父亲那时是送姐姐去上海看腿病的——姐姐的腿被滚水严重烫伤,整日整夜地哭。父亲的心被折磨得七零八落。在姐姐的腿伤稍稍好了之后,从不迷信的父亲竟然跑去城隍庙,想给姐姐买一个护身符。
父亲最终在城隍庙买没买到护身符,我不得而知。但父亲却留下一张小照。当时父亲看到一家照相馆,不知出于什么心理,就走了进去,就拍了一张二寸的黑白照。照片上的父亲,脸上有着深刻的忧伤,却挡不住风华正茂的英气。那张小照带回来,被许多人争相传着看,都说照得好。多年之后,我在镜框里再看时,发觉父亲的那张小照,特像电影演员赵丹。而这时的父亲,正倚在家里的沙发上打瞌睡,衰老得似一口老钟。
记忆中的父亲,是没有这么老的,是永远的32岁的风华。在一大帮大字不识一个的乡人里头,父亲是多么的出色,他不但断文识字,吹拉弹唱,也无所不会。那时的我们,喜欢围了父亲转,喜欢听父亲拉二胡、吹口琴、哼《拔根芦柴花》的小调。我们也喜欢争相把父亲的小照偷出来,在别的小朋友面前炫耀,说,喏,这是我爸。赚尽骄傲和自豪。
我上学了,成绩很好。父亲跟人说,只这个女儿是他的翻版。但父亲从未指导过我的学习。只有一次,我伏在桌上用红红绿绿的粉笔画人,那时我迷恋画画,喜欢画人,把人涂得五颜六色才觉得漂亮。父亲从我身旁经过,停下来看我画,看了会儿,他俯下身子,帮我把人的耳朵加上,温柔地说,应该这样画。又揩掉那些五颜六色,给人穿上浅褐色的中山装。我对着看,竟发觉那画儿有些像镜框中的父亲了。父亲原来还会画画啊,我那时的惊异简直无以复加。到学校后,自是免不了在同学面前夸耀一番,说我爸会画照片上的人呢。
当我的书渐渐读多了后,对父亲的崇拜渐渐少了,以至到无。我眼中的父亲,与其他庸常的父亲没什么两样,他抽难闻的水烟,半蹲在檐下,呼哧呼哧喝稀饭。及至我工作了,父亲来城里看我,当着我的一帮同事,他把大厦读成大夏。我羞红了脸纠正。父亲讪讪笑,再读,还是读成夏。我只有摇头。
父亲老了,很多的病也就上了身。最严重的是脊椎病,压迫得双腿不能走路。这时的父亲无助得像个小孩,被我接进城里来看病,完全听任我的“摆布”。神情落寞。
一日,我约了几个朋友出外游玩,拍了许多照片。回来,我一边翻看照片,一边随口对坐在沙发上眯着眼打盹的父亲说,爸,我们也来照张合影吧。父亲一下子睁开眼(我怀疑他一直在假寐),眼神亮亮的。他站起来,病腿也好似比平常好了几分,他走到我面前的椅子上坐了,對着镜头认真摆好姿势,开心地说,你不嫌爸爸老吧?
我把那张照片洗出来,效果很好。照片上,我与父亲都笑得满脸生辉。父亲久久地对着看,嘴里说着,拍得真好啊。我知道,这张照片从此后父亲将会贴身揣着,逢人便要掏出来炫耀,像小时我炫耀他的照片一样,他会指着照片上的我对别人说,喏,这是我小女儿,是个作家呢。
(摘自作家出版社《仿佛多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