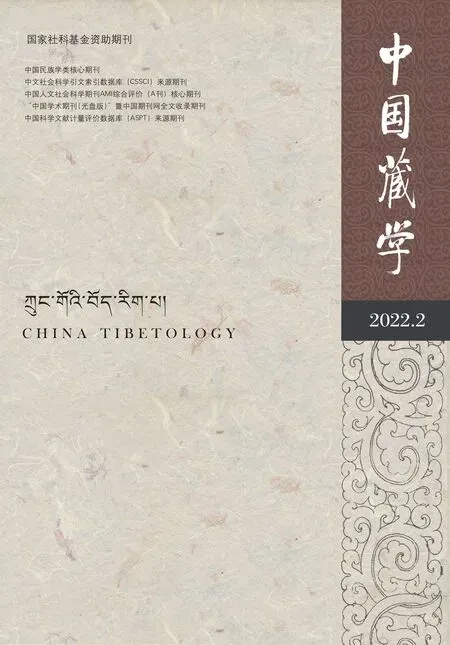西藏珍藏的明代内地玉器刍议
石婷婷
自7世纪起,西藏与内地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元代中央政府对西藏进行了直接治理,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往来互动频繁,不仅在政治上,在经济、文化等方面也空前频繁与深化。明廷沿袭元制,继续加强对西藏的治理,实行 “多封众建,尚用僧徒”的治藏政策,分封藏传佛教各教派和各地大小头目;订立朝贡制度,加强西藏等地与中央政府的联系;还在汉藏交界地区设立茶马互市,以促进西藏和祖国内地之间的物资流通。①吴明娣:《汉藏工艺美术交流史》,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第85页。这些政策、措施令汉藏工艺美术交流在元代已有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加强,以丝绸、瓷器、玉器为代表的工艺美术品在汉藏交往交流交融中发挥了重要纽带作用。在明廷输入西藏的各类工艺美术品中,玉器所占份额少,但地位甚高。一方面,始终被中国人奉若至宝的于阗美玉不易获取,玉料珍稀;另一方面,官方礼制规定玉器是等级最高的工艺美术品;外加上古以来,玉被赋予的种种礼法、道德含义,使玉器具有集经济、权力符号、艺术价值于一体的特性。据《西藏博物馆藏元明清玉器精品》和《布达拉宫珍宝馆图录》公布的材料,西藏博物馆、布达拉宫 (以下简称 “两馆”)两处收藏有明代内地玉器 (不含玛瑙、水晶质品)共40件,其中35件在西藏博物馆①西藏博物馆:《西藏博物馆藏元明清玉器精品》,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34—60、69—76、78—81页。,5件在布达拉宫②布达拉宫管理处:《布达拉宫珍宝馆图录》,中国藏学出版社,2013年,第99、103—107页。。苏发祥教授在《论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基础》一文中说:“共同的历史根源和历史记忆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前提和条件。”③苏发祥、马妍:《论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基础》,《中国藏学》2021年第1期,第36页。目前学界对西藏所藏明代玉器已有关注④何晓东:《西藏博物馆的馆藏玉器》,《中国西藏》2007年第1期,第72—74页;石晓:《雪域高原的璀璨明珠——西藏博物馆藏玉鉴赏 (二)明代玉器》,《收藏界》2009年第2期,第97—98页。,但未对其进行细致分类,关于它们的时代、造型、装饰、工艺等问题仍待深入探讨。本文主要根据 “两馆”已公布的所藏明代内地玉器实物材料,结合可信的文献史料,分门别类地对这批文物作进一步分析,并尝试探寻其中蕴含的包括汉藏民族在内的中华各民族共同的历史根源和历史记忆。
一、玉 印
各类玉器中,玉印地位最尊。按明制,唯皇帝印为玉质,并专称 “玉玺”“御玺”或 “宝玺”,皇后、皇太子、亲王印为金质⑤[明]李东阳等撰,申时行等重修:《大明会典》卷60,冠服一,扬州:广陵书社,2007年,第1035—1043页。,郡王用镀金银质⑥[清]张廷玉等:《明史》卷116,诸王传四,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351页。。玉印非一般日用器皿,帝王之玺是无上皇权的象征,臣子所用玉印只能由皇帝颁发。西藏博物馆藏两方玉印,一为白玉 “如来大宝法王之印”(图1)⑦西藏博物馆:《西藏博物馆藏元明清玉器精品》,第34—35页。,一为青玉 “正觉大乘法王之印”(图2)⑧同上,第36—37页。,都是明成祖朱棣颁给西藏宗教首脑的。

图1 白玉 “如来大宝法王之印”

图2 青玉 “正觉大乘法王之印”
如来大宝法王是朱棣授予藏传佛教噶玛噶举黑帽系第五世活佛哈立麻的称号。永乐四年 (1406)十二月哈立麻应召赴南京,⑨《明太宗实录》卷62,永乐四年十二月戊子,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社,1962年,第890页。留驻期间为已故明太祖朱元璋及其皇后 “荐福”[10]《明太宗实录》卷64,永乐五年二月庚寅,第910页。,永乐五年 (1407)三月获赐封号 “万行具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慧善普应佑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简称如来大宝法王,并得赐印章①《明太宗实录》卷65,永乐五年三月丁巳,第915页。,应是这方白玉 “如来大宝法王之印”。
《明英宗实录》载,哈立麻刚到南京时,永乐帝欲赐其玉印,并将玉料示予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读黄淮 (1367—1449)看,黄淮看后认为此玉料大于其他诸蕃所得,并不合适,终未用其制印。②《明英宗实录》卷179,正统十四年六月辛亥,第3455页。如今所见白玉 “如来大宝法王之印”,应由后来挑选的相对小些的玉料制成,长宽皆13厘米、高9厘米,羊脂玉料颇为纯净。当年如此尺寸、质量的玉料并不易得。
正觉大乘法王是朱棣颁赐给藏传佛教萨迦派高僧昆泽思巴的称号。昆泽思巴于永乐十一年(1413)二月应召到南京,③《明太宗实录》卷137,永乐十一年二月戊午,第1664—1665页。五月被封为 “万行圆融妙法最胜真如智慧弘慈广济护国宣教正觉大乘法王西天上善金刚普应大光明佛”,简称正觉大乘法王,获赐诰、印等物,④《明太宗实录》卷140,永乐十一年五月辛巳,第1680页。所得之印应是此青玉 “正觉大乘法王之印”。这方印长宽尺寸与白玉 “如来大宝法王之印”一致,略微高些,有10.5厘米,用料更多,且甚为莹润。
成书于洪武二十一年 (1388)的《格古要论》是明初最重要的鉴赏类笔记,作者曹昭在书中列8种颜色玉,并称白玉 “其色如酥者最贵”,黄玉、碧玉、墨玉、赤玉、绿玉、甘青玉、菜玉皆不及它。⑤[明]曹昭:《格古要论》,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00—105页。正觉大乘法王地位不比如来大宝法王,因此 “礼之亚于大宝法王”⑥[清]张廷玉等:《明史》卷331,西域传三,第5748页。,所以在颁赐玉印时对其颜色作了一白一青的处理。二者之间的等级差异,从玉料的选择上便可体现。
这两方玉印皆为汉文,朱文九叠体,有黄色印绶,与同馆所藏元代 “统领释教大元国师”青玉印 (图3)⑦西藏博物馆:《西藏博物馆藏元明清玉器精品》,第27页。和白色 “国师玉印”⑧同上,第28—29页。形制相同,均为扁方形,双龙纽。纽的造型与元印一致,二龙背向蹲伏,身体相互交缠,但气韵全然不同。元代玉工喜欢深雕重刻,下铊时毫不拘谨,雕琢的线条粗而深凹,⑨李海:《出土元代玉器及工艺特征综述》,《东方博物》2008年第3期,第18—27页。如上述两方元印龙纽的口鼻、鬃毛、龙鳞处线条被琢制得很深。明代玉印龙纽上的线条细劲柔和,除口鼻处琢制得略深一点,其余每一处线条都圆转流畅、匀净自如。明嘉万时人高濂在《遵生八笺》中赞叹汉代玉工的 “双钩碾法”,称 “宛转流动,细入秋毫,更无疏密不匀,交接断续,俨若游丝白描,曾无滞迹”[10][明]高濂著,[清]钟惺校阅:《遵生八笺》卷15,《燕闲清赏笺 (上卷)·论文房器具》,嘉庆十五年弦雪居重订本,第91页。,将此番记载与两方明代玉印对照,不难发现明初玉匠对汉代玉作的继承。

图3 元代 “统领释教大元国师”青玉印
明代帝王赏赐藏传佛教领袖的玉印不只上述两件,见诸文献记录的还有不少,可惜年代湮远,多已遗矢。如洪武五年 (1372)四月,朱元璋遣使特赐故元灌顶国师章阳沙加玉印。①《明太祖实录》卷73,洪武五年四月丁酉,第1342页;[清]张廷玉等:《明史》卷331,西域传三·阐化王,第5750—5751页。元末明初帕木竹巴地方政权取代萨迦地方政权,成为西藏最大的地方势力,章阳沙加即西藏帕木竹巴地方政权的第二任第悉。洪武六年 (1373)二月,又赐元末摄帝师喃加巴藏卜 “炽盛佛宝国师”称号和兽纽玉印,玉工将印制成后呈给朱元璋验看,朱元璋觉得玉料不美,又命玉工重选玉料而制。②《明太祖实录》卷79,洪武六年二月癸酉,第1437—1439页;[清]张廷玉等:《明史》卷219,西域传三·乌斯藏大宝法王,第5745页。明初宫廷玉料储备并不充裕,朱元璋对玉料的选择如此精心,可见对西藏宗教上层的重视。随后一年的七月,朱元璋又颁赐萨迦派两位高僧,一为答力麻八剌 “灌顶国师”称号和海兽纽玉印,二为元代帝师八思巴后裔公哥坚藏 “圆智妙觉弘教大国师”称号和狮纽玉印。③《明太祖实录》卷91,洪武七年七月己卯,第1595页;[清]张廷玉等:《明史》卷219,西域传三·乌斯藏大宝法王,第5745页。洪武一朝,皇帝赐予西藏宗教上层的玉印形制多样,仅前述记载就含兽纽、海兽纽、狮纽3种,不过,它们都不及龙纽玉印等级高,亦与获赐者的地位有关。
二、玉器皿
在 “两馆”所藏明代内地玉器中,器皿数量最多,已知31件,占比77.5%,品类涉及杯具 (含杯与杯托)、壶、碗、瓶、盒、笔洗等,与玉器皿在明代玉器总量中占据份额较少的情况正相反。玉器皿与玉印、玉佩、玉带等玉器相比,往往器型更大,用料更多,制作也更繁难。依典章制度,明代一二品职官器皿不许用玉,④[明]李东阳等撰,申时行等重修:《大明会典》卷62,冠服二·房屋器用等第,第1075页。下不可僭上,庶民器皿更不得以玉制,可见玉器皿之珍贵。今 “两馆”藏如此多的明代珍稀玉器皿,应也得自皇家赏赐。明代统治者对藏传佛教高僧不惜工本的赏赐,反映出对治理西藏地区的重视程度。
“两馆”藏明代玉器皿中,杯具最多,有19件;壶的数量次之,有5件;碗和笔洗各2件。在明代极少的玉器皿出土物中,杯、壶、碗俱全,这三类玉器皿尤其是前二者,比其他玉器皿在明代贵族生活中更为流行,正与 “两馆”藏同类器物较多的状况吻合。如玉笔洗一类的文具终明一代都很罕见,故 “两馆”珍藏的2件十分可贵,且工艺精湛,颇具艺术价值。因此,本文对玉器皿的讨论,主要聚焦于杯具、壶、碗、笔洗4类。
(一)杯具
明人最看重杯具,“杯为席上珍”⑤《一笠庵新编一捧雪传奇》上卷第6回,婪贿,明崇祯刊本。,这与中国源远流长的茶酒文化有关。明墓出土玉器皿虽少,但杯具是其中最多者,且在明代早、中、晚期墓中都有出土。西藏博物馆所藏19件玉杯具中,有杯14件、杯托5件 (有2件为1对)。其中西藏博物馆藏青白玉桃形杯 (图4)①西藏博物馆:《西藏博物馆藏元明清玉器精品》,第59页。为明代常见的一种单耳杯,长11.7厘米、高5.3厘米,杯呈半桃形,桃嘴作流,杯耳及杯托镂雕成枝叶,叶脉由阴线刻成,造型典雅,工艺讲究。《明太祖实录》载,洪武二十三年 (1390),监察御史揭发李善长罪状,罪证就有胡惟庸 “以玉酒壶、玉刻龙盏、蟠桃玉杯奉善长”②《明太祖实录》卷202,洪武二十三年五月庚子,第3024页。,其中的 “蟠桃玉杯”应就是如此模样。明墓出土过类似的仿生型玉杯,1970—1971年在发掘山东邹城鲁荒王朱檀墓过程中出土了白玉花形杯,是明早期少见的玉器皿,器为五瓣花状,杯耳同杯托雕成藤状枝叶,构成一枝盛开的花朵,内底阴线刻五瓣花形花蕊,叶脉也由阴线刻成,其与此青白玉桃形杯做工肖似、装饰手法雷同,制作年代或为相近。

图4 青白玉桃形杯
玉桃杯在元代就已出现,在江苏无锡钱裕墓出土的元延祐八年 (1321)1件青玉桃形杯,装饰题材与工艺和西藏博物馆藏青白玉桃形杯相近,不过,后者较之元作更具装饰性。玉桃杯虽非明人首创,却在明代大肆流行。《天水冰山录》记载嘉靖末年朝廷抄没严嵩父子的家财,玉桃杯多至56个,包括 “玉寿字桃杯二个”“玉大桃杯三个”“玉中桃杯一十二个”“玉小桃杯二十三个”“玉鹦鹉桃杯一个”“玉桃杯七个”“玉金镶边鹦鹉桃杯二个”“墨玉桃杯二个”“菜玉桃杯四个”,③佚名:《天水冰山录》,知不足斋丛书本。可知,玉桃杯有大、中、小之分,各种尺寸的规格应较固定。今所见明代玉桃杯都只表现桃这一个题材,还未见 “玉寿字桃杯”“玉鹦鹉桃杯”。西藏博物馆藏1件桃形螭耳玛瑙杯,杯为半桃状,一螭虎攀伏于杯沿作耳,外壁有枝叶作托,样式别致,在明代,此杯或可称作玉螭虎桃杯。
中国人自古喜以桃祝寿,玉桃杯的吉祥寓意不言自明。《金瓶梅》中,西门庆第一次为蔡太师准备寿礼就含 “两副玉桃杯”④[明]兰陵笑笑生著,[清]张竹坡批评:《金瓶梅》第27回,“李瓶儿私语翡翠轩 潘金莲醉闹葡萄架”,第5页。。蔡太师所见 “黄烘烘金壶玉盏”⑤[明]兰陵笑笑生著,[清]张竹坡批评:《金瓶梅》第30回,“蔡太师擅恩锡爵 西门庆生子加官”,第7—8页。,甚是华美。现实生活中,有胡惟庸送李善长 “蟠桃玉杯”、严嵩父子庋藏各式玉桃杯;文学作品里,主人公也常以之作寿礼,玉桃杯的贵重自不待言。
西藏博物馆还藏两种双耳杯,分别是花卉耳和螭虎耳,都是明代玉杯中的典型。双花耳玉杯在万历、天启两朝墓中均有出土,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定陵博物馆、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定陵》(上),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188—189页;南京市博物馆:《江苏南京市明黔国公沐昌祚、沐睿墓》,《考古》1999年第10期,第45—56页。据此判断,其流行时间应在晚明。西藏博物馆藏多件以双花作耳的玉杯,器型都较小巧,杯身有的为圆形,有的是多边棱形。圆杯身者如花卉纹双花耳青白玉杯(图5)①西藏博物馆:《西藏博物馆藏元明清玉器精品》,第57页。、万寿纹双花耳青白玉杯②同上,第25页。,棱形杯身者如花卉纹双花耳青白玉六棱杯③同上,第23页。。
花卉纹双花耳青白玉杯和万寿纹双花耳青白玉杯,造型、尺寸相类,皆侈口、深腹、圈足,两侧附双花耳,花卉纹双花耳青白玉环高3.3厘米、口径6.5厘米,杯口内沿一周饰回纹,外沿和圈足上部各阴刻一道弦纹,中间浅浮雕玉兰花和山纹,似花儿开在悬崖峭壁间,生机盎然。万寿纹双花耳青白玉杯高3.5厘米、口径7.4厘米,外沿和圈足上部也各阴刻一道弦纹,腹部两面各琢一寿二 “卍”字纹,寿字纹下托灵芝。“卍”寿纹是晚明玉器皿的常见装饰,北京定陵出土万历四十八年 (1620)的金托白玉执壶上的纹样即为此式。从题材及图案设计风格来看,万寿纹双花耳青白玉杯也是晚明作品。西藏博物馆藏这2件双花耳青白玉杯在造型上有相同的特点,即杯身两侧的花朵都状似玉兰,却又与现实中的玉兰形象有别,当是玉工从自然中获取素材后再加创作的结果。这种倒圆锥体花卉双耳,既与中间稍大、略显敦厚的杯身形成对比,增添灵动之气,又便于人持握,可见设计者的巧思。

图5 花卉纹双花耳青白玉杯
西藏博物馆另藏花卉纹双花耳青白玉六棱杯,除杯身取六棱形外,其他细节与圆杯身的双花耳杯区别不大。在明墓出土的实物中,尚未发现多边棱形杯身的玉质双耳杯,但江苏南京太平门外板仓村明墓出土1件用于承托八棱形杯的白玉双螭虎纹杯托④南京市博物馆:《江苏南京市板仓村明墓的发掘》,《考古》1999年第10期,第39—44页。。明人用杯,常加盘托,一杯一盘之组合在当时被称作 “盘盏”或 “台盏”⑤扬之水:《奢华之色——宋元明金银器研究》卷3,中华书局,2016年,第136页。。西藏博物馆也藏有玉杯托,只是比明墓出土同类器皿的装饰更加繁缛。以双龙捧寿纹青白玉杯托 (图6)⑥西藏博物馆:《西藏博物馆藏元明清玉器精品》,第69页。为例,器取委角长方形,中心有一圆形突棱,可纳杯足;突棱之外,托盘沿内减地浮雕双龙捧寿纹,盘边沿阴线琢卷草纹。该馆藏另外4件玉杯托或圆形、椭圆形,或八角形,造型虽不尽同,但采用具有祈福求寿寓意的花纹和减地浮雕的工艺手法,都具明代玉作风格。

图6 双龙捧寿纹青白玉杯托
双螭虎耳杯是明代玉杯之又一典型。1957年在北京市宣武区右安门外明代锦衣卫指挥使万贵(1392—1475)墓出土的白玉双螭虎耳杯,杯身圆形,深腹圈足,通体光素,杯身两侧镂雕双螭虎作耳,螭首略扁,额上琢 “王”字;双爪伏于杯口,似窥视杯中美酒;尾分岔贴于杯壁,神态生动自然。此杯出土时置于万贵胸前,墓主生前对它的喜爱可想而知。⑦郭存仁:《万贵墓清理简报》,《北京文物与考古》第三辑,北京:北京市文物研究所,1992年,第238页;古方:《中国玉器出土全集》1(北京 天津 河北),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62页。同式玉双螭耳杯也出土于沐睿(?—1609)墓①墓址在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将军山,1974年发掘。。已发掘的明早期墓中未见同款玉杯,但从成化十一年 (1475)至天启七年(1627)逾150年,玉双螭虎耳杯一直流行,显示出明代中晚期人们对它的喜爱。西藏博物馆藏同款玉杯3件,1件为白玉质 (图7)②西藏博物馆:《西藏博物馆藏元明清玉器精品》,第54页。、2件为青玉质,它们的制作年代也应在明代中晚期。此外,西藏博物馆藏1件青白玉双螭虎耳八棱杯,杯身和足均呈八棱状,两侧附双螭虎耳,与相关文献《天水冰山录》③佚名:《天水冰山录》,知不足斋丛书本。中记载的玉螭虎耳八角杯正合。此馆还藏1件碧玉莲口单螭虎耳杯,应就是《天水冰山录》所说之 “玉螭虎花杯”。

图7 白玉双螭虎耳杯
明代玉杯常仿高古之作,所仿器物以三代青铜器和汉代玉器为多。爵是先秦礼器中的酒器,在祭礼中被用于敬神,在宴饮中用于宴客。敬神与宴客,这两种用途后世一直被沿用下来,直到明清。④扬之水:《奢华之色——宋元明金银器研究》卷3,142页。玉杯具中,玉爵颇为尊贵,明代从景泰朝起,玉爵就作为祭器在明代的国家祭祀典礼中使用。⑤《明英宗实录》卷274,天顺元年正月庚寅,第5818页。目前出土明代玉爵仅知1件,得自万历帝之定陵。布达拉宫藏青白玉爵 (图8)⑥布达拉宫管理处:《布达拉宫珍宝馆图录》,第99页。之高贵程度由此可以想见。此件青白玉爵样式别致,两柱较短呈菇状,三足外撇作竹节式,两耳极小,口沿处刻回纹,身琢云凤八卦纹、松鹤纹等祥瑞图案,其与定陵出土的金托玉爵艺术风貌差别很大,前者更加简素,制作年代应当较早。
西藏博物馆藏龙凤纹青玉白卮①西藏博物馆:《西藏博物馆藏元明清玉器精品》,第40页。是1件仿汉玉的明代作品,此卮亦为盛酒器,为圆柱形直口器,环形柄,三人形足,造型与广州南越王赵眛墓出土西汉前期金铜镶玉卮基本一致,只是后者非纯玉质,而是由金铜框架嵌9块玉片组成杯身,环形柄和三足都取简单的几何造型,花纹略有不同。北京清黑舍里氏墓出土的白玉卮和西藏博物馆的龙凤纹青玉白卮也很相似,也是仿汉玉之作。此器和西汉前期的金铜镶玉卮都有玉盖,西藏博物馆藏龙凤纹青玉白卮原本也应有。
(二) 壶
洪武年间,胡惟庸献李善长的玉器不仅有杯盏,还有 “玉酒壶”,后者也是珍稀之物。出土明代玉壶极少,目前仅知2件。西藏收藏的5件玉壶十分精美,通过与出土物比对,可推断它们的年代。
西藏博物馆藏灵芝纹青玉执壶,高23.1厘米,器型大,体扁圆,长颈宽腹,直流圈足,颈与流间以三角状灵芝相连,耳形把,覆盆形盖,盖顶有水滴形纽,纽与把以连环长链相连,壶口一圈琢回形纹,周身饰灵芝纹,其造型与定陵出土的金托白玉执壶近似,只是后者为帝王所用,规格最高、工艺更精。定陵所出执壶周身无繁密花纹,但仿金银执壶做法,壶腹两侧浅刻杏叶,杏叶内雕花叶托 “卍”寿字纹。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入跸图》中,绘有明代皇帝出行时的排场,画中一条随驾小舟舱内置一食案,上面陈设各色器皿,其中有一类似的白玉执壶②台北故宫博物院:《故宫图像选萃》,台北:台北故宫博物院,1973年,第46页。。西藏博物馆还藏1件龙纹青白玉方执壶,除壶身为四方体外,壶腹所琢龙托 “卍”寿字纹、壶盖与把手相连的锁链,以及滞涩的刀工风格,都与定陵出土玉壶相类,它们的创作年代应较接近。布达拉宫也藏1件碧玉万寿纹龙纽盖执壶 (图9)③布达拉宫管理处:《布达拉宫珍宝馆图录》,第104页。,造型比前述玉壶都复杂,壶身、壶盖饰仰覆莲瓣纹,腹部琢莲花瓣,瓣上有各式花卉和 “万寿无疆”纹,高足亦取莲瓣式。此壶装饰虽繁缛,但一些细节仍流露出明式玉器的特点,如扁腹、盖与把之间的锁链,以及晚明玉器上常见的万寿纹。

图9 碧玉万寿纹龙纽盖执壶
(三) 碗
玉碗,不像玉杯、玉壶之类的酒具,因常得风雅之士的垂青而被频频描述、记录。明末清初文人李渔在《闲情偶寄》中引唐人诗句:“玉碗盛来琥珀光”,称 “玉能显色,犀能助香,二物之于酒,皆功臣也。”④[清]李渔著,沈勇译注:《闲情偶寄》,器玩部·制度·酒具,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第308页。其所赞美的玉碗,仍作酒具之用,而非盛汤食之碗。出土明代玉碗不多,目前仅见于定陵和沐睿墓。西藏博物馆藏山水人物纹青白玉碗和四仙寿字纹碧玉碗2件。这2件玉碗传世品都值得称道,皆敞口、弧腹、圈足,与定陵出土玉碗相似,只是后者配有金托金盖、器璧更薄透,更具皇家威仪;这二碗内壁光素,前者外壁阴线琢山水人物图,玉工以碗为画卷,取元末明初画家倪瓒创制的 “一河两岸式”构图,表现近坡、中水、远丘的三段风景,碗色淡雅朦胧,图案意境萧疏,颇有水墨画之韵味,设计者当具文人情思。后者风格与之全然不同,碗外壁深阴线刻四仙纹,每个仙人之间刻灵芝托寿字纹,寓意四仙拱寿,构图满密,有晚明玉作之风。
(四)笔洗
藏族虽无用毛笔书画的传统,但西藏博物馆却藏2件明代玉笔洗,它们未必被作文具使用,却可代表持有者尊贵的身份。高濂《遵生八笺》专门记录笔洗,曰:“玉有钵盂洗、长方洗、玉环洗,或素或花,工巧拟古……近人多以洗为杯,孰知厚卷口而匾 (扁)浅者,洗也,岂杯有此制?”①[明]高濂著,[清]钟惺校阅:《遵生八笺》卷15,《燕闲清赏笺 (上卷)·论文房器具》,嘉庆十五年弦雪居重订本,第45—46页。西藏博物馆藏2件玉笔洗都属花器,1件为白玉桃形洗,器身呈半桃形,周身缠绕参差扶疏的枝叶,枝叶间有4朵盛开的桃花与一只展翅飞翔的鸟儿,艺术风格清新自然;另1件是青玉螭纹洗(图10)②西藏博物馆:《西藏博物馆藏元明清玉器精品》,第78页。,形似单耳杯,洗壁四周以镂雕、浮雕相结合的手法装饰群螭纹,螭造型各异,或昂首挺立,或屈身低俯,或攀缘匍匐,或伸头窥探,玉工运用俏色工艺,将玉料中色沉近黑者制成荔枝纹足托,构思十分精巧。初看二器,极易将它们误认为玉杯,如白玉桃形洗与同馆所藏青白玉桃杯十分相近,不过,按高濂说法,笔洗口又厚又卷、器型偏扁,玉桃笔洗和玉桃杯的区别则一目了然。

图10 青玉螭纹洗
三、其 他
除玉印和玉器皿外,西藏博物馆还珍藏2块玉带板,它们是革带上的装饰。古人用金银犀玉等质料装饰革带的初衷应为美观,但在等级制度森严的封建社会,只要统治者有意愿,万事万物都可成为别尊卑、辨上下的工具。以佩玉带区分品官等级一事始自唐,那时,只有三品以上的达官才有佩玉带的荣耀③尚刚:《隋唐五代工艺美术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13页。。一直到明代,玉带始终是显赫者的装束。洪武二十四年 (1391),朱元璋规定,公、侯、驸马、伯、文武一品官员佩玉带,二品用犀带,三四品用金带,五品用银钑花带,六品、七品用银带,八品、九品用乌角带。④《明太祖实录》卷209,洪武二十四年六月己未,第3110—3119页。永乐三年 (1405),朱棣又制定玉带使用制度,皇亲国戚中,郡王长子、镇国将军及以上的男性,和郡主、郡王妃、镇国将军夫人及以上的女性可佩玉带,辅国将军用犀带,奉国将军和镇国中尉用素金带。①[明]李东阳等撰,申时行等重修:《大明会典》卷62,冠服一,第1050—1051页。除上述达官显贵外,有资格系玉带者,非皇帝特赐不可。②[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11,二品赐玉带,中华书局,1985年,第206—207页。《明武宗实录》载,弘治帝朱祐樘宾天,“真人陈应循、西番灌顶大国师那卜坚参及班丹罗竹等”因不守宫规、滥设斋醮等事被撤销封号,被没收得赐玉带。③《明武宗实录》卷1,弘治十八年五月壬子,第33—34页。可知弘治帝在位时,赏赐藏传佛教僧人不少玉带。
明末清初人张自烈和方以智都曾记录明代最流行的革带样式,张自烈《正字通》云:“明制革带,前合口处曰三台,左右排三圆桃。排方左右曰鱼尾,有辅弼两小方,后七枚,前大小十三枚。”④[明]张自烈、[清]廖文英编,董琨整理:《正字通》卷11,《戌集上·銙》,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6年,第1198页。方以智《通雅》记录内容基本与之相同。⑤[明]方以智:《通雅》卷37,衣服 (佩饰),北京:中国书店,1990年,第445页。从二人记载来看,标准的明式革带应由20块带板组成,前有三台,左右六圆桃、二鱼尾、二辅弼,后有七排方。从形制上判断,西藏博物馆所藏玉带板分属两条玉带之构件,长方形的是鱼尾 (图11)⑥西藏博物馆:《西藏博物馆藏元明清玉器精品》,第39页。,近方形者是后七排方中的一块 (图12)⑦同上,第38页。,它们都是青白玉质的龙纹带板,但花纹装饰工艺不同,前者采用双层镂雕工艺,后者作浅地浮雕,都是明代最流行的玉带装饰手法。晚明宦官刘若愚《酌中志》记录太监所服玉带,曰:“冬则光素,夏则玲珑,三月九月则顶妆玉带。”⑧[明]刘若愚:《酌中志》卷19,内臣佩服纪略,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66页。“光素”即素面无纹,“玲珑”指镂雕。瓷器上的顶妆是一种绘塑结合的装饰手法⑨张北霞:《万历官府瓷器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学位论文,2020年,第161页。,“顶妆玉带”应是用减地浮雕装饰的玉带。按刘若愚之说,西藏博物馆所藏2件玉带板分别运用了 “玲珑”和 “顶妆”工艺,宜于夏日、春秋佩戴。

图11 青白玉龙纹带板

图12 青白玉龙纹带板
结 语
纵观 “两馆”藏明代内地玉器,除玉印为永乐一朝之物外,西藏博物馆藏青白玉桃形杯可能是明初作品,其余器皿大多制作于晚明,并以嘉万时期作品为主,带饰的制作时间上限应在明中期。这40件作品中,仅有3件白玉质品,即西藏博物馆藏白玉 “如来大宝法王之印”、白玉桃形洗和白玉双螭虎耳杯,唯前者质料是羊脂玉,后二者质地不甚清透。剩余37件作品为青白玉、青玉和碧玉器,玉料不如白玉尊贵,但并非明廷吝啬,而是明朝玉料整体质量确实不佳。综合来看,这批玉器的工艺水平不逊色于明代帝王、藩王墓出土玉器,它们中的大部分应出自宫廷内府制作,尤以2件玉印工艺最佳。
与元朝相比,明廷输入西藏的玉器品种更丰富,清代在此基础上有所拓展,多出金刚杵、念珠等法器,扁方、扳指等首饰,各式动物、人物造型的陈设品,乃至刀具等,显然,明代在其间起到了承上启下作用。相较于丝绸、陶瓷两个大宗工艺美术门类,明代流入西藏的玉器在数量上并无优势,但玉质品等级最高,无论是作为权力信物的玉印,还是专供宗亲勋贵使用的玉器皿、玉带具,在被当作重礼颁赐给西藏宗教首脑时,都更能凸显明中央政府对藏传佛教的尊崇与优待。
西藏今存历代玉器基本都得自内地。西藏不产玉料,因而难以诞生较为成熟的玉作,玉器艺术对藏族文化的影响,也难体现在造型、纹饰等具象审美元素上,却可融于抽象的文化观念中。在西藏流传已久的民间故事《黑面王子》里,西方那哇波登王国有3个尊贵的公主,分别名为金叶公主、玉叶公主和螺叶公主,①廖东凡:《西藏民间故事》,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89页。金、玉、海螺都极其稀罕,藏族同胞对玉的爱重据此可以想见。明代内地治玉工艺和藏族文化间的影响从不是单向的,在明廷与西藏宗教上层的频繁往来中,藏传佛教艺术不仅流传于内地,亦对内地玉作产生明显影响。②湖北省博物馆藏一块白玉带板,是明代玉带中的鱼尾,玉工用双层镂雕工艺,以卷草纹作底,上层镂雕龙纹和藏传佛教典型的八吉祥纹;天津博物馆藏僧帽形玉执壶,与明代常见的瓷质僧帽形造型相类,尺寸很小,高仅11.8厘米,实用价值不高,但文化意义重大。两件器物分别见于古方:《中国传世玉器全集》4(明),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2页;古方:《中国传世玉器全集》5“明清”,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7页。今西藏所藏明代内地玉器已非当年的全部,这些 “历史实物碎片”作为宝贵的物质文化遗产,在汉藏往来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不容小觑。它们的珍贵之处不止在于所传递的审美范式、文化面貌,这些清隽典雅的器物更是汉藏民族政治、经济、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见证,参与推动了中华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些明代玉器是西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基础或其中的重要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