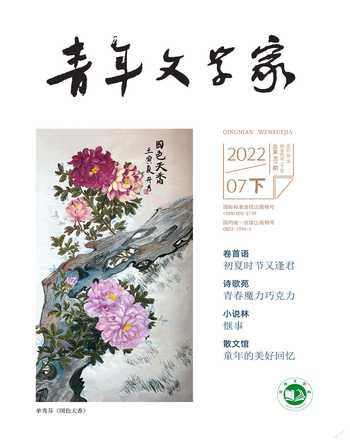生命史诗巨作《活着》品鉴
朱家胜


余华的《活着》,每捧读一次,都让我潸然泪下,悲从中来,不能断绝。但往往也有悲痛之后的淡然与洒脱。这部伟大的作品,让我感悟生命,理解自身的存在。我试着从几个方面对这部伟大的作品作以注解,仅是一家之言,发表自己的浅浅看法。我之所以将这部满篇都是关于悲剧、关于死亡的作品称之为“生命史诗”,是因为那些生命的脆弱与消逝,正是为了衬托活着的不易,衬托生命的顽强,这当然是值得我们歌颂的。
一、故事重温
《活着》讲述的是一位中国农村老人和命运作斗争的故事。这个老人就是作家余华笔下的徐福贵。福贵的父亲因福贵赌博输光了家里的房产地契,感到无奈无助,上厕所时摔了一跤便死了;福贵的母亲因为身体患病没有及时医治也撒手人寰;福贵的儿子因为献血过多而死亡;福贵的女儿因为生孩子失血过多也离开了他;然后是福贵的妻子,因患软骨病以及长期的精神折磨也在他女儿离世不久后就死了;福贵的女婿二喜因为在工作过程中被几块石板挤压也离开了这个世界;而福贵最后的牵挂,他的外孙也在生病后,因过多地吃他煮的豆子而撑死了。福贵的亲人相继离去,直到他唯一的外孙也走了,他买了一头垂危的老牛,从此他与老牛相依为命,并给老牛也起名叫“福贵”。村里人都觉得两个“福贵”垂垂老矣,命不久矣,福贵自己也这么觉得,感觉自己活不了多久了。曾经多少次,福贵“早该”死了的,比如因为赌博将家产败光,他想过去上吊结束自己的生命。类似的情节我们在小说后面也多次见到。但福贵依旧活着,哪怕最后只有他一个人,只有一头年迈的老牛同他作伴,经历了生活的风霜洗礼,他老而弥坚,仿佛曾经的苦难从未光顾他的生活。又或者说经历了这世间重重悲剧的洗礼,他看透了这生命的本质。他的活着是一个结局,也同样是一个新的开始。正如余华说的那样:“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的,而不是为活着以外的任何事情而活的。”
二、福贵的人物形象分析
在《活着》整部小说的叙述中,福贵的口气大都是平平淡淡,似乎是在讲述自己從别处听来的故事一般,而他则是一个毫无关系的旁观者,这中间发生的一切都与他无关,但发生的一切都是那样真真切切。甚至,小说情节中福贵在讲述自己往事的时候,还提及了一些比较有趣的场面,让人忍俊不禁。比如,福贵在干下流事的时候,在经过他老丈人米店的时候,他还要专门停下来给老丈人打招呼,向他老人家问好,真气死了老丈人。我想这大概是作者想把零度介入这种写作手法发挥到极致。福贵的讲述很直白,他就是要塑造出这种仿佛发生的事情跟自己毫无关系的这种印象,反而是越平淡的讲述越能体会当事人在经历这些时的荒唐。荒唐归荒唐,但它确实那么实实在在地发生了。生活其实就是这样,很多时候并不是我们所期待的那样,无风无雨,一帆风顺,总会有各种涟漪泛起,甚至惊涛骇浪。
小说的作者余华说福贵有各种比死去的人更多去死的“机缘”,各种理由,而他却经历一次次的生离死别,送走了一个又一个亲人、朋友,将他们埋葬后,又开始了自己的苦难生活。以至于到最后他自己也看开了,在自己外孙离开后的第二年,他履行了和外孙的约定,他买了一头牛。机缘巧合,他正好碰到了一头待宰的老牛,因为可怜老牛,同情它,想到了自己的遭遇,他买下了老牛,并给老牛取了个和自己一样的名字。历经生活的风霜摧残,他依旧勇敢,依旧热爱生活,往日的痛苦已经过去,现在的生活还得继续。往前看,活着一天,就做一天的事。正是“生活虐我千万遍,我待生活如初恋”。
三、作品中的语言运用
作者在作品中有很多描写福贵的文字,但没有给人很沉重之感,这和作者的用词有很大关系。
“噢”—老人高兴地笑起来,他很神秘的向我招招手,当我凑过去时,他欲言又止,他看到牛正抬着头,就训斥他:“你别偷听,把头低下。”牛果然低下了头,这时老人悄声对我说:“我怕它知道只有自己耕田,就多叫出几个名字去骗它,它听到还有别的牛也在耕田,就不会不高兴,耕田也就起劲啦。”
作为旁观者,我们兴许认为福贵多是一种自我安慰的阿Q精神,在那样孤独无助,艰难苦涩的环境中,福贵一样活得有滋有味,生趣盎然。而实际上,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也不乏各种各样的“福贵”,他们虽然处在非常艰难的环境中,但是依然保持着乐观向上的心态,保持着昂扬的斗志。这一点,在美国作家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中也有异曲同工、淋漓尽致的展示。而我又想起了非常敬佩的王阳明,当年他因参与谏言,被发配至贵州龙场当驿丞。按说,像他这样出身显赫的才子,过惯了受人伺候的日子,怎能耐得住当年那偏远龙场的孤独寂寞与苦寒。但他不但让自己去适应非常糟糕的境况,还时常宽慰仆从的心,疏导他们的心理。日复一日的坚持,坚持不懈的求索,这也才有了为人所称道的“龙场悟道”,也才有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又一开端—“心学”的创立。正是因为他熬过了这艰难困苦的日子,才让自己实现了“立功、立德、立言”,“真三不朽”为世人称颂,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
在后来福贵的讲述中,我们也不难看出这种历经风雨、处变不惊的心态。在那个年代,教育的普及程度非常低,由于自身的文化水平有限,福贵在讲述自己往事的过程中,并不会使用特别复杂的词汇。当然,用那些比较生活化的词去形容自己的心情,这也更接地气,更贴近人物的生活实际。福贵遇到开心的事情就开心地笑,丝毫不掩饰自己内心的愉悦。比如,福贵和家珍因为女儿凤霞的婚事发愁,凤霞人很聪明,但是因为小时候一次偶然的高烧烧出了更严重的问题,成了聋哑人。当村长介绍人来家里相亲的时候,福贵和家珍就非常担心,怕来相亲的人看不上凤霞。相亲的二喜来了之后,话很少,只是不断打量他们的住所,这次相亲见面会草草收场,至少在福贵看来是这样的。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没过几天,二喜又带着几个人回来了。原来,他看福贵家的居住条件比较差,所以,帮他们把破旧的茅屋翻新一下,又给福贵家用白灰抹了墙。福贵和家珍都看在眼里。他们坐在一起吃饭时,二喜问他什么时候能娶凤霞过门,这着实给福贵开心坏了。他们本来还特别担心二喜看不上凤霞,但是没想到二喜特别中意凤霞,他们俩在一起干活儿的时候,福贵和家珍就觉得他们真是非常般配的一对。而当二喜和凤霞结婚不久,回来串门的时候,二喜想要去背卧床的家珍,福贵拒绝了,他说他自己的媳妇自己背,以后二喜要背的话就背凤霞吧,话毕一家人相视而笑。
而当福贵遇到难过的事的时候,余华是这样形容福贵的。“说完我就呜呜地哭了起来”“我的心像被刀割了一样”“这么一想我就忍不住哭了起来”“我娘在一旁哭得呜呜响”“随即心里一酸”“凤霞的眼泪在脸上哗哗地流,她哭得身体一抖一抖”“那天晚上,家珍的眼泪流个不停”“她是在交代后事,我心里听了酸一阵苦一阵”“那是哭得,把腰哭疼了”“我的眼泪刷刷地流出来了,二喜本来已经不哭了,一看到家珍又呜呜地哭起来”“看着她老了许多的脸,我的心里一阵酸苦”“他伤心地哭了”“就坐在地上大声哭起来”,从上述句子来看,福贵每次遇到难过的事,伤心似乎程度差不多,也都不至于让他想到要去死。这大概也是他之所以能活下来,一次次挺过悲痛的原因吧。或许正是这一次次的揪心之痛,痛之骨髓,让福贵越来越体会到生命之“轻”,也更能感悟到命之“重”。所以,他也就更加坚定了自己活下去的信念,他要活着,为那些死去的人;他要活着,为了自己而活着。作者在小说中的语言运用,可谓是独辟蹊径,他就要用这种看似平平无奇的描写,让我们感受到这样的独到见解:一个人活着的意义,本身就在于活着。
四、作品中的死亡意象分析
在《活着》的一幕幕悲剧描写中,许多人物都在偶然的事故中丧失了自己的生命,与死亡相关的意象在小说中随处可见。作者特意使用这种描述方法,表达自己对死亡的独特见解。很多时候,死神总不顺着我们的心意,让你准备好了,才剥夺你的生命,往往总在不经意之间,顺手就夺走了你的生命,这也是作者语言运用的妙处,同时也借用死亡这样的意象来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在这里,死亡似乎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当读者还沉浸在一次难以自拔的悲伤中时,刚有了片刻的欢愉,作者又给你心上重重一击。而我们不免会产生这样的阅读感受,死亡似乎成了作者惯用的一种工具,他是为了体现故事情节的悲剧性安排了一次又一次的死亡。同样,他也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死亡也是生命的一部分。一个生命从出生开始,就注定会消亡,或早或晚。同时,作者也借用一次次的死亡意象,让我们感受到活下去的不易,也才更加珍视生命,更加坚强地面对生活中的挫折。历经风雨,终见彩虹。
在《活着》的描写中,与福贵关联的人物一个个都先后离开福贵而去,最后只剩他一个人孤零零地活在这人世间。面对这样凄惨的身世,我一次次感受到了锥心之痛。我有这样的假设,如果福贵不是一个败家子,他最终的命运会不会改写?会不会不一样?答案是否定的。所以,我们可以有这样的认识:死亡是生命的一个环节,一个过程,是生命自诞生以来的天然属性,任何生命都难逃最终死亡的命运,人作为一个生命体,当然也不例外。小說中的死亡一次又一次上演,人类对生命的最终结局抗争宣告失败。然而,面对必将消亡的生命,我们真的就是无能为力,无所作为吗?答案是否定的。可以这么说,正是对死亡结局必将到来的认识,让我们认识到活着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即使活着非常艰难,人生遭遇多少苦难。余华采用直面死亡的方式叙写死亡,让我们感受到死亡也是生命的新起点,正与“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所表达的哲理有异曲同工之妙。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生和死本身就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新的生命的延续本身就需要以消耗自己的生命为代价,而随着生命持续的时间越来越长,其和死亡的距离也就越来越近。其实我们可以发现,把死亡作为生命一个过程、一个环节的认识,会让我们减少对死亡的恐惧,对死亡的坦然态度更能让我们体会到活在这世上的意义。美国一首著名民歌中的主角经历了一生的苦难,家人都先他而去,而他依然友好地对待世界,没有一句抱怨的话。这也正是启迪作者写出这部平凡而又超凡的作品的感悟所在。
故事终将结尾,我们的人生还在继续,不管是风和日丽,还是狂风暴雨,都是生活给予我们的阅历,不管我们身在何处,希望我们都有“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豁达与洒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