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而不耀”的《老子》
郭永秉
如果把《老子》看作是中国现存第一部成体系的哲学家著作,那么也就可以说,我们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系统性认知,是以《老子》为开端的。一百多年前,胡适先生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截断众流,以老子、孔子为中国哲学诞生时代的两位哲学家。老子的年辈高于孔子,所以,说他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开山鼻祖确实并不为过。
在老子、孔子之前,当然也有很多称得上思想家、政治家的人物,他们立德、立言,成为春秋以后人们效法、引据的典型;他们的言论本或有篇什记录,但后来大多散佚,经由春秋战国时代的君主、贵族、政治家、学者之口援引而为我们所知。从现存资料来看,这些人通常是遵循殷周以来的传统政治秩序、道德法则以及言说方式来表达自己思想的。例如,仲虺(与老彭并称的商代贤臣)、史佚(周初史官)、周任(上古良史)、臧文仲(春秋前期鲁大夫)等先于孔子的著名贤人的箴言,都着眼于人伦、政治方面经验教训的总结:
· 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左传·文公十五年》)
· 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左传·成公四年》)
· 昔史佚有言曰:“动莫若敬,居莫若俭,德莫若让,事莫若咨。”(《国语·周语下》)
· 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抚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乱者取之,推亡固存,国之道也。”(《左传·襄公十四年》)
· 仲虺有言,不穀说之,曰:“诸侯之德,能自为取师者王,能自取友者存,其所择而莫如己者亡。”(《吕氏春秋·骄恣》)
· 周任有言曰:“为国家者,见恶如农夫之务去草焉,芟夷蕴崇之,绝其本根,勿使能殖,则善者信矣。”(《左传·隐公六年》)
· 周任有言曰:“为政者不赏私劳,不罚私怨。”(《左传·昭公五年》“仲尼曰”引)
· 周任有言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论语·季氏》“孔子曰”引)
· 臧文仲闻之曰:“以欲从人则可,以人从欲鲜济。”(《左传·僖公二十年》)
· 臧文仲曰:“国无小,不可易也。无备,虽众,不可恃也。”(《左传·僖公二十二年》)
· 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左传·文公十七年》)


虽然只是片言只语,但从中可管窥早期中国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官所关心的主题,大致不外乎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国族对外的相处、压制攻取及守备之法;第二,治官、临民、莅政之道;第三,君主、贵族个体的德行修养;第四,宗族内部的人伦规范。尽管他们有时也意识到“俭”“让”等卑约之德的价值,但在主体给予一定克制的前提下,总体上是不否定个人之“欲”的,主张以积极进取的态度去处理政治与人生中所遇到的各種情况—对于外国、异族要存有戒备,对于乱国危邦要侮慢以至攻取,对邦国内的罪恶要彻底剿灭,重视选任能人、师法贤者对执政治国的意义等。作为服务于王朝、诸侯的精英,他们创造、遵循并完善着既有的天下秩序、人伦规范,适应于不断拓土开疆、发展生产、丰富物质的历史进程,嘉言懿行被后世铭记。
然而,被孔子描述成“先进于礼乐”“郁郁乎文哉”的商周古代社会,实际并没有那么美好,尤其是东周以后的历史逐步演变成“内废公族、外灭人国”(钱穆先生《国史大纲》语)的失控舞台剧。旧有的秩序、规范、道德被打破了,但又找不到出路、看不见希望,弱肉强食、劣币驱逐良币的法则引导了社会历史进程的主流。
孔子说,《诗》“可以怨”(《论语·阳货》),意思就是《诗》可用以“发泄牢骚”(朱自清先生《诗言志辨》语)。按照司马迁《报任安书》中的看法,《诗》三百篇都是“贤圣发愤之所为作”的,正所谓“心之忧矣,我歌且谣”(《诗经·魏风·园有桃》);《周易》《春秋》《国语》诸书,同样是古圣先贤因“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而作。在有资格立言的主流知识分子、贵族之外,其实还有相当多对国家社会前途、百姓命运怀有隐忧与不满的人,他们多半不得遂志,又“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所以要么是选择做隐士逸民,要么把怨刺寄托于历史著作、文学作品中,以抒胸中愤懑。
胡适先生《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开篇,就把《诗经》当中所反映的时代思潮归纳为“忧时派”“厌世派”“乐天安命派”“纵欲自恣派”和“愤世派”(激烈派)。他说,这些思潮“没有一派不是消极的”。“到了这时代,思想界中已下了革命的种子了。这些革命种子发生出来,便成了老子、孔子的时代。”“老子亲见那种时势,又受了那些思潮的影响,故他的思想,完全是那个时代的产儿,完全是那个时代的反动。”他甚至把老子称为“革命家”。
老子是不是一位“革命家”,也许还可以讨论。我们只知道,老子与史佚、周任身份接近,是服务于周王朝的“史”(虽然他在王朝内的职务、地位不能与史佚、周任这些地位隆崇的良史相比)。他深通古礼,习知文献掌故,然而作为开宗立派的思想家,他又呈现出与以往不同调的、卓立的批判色彩,不是一位温柔敦厚的妥协者。
老子的批判性,并非体现在对具体人事的形而下反思,也不通过情感浓烈饱满的文学创作来鞭挞与控诉,更非诉诸天帝、鬼神以求安慰解脱。他抱有沉重的忧患意识,结合自身职掌与训练,从古中国原始思想的元素当中汲取养分并加以扬弃利用,由此深刻思考终极性、普遍性的问题与方法,向统治者提出自己善意的建言。这一整套主张,与前述所有主积极进取的传统治术大为不同,显示出老子对宇宙、社会、人生深邃的观察与独到的智慧,是对中国古代文明高度发达时所凸显出的各种问题的根本性省察。他的睿智箴言虽然未必能为侯王君主所用(甚至未必能为在位者真正理解),却在以儒术为基调的古代政教传统之中,自然地形成一种巧妙的制衡力量与补充手段,影响至为深远。

老子思想清静无为的一面为世人所习知,这是老子重视柔弱之德的智慧。章太炎对老子学说中“阴骘”之术高明于儒家的地方评价不低。他在《訄书·儒道》里说:老聃著五千言,“其治天下同,其术甚异于儒者矣”。“儒家之术,盗之不过为新莽;而盗道家之术者,则不失为田常、汉高祖。……其始与之而终以取之,比于诱人以《诗》、礼者,其庙算已多。夫不幸污下以至于盗,而道犹胜于儒。”取法道家之术的政治家,往往具有更多的谋略,考虑得更透彻,比起只重虚文末节的儒生仍要胜过一筹,即便从窃国者来看,也是道胜于儒。然而,机谋深刻,对于私欲膨胀的君主、政客甚至窃国者而言意味着什么,章太炎又在《訄书·儒法》中用八个字告诉我们:“道其本已,法其末已!”儒道互补、道法相生,在“儒表法里”的政治统御术主调之下,老子创立的道家思想从来不是可以轻忽的低音,它与另外两者之间构成了富有弹性的思想张力,制衡历史车轮的前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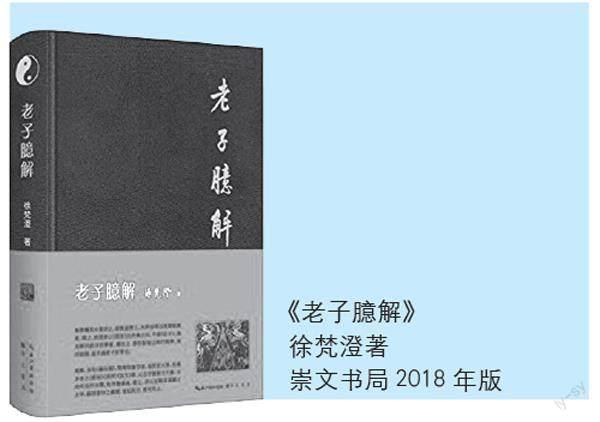
很多人都以为,主张清静无为、柔弱谦卑的老子所设计的理想社会,是最终要倒退回彻底弃绝文明、制度的状态当中的,因此不少学者站在进化论的立场对老子思想提出批评,认为他的设想过于脱离现实。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徐梵澄先生《老子臆解》认为,老子的意思并不与进化之理相悖:
若推其意,以人类之不齐,万物之相胜,皆率自然之道而返于朴,则且归于野蛮时代,文明亦几乎息矣,尚何“自宾”“自均”之有?老子之意,盖不其然。或者,仍诲人以“知止”(引者按: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一句),谓此有其极限也。要之,此不失为一至高远之理想。
也就是说,侯王在“名”既已制作之后,要承认这一事实,要“知止”而不可刻意,既要守道无为,也不可能真倒退到“无名”的状态。如果这种对于“知止”的主体的解释合乎《老子》原意的话,那么老子本来并没有真正彻底弃绝文明、归于野蛮的意图,确实是一种“高远之理想”。宋人王安石注《老子》十一章说:“故无之所以为用者,以有毂辐也;无之所以为天下用者,以有礼乐刑政也。如其废毂辐于车,废礼乐刑政于天下,而坐求其无之为用也,则亦近于愚也。”陈柱先生《老子之学说》认为,“老子亦非不见及此也”,“老子盖未尝去有,特以当时之人,皆从事于‘有之为利,而忘夫‘无之为用,故为矫枉过正之谈耳”。他们的意见,可以从《老子》十四章的一句话里得到印证:
执今之道,以御今之有,以知古始,是谓道纪。
“今之道”,传本和北大汉简本《老子》皆作“古之道”,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两种帛书本《老子》都作“今之道”,文义较长。可见老子并不无视或抵制“今之有”(也就是当下既已存在的“有”和“有名”,文明制度、礼乐刑政这些东西都包含在内);而且,他主张用“今之道”去控御主宰“今之有”,也就是顺应既存的社会现实、以因应之法加以治理,而不是执一成不变的“道”去应对。但同时,老子又告诉统治者,在这过程当中,要把握道的根本特质,也就是“大曰逝,逝曰远,远曰返”并最终“复归于无物”的虚无,虚无才是“道”之根本要領。因此以“自然”“无为”“清静”的、合乎道的方式行事才能真正“御今之有”。这就是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所说的:“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据同出于马王堆汉墓的帛书《十六经·观》(《十六经》或称《十大经》,唐兰先生认为即道家著作《黄帝四经》的一篇),“圣人不朽”当理解为“圣人不巧”,就是说圣人不尚机巧功利,只是顺应时变行事而已。太史公曾“习道论于黄子”,这段话可称深得黄老道家思想的精髓,是真知老子之言。
司马迁分析儒家和老子学说的分歧,借用了孔子语“道不同不相为谋”作为结论。此点实亦非深知孔老思想差异者所不能道。今天解读分析《论语》和孔子思想,不对年辈先于孔子甚至是孔子师辈的老子的思想有比较深刻了解的话,也就很难透彻地知晓孔子和早期儒家言论的因承关系与针对性。这方面的例子,陈鼓应先生《老学先于孔学》《老子与孔子思想比较研究》等文(收入《中国哲学创始者—老子新论》)有集中论述。我想再根据自己对《老子》文本的理解补充两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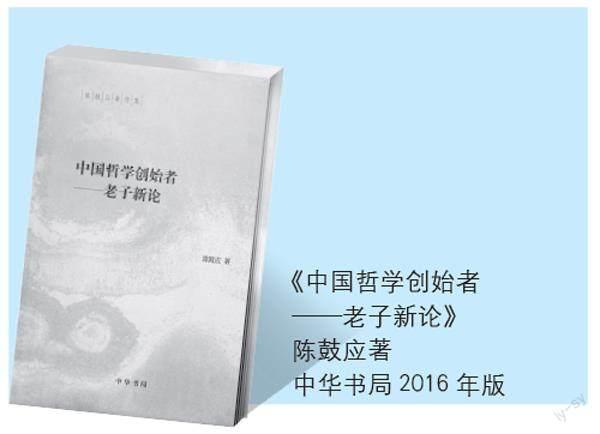
一是对待隐逸的态度。孔子从根本上是不赞成隐逸的,他与隐士、逸民大致都保持一定距离,甚至隐隐地批评长沮、桀溺这一类避世之人。虽然孔子有的时候也发出“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的感叹,但发完牢骚、开了玩笑之后,便马上说浮海之“桴”根本“无所取材”,即明确地否定避世道路的选择。而老子在司马迁的叙述当中,则正是一位曾仕于周朝的隐君子,这种关于老子身世的传说,具有深刻的思想和历史依据,并非随意编造。在《老子》中,这位思想家经常告诫人们要自爱、自重己身,极端慎重对待自身大患。十三章是对欲取天下的侯王而言的,老子强调“贵大患若身”,将重视死生大患与宝爱自身放在同等地位,指出只有“贵为身于为天下”的人,才可以被托付天下、统治天下,也就是说,“贵身”是取天下的先决条件。但如果说这个人过于宝爱、吝惜自身,想远避取天下为侯王可能带来的祸患的话,老子认为,“爱以身为天下,若可以去天下矣”(此为郭店简本,帛书甲本后半句作“如何以寄天下”,意思就是怎么能寄付天下给他呢?意思接近),其实就是赞成这些吝惜以身来为天下付出的人,离开天下之位去归隐。《庄子·让王》:“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国无君,求王之搜不得,从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舆。王子搜援绥登车,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独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恶为君也,恶为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谓不以国伤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为君也。”王子搜就是这样一位坚决地“不以国伤身”“恶为君之患”的人物,按照老子的看法,他既然如此不愿承担以身为天下之任,不愿承受可能招致的大患,是可以选择避世的,而不见得非要像越国人那样千方百计地逼迫王子搜做国君。因此,孔子“鸟兽不可与同群”之语,针对的或许还不仅仅是长沮、桀溺这些人物,更有可能就是对早期道家关于进退出处表态的一种反应。
二是对待为政者卑辱处下的态度。老子因其所主张的道之弱德的特性,认为君主本身应当以卑下自处,不可傲慢压迫、高高在上,例如其自称皆用卑贱之名而不求下民赞誉等。七十八章说:“故圣人之言云:受国之诟,是谓社稷之主;受国之不祥,是谓天下之王。”此语与《左传》宣公十五年晋大夫伯宗语“国君含垢,天之道也”有关,很可能是对古语的引申发挥。十三章的“宠辱若惊”,也是要求侯王、君主重视“为下”的可贵,面对遭受的诟辱、卑贱要以惊喜态度面对。八章“上善如水。水善利万物,而又争居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矣”,同样是希望统治者效法几近于道的水的美德,不避污垢,甘于居之,甚至居之若争。《论语·子张》记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子贡这两句话,一般认为是表达一旦为不善就是居下流,所以不可开启不善之端的意思。其实,“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两句,很可能同时是针对老子要求君主受诟、受不祥、宠辱、为下而为言的。子贡的话所隐含的意思是,国君一旦受诟辱,便免不了天下之恶全归于他的命运,商纣王其实也并非如一般所想象的那样不善,他的恶是居下流的必然结果,所以作为君主仍應如孔子所言,像北辰那样高高在上,“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决不能如道家所主张的那样,真的去“争居众人之所恶”“受国之诟”。
儒道两家在早期的呼应与交锋,以及老学对孔学的深刻熏染,只要细心去摸索,也许还能找到不少证据。虽然“道家”之名与“儒”“法”等家派名称不同,要晚到西汉才出现,但是老子创立的道家思想实际所产生的影响,却可以说在先秦时代的许多经子著作中在在可见,如气体一般弥漫,是先秦思想中真正的“无冕之王”。
从一部中国古书的角度而言,《老子》也有几个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地方。
首先,全书不出现具体的人物、事件、对话(纵有问答也是自问自答),完全是一部格言体裁的著作。然而这些格言,也并不记载说话人姓甚名谁,仿佛空谷中回响着一位容颜模糊的旷古智者的大段诗意独白(这种诗意,主要来自全书大部分章节严密用韵的特色)。日本学者福永光司解释《老子》中的“我”说:
老子的“我”是跟“道”对话的“我”,不是跟世俗对话的“我”。老子便以这个“我”做主词,盘坐在中国历史的山谷间,以自语著人的忧愁与欢喜。他的自语,正像山谷间的松涛,格调高越,也像夜海的荡音,清澈如诗。
《老子》的独白是类于呵壁问天式的,但又不像屈原《天问》那样落到对历史细节的关心上。文字所涉无一具体人事,这在古代中国著述当中独树一帜,完全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来分章节的“语录体”著作方式或许多少滥觞于此书,但韵旨则皆远不可及了。

其次,因为篇幅小、韵文又适于记诵,所以《老子》在历代流传极广(这种流传必然不单单是书面的抄写流布);道教成立以后,《老子》又被奉为这门宗教的主要经典,流传的版本相当多。李若晖先生主编《老子异文总汇》,收罗了一百余种《老子》版本,编成五百多页的八开大书。这在任何中国典籍中似乎都难以找到可相比较的例子。但事情总是一体两面的,《老子》的阅读、研究因此而具有特别的有利之处。从战国时代的《老子》选抄本一直到唐宋时代的《老子》文本序列相当之完备,也许除了《诗经》之外,先秦典籍很少可以观察到这样完整的文献流变脉络(有意思的是,这正好是两种有韵的上古文献)。《老子》文本、思想的演变及其接受史,因此就格外具备探究的条件了。但因为《老子》的版本极为复杂、文字上的歧异不可胜数,而且异文占全书的比例相当之高,这导致对它的研究举步维艰。
第三,大凡简单的话语,就比较容易产生理解上的歧义。早期的古典著作多有这方面的问题,例如解读《论语》就相当不易,主要就是因为其话语简洁、背景难晓。《老子》言简意赅、类于诗体,多义性的指向也非常突出。汉语本身就带有相当程度的模糊性,而且我们其实并不完全知道,到底老子就是将问题看得非常复杂、不愿意把话说得太明白,或者是因“趁韵”的考虑而把许多话讲得形式美感大于表意的确切,还是他本来确实是有一个明确的意思,只是后来人在运用、说解《老子》文本时丛生歧读异解(当然,也很有可能上述这几方面是同时交织的)。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早已感叹,道家学说“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学术史上从《韩非子》《庄子》以来,关于《老子》文本内容无穷无尽的解释争论、引用发挥,多半都与这方面的因素牵连。学者常说“《诗》无达诂”(见董仲舒《春秋繁露·精华》,《说苑·奉使》作“《诗》无通故”。所谓“《诗》无达诂”的含义,在经学史、文学史上颇有争论,此取一般认为的《诗》可断章取义、没有遍彻所有场合的诂训的意思),我想同样也可以说“《老》无达诂”。李若晖先生为《老子》第一章做了汇集古今解释的工作,编成近九百页的《老子集注汇考》第一卷,亦可见一斑。可以说,《老子》一书,迄今仍有个别章的文句无法确解,有待后来者不断努力。这也是《老子》一书能吸引千百年来的学者去探索、读解的特殊魅力所在。

第四,中国古代典籍在世界上影响力最广远的,不是《论语》,也不是《孙子兵法》,而很可能是《老子》。据德国学者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统计,《老子》西文译本的总数在二百五十种以上;二○一九年美国学者邰谧侠(Misha Tadd)编录《〈老子〉译本总目》,搜集了《老子》七十三种语言的一千五百七十六种译本,并称该书是除《圣经》以外译本最多的经典。我想,这不单是因为《老子》短小精悍、较便迻译,更主要是由于《老子》“正言若反”(七十八章)的智慧、深具思辨色彩的特点,在以军国大事、礼乐教化、人伦日用为主要关注点的中国古代典籍中,尤能吸引西人目光的缘故。
最后,《老子》与一门真正的也是中国唯一本土产生的宗教—道教密切相关联。有的学者认为,老子这个人的经历、风格,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已经是西汉流行的老寿的神仙形象,带有神仙家的味道了,因此东汉以后的道教奉老子为道教创始者,奉意旨玄远的《老子》为教派最重要经典,或者换句话说,从先秦古书中最具神秘主义玄妙气质的《老子》思想里孕育出希望通过得“道”而成为神仙的“道教”来,是十分自然的。好像中国还不曾有其他的古书,在建立一种宗教的意义上,可与《老子》相提并论,而这跟上面我们提到的《圣经》在某种程度上倒有着相似性。如果承认鲁迅对许寿裳说过的那句名言—“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不是一句错误的判断,同时承认在儒法治术之下道家的底色与补充,那么也可以认为,要真正懂得中国文化,不读一读《老子》恐怕也是不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