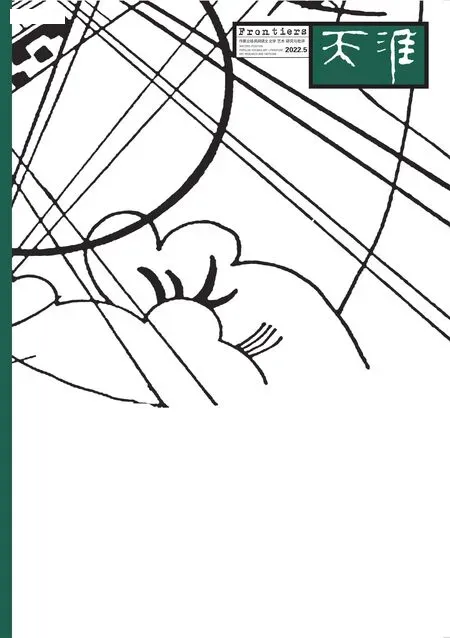女性也是浪潮的一部分
唐棣
瓦尔达与中国
2019年,法国女导演阿涅斯·瓦尔达去世,国内一波纪念文章发表,除了写她与新浪潮的渊源,还都写到她与中国的不解之缘。
缘分具体就是指1957年,她曾到北京、上海、沈阳拍了不少照片,她也参与过法国纪录片导演克里斯·马克的短片《北京的星期天》的拍摄。克里斯·马克这部短片中,瓦尔达的可爱体现在我们看着有些“滑稽”的中文字幕上——我想,滑稽的部分,可能没有恶意,包括镜头下的那些风景和人,看着也有些莫名的感觉,那就是当时西方人想象中的中国了——长相朴实的人民、汽车和人力车交织的街景、叫卖的人、在公园晨练的人、阅兵队伍中耍杂技的人……
西方对中国(或者说东方)产生过疯狂的好奇,如法国小说家安德烈·马尔罗、考古学家维克多·谢阁兰和诗人保罗·克洛岱尔等人都很迷中国。后来,当上文化部部长的马尔罗(1968年,他开除电影资料馆馆长亨利·朗格卢瓦间接导致了新浪潮运动的改变)凭着两次短暂的中国之旅(第一次是1925年在香港和澳门逗留了四五天;第二次是1931年,在广州、上海、北京三个城市游览,后来又去了哈尔滨和满洲里)就写出了两部小说:《征服者》(1928)和《人的境遇》(1932)。马尔罗在1965年还作为戴高乐总统的特使访问了北京,一生三次到访中国。
据说1984年,意大利导演贝纳尔多·贝托鲁奇来中国考察之后,非常想在这个神秘的国度拍电影,向中国政府上交过两个项目计划书,一个是后来拍成的电影《末代皇帝》,另一个就是改编马尔罗的小说《人的境遇》——可见马尔罗在小说里塑造的“中国革命者”形象,在西方是很有影响的。

女导演瓦尔达
这和西方的革命环境也有关系,他们需要一个参照物。当时的中国很大程度上是被西方一些反对现代文明的人当成避难所了。“这里的生活还没有受到现代精神之恶的影响……中国的生活纷繁杂乱而朴素天然,本能和传统在这里积累出深厚的财富。我厌恶现代文明,在那里我总觉得自己是个外来者。而在这里恰恰相反,一切都是那么自然而正常。”(保罗·克洛岱尔)东方的神秘布满在他们的诗歌和小说中。这其中,还有谢阁兰,他是学考古的,会汉语,能读中国古籍,长期在中国旅行。有特点的是,他大多是从历史角度来写那些关于中国的文章,这就加大了对神秘那一面的渲染。
一个真实的、发展的中国完全被这些东西遮蔽了。
2005年,瓦尔达在北京参加法国电影回顾展时,提到来中国的情况:“来到中国的法国人非常少。他们都要通过一个叫中法友协的组织来华。是一些亲中国的人,是一些对中国特别好奇的人,像我这样……”
好在摄影、电影这些所谓反映真实的工具,被西方人带进了当时的中国。神秘之外的那个中国,才有可能得到呈现。回忆结束,瓦尔达补充说:“今天的中国与当年的中国毫无相似之处。”
“今天的中国”和“当年的中国”是有落差的。瓦尔达当年来中国拍下的照片,目的就是想讓世界看看中国正发生着什么。
“落差”像想象与现实间的断裂,反映在瓦尔达的照片上。现实里,理论层面,实践中,“断裂也体现在各项艺术实践本身之间,从此以后,我们再也不能假装认为,这些实践是处于同一层面的”。虽然,于贝尔·达弥施那本《落差》主要讲的是摄影,但作为摄影近亲的电影,情况也差不多。拍下来的,和想要拍的,到呈现出的,最后和观众获取的,每个层面都有“信息差”。有一点是无法回避的——瓦尔达关于中国的记忆都是静态的。在这里,也可以看到,一种静止与剧变的“落差”。
对于中国之行,瓦尔达的感觉是“过去的时间并不总是真实的”。带着“落差”的想法来看,历史自古也布满了人和人、时代与时代、东方与西方的“落差”,这在瓦尔达的那些中国照片上也有体现。
“(20世纪)50年代我对中国知之甚少,现在虽然了解得多些但依然微不足道。”(《阿涅斯·瓦尔达的中国照相簿》)瓦尔达为2012年中央美术学院的摄影展写的这句话,确实是她在中国两个月的真实感受,但“真实”是一个非常不可靠的词语。
瓦尔达说:“我的1957年中国行照片在法国并不知名。当时,两位著名的摄影家布列松和吕布也在中国。他们的照片做成了书,成了杂志封面。彼时籍籍无名的我,则并未如此。”这些照片洗出来之后,没有多少人看过(没有在中国面世,当年瓦尔达只在法国自家的庭院里向朋友们展示过),即使看过,可能也改变不了什么。除了留下当时的中国风貌,起不到向世界介绍中国的作用。
我说这些的意思是,瓦尔达的想法和投身新浪潮时的身份,决定了她不可能像“手册派”那些人似的倾向于剧情片的革新,或者向好莱坞陈旧的电影观念发起挑战。这个生于1928年的比利时女孩,在普罗旺斯海边长大,1940年为躲避战火,来到巴黎上学。她大学读的是文学和心理学,晚上自学摄影,毕业后成了剧院摄影师。后来,她在塞纳河边的咖啡馆认识了克里斯·马克等这些新浪潮的“左岸派”。
显然,拍电影已经成了一种时髦。每个人都跃跃欲试,谁也没想到,年轻的瓦尔达真的会去行动——她在法国南部小城赛特拍《短角情事》时,正是《电影手册》那帮人提出“法国电影已死”的时候。
这部短片反响平平,瓦尔达好像被泼了一盆冷水。就是在这时,克里斯·马克带来一个可以去中国参观的机会。
电影与电影观
摄影师的身份影响着瓦尔达的电影观,比如她认为“电影可以通过摄影机的过渡,将静止、定格的画面向过去、未来和想象三个维度延展”。新浪潮,尤其是“手册派”的人在意“场面调度”,她在意的却是“从定格,到动态的变化”。
过去、未来和想象都是关于时间的,难怪她总结自己的工作时会说:“我拍照,或者电影。或者,将电影放到照片去,又或将照片放到电影去。”这就是瓦尔达身上的那种作者性。
早期,她的电影也带有新浪潮的几个共同特点:用非职业演员和简易的摄影器材,在熟悉的环境拍眼前的生活。
当她意识到“这只是一种真实”后就转向了对“另一种真实”的反映。
另一种真实就是和新浪潮高潮期的剧情片一样精彩的纪录片。也许,瓦尔达的纪录片和实验片更能代表法国先锋电影,而不是新浪潮电影的剧情片。有个误会是,好事的媒体似乎把她作为一个女性主义创作者,硬生生给扔到新浪潮这帮男性荷尔蒙膨胀的群体里去了,她因此也有了个“新浪潮老祖母”的称号。
瓦尔达拍第一部短片时,新浪潮还没有正式开始。剪辑师一边剪片子,一边对她说,在她的影片中看到了维斯康蒂和安东尼奥尼影片相同的场景。瓦尔达却反问,他们是谁?
这不是假装的,可爱的瓦尔达是在剪辑室里,的确是头一次听说“手册派”这些人津津乐道的那些电影大师。
当她有资格坐下来回顾创作时,不仅没有骄傲,还有少有的清醒:“我知道我是一个先锋,我在1955年拍了一部激进的电影,他们所说的新浪潮开始于1959年、1960年。当我拍第一部电影的时候,我远离电影的世界,我甚至没有看过电影。”
其实在1961年,她也拍过一部不知名短片《麦当劳桥上的未婚妻》,演员就是新浪潮主将戈达尔和他的未婚妻安娜·卡里娜。戈达尔戴着标志性的墨镜,安娜·卡里娜穿着漂亮的裙子。他们真实的关系为这部短片带来了奇妙的感觉。短片拍完没多久,两个“演员”就结婚了。从此,安娜·卡里娜成了戈达尔电影的标志,永远的女主角。如果说,新浪潮时期最有名的一张脸是《四百击》里小男孩安托万的扮演者让-皮埃尔·利奥德,那么随着戈达尔的《小兵》《随心所欲》《法外之徒》《阿尔法城》和《狂人皮埃罗》的问世,安娜·卡里娜的脸,也成为新浪潮最具标志性的一张女性面孔。

《麦当劳桥上的未婚妻》(1961)剧照
有趣的历史,存在于瓦尔达的回忆里:“我们与时间斗争,但是时间就那样流逝。只能用幽默来对付了,时间多可怕,时间多可笑。电影就是90分钟的时间游戏。”这是瓦尔达一贯的态度,和新浪潮其他人的激进、严肃完全不同。
2019年2月,纪录片《阿涅斯论瓦尔达》在柏林电影节放映。九十岁高龄的瓦尔达不再像以前那样来者不拒,她突然不想在放映后说话。“这是我的作品,这就是我要说的话。”一个月后,瓦尔达就在巴黎的家里去世了。
一直有个问题被混淆了。新浪潮倡导的“作者性”和瓦尔达说的“电影写作”是两回事。早期很多人,包括新浪潮群体也经常混淆——这是因为翻译的问题吗?
明确下来的是,“作者性”强调表达自己,就是作者的想法;“电影写作”侧重如何做到这些,更类似于一种创作“风格”。二者之间的关系有点像内容和形式的关系。
关注怎么做,是“左岸派”的特点。瓦尔达在访谈里提到“电影写作”时是这么说的:“就是我必须选择或利用所有元素,以使某些事物可以被分享。在《五至七时的克莱奥》《幸福》和《天涯沦落女》这类剧情片中,我的目的是选取一個主角、一种情境或与社会关联的什么事物。我想,触碰或分享的常常是心理活动。”
人的心理活动,比故事有意思——故事里的人物心里想什么,和观众所想也一定是有“信息差”的,但故事很快就会解开所有谜题。按这个程序进行下去,观众就能分享到秘密。我们常听人说,电影没白看,可能就是内心得到了满足。而其中的体会,早就随着这个结果消失了。只不过,很多观众习惯了这种方式而已。商业化的永远是剧情电影。纪录片根本上没法给观众这个满足感,因为它是“真实”的,观众也能理解。其实,纪录片里也有“落差”,只是和剧情片不一样。纪录片的“信息差”会长久地埋藏其中,就像生活中总有不曾被发现过的秘密。一代又一代的人在生活,也是在发现。
我们能记录什么呢?永远是生活。瓦尔达如此热爱生活,她在最后一部纪录片《阿涅斯论瓦尔达》里说:“我喜欢纪录片,有一些拍的很好的纪录片,在世界上很遥远的地方拍摄完成,这些长途跋涉的旅程对我来说太遥远了,我想要拍摄我身边的,我所认识的一些人或事。”
女性主义与代表作
从1954年自编自导第一部短片《短角情事》到2019年的纪录片《阿涅斯论瓦尔达》,瓦尔达没有停止过拍电影。“当我年轻的时候,人们都在创造全新的写作手法——乔伊斯、海明威、福克纳。我当时想我们也要找到电影的拍摄方式。我一直为拍摄激进的电影而奋斗,这一辈子都不曾停止过。”瓦尔达对英国《卫报》的记者说。
“正是因为我小时候没有看很多电影,所以我才可以以一个在电影界刚出世的孩子的身份任意地拍出我想拍的东西。”如同1954年夏,她在摄影工作之余,成立了一家电影制作公司,又在法国南部塞特港用一个月时间拍了处女作短片。她从没把拍电影的事情说得多么严肃:“我对自己所思考和分享的东西保持诚实,但我不会把自己表现得知道事情该如何如何去做……我努力地创作诚实的电影,但我不会自命不凡到认为自己可以改变世界。”(《好莱坞报道者》访谈)
新浪潮主力是“手册派”,瓦尔达身在支流“左岸派”,并且她是这帮人里唯一的一个女性导演。她一生拍了近四十部短片、纪录片、剧情片,其中记录性的片子占大多数。
瓦尔达的影坛地位,也和她是个女性主义者有关。
1971年,她与法国著名的女性主义代表波伏娃等人一同联署“343名荡妇宣言”,要求法国政府将堕胎合法化,1975年获得了成功;2018年在戛纳电影节上,和凯特·布兰切特等81名女性电影人一同走上红毯,抗议电影行业的性别歧视……
她的代表作《五至七时的克莱奥》的故事背景是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人们普遍害怕癌症,而女性患病率最高。当时,新浪潮正兴起,很多制片人都想从新导演身上大赚一笔。如日中天的戈达尔,把朋友雅克·德米介绍给自己的制片人,他们合作拍摄了《萝拉》。后来,雅克·德米又给制片人推荐了自己日后的妻子瓦尔达。不过,制片人不想出很多钱,只支持她拍一部廉价的黑白电影。
瓦尔达身边的现实,就是女性对不治之症的恐惧。拍小成本电影是新浪潮导演的长项。“如果电影的拍摄地在巴黎,那么我们就不用支付差旅费和酒店住宿的费用。接着我想,我在一天之内完成拍摄,这样的话就不会有太多的布景。”
就这样,一部电影时间和现实时间“共时”——都是九十分钟的电影诞生了。
关于电影是时间艺术的讨论有很多。这里只想说,电影时长固定,一般在九十分钟至一百二十分钟,再长就影响票房了(电影和文学不一样,看书找个地方就行,电影要在影院看,成本大,时间就是金钱)。时间有限,电影里的时间,却可以缩小或放大——几小时之内(罗德里戈·科尔特斯的《活埋》)或几百年(库布里克的《2001太空漫游》)都可以,这看导演想表达什么了。

《五至七时的克莱奥》(1962)剧照
瓦尔达在《五至七时的克莱奥》里,把时间限制在下午五点到六点半的范围,九十分钟,镜头陪着克莱奥经历了一遍恐惧,九十分钟之后会发生什么?更多的恐惧?完全的平静?
2005年导演本人到北京参加法国电影回顾展时,提到自己在九十分钟里做了什么:
在45分的时候有一个断裂,有一个45分钟的片子,后面就是说有另一个45分钟的片子。像诗句中的顿挫。如果我们想安静地谈一部影片,这不正是你想要的吗?谈一谈电影。整个第一部分,克莱奥由所有看到她的目光描绘出来。她是被观看的,就是说她被她的女佣人所描述,被算命女人描绘,卖帽子的女售货员向她惊叹:“您真是美丽,维克多利亚小姐。”还被咖啡馆里的人描绘……她像一个小洋娃娃,她被别人赞叹和恭维,就像在镜子中一样。她和其他的女人一样,别人描述的是她的镜像。走廊里、楼梯里都有镜子,在第45分的时候,她突然产生了恐惧,但别人并不知道。她的佣人、情人,都把她当作布娃娃,所以她突然生气了。她就不是个洋娃娃了。所以她突然脱衣服,扯掉假发,把里面的衣服脱了。突然她变成了小短发,黑衣裙,出走了。从此刻开始,是她在观察别人。她观察街道上的人……
恐惧是那个时代的重要主题,观看是任何电影的核心。女性从被观看,到观看他人的转变,代表了时代呼唤不被重视的一股力量。
她另一部有名的电影《天涯沦落女》,是讲一个流浪女孩如何死去的。
郊区清晨,警察正在处理一具女孩的尸体。电影剩下的时间,就是回溯女孩一路上的经历,每个人都曾想拯救她,但她每次都从安定的生活里逃出来,最后还是死在了郊区的田边。电影4分50秒后,画面出现了一片海滩,伴随旁白,又出现了一片海。一个女孩从海里走上岸。“我对她一无所知,不过看样子她来自大海。”旁白道。
瓦尔达迷恋海滩,可能和她在海边长大有关,在她电影里关于海的镜头真的太多了。据说,瓦尔达八十岁生日时说过:“如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景,那么她就会拥有一片海滩。”这让人想起《阿涅斯的沙滩》开头的旁白:“如果打开我的心扉,我们会发现海滩。”

《天涯沦落女》(1985)剧照
《天涯沦落女》里的这个来自海边的女孩,不知何故,流浪到城郊,执意要走下去。所有人都知道,包括她自己,走下去,只能有去无回。为什么还要走?瓦尔达在《天涯沦落女》里讲的是一种选择的权利。当选择不止有一个时,选择才更代表个人意愿。当选择的可能性增多,明显看上去更好,你选什么,就变得更重要。
瓦尔达的女性主义,来自她对当时社会感受的一部分。人,尤其是女性,在社会中无所依靠。“我们从没有讲述这个女人她从哪里来,为什么她在路上流浪,我们只是想要展现她如何生存,她怎么找吃的,她睡在哪里,她的行为。”瓦尔达的说法,指向了流浪女孩个人的生活价值。理解了那片海,也就理解了人,瓦尔达把海作为延续那种对生活无望情绪的缓冲,它是温暖和广阔的,只是走着走着,走向了毁灭。
电影的35分11秒至36分24秒,流浪女和牧羊人有段对话。他们的共同点——牧羊人赶着羊不断迁徙,不断搬家;女孩什么也不在乎,就是不停地走。“我们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这就是生活。”牧羊人一脸无奈,“我选择了一条折中的路,介于孤独和自由之间……”他告诉女孩,“你选择彻底的自由,得到的却是彻底的孤独。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你迟早会把自己毁了,你正走向毁灭,如果想活着,就停下来。”她像牧羊人所说的一样,最终还是毁灭了。
《天涯沦落女》的核心是固执地相信着什么,可是没人问过那是什么。无因的信心推动了叙事。这部电影是瓦尔达作品里比较客观的一部,不带情感判断。流浪女孩简直是一座孤岛,生活给予她的东西越来越少,现实离她越来越远,无论走到哪,那种定义不清的“自由”都像海浪一样把她推远一点。女孩的流浪,就是在消耗孤独,孤独耗完了,电影就结束了。
沙滩与别离
电影《南特的雅克·德米》(1991)是瓦尔达一生最重要的作品。如果我告诉你,那种既温暖又阳光,温情又有趣的影调,是建立在她对去世爱人的思念,也是對自己的安慰上,也许你就能理解这部电影的重要性。

《南特的雅克·德米》(1991)剧照
“有时,一部电影的开始,是因为生活迫使我们去拍摄它。”就是说,生活里的雅克·德米,即将去世,瓦尔达称那是“生命中非常悲伤的一个时刻”——雅克·德米生病时,向瓦尔达诉说童年,比如南特的沙滩、门廊、车场、内院、小镇、街道,等等。
这部电影让他们的感情变得更长,而不是就此结束。
在《五至七时的克莱奥》(1962)诞生这一年,她嫁给了雅克·德米。相当长的时间,他们住在努瓦尔穆捷岛上的小屋,两人最爱做的事,就是去海滩散步。
“大海让他感到亲切,海水总是不断变换着颜色,时而灰,时而蓝,这就像他自己。”
于是,《南特的雅克·德米》开场是雅克·德米躺在沙滩上,手中攥着一把沙子……电影里插入了雅克·德米之前拍的电影片段,看样子瓦尔达有点想要试着找到生活与电影的联系——新浪潮不是一直强调这些吗?
最早是父亲为人修车的场景,7分13秒至40秒,插入了电影《秋水伊人》里修车人与客人的交谈,然后是着迷上轮盘赌的表姑在13分57秒到14分17秒之间,对应电影《天使湾》里的赌局。
他们一家和表姑在餐厅吃饭时,突然听到躺在钢琴上的女人开始唱歌,15分26秒至38秒这段插入《萝拉》里的唱歌场景。后来18分9秒至22秒,父母对话说,表姑当了间谍,对应《怀孕的男人》。接下去是20分12秒至39秒,对应《驴皮公主》。母亲做家务时嘴里哼着歌,她一个在雅克·德米的生活中随时在场的人;再后来是雅克·德米准备了第一场木偶戏演出,却没有人来看。26分57秒至27分08秒,雅克·德米站上墙头吹笛子,对应《吹笛手》,吹笛子的人在街头呼唤孩子们。再后来是弟弟怕黑,30分28秒至40秒,对应《停车场》游荡在黑暗空间里的人。还有就是38分51秒,神出鬼没的女邻居死在门口,小雅克·德米第一次透过敞开的门看她家的陈设,装饰和《城里的房间》里算命人的家一模一样……
战事来临,父母不得不把他和弟弟送到乡下,交给一个鞋匠照顾,在41分16秒,小雅克·德米第一次与父母分离,说再见。41分45秒时插入《卢瓦河谷的木鞋匠》。随后,一家人很快团聚,43分35秒至50秒对应《七大罪》。
50分50秒,小雅克·德米用最高的代价——一个能看到游轮的转笔刀,换到一些胶片,并且通过那个换走他转笔刀的男孩知道了地方,找到了更多胶片。这些被雅克·德米开心带回家的胶片,如旁白所说,并没有成为启动他电影热情的催化剂,妈妈把他们当做垃圾或者危险品给丢了。
直到62分,关于电影的话题再次出现。邻居深夜来访,说德国人随便抓壮丁去劳动,小雅克·德米则唱起《夜间访客》的歌曲。鞋匠妻子说,他满脑子都是在南特看的电影。邻居说,你应该去找那对退休的老师姐妹,她们有放映机和一些卓别林的短片。然后他去借来给全家人放映,大家都被电影里的人逗笑了。
75分,小雅克·德米在商场玩时遇上了一台旧的电影摄影机,然后他拿一座模型桥和一些书作为交换,剩下就是雅克·德米和摄影机的故事了。雅克·德米拿着个摄影机带着小伙伴们一起拍了一部短片,但因为没调光圈,什么也没拍到,84分,伤心的雅克·德米对母亲说,我想去读电影学校。
第二台摄影机出现在90分,母亲为他买了电动摄影机,小雅克·德米一直留着这台机器。纪录片后半段完全是在拍一个年轻人多么热爱电影,但父亲一直不同意。这是一个在幸福的家庭中长大的充满想法的小朋友从儿时喜欢琢磨电影,后来经过努力投入进去的故事。没有意外的剧情反而更像生活,打动人的是真实的。最后,雅克·德米顺利地到巴黎学电影,当了导演,娶了一个拍电影的女人——瓦尔达。
镜头转回沙滩,雅克·德米身穿牛仔夹克,一个人——雅克·德米已经去世,瓦尔达也是一个人了。他们在电影里,通过旁白交流,细沙从指缝间流走,童年记忆,随风而至。
印象中,电影里有两次提到观众——
第一次是在27分钟56秒,母亲指责他从流浪小孩那里搞得一头跳蚤,但小雅克·德米显然对自己的木偶剧演出很满意,他说,他们有鼓掌,我们有谢幕。
第二次提到观众是在65分7秒,旁白说,他很享受观众的笑声,仿佛片子是他拍的似的。
年轻观众与一个时代的逝去
在瓦尔达那里,观众是看电影会心一笑的人,不是落泪的人。她去世前,还和年轻的街头艺术家让·热内合作了纪录片《脸庞,村庄》(2017)。
她说:“有时《脸庞,村庄》放映过后观众鼓掌致意,我认为这是因为它触动了人们,让他们明白他们可以分享一些东西。而且我们需要这一切。因为我们需要彼此联结。世界是充满了困难,生活中的事情往往是支离破碎的。但仍然要创造一些什么,让人们见证彼此间的联结……”
不少年轻观众第一次看瓦尔达的电影就是这部纪录片。这个法国老太太的生活态度特别自在,面对镜头,就像面对朋友,说话时常像个孩子似的手舞足蹈,有趣是最重要的——毕竟和他们提什么新浪潮,已经勾不起什么情感了。
从此,我身边突然多了很多喜欢纪录片的年轻观众。我想,是这个已经九十岁,活力四射,偶有疲惫,对很多事情仍好奇得像个孩子的瓦尔达打动了他们。
瓦尔达上了年纪之后,也从来不避讳谈论死亡。七十二岁那年拍《拾穗者与我》时,她就说:“我正在变得越来越老,越来越接近终点。我试着去看2000年的拾穗者是什么样,也看2000年的瓦尔达变成什么样。我已经进入老年期了,所以,我看不出有什么原因我不试着去纪录它。”她觉得“所有死亡都将我引回雅克,每一滴泪,每一束花,每一支玫瑰,每一朵秋海棠,都是献给雅克的花”。(《阿涅斯的海滩》里的独白)
随着一个时代的逝去,新浪潮这些严肃、充满战斗性的男性大师们陆续去世了,瓦尔达“无辜”地成了除戈达尔之外,对新浪潮最有发言权的人。
很多影迷把她最后一部纪录片《阿涅斯论瓦尔达》视为“瓦尔达的电影大师课”,可瓦尔达生前总说:“在我所处的边缘地带,我感觉自己像个公主。”

瓦爾达最后一部纪录片《阿涅斯论瓦尔达》(2019)海报
在人生的最后一次访谈中,记者问“老去的公主”瓦尔达,希望自己如何被人们记住。
“我想被人们记住我是一位热爱生活与痛苦的导演。这是一个可怕的世界,但是我一直觉得每一天都充满乐趣。在我的日常生活中,无论工作、与人会面还是倾听,都令我相信自己值得活在这个世界上。”她带着那种一贯的微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