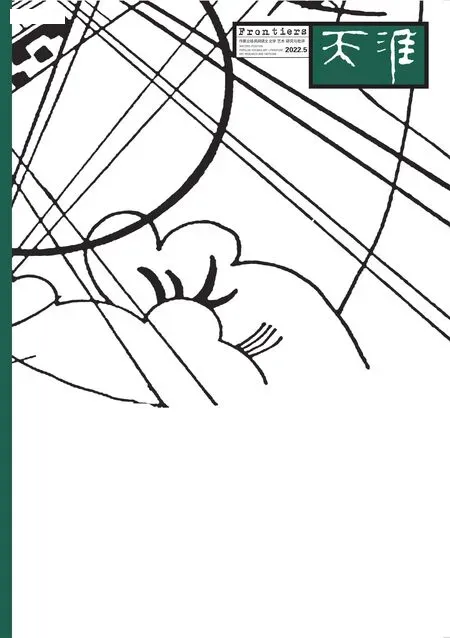新一代在如何对抗数字监控
肖芯妍
2022年6月2日《波士顿评论》的网站上,刊载了该网站记者对普林斯顿大学两位研究者——肯妮娅·黑尔和佩顿·克罗斯基的访谈,题为《新一代在如何对抗数字监控》。
随着数字技术的日益普及,我们也越发明白:我们的设备在监听我们的谈话,我们的个人数据在被追踪和售卖,商家和有关部门在存储我们的面部图像,等等。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在探讨保护我们数字隐私的办法——普林斯顿大学的“艾达·贝尔·韦尔斯‘只是数据实验室”即致力于此,但它的关注点更为集中,即黑人和其他边缘人群在数字监控时代所遭遇的挑战和威胁。该实验室试图将学生、教育工作者、社會活动家和艺术家等集结起来,以共同探讨针对数据生产和流通的批判性、创造性思考,黑尔和克罗斯基即在该实验室工作。
面对数字监控的指控,系统和软件的开发者们可能会回应说,情况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是新技术,还有待进一步完善,而且随着新技术的增多,情况会变得越来越好。但黑尔和克罗斯基并不认同这样的说法,在她们看来,技术并非中性或无偏向的——我们将自己的价值观和信仰编码进技术之中,而技术之所以存在问题,是因为我们有对边缘社群进行奴役和剥削的历史,因此技术虽然是新的,但与技术有关的问题却一点也不新:它们只不过是被重新塑形并被重新打包而已。新的软件使得技术的运行速度更快,但它同时也使得歧视的运行速度更快,因此要解决技术的问题,我们还是要回到人和历史那里。
从这一思考出发,黑尔和克罗斯基所在的团队正在研发一款名为“我们的空间”的应用软件。两人对这款软件做了介绍:一般流行的精神健康应用软件都是针对个人的,它会问你今天过得怎么样,或者追踪你一周的情绪变化。但“我们的空间”要抵制的正是这一假设,即疾病的疗治只能依靠身处资本主义重压之下的你自己——“我们的空间”意在成为一个疾病疗治的社群,比如:当你感到焦虑或者沮丧时,你和你所在的社群都知道如何能帮助你,这时有人就会告诉你,可以看看电视、吃点什么或者做点什么;你还可以在感到焦虑时向社群里的人发出警报,这样其他人就会知道你的情况,并对你进行关照。
当然,从大的方面来说,这样的对抗似乎于事无补:这就好像个体在对抗气候变化——你大力践行环保理念,但个人的努力在大规模排放的企业面前,简直不值一提。同样的道理,你在努力对抗数字监控,但相关的大型企业和机构似乎还越发壮大。对此,黑尔和克罗斯基回应说,我们的确无法指望一款应用软件或者一项技术就能改变监控资本主义的现状,但在现状被彻底改变之前,我们还是得集体行动起来并汇集解放性力量,以求得生存,并矫正最终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