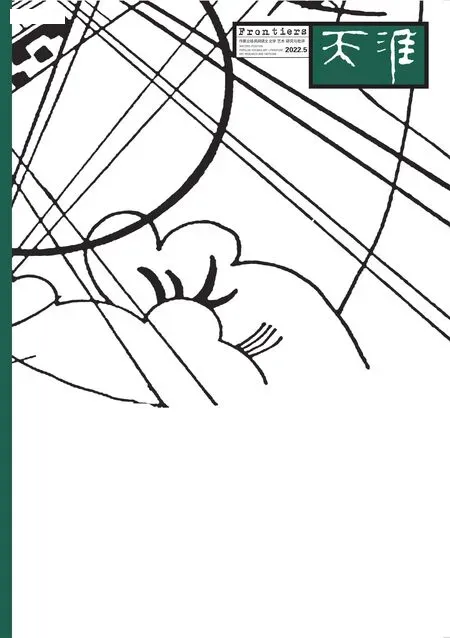“媒介资本主义”
郝晓菲
2022年6月2日《传播、资本主义与批判》的网站上,刊载了克里斯托弗·阿里对托马斯·克里考尔2021年的著作——《媒介资本主义:大众欺骗时代的统识》的书评。
十多年来,在批判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关于如何认识和理解当下社会的性质,人们众说纷纭:我们如今正处于与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截然不同的信息社会或网络社会?还是说,数字时代不过是马克思所理解和批判的资本主义的延伸?在丹·席勒看来,我们如今正处于“数字资本主义”的时代;而曼努埃尔·卡斯特更推崇“网络社会”这一说法;克里斯蒂安·福克斯試图给出更为辩证的理解,即从生产力角度说,我们如今处于信息社会之中,但从生产关系角度说,当下社会似乎仍然还是资本主义的延伸;2020年肖莎娜·祖博夫则提出了“监控资本主义”的说法,即信息资本主义的特征,就是对社交媒体平台目标群体行为实践的关注和对其数据的收集。
我们对于克里考尔的著作《媒介资本主义》的考察,也应该在上述语境之中展开。比如,祖博夫认为,监控资本主义是社交媒体产业的特定产物,但自诞生以来,它便延伸至信息和数字生活的其他方面。克里考尔的看法与之不同,在他看来,媒介资本主义裹挟了一切,它表达的是受企业媒体和公关产业驱动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且媒介资本主义并非信息资本主义的分支,毋宁说,它是对此前一切说法——“文化工业”“意识工业”“依附之路”“宣传”等——的取而代之。换言之,大众传媒与新型数字媒体企业及公关公司,共同传播着某种总体性的资本主义,人们对此常常习焉不察,但它却影响着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媒介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也与之相关:克里考尔为此给出了一个公式:媒介(M)+消费主义(C)=媒介-消费主义-意识形态(MCI)。不仅如此,克里考尔认为,该意识形态的影响无所不包,没有人可以逃脱媒介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包围。
作为一本507页的“大书”来说,克里考尔的著作无疑为我们思考当下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但阿里也指出,由于并非经验性分析,对其“媒介资本主义”这样的概念在日常生活中的运用,读者可能会很感兴趣。比如,对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消费、教育等不同领域来说,“媒介资本主义”的影响是大致相似呢,还是各有差异?面对“媒介资本主义”无处不在的影响,人们是否还有反抗的空间?如果有,那么这样的反抗又能够以怎样的形式展开?等等。凡此种种,都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关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