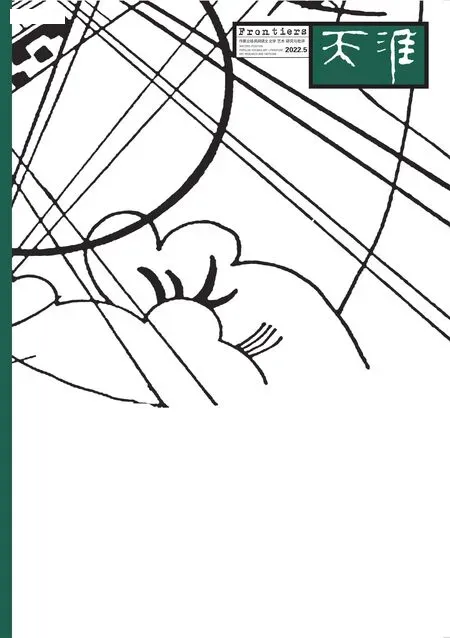人间遇雨
丁威
一
他身后是一间矮小到轻易碰到脑门的土坯厨屋,背对着太阳,一天到晚不见阳光,屋内黑麻麻的像夜色照进了浓稠的蜂蜜。屋里矮于地面,虽垫上了一层泥门槛,但一遇上大雨,雨水便漫灌着淌进厨屋,像浇灌水稻那样把屋里浸润透。厨屋又照不着阳光,便终年是满屋子的潮气。锅门巢堆积着烧火的柴禾,有早已晒得干透散发着草木暖香的稻草,有坚硬耐烧的大豆秸秆,有长长的扎成一捆的芝麻秸秆,有巴掌大小一爬篓一爬篓捡回来的杨树叶……它们在锅门巢里挨不过一个夜晚,就被屋内的潮气咬噬得浑身瘫软发霉了。一到烧火做饭,屋内便狼烟四起,柱状的粗滚滚的浓烟从烟囱里钻出去,多余的,又粗滚滚地从矮小的屋门挤出来。我妈在厨屋里高一声低一声地咳嗽,眼泪像捻动的珠子一样滚落下来,一顿饭做好,我妈便像嚎啕大哭了一场,双眼通红如枣。
另有一间高于厨屋的土坯房子,既做堂屋又做卧房,一日三餐,待客闲谈,日落而息,都在这一间土坯房子里。年岁久远,屋根脚已有不少残缺处,让人觉得它仿佛是一个醉汉,根底飘忽,脚掌不稳,随时都要倾倒下去,把自个儿狠狠地丢在地面上。也未见我爸去填补它,但一年年过去,虽一直像要倒塌,却始终一年年看过去,依旧是老样子,新出现的那几块残缺,也无伤筋骨,屋子仍旧是苟延残喘般站立着。那墙面上闪电一样的裂痕,在日晒雨淋中,也新添了皱纹,却如同老人被风霜割面,只要还能走动、做活,还能到荒地里捆一背的柴禾,把水挑进缸里,把米挖进锅里,让炊烟在烟囱上升起,吃下一碗饭,便继续活下去。我们看那道道裂痕,就泰然处之,那是一间老房子历经风霜的自然现象,打我落地在这间老房子里,在这铺就散发着新鲜稻草暖融融的草木阳光气味的新床上,后又用尿溺让整张床成了整间屋子熏人窒息气味的生产地,到我渐次知晓周遭事物,知晓时间在四季里写下的种种,这座老房子就是这般面貌,我看它如同看自己的身体,我接受它也一样如接受自己的身体。
但我爸是不同的,他知晓的事物要比我多得多,他不但知晓我们朱皋村,还知晓往流镇,知晓固始县……再过几年,他将知晓更遥远的北京、新疆,知晓天南海北。在他骨子里扎下最深根茎的是“人情世故”,是“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张脸”,是“争气”。
先前,逢一个闲散晴朗的天气,他还挖土和泥拌上稻草,拿泥抹子把屋根脚的残损处仔细地抹平加固,把墙上的裂缝用泥灰细细地填塞,直到围着屋子前后转悠一圈,四面的根脚再无破损处,四面的墙壁也都再无空隙处,他才满意地点燃一根烟,像端详一件艺术品那样享受着自己的成就,仿佛是他把这间老房子从往昔的时光里拉回来了。虽然早已不复当年的青春容颜,但经他的手一打理,那些因时光的流逝而侵蚀的部分,又焕然一新。
晴好的日子里,从屋顶缝隙处透进来的金色太阳光斑,那明晃晃的影子随着太阳的运动,也在屋子里四处走动,四季里还留下不同的行走轨迹。一只小猫时常把影子当作活物扑腾过去,扑了个空,又乐此不疲地继续下去,想要捉住它,又不厌倦它似乎总在捉弄自己。
但到了有暴风雨的夜晚,一切都变了模样了。那雨起先还小心翼翼地试探,很快便找到了房子的脆弱破绽处,几滴雨水打了头阵,察觉出了破绽处的不堪一击,便把别处的雨水,甚至那些本该流下屋檐的雨水一同喊来,告诉它们此处有捷径。雨水们听从了召唤,一涌而来,很快的,那晴日里筛下生动阳光的地方,便在这样的雨夜里,筛下苦涩的雨水来。噼里啪啦,一阵响过一阵,起先还似跳伞一般一个接着一个地坠落,很快,那些围拢聚集过来的雨水,便结成了一股绳,拉下长长的雨线来,只在快接近地面处,才在地球的引力下扯断了连缀着的雨线。坐在空中的老天爷玩兴越来越大了,再不满足于瓢泼雨水,他像是醉了酒一般的疯狂,高兴得拍手跺脚,一跺脚,天便多一处窟窿,天空塌陷,暴雨再无承载的依托,全世界所有的雨水,都汹涌而来,攒足了胸中的憋闷,长长地舒缓心中的块垒,下吧,下吧,下吧,任谁也止不住天空狂歡的夜晚。
风和雨像窃贼一样守在破损处,不待一声哨响,便乘虚而入,那屋外暴风吹奏的呜咽声中,又在我家里平添了一种怪异的曲调。那是暴风吹过墙缝发出的独特呼哨,像晴空中突然扯起的往高亢处攀升的鸣响,到了高处,便一跟头跌落下来,但又一声连着一声,撕扯着夜晚的沉沉睡眠,撕扯着干涩的眼眶,像夜游的孤魂一般在狭小局促的一室之内逡巡,专找你的耳朵钻进去。那一声连着的一声,像千足虫的一条条颤动的腿脚,在你耳朵里翻江倒海。这样暴风骤雨的夜晚,当然不止屋外的风吹雨淋声,也不止风穿过墙缝的呼哨声。这一间年久失修、缝补亦不堪大用的房子,它早已是千疮百孔,早已是遍体鳞伤。
二
人间遇雨的夜晚,世间所有的雨水都到了我家,那骇人的风声早已叫醒了所有人,雨水像是浇灌干涸焦渴的河床那样,浇灌着我家屋里的土地。它一进来,便要四处横流,想把巴掌大的屋子变成泽国,想把我们安卧的木床变做一艘在风雨飘摇中的小船,至于要将我们载向哪里,全看它的心思了。外面是浓墨般风雨飘摇的世界,大风吹过所有的树,大雨淋湿所有的树,沾染了雨水的树叶在大风的鼓吹下,拍起了更加响亮清脆的巴掌,风呜呜叫,雨哗哗响,大风大雨下的树叶癫狂一般拍着巴掌,像是冥冥中有神武之人降临世间,需要这样一场撼人心魄的暴风骤雨来迎接。
那细电线绕着墙头和房梁扯上去的灯泡,怀着内心明亮的电流瑟瑟发抖。每天夜里,房梁上都有吱吱叫唤的老鼠逡巡,咯吱咯吱地啃咬着什么,甚至直接在房梁上嬉闹、厮打,一个跟头从房梁上跌落下来的情况也时常发生,“噗咕”一声,一包肥硕的肉团从天而降,在地面上砸出一股沉闷柔软的声响。摔下房梁的老鼠只一个翻身,就吱叫着迅速消失了,房梁上的老鼠也吱叫着。像做错事一样消失了。但过不了多久,它们又顺着房梁、墙角、桌椅攀爬往复,夜色给它们披上最好的伪装,给它们打上强心针,仿佛这间破旧的房子到了夜晚就不再是我们的家了,而是成了这群老鼠的家,它们在夜色里如此招摇,毫无顾忌,像是我爸的许久不见的老朋友,风尘仆仆地从远方赶来,不打招呼,无需礼道,只管带着一身风尘推门而入,如入无人之境,拿起筷子就吃肉,端起杯子就喝酒。在夜色中,这群主人似的老鼠,拿所有可见的吃食填饱肚子,拿所有可啃的硬物磨牙齿,粮食口袋上缝缀着一块又一块破布,那都是它们偷盗啃咬的结果。它们小小的肠胃,任它们偷吃吧,也吃不穷尽我家的粮食,可最让全家痛恨的,是它们磨牙齿的啃咬,新打就的座椅板凳,还泛着清新的油漆味,这是属于新生事物的气味,闻起来都让人有一种新生的喜悦。这些新家当进了家门就被这群家伙循着气味啃咬成东一块西一块的了,板凳腿上,椅子脚上,处处都是啃咬的缺口,新油漆下裸露出新木头的伤口,看起来像是身体上的伤口那般触目惊心。
我妈气不打一处来,转身出去往朱西街走,要去买一包老鼠药,那种无色无味却最烈最要命的毒鼠强。我妈的眼前晃动着那些新鲜木头的伤口,可是她还没走到朱西街,就停住了,她脑子里出现了一个前不久发生的熟悉的场景。
三
我妈走到半道,像光脚踩在烈日炙烤过的路面上那样把脚步缩回来了,她想起村里曾有一对姐弟,把家里墙角洒落的毒鼠强当糖精吃下而丧命的场景,孩子的爸妈在地上嚎啕大哭的声音还嗡嗡地吵着她的耳朵。
我妈孤零零地坐在屋子里,瞧着被老鼠啃坏的桌椅板凳,瞧着屋顶上被雨水浸得朽烂的屋笆,黄泥早已灰黑,雨水就是从那个地方肆意流淌进来的。瞧着四面墙壁上闪电一样的裂缝,风从那里吹进来,夜深人静的时候,鬼一样吹响的呼哨声,搅得她头皮发麻,早上醒来,脑袋像一块木头,又沉又飘。钻进厨屋,一顿饭下来,像打了一场硝烟弥漫的仗,油烟和落灰裹住了灯泡,即使深夜那灯泡也只像油盏一样,发着晕黄微弱的光,擦了又擦,那光亮也未见增强多少。我妈坐在堂屋里,瞧着那残破的桌子腿,抹起了眼泪。
没有毒鼠强的家,四面漏风漏雨的家,暴风骤雨的夜晚,不请自来。黄昏来临时,风把天上的流云迅疾地吹动,天空变了颜色,像一个黑沉的锅盖扣在头顶,云层低得几乎要垂落下来,把我们家那间矮小的房子压迫得更显矮小了。我妈早早地做了饭,吃完饭就躺下了,趁着暴风骤雨还没到来,她能多睡一会,等到风吹雨落,再想睡踏实,那等于是异想天开了。我妈也早就备好了各样的盆,那些惯常落雨的位置,她不需抬头瞧着屋笆寻找,像熟悉自己的掌纹那样,就在地上把盆摆好了,只等着雨落下来,雨水从屋顶上渗漏下来,一串串地滴落在盆里,地上的盆像道行深厚的术士那样,捉住那些滴落的鬼魅雨水。各样的盆里先是空空荡荡,那雨水滴落的声音就是金属、瓷器、塑料的声音,空洞而喧响。待雨水渐渐聚集,又成了雨水和雨水的奏鸣,随着盆里的雨水水位渐次升高,声音也渐渐不同。夜色中,眼睛闭上了,耳朵却张开了,耳听也为实了,雨水落在洗菜的铝盆里,声音清脆,余音萦绕;落在洗脸的瓷盆里,声音更脆,像拦腰折断一根刚刚摘下来的新鲜黄瓜;落在洗脚的塑料盆里,声音沉闷,像一滩烂泥远远地砸在墙上;落在洗衣的木盆里,声音旋即消失,像是木头有了吸力,那声音被吞进海绵一样的木盆里。我妈像一个下棋的圣手,每一枚棋子都清清楚楚地落在心里,那盆摆放的位置,和各处雨水渗漏的速率有关。最大的洗衣木盆放在渗漏最严重的地方,依次是洗脚的塑料盆、洗脸的瓷盆、洗菜的铝盆,甚至那些盛菜的盆也来补位。屋外风急雨骤,屋内的滴漏之声连绵不绝,随着雨势渐大,滴漏的雨水像是鼓槌敲击着鼓面那般,鼓手敲击到了高潮处,那起落的鼓槌没有一丝松懈,一下赶着一下,将鼓声敲成了一张密不透风的帘子,再敏锐的耳朵也听不出那滴漏的缝隙之处了。
盆里的雨水渐多,由先前的生硬之声变得绵软黏稠了,噗咕噗咕,都是雨水咬合雨水的声音,却又因盆里雨水的水位高低而各有不同。木盆大,渗漏得快,半天只覆盖住了盆底;菜盆小,渗漏得慢,只不多会,就将要满溢了。我妈在黑暗中,眼睛全然瞧不见,耳朵却灵得很。她也不敢拉亮灯泡,那些在房梁上厮打的老鼠们,不晓得哪一只黑闷了心,把尖利的牙齿磨到电线上了,虽没有咬断电线,可也许皮子已经咬破了,晴天还好,这样渗漏雨水的雨天,不晓得破皮处有无浸到雨水,一拉灯绳,漏电也是可能的。所以逢上暴风雨之夜,拉亮电灯是我家的忌讳,耳闻目睹过不少被电杀死的人。电,这样一种无影无形的东西,竟能像人捏一只蚂蚁那样,轻易杀死一个人,不留半点痕迹,这太过可怖,谁也不敢去冒险。在这样的家里,我妈早就练就了属于黑夜的眼睛和耳朵,任屋内漆黑如鸦,瞧不见一丝光亮,却也不需要一丝光亮,两只脚准确地在黑暗中找到两只拖鞋,两只耳朵又准确找到那个快要满溢的菜盆,一手捉过去,像抓住菜板上已经拔干净毛的鸡,稳稳当当地抓在手里。她将菜盆里的水准确地倒进洗衣的大木盆里,再准确地将菜盆放回原处,动作熟练迅速,没有丝毫拖泥带水,待她又躺到床上时,那个又重又空荡的菜盆的响声再次变得脆硬起来。就这样,在这个漫长夜晚的暴风雨中,我妈时不时地起身,抓起那些已经盛满水的盆,将雨水倒入大木盆里。雨水就是时间的滴漏,有时大,有时小,有时快,有时慢。我妈在这起身的间隙里,还能闭上眼,稍稍睡会儿,那迷顿的瞬间,也并不妨碍她随时起身,把那将要满溢的盆倒空。如此这般,漫漫长夜就在倾倒雨水中过去了。
四
随着夜色的浓稠渐渐化开,暴风一夜的啸叫声渐渐止息了,急骤的雨水敲打屋瓦的声音,也渐渐止息了。远远的,公鸡开始鸣叫,此起彼落,一声声的鸡鸣缝缀着被暴风雨摧残着的破旧的村庄,仔细听去,那鸡鸣声中也有一丝丝的颤抖,人都无一处遮风避雨的安适的家,更不要说一群鸡了。多少人家彻夜不眠,在鸡鸣声中,睁开惺忪的睡眼,耳朵里吵了一整夜的雨水滴漏声,让他们的脑袋像一截被大水浮起的木头,迷迷糊糊,漂荡于大水中。
但太阳照常升起了,一夜的暴风雨之后的清晨,世界更显清亮了。一座村庄被风雨摧残,可村庄各处站立的树木,各处生长的植物,各处苟且的杂草,却比往日更加鲜活,更透出勃勃生机,雨水被输送到树木的顶梢,每一片叶子都喝得饱饱的,身体里充满了水,让一棵树浑身满溢的劲儿,仿佛要离地飞奔而去;每一片叶子上的积灰都被冲洗干净,上面的雨水还未蒸腾干净,阳光照上去,光彩夺目,远远望去,一棵大树上布满了阳光的碎金子。雨水累积着,又层层滴落,在清晨的阳光里,一棵树继续下着碎金子般的雨。
一棵经历彻夜暴风骤雨的树,在清晨醒来的时候,是静默的,浑身的劲儿在枝干枝叶里窜动。树不像一夜未眠的村人,它的静默里窜动着生机,却把浑身的力道按捺下去,沉潜下去,只是滋润它的枝干、枝叶生长就好,只是滋润它体内的年轮潜滋暗长就好,它沉默地接受摇撼它的暴风,晓得伴随着暴风的便是暴雨,摇撼它筋骨的,也必将滋润它,它坦然接受这摇撼与滋润。阳光此刻透着蜜糖一样的亮,是一汪蜜糖里点上了一盏灯,灯光和蜜光交相辉映,这样的阳光泼洒向一棵静默的树。你无法不凝视一棵树身上,它渾身静默的叶子,叶子上静默的雨水,把蜜一样的光收纳起来,那光也随同雨水一道聚集,悬在叶尖上,如一盏小灯,点亮了每一片叶尖。若陡然跌落了,坠向另一片叶子,则像一场起义一般,一滴坠落的雨水的灯盏,召唤起了千百滴雨水的灯盏。这样一棵阳光里静默的树,动与静的和谐,构成了暴风雨之夜后最动人的清晨景象。
各处的庄稼和野草,被一夜风雨吹打得倒伏下去,可它们全然没有失去精气神,仿佛是常日的站立,需要这样一场风雨来让它们弯下腰,歇一个漫长黑夜,以倒伏的姿态,来向暴风雨致敬,向生养它的大地致敬。黎明来临,太阳洒下万道金光的伟与力,你看吧,不要多时,几乎你一转身,这一片庄稼和野草,就又都立起身了。
阳光遍洒,你用内心谛听着千亩良田和万亩野草,那是一声声酣畅的“啊”,让它们回想起先前盼雨忆苦的日子。焦渴的身体疲软地抓紧脚下的土地,日光强烈的正午,它们时常觉得,脚下的根须有一瞬间的松懈,仿佛攥紧太久的拳头,再也无力为继,浑身散了架,整株身体像被烈日抽走了游魂,根须走了那么漆黑那么遥远的路,寻得的水不解燃眉之急,根须泄了气,周身也便跟着泄了气。你躺在夏日的屋檐或大槐树下,眯缝着焦渴但难捱的睡眼,望向远处的植物,无一不是蔫头耷脑,连远远响彻的蝉鸣也显出嗓子眼里的焦躁了,柳树汁液也吸不出更多的甘甜了。
一切庄稼和野草,一切往上伸展腰肢的树木,都把一棵身子化成鼻腔,嗅闻着空气中的潮气,希望从那潮气的蒸腾中嗅闻出雨意来,雨意的触角小心翼翼,在烈日的眼色里,潜滋暗长。
五
村庄里那棵最高大的国槐,当然是最先嗅闻到雨意的;家里最先嗅闻到雨意的,是我的爷爷。雨意最早像空气中飘忽不定的游丝,只有对农事最敏锐的眼睛和嗅觉,才能察觉。
我爷爷说,怕是要下雨了,要下大雨了,庄稼都等得发焦了。
我爷爷吩咐家人,把晾晒的粮食收好,把漏雨的屋子补好,把晒干的衣服叠好,别让一场雨坏了事儿,他慌得不成样子,没个人形。吩咐完,他就扛起一把铁锹下地去了,雨当然会来,嗅闻着空气中若有若无的雨意,我爷爷晓得这必定是一场了不起的雨,恐怕要下一整夜。他掐算着指头,已经月余未曾有点滴雨水落下了,人、土地、庄稼、一切活物都是焦干的,风一吹,都是在空洞洞地响。只有一回,瞧着天黑得穹顶贴到地面,直通通地压在人的头顶上,村里人都像雨前蚂蚁似的忙碌着,唯有我爷爷站立不动,似成竹在胸,又似无动于衷。任谁都觉得雨定是要下来了,云压得这样低,天黑浓得似一杯糖水,浓稠得再搅拌也化不开,雨不落下,云自个儿都承受不住,村里人瞧着自家的庄稼地,都欣喜地拍起了巴掌,为老天爷的开眼喝彩。
我爷爷还是站在开阔的场院里,毫无动静,只把一根又一根烟点燃了,不断地抽。我爷爷又点燃了一根烟,并不抽它,而是把它平直地遥指苍天,那烟气从烟头一生出来,就仿佛吐丝的蚕蛹,一刻不停地往外抽丝,那丝只往上升腾的一小截,就又箭矢一样地平飘过去了,一根烟,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就被风抽完了,像一只吐尽了丝的蚕,干瘪下去,瞬间苍老。我爷爷把烟蒂丢到地上,右脚踩上去,细细地碾几下。我爷爷把一口浓痰射到远远的地上,抖抖披挂在身上的衣裳,转身进了堂屋,不一会儿,就掇条凳子坐在了屋檐下,手里抱着一个盖着盖的大搪瓷缸子,里头泡了苦涩大叶子的酽茶,喝一口比喝药也不差几分,我爷爷倒喝得怡然,一边抽烟,一边喝茶,有无限的享受在里面。
此刻,我爷爷就端坐在屋檐下,瞧着场院里忙碌的人,瞧着鸡鸭涌进院子,扯着嗓子叫;瞧着牛被拴回牛棚,卧在稻草铺就的地上,眯缝着眼睛反刍;瞧着风把墙角花池里的月季、栀子吹刮得弯折到一边,几乎要倾倒下去,挂在门楣上的去年的粽叶,像砂纸一样摩擦着墙面;风一个劲地吹,万物都在风的吹动下,弯折下来,倾倒下来,声响碰撞着声响,铁器的声响,木器的声响,铁锹摔倒磕碰在砖地上。这会子,各人忙各人的,目光被引过去了,却并不过去把铁锹扶起来,倒下去就倒下去,被攥在手里干活累,被竖立在墙根站直了也累,索性就让它躺下去吧,也算歇息歇息。我爷爷瞧着开阔的院落,村人收拾完了东西,有的回到屋里,有的立在屋檐下,婶子们回到厨屋去了,天还压得那么低,黑洞洞的厨屋里一切已经皆不可见,却没人拉亮电灯。离着晚饭时间还远,蒸馍的面团醒在面盆里,择菜不要光,手指熟悉它们,黑暗里照样一根根择得干净。鸡鸭在吃食,牛在反刍,月季、栀子在倾倒,四轮车静静爬着,车厢里空荡荡的,只有细小沉默的铁锈在缓缓生长,大风奈何不得它一分,细粉似的铁锈却有着宏大的野心。方才忙碌的家人,此刻都各自做各自的事了。
我爷爷也不言语,只一根根地抽烟,一口口喝下苦涩的酽茶,把大风一遍遍地看过,也把大风吹过的物件一遍遍看过。爷爷端端坐着,瞧着家人为暴雨来临做的准备,那些庞大的物件,在风中岿然不动,就像此刻神态淡定的爷爷。那些细小的事物,在风中簌簌抖动着,更加细小的事物,则全部在空中化成风的形状。落下枝头的叶子,随着风吹旋作一团,直到被风吹旋到角落里才安定下来,时而还抽搐般地抖动一下。搭在屋棚或者菜籽堆上的雨布,被风鼓胀起来,根脚却被几块沉重的石头拽住了,风奈何不得石头,就只管闷头往雨布里扎,把雨布鼓胀得像要离地飞升。塑料袋还很少的年代,瞧着风中飞起一朵红色或者白色的塑料袋云朵时,孩子们是最兴奋的,追着塑料袋,瞧着它插上翅膀一般高高低低地飞翔着,似乎要俯冲下来,被孩子们捉住,却又一个筋斗,直直地翻腾上去,孩子们再蹦跳,也触手不及。那风似乎给了塑料袋眼睛,它们一挨近树杈,几乎被树杈伸手抓住,却又像精灵似的轻巧地兜转开去。孩子们追着塑料袋,瞧着这朵红色或者白色的云朵,像电视中的章鱼那般,变化出不同的形状,距离也时远时近。但那大风跟孩子们玩了不多会,就厌倦了,塑料袋飘飘荡荡地朝着山坎飛去了,轻松地越过山坎里最高的那棵国槐树,一头扎进山坎那边那一片傲然挺立的杨树林里了,扎进去又挣出来,远远地朝着淮河飘过去,朝着对岸的外省飘过去,那里有广阔的平原和一望无际的菜地。它可以尽情飞翔了,再不必担心有哪一棵大树给它一座囚牢,在那座囚牢里日晒雨淋直到朽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