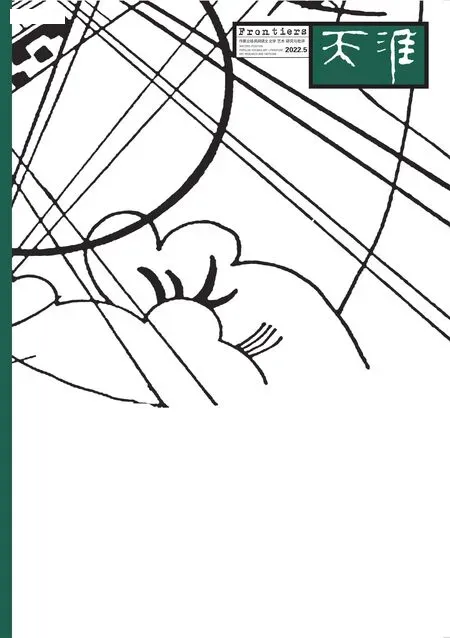族谱里的血脉
欧阳国
一
清末光绪二十年(1894年),满目疮痍的清政府被迫对日宣战,中日甲午战争全面爆发。
时值酷夏,与硝烟滚滚的战场相比,距战场两千多公里的中国南方的一个偏僻村庄显得异常安静,而实际却是暗流涌动。贫穷带来的疾病和饥饿像一场残酷不堪的战争,正在一步步吞噬这个渺小的村庄。
深夜,一阵又一阵孩子的啼哭声打破了村庄的宁静。房屋四面环山,没有一丝风,月亮在夜空中缓慢移动,时而隐蔽,时而呈现,村庄或明或暗。
一个男人默默地坐在屋檐下,月光散落在他脸上。这是一张忧伤的脸庞,粗糙、消瘦、黝黑,像干旱的土地间已经枯萎的庄稼,奄奄一息,毫无生机。
这个男人的名字叫作世樽,世是他的字辈,樽是古代盛酒的器具。也许,给他取名的父亲是一位嗜酒如命的酒徒。也许,现实中他并不叫世樽,他应该还有自己的乳名或者绰号。世樽,是他在族谱里的名字,这是一个多么雅致的名字。他父亲的名字叫作正琪,族谱记载为“冠带乡耆”。原来,他父亲是一名年高德劭的乡贤,有才华,有名望,世樽有如此雅致的名字一点也不足为奇。
屋内的孩子未满周岁,前几日不慎患上风寒,每至夜深人静时,孩子就不停地哭闹和咳嗽。孩子的哭声让男人焦虑和恐惧。他汗流浃背,心脏扑通扑通地加速跳动,消瘦的身体在黑暗中微微颤抖。孩子突然停止了啼哭,夜色瞬间凝滞,他快步冲进房间。妻子示意他说没事,孩子入睡了。他以为孩子又夭折了,原来是虚惊一场。他走出房间,继续坐在屋檐下,痴痴地望着天空,数着天上闪闪的星星。他凝望其中几颗耀眼的星星,一闪一闪,感觉是夭折的孩子的化身,跟他打招呼,它们一个个正朝他的方向移动。
他害怕孩子突然死亡,也似乎习惯了一个又一个孩子夭折。这是他的第八个儿子,父亲给孩子取名隆代,寓意隆盛万代。显然,他期盼这个孩子能够活下来,为他养老送终,为家族延续血脉。
不过,民不聊生的清朝末年,养大一个孩子谈何容易!在此之前,他六个孩子先后夭折。死亡,一次次血淋淋地撕开他残酷的一生。一次次亲手埋葬自己的骨肉,这是一件多么残酷的事情。每次孩子离开,他都要颤颤巍巍爬上楼顶,丢下一捆干枯的稻草,包裹僵硬冰冷的骨肉。他一只手提着孩子的尸体,一只手拿着锄头,一声不吭地朝后山走去。他弯腰对峙大地,对峙沉重的生活和多舛的命运,双手举起锄头,使出满腔的悲痛拼命地挖掘墓穴。在層层叠叠的青山之间,他的身体显得渺小和卑微,他无法控制自己无尽的悲伤,一边用力挖墓穴,一边热泪肆意横流。最后,他不禁嚎啕大哭,似乎有一条河流在他身体中奔腾。
每次,他都习惯把孩子埋葬在一棵树下,树木葱茏,树干笔直,像一个个站立着的孩子。天空乌云密布,骤雨将临,狂风呼啸,吹得树林哗啦啦作响,他分明听到孩子的嬉笑打闹声。一个孩子就是一棵树,这些树永远植入他心里,一天天长大。
二
我的祖父在世时告诉我,他的祖父有九个儿子,六个儿子幼年夭折,两个儿子中年离世。最终,只剩下他父亲一人。这个传宗接代的人就是隆代——我的曾祖父,他出生于中日甲午战争即将爆发之际。那个叫作世樽的男人,是我的高祖父。
曾祖父出生一年多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以中方惨败而告终,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同年,中国北方开始出现“清末疫疾”。春荒严重,耕收望绝。御史李念兹对光绪说:“京外灾黎扶老负幼,来京田食,其鹄面鸠形,贸贸溃乱之状,实屑目不忍睹。”《庚子纪事记》记载:“居民死者枕藉。”
清朝末年,疫疠、霍乱和鼠疫大肆流行。1910年,东北三省发生了一场举世震惊的大鼠疫,这场恐怖的疫情随后席卷大半个中国,吞噬了六万条鲜活的生命。病入膏肓的晚清处处积棺遍野,尸骸暴露,积贫积弱的中国千疮百孔,惨不忍睹。比自然灾害和疾病更可怕的是列强的侵略和残酷无情的战争,帝国主义的魔爪正肆意疯狂扑向中国腹地。
据清代人口社会研究表明,当时人均寿命仅三十岁左右,婴儿和儿童的死亡率高得离谱。医疗条件差、贫苦饥饿、战乱频繁和瘟疫横行,出生的孩子往往因风寒、天花、咳嗽不治而夭折。族谱的记载印证了祖父的话,高祖父九个儿子,只有曾祖父延续了血脉。
清明,我回到村庄。六卷封面深红色的族谱摆放在祠堂中央,在通红的烛光照耀下,时光闪烁,族谱神秘而庄严。翻开泛黄的族谱,每一个祖先的名字,都曾经是一条鲜活的生命。他们有过喜怒哀乐,有过爱恨情仇,不管是富贵还是贫穷,不管是显赫还是卑微,不管是高寿还是夭折,每个人的归宿都是回到厚重的族谱里,他们平等地在这里大集结,以纸墨书写的形式安静地呈现在子孙后代面前。连绵有序的族谱,静静地流淌着不绝的血脉,像一棵参天大树,开枝散叶,枝繁叶茂。
族谱记载:世樽,正琪四子。生九子。店长(殇)、次子(殇)、三子(殇)、四子(殇)、隆伟、地苍(殇)、双喜(殇)、隆代、隆佳(止)。高祖父一生最终浓缩为短短的三十四个汉字。它们生硬、冰冷,像高祖父残酷的一生。从族谱可以看出,高祖父六个儿子幼年夭折。最后一个儿子隆佳失传,族谱里除了他的名字,找不到关于他的其他任何记载。我再查找他的第五个儿子隆伟,族谱记载他生一子,夭折,从记载的出生和死亡时间计算,隆伟三十岁逝世。
一个男人,一个父亲,面对孩子一个又一个离去,并亲手安葬他们。人世间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悲恸欲绝的?
这究竟是一个怎样坚强的男人?他的身高、相貌和秉性如何?当我反复盯着族谱记载的高祖父的名字及三十四个汉字时,总感觉少了些什么。前后对比,我终于发现族谱并没有记载高祖父的生殁时间,没有安葬地点,也没有迎娶信息。我快速翻阅六卷族谱,每个祖先基本都记载了子嗣、生殁、迎娶、安葬等信息,简单得只有子嗣情况的唯独高祖父一人。
在世命运多舛的高祖父,死后世界为何还对他如此不公!是上谱的人故意漏写,还是修谱的人不慎?这些都无法考究。只是,他的生殁时间成为一个永远的谜团。从高祖父兄长出生于清道光甲午年(1834年),和我曾祖父隆代出生于清光绪癸巳年(1893年)推测,高祖父大概出生于十九世纪中期。
为了解开谜团,我曾跋山涉水、披荆斩棘,钻进深山老林找到了高祖父的墓地。只见祖坟一片荒芜,坟身坍塌凹陷,墓碑倾斜,碑文上的字被风化得模糊不清。我用手掌小心翼翼地触摸陈旧的墓碑,突然感觉一股强大的暖流在血液里激烈地涌动着。
我安静地坐在墓地斜坡上,这里坐北朝南,视野开阔,只见远处层峦叠嶂,天空澄净蔚蓝,蓝得耀眼,偶尔有朵朵白云飘过。
一粒飞扬的尘土,它的归宿是落于大地。
族谱是家族的历史,是家族的精神图腾。树高千丈,本由根生;江河流远,当有源头。一个飞得再高的人,最终都要落到族谱之上;一个走得再远的人,最终都要回归族谱之间。
三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历史长河,大浪淘沙,名垂青史之人毕竟寥寥无几。可是,只要在人世间走过一遭的人,哪怕是平凡的、卑微的,都会在族谱里有一席之地。
历史回到四百年前,这是明朝万历庚申年(1620年)。
这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份。这一年,一个月左右换了三位皇帝。七月二十一日,享年五十七岁的明神宗朱翊钧驾崩,明神宗三十八岁的长子朱常洛登基,称明光宗。可好景不长,九月初一,明光宗因病逝世。
《国榷》记载,郑贵妃“进侍姬八人,上疾始惫”。《罪惟录》也记载,“及登极,贵妃进美女侍帝。未十日,帝患病”。纵欲过度的明光宗身体极度虛弱,卧床不起。太监崔文升进泻药,明光宗服后病情加剧,一天竟然上了三四十次厕所。八月二十九日,明光宗病情进一步加剧,鸿胪寺丞李可灼进“红丸”,明光宗服后,九月初一死亡,史称“红丸案”。九月初六,明光宗长子朱由校即位,称明熹宗。
这一年,我的鼻祖父仕鎅出生。族谱记载:“仕鎅,字景明。生三子,春訄,春先,春寿。明万历庚申三月二十三日生,清康熙甲申二月十二殁。享年八十五。配乐安陈氏,明天启丁卯九月初四生,康熙乙亥正月初八殁。合葬冢坑子虎形,后迁新田鲇形。”
当我翻阅泛黄的族谱,逐字逐句念着记载鼻祖父的文字时,不禁为他的高寿感到无比惊讶。明朝万历庚申年(1620年)至清朝康熙甲申年(1704年)相隔八十四年,鼻祖父虚岁为八十五岁,完全准确。当我计算鼻祖母陈氏年龄时,她享年六十九岁。据相关数据表明,明朝男性平均寿命只有四十六岁,女性平均寿命也仅为五十一岁。
耄耋之年的鼻祖父已是子孙满堂。可是,二儿子春先的婚姻大事一直是他的一桩心病。天命之年的春先一直单身。春先,是我的远祖父。
三百多年过去了,我无法知晓春先单身的理由。或许,他长相丑陋,个子矮小,皮肤黝黑,没有一个女人相中他。或许,他一表人才,才华横溢,眼光太高,他看不上任何一个女子。也或许,他压根儿就没想过结婚生子。我的父亲给出的答案是:家庭贫困,没钱娶妻。可是,他两个兄弟早早就结婚生子了。
祖父在世时经常提到春先老来得子的故事。
当父老乡亲都觉得春先这辈子不会结婚,更不会有子孙后代时,已到天命之年的他竟然结婚了。这无疑像在巴掌大的村庄扔了一颗炸弹,小小的村子变得热闹非凡。
春先的妻子是比自己小九岁的章氏。当时,远祖母章氏也是不惑之年了。章氏,她是一个怎样的女人呢?祖父曾经告诉我,章氏是一个流浪街头的疯婆子。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远祖父把章氏带回家里,给她洗脸梳头,穿上暖和的衣裳,收拾得干干净净。梳妆打扮后,章氏变成一个漂亮的女子。春先望着章氏,章氏也望着春先。章氏泪眼汪汪,最后竟然嚎啕大哭起来。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时值秋末,春先弯腰在梯田收割,沉甸甸的稻子在阳光照耀下,灿烂金黄。春先汗如雨下,他看到饱满的稻穗,不禁联想到妻子肚子里成熟得快要降临的孩子。他用力挥舞手中的镰刀,埋头收割。
当太阳升到天空正中央时,正值午时,屋内传来婴儿的啼哭,声音响亮,传遍村庄。春先丢下手中的稻穗和镰刀,像一只敏捷的兔子一样奋力往家中奔跑。春先看着红润而充满活力的孩子激动不已,甚至不知所措,紧接着情不自禁热泪盈眶,长声哭喊。那一年,章氏四十一岁,身为高龄产妇,她冒着生命危险报答丈夫,为他延续血脉。这个孩子叫作名昱,名是字辈,昱代表的是光明。名昱,是我的太祖父。
两年后,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我远祖母章氏逝世。
四年后,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我鼻祖父仕鎅逝世。
八年后,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我远祖父春先逝世。
名昱,两岁时失去了母亲,四岁时失去了祖父,八岁时失去了父亲。他们化作了一束永不熄灭的星火,成为名昱心中最明亮的地方;他们的身体变成了一条源源不断的河流,融入名昱血脉之中,不断奔涌向前。
四
我小心翼翼地翻阅泛黄而厚重的族谱,目光停留在第八世。历史回到了一千多年前。
这是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年),盛夏时节,蝉鸣阵阵,一个男人带着怀孕的妻子从泗州(今安徽省泗县)前往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赴任。那一年,男人已经五十五岁了,他满脸沧桑,头发白了一大半。朝廷一纸诏书,他奉旨赴四川绵州任军事推官,主管刑狱工作。他的妻子才刚刚二十出头,足足比他小了三十多岁。妻子正值桃李年华,仿若一朵娇艳欲滴的花朵,温婉娴淑,楚楚可人。妻子出身名门望族,知书达礼,看中的是他满腹的才华,正直仁善的性格和他为官勤政廉洁的作风。从泗州到绵州,再从绵州到泰州(今江苏省泰州市),这段夫妻年龄相差悬殊的婚姻,在宦游漂泊之间,因两人相濡以沫,日渐牢固。
从泗州至绵州,一千五百多公里路程,他们走得并不顺利,车辚辚、马萧萧,一路颠簸。一路向西,一路风雨,日夜兼程,舟车劳顿让刚刚怀孕的妻子脸色苍白,一身疲倦,她紧紧偎依在丈夫的肩膀上,一路恶心呕吐。男人自己身体并不好,他被长途奔波折磨得面容憔悴。但男人一看身旁小鸟依人的娇妻,倦意散尽,心生欢喜。
这个男人是观,字仲宾,族谱记载:“周太祖广顺二年壬子(952年)生,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庚戊(1010年)卒,享年五十有九,葬永丰沙溪泷冈蟠龙形向东……”他的妻子是郑氏,族谱记载:“宋太宗太平兴国六年辛巳(981年)生,仁宗皇祐四年壬辰(1052年)卒,享年七十有二,俱葬泷冈……”
是的,他们就是修的父母。
观和郑氏到绵州不到一年,孩子出生了。这是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农历六月二十一日,时值盛夏,天气炎热,观正在为难断的案子苦思冥想,来回踱步于廨舍厅堂之间。一阵高亢的男婴哭啼声打破了夜的宁静,观快步冲进房间,看到妻子生下一个男孩。婴儿面色红润,哭声嘹亮。这个孩子就是修,字永叔。
明月当空,夜色皎洁。年近花甲的观凝望夜空,繁星点点,心中泛起一片光明。
观为政清廉,豁达大度,匡贫济困。修在《泷冈阡表》写道:“太夫人告之曰:汝父为吏廉,而好施与,喜宾客;其俸禄虽薄,常不使有余。”族谱记载,“观居官清廉”。
除夕当天,观处理好案件,收拾行李,怀揣俸禄走在回家途中。此时,身怀六甲的郑氏站在家门口翘首等待,等着丈夫的俸禄购置年货。天空阴沉,大雪纷飞。观在回家路上遇见了一个衣衫褴缕的老人。老人手持拐杖,一边颤颤巍巍行走,一边断断续续哭泣。观走到老人身边,询问她为什么哭泣?老人告诉他,自己还不起地主的巨额债务,女儿被抓到青楼当妓女了。观听后甚是伤心,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全部俸禄送给了老人,叫她赶快把女儿赎回来过年。观回到家中,郑氏叫他把俸禄拿出来买年货。观一摸口袋,才想起自己把俸禄都给了老人。他支支吾吾把事情缘由告诉妻子。郑氏不但没有责怪观,反而称赞他做得好。第二年夏天,修出生了。
小时候,祖父经常给我讲这个观救济贫苦的故事。修在《泷冈阡表》中写道:“为善无不报,而迟速有时,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积善成德,宜享其隆。”祖父在世时常说,修之所以名垂青史,是因为他的父亲观一辈子积的德。祖父告诉我说,为官要清正廉洁,不可拿公家一分钱,做人要施善积德,不可有害人之心。这样,子孙后代才能源远流长。每年春節,祖父在大厅贴对联的横批都是“祖德流芳”,这四个清香端正的大字,透过祭祖的香烛至今依然照耀在我内心深处。
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观带着郑氏和修离开了绵州,赴泰州任军事推官。不幸的是,观在途中染上重病,到泰州不久后就逝世了。此时,修只有四岁。观去世时没有留下“一瓦之覆,一垄之植”。
一贫如洗的郑氏把观安葬在他的家乡永丰沙溪泷冈后,带着修到随州(今湖北省随县)投靠修的叔父晔。族谱这样记载晔对修:“所得廉俸分给孤遗其兄子修,少孤教之,如己出。”
因家境贫寒,郑氏以芦荻代笔、泥沙代纸,教修读书写字。族谱记载:“郑氏守节自誓,慈严兼济,画荻教子。”
这就是欧母“画荻教子”的故事。
族谱,流淌血脉,更传承精神。老家祠堂门楣上悬挂着“理学名家”大匾,赓续着家族“唯读唯耕、忠孝传家”的精神血脉。
五
一百二十多年前,那个叫作世樽的男人——我的高祖父,一次次将自己的骨肉埋葬。是什么力量让他如此坚强地活着?无疑是血脉的力量。血脉,它是一束明亮而纯洁的光,生长出我们继续活着的哲学与诗意。
文,是我同族的叔叔。他原来是一名小学语文教师,通晓文墨和乡村习俗,家族的红白喜事都是他主持张罗。他用笔墨书写乡间的生生死死、喜怒哀乐,在孩子满月、婚丧嫁娶、乔迁祝寿、子女升学的仪式间都能看到他忙碌的身影。我曾在多个场合看到他主持婚礼,他脸上略显喜色,声音洪亮,他大声念主持词,喉结上下滚动。我也曾在葬礼看到过他当司仪,他表情严肃,声音低沉。在出殡前,死者的亲属对着灵牌依次下跪道别。他手持写满密密麻麻文字的草纸在一旁低声念叨,他微弱的声音和哀痛的哭声混为一体。每念完一张,他就把草纸扔进熊熊燃烧的火盆,瞬间化为灰烬,青烟萦绕。
一次次葬礼,文送走一个又一个熟悉的人。他想到死者活着的样子,想到自己也将有这一天,内心不禁伤感起来。让他悲伤的是,谁来为他送行,又是谁来为他端灵牌?
文的妻子生的是三个女儿。第一胎是女儿,文把小学教师的工作丢了偷偷生二胎,可还是女儿。二胎后,文还是想再赌一把,结果还是女儿,他彻底失望了。文的妻子目不识丁,当然不知道生男生女取决于男性,她也总认为是自己身体的原因,并时常为不能给丈夫传宗接代而自惭形秽。
在乡间红白喜事间摆砚挥笔的文表面上受人尊敬和爱戴,他内心也常常油然而生一种满足感、获得感。可是,每次锣鼓一阵喧嚣之后,回到家中,安静下来,他不免有些伤感。
尤其是每到清明,文把族谱从楼上搬下来,他心里就更加难受了。他根本不愿意翻阅族谱,当他眼睛盯着泛黄的纸张留下的“止”字时,他不禁想到,这不就是自己的归宿吗?他眼睛变得模糊,“止”好像长了刺一样扎得他难受至极。他越看越心痛,一个“止”字分明变成一根根尖锐的箭凶猛地朝自己射来。
文的大女儿琳和我同龄,小学同在一个班。琳小时候长得黝黑,嘴里冒出几颗龅牙,成绩不好,小学没有毕业就外出务工去了。三个女儿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文提出有一个女儿要招“上门女婿”,生儿子随他姓。三个女儿谁都想嫁出去,不愿意留在家里“招亲”。于是,文决定三个女儿一起抓阄。这时候,大女儿琳站了出来。她愿意不嫁。
多少年后,我见到琳。她变成了一位皮肤白皙、面容娇好的少妇,龅牙也不见了。冬日暖阳下,她抱着襁褓中的婴儿坐在院子里晒太阳。琳刚出月子,这是她第二个儿子。琳的丈夫笑嘻嘻地告诉我,小儿子随他姓。他和我攀谈,聊东聊西,而之前他是沉默寡言的,绽放在他脸上的灿烂的笑容,足以说明他是幸福的。
文,从此不再忧伤……
同族的善,他的人生似乎就没有文完美。在一个薄雾笼罩村庄的早晨我遇见了善,他正牵着耕牛在乡间小道啃草。这头老黄牛消瘦得吓人,像长期吸鸦片的老人佝偻在大地上,它的尾巴不停地甩打身子,驱赶身边的苍蝇蚊虫。善和牛一样,瘦骨嶙峋,皮肤粗糙、黝黑。善的眼睛患了白内障,他看世界一片模糊。牛,是善在世界上唯一的亲人。在丝丝凉意的清晨,我望着花甲之年的善,他眼神朝向村口。这一幕,让我感觉到村庄的深秋充满无穷的悲怆。
三十年前,村里人都羡慕善。他有一个能干漂亮的妻子,有一个成绩优异的儿子。善的儿子比我年长几岁,英俊潇洒,成绩优异。他经常站在主席台领奖,并作为学生代表发表获奖感言。他声音洪亮,沉稳自信,他的发言无疑每次都会赢得雷鸣般热烈的掌声。他的成绩遥遥领先,轻而易举考上了县重点高中,并分到重点班。
事情在高考时发生了彻底转变。善的儿子高考没有发挥好,竟然意外落榜。他回到家中把自己关在房间,夜深人静时,他哀声痛哭,叫得撕心裂肺。几个月后,他变得蓬头散发,精神恍惚,见人也不打招呼。
他患上了抑郁症。村里人私下里说他发癫了,都远远地躲着他。当时,我正在读高中,没有见过他生病时的样子。他逝世后,我的脑海里一直是他意气风发的模样。他像一只断翅的雄鹰,伴随着一声尖叫,瞬间就从辽阔的天空坠落……
儿子的离开改变了善的家庭的命运,像一阵狂风暴雨把他的家吹得支离破碎。善变得郁郁寡欢,他酗酒,经常喝得酩酊大醉,世间唯有酒精能让他获得精神上短暂的愉悦。几年后,善的妻子离开了他。二十多年了,她再也没有回来。对孤独终老的善而言,活着也许比死亡更难,因为他要背负终断血脉的罪名。
清明,我回到村庄,再次见到善,他显得愈加苍老。他孤身一人坐在祠堂的墙角,眼神迷离,身体蜷缩,像一只伤痕累累的动物。我们在旁边翻阅族谱,追根溯源,寻找自己的来路。
族谱是温暖的,成千上万条血脉在这里静静地流淌;族谱又是冰冷的,一个生硬的“止”字,不仅意味着一个生命的终结,更表明一条血脉的终止,他们在世间的一切,由此戛然而止。我们的归宿是记录于族谱之上,我们的愿望是血脉源远流长。
祭祖的鞭炮声响起,善用双手紧紧地贴住耳朵,他听不见外界的声音。他用患白内障的眼睛看世界,一切都是模糊的。
鞭炮的烟雾淹没了看族谱的人,笼罩了陈旧的庄严的祠堂,村庄的天空烟雾缭绕,但很快就烟消云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