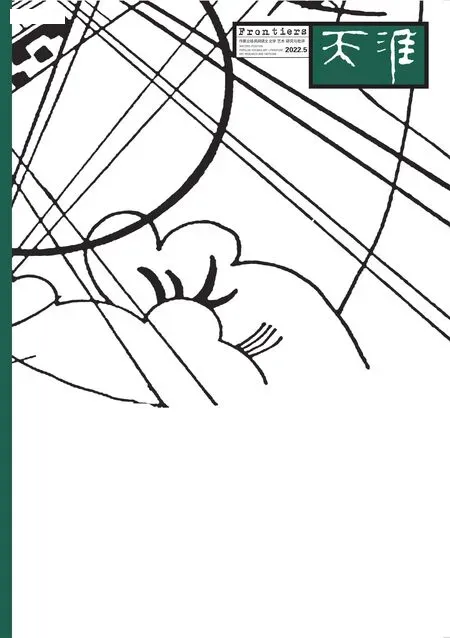韩熙载夜宴秋初凉
栗温
初秋风凉,我与同伴们正备制冬衣。管家过来传话,今晚的宴会要我帮忙。
自然不是列席,我一介婢女,即便在韩府有些年头,也不是可与这群南唐国的达官显贵平坐的。某种意义上,与他们平坐的也有,那都是身怀技艺的人。那如弱柳扶风的,身姿或婆娑或蹀躞、以肢体动情的,那如意气风发的,丝竹或鼓噪或撩拨、以弦音动心的,或抒发他们抒发不得的情愫的,或表达他们表达不出的感怀的。可以说,他们是彼此交心的人。
这府的主人韩熙载,我称之为先生,是因他教会我识字、作诗,我视之如恩师。何止是“达者为先”的先生、师父,他能摒弃这个时代尊卑贵贱的秩序,将其视为“所谓的”,视我为孙女,和他的孙辈一起学习。他已成为我的敬仰与方向。可惜我只是婢女,没有途径为他向世人歌颂。而南唐进入当今皇帝的时代,年逾花甲的先生心志上日渐衰颓,那不是出于他身体的衰落,是他对南唐的伤感泛滥限制了自己的行为。我也逐渐为先生悲伤——昔日的敬仰与方向自己都迷失了,我便更迷惘了。
我见到的时局,先皇帝保大年间接连失地,随后赵宋代周,皇帝屡次向宋进贡;那么,这个帝号可以保留几年,这个帝位又可以坐几年?哪怕除去帝号,俯首称臣,又能苟得几日安宁?我不敢想。我都如此,何况是为君谋的兵部尚书。
南唐,世人所称。割据东南方的小国罢了,不是奉大唐的遗命,如今看来也没有大唐那般逐鹿中原、吞吐天下的气魄与能力。李渊的唐朝国祚二百八十九年,其藩镇割据的末年是唐政权的结构性问题,非一时半会能扭转,于是滋生了许多势力蚕食巨人的尸体,盘踞一方。我的南唐便如是,大唐已故去,如今这偏安一隅的朝廷,只是借唐起势;此势借得不得力、不讨巧,就好似前头所有想借旧势力的名头兴业的朝廷,借来的都是衰颓之势。究其原因,国号、帝号都只是名目,支撑他们野心的建构未能跟上社会的变迁,而一味地为前代辉煌招魂,未能找出此番动荡的本质,那么趁乱而起的他们只能是所求甚大的打劫者,而不能如他们所愿的那般成一番事业。他们不明白,他们能起势,靠的是打劫现有秩序,而他们想成事而兴其业,要能靠重建秩序,而非吃脚下寸土已在乱世消耗得差不多的老本。于是,在乱世中,那些地方政权无论是囿于结构问题而衰退,抑或人事党争消耗了根基而垂危,最终都如走马灯般,三两成群,无序登场,仓皇而退。
只是面对这些,朝廷要员都在叹气的,我一介婢女又能做些什么?至少,从韩府窗棂看出去,看到的天,还是安稳的,只是初秋的风已经足够让人打冷颤,吹得竹叶暴躁,吹散了江左江南的热闹,为它的繁华笼了一层阴影。
不过和别地不同,韩府总是热闹的;即便不热闹,先生也总有办法创造条件,让它热闹。先生有这世上所有文人都爱的追求,只不过他的追求极致了些。他喜欢舞乐、美酒、文墨,这些喜欢建立在他对士人风骨的理解上,就呈现出如今热闹的样子。“今朝有酒今朝醉”,他不惜家财,不谋明日,只求尽兴在今朝。他在家养了不少艺伎,也与太常寺、教坊司的官员熟识,于是舞乐的宴会在家少不了。
他也好客,交友广阔,又因是南唐的三朝老臣,加之精通音律、擅于书画,慕名拜访他的人不少,想与之交好者甚。这不,近两日家里就留了客人。我作为府上资历颇深的婢女,多少有事需要我打点。虽然不是我一人作主,先生又让我不要放下少时习书画的底子,分摊到我的事务不多,但因为在韩府的时间长,总有事情找到我,也总有些事只能我来做。
我是出生在韩府的。先生之所以对我例外,除了他常提及我天资聪颖,还有我祖父的缘故。祖父自然也是家仆,不過那是他后半生的事;先生的原籍也是我的原籍,他的父亲回家乡时出了意外,被我祖父所救,祖父贫苦,因有这份救命之恩,便跟着来到他家,埋下我这份际遇的渊源。
我所谓的天资,其实是一些小聪明。譬如,我擅长记人记事,基本上能做到过目不忘,看得懂唇语,善于观察,行动灵活。这里还有段趣事,幼时好奇,学着舞女的样子练舞,反被他说自己很适合练武。不过我生性贪玩,练舞或练武都太辛苦,我不可能坚持。他希望我掌握的书画,我也少有长进,平常人罢了。
这么一会儿,从偏房走到内厅,我就在内院的景观里察觉了异动。可当我提着灯笼,仔细去看那片菊花丛,疑影却消失了。在洞察力这方面,我不会出错;这儿确实另有人息,哪怕我连完整的影子都没捕捉到。
入了秋的戚家山,尚有夏的余温,只是夜里被竹叶带入了风,起了冷意。秋菊早早接收到江南要变天的讯息,长出蓓蕾;不过时节未至,花也差点火候。往常,还需一个月,庭院就会是热烈的秋菊盛宴;菊是名士,脱俗的它高雅,清丽的它高洁,因可入药还被赋予了吉祥长寿的意象。而在我眼里,她便是热闹的、丰饶的、充满人烟的,或许是因秋日里数它最秀丽,在寂寥里它能带给人安慰与欣喜。先生也喜欢菊花,于是菊花肆无忌惮地开在府上,颇受宠。
走过一小段檐廊,绕过一株黄栌,就到了宴会地。我今天系的丝绦就是黄栌的颜色,在浅色的衣裙上,提了些亮色,好进入热闹的世界。
还未进门,就已经听到琵琶的轻灵,如推给我一番雾气,以踏入这别有洞天的所在。可我还是疑心刚刚瞧见的那团阴影,不知飘向何处,就站在门槛前,张望。
“素哥,站这儿做什么?大人们等你进去。”门里出来一人,拉着我就要跨过门槛,着急得很。
素帛是我的名字,从小一起长起来的人会叫我“素哥”,就好像面前这位梨暖;只因我少时的性子可用“顽劣”来形容,遂得到这个男性化的称呼。
“能有什么事儿,这么急?”我被她拉着,两三步就走到了屋内屏风前。
“李家妹妹的琵琶演奏开始了,你不是想听吗?”她倒是贴心,记得我的喜好。
这位李家妹妹,叫李媺,是教坊副使李家明的妹妹,我要是没猜错,今天李家明也来了。
不过我还没看着人,心不在焉的,就和屏风上的老山松撞个满怀。怕弄坏了它的意境,我用手扶了扶这张折叠屏风的边角,幸而它让我扶。我留神在这棵老山松上,道:“画得是好。”
“我家老爷的笔墨还能差?要不然怎么这么多人求呢?”她的语气,也是全府上下对先生作品的统一态度。或许是待久了,都喜欢上了先生的书画,又或是泡在外界对先生的赞美之辞中,连带我们这些家仆都喜不自胜起来。
梨暖这丫头拍了拍我的肩,说:“我还有事要忙,这儿你来照管。”
她行色匆匆,就为了赶上这府上宴会的节奏。而我向来以敏捷著称,在她走出屋子前,我拉住她的衣袖,说:“梨暖,帮我留意一个人——也可以是一件事。”我也说不清那团疑影是个什么,不过梨暖应该懂我的意思。两人自小在韩府长大,有这份默契。
看她迈出门槛,我才转身走进屏风提示的世界里。和外头初秋气象很不相同,里头被热闹的气氛点燃,一股暖意乘仙乐将我捕获。我扠手示敬,向先生请安。
先生看到我来,将我叫到他身边。他在屋子的里头,坐在一张坐床上,一张小漆案旁,同坐的是状元郎粲。好一个状元郎,意气风发,连坐姿都符合他的境遇。瞧他的样子,真让我羡慕:红袍黑巾,眼神炯然,眉宇里是光亮,举手间是气韵;他拿执壶倒酒,仿佛是拿笔墨挥洒,文明的过去在他的心胸里,生民的未来在他的实践中。我在他身侧站了一会儿,隔着坐床的围屏,投去的尽是钦羡。我是该许愿来生做个男儿,还是该一脚踢了这个无耻的规矩,让巾帼也作幞头?
我没着急走近,先打量了环境。来者都是熟人,有教坊的,有共事的,还有常拜访的。主人肆筵设席,嘉宾拨弦以和,乐音从人声里蹿出,流转入人生里;在座的,各个都在侧耳听,各个听得都不同。而我,却听出了穿越时空的轻灵。杨泉在《物理论》中有云:“皓天,元气也,皓然而已。”若真是皓然之元气,那是否有办法使天的不同状态、不同时态在某种机会下耦合、交叠,实现穿梭,也好让我见见这琵琶声里跳脱出的异世界。
我绕到床榻后,看向里屋,那儿有一张设了纱帐的床,被褥散乱,压着一琵琶。见此,我便唤来一婢女,让她打扫,自己接过她手里的托盘,走向坐床的另一边。托盘里是两注壶、两温碗,来为他们的雅兴助兴。
“我一直在找你。这是你喜欢的琵琶。”先生找我来,不过是为了听琵琶声。
这府上的都随主人,随性。
我放下酒,站在他身旁,随着宾客注目在横抱琵琶的李媺身上。她抱着个四弦琵琶,曲项朝上,用拨子轻挑,身体随乐音而动,观众随她而动。可不知怎么的,原本轻盈的声音突然变得急躁,有序的急营造出了喧嚣,可这平地而起的喧嚣,却没有指向——是演奏者的心境如是,未来的风雨已经吹入她的心头,还是演奏者洞察了局中人的心思,挑明了秋日光景?
我下意识看向窗外,想知道是风卷残云,讓人间陡然凄凉,还是屋内琵琶声乱了心、慌了神,让人不安。可窗外只有树影婆娑于窗棂,缱绻于人群外。这么一会儿,我的疑云又飘了过来,我绕到正门,推铜门环,在门口张望。
“怎么了?”一声呼唤,居然带着股精心烹制的饱满的肉味。
我又遇到了梨暖,她端着一盘香气扑鼻的醓醢,收了我的目光。
她想起来了:“哦,刚刚我都找过了,没有异常。”
“是吗?”我看着托盘上的酒菜,想了想,遂说,“那你再帮我一个忙。”
我轻声耳语,随后出门,绕着屋子看了一圈,确认只有驱赶暖意的秋风。应该是自己多心。
菊花开,石榴也该熟了。我摘了两颗彤红的宝石,捧在手心,想进门,却被一人挡住去路。他扠手行礼,我站在后头对他说道:“朱大人,尝尝石榴?”
姗姗来迟的是中书舍人朱铣,家里的常客了。他本要接过石榴,却被身旁的舒雅拉了过去,一同伴奏。先生的学生舒雅拿一笛子,正在听弦音,准备伴奏,而坐着的李家明早扣上酒杯,拿起檀板,为妹妹的琵琶曲增添音色。太常博士陈致雍坐得离李媺最近,身旁的王屋山见我来,想把我拉来同坐,我推脱:“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喜欢站远点儿看热闹。”
别人来,可能是“听乐”“赏乐”,而我每每在这类场景中就喜欢“观乐”。演奏者为了奏出或急或缓或婉转或蜿蜒的神形,听众沉浸于乐音结界里的模样,他们都是被乐音推着走入另一个世界的,而我就站在烟火气笼罩的地界,看他们的投入,有如欣赏一幅画。我的笔力一般,天赋更是普通,却因从小受训于文人画作,学到了些欣赏画作的能力与角度。应物象形,随类赋彩,乐音斡染宾客的面目,鼓舞折带皴传移士人的兴致,我借形望神,望到了歌舞里帏薄不修的士人热闹中的孤独,也刻意让自己保持格格不入,好保持冷静。
冷静,是我洞察的基础。
不过,曲子还没听完一章,我便慌了。
“我的玉呢?”
郎粲看到我转身沿屏风翻找。
“姑娘,怎么了?”
“我的玉不在了。”
“‘彼其之子,美如玉,又何须再找?”他如此回复。
这样的话,也只有郎粲这样相熟的人说,我能听得下。这一屋子的人里,也只有从他口中说出,才不轻佻轻慢——玩笑罢了。不过他确实是屋子里最放松的人——这里的人,有老迈无望前路的,有无人相识孤独行路的,有技艺逢生别无出路的,还有我这样的下人忙碌而无暇前路的。尚书夜宴的屋檐下,南唐士大夫的交际场所,看似热闹灿烂,稍微被风吹一吹,便揭开了灰蒙蒙的底色。所以,我才羡慕状元郎,能在大好年华放肆,尽享年华大好。他的眼前是光明的,他的笑是明媚的,他的步伐是轻快的,纵然有阻碍、有荆棘,他挥挥手,瑕疵便都听话地隐去了。这样想着,我多看了他一眼。
他正经回道:“长什么样?我帮你找找。”
“您是先生的座上宾,素帛可不敢差使您。”
那是一块饰夔纹的方形玉佩,难得透彻的月白色,陪了我二十一年,据说是先生给刚出生的我的贺礼。玉上饰夔纹本因画风沉重而僵硬,又因图腾刻纹的演变,到了当今时代已经极少应用,更是不入寻常百姓家,只是先生的郡望依然有纹饰此图案的习惯,我祖父于韩家又有救命之恩,于是当年就送了一个同乡的婴孩带故地习俗的饰物。我虽也喜佩玉,但唯独这一块,怕磕着碰着,不是日日都带上,今儿就挂在腰间。在偏屋和同伴准备冬衣时,玉还缠上丝绦,被我整理了一番;走到内院,心生疑影时,脚步迈上台阶,还能听到玉坠扫过布衣的利落声;倒是入了宴会,被琵琶勾了魂,没注意了。
那就应该还在屋子里。我低头找着,大概这动作在听乐的人里最显眼,就被王屋山留意到了。
冷不防,她抓住我的手,说:“素素,找什么?”这称呼,也只有同辈中亲近的人会用。
“欸,你的玉不在了。”她见过我的玉。
她也是喜欢玉的人。她是拔尖的舞者,见过的得到过的美玉如她得到的美誉一般繁多。她这会儿就带了一条饰玉的黑鞓带,衬她的青色衣裳,衣裳有十数层,每一层薄如蝉翼,烛光里、灯火中,走动中有如月影浮动于湖中,而湖中闪烁宝玉。她便是宝玉。
她起身帮我找玉,一瞬间,动静就大了。“媺儿,别为我停下。”我示意,转身隐入折立屏风中。
这次我转入的是另一道门,玉没找到,倒是找到了那团疑影的真面目。
“素哥,人我给你请来了。”梨暖推门便撞见了我,介绍她带来的人,“顾闳中顾大人。”
来人同样是着青褐色圆领衣、带黑幞头,今晚看着却稍显朴素,可能是里头太热闹,我突然看到顾大人,就觉得冷了下来。倒不是他人冷,而是他的装扮和周围的环境所致。顾闳中,画院待诏,作画能力毋庸置疑。我家先生也是擅长书画,又不慕权贵,按理顾闳中与我家先生应该有兴趣相投之处,不过天底下的事多被缘分牵着,没有那么多“按理”的发展。顾闳中与韩府尚无交情,不知怎么的,前两日托了个缘故,借住几日,或许是缘分到了吧。
“哟,今日宴客,怎么先生迟到了?”我明知故问。
“我白天外出,回来得晚,没收到邀请,还不知府上有宴会,是被这位梨暖姑娘拉了来,才发现有这么一出热闹。”
我回道:“梨暖,这是你的不是了,家里有客人,居然没有悉数请来。”
“素大小姐,是我初来乍到,不知府上的规矩。”“大小姐”这个虚衔一般是外人的客气话,见我在府上的待遇有如自家孙女,便给了我这个婢女半开玩笑的头衔。这么说的不止她一个,大概是听到了韩府的熟客如此称呼,便也跟着说了。
“随性便是习惯,您千万别客气。”我将他请进门来,告知先生,又准备了一桌酒菜。
韩府好客,宴客的准备一应俱全,不差一两人的份,我们应对起来方便。府上的人自然知道这两天来了顾闳中,他来赴宴也在情理之中。先生和坐在一起的郎粲见他来,便和他聊了两句,看似很平常地欢迎一位迟来的客人入席。先生还道歉,说是不知顾大人已经从外头回来了,宴席也没等他。
屋子里的人都不知道,或说都表现得不知道,顾闳中其实是不速之客。先生或許是想,一场宴席罢了,府上不少这一场,也不怕多一两位客人。
先生对自己的作风是坦然的。若说二十出头的状元还需要瞻前顾后地思虑,计算自己的前途能否落在抱负的践行上,外界对自己有怎样的看法,自己又能否青史留名;可年逾六旬、有辞官之意的兵部尚书,在几乎不可能实现抱负的背景下,料想于己身于君主的晦暗的前途,逡巡于酒色以避苦痛,加之本性,某种程度的放浪形骸似乎不可避免。我自然是为先生说话的。
可我冷眼旁观,还是会可惜。以酒色自污,污的不止是皇帝的重视,更推却了天下的交托,搪塞了自己的人生与抱负。
总之,虽说是为避世,但沉迷于酒色,确实是先生自己的选择。不过,他的选择并非是在自己晚年的自暴自弃,这样的行径早已有之,不过是遵从本心。“得之则佐时成绩,救万姓之焦熬;失之则遁世藏名,卧一山之苍翠。”先生早年曾如此表明心迹,如今屋檐下的宴席便是他笔下钓鱼者所卧的苍翠之山。
现下,宴会正酣,歌舞正兴,王屋山为众人跳起了《绿腰》。王屋山的舞以迅速与轻灵著称,因她在舞蹈上卓越的理解能力,精密地控制肢体来传达情感,所以《绿腰》这样抒情类的软舞,她的表现依然不俗,这应该就是天赋之人。《绿腰》是唐朝燕乐歌舞大曲,“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幺”便是此传世之作的侧写。我没见过前朝舞乐的绰约风姿,不过仅在韩府,我就看过不少的演绎,王屋山的版本更合先生之意,柔雅而灵秀,缱绻却不失气度,让人痴迷却不沉湎,比寻常的舞更有叙事的能力——只是叙话的是什么事,就见仁见智了。
无论观众从舞里品出了什么,他们都是投入的,投入可忘忧,这是王屋山的本意。“夜晚就只有舞乐,忘了外头的黑蒙吧。”也是个暗夜,她曾这么对我说过。
先生兴起,拿起了鼓槌,如雨点般落在公羊皮面上,为舞伴奏。红色大鼓旁,舒雅拿着拍板配合,右手拿着拍板的最右页,左手控制节奏,注目王屋山。谁的眼神能离开跳舞的王屋山呢?我引陈致雍来近处观看《绿腰》舞,他顺便问我:“姑娘方才在找什么?”
“没什么,是我的玉不见了。”
“玉啊——‘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重视玉,姑娘真是好性情。”
“您真会开玩笑。小女子怎掌万国,珍视玉,不过是珍视它的风骨罢了。”
郎粲右手垂于椅背,转身对我说:“这就是素帛,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她。”
“所以您看,舞我大概是观不成了。”我说着,便瞧见一僧衣,在这人间烟火里格外显眼。
我对来者德明和尚作揖,他回了礼。他和先生的关系非常好,好到可以随意出入府上,更是听过先生掸去官僚与士人外皮留下的真话。“也好,正是避入相之命。”这是先生当时对德明说的话,这并非是他全部的犹疑,却是为数不多能使用的小手段。波谲云诡中,多情无奈,只能以不寻常之为寄寻常之事。
我隐去一旁,在桌案前动笔。这一处侧室,床榻桌椅等陈设一应俱全,又刚好能看到宴会的全貌。我让人多添些烛火,备好桌椅,客人们肯定要坐坐,但在那之前,我还要会一个人。
“顾大人。”顾闳中也在最外围的我这一侧,看上去格格不入,面对韩府的热闹手足无措,有些孤独。
“我不是什么大人。”他摆摆手,朝我走来。
“那我称您为先生呢?小女子蒙恩自幼学习诗画,可惜天资一般,今日遇到先生,不知能否讨教一番?”
顾闳中听了,站定在书案前:“姑娘过谦了,姑娘的字俊气,想必人也灵慧。”
“今日之宴,我本想写些诗句,起了个头,不知怎么接。”
“秋凉夜暮江南路,露浥风凌旧舞衣。”我正好写下律诗的首联。
他抬头观瞧,这儿的位置好,刚好能看见王屋山的独舞。他也只是瞟了一眼,就动笔了。“‘筚篥鼓吹花钿曳,姑娘觉得如何?”
我接了下句:“琵琶轻挑泪烛凄。”
“泪?”他疑惑,“光景大好,盛宴沸腾,蜡烛又在哭泣什么?”
“您看——”我指了指里头床榻边的灯檠,“这长灯檠必设托盘,为的便是盛烛泪;蜡烛只要燃烧求光明,就必然哭泣。”
他笑了笑,说:“夜宴本是件开心的事。”顺而写下一句“主人摇扇嘉宾语,兴起弦音耳外弥”,只是他笑得有些僵硬。
“耳外弥漫的弦音?”我有所思,最后决定直接给暗示。
秋凉夜暮江南路,露浥风凌旧舞衣。
筚篥鼓吹花钿曳,琵琶轻挑泪烛凄。
主人摇扇嘉宾语,兴起弦音耳外弥。
粉本千年逢落墨,可识丹心画相思?
我补完全诗,可他读完只问了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居然还有粉本可传千年?”
“说不定。上古意志传到如今,何止千年,绢本为什么不行?”
“姑娘看得比我远。可他的丹心在思念什么?不然你叫后人怎么画出相思意。”他还是问出来了。
“思念,也是期待,它本来的样子。你看这秋的江南,雾气重重,露水沾湿舞衣,舞姬都徘徊迟疑,何况肩负各种责任的大人们呢?”我放下笔时,王屋山正甩出袖子,结束了《绿腰》。
“姑娘似乎有言外之音,不知是否也是韩……”
我可不想听到他接下来想说的话,赶紧打断他:“秋天的第一阵风到了,婢女也要开始打扫庭院里的落叶,因而有感。”
他自然注意到我刻意转移话题,便取了桌案上的一个漆耳杯,说:“那这杯酒,就当作是我对诗答句的谢礼了。”
他转身,端着杯,继续站回人群边缘不远不近的位置。他的离开让我松了口气,却并未放心。我折起诗稿,收了起来。这诗并非打发时间,而是写给顾闳中的。我之所以与顾闳中聊这么一段,是因之前请梨暖帮我做的那件事。事情很简单,我只是让梨暖帮我请顾闳中赴宴。我在内院花丛遇到那团疑影却遍寻无果后,想起家中客人并未全数在席,刚好遇到梨暖,就让她去一趟客房,请客人顾闳中来。她很快便带了人来,可就是太快了,我问,你们从客房来的?她回我说,那儿,就在内院的三角槭旁。就这么点算不上事的事,让我对顾闳中的来意有个别的猜想。
秋宴自有秋风赴,何事要扬起尘灰,搅了卮里的美酒,扰了兴致。
偏房桌上的酒樽茶杯不止这一个,不只有茶酒,还有吃食,不过不是之前的醓醢类菜品,而是换了爽口的。这儿收拾收拾,可以休息叙话。
我点了一支蜡烛,插在灯檠的上端,这里已经有足够多的烛火,我却觉得还跟不上这满屋的热情。我将帐幔收起,正准备整理床铺,却在床裙底下找到了一把扇子。
一把干干净净没有任何装饰的纸折扇,也就识别不了主人的身份了。
“我的,我的。”梨暖侧身倚在衣架,抢了扇子。
我从来都拿她们没办法,不只是梨暖,是府上所有的婢女,她们总能利用我的心软。而松散的管理或许也是韩府的又一特征,所以盛宴中藏了不少失序的隐忧,可理解为杂乱,亦可理解为活泼。我们没有什么可拘束的。
“先别收拾了,你的玉找到了吗?”我和梨暖吵闹之际,先生竟走了过来,同我说话。
听,这府的主人头一个不喜拘束。但他的一生都在拘束里,不止于此,他还想去参与建立秩序。“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天地之道以秩序立,约束必然存在,就看人如何服从与引导。他想斧正之,却无法发挥万一。
“您先别管玉了……”我接过小丫头端着的盆,伺候先生洗手,顺便打量了周遭,见客人们还没来,压低声音说道,“有件要紧事。”
他看着我严肃的神色,又看向我背后的主厅,说:“我知道你要说的事,不用担心,你放下心事,宴会就是用来享乐的。”
小丫头拿来手帕,梨暖又带了几位歌女,这个靠窗的偏房瞬间暖和许多。
王屋山见到我就说:“素素,这事怎么能让你来。”她端过水盆,我便让给了她。
见主人歇而席未息,我让小丫头随侍,自己走了出去。
“诶,你干什么去?”梨暖眼疾手快,拉住了我。
“找玉。”
“先生叫你来,是让你观舞聽曲的,何必行色匆匆,雅兴可不好辜负。”
“玉不在,我心不安。”我示意她,“你帮我仔细看着。”
梨暖知道我的习惯,也听得懂我的暗示。她本坐在床榻边,听了我的话,起身立在先生旁,有所警惕。
而我去到正厅,找了个绣墩,就坐在李家明旁边。既然要听乐,就离近些听。他拿的还是檀板,正在与五位乐伎试练合奏。我仔细观察他演奏的样子,可能让他觉得不自在,便问我:“姑娘这样看着,是有什么不妥吗?”
“今晚的曲我怕是没心思听全了,先来听个前奏。”
“府上的乐音兴而不竭,姑娘还怕没时间听?”他想了想,还是问出了口,“可是有什么心事?”
我找了个由头:“没什么,我的玉找不到了,心里烦闷。”
不过这也不算什么借口,是我真实的想法。从出生就跟着自己的玉丢了,任谁都会心慌烦闷。那块玉就像我自己。我喜欢听它的声音,就把它放在绸缎上,簌簌如风过山阿;也可以把它放在夜里的窗台上,凝了半夜的霜露,再清澈垂下,如夜只袒露给我的泣诉。它听惯了我的自怨自艾,也分享我的欢欣雀跃,陪我见证过无奈和振奋,见我在失望中探索希望,见我在幼稚里学会思考。它见过我最真的模样,可还没见到我想成为的样子,怎么可以丢了呢?
想着想着,耳边便浮上筚篥的悠扬,我顺道说了一句:“今晚的曲要撇尽了烟火气,越仙越好。”
李家明却说:“难啊。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乐既然是礼之用,这体用关系就注定它无法脱离人间。”
“大人这话似有深意。”我叹道。
“我一教坊之人,能有什么深意,无非研究研究音律。”
“那是我多心了。恐怕是今晚起风了,扰得人心不安。”我明白,我对玉过于敏感了。我更明白,顾闳中的登门扰乱了我的心,我怕这是秋风到来的预兆之一。秋风扫荡江南路,凋敝的不是土地,秋雾黯淡天色,总归有出路,可秋叶葬了一代人的心血,这一辈的心魄也就四散了。我无奈,不是无奈畸形的软弱被摧枯拉朽,也不是花到了凋零之期,道自有人传,花自会再开,只是自己再也无法参与期待已久的盛宴了。
我惆怅之时,见舒雅拿着根笛子,晃到我们中间来。“渊清玉絜,则有礼有法。素帛在意玉,可是有番大道理。”舒雅说。
他的话改自《三国志》,听着是在夸我,可我不喜被与事件无干的人看出心事,于是催促他别的事:“等会儿,这儿可没你的位置,今晚的节目是定好了的,你去找先生去。”他是先生的学生,自然是这里的男性中我最熟悉的一位,说话就随意了些。
“这儿有美人仙乐,我为什么还要往人堆里凑?”舒雅是一个甚为老实的修书郎,今儿也开发了性情。
我知道,总要往人群里去,你我的成就与牵挂都会在那里。可是风霜雨露,已经绊住我们,不知何时能走过去,又或许走不过去了。我知道不该伤一时一人的际遇,可又怎么可能完全摆脱自身的感受,就好像乐器之音,又怎么能真地摆脱人的设计。“就怕是走不到人堆儿里去。”我回答道。
看看这屋子里的人,关上门来自娱自乐,被乐音鼓舞所裹挟的,其实是宴会主人一颗孤独的心。他曾试图在人群中建立秩序,却被推开,于是他又试图疏离人群,就凑到人堆里,折腾一番,到头来落到心里的竟还是孤独。他并非没遇上志同道合的人,只是时过境迁,周遭已无人能读懂他了。这样的境遇还能怪谁?大抵是要怪秋风无情,容不得人半点留恋。
“那就让人群往我们这儿来。”舒雅唤上众人,李家明顺势拍板。
顿时,乐音唤来了尘嚣,驱散了我的孤独。“二位大人今晚的话,让我想通不少。”我作揖退席。
“姑娘,我们今晚都是宴席中人,只聊歌舞,不谈未来。”舒雅劝我。
“希望我也能如此。纵然身份不同,处境不同,你我的际遇都像这席上的乐音,终要散去。只是希望曲或散尽,意犹未尽。”我自己倒没什么,只是可惜了菊花开在秋日里,直面残败,芳华历尽孤独,未能有来日。
可我还没离席,任务就来了。“阿素姐姐,高僧要离开,老爷正在辞别。”小丫头过来传话。
“是,我该替先生送送。”我怎么忘了,我一介婢女罢了,竟操心起尚书大人的境遇来。
我退到屏风后,见一位家伎拿着琵琶出来,打了声招呼。又遇到德明和尚在门口与先生辞行,他今日本未被邀请,来这儿只是撞见宴会。达官贵族的宴席他不是没参加过,即便先生也并不标榜自己在朝廷的身份,高僧的神情也与靡靡之音不合,酒色污得了乐意之人,但染不得自在之境,他便早早地走了。
“我送您。”我和德明迈出门槛。
他却说:“姑娘请回吧,不是还要找玉吗?”
身边的小丫鬟给我递了引路的灯笼,我下了台阶,说:“说不定玉就落在眼前这条路上,素帛也是顺道,大师何必推却。”
“玉或在阁下心中。”走到半道,德明突然说了一句。
我踩着石板上的落叶,听到了秋的声音,顿觉恍惚。
“‘阁下这个称呼不是我能受的。”
“素帛姑娘,你很不一般。”
“如若你看到什么不一般之处,那也是我跟在先生身边,学了些表面的清高,仅此而已。”
“你今晚找玉,找的不只是玉,不是吗?”他叹了口气,“北边的李惟珍,你还记得吗?他是你家先生的故交,七年前去世,前几日正是他的忌日。他故去后,叔言兄每年都托我在此日为他的亡魂祝祷超度,这次来就是和他说明此事的。”
他看似转了话题,其实是直言。宋廷的李谷是先生的至交,两人相识于意气风发青年时,先生渡江之前曾与他有个关乎江山大志的约定,最终李谷辅后周定华夏中原,一取淮南,而先生没有发挥,眼看南唐失去了一道天然屏障,自身岌岌可危。
士人自古都与历史有类似的约定,能流传下来的佳话多数是成了的,先生的约定似乎只能是李谷的成功的对照,烘托气氛罢了。
我若有所思地將德明送到大门口,又说了辞别的话。天气转凉,我要尽快回到屋子里去,去感受那份热闹,来麻痹自己。
回到屋里,灭了灯笼,我找到了梨暖,直奔主题:“刚刚在偏房找到的那把扇子给我,我明儿还你三把。”
“要那么多做什么?我又不卖。”
“那你要什么?”
“我要你写上字还给我。”
“成交。”我的字确实比画要好些,即便都是玩笑之作,不过能如此捧场的,也只有梨暖了。
我溜进此时没人的偏房,见之前磨的墨还没干,思索着要做点什么。我就正对着正厅五位奏乐的人,三筚篥二笛子,筚篥的悠扬领头,将我的思绪带到了外头:是屏风上的山石老松,是窗外黄栌的枝头红叶,也是天外残月的冷辉。
先生敞开衣襟而盘坐于禅椅上,手执扇子,梨暖站在身后,正把自己一把缂丝的纨扇递给身侧的王屋山。
梨暖抬头看见了我,招手想叫我过去。
“还没找着?”她问。
“别提了,刚刚又顺路在院子里找了一圈,大概是真找不到了吧。”
这话被先生听到了,就对我说:“那就不要找了,我再给你一块。”
“那块不一样。”我向来敢拒绝。
果然,他怎么会听不出我的话中意。
“你今天奇怪,我却因理解而劝说不了。要说也只能说一句,玉之五德,我崇‘锐廉而不忮,絜之方也。——玉自在你心中,从未离开。”
“您倒是提醒我了,它或许是经受不住世之浊气,所以走了。”
“总有归期,会等到的。”先生对我说,似乎也是在对自己说。
“只是,俟河之清,人寿几何?”我反问,已然不是在问玉。
“一片冰心,就放在玉中吧。你还年轻,可我已是这年之寒秋……”
梨暖拍了拍我,为我打了圆场:“你看看,酒还没喝,就醉了,都招来了什么伤感的话。”
“也对,是我的错。”我自认不合时宜。
“好了,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宴席将散,哪些客人要留下来,哪些要送,都要你们去安排。”先生没有责备我的多言。
之前我留意的那位顾闳中,留到了最后。我靠着屏风,等着他一一与士人同僚叙话告别,他也看出我在等他。
“素帛姑娘的玉找到了?”
“找不到,不找了。”
“那姑娘既然没事,可否送送我?”
“是该送您回客房。”
“不,我是说我明天就要回去了,方才看姑娘的诗和字颇有意味,想再……”
我打断了他的话:“我一介婢女能论什么意味,只是这儿有把扇子,上头被我写了首诗——拙作难入眼,可我只有这点本事,还请您收下,本想当见面之礼的,但您都说了要告别,那算是我的饯别之礼吧。”
他想都没想,便打开了。其中的诗,我还特意找了个题目,叫作《夜宴赴丹青》。
素帛幸会先生面,粉墨丹青饰我荣。
鼓舞重叠花钿靥,题跋莫忘老山松。
梨暖的扇子制作精良,用的都是好材料,配我的诗文有些可惜。不过只要这诗能入他的眼,也算物尽其用了。
他沉吟片刻,大约读了三四遍,估计不是我的诗难懂,而是惊讶于我一个婢女敢这么说话。于是,他说了一句:“你这是僭越了。”
“醉酒之言,大人见笑。”我看向身旁的屏风,他也随之看到了。
“這儿也有棵老山松。”他指着屏风,扇起了刚到手的扇子。
看来,他是看进去了。
我何曾乐意让靡靡之音掩盖我的抱负,可如今只能托情怀于山松,还请他着墨,消弭我的不安。我本想这么说,却又觉得多余,就闭嘴不谈了。
我一路无言,送他回房,又站在屋檐下,眺望刚刚举办宴会的屋子。那儿还亮着灯,是欢愉的余晖。
一场盛宴就这么结束了。显贵之人与艺人的,士人与南唐的,以及我和我敬仰的人的一场盛宴,草率地收场在秋风扫落叶、筚篥声歇时。
我的玉不在了,它或许是知道将其赠予它的前主人,无奈迷散于悲剧局面无可逆转地迫近时刻,而我也会随之沮丧落魄,于是它提前走了。
礼云乐云,礼乐在我的年代就代表着秩序,这一象征存在了数千年。如今在动乱中,是否就会像我的玉离开我那样,礼乐的象征性也要离开礼乐本身——这一趋势的起因,其实是我们将它推开的。动乱,也意味着变革的契机大开,现在的我再愚钝也能看到不远处的走向,我祝福动荡过后繁花开遍春野,只是我要留在秋之遍地黄叶里了,怅惘那个无法兑现的自己的模样。
“阿素,别发愣了,宴会前你还没整完的冬衣,现在要继续了。”梨暖在转角唤我。
其实,这才是我真实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