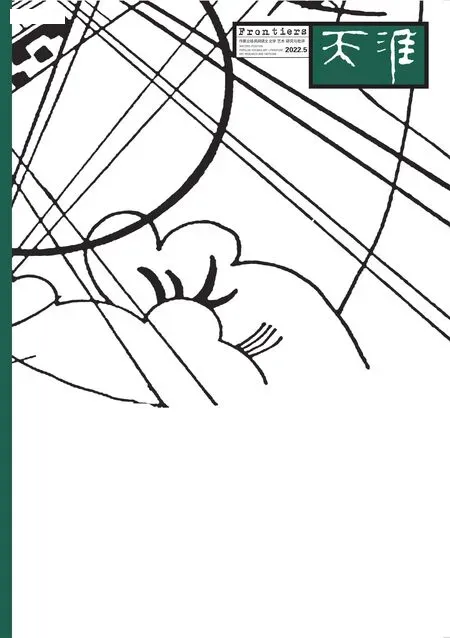出了问题
陈鹏
因此我们长久以来所经历的
都是,或多或少
心甘情愿的,直面生活的
——露易丝·格吕克
没什么事情能让你高兴起来。儿子抬起胳臂晃了晃,你更伤心了。又一个礼拜。又一個礼拜见不着。为什么就不让你送他?长大了?叛逆期?还是,故意和你这个越来越老,脸像树皮的亲妈保持距离?胳膊缩进车窗,不见了。你还站着,113路越开越远,越开越远。你走回来,进小区大门,看门的老张招呼说,走啦?走啦,你说。进单元门,门洞很暗;上二楼,老刘儿子拍着篮球出来,你躲闪不及,篮球撞了你的腰顺着楼道往下滚,小刘大喊一声“我×”,恶狠狠瞪你一眼噼里啪啦往下追。你贴墙站着,一动不敢动,似乎担心他伸手打你。这小子才十九岁,比儿子大两岁,比儿子彪悍多了。你深呼吸,闻见楼底冲上来的灰味。你扭身往上,三楼,门虚掩着,你站下来。明明知道不该站下来可你站了。老方家的门咋开着?你没想明白。你死死盯住门缝。你在打量一件不该打量的东西。门突然被推开,老方的女人大喊,看你妈呀,又想我家老方了?你奔向五楼,步子惊心动魄。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老方女人嘭地砸门,扔出一句更狠的,瞧我不撕烂你,想男人花钱找啊……
501。进门。你死死按着胸口,闭上眼睛,靠着墙。几分钟后你去儿子做作业、睡觉的小间,打开CD机。老掉牙的CD机。《梁祝》淌出来。两只蝴蝶来了,一白一黑,在屋里上下疾飞,在他最喜欢的餐厅圆桌上停了几秒,拖着宽大的翅膀斜逸出去。窗外很亮,光照进来,烙出一块凹痕。那是他日积月累摸出来、压出来的。他说话的时候喜欢在桌上摩擦,像要把花梨木板里外研究个遍。你后悔没把桌子也烧成灰,那样他就能继续抚摸它、依靠它了。可也只是想想。你留下它,每次坐桌前吃饭,坐他坐过的椅子,听《梁祝》你就想他。这种感觉不再强烈,像《梁祝》平缓推进,慢慢消失。有时候连他的长相都模糊了,更清晰的是儿子的脸。都说儿子越长越像他,甚至,是另一个他。比他白嘛,也比他瘦。到底像不像呢?哪像呢?鼻子、眼睛、嘴巴?你也搞不清楚了。你把他们弄混了。瞧瞧墙上的照片,他的照片,活脱脱儿子长大变老的样子,嘴角的微笑特别像。多不真实啊,对这个人,墙上这个,连伤感难过都像假的了,反而觉得他长时间缺席是好事;十年了,不然你真不知道他会不会影响儿子。好影响还是坏影响?他太宠儿子了。你进小间,把音量调大,调很大。就像抗议。向谁抗议,为什么抗议?你不清楚也不想弄清楚。音量冲到极限。嘭嘭嘭。你眼前一闪,两只蝴蝶扎进耳朵,扎进大脑。嘭。什么东西断了。小刘往下,你往上。老方的女人恶狠狠砸门,一把薅住翅膀钉在墙上。黑暗压下来。你知道出事了。你心里很清楚。你带着幸灾乐祸的畅快喊了一声,妈吔。
醒来是躺在沙发上,自家沙发,十几年前的老式沙发,这是一张很宽的太妃椅沙发,倒也让你躺得舒舒服服的。菊姐说,醒啦?喝水,来来,喝水。你看着她,她抄起杯子接了半杯水。你咕咚咕咚喝下去。《梁祝》播放完了。两只蝴蝶,白的黑的还在翻飞,忽上忽下,忽左忽右。你让菊姐打开窗户放它们走,菊姐说,什么,放什么走?蝴蝶啊,你没看见?飞一下午了。菊姐瞪着你,眼窝湿漉漉的,嘴里有酸味。她说,没有蝴蝶,哪来的蝴蝶,小周哟,你莫吓我。你说,明明有啊,你瞎啦,开窗,赶紧开窗。菊姐只好推开窗。两只蝴蝶呼一下出去了,快得像风。你愣怔着说,你真没看见?菊姐摇摇头,又点点头。我咋了?你说,你咋这样看我?菊姐说,她听见你在屋里大喊一声,嘭地摔地上了。幸好,门开着。什么意思?门开着?我的门咋会开着?你的意思是,我的门也像老方家一样开着?是开着啊,不然我咋个进来?你瞎说,咋会开着?咋可能开着?我送儿子回来咋可能开着?菊姐泪光闪烁。好好好,关了,你关门了。你更慌了,大声说,那你咋进来的,菊姐你咋进来的?我没给你钥匙啊,你咋进来的?你死死拽住菊姐的手,像要把她整条胳臂扯下来。菊姐不说话,只是看着你。你想了想,说,我知道了,康康回来给你开的门,对吧?我儿子给你开的门,没错吧?菊姐一声不吭。康康呢?我的康康呢?回来又走了,回学校了,再不走就晚了。哦哦,对嘛,我说嘛,我就说嘛。你四下打量,你很不解,你怎么躺在沙发上。我咋了?你说,我出什么问题了?你告诉我,菊姐,我出问题了?我一定出问题了。我明明坐在桌子边上听《梁祝》呢,还想吃块蛋糕,昨天买的蛋糕,哦,不对,你送我的蛋糕,你早上送我的,你记得吧?我正要吃呢。嘭嘭嘭,什么东西一闪,就好像,钢丝断了。怎么就躺沙发上了?是我家?是不是我家?你挺身起来。的确是你家。就是你自己的家。他在墙上冲你笑哩。不是你家是哪个家?你放心了。你看,这两个人,这俩父子,越来越像,简直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对吧,菊姐?对,没错。菊姐问你,还要不要来杯水。你说,不喝了,喝太多了。菊姐小心翼翼地说,要么,我带你上医院?上医院?上什么医院?我出问题了?菊姐凝视着你,泪水越来越多。她强忍着不让它们冲出来。是,有可能,你可能——她说一半,不说了。
什么问题?说啊,菊姐,我出了问题?我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一定出了问题,否则解释不了怎么躺沙发上的。你知道你和菊姐之间一定被十分钟的黑暗隔开了。你也知道你这个年纪出点问题很正常。没人不在你这个年纪出点问题。很多人,比如他就出了问题,你的亲哥也出了问题。他们都是出了问题但没办法解决问题的典型,反而被问题解决了。还有更多人出问题,老方的老婆不就出了问题?老方自己不也在你面前出了天大的问题?幸好救回来了,幸好被七楼的老董救回来了。你不怕问题,你怕的是没人照顾儿子,你怕的是出的问题不够狠,让你还见不着他。十年了。他胖了瘦了?哟,蝴蝶,蝴蝶又来了。一黄一红。不对,一白一黑,又来了。菊姐,麻烦你把窗子开开,放它们走,赶紧,放它们走,不然会被活活憋死呀。
菊姐说,今天她和她堂弟照顾你。堂弟?她哪来的堂弟?你没意见。你知道你特别害怕,特别无助。有人在是好事,何况是对门菊姐。你说,冰箱里有两棵水灵灵的大白菜,还有三两猪肉、半只鸡。菊姐说,你放心吧,放一百个心。这位堂弟,胖乎乎的堂弟不到一小时就赶来了,拎着一大堆东西;五十不到吧,寸头,肚子滚圆,笑起来的样子有点傻;腰间挂一串钥匙,走路就丁零当啷,丁零当啷。菊姐说,堂弟属虎,四十八了。又对他说,你属兔,属相和八字找人看过,那叫一个合适。她说,你今天出了点状况,一定是累的,一定是累狠了。堂弟说,你们都歇着,其他交给我,都交给我。他一头扎进厨房,丁零当啷,丁零当啷。你担心把蝴蝶吓着,说,轻点好吗?你轻点,你声音太响了。堂弟赶紧把厨房门关上。菊姐说,你没事吧?你说,我没事啊。菊姐说,蝴蝶早飞出去了,我放出去了,你没瞧见?你说,是没瞧见。不过——你使劲瞅着桌子、杯子。没有蝴蝶。飞走了,应该飞走了。菊姐说,你听CD还是看电视?你说,菊姐你等等。菊姐说等什么?你侧着脸,一动不动,然后压低声音,你没听见老朱在吹笛子?菊姐看着你,像打量走丢的娃娃。吹了半小时了,你没听见?哦,哦,听见了,菊姐说,还那么好听,跟十年前一样好听。那是,全厂还有谁吹笛子比得上我家老朱?是啊,是啊,比不了。你们凝神坐着、听着。你问她,要看竹笛吗?我给你看,你要看吗?菊姐摇头,又点头。她还从没看过老朱的笛子哩。你去小间,拉开柜子,往里掏啊掏,端出一只纸盒子,打开,两支竹笛躺在里面。一支橙黄,一支有黑斑,拿在手里很轻,像纸做的。当年老朱每天傍晚坐在阳台上吹它们,两支换着吹,你说不上来他更喜欢哪支,你自己更中意带黑斑的,让你想起老虎和豹子。菊姐说,行啦,放好,你放好,啊!我差点忘了,堂弟会吹呀。会吗?他会?厨房里面传出抽油烟机的轰隆声。菊姐进去又出来,说,堂弟会,我说嘛。哦,那么,不,不行,你说,老朱的笛子,咋能随随便便让人吹?就是,就是,他一个修车的大老粗,吹再好也比不了老朱啊。不过,他车修得相当牛,能把一辆车抖散了,每个零件卸下来再妥妥给你装回去,原模原样装回去,你车子哪里出点毛病,他一只耳朵就能听出来。连排气管松了0.1公分,他也听得出来。他的手艺啊,全昆明,他称第二没人敢称第一,他老板每月给他一万。一万呐,小周。你想想,一个月,一万!你看着菊姐,可惜了,我没车,我们家买不起车,我也不会开车。菊姐说,啊呀呀,瞧我这张嘴,没别的意思妹子,你千万莫多心。你说,不多心,每月挣一万的修车大师跑来给我做饭呢,还多什么心?你把笛子拿起来,又轻又薄,你把黑斑凑到嘴边,你吹出来的是笨拙的噗噗声,比放屁还可怜。收好,你收好,菊姐说。她看看笛子又看看你,似乎担心你把它们砸了。她帮你小心收好,放回去。你突然不明白干吗把它们翻出来。你这么做,意义何在?凭什么给她看老朱的笛子?还问了她堂弟会不会吹笛子,人家会吹啊,你又不让吹啦。你咋想的?到底哪出了问题?
凉拌木耳、糖醋排骨、宫保鸡丁、青椒腌肉、葱花鸡蛋羹、排骨莲藕汤、油炸花生米。不到两小时他就弄出这么一大桌。菊姐使劲夸他,他呢,眯着眼睛使劲傻笑,你想起老家羊圈里的肥羊。他還使劲为你夹菜,碗里堆出一座山了。吃不了啊,你已经不晓得好吃还是不好吃了。菊姐说,堂弟最拿手的就是宫保鸡丁,多吃点,多吃点,不是每个男人都会做宫保鸡丁呀。你咬一口,四四方方不知怎么切出来的,勾芡太多了,黏糊糊的像块抹布。你胃里一阵翻腾。你问他们听没听见笛声。堂弟看看菊姐说,没有啊。菊姐说,我好像也——你看着他们。没听见吗?老朱的笛声,没听见?没有。堂弟摇头。你连排气管松了0.1公分都能听出来,真没听见?堂弟不吭声了,喉结上下滑动,像个白痴。肥羊都像白痴。非要人揍它,咩的一声跳出去。非要人狠揍啊。你又问,蝴蝶,蝴蝶飞出去了?他刚要说话,菊姐连忙制止,说,飞出去了,飞出去了。你往外看,往下看,小区水泥地白亮干燥。你看见老朱脸朝下趴着。十年前他下楼遛弯,一头栽下去再没起来。你像被人狠狠踢一下,又踢一下。堂弟问你,康康周末都回家?你把顶到喉咙的宫保鸡丁强压下去。不回来去哪里?哦哦,我是说——你是说,他不是个乖娃娃?不不不,我就问一下,就问一下。他太乖了,没有比他——你突然说不下去了。为什么提起康康你都会说不下去?也许要说的太多了。这种感觉不像被踢了,更像被狠狠踹着,一脚一脚往背上踹着。老朱那一跤下去一定是这种感觉,一定像是被人踹着,一脚一脚往后背上踹着。菊姐也给你夹菜,你说“行了”太多了。菊姐还是夹,说堂弟心好,信佛,天天烧香念经呐。老婆走了一年了。和你一样,照片还挂着,天天烧香,天天磕头。堂弟埋头吃饭,一脸憨笑跟傻子没两样。好歹吃完,菊姐收拾桌子,堂弟和你并肩坐着,粗短的手指按亮电视。你发现他每根粗短的指关节上都长着黑毛。不多,猪鬃一样稀稀拉拉,再细看,像钉子扎的一个一个洞。你冲进卫生间吐了,他吓得追着问你,没事吧,没事吧?菊姐赶过来,拍着你的背问,你咋啦,还好吗?啊?你不搭理,谁的话也不搭理。使劲吐啊,把宫保鸡丁啦糖醋排骨啦统统吐出来,把另一个你也他妈的吐出来。
两人的目光很凝重。也许被你吓懵了,不知道接下来咋办。你说,我累了,你们回家吧。菊姐说,那怎么行,你一个人,那怎么行。你说,走吧,我没事,我好好的。那我回去,堂弟留着,行吗?你没反对,不是不想反对是没力气反对。不是你出了问题,是他们出了问题。她磨磨唧唧的样子太可笑了,太不像菊姐了。不就介绍个男人吗?不就是她堂弟吗?两人一鳏一寡,完美啊。你又听见笛声,低低的,像雾一样洒下来,沿湿答答的湖岸漫过来,就连丁零当啷的响声也盖不住它。你们没听见?你们像聋子一样什么也没听见?
那我走啦,菊姐巴巴地望着你。远亲不如近邻,用在她身上再合适不过。她让你想起你妈,虽然她们差别很大。菊姐是头一个发现老朱趴在水泥地上的人,也是头一个大喊着冲下去的人。这件事情把你们紧紧拴在一起。你不能想象你身边没有菊姐,有时候又非常希望你身边没有菊姐。她拽开门,就要出去了,就要回对面了。你一下子喊出来,突然喊出来,不不,菊姐,你回来,你回来,你不能走,你莫走!你扑上去,死死抓住她,抱着她,整个人趴在她身上。你害怕,你非常害怕。更恐怖的是你说不出你为什么害怕。你怕得发抖。也许怕再也见不到她了,再也见不到比亲姐还亲的菊姐了。
好好好,不走不走。菊姐吓坏了,堂弟也吓坏了。你扎进她怀里像婴儿扎进妈妈的怀里,你闻见护肤膏的香气,闻见淡淡的汗味,像野地里的金雀花。两只蝴蝶来了又走了。你说,《梁祝》,菊姐,我们一起听《梁祝》,好吗?好好好,菊姐抱着你,像抱小猫小狗一样抱着你。你动作熟练,打开CD,音量开大。你们安静了。老朱望着你们,望着堂弟。大提琴像融化的星星。远处传来人声,传来狗叫。房子像小船一样漂来荡去。从头到尾听完一遍,你看看老朱,看看菊姐,又看看堂弟。你说,康康多优秀啊,菊姐,你告诉他,康康优秀吧?当然当然,菊姐冲堂弟眨眨眼。康康能考清华北大,信吗?信信信,我信,菊姐说。我也信,堂弟说。你对堂弟说,你啊,你不知道我儿子多优秀,没有比他更优秀的娃娃了,我告诉你,我要骗你我周字倒着写,才十七呀,十七就会省钱给我买礼物了——每月我给他三百零花钱,他居然省下五十给我买衬衫,买欧莱雅,买这个那个;我说,康康,你妈是不是老得没法看了,他说,才不是呢,妈妈还年轻,永远年轻。哦,哦,康康。菊姐最受不了这个,声音微微发颤。你知道她受不了这个所以你非说不可。当年野地还没平出来盖楼房,废水塘边上长满金雀花和野番茄,康康五岁那年一脚踩空掉下去了,我靠,要不是老刘发现,要不是老方二话不说跳下去——你心里一惊,咋又提老方?咋又要提他?你又放《梁祝》。反正他们陪着你,一声不吭陪着你。到底咋了?你没问题。你知道你好好的。《梁祝》经常让你流眼泪。最奇怪的是明明听了无数遍,但每次听和头一次听没两样。大提琴一出来,往兜心窝子扎进去,深深扎进去。你又要哭了。他们安安静静的,像要辨认音节的细微喘息和大提琴琴弦的嗞啦声。堂弟去了卫生间,丁零当啷的响动实在让你忍不住了,你说,解下来,你给我解下来。肥羊脸刷地红了,呆呆看着你。你盯着他的腰,说,钥匙,麻烦你解下来。堂弟赶紧解下来放在桌上。你接着讲,康康被捞上来还剩半口气,一通抢救总算活了,嗷地一声吐出水来,你紧紧抱着他,胸膛紧贴胸膛,他肋条那么小,那么硬。晚上你们给老方家送去一只土鸡、一条火腿、一篮鸡蛋。那时候厂区老平房彼此紧挨着。老方的女人不在。老方瞧着你的胸,瞧着你贴过儿子的湿漉漉的胸。你退出去了。老朱啊老朱,你眼珠被狗吃了吗?你硬是瞧不出来?你是瞧不出来,老朱你心太善啦。老方收了鸡蛋,别的一概不要。怎么劝都不要。你心里空荡荡的,能闻见差点要了你儿子命的废水塘的臭味和金雀花香,浓得让人恶心。好吧,好吧,康康你给方大爹磕三个头吧,谢他救命之恩。康康磕了头。老方赶紧扶他起来,身子凑过来,身上有刚洗了澡的香皂味,乘势往你胸脯上蹭,你没躲开。你没太往心里去,毕竟他救了儿子一命。哦,有的话对谁也不能讲,老朱都不能讲,莫说是菊姐和她堂弟。他听《梁祝》的模样很迷茫,像肥羊要被拖出去宰了,把皮剥下来。这个傻子呀,这个大胖傻子。哪能看上他呀?哪有老朱的百分之一?他两条腿,穿宽肥的米色休闲裤的大腿来回抖着,露出膝盖下面深深的折痕。
五遍了。你让堂弟关了吧,不听了。外面真黑,比墨汁还黑。你还趴她身上,小心问她,我咋了?我到底咋了?今天——没事,没事,谁都有撑不住的时候。撑不住?撑不住什么?康康的胳臂晃了晃,消失了。后来呢?后来,你回家,上楼回家,两只蝴蝶窜进来,一道闪电在你脑子里炸了。她怎么进来的?关门还是没关门?到底怎么进来的?好了,不想了,不重要了。她多好啊,多好的菊姐啊。没她,这么多年咋撑得过去?菊姐让你给堂弟看看儿子照片,手机上多得很:康康在学校当主持人、康康在全校大会上朗读诗歌、康康带领新团员宣誓……你一张一张划拉,堂弟惊得合不拢嘴。多牛啊,他说,你这个儿子,多牛啊。你挺直腰板,告诉他,要考清华呢,我告诉你,他就考清华。
头三个月是最难熬的。你睡不着,每晚见他坐在堂弟现在坐的地方吹《梁祝》。吹得真好(可惜CD播放的不是笛子,而是大提琴)。除了《梁祝》还有别的,《姑苏行》《喜相逢》《牧童》,没一样难得住他。天快亮了,他告诉你,我走了,小周。你说,去哪里?他说,湖边。湖边?哪个湖边?老朱笑而不答。当年的废水塘?怎么会呢?怎么可能是那种破地方呢?周围一圈平房,破破烂烂,垃圾遍地。怎么可能呢?你问他,你不想儿子?想啊,很想,我在湖边等你们。那天之后,他就不来了。你后悔啊,咋非要跟他讲话,讲完了又何必问他。否则,他隔三差五还会回来,还会坐在桌边吹他的黑斑竹笛。你坐下来听着,你听着就够了。那之后只能听CD了。刚开始不习惯,后来,你发现你不单单在想他,还想康康,想别的,他在大提琴声中一步一步退出去。终于,你看不见他了,也不再计较他来还是不来了。反正他就在墙上,一直在,一直冲你笑着,笑了十年。
来的是老方。他和菊姐一起来,临走把一个牛皮纸信封留下,你不要,他非给不可。你不再拉拉扯扯了。他低头告辞。菊姐帮你数,两千元整。你说,咋能要,他救过康康一命呐。菊姐说,收着吧,收着,老朱走了,低头不见抬头见,哪有把人家一点心意往外推的道理。凌晨一点有人敲门,你以为是菊姐。不,还是老方。他说就讲几句话,讲完就走。你只好让他进来。他说,妹子,我睡不着,一直睡不着。每晚躺下去有刀子戳我。你问他,为什么?他说,也许,老朱就不该列在解聘名单上呐!但是我,我他妈的——你问他,到底什么意思?他一屁股坐在桌子边上,坐在老朱每夜吹笛子的地方,两手捧着脸,手拿开的时候你见他哭了。他说,我告诉你啊小周,我他妈的不是东西,真不是东西。我,我该走了。你说,你还没讲完哩。他说,讲完了,老朱的资历、为人、技术都是这个。他伸出大拇指,接着说,该走的没走,该留的没留。怨我,都怨我。你把钱还他,他坚决不干,不不不,小周你这是要我命呐。他拔腿就走。你又闻见他的香皂味了。康康醒过来,问你,哪个来啦?你说,哪个也没来,你接着睡,儿子,你接着睡。
该来的必然会来。你偷偷打量堂弟,这个胖子啊,咋看起来那么老呢,一个傻乎乎的修车胖子,一身油臭再也洗不掉了。现在到处是这股味道。现在身上飘出这股味道的男人还没有一点要走的意思,还在陪你坐着,东一句西一句。你问他们,蝴蝶又来了?大晚上的哪来蝴蝶?菊姐说。有,你说,刚飞进来,看呐,停桌上了。没有嘛,早飞走了。菊姐拍拍桌子。蝴蝶呼一下往外串,你蹦起来,想抓住它们。一只也行啊,眼瞅着就在手边,呼,闪电一样射进黑暗。你说,你们没瞧见?白的雪白,黑的漆黑。看见了,看见了,菊姐说,飞走了,太晚了,它们回家睡了。你要睡吗?不,我不想睡。那你看电视?我们陪你看电视。你说,你陪我就行,菊姐啊,你让堂弟回去。堂弟挠挠头,站起来说,好,好,那我回了。菊姐说,行啊,床我给你铺好了,你洗个澡,有太阳能热水。堂弟开门出去,你听见对门打开又关上。菊姐说,十年啦,小周,你不能一直这样。他不错,我堂弟,很不错。钱不用担心,我说了,今后工资卡交给你,每花一分钱都给你打报告。菊姐你说哪样哟,不行,十年都过来了我还找个屁的男人哟。你听我一句,再这么下去,不行。人有血有肉,不是机器,你不能——不不,菊姐,这事听我的。你听我给你讲讲三年前那件事吧,我没跟任何人讲过,我今天跟你讲。嗯,三年前,老方摸上来,不是头一次了,第三次还是第四次了。他硬闯进来,说他对不住老朱。他每次都这么说,对不住我家老朱。三年前,他说——你犹豫着,要不要告诉菊姐。其实你知道他们早就晓得了,问题是他们晓得的不是真相啊。哎,说吧,说出来,都说出来——嗯,老方说他喝了点酒,又从怀里掏出个信封,少说一千吧,塞过来,然后说他想看看老朱的笛子,说他多想念老朱的《梁祝》啊。我不要他钱。他不管三七二十一,硬塞进柜子里,笛子抄在手上,坐下来,开始吹它。康康那时候住校了。三年前上初二,已经住校啦。我真没想到啊,他吹出来的和老朱一模一样。我一听就哭了。他反反复复吹《梁祝》。他记得我最喜欢老朱的《梁祝》。吹完了他讲,他走了。他讲这话明显想让你留他。可咋能留他呢?他家就在楼下。你突然听见他说,他老婆刚住院,家是空的。你问他,出什么事了,住院?前几天不还好好的,还在楼下见过笑眯眯的,多么和善的美人呐。老方戳戳脑袋,说,这里病了,这里,像钢丝一样,啪就断了,说有人举着大刀砍她——他叹气,比起她来,老朱是幸运的。这话让你很难受。然后你突然瞅见一白一黑两只蝴蝶,当年还不像今天这么大,这么漂亮,淡得像风的影子。你刚要说,看呐,看呐,蝴蝶!老方突然硬着脖颈拽你的手。你吓懵了。那只手凉凉的,你不敢想象如果它热得烫人你该咋办?他说,马上走,马上,不给你添麻烦,我决不给你——菊姐啊,事情就是这样,绝对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天晓得到了别人嘴巴里就变样啦,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啦。菊姐抬手摸你的脸,说,你瘦了,太瘦了,我心疼啊小周。哎,老方人不坏。什么呀,你听我说呀,菊姐,他拽我的手我使劲推就是推不开,他像老虎钳子一样把我死死钳住了,一只凉飕飕的手从我衣领伸进去摸我。——菊姐瞪着你,像不会呼吸一样瞪着——然后,他砰地一声就栽下去了,就那么直直栽下去……幸好啊,七楼的老董在社区医院干过,以最快速度救了他一命。事情传开了,说哪样的都有啊。老方的女人恨不能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哎,小周,菊姐长长叹气。我倒真希望你和老方睡了,我倒真希望他——你说哪样哟,菊姐!你一下子怒了。这不是你想讲的,重点不是这个,重点是你从没干过任何对不起老朱的事情。一丁点也没有。否则天打五雷轰呀,老天爷是睁着眼睛的。你每天早早出去,在厂门口飞鸟影楼煮饭做菜,中午一点过就能回来。每天的活就那么多,不算累,下午你把屋子收拾了再收拾,地板拖了又拖,然后出门走啊走,每次五六公里。他们说你瘦了是走太多了。不跟不三不四的人说话。从不。几个二十左右吊儿郎当的小半截儿坐栏杆上对你吹口哨,你回头骂他们,给老娘闭嘴,回家对你妈吹去。后来再没有小半截儿对你吹口哨了。你故意往那邊走,他们要么装没看见,要么一哄而散。你又气又急,像丢了什么东西,想找回来又故意不想找回来。亲戚朋友介绍男人给你,你一概推了。十年了,你不让任何男人插在你和康康中间。不行。你要把他带大,要考北大清华。不行。连老方也不行。所以他拽你的手摸你,你叫得惊天动地,差点要了他的命。好好好,老天爷是睁着眼睛的,菊姐说,问题是,你的老天爷已经让你守了十年寡,你要不要问问他,猴年马月是个头啊?你问问他,必须问问他。死人已经死了,哪还管得了活人?你是活的,儿子也是活的,你们必须好好的。再这么下去绝对要出问题,而且你已经出了问题,我的小周啊。你瞪着菊姐,瞪着她红彤彤的眼睛。你叫起来了,像被鞭子抽在脸上。那种感觉回来了。嘭嘭嘭。钢丝越绷越紧。她咋能讲出这种话呢?咋能讲出来呢?菊姐死死抱住你,央求你。你挣扎,反抗,你叫,你大叫。能活活把房顶拆了。堂弟从对面冲过来,你见他就骂,我×你妈,我×你妈吔。老娘的事情要你管?要你管?
好半天才静下来,是笛声让你静下来的。堂弟,肥羊似的堂弟吹的正是《梁祝》。和老朱一模一样的《梁祝》。你呆站着,脸上又湿又热。蝴蝶呀,你们看见了吗?两只,一黑一白,一只白天,一只黑夜。屋里很亮。外面也跟着亮起来了。
你吹得好啊,真好。是吗?嘿嘿,谢谢,谢谢表扬。菊姐说的时候我还不信,以为她诳我呢,以为你们拿我寻开心。咋会嘛,哪个敢拿你寻开心嘛。楼下老方也吹过,没你好。嘿嘿,我从小就吹,十岁,十岁不到。那时候就吹《梁祝》?不不,后来学的,专门找人学的。老朱没找人学过,自己瞎吹。可我姐说他吹得相当好。是啊,相当好,好得不能再好啦。是,我姐说——嘿,你看,蝴蝶!哪里?你一直说蝴蝶,可我和我姐都——它们追着《梁祝》来啦,你没瞧见?喏喏,你过来,过来!啊,瞧见了。你快开窗子,放它们走,快放它们走。为什么?刚来怎么就走?因为喜欢呀,你喜欢它们就必须放它们走,不然它们会被憋死的,会活活被憋死。好,好,放它们走,我放它们走。
屋子大了,也空了。你在这头,他在另一头。你聊康康,聊楼下老刘、老马,聊楼上老董、老江。然后你问他,老婆怎么走的?他讲,癌症。乳腺癌。啊呀——你叹口气。相片也在墙上,他说,跟你家老朱不一样,彩色的。哦,那么,你说,你咋想?想什么?他说。你没吭声。废话呀,何必问他?你要他回答还是不回答?其实你很不习惯更不喜欢这种感觉,家里坐进一个大男人的感觉。你紧张又难受,又盼着不必马上结束这种紧张和难受。你聊老方的女人,从医院回来人就变了,见谁骂谁,要么说家里丢东西,要么走三步退两步管一楼小丁的三岁娃娃叫妈。骂你的话最难听,非常难听。你都不好意思说出口。堂弟说,知道。你说,你咋可能知道?堂弟说,我听我姐说过啊,再说——他低下脑袋接着说,你那么漂亮,硬是挺了十年,我咋可能不知道?你问他,什么意思?你夸我漂亮?我听见你夸我漂亮,你的潜台词是什么?堂弟说,我没什么潜台词,我的潜台词——太晚了,蝴蝶飞走了,笛子躺在桌上——你嫌我老?又老又丑?不不不,你莫理解错了。你就是嫌我老!冲我吹口哨的小半截儿都不敢嫌我,你嫌我老?我真没嫌你老,我发誓。堂弟满脸通红,将钥匙串挂回去。你讨厌这个动作,更讨厌这件东西。你说,你什么时候学的笛子?小学,他说,九岁多十岁吧。哦对,想起来了。他说,我姐讲,我很像你家老朱。脾气性格,爱玩的乐器,爱听的歌,都像,所以——你半天没吭声。他哪像呢?那么胖,腿那么粗,一身的油臭。老朱绝不这样,老朱收拾得干干净净,腰板笔直,哪像他?你回头看,夜里他更生动了,直直望着你,望着堂弟,目光悲戚又温柔。三年前,老方出事那天,你是因为他摸你大叫的还是受不了老朱的目光才叫的?是后者吧。你不确定,又相当确定。堂弟拿起竹笛,仔细端详着。他说,人嘛,还是要往前看。你想大笑。听这种话耳朵都磨出茧子了。你说,男人呐,你们男人。堂弟看着你,眼睛还算好看,亮亮的,黑黑的。我姐说,我老实,手艺不错,能修车,能做菜,能干活,会疼人,还会吹笛子,像吗?真不像?你半天没说话。你听见蝴蝶擦着头发丝飞走的呲呲声,像撕破什么东西,像翅膀断了。堂弟走过来,拉你的手,你没躲,也没喊。蝴蝶上下翻飞,一只前一只后,速度明显慢了,停在桌上,停在笛子上。两片厚嘴唇贴上来的时候你也没躲,甚至迎上去了,你战战兢兢像头一次那样浑身发抖,害怕得发抖。怕什么呢?你随手把灯关了,不能让老朱看见呀,绝不能。一片黑暗。丁零当啷,丁零当啷。你真想把他的破东西扔出去。蝴蝶飞起来,又薄又大的翅膀比钻石还亮。胖子终究是修车的,有的是力气,一把抄起你来去了卧室。你一直抖啊抖,你赤身裸体的时候忽然觉得老方的女人骂得对。蝴蝶绕着你飞。来不及了,来不及放出去了。你狠狠骂出来,一个字一个字蹦出来。堂弟哼哼着,这头肥羊,哼哼着,手指拂过小腹,关节上的毛根根直立,像一排阴森森的獠牙。你觉得他闯进来了,你惊异又迟钝,像斧子砍进肉里,像拉毛的墙塌下来,连疼痛也是粗糙的。然后你躺着,一动不能动。堂弟穿好衣服,钥匙串又响了,丁零当啷,丁零当啷。他回头看你。太黑了,你不能分辨这个人形。你问他,你要去哪里?他不回答,幽灵一样穿过客厅走到门口,身影堆在黑暗中。你要走?你忽然意識到一个男人,十年来头一个男人刚来过就要走了。似乎有光躺在地板上,窄窄一小绺,像支笛子。你感到羞耻,深深的羞耻。我走了,他说。去哪里?你说。回去,回对面,他说。你每天都给你老婆烧香?他没吭声。我给老朱烧香,你说,我也天天给他烧香吧。这个胖男人嘶嘶喘着,倦怠而恼怒地打开门,行了,我走了。你直起身,像在威胁他,什么,你说什么?你听不懂啊,你听不懂我讲话?哦,我忘了你有问题,你这个地方,有点问题。黑暗中他抬了抬手。你听见门开了,他走出去,哐当一声,关上门。丁零当啷,声音又细又小,可你还是听见了。你听得真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