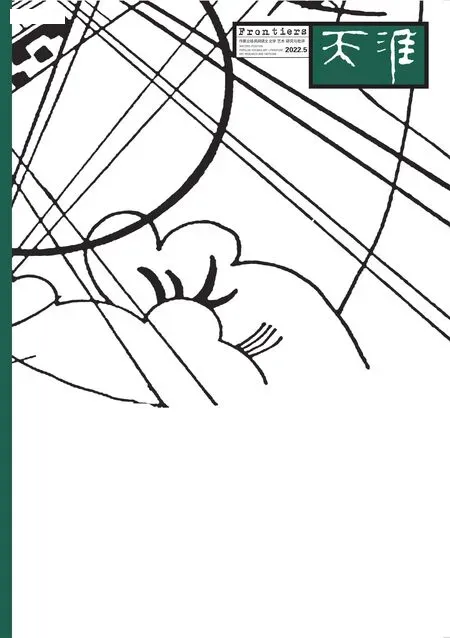云彩剪辑师
李宏伟
阿懒并不剪辑所有的云彩。有空又有心情时,他会推开门,来到狭长的阳台,将酒放在玻璃条桌上,躺进白色的塑料躺椅,望着天上的云彩出神。谁都不知道阿懒在想什么,他那样子本身就像一朵云。要是房东胡伯恰巧在这时从三楼阳台探出身子,就会喊一声阿懒,问他,你现在飘到什么地方去了?问完,胡伯抬头望一望,想认清哪一片云彩是阿懒,但总是确定不了。直到胡伯缩回房间,阿懒也不会回答,更不会动一动。
动的话,常常就是拿过酒来。阿懒喝酒不挑,根据手里的钱,依据当时的心情,下班路上,拐进那家专营酒的便利店,将酒塞进老T递来的布袋,拎回来。有时,他刚走到门口,布袋就已经在老T手里,里面装着一两瓶酒,他依老T说的数递上钱,回家再打开。老T选的酒总会带来不一样的感受,仿佛事先洞悉了什么。不过,这种情况不多。一般情况下,老T都让阿懒自己看,自己拿。便利店不大,酒的品种却多到令人眼花缭乱,有时让阿懒感到新鲜,有时让阿懒感到疲惫。新鲜或疲惫到头,便随手抄起一瓶。要刚好是啤酒,无论哪一款,老T都会露出一脸搁不下的嫌弃,非得赶紧将它藏进布袋后,才找钱,才搭话,就好像那酒不是他进的货,而是谁寄存代售的,阿懒更不是他的顾客,而是他不争气的儿子。
拿过酒来,举在略高于目光平行处,阿懒凝视,等待酒安静下来。要是喜欢漂浮沫子的酒,便等待每一个泡沫破裂、消散,酒面与酒杯归于阒寂。有时,这需要很长时间,还得保证手的稳定,不会晃动或抖动,以免催生新的泡沫。阿懒有的是时间,定力惊人,这样总会等到那一刻到来。整个酒杯安静如一块石子,除了天生的透明或者自带的颜色,乃至一片静默的浑浊外,无法从被等量齐观的空中区分开。阿懒用这样的酒对着或远或近,或浓或淡,或厚或薄,或者干脆懒得形容的云彩。哪一片云让他心里一动,无论是喜欢还是讨厌,他都注目其上,多看两眼,便能从中发现不足,至少是他不满意的地方。先在心里勾勒,差不多时,将酒杯举到面前,低下去,再从酒水的倒映中,找出那片云,另一只手的食指在倒映的云影上轻轻划动。
再看那云,依从阿懒的动作,温馴地舍弃被他剪切的部分,卸去负担般更轻逸地流荡起来,要么就是更专注地行起当行之事来。这时的阿懒已经不关心那云,他只盯着杯中的酒,颇为紧张,颇为期待,仿佛这是新酿得的,至少也是刚用全新的手法调制而成的。看上好一会儿,他举到嘴边,呷一口,让云彩的味道在口腔游走。随后,顺从咽喉落入胃里,扩散至全身。等上三五分钟——大约是被一朵云托起来的那个时间,阿懒便会露出满意的神色——到目前为止,他没有不满意的。谁都知道,每一朵云彩都是独一无二的;阿懒知道,他每一次的剪辑手法都是不重复的。两相重叠,怎么可能不是一杯值得用更多耐心去品味的酒呢?
当然,事情没有说来那么简单。云彩不是阿懒的专供,可以拿过来随意把玩,他必须考虑剪辑带来的后果。二十岁那年,教会阿懒这一切的那个女人让他离开自己的屋子,并且不允许他再登门。女人说,他应该去看看远方的云,品尝它们的滋味。更重要的是,领会一下,动一朵云彩对不相干的人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女人还说,你不可能知道每一次剪辑的后果,但你必须事先知道,一定有后果。那时,阿懒还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说这些废话。他甚至认为,她不过是在敷衍,不过是在戏弄,她只是为了赶他走。他的心里充满了愤怒,乃至对女人的恨。
后来阿懒明白了,可他已不愿再想那么多,他不过是品尝一下云彩的滋味,打乱一下它们的顺序。偶尔,他也通过那些简单的手法,改变一下云彩投射到地上的影响,寻得一点无关紧要的乐趣——至于后果,总会有后果的,什么都不做也会有后果——只要适可而止就行。现在,阿懒就看着从马路那头走过来的那个女孩,看着在她身后五六米远跟着的那个男孩,想着怎么给他俩捣捣乱,如果能顺带帮帮那个男孩更好。两个人都十五六岁,每个周一到周五,女孩早晚从楼下经过一次,阿懒知道,她早上去的那边有一所学校。男孩通常会在黄昏,在女孩回家时,跟在她身后,远时十来米,近时两三米,从来没有过肩并肩。现在,男孩如往常那样小心,不让自己的身影与步子惊扰到女孩,但他的小心并不畏缩,谨慎中带着坦然,仿佛在宣告,他对女孩负有的责任。
女孩是知道男孩在的,阿懒对此洞若观火。阿懒还知道,女孩有些左右为难。毕竟,要是男孩更勇敢一点,或者说鲁莽一些,她反倒应对有策。或者说,如果这是男孩第一次跟随,她也知道怎么办。现在,两个人已经用不远不近的距离、不咸不淡的沉默,筑起一道柔韧的防护圈,轻易撕扯不动。推不开,走不近。眼看着女孩走到楼下,看着她很快会走到这条马路的尽头,在十字路口拐弯,阿懒不禁站起来。男孩走近了一些,但还是离着两个身位,这是突破,也是突破的极限。阿懒知道,决定性的时刻将要来临,要么女孩接受男孩,两个人并肩而行,要么女孩继续沉默以对,男孩转身离去。
阿懒抬头望,日头在加速向西奔去,可离到达山顶还有好一会儿。城市的上空是一大片摊开的白色的云彩,刚好挡住尚有余味的阳光。阿懒拿过酒杯——这次是老T特意推荐的一种蓝宝石颜色的酒——望进去,云彩都仿佛被洇染成了天空之蓝。不,比天空之蓝更蓝。左手持杯,右手拇指、食指、中指并拢又伸开,反复几次,杯中的云彩得以放大,突出他选中的位置。女孩已站在十字路口,准备拐弯,男孩则并住脚,显然准备以目送道别。阿懒瞅准时机,在绿灯亮起、女孩犹豫一下往前跨步时,他的手指按住选中的那点云彩,往杯子里滑动一下,一点白掉进蓝里,仿佛冲淡了酒。随着那一点云彩的消失,女孩头顶上的天空漏出一条圆柱体的光,将她罩住。女孩吃了一惊,随即接受这启示似的,身子歪了下去。正在转身,但目光仍未脱离女孩的男孩,体内的弹簧瞬间被触动,扭身、跑起,一气呵成地冲上去,完成他酝酿已久的动作,抱住女孩。极其短暂,两个人身体在触及彼此的同时分开,但他们迎着绿灯闪烁的提示,终于并肩走了过去。
阿懒没有再追看男孩和女孩的背影,他一口饮下杯子里的酒,在杜松子的味道中,用舌尖感受那一团即将消失的白云的味道,它上面一层被阳光持续照晒的热已不强烈,但依旧隐秘而绵长。随着吞咽,一种旧日的带着灰尘的暖意,漫延于体内。接下来一段时间,阿懒经常看见楼下马路上女孩和男孩的身影,有时肩并着肩,有时手牵着手。大多数时候,是在黄昏时,从马路的那头,学校的那边走过来。偶尔,是在早晨,男孩先骑着自行车从那边呼啸着过来,不一会儿,女孩也骑着自行车,和他一起再从这边缓缓过去。极少数时候,两个人或者骑着一辆自行车,或者就那么手拉着手,在马路上溜达够两三个来回,才道别分开。看着道别之后迈着大步幅的男孩的身影,看着他走到最后总会跑起来,阿懒忍不住就会干掉杯子里的酒。
这天下班进到店里,老T没有如往常那样递过装酒的布袋,而是看着阿懒,几次欲言又止。阿懒看着老T,静心等待。终于,老T挠挠头说,明天晚上有空的话,在胡伯家喝酒。三个人一起喝酒的机会不算多,可绝对不需要这么扭捏。阿懒没吭声,继续看着老T。哎呀,老T更加不好意思起来,明天是胡伯的生日。哦,阿懒点点头,我下班就过来——需要做什么特别的准备吗?老T再次挠挠头,为难地看着阿懒,不是要礼物,胡伯很想他女儿,要是……阿懒截住老T的话,要是他女儿能回来的话,胡伯会高兴得跳起来吗?说完,阿懒自己先笑了,他想象着七十多岁的胡伯,像个孩子那样高高跳起,稀而长的银白色头发在脑袋上飘荡、起落。老T瞪阿懒一眼,回来是不可能的,能来个电话,道一声生日快乐,胡伯就心满意足啦。
怎么,父女俩有什么心结解不开?阿懒听胡伯唠叨过一两回,知道他有个女儿,自租住以来却从未见过,虽然奇怪,但也没多想,更不好问。既然老T说到……心结这种事,谁知道呢,你以为还是一根线,谁知道别人什么时候就打上结了,就算是你的老婆、儿子,就算是你的掌上明珠,你又怎么能知道呢?老T说着,往外看了看,并没人来。胡伯女儿小时候,跟他可亲了,他走到哪儿女儿跟到哪儿,胡伯也真疼女儿,从来不说个“不”字,脸色都不舍得变一下,永远笑着对她。老T声音低下去,咕哝几句,才又意识到阿懒在,声音高了起来,谁知道后来就不来往了。我能做什么呢?阿懒望望门外,淡淡的霞光散落在地上。不用做什么,老T摇摇头,我就是和你说说,你进来之前,我刚给她女儿打电话,想提醒一声,可拨打两次都没人接,便再没力气打了。老T停顿好一会儿,恢复些精神,不是要让你来打,明天晚上,别提这些事就成。
第二天,天一直阴着,阿懒加了会儿班,处理完手边事走出公司楼时,预报了一天的暴雨仍旧卷在天上。走到便利店前,老T早已关门而去,阿懒在门前站了会儿,想起前几日买的啤酒还有两罐,便走回去。到家里,刚从橱柜里拿出那瓶多年带在身边的白酒,敲门声就响了起来。老T站在门口,不太高兴的样子。你总算回来了,我一个人面对胡伯,真有点扛不住。胡伯站在厨房的窗户边,望着又暗去几分的天空,那身影比天空还暗。桌上摆着一堆带壳花生、一碟开心果、一盘洗净没切的黄瓜。三只酒杯,其中两只已然动过。阿懒打过招呼,依着老T的话,坐在朝向窗户那一边。天上的云在加速流动,要不了多久雨肯定落下来。胡伯转过身,看着桌面,似乎生出歉意。本来想做几个菜,实在……
这样挺好,就喝点酒,聊会儿天。老T早就倒满三只杯子,趁势端起,向着阿懒,说,胡伯的厨艺那是没得说,一道菜你吃了无数遍,下次仍旧像第一次尝到。胡伯笑着举起杯,你直接说我只会那几样不就得了。他又向着阿懒,早年好琢磨这些,现在懒得动了,过几天吧,我来整条鱼。谢谢胡伯——阿懒举起酒杯,顿一顿,祝胡伯身体健康。三个人喝下去,各自倒上,阿懒正伸手去抓一把花生,一串雷炸过来,回音未绝,雨便赶了下来。到处都是雨水击打的声音,迅速由滴变成串,一股薄薄的湿气入到鼻中,内中夹杂的灰尘的味道散开,有些呛人。胡伯偏过头,望着雨以及挂下雨水的晦暗天色,出着神。阿懒看着老T,老T正示意他别说话。两人目光还没交接到第二个回合,胡伯已回过头,举杯碰过来,干掉这一杯,又去倒上一杯,举起。
接下来喝得就更快了,还没说上几句,一瓶酒已没了大半。像是配合他们的节奏似的,雨还在加大速度,哗哗的声音带着爆裂声,电闪雷鸣都难以从中突围,仿佛整个小城正被由上往下地吞没。小城之外的世界,早与雨水沆瀣一气。老T一边示意阿懒不要担心,只管配合胡伯的节奏,一边东拉西扯些笑话闲篇。老T成型的话不多,不一会儿,流浪汉到他店里骗酒喝的故事就讲上两遍。阿懒听着老T的絮叨,勉强配合着。老T总算意识到了尴尬,连连向阿懒递眼色。阿懒正愁着不知道讲什么时,胡伯开口了。胡伯问,你们见过空心的雨吗?问完,又另起一行似的,说那天的雨比今天的还大,一盆盆倒下来,从午饭后一直不停歇,你都搞不清楚,天是真的到时间黑下来的,还是雨把天下黑的。但那场雨是实心的,因为我女儿生在那天。天上倒的是雨水,落在我心里可都是绸缎,都是珍珠。
我女儿啊——胡伯正正身子,拿过杯子喝掉一口,又靠在椅子上——和雨真是有不解之緣。雨在她的名字里,在她所有的大事里。出生那天的大雨起了个头,后来就没再断过。就连她上小学当天,前一天晴朗无比,晚上漫天的星,早上一阵风过,雨就落下来,持续一整天都没停半会儿。那雨格外细,特别冷,送她去学校的路上,她一个劲往我雨衣的深处钻。她伤到膝盖,留下一拃长的伤疤。那天雨就更大了,水漫过大半个城,我拉着她说,你小心点,小心点。小心是小心了,可是谁知道从什么地方冲过来的木头上有那么锋利的一个茬口呢。你们是不知道,别说走在水里,走在路上,不管走在哪里,只要你走着,就指不定从哪里冲出来什么东西。她尖叫一声,整个人扑下去,亏得我动作快,要不然……胡伯拿过两颗开心果,却没有剥开。我一只手把她抱起,另一只手撑着伞,那时候她不小了,伞遮不住膝盖,雨冲在伤口上,血顺着往下淌,落到水里就没了颜色……就是那时候,她问我。她说,爸爸,你见过空心的雨吗?我说没见过呀。她又说,我想见见……
胡伯,你女儿在哪儿?阿懒问道,问完被自己吓得酒醒两分,看胡伯根本没留意,就盯着老T。老T也钝了,胡乱指指,那边那座城市里。胡伯不管他们,继续说。后来不止是女儿,连她妈妈和我都觉得,女儿的生日、升学这些事,不下场雨,就跟假的似的。有几次生日没下雨,我们要么带她去找喷泉淋一场,要么干脆在浴室用莲蓬头人工降雨。这家伙,一到雨里,完全和平常不一样,那个舒展啊,那个开心啊……胡伯这才掰开白色的壳,将两颗灰绿色的开心果扔进嘴里,嚼着。又伸手,杯子空了,摇摇分酒器,也空了,弯腰从桌下又摸出一瓶酒来。阿懒看看自己带来的那一瓶,心想不着急,便挪过分酒器,让胡伯给倒上,满上一整杯后,端起它,推开厨房门,走到阳台上。胡伯的声音追上来,可是她一直说,不是空心的……雨水落在遮篷上,再分作几股流下,一片哗哗声。望出去的天地一片混沌,一片汪洋,但仍旧能看得清楚在雨水中的乌黑的云彩的那些层次,低头从小小的酒杯里看去,更是分明。可几番尝试,阿懒都找不准具体的方位,都无从下手。
你见过空心的雨吗?阿懒自问,但给不出肯定的答案。空心的雨该是什么样的?如鸡蛋那样,一层薄薄的壳,内里包着空无的蛋清、蛋黄?如樱桃那样,饱满丰盈的果肉中,藏着一粒空无的核?如泡泡那样,雨水只是外围的象征性的膜?……那空的心里,究竟是什么呢?阿懒想不明白,但他知道,就算他能想明白,也无法通过剪辑云彩,达成那样的效果;就算他能完成空心的雨,让它落在胡伯的女儿所在的城市,胡伯的女儿也认不出来。甚至,她很有可能早忘了问过胡伯这样的问题。想到这里,阿懒叹一口气,选了最浓重的那一朵,取了最黑暗的那一缕,迅速剪辑,落进杯中,随后一口将酒吞进去,是一团墨汁般的苦涩味道。阿懒又在遮篷下站立一会儿,伸出手去,用雨水冲刷一下杯子,让喝不尽的一两滴云彩落回水中,这才回到厨房。胡伯还在说着,但语词已连不成句,零碎的词语从他嘴里飘出,濡湿四周。……那天也是雨……雨呀,开成了花……空空的心里藏着雨,藏着花……你还笑……我没见过那么大……我耳朵尖……鼻子尖……她……她……你说再也……你说……你的手……谁敢……现在我……雨呀,开得出……听听……空的花……阿懒知道,应该让这些话语自顾自地喷涌,老T目光已然有些呆滞,浑似无所见地望着胡伯,但仍旧没忘伸手,不管杯子里有没有酒。阿懒在老T小臂上拍打一下,在他抬头时,示意将胡伯送回卧室。
这么干瘦的胡伯,醉酒后依旧沉如铁,要不是阿懒也喝得无法准确感知时间,完全不怵重复,真不知道怎么把他放回床上。好歹,胡伯躺下了。老T在床头坐上一会儿,双手一拍床,撑起自己,跟在阿懒身后走出卧室。两个人在狭小客厅的竹沙发上坐着,缓过最浑噩的那一段,阿懒站起来要走,老T突然叫住他。阿懒,那边的大城市你去过吗?阿懒点头。大城市的那边,那几座城市你去过吗?再过去就是海,你去过吗?这次不待阿懒点头,老T就叹了口气,我去过,好多年前。后来我就在这里,现在我就在这里。一直就在这里,不离开这两条街,不离开我的店子。你给我说说,外面现在是什么样。说完,老T往后一仰,靠在沙发上,两只眼睛如水泡般望过来。
阿懒看着老T好一会儿,站起来,略微摇晃地走到厨房,从橱柜里找出一只四方玻璃杯,拎着他之前放在桌上的那瓶白酒。看着阿懒把酒杯放在自己面前的茶几上,拧开瓶盖,倒上没过杯底半指深的酒。老T说,还喝啊?再喝下去我只怕……阿懒摆手止住老T,他拿过茶几上那盒火柴,划燃一根,伸到杯子里。杯子里的酒迟疑了一小会儿,然后燃起来,一团淡蓝色的火焰在酒面跳动着,随即往上蹿升。互相挨挤,互相簇拥,火焰没有散开,只是在水面上方撕扯着,发出轻微的嗞啦的声响。出了杯子的火焰开始蓬松,燃烧薄了起来,摊开去,不过仍旧没超过一张垫子的大小。升到吊灯下方时,火焰停住,它不再透明,开始由边缘往内,呈现一层层絮状的白。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海时,剪下来的一小片云。阿懒告诉如痴如醉望着那一小团云彩的老T,也是在告诉自己,或者还有别的人。和陆地上的云没多大区别,重一点,湿一点,藏在里面的叫声不太一样。你听,这两声是海鸥,是不是又有点像鸭子,又有点像大雁?
老T咧嘴一笑,说,云是好云,你那酒差了点。他突然又静下来,眯缝着眼听上好一会儿,摇摇头,说,都不像,就是海鸥的声音,我知道。那一团白云在他们的注视下,一点一点地变浅变淡,然后突然过了自己设定的界,消失了。阿懒再往杯里倒上半指深的白酒,用火柴点燃。这一次还是一团白云,只不过比刚才的更蓬松,底如熨过般平整。这团白云直升到天花板下,穿过吊灯时,擦得灯泡直晃,并且亮了几分。这是我在高原上剪下的,那时候我已经到处跑了一段时间,没那么兴奋,只对它的平底印象深刻。老T不一样,他不但望着,还站起来,要摸摸那云底,仍够不着,正准备往茶几上爬,云又散了。就这样,酒从瓶子倒进杯子,点燃的火焰升起来,在房间里高高低低处停留,随着阿懒或长或短的讲述,然后散去。这不成规模的小小的云彩,经过酒瓶里的禁锢,酒杯里的发酵、燃烧,似乎把时间和酒精扩散在空气中。阿懒说,再倒一次就结束时。东方已经发白,胡伯在卧室里的齁声早变得均匀。
那团火不太一样,内里仍旧是透明的但能感知的跳动,外围却不是单纯的蓝,而是颜色混杂且在不断生灭。因此,当它不是化成一团云彩浮出杯子,而是作为一道彩虹,从杯子跨出来,斜向上搭在房间里无明之处时,也就在情理之中。但这却出乎阿懒的意料,他愣上好一会儿,才窘迫、欣喜、伤感诸多情绪掺杂地哎呀出声。没想到,没想到,阿懒连连摇头,这个居然还在,这是我离开……离开之后,第一次剪辑下来的,就剪了一小块。当时我想的是,剪下来的都不喝,都是最宝贵的记忆,留着以后,说不定留到老了再拿出来。阿懒看老T望着自己,有点不好意思,平静下来。那天上午的雪可真大,谁知道中午又换成了雨,谁知道雨落着落着就出了大太阳。你说,天气都能变得这么快,何况……
后面的话到底没再说下去,也用不着说了。那彩虹停留的时间比之前的云彩都短,倏然消失,仿佛压根儿没有存在过。老T望着空白处的目光空了一会儿,才又落向阿懒这里。结束啦,阿懶没有解释,只是伸手指着玻璃杯,你尝尝,这可是过滤掉云彩之后的味道。老T面露疑惑,但还是拿起来,抿了一口,随即仰脖将余下的全部倒进嘴里。杯子里的液体没剩多少。是水的味道,老T说完咂咂嘴,又不是水的味道。再咂咂嘴,肯定不是酒的味道。是啊,外面现在差不多也还是这样。老T点点头,这么说来,我留在这儿没错。那,那件事我就可以跟你说说了,我被云烫伤的那件事,一朵云……今天不说了,阿懒止住他,拿起酒瓶,晃几下,递给老T。还有一点,什么时候你自己把它点了吧。
阿懒下楼回到房间,转了一圈半,丝毫没有睡意。他又站上片刻,走进厨房,打开冰箱,拿出两罐啤酒,一个玻璃杯,来到阳台。塑料椅子上还留着未蒸发的雨水,也可能是露水,微凉湿意顺着裤子渗进来,贴在皮肤上,呼应了入喉的酒。东方一片的白正在分出层次,注入颜色,并且开始提速。女人让他离开时,也是这样一个早上,他当时刚熟练云彩的剪辑技术不久,早早起了床,想剪下金光灿然的一缕,为她调一杯清晨的饮料,还没动手,女人披衣出来,挨着他站了好一会儿,说了那番话,让他离开。现在,似乎一切都没有变化,东方还是东方,彩霞仍旧灿烂,就连手里握着的,也是同一款啤酒。阿懒站起来,低下头,望着酒里映衬的似有若无的云彩,始终没有上手的意兴。迟疑间,他瞥见一个人影从远处走过来,那身形有些熟悉。
移开杯子,直望下去,是那个女孩。这一次,她是从学校的方向往家这边而来,仍旧在马路的对面,仍旧是他见过很多次的那身衣服,但这个时间,她怎么会从学校过来,而且一个人走着?阿懒不用看时间,根据朝霞也知道,就算是往学校去,通常也还得有半个小时。女孩步子比平常快一些,清晨的光线还带着几分朦胧,从这个距离更无从分辨她的表情,判断不了是喜是悲。阿懒就这么站着,看着女孩走过对面两家尚未开门的服装店,走过街面上摆了三张桌子、桌子旁都坐着人的早点店。女孩在早点店旁停下脚步,过了一会儿才继续往前走。至少没那么糟糕,阿懒想。女孩已经走到那个路口,正要拐弯。阿懒抬头,想着是不是照着上次那样,再给她一团意外的光。太阳还没浮出来,东方的云彩足够绚烂,要剪辑到合乎所用却难。这时,阿懒才知道自己酒劲上了头。醉眼看下去,女孩已经等来绿灯,走过路口。阿懒看看女孩的背影,再看看颜色愈发浓重的云彩,忽然觉得,也许他可以在其中一朵云彩上做个标记。这样,不管女人在哪儿,要是看见,就能明白是他在致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