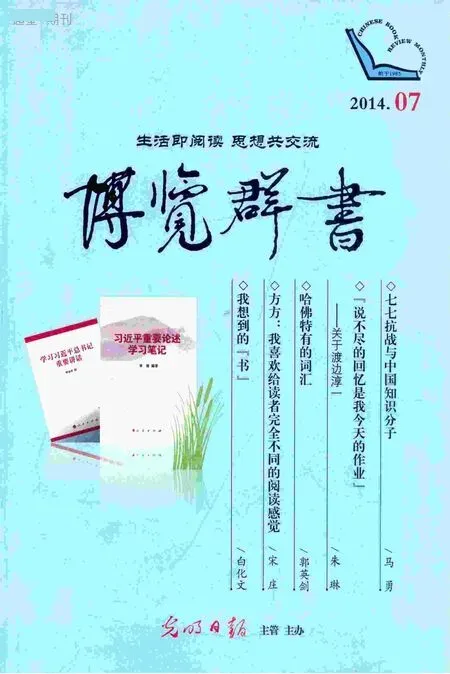这所《草房子》有三重美
胡红草
曹文轩的长篇小说《草房子》是儿童文学的经典名著,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作品格调高雅,充满悲悯与崇高的感情。该书自1997年出版后,就畅销不衰,这一“出圈”现象正应了曹文轩提出的文学命题:“如何使今天的孩子感动?”他说:“感动他们的,应是道义的力量、情感的力量、智慧的力量和美的力量。而这一切是永在的。”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也是一部经典的儿童影片,荣获了包括华表奖、金鸡奖在内的诸多大奖。电影的成功一方面得益于原著的精美品质,另一方面来源于编导深厚的艺术功底与改编才华。
叙事视角:视角转换陶冶观众心灵美
“叙事视角是一部作品,或一个文本,看世界的特殊眼光和角度。”杨义在《中国叙事学》中提出两种叙事视角,一是全知视角,一是限知视角,并指出“第一人称视角虽然不是限知视角的全部,但无疑是它的一个重要侧面”。
曹文轩的长篇小说《草房子》是在全知视角下展开叙事的,叙述者犹如一个局外的“说书人”,为读者娓娓道来一段发生在油麻地的故事。
那是1961年8月的一个上午,秋风乍起,暑气已去,14岁的男孩桑桑登上了油麻地小学那一片草房子中间最高一幢的房顶……
显然以全知视角叙述一段遥远年代的童年往事,会让如今的读者产生一定的阅读距离。然而这种有意营造出的疏离感与时空感,正构成了曹文轩小说的主题——“在那一处处或一件件过去的风景与醉梦里,实现古典诗情与现代生命的真实结合。”如果说原著《草房子》是为了让读者在时间的向度中追寻永恒的话,那么以大众审美为基础的电影《草房子》则是希望观众在情趣隽永、诗情画意的银幕空间中,与主人公桑桑一起重温童年岁月的纯真美好,起到陶冶心灵、润泽人生的作用。电影《草房子》将原著的全知视角改为第一人称视角,以儿童桑桑的视角作为观察的视点,以成年桑桑的回忆作为叙事的辅助。影片第一个镜头就是桑桑向景深处行走的后跟镜头,后跟镜头能模拟观众的眼睛,犹如观众跟随桑桑一同穿过麦地,一起重回童年的课堂。之后响起成年桑桑的旁白:“那年是虎年,可我不属虎,我属龙,纸月大我两岁,她属虎,那天我第一次见到了纸月。”伴随儿童桑桑主观镜头中纸月的出现,电影缓缓拉开了序幕。第一人称视角具有“情感召唤”的作用,在视听语言的综合配合下,电影《草房子》一开篇就成功地将观众带进了“我”的故事,“我”的情感中。
影片具有双重叙事视角,一重是“显影”的儿童叙事视角,即影片中儿童桑桑的观察视角;一重是“显声”的成人叙事视角,即影片的叙述者。他站在成年人的思想高度,以旁白的形式对影片中的儿童叙事做了说明、补充、总结和升华。双重叙事视角的设定体现了编导深厚的艺术功底与改编才华,在影片中具有以下两点作用。
第一,赋予作品怀旧、浪漫、温情的底色。影片的主色调是暖黄色的,如同泛黄的老照片,成人的回忆叙事缓缓拉开记忆的闸门,勾起了观众对童年温暖的追忆以及对时光流逝的慨叹,具有一种温馨与温情的审美感受。
第二,以成年人成熟的情感丰盈、完善了儿童的认知视野,具有对观众,尤其是对儿童观影者的引导与教育作用。在小说中童年桑桑对杜小康承认放火一事耿耿于怀,原文写道:
桑桑看到,当孩子们在用钦佩甚至崇拜的目光去看杜小康之后,都在用蔑视甚至鄙夷的目光看着他……桑桑绝不肯原谅杜小康。因为杜小康使他感到了让他无法抬头的卑微。
显然儿时的桑桑只顾着自己的自尊心,不仅误解了杜小康,也没能正确认识放火的危害,但这就是儿童视野的天然局限性,是儿童本位的情节设计。在改编时,编导考虑到了电影的感染力和受众面,删掉了小说中童年桑桑的错误认知,加入了成年桑桑的反思:
直到我长大成了爸爸,我还在恨我自己,为什么那天挺身而出的不是我,而是杜小康。
同样在对陆鹤秃头的认识上,原著的表述是委婉蕴藉的。“纯净的月光照着大河,照着油麻地小学的师生们,也照着世界上最英俊的少年……”电影则以成年桑桑的旁白直抒胸臆,传达出关于美丽与尊严的正确价值观:“他终于真正地赢得了自己的尊严,也使我们懂得了什么才是真正的美丽。”由此可见,适时响起的成年旁白在儿童视角的影像叙事中起了“画龙点睛,陶冶心灵”的教化作用。
叙事聚焦:情节净化构建乡土人情美
“视点讲的是谁在看,聚焦讲的是什么被看。”曹文轩的《草房子》是一部长达十万余字的长篇小说,讲述了一段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江南水乡的童年故事。小说《草房子》采用的是散点叙事的手法,轻情节重情境。全书共分九章,第一章秃鹤,讲的是陆鹤的秃头给他带来的痛苦与成长;第二章纸月,围绕纸月的身世、纸月在油麻地的学习以及与桑桑的朦胧情感展开;第三章白雀(一)和第七章白雀(二),主要讲白雀与蒋一轮的爱情故事。第四章艾地,讲述了秦大奶奶与土地的故事;第五章红门(一)和第八章红门(二),讲述了杜小康及杜家从兴盛到败落的故事。第六章细马,讲邱二爷、邱二妈与过继的孩子细马的故事;第九章药寮,主要是围绕桑桑生病,治病展开叙事,并插入了父亲桑乔与温幼菊老师的往事。在改编电影时,编导首先考虑的便是影片的叙事结构,《草房子》不适合拍成《城南旧事》这种散文式风格,更何况珠玉在前,也不适宜传奇叙事或戏剧性叙事。因此徐耿导演就将原著中的散点叙事交织在一次,以油麻地小学为主要空间,以油麻地小学的师生为主要人物(删掉了与之关联不大的第四章与第六章),将原本散落在各章中的重要情节,以平行蒙太奇和连续蒙太奇的手法连缀起来。例如影片先交代纸月来到油麻地小学,然后通过会操、排戏、红门败落、爱情传书、桑桑生病等事件的交织叙事,表现了陆鹤的痛苦成长,蒋一轮的爱情悲剧,桑桑与纸月、杜小康等同学的关系以及桑桑生病后的父子亲情。显然交织叙事能更加清晰、连贯、集中地串联起故事,适合大众电影的表达特性。
曹文轩认为:“摇摆是小说运行的动力所在。通过语言、情节、性格以及主题的摇摆,小说得以获得引人入胜的魅力。”诚然在小说中我们可以明确地感到杜小康与桑桑,白雀与蒋一轮性格与关系的摇摆。例如杜小康最初冷漠桑桑,之后主动示好。两人成为朋友后又变为“敌人”,最后又和好。白雀起初对蒋一轮情有独钟,之后对谷苇有好感,后又讨厌谷苇,再次喜欢蒋一轮。蒋一轮恋爱前对工作有热情,对学生有耐心。失恋后,则懈怠工作、漫骂学生。这些性格与情节的摇摆叙事在长篇小说中会形成一种“九曲十八弯”的阅读魅力,但若放到一部100分钟的电影中则很难讲述清楚,容易造成观众理解与共情的障碍。因此在小说到电影的跨文本改编时,编导缩减了摇摆叙事的频率,集中通过排戏和送信这两件事展现了友情与爱情的美好崇高。编导有意在排戏情节中,增设了桑桑与杜小康都演新四军连长的小矛盾,然后通过骑车化解矛盾,之后则表现了桑桑对杜小康的同情和杜小康对桑桑读书的嘱托,随后又通过送鸭蛋和抄书深化了两人之间的友情,书写了人性的真善美。在白雀与蒋一轮的爱情叙事上,编导聚焦于传书、约会、误会、白父反对、白雀结婚这几个情节点,以诗意化、简约化的镜头语言娓娓道来,在美化人物形象、净化人物感情的同时,也让观众随着他们的爱情或喜或悲,形成一種爱情悲剧的咏叹调。原著中有些叙事内容具有一定的多义性、复杂性和暧昧性,编导对此作了净化处理。例如原著将浸月寺的慧思和尚与纸月的生父做了暧昧性的连接:
纸月失踪了,与她同时失踪的还有浸月寺的慧思僧人……仿佛有一对父女俩,偶然地到板仓住了一些日子,现在不想再住了,终于回故乡去了。
为了不破坏电影乡土田园的审美意蕴,编导有意将这一“有伤风化”的内容删掉了。影片制造了桑乔与纸月生父关联的悬念,这个悬念设计得非常巧妙,既能引发观众的好奇心,增强电影的戏剧性张力,又为纸月来油麻地读书做了合理性铺垫。在教师们的议论以及桑乔夫妻的争论中,观众得知了真相,桑乔并不是纸月的生父,但桑乔曾经喜欢过纸月的母亲。这样的改编不仅没有损害人物形象,反而更易让人理解与感动。同样的改编策略还出现在杜小康的父亲杜雍和身上。原著中有杜雍和在酱油里掺水,朱一世大闹红门的情节,还有杜雍和因喝酒开船而导致家门败落的情节,这些叙事在电影中都删掉了。导演希望给观众打造一个充满人情美、风景美、伦理美的“桃花源”。
叙事意象:情景交融营造影片诗化美
宗白华说过:
主观的生命情调与客观的自然景象交融互渗,成就一个鸢飞鱼跃,活泼玲珑,渊然而深的灵境,这灵境就是构成艺术之所以为艺术的“意境”。意境的构成单位是意象,不论是小说还是电影,《草房子》都反复书写了“水”和“鸽子”这两个重要意象,营造了影片情景交融的诗化美。
曹文轩在《一根燃烧尽了的绳子》中说:
水对我的价值绝非仅仅是生物意义上的。它参与了我之性格,我之脾气,我之人生观,我之美学情调的构造。
水有温柔、善良、忧伤、坚韧、勇敢、生命的象征。在电影《草房子》中,不论是油麻地小学的金色池塘,还是小镇的水码头,导演都用极富诗意的光影、色调营造出波光粼粼的水面。这艳阳下的水面是桑桑生命力的写照,是杜小康坚韧勇敢的新生;这余晖下的水面是蒋一轮与白雀爱情的光晕;这月光下的水面是陆鹤的心酸与欣慰,是蒋一轮的幸福与忧伤。
水意象在电影中除了表现为池塘、大河,并与水车、芦苇荡形成意象群外,还化为“雨水”参与了叙事。电影中有多次下雨的场景,在广角镜头下孩子们或撑着油纸伞,或披着蓑衣在雨中三五成群的行走;在全景镜头中,草房子的屋檐下连成了一串串晶莹剔透的“水珍珠”;在景深镜头中,青石路的小巷里溅起一滩滩水花;在特写镜头中,披着蓑衣的纸月露出淡淡的忧愁,回不去的白雀与桑桑相拥哭泣。这些下雨的镜头被导演拍摄的富有诗意,雨声音响和抒情音乐融合,与画面形成音画同步,给人一种“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的唯美意境,或给人一种戴望舒《雨巷》般的忧愁意境。
在西方文化中,鸽子有和平、爱情的象征;在中国文化中,鸟有情使的角色,例如鹊桥,飞鸟则是自由与理想的寄托。纵观《草房子》的小说与电影文本,我们会发现鸽子意象常与纸月相连。例如桑桑第一次见到纸月时,原著是这样描写的:
这些小家伙,居然在见了陌生人之后,产生了表演的欲望,在空中潇洒而优美地展翅、滑翔或做集体性的俯冲、拔高与穿梭。
显然这里的鸽子被拟人化了,以鸽拟人,表现了桑桑在见到纸月后的开心与兴奋。文学使用拟人化手法,能给予读者想象的空间,但电影如果只表现鸽子飞舞,则会产生一种艺术的“失真”。因此导演将桑桑与鸽子的意象充分融合,桑桑将笼子里的鸽子都放出来,他一边挥舞油纸伞一边忘情地高呼,白鸽盘旋于他的头顶。导演通过俯拍、平拍组合的重复蒙太奇镜头,诗意化地表现了鸽子飞舞与桑桑狂欢的意象组合。影片结尾一改原著离别伤感的情调,在极具浪漫感与崇高感的升格镜头下,漫天飞舞的白鸽是桑桑重获新生,重拾理想的视觉象征。徐耿导演通过光线、影调、色调、意象与人情的交融,“为影片赋予了一种托物言情、情景交融的诗学品格”。
樊发稼说:“读《草房子》真正是一种享受,是一种文学的享受,艺术的享受;是一种真、善、美的享受。”同样观看电影《草房子》也是一次审美的享受。对新世纪欲望躁动的文坛与影坛而言,《草房子》互文本的双双成功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它毋庸置疑地证明了——“感动人的那些东西是千古不变的,我们應当提醒自己追随永恒。”
(作者系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