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间”与“甚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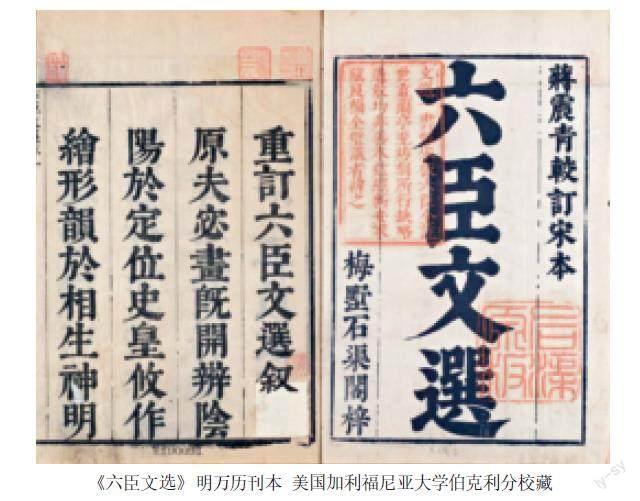

《隋书·经籍志》被看作走进中古学术领域的津筏,如何阅读成为理解和研究其学术内容的关键。本文提供了它的别集目录的三种读法,为读者提供参考和帮助。
近十年来,笔者专心致力于汉魏六朝集部典籍,特别是别集的研理,《隋书·经籍志》(以下简称《经籍志》)是翻检最勤的一部史志。若论唐初魏征等纂修《隋书》的学术史价值之要,恐怕莫过于书中“十志”里的《经籍志》。自班固《汉书·艺文志》之后,对典籍源流、艺文升降和学术变迁的考索无不仰赖于《经籍志》,其可谓走进中古学术领域的津筏。四库提要在肯定《经籍志》“考见源流,辨别真伪”之余,也持言辞激烈的贬低批评态度,认为它“编次无法”,在“十志”中“最下”。四库馆臣博稽群籍,自然有其独到的评价眼光,实际这种“褒贬相兼”的取态能够让人们更加平和地看待《经籍志》,信奉而不迷信,倒不失为阅读《经籍志》的恰当态度。
由于所从事的学术专题的关系,笔者对《经籍志》“集部”的别集类和总集类算是下了一番功夫,不避敝帚之讥,略有读《经籍志》的“得间”和“甚解”之处。以别集类为例,初看著录的鳞次栉比的书目,难免有不想读之感。因为这些别集大多已亡佚不存,阅读它们就像是在与一部部“消逝”的典籍对话,若不具备强烈的学术求知欲,对此类史志目录性质的著述确实难以阅读下来。曾听李致忠先生讲过一番意味深长的话,说拿起一部目录书而能逐条地看下去,说明有功夫了。一條目录就是一部微型的书籍,浓缩着原汁原味的学术,表面上是在看书目,脑海里浮现的却是书里的大千世界。
读法之一:典籍的分合关系
有耐性而能坐得住看一部目录书的人,可以想见他背后有多少部书的“储存”。以《贾谊集》为例,《经籍志》并不著录该集,只是在小注里称梁又有《贾谊集》四卷,难道唐初编《经籍志》时《贾谊集》“亡佚”了?显然不是,因为《贾谊集》的内容被合编到子部儒家类著录的《贾子》十一卷里。依据是《旧唐书·经籍志》著录《贾子》九卷和《贾谊集》二卷,两书相合就是《经籍志》著录的十一卷本《贾子》。这意味着唐初流传有《贾谊集》,只不过卷数由南朝梁时的四卷变成了二卷,可能是考虑到卷数有限,于是与《新书》合编为《贾子》。如此反复地从史志目录的缝隙里去推敲,《经籍志》小注提及的“贾谊集四卷”这条目录就被“盘活”了,析出了《贾谊集》这部书在南朝梁至隋唐时期的编撰和流传的基本脉络。如果《经籍志》著录的每种典籍都可以做到这样的“盘活”,那书目的阅读就会不再枯燥单调,因为它潜藏着跃动的书籍史和学术史。
再如东汉注释《楚辞》的王逸的作品集,同样仅见于《经籍志》的小注,著录为“王逸集二卷”,子部儒家类小注里还著录了他的《正部论》八卷。实际上,王逸的这两部著述是从同一部书里各自分出来的,它就是唐马总《意林》著录的《正部》十卷。《正部》十卷因袭的是南朝梁庾仲容的《子钞》,到了梁武帝普通年间阮孝绪编《七录》时,将此部书析分为了两卷本《王逸集》和八卷本《正部论》。《经籍志》开篇的总序称阮孝绪“割析辞义,浅薄不经”,应该指的就是此类情况。但也应该看到阮孝绪析分背后的学术背景,就是别集编撰在南朝梁时呈现繁盛的局面,透露出的是四部之集部地位上升的情形。
这里举的《贾谊集》和《王逸集》两个例子,放在纵向目录里予以审视都存在分与合的现象,从而避免了孤立地看待《经籍志》的别集著录,实际上是把此部史志的别集目录读活了。别集类还有不少的目录符合这种或分或合的现象,如著录的《温子昇集》三十九卷,实际也是合编两部书的结果。因为《魏书·文苑》本传称,温子昇有集三十五卷,又撰有《永安记》三卷,两者相合是三十八卷,如果再算上目录一卷的话也正是《经籍志》著录的三十九卷。再比如著录的宋《王叔之集》七卷,小注说南朝梁时的《王叔之集》是十卷,那么到了唐初修《经籍志》时貌似“丢失”了三卷。其实也没有“丢”,这三卷著录在子部道家类,即《庄子义疏》三卷。
似乎梁时更重视一人各书之合“集”,强调别集的地位,而到了唐初又注重一人之各书分列,存在着明显的一人之集与经子史两类撰述各自升降有别,这是很有趣的现象。目录向称专门之学,如果摸索不到目录之间的义例,就如同不得其门目,也就很难理解目录学。在此意义上讲,典籍的分合关系,为阅读《经籍志》的集部别集类目录提供了一把切实可用的钥匙。
读法之二:著录格式
《经籍志》别集目录的另一种读法,是从它著录形式不同于经、史、子三部入手,统观汉魏六朝时期的别集成书细节。别集类的著录格式是固定的,表现为“职官+作者+集”的格式,比如“汉太中大夫东方朔集”。它的目录学意义,在于揭示出汉魏六朝别集的成书是秘阁整理编订的结果,基本上不出于作者之手。如果借鉴西方的书籍史理念,就是作者只对集子里的作品享有著作权,而作品集的成书则与作者没有任何关系,编者即古代的秘阁人员才是作品集成书的关键角色。
根据文献记载,秘阁编订作品集似乎可以追溯到东汉时诏令中傅整理刘苍作品,最明显的例证就是魏明帝曹叡下诏撰录曹植作品,副藏内外。这种制度性安排贯穿了整个汉魏六朝时期,使作家作品得到保存,而且还以正、副本的方式促进了作品的阅读和传播。由于是秘阁人员整理编订作家的作品集,一般情况多发生在作家去世之后,所以在题作品集之名时形成了署作家职官的格式。马楠博士研究认为,所署职官多为作家的终官,这与秘阁编订作品集是在作家去世之后进行是相吻合的。
唐宋及以后,作家给自己的作品编集子是司空见惯的现象,但在六朝却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很多作家没有条件或能力为自己编集子。其中制约性的因素可能还是纸张的问题,虽说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术,纸在晋代开始较为广泛使用,但也不是人人可得而写之,恐怕还只局限在权贵上层的小圈子里。西晋时人们竞相传抄左思《三都赋》而致洛阳纸贵的掌故,说明纸张还是紧俏品。陆云《与兄平原书》说,给其兄陆机编集子用的纸就是“恶”品。
在南朝宋已享盛名的鲍照,也只能遗憾地等待身后才能有机缘被编集子,“仰赖”于文惠太子萧长懋喜欢读他的作品这种偶然性的因素。鲍照的例子,表明秘阁人员虽有典籍保存和整理的职责,也不是当时所有作家的作品都有机会进入秘阁编集成书。曹道衡先生有一个精到的论断—大致高官的文集可以更容易地进入国家藏书,并著录在国家藏书的目录里。
总而言之,读《经籍志》别集目录要有历史的观念,有集部形成发展史的学术观照,否则一条条簿录式的书目,不令人疲倦才怪,而且还可能生出一些“误解”,即这些作品集不是作者自己本人编辑的。所以著录了汉人集并不意味着汉代出现了作品集,它们是魏晋以来秘阁人员整理编订的结果,而且一直到南朝都沿袭着这种方式,最终推动了集部的确立。
读法之三:还原
《经籍志》别集目录的第三种读法,不妨称之为“还原式读法”。还原之一是结合作家的史传对读,比如“宋秘书监王微集十卷”一条下有小注称梁又有“宋太子舍人王僧谦集”二卷,王僧谦就是王微之弟。《宋书·王微传》记载王僧谦因服食丹藥过度而卒,王微感到很愧疚,就在王僧谦的灵位前祷告说要给他编一部作品集。请注意,王微可是任职秘书监,编集子是他的职责之事,那么这部两卷本的王僧谦集恐怕就是王微亲自谋划而编,这很有点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味道。比如,著录的“晋孙恩集五卷”,根据《晋书·孙恩传》的记载,他盘踞在沿海一带,屡次为乱,最终落个跳海自杀的结局,但还是留存下了他的作品集,秘阁照样为反面人物编集子。再比如著录的“晋大司马桓温集十一卷”,《史记集解》又引有车胤《桓温集》,车胤是谁呢?他和桓温是何关系?查《世说新语·识鉴》和《晋书·车胤传》,知道车胤颇得桓温的赏识和提携,本人也博学多闻,所以为桓温编了集子。不排除所编之集旋即被收藏、著录于秘阁,或许这条目录的集子就是车胤所编。结合史传读目录,可以了解到一些相关的人和事,赋予目录以饱满的血肉。
还原之二是结合阮孝绪的《七录》对读。别集目录下附有一定数量的小注,以“梁有”作为领起词,一般认为这是《七录》里的著录,四库馆臣就说《经籍志》参考《七录》,互注存佚。当然实际情形可能不仅是《七录》,还应包括其他的目录书来源,这个问题文献学界有讨论。比如别集目录的小注至《刘缓集》和《释智藏集》而终,清人姚振宗据刘缓卒在阮孝绪之后而断定这两条小注的著录不是来自《七录》,这是很有道理的。
当然还应主要以《七录》做对读,《经籍志》总序是明确提到《七录》和阮孝绪的,称他“沉静寡欲,笃好坟史”。从小注的情况推知,《七录》没有收北朝人的作品集,另外《七录》著录的作品集的下限至迟到《刘缓集》和《释智藏集》,与《文选》选录作品至陆倕止也大致接近。因为小注《刘缓集》《释智藏集》的下一条目录恰就是《陆倕集》,这似乎说明萧统编《文选》主要依据别集再选编,不见得是不录当时尚在世作家的作品,即所谓的“不录生人”,而是因为他们的作品集还没有编出来,这也提供了认识萧统编《文选》的新角度。
以上根据别集目录的拉杂所写,权为读《经籍志》的心得体会,一隅之见甚或固陋谬说在所难免。《经籍志》值得反复细读和揣摩感悟,但真要做到“读熟读透”又的确不那么容易。特别是不同的文史领域,阅读出来的感悟必定各具姿采,如若汇集诸流,形成解读的合力,想必《经籍志》隐含的中古学术史真相会绽放开来。
刘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