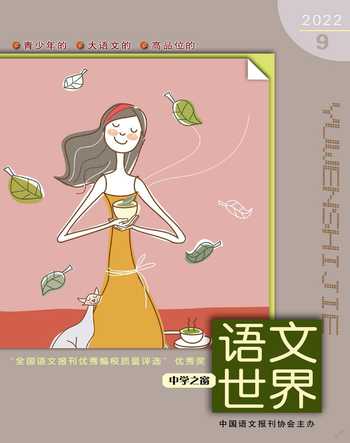刘傲夫:用诗歌让我们看见鸟鸣
黄志兵
窗外鸟鸣
刘傲夫
姐姐穿着碎花裙子
一路笑过来的样子
刘傲夫一首《窗外鸟鸣》,给当代诗坛带来惊喜,却也引来无数争议。视之如珍品者,认为该诗“提纯特点,清脆而又明亮”。视之如垃圾者,认为该诗“不符合现代汉语语法,不合常理,根本称不上是诗”。其实,一首诗若能引来诗家争鸣,是诗坛之幸。但是,一首诗若让众人趋之若鹜,乱加点评,则是艺术的不幸了。
鸟鸣,是宣告春天到来最动听的啼唱。一如破土而出的嫩芽,让我们在历经寒冬后,用一星绿意让视觉为之一亮。鸟鸣,让我们走过哑然的季节,空寂的原野传来一声清脆,顿时让耳朵怀孕,便有一江春水流过我们沉睡的心田。
鸟鸣,天然属于鸟的语言,但天籁入耳,人们就有了属于自己的倾听和解读。一如著名诗人伊沙曾写过一组关于鸟鸣的诗歌。他说,鸟鸣是“二维码”“马赛克”,是“天国密电码”。每一個人都是翻译家,都有属于自己谛听鸟鸣后的“读后感”。伊沙又说,“鸟儿争鸣,诗岂能无声”。鸟鸣一旦进入诗人灵敏的耳朵,诗人一旦用一颗诗心和鸟鸣对话时,便有了诗人的再现方式。诗人的再现,则是审美的再现,是突破程式化叙事的个性化、诗意化的再现。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这是孟浩然笔下的鸟鸣,他更侧重于客观叙述,让读者体会到鸟鸣攻陷了春天的早晨。“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这是杜牧笔下的莺啼,他通过“视听结合”,以夸张的方式凸现了春天已在天地间婉转千里。杜甫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和“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那则是人生不同境遇下,“鸟鸣”带给诗人不同的或悲或喜的心理感受。这些“鸟鸣”诗句,之所以流传千古,正在于诗人用自己的耳朵倾听,用自己的文字表达,同时又令读者在咀嚼诗句中达成了生活和精神上的某种契合。
古典诗歌中,写鸟鸣的经典名句俯拾皆是。诸如“二月湖水清,家家春鸟鸣”,又如“喧鸟覆春洲,杂英满芳甸”,还有“入春解作千般语,拂曙能先百鸟啼”,以及妇孺皆知的“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但在众多写鸟鸣的古诗中,金昌绪的一首五言绝句《春怨》,堪称精妙之至的诗作——
打起黄莺儿,
莫教枝上啼。
啼时惊妾梦,
不得到辽西。
此诗具有民歌色彩,阅读时没有字词障碍,无须翻译。而所谓民歌色彩,即诗歌语言来自民间,来自日常生活中的习惯语言。诗句是诗人对生活语言的高度提纯,是看似简单叙述下隐藏的“浑圆”,是看似肤浅中潜存的“隽永”。一如海明威的冰山理论:“冰山在海里移动很是庄严,这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露出水面。”海明威一部《老人与海》,初读不过是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渔夫捕鱼”的故事,深度阅读,才发现 “它是对一种即使一无所获仍旧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的讴歌,是对不畏艰险、不惧失败的那种道义胜利的讴歌”, 是一部关于人类命运的深刻寓言。我认为,金昌绪的《春怨》,四句诗下,涌动的是一条血泪的河流,是一部古代征战对美好情感毁灭的历史。
一声黄莺啼,啼出了春天,啼出了泛滥的春思。而闺中少妇却要“打起”,想要止住春天的放歌。原来是鸟鸣惊醒了“妾梦”,原来是少妇好不容易在梦中前往辽西,即将与爱人梦中相会,却被这一声鸟鸣唤回了现实。全诗以层层倒叙的手法,最后才揭开了谜底,说出了答案。而最后的答案,又留下想象的空间:少妇为何梦辽西?所思之人为何在辽西?……我们将诗句拓展演绎,不就是一个曲折的故事?正如《唐诗笺注》所言:“忆辽西而怨思无那,闻莺语而迁怒相惊,天然白描文笔,无可移易一字。”这也正道出《春怨》一诗最本质的特点,即天然白描,用笔无须铺排;冷静叙述,情感无须外露;用字精简,力求以少胜多。
再回到刘傲夫的诗。“窗外鸟鸣”是诗题,也是叙述的对象,是表现的客体。“姐姐穿着碎花裙子/一路笑过来的样子”是诗歌内容,也是对客体的主观表现。我们首先应将诗题和诗句串联为一个艺术整体,才能将之构成一个完整的审美世界。北岛以“生活”为诗题,这一诗题不可谓不大;但全诗就一个字“网”,不可谓不简。两者相关联,不可谓不妙。该诗不得不让我们承认人生其实就是“网中的挣扎”。仿佛陶渊明的“误落尘网中”,每一个人都是眷恋旧林的“羁鸟”,都是向往大江大河的“池鱼”。窗外的鸟鸣,一旦和穿着碎花裙子的姐姐、笑着的姐姐、一路走过来的姐姐连接起来,主客体融合,鸟和姐姐融合,鸟鸣和姐姐的笑声融合,这其间不就荡漾着浓浓的春意吗?
陆游说:“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刘傲夫这首妙手偶得的诗歌,得益于一个长期写诗的人“打通了任督二脉”,得益于找到了诗人心灵最高级的打开方式,那就是“五觉”自由开放后形成的交融一体,这也就是诗歌创作最具灵性的“移觉”。“移觉,也称通感,即感觉的转移和相通,心理学上叫感觉错移,指一种感觉超越了本身的局限而领会到属于另一种感觉的印象,就是把人们的各种感觉(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等)通过比喻或形容沟通起来的修辞方法。”譬如“红杏枝头春意闹”,一个“闹”字,视觉转化为听觉,成为千古名句。再譬如朱自清《荷塘月色》中“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嗅觉转化为听觉,成为中学教材中不可多得的“通感”实例。
刘傲夫将诉诸听觉的“窗外鸟鸣”,转化为诉诸视觉形象的“穿着碎花裙子的姐姐”,就完成了诗意的“移觉”。移觉,必须找到两者的“沟通点”,或者说“相似点”,本诗巧妙地抓住了多个相似点。“姐姐”,让人联想到姑娘,想到青春期的少女,恰如春天的小鸟。“碎花裙子”,不是旗袍,不是晚礼服。“碎花”,就是春天刚刚吐芽的花朵,就是鸟的羽毛上的点点色彩,富有乡土气息。而一个“笑”字,极为传神。少女的笑,应是生命中最不矫饰、最干净、最悦耳的乐音,这不正和春天鸟鸣一起构成了最美的合唱吗?再加上诗人用“一路”二字,让整个画面富有了动态之美,让我们在“一路鸟鸣,一路笑声”中感到了春天的生机。这样的盎然生机,不就是我们在一个最好时代里体验到的春天之美吗?
刘傲夫“不经意间,完成了一次从听觉到视觉的转换”。听见鸟鸣,是常态;看见鸟鸣,则是创意。苏轼《赤壁赋》中曾写道:“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这是人与自然构建的舒适境界。但若能“耳得之而为形,目遇之而成声”,这应是人与自然相融后的最高審美境界了。汉语“听见”一词,并不只是“偏义复词”,应是“听中有见”,也是“见中有听”。所以,我认为 “耳得之为听,目遇之为见,神会之才为听见”。傲夫正是给予读者一篇神会之作。
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说:“诗歌的写作——如同镭的开采一样,开采一克镭,需要终年劳动。一个字,用得恰当就需要几千吨语言的矿藏。”英国大诗人华兹华斯说:“凝练是一种将感情通过沉思的沉淀,再以一种平静的方式抒发的事,而不是那种单凭才气,一任感情和想象无拘无束发挥的诗。”刘傲夫的《窗外鸟鸣》另一特点即是凝练。口语诗最忌啰唆,最烦铺排。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就是一滴露珠,可以折射太阳的光辉。
想起另一首写鸟鸣的佳作,那是王维的《鸟鸣涧》。
人闲桂花落,
夜静春山空。
月出惊山鸟,
时鸣春涧中。
四句诗,一句一画面,却启迪读者在一幅静谧的春山月夜图中,在“闲、静、落、空”四字里,去悟出一份禅意。当然,这首诗不是口语诗,但口语诗也可抵达更高的境界。《窗外鸟鸣》,极简的两句诗,却简出一个生动的世界。这一简,又非概念化的简,而是形象化的,形象大于思维。简单的口语,却增加了更丰富的叙事可能,可以让读者演化出无数美妙、明媚场景。这和散文不一样。读这首诗,我们很容易想起朱自清先生的名篇《春》,特别是文章结尾处写道:
“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他生长着。
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着,走着。
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他领着我们上前去。”
但这是散文语言,即使分行断句,也不是诗。时下很多人嘲笑口语诗是“回车体”,那是对口语诗极深误解。著名评论家耿建华教授说:“散文如果是糖水的话,那诗就是糖精。”我想,这就是诗和散文最好的区别。或者说,这是口语诗和抒情散文最好的区别。
感谢诗人刘傲夫,让我们在品味诗句中不只是听见鸟鸣,而且看见了鸟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