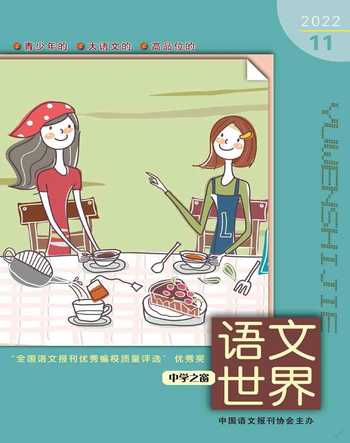上 学
张虎
2001年,我考上了山东大学,是村子里第一个考上重点大学的孩子。为了凑学费,父亲要出去打工,他的好朋友劝他:“咱们祖祖辈辈都在这里生活,也没有把谁饿死?没有钱,干吗还让他去那么远的地方上学?”听到这里,我默默地走出屋子。最终,父亲还是出去打工了,临走前嘱咐在银川的哥哥,让他一定要送我到学校报到。
8月是西北农村收获的季节,家家户户门口已码起麦垛。那天,母亲坐在炕头上,把借来的8000块钱的存折,一针一线地缝在我的贴身内衣上,一再叮嘱我:“存折千万别弄丢了!到了学校后一定要好好读书,要争气!”第二天,天还没亮,和父亲出去打工时一样,我用装化肥的塑料编织袋,装着衣物、铺盖,踏上求学路。在村口,我坐上了去县城的汽车,母亲和患有小儿麻痹症的弟弟在汽车后面跟着走了很远很远。
到了县城车站,我又坐上了去银川的私人客运车,售票大哥是高我一年级的学长,看我窘迫的样子,问我干吗去,我说上大学。他丢下一句:“上大学也不买个行李箱,还背个塑料编织袋!我以为你要去打工呢!”他转头对司机师傅说:“这个娃不用买票了!”
一路近七个小时的车程终于到了银川,然而哥哥因种种原因不能送我去学校,买了一张火车票送我上车后,把我托付给邻座的陌生大哥,请他提醒我到南京后转车。那一刻,我觉得整个人就像一张飘荡在半空的碎纸片,无所依凭。火车开动了,往后一切的一切都需要我独自面对了。在绿皮火车上接近40小时的路程里,陪着我的只有编织袋和里边装的简单衣物、干粮,还有一本散文集《空信封》,书中的一行行文字,似乎在一点点化解我内心郁结的疙瘩。
到了学校,别人都有家长陪着报到,而我只能自己解决一切问题。当时异地取款网络不是很畅通,我迟迟取不出钱,无法办理入学手续。银行工作人员建议我到济南解放阁附近的银行再试试。一路边问边走,终于到了目的地,但依然没能取出钱,只能第二天再试。走出银行,外面下起了雨,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淋着雨走回了学校,在宿舍楼下用IC电话机让别人给父亲捎话:“哥哥已经把我送到了学校,并且办理好了入学手续,让父亲放心!”放下电话,从来没有过的委屈一股脑涌上心头,哭够了才回到宿舍。
第二天,在同學们的帮助下,我顺利办好了入学手续,鉴于家庭情况,学院还为我协调办理了助学贷款。
后来,父亲得知哥哥没有送我到学校,给我写信表达歉疚,说没有照顾好我。其实真正歉疚的是我,因为我,年迈的父亲不得不出去打工。记得父亲在信中说,希望我好好努力,他过得苦一点,是为了将来能给我一个好的起点。大学期间和父亲往来的大量信件我都没能保存下来,但我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父亲在字里行间流露出的疼爱、牵挂与期许。
(选摘自《光明日报》2022年7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