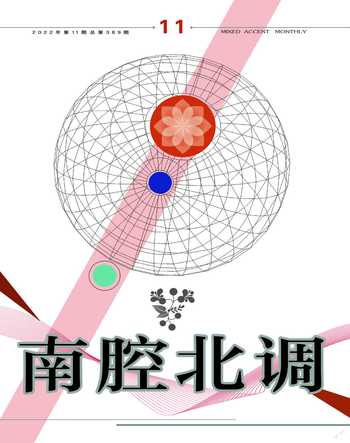元稹《莺莺传》“尤物论”劝诫主旨与文本建构之关系研究
郭树伟
摘要:元稹的《莺莺传》首先是一篇中唐士人对唐代安史之乱及贵族女性参政问题进行反思的劝诫文章,其次才是一篇描写唐代人爱情故事的传奇小说。元稹对唐玄宗为杨贵妃这个“尤物”所困,一不能“以德胜尤”,二不能“忍情补过”,终于导致安史之乱提出了严肃批评。作者的观点得到了当时士人阶层的普遍认同,李绅、杨巨源、白居易和陈鸿诸人的唱和之作,进一步强化了作者“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將来者”的劝诫命题,这表明《莺莺传》与《长恨歌传》《李夫人》等以劝诫为主旨的作品具有同时代文化共振的内在联系,也是对唐代宪宗皇帝“多内宠”的政治生态提出的委婉警醒。
关键词:元稹;白居易;《莺莺传》;“尤物论”;文本建构
中唐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1],元稹的《莺莺传》一经问世,就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堪称唐代传奇的巅峰之作,其题材内容对于后世宋元明清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唐代传奇中罕有其匹,鲁迅誉之曰:“震撼文林,为力甚大。”[2]然而,不同时代的研究者在对作品的不断阐释中产生了不少的分歧,例如:张生是不是元稹本人自寓?张生为什么抛弃了莺莺?崔莺莺究竟身份如何?《莺莺传》的主旨到底是什么?产生这几个问题的原因既有作品的爱情叙事胜过其劝诫命题的客观因素,也有后来作者借助名篇进行作品立意再开拓的主观因素。笔者认为,结合贞元时期《莺莺传》写作时代的反思语境,元稹的《莺莺传》首先是一篇中唐士人对盛唐安史之乱进行反思的劝诫文章,其次才是一篇描写唐代人爱情故事的传奇小说。坚持《莺莺传》作者元稹的“尤物论”劝诫命意的论断,坚持作品的爱情叙事是为劝诫命题服务的论断,则过往《莺莺传》研究中的种种悖理之处即可得到合理解释。
一、自宋元以来关于《莺莺传》主题研究的成就和缺陷
唐代传奇《莺莺传》的文本情节大致如此:故事伊始,张生在蒲州普救寺时兵乱发生,他出力营救了同在寺中寄寓的远房亲戚崔氏一家。张生在姨母郑氏的答谢宴席上对表妹莺莺一见钟情,婢女红娘几经反复传书,俩人终于得偿所愿。后来张生进京应试滞留寓所,与莺莺情书来往并互赠信物。但张生认为莺莺是天生尤物,自己“德不足以胜妖孽”故而抛弃莺莺。这种“始乱终弃”的行为,在当时被人们称赞是“善于补过”。从文本传播反应来说,张生的这个行为在当时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时人多闻之”“张之友闻之者,莫不耸异之”。然而更令人“耸异”的不仅是崔张恋爱事件本身,更有元稹明明知道这件事会使得时人认为是作者本身经历的嫌疑,然而作者却不介意这个事件能够在更为广阔的空间传播,这就引起研究者的质疑!通俗一点儿说,“始乱终弃”的事件本身就是不道德的行为,而作者更把这件不道德的事情播弄得人尽皆知,这次情事的发生及其后传播事件,使得后人阅读这个故事之际每每感到困惑不解,成为自宋元以来《莺莺传》研究的一个死结,以至于每一个研究者都要对此情节作出自己的解释才能展开进一步研究。
宋人赵令畤认为:“盖昔人事有悖于义者,多托鬼神梦寐,或假之他人,或云见他书,后世犹可考也。微之心不自聊。既出之翰墨。姑易其姓氏耳。”[3]赵令畤认为:因为这件事“悖于义”,故而元稹借用“尤物惑人”的传统儒家观点对张生进行开脱;其后更有董解元的《西厢记》、王实甫的《西厢记》对《莺莺传》的故事题材进行不断改编,使得这个在原作品中被离弃的女性,在舞台上得到了完美的结局,寄托了人们“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的善良愿望;近代以来,更有大方之家对《莺莺传》这个问题质疑,其中较为著名的有鲁迅、陈寅恪、周振甫诸人。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评价《会真记》时说:“元稹以张生自寓,述其亲历之境,虽文章尚非上乘,而时有情致,固亦可观,惟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而李绅、杨巨源既各赋诗以张之,稹又早有诗名,后秉节钺,故世人仍多乐道。”[4]鲁迅先生接受了宋代王性之提出的张生为元稹自寓的说法,从道德标准来评价元稹的思路,遂成为权威观点。在其后的刘大杰、余冠英、游国恩、章培恒、郭预衡等人的文学史对此事件的论述基本上是陈陈相因,不能更置一词,即便现在通行的袁行霈主编的教材《中国文学史》也沿袭此说。20世纪30年代,陈寅恪先生也在《元白诗笺证稿》一书中对《莺莺传》研究的几个焦点问题发表看法:“《莺莺传》中张生忍情之说一节,今人视之既最为可厌,亦不能解其真意所在。夫微之善于为文者也,何为著此一段迂矫议论耶?”[5]然后,作者仍然尝试给予解释。陈先生说:“唐世娼妓往往谬托高门。”这样一来《莺莺传》中所谓崔氏高门家世之身份也被置于可疑的地步,这就是站在元稹一边卑鄙莺莺的社会身份,替他开脱不道德行为,如此一来,张生的始乱终弃行为就变成一种纯粹的狎妓行为,无可厚非。概言之,鲁迅直接对作者的行为提出了道德批评,陈寅恪尝试对作者的“始乱终弃”的情节作出一定的回护,而这些阐释仍然不能给人以中的之感。
中唐贞元时期的元稹是“早有诗名,后秉节钺”的社会名流,要想全面理解《莺莺传》故事的矛盾之处,还需要从元稹其他作品的论述中爬梳更多的线索。作者在《叙诗寄乐天书》言道:“德宗皇帝春秋高,理务因人,最不欲文法吏生天下罪过。阃节将动十余年不许朝觐,死于其地,不易者十八九。而又将豪座复之处,因丧负众,横相贼杀,告变骆驿。适有人以陈子昂《感遇诗》相示,吟玩激烈,即日为《寄思玄子诗》二十首。……又久之,得杜甫诗数百首,爱其浩荡津涯,处处臻到,始病沈宋之不存寄兴,而讶子昂之未暇旁备矣。”[6]从这段元稹对时局的认识和作者的文学观点来看,元稹是一个关心时事的严肃作家,虽然有留恋少年狎妓的思想,断不至于把这些事情弄到士大夫沙龙场合评头论足。诚如胡适之所谓“这样的世风,使得元稹他们觉得这不是文人嘲风雪、弄花草的时候了,他们都感觉文学的态度应该变得严肃了”[7]。但是作者怎么会写出与自己创作理念相违背的不严肃的作品呢?然而,对张生这种不明不白的“始乱终弃”行为,与元稹同时代的人却是认同的,他们认为张生“善为补过”。宋代以后,越来越多的人认可元稹的行为是“恶趣说”,批评他不但犯了“始乱终弃”的错误,还到处播弄绯闻,真真是突破了文学研究者、阅读者的道德极限,远非“恶趣”二字即可为之辩解的地步;金元时期,以王实甫的《西厢记》为代表的作家对《莺莺传》故事主题进行了颠覆性的改编,使得这个在原作品中被离弃的女性,在舞台上得到了完美的结局,寄托了人们“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善良愿望,其实这种再改编的行为本身就是对《莺莺传》原作中张生“始乱终弃”行为的一种否定!
二、《莺莺传》是以“尤物论”为主题反思安史之乱的劝诫小说
安史之乱以后,唐代王室从开元盛世忽然跌落,中央政府对地方军阀藩镇的管控能力日益萎缩,而在思想领域内,当时士人对国家的中衰事件也在不断地进行多角度的反思。元稹《叙诗寄乐天书》对时局分析认为:德宗皇帝不愿生事,藩镇割据在外,朝廷大臣因循苟且,佛道二教相扇成风,国家的政治、經济、军事和文化处于剧烈的衰微过程之中。这基本上是元稹对时代的认识,同时作者也表达了自己“思欲发之久矣”的救世创作思想,《莺莺传》也正是作者这样“思欲发之”的反思作品!黄大宏先生认为:“这一由宫廷宗室女性的政治、道德失范为基本内涵的唐代前期政治、婚姻关系史,作为元稹的历史视野,潜伏在士人私情故事的背后,成为《莺莺传》主题生成语境的一个方面。……抛开以爱情传奇与元稹自寓为研究前提,而是把《莺莺传》当作唐代中期士大夫对抗唐代前期历史政治的一次反思。”[8]实际上,陈寅恪先生认为:“《会真记》中有元微之一段迂腐论调,其中莺莺的譬喻也是欠妥当的,启动对应的比喻也是欠妥当的。若把它放在杨贵妃身上倒挺合适。白居易看出了这个缺点,写了《长恨歌》,《长恨歌》才适合元稹那个论调。”[9]陈先生灵光一闪把《莺莺传》和《长恨歌》联系在一起,可惜未能继续深入下去,忽视这两篇传奇内在的联系性!实际上,二者完全可以联系在一起,甚至《莺莺传》能和更多的作品联系在一起,其中元稹的《连昌宫词》,陈鸿的《长恨歌传》具有时代文化共振的内在联系,是一篇中唐士人反思安史之乱的劝诫之作,不可仅仅目之为风情小说。
《莺莺传》是元稹“思欲发之久矣”的寄托之作!元稹在《莺莺传》中这样表述:“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贵,乘宠娇,不为云,不为雨,为蛟为螭,吾不知其所变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据百万之国,其势甚厚。然而一女子败之,溃其众,屠其身,至今为天下僇笑。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10]所以,说研究者只把“《莺莺传》视之为个人私生活经历的回顾以及对个人道德情感的辩解是不够的”[11],实际上,元稹的“尤物论”得到了时人的肯定,“于时坐者皆为深叹。”白居易、杨巨源、李绅诸人多有肯定《莺莺传》立论的唱和之作。先来看看李绅为《莺莺传》的唱和之作:“伯劳飞迟燕飞疾,垂杨绽金花笑日。绿窗娇女字莺莺,金雀娅鬟年十七。黄姑上天阿母在,寂寞霜姿素莲质。门掩重关萧寺中,芳草花时不曾出。”[12]再来看看白居易的《李夫人》诗累举几个溺于私情而亡家破国悲剧人物后说道:“生亦惑,死亦惑,尤物惑人忘不得。人非木石皆有情,不如不遇倾城色。”[13]白居易在《古冢狐》中说得就更为直白:“古冢狐,妖且老,化为妇人颜色好。……狐假女妖害犹浅,一朝一夕迷人眼。……何况褒妲之色善蛊惑,能丧人家覆人国。”[14]以为狐媚害人的女人有丧家覆国的祸害。同时代的作家陈鸿在《长恨歌传》的结尾中写道:“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15]诸位作家在“尤物论”方面达成了共识,这是中唐时代士人对安史之乱的集体文化反思。
何为尤物?尤物的基本含义有两层,一为绝色美女;一为珍奇之物。《春秋左传》中开始出现“尤物”一词,意为特别漂亮的女性。故事记载的是晋国大臣叔向想娶楚国大夫申公巫臣的女儿,然而叔向的母亲不同意这门婚事,用“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义,则必有祸”[16]来劝诫自己的儿子。她认为美女足以能改变一个人,如果没有德义的话,早晚会带来灾祸,这应该也是元稹“以德胜尤”的思想来源。欧阳修在《伶官传序》所谓“智勇多困于所溺”[17]之论。人们在生活中被各种欲望左右,如果客体蕴含了主体所强烈关注需要的内容,主体在客体面前失去了自我,失去了价值判断,作为“尤物”的客体的存亡离合能引发主体强烈的情感波动,足以夺人魂魄,“不觉自失”是一个恰当的词汇。在这里,尤物非专指女性,大致也可以认为是那些自己驾驭不了的欲望。
具体到《莺莺传》作品本身,在普救寺那一刻,莺莺就是“张生”眼里的尤物,他神不守舍,心神摇荡!她有才调,通音律,会吟诗,有胆略,敢于行动,是个“颜色艳异,光辉动人”[18]的尤物!那么,作为劝诫文的“尤物”,元稹暗喻谁呢?元稹的《连昌宫词》给出了答案:“开元之末姚宋死,朝廷渐渐由妃子。禄山宫里养作儿,虢国门前闹如市。弄权宰相不记名,依稀忆得杨与李。”[19]在这里,对比历史上的“昔殷之辛,周之幽”,引发唐代王室国运衰微的“尤物”就是杨玉环,“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貌华服参差是”[20],这才是《会真记》之“真”。《莺莺传》里面莺莺送别张生之际,“因命拂琴,鼓《霓裳羽衣序》,不数声,哀音怨乱,不复知其是曲也”[21]。《霓裳羽衣序》是唐明皇和杨玉环游玩之际的代表曲目,白居易也有“惊破霓裳羽衣曲”之句,恰恰说明了《莺莺传》的主题命意之所在,文章在处处影射李杨之悲剧!
《莺莺传》的这种“尤物论”也为后世作家认可。宋代苏轼的《荔枝叹》云:“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永元荔枝来交州,天宝岁贡取之涪。……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22]如何克服尤物,战而胜之?元稹的《莺莺传》提出了两种胜尤之策:一是“以德胜尤”,二是“忍情补过”,他的见解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于时坐者皆为深叹。”对比之下,张生能“忍情胜尤”,玄宗不能忍情终致败亡,高下立判,作者劝诫之意不言而明。故而李绅、杨巨源、白居易诸人为之唱和,其立意不言自喻矣!然而,元稹的隐喻并不到此为止,贞元年间,宪宗皇帝多内宠,不立皇后,而郭贵妃、穆宗势力潜滋暗长,直到最后,宪宗死于皇宫内部的政治争斗中!元稹的《莺莺传》诚可谓切中时弊之作。
三、从 “尤物论”主题角度考察《莺莺传》的文本建构
前人研究《莺莺传》经常问元稹为什么要写《莺莺传》?崔莺莺是不是确有其人?张生和作者元稹之间是不是存在着某种自寓关系?张生为什么抛弃崔莺莺?如果从“尤物论”主题角度考察《莺莺传》的文本建构出发,前人一系列的研究疑问于此便可涣然冰释。《莺莺传》的爱情叙事应该服务于文本的劝诫命题,篇尾的“尤物论”是作品的曲终奏雅!
首先,元稹为什么要写《莺莺传》?这里面既有从时代背景上考虑,也有元稹本人的主观原因。中唐以来,国家从开元天宝年间的极度繁华,跌落到安史之乱之后的社会动荡,这就引起当时的中唐士人对一系列历史的反思。杜甫的《忆昔》最能反映这种时代情绪:“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百余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岂闻一绢直万钱,有田种谷今流血。洛阳宫殿烧焚尽,宗庙新除狐兔穴。伤心不忍问耆旧,复恐初从乱离说。小臣鲁钝无所能,朝廷记识蒙禄秩。周宣中兴望我皇,洒泪江汉身衰疾。”[23]而对于安史之乱的发生,许多诗人把原因归结于唐玄宗宠幸杨贵妃和任用杨门贵戚杨国忠的这些事件。杜甫《北征》:“忆昨狼狈初,事与古先别,奸臣竟菹醢,同恶随荡析。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周汉获再兴,宣光果明哲。”[24]实际上安史之乱的发生有政治、文化、经济、军事的多种因素,而普通民众则更多地把注意力倾注到天宝年间李杨爱情故事之上,“女人尤物”成为他们反思安史之乱的主流论调,这就是元稹写作《莺莺传》的时代背景。同时《莺莺传》的写作也有元稹本人的主观原因,他在《叙诗寄乐天书》言道:“阃节将动十余年不许朝觐,死于其地,不易者十八九。而又将豪座复之处,因丧负众,横相贼杀,告变骆驿。……仆时孩呆,不惯闻见,独于书传中初习理乱,萌渐心体,悸震若不可活,思欲发之久矣。”这表明元稹对时代有着清醒的认识。同时,元稹作为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强烈关注社会现实的精神,必然使他也要反思这些历史重大事件!刘成荣先生认为:“元稹以明经及第,熟悉儒家的经典著作,有模仿《左传》的主客观条件。”[25]当他读到《左传》的“尤物论”一节,仿佛感到历史的再现。刘成荣先生论述元稹的创作动机诚可谓中的之言,“元稹创作《会真记》,并非要追忆早年未果的爱情,而是他受中唐政治变革的时代潮流影响,依托于自己的读书经历,做一次经学论政的尝试,其中虽然有较多封建俗见,……但仍不失为一篇成功表达政治立场的习作。”[26]元稹写《莺莺传》本意是要“使知之者不为,为之者不惑”以垂戒将来。此诚乃元稹写作《莺莺传》的主客观因素。
其次,崔莺莺是不是确有其人?这个问题也是宋代王铚《传奇辨正》之后一直纠缠不清的重要问题。其实,如果考虑到元稹作《莺莺传》之先存在着一个“尤物论”的创作主旨,而崔张俩人的角色设定就必须首先服务文本主题的表达!人物角色的真实性就不是必需的因素,当然可以采取鲁迅先生“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的创作方法。考察崔氏的真实性之前,首先要意识到这也是作者要塑造的一个艺术典型,是作者表达“尤物”形象的具体体现者。崔氏之“尤”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颜色“尤”,“垂鬟接黛,双脸销红而已,颜色艳异,光辉动人。”“娇羞融冶”“娇啼宛转”,莺莺首先是一个颜色艳异、光辉动人的美女。其次,莺莺之才具尤胜才貌一筹,“崔氏甚工刀札,善属文,求索再三,终不可见。往往张生自以文挑,亦不甚睹览。大略崔之出人者,艺必穷极,而貌若不知;言则敏辩,而寡于酬对。待张之意甚厚,然未尝以词继之。时愁艳幽邃,恒若不识;喜愠之容,亦罕形见。异时独夜操琴,愁弄凄恻,张窃听之,求之,则终不复鼓矣。”最后是崔氏门第“尤”,陈寅恪有这样的论断:“唐代社会承南北朝之旧俗,通此二事评量人品之高下。此二事,一曰婚,二曰官。凡婚而不娶名家女,与仕不由清望官,俱为社会所不齿。”“元稹作《莺莺传》,直叙自身始乱终弃之事迹,绝不为之少惭,或略讳者,即职是故也。”[27]且兼“崔氏之家,财产甚厚,多有奴仆”,颜色尤、才具尤、门第尤、财产甚厚,这是多少青年男子艳羡的对象!这里也可以认为是作者夸张的写法,目的要营造出崔氏之“尤物”意象,其间或许有元稹个人的情感经历在里面,但是读者不必拘泥于某一个具体的人物。陈寅恪先生对《读莺莺传》进行了细致地研究,推翻了“莺莺乃高门女子”的观点。目莺莺为一般“娼妓”[28]自托高门,委婉地为元稹不道德行为进行辩解,实属多余,因为这里所谓的“高门”乃作者刻意经营之情节,以显示莺莺的名门贵媛的身份,加剧这个“尤物”对张生的心理冲击,实际上崔莺莺这种容貌、才具、门第之尤,加深了我们对女主人公的同情直至今天,小说家言不必为之坐实而过分解读。
张生和作者元稹之间是不是存在着某种自寓关系?陈寅恪先生认为“张生”就是元稹自己:“《莺莺传》为微之自叙之作,其所谓张生即微之之化名,此固无可疑。”[29]其实不然,张生的存在实在是为崔氏的存在作铺垫而已,也是一个艺术典型的塑造。张生越是对莺莺感到女神般的存在,更衬托出崔氏之尤艳绝人!考察张生得到莺莺之前的心理状态,诚可谓宠辱皆惊:“垂鬟接黛,双脸销红而已,颜色艳异,光辉动人。张惊为之礼,因坐郑旁。”“张自是惑之,愿致其情,无由得也。”“翼日,婢复至,张生乃羞而谢之,不复云所求矣。”“张大喜,立缀春词二首以授之。”“红娘寝于床,生因惊之。”“张生且喜且骇,必谓获济。”“张自失者久之,复逾而出,于是绝望。”“数夕,张生临轩独寝,忽有人觉之。惊骇而起,则红娘敛衾携枕而至。”“张生拭目危坐久之,犹疑梦寐,然而修谨以俟。”“张生飘飘然,且疑神仙之徒,不谓从人间至矣。”“张生辨色而兴,自疑曰:‘岂其梦邪?”作者采用这一系列词汇“惊”“惑”“几不自持”“惊之”“自失者久之”“惊骇”,表达了崔氏之“尤”引起张生的“宠辱皆惊”“几不自持”不觉自失的种种羞态,也正显示出莺莺作为“尤物”使得张生不能把控自己失去自我的精神状态。作者在张生失态之前,先作了一段铺叙:“有张生者,性温茂,美风容,内秉坚孤,非礼不可入。或朋从游宴,扰杂其间,他人皆汹汹拳拳,若将不及;张生容顺而已,终不能乱。以是年二十三,未尝近女色。知者诘之,谢而言曰:‘登徒子非好色者,是有凶行。余真好色者,而适不我值。何以言之?大凡物之尤者,未尝不留连于心,是知其非忘情者也。诘者识之。”[30]这段话的意思告诉我们,张生自高身价,是不容易失态的人!然而见到莺莺之后,这个“内秉坚孤,非礼不可入”的人却完全沦陷了!张曰:“余始自孩提,性不苟合。或时纨绮间居,曾莫流盼。……昨日一席间,几不自持。数日来,行忘止,食忘饱,恐不能逾旦暮。若因媒氏而娶,纳采问名,则三数月间,索我于枯鱼之肆矣。尔其谓我何? ”这一段是从张生的角度描写崔莺莺惊艳绝人之美,以至于这个“年二十三,未尝近女色”“性不苟合”“内秉坚孤,非礼不可入”老实人彻底沦陷缴械投降了,正是为了证明崔氏“尤物之尤”!这段文字把人物的心理刻画得惟妙惟肖,以至于人们都认为这是元稹自己的人生经历。张生并不等于元稹,唐人从来没有认为是元稹自叙,宋人始加附会。这种附会不无道理,元稹把青年男女恋爱时刻的那种患得患失、宠辱皆惊的心态写得令人胆颤!写出了青年男女恋爱之际那种如痴如狂的精神状态!元稹以诗出名,宫中“呼为才子”。《莺莺传》中情感波动描写是否也可能是作家一些亲身体验过的生活感情呢?当然也是有的。考察元稹的《梦游春七十韵》云:“逡巡日渐高,影响人将寤。鹦鹉饥乱鸣,娇娃睡犹怒。帘开侍儿起,见我遥相谕。……不辨花貌人,空惊香若雾。睡脸桃破风,汗妆莲委露。……鲜妍脂粉薄,暗淡衣裳故。最似红牡丹,雨来春欲暮。”[31]这些描寫也很像《会真记》中的莺莺。在这里,刻意把崔莺莺坐实为某个女性似无必要,作者真正要表达的是“尤物”给人带来那种宠辱皆惊的一种情绪,一种失去自我情深状态!这种情绪在作者看来是有害的,它会使人失去了价值判断,做出一些非理性的事情,这不是儒者所要求的理性中庸状态。张生也只是一个艺术形象,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其间或许渗透了元稹自己的生活经历。霍松林先生在《略谈〈莺莺传〉》中认为: “《莺莺传》中与史实相符的部分只能说明元稹的《莺莺传》植根于生活的沃壤。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它里面的人物张生并不是元稹,如崔莺莺并不是崔鹏的女儿或某一个娼妓,而是艺术典型,把《莺莺传》完全看成元稹的“自传”,这种说法是应该抛弃的。”[32]诚乃中的之论。
元稹为什么会抛弃莺莺?陈寅恪解释说:“舍弃寒门,而别婚高门,当日社会所公认正当行为也。”[33]《莺莺传》中张生始乱终弃就是这种问题观念的必然结果。张生的经历可能是元稹的“某一次”经历,但张生作出的抛弃莺莺决定,却是作品必须作出的必然选择,是作品主题内在的规定性。实际上,从恋爱心理学角度而言,张生未必会抛弃莺莺,但是元稹为什么会抛弃莺莺?是劝诫文的文本建构的前置设定,如果张生不抛弃崔莺莺,就达不到“忍情绝尤”的文章效果。元稹为什么抛弃崔莺莺?研究者替元稹开脱了数十种理由,而忘了本文的宗旨“忍情胜尤”,因为自己不能“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所以,文本中抛弃莺莺是劝诫文创作需要。崔张为什么分手,不是张生不爱莺莺,也不是什么身份问题,作者的命题立意需要他们分手,作者“忍情”的解决问题的方法需要主人公分手,如果不分手,作者完不成劝诫的主题,仅此而已。作品的主人公需要出来告诉你一件事情,要“以德胜欲”“忍情胜尤”,张生抛弃莺莺,是“以德胜欲”“以德胜尤”的文理要求,文本的建构需要完成需要如此!这就说明了《莺莺传》不是一部即兴之作,而是一部深思熟虑之作,用我们今人的文学批评语言来说,《莺莺传》是一部“主题先行”的作品,张生“忍情胜尤”议论文字正是作者曲终奏雅之意。阅读者认为《莺莺传》中女主人公最后被遗弃是一场爱情悲剧,引起阅读者强烈的情感不适,故而有各种版本《西厢记》对这个题材再开拓,其实不然,这种悲剧效果是作者刻意经营的效果,是文本建构的内在要求!作品中莺莺的失恋是人生个体的小悲剧,而唐王室李杨爱情故事引起的亡家破国之祸才是大悲剧。贞元年间,宪宗皇帝多内宠,不立皇后,而郭贵妃、穆宗势力潜滋暗长,直到最后,宪宗死于皇宫内部的政治争斗中!玄宗的故事应该足以引起宪宗皇帝“忍情补过”“以德胜欲”的鉴戒,才是作者要表达的真正内容!
结 语
元稹的《莺莺传》首先是一篇中唐士人对唐代安史之乱进行反思的劝诫文章,其次才是一部描写唐代人爱情故事的传奇小说。元稹对唐玄宗为杨贵妃这个“尤物”所困,一不能“以德胜尤”,二不能“忍情补过”,终于导致安史之乱的政治灾难提出严厉批评。作者的观点得到了当时士人阶层的普遍理解和支持,李绅的《莺莺歌》、杨巨源的《崔娘诗》、白居易的《李夫人》和陈鸿《长恨歌传》诸人的唱和之作,进一步强化了作者“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的劝诫命题,也对宪宗皇帝“多内宠”的政治生态提出了委婉地警醒,是中唐士人反思安史之乱的劝诫文。元稹在写作过程中对爱情故事的渲染,使得作品实际上出现了形象溢出主题的情况,但是不能否认作者主题先行对文本角色人物、情节架构的剪裁痕迹。
基金项目:2022年河南兴文化工程文化研究专项项目(项目号:2022XWH202);2022年度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项目号:22A36)
参考文献:
[1]吴伟斌.《莺莺传》的写作时间浅探[J].南京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86年(1):100.
[2]鲁迅.唐宋传奇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06.
[3][宋]赵令畤.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侯鲭录·卷五[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065.
[4]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65.
[5][27][28][29][33]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116,113,107,108,113.
[6][唐]元稹.元稹集[M].北京:中华书局, 1982:531-532.
[7]胡适.白话文学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 1996:313.
[8][11]黄大宏.《莺莺传》中唐政治文化变迁与唐传奇诗法叙事的典型读本[J].东方论丛,2005(3):51,56.
[9]陈寅恪遗作,刘隆凯整理.元白诗证之《莺莺传》[J].广东社会科学,2003(4):48.
[10][18][21][30][宋]李昉.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1:4016,4012,4015,4012.
[12][19][23][24][31][清]彭定求.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5493,4612,2324,2275,4635.
[13][14][唐]白居易.白居易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83,88.
[15][宋]李昉等.文苑英华[M].北京:中华书局1966:4201.
[16]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1492.
[17][宋]欧阳修.新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1:397.
[20]谢思炜撰.白居易诗集校注[M].北京:中華书局,2006:944.
[22][宋]宋苏轼撰, 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 1982:2126-2127.
[25][26]刘成荣.《会真记》与《左传》——兼论元稹传奇创作的动机[J].井冈山大学学,2013(3):86,89.
[32]霍松林.略谈《莺莺传》[N].光明日报,1956-5-20.
作者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