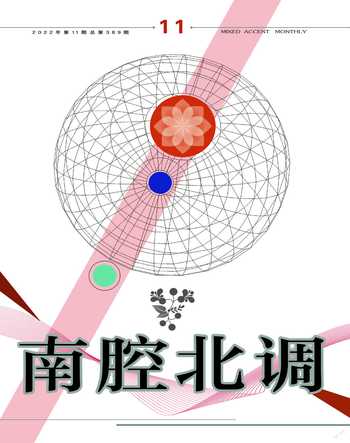超越政治和男权双重宰制的西施
刘成勇

自2016年以来,柳岸陆续推出了“春秋名姝”系列长篇小说,包括《公子桃花》《夏姬传》《文姜传》《西施传》四部。四部长篇小说卷帙浩繁,以春秋时期四位极具代表性的女性——息妫、夏姬、文姜、西施为主人公,展示了波诡云谲的春秋历史,其中既有对春秋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宏大叙事,也有对家庭、人性等的微观书写。“春秋名姝”系列小说在切近历史的基础上,以新历史主义的人文精神赋予笔下人物以鲜活生命和鮮明性格。尊重历史、尊重人物的严肃创作态度,使“春秋名姝”系列既有密实的历史知识,又有文学虚构与想象的美学价值。
《越女夷光——西施传》(以下简称《西施传》)是“春秋名姝”系列的最后一部。相比较而言,《西施传》是该系列中写作难度最大的一部。首先,史书中关于西施的信息语焉不详。比如,历史上到底有没有西施这个人,各有不同的说法。如果西施确有其人的话,她的最终结局是像《墨子》说的沉江而亡,还是《越绝书》认为的与范蠡“同泛五湖”?这也是模棱两可。其次,文学作品对西施的形象塑造比较单一僵化,要么渲染西施沉鱼落雁的美色,要么在政治道义层面肯定西施的爱国行为。但无论何种叙事,西施始终是一个被言说的客体,她的主体思想、内在情感无从表现。再次,与息妫、夏姬、文姜相比,西施没有她们的高贵身份,在历史事件中也缺少话语权。事实上,“美人计”只是文种灭吴九术中的一术,在吴亡越兴的历史嬗变中并不起主要的或关键性作用。西施与政治的密切关联,只不过是一种历史想象和话语渲染的结果。
因此,如何延续前三部的风格,将人物形象与历史事件有机结合在一起,是柳岸首先要面对的问题。在《西施传》中,柳岸设置了两条情节线:一条线讲述西施的出生成长,一条线讲述吴越两国强弱的此消彼长。同时,小说将这两条情节线有机贯通在一起的,又有两条线:其一是西施出生时出现了“竺萝红光”的异象。小说的第一章,“竺萝红光”出现在吴王阖闾的梦中。这道红光,给吴国的命运和前途笼上一层隐隐不安的阴影。小说结尾,王孙骆向夫差揭破了“竺萝红光”与吴国命运的神秘关联。以红光始,又以红光终,小说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结构。其二是范蠡在叙事中所具有的起承转合的作用。小说通过范蠡的视角,一方面表现了西施的成长及其在成长中表现出来的智慧和识见,另一方面表现了政治军事纷争的风云变幻。
另外,贯通全文的还有谍樟这个人物。在小说开头中,伍子胥的亲信谍甲探寻到“竺萝红光”与西施出生之间的关联,便有了将其除掉的想法。但一想到自己的女儿与眼前婴儿一模一样,心中又有不忍。多年之后,谍甲行刺西施,事败被杀,妻女被收入王宫为奴。谍甲的女儿就是谍樟。西施偶然发现谍樟与自己极其相像,于是将其收在身边,以备患病时由谍樟替代自己侍奉夫差。作为西施的影子,谍樟的存在不仅给小说增添了趣味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情节走向,深化了作品意蕴。比如围绕谍樟怀孕,作者写出了西施不能为夫差生子的遗憾、夫差有子嗣传承的欣喜、范蠡以为西施怀的是夫差孩子时内心酸楚等,反映出人物心绪的复杂微妙。
从总体来看,作者借鉴了中国古典小说“草蛇灰线”的写作技法,巧妙布局,穿针引线,给读者一种阅读上的心理期待。
在这种经纬纵横的结构中,小说展现了西施跌宕起伏的传奇一生。与大多数西施题材的文艺作品相同,西施不仅美貌出众,而且聪明智慧,比如发现吃香榧子的方法并教于乡亲。但这样的西施形象,并没有超出既有的文学叙事规约。相比之下,《西施传》所塑造的西施形象最值得被肯定的地方,在于刻画了一个内心矛盾的西施,一个具有现代女性意识的西施,一个有着悲剧命运的西施。
西施固然是肩负着“灭吴”的重任来到吴国,但随着与夫差交往的深入,竟然对这个作为敌人的男人有了一种依恋的情愫:“只有在这个男人怀里,她才可以这样任性地哭啊!”
其实在西施的心中,夫差有着两重身份:夫差既是一国之君,又是一个有情之人。如果说一开始夫差惊诧于西施的貌美,那么渐渐地就有了对西施的情感之爱:“这女子仿佛是他前世之缘,没什么抵得上她在他心里的分量”,“他只想和她这样待着,宛如水中雎鸠。”[1]他耗费巨资,给西施建馆娃宫、离宫。西施何尝感受不到夫差的良苦用心?吴国战败后,想到夫差可能会有的死亡结局,“她的心中全都是她和吴王恩爱的情景,花间醉卧,洞中依偎,舟中揽扶,同歌偕舞,琴瑟合操……君王为她宽衣解带,梳理妆容,插钗及笄,穿襦着舄……”[2]西施对两个男人动过感情:范蠡和夫差。但感情的程度不一样:“她对范子的感情,不过是人对神的敬仰。而她与吴王的恩爱,才是真正的男欢女爱。”[3]
范蠡也是发自心底地喜欢西施。但为了“越国必霸”的“宏图抱负”,他亲手将西施送到吴王宫。如果说作为男性的勾践、夫差贪恋于西施的美色,体现出男性对女性的身体欲望,那么在范蠡这里,则最能表现出男性追逐权力的政治性本能。
西施也许感受到了范蠡对她的爱中掺杂的功利性,同时她也真切感受到了夫差对她“全心全意”的爱。两相比较,她的复仇意志在不断地摇摆动摇。这种“人性的软弱”表明西施不再是一个功能性人物,或一个工具性人物,而是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生命主体。西施内心的种种纠葛,既是儒家集体伦理与个体生命伦理之间冲突的反映,也是男权话语与女性自我之间碰撞的结果。
尽管西施居于政治斗争的漩涡,但小说写出了她被动卷入的过程,以批判男权文化争夺权力的欲望化实质。少女时代的西施,她的思想观念并没有上升到形而上的国家层面。在邑市上听到了越国被打败的消息时,“她并不知道国家出现了那么大的变故,她只是觉得自家遭受了不幸,有些忧伤,可也不知道该怨恨谁。她觉得吴王、越王都离她太远,也许这一辈子都不会见到他们,恨他们又有何用?”[4]
是的,王权更迭,与一个乱世中的女子有何干系?那不过是由男性欲望激发的权力之争,女性只不过是其中的祭品。就像西施这样,承受了她不该承受之重:“馆娃宫、响屧廊、高景离宫、养心亭,都是吴王对她的宠爱。越国、土城宫、诸暨邑、苎萝山,范子的恩典,故国的情怀,故土的养恩,越王的厚望。西施,不过一介弱女子而已,而这一切重负,情何以堪啊?” [5]
奔赴吴国固然是西施自己作出的决定,但那也是因为范大夫需要,越国需要,也是为兄长薪男报仇的需要。范大夫也好,越国也好,兄长也好,都是男性话语对西施身体的询唤。作出决定之后的西施,也是怅惘踌躇,将这一切归为“命数”:“不是谁想去,或者不想去。想去不一定能去,不想去也许必去。谁又能知道结果呢?”[6]
不仅西施不知道最终结局如何,小说对西施最终结局的处理也远远超出我们读者的预料。以往文艺作品中的西施故事,一般是在越国灭吴后,西施或泛湖而去,或沉江而亡。但无论何种结局,总是草草收场。在结局方面,《西施传》提供了西施另外一种可能:隐居。
隐居即是逃离。不仅是逃离纷扰的现实世界,也是逃离男权话语世界。男权话语下,西施要么因其被认为是红颜祸水而被鄙视唾骂,要么因其助越灭吴而被肯定颂扬。但无论如何,西施都是男性权力角斗的政治筹码。她是一个发不出任何声音的空洞能指,一个在场的隐匿者。就像小说中所说:“吴王宫里这个女子,叫西施,只是一具没有灵魂的尸体。”[7]
经历过世事浮沉,西施开始安排好自己的后半生。一方面她让谍樟冒充自己嫁给范蠡,算是“不负如来不负卿”;另一方面她隐居于檇李林,在萧条孤寂中度过余生。即使发现远道而来寻找自己的范蠡,她也是视而不见——有意味的是,当“看与被看”的性别视角颠倒過来,曾经被奉若神人的范蠡再也没有昔日的风采:“那身影不再挺拔,苍老而佝偻……那步履不再矫健,孤独而蹒跚……”[8]
西施的这些主动行为,意味着她超越了政治话语和男权话语的双重宰制。即使不能颠覆男权话语,却可以“成为我自己”。至此,西施的悲剧形象从吴越争霸的宏大叙事中逐渐显影。拥有个体生命的西施也拥有了独立的思考,就像结尾处她对世事的勘破:“世事若梦,亦真亦幻,皆如云烟,天地各有其道,人事自有定数……何人又能独处其外。”[9]与之前的身不由己相比,此时的西施显然已超越性别困境,而对人类存在发出终极性追问。西施发出如此的感叹,是在檇李。檇李曾经是“吴越之争的战场,厮杀尸骨,胜败交迭,霸起霸落” [10],而眼下只剩下苍茫荒漠。光阴轮转,世事沧桑,林子间回荡着“胡姬凤仪”奏出的凄婉琴声,越发显得西施之言格外悲怆。
既有文艺作品中的西施,以客体化的美人身份参与历史叙事,其政治属性掩盖了应有的人文属性。柳岸在继承西施既定文学形象的基础上,由生命、人性、情感等入手,以女性意识为底色,写出了西施摇曳多姿的一生,赋予她生命的温度和人文内涵。就此意义而言,《越女夷光——西施传》将“西施故事”推进到了新的历史高度!
参考文献:
[1] [2] [3] [4] [5] [6] [7] [8] [9] [10]柳岸.西施传[M].北京:作家出版社,2022:289,374,374,147,301-302,216,289,404,404,404.
作者单位:周口师范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