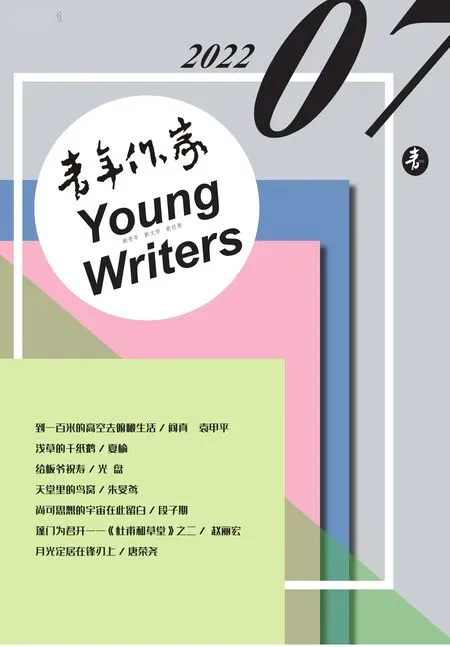水 影
成都市树德中学光华校区高2019级 杜亦豪
太阳底下,一群人被推进了电动门内。外面的人向他们招手,或是从一旁的窄道进去,负着绿麻的或蓝黑的布袋。诸多颜色在半空中举着托着顶着并伴随一片荫翳向园中走去。
这本是不必要的,在原初进校过程中不必这样的陪同与监督,正如押送一群犯人只需四五持械者即可。言语与公告板已是最好的武器,它将指示我们在某一栋某一单元某一层某一间某一床放上我们的布袋,然后打开,铺上,并依照喇叭或铃声的指定程序走向另一栋另一层另一间另一桌。与生俱来的提线使我们甚至不用某人的实际操作便可完成上述工作,这对于大部分人而言都是极好的。
然而,麻袋在半空中悬浮着的不确定因素显然搅扰了既定秩序。袋子在空中相互彼此又彼此相互,或由此至彼由彼至此的碰撞甚至旋转甚至迷路造成了极大不便。熙攘间充满着这样的对话。请问某某班在哪里?哦,您也是送学生的吧?没错。是第一次来吧。诚然如此。当然如此。你也问过其他人了吗?是的。那么,还该问谁呢?没有问过的。已经问过的。似乎问过的。似乎没有问过的。那怎么确定谁有知道此事的可能性呢……诸如此类的对话在这短短的上午继续重演,直至命令与呵斥盖过了疑问才让这个上午彻底浪费。
上楼者左,下楼者右。靠栏者男,靠墙者女。入前门者短发,入后门者长发。在一段极尽言语亦难以描述的庞大汇流后,这份临时的权威终于得以暂时休息——每个人都依照某种理性规定在错综对立的迷宫中找到自己相应的位置,受一系列的精心安排隔除了可能或本就不可能或已经或尚未发生的反应——在他们眼里看来。
一刻钟后(如此精准的)开始响铃,这时的我们注意到彼此。阳光如游鱼落到身上,滑向地面,短发留着银亮的水迹(穿过云穿过雾,穿过丁达尔效应)。这立身与回位的时间便又是一刻钟。这将使他们恐惧,那是料想之外的——那光线随线条与银鱼流去,流到晚上和月亮下的池子里。淡金色的石砖残存白天的记忆,钩上月弦镌出迷蒙的梦乡与符号。
两刻钟结束。可以离位。讲台上宣布。六面体的教室被各样的影子扰动。地面碎白石纹积满了阴影间留下的水洼并随着双足的踏入而隐隐颤抖,于是很快缩回窗外的叶子上,从叶子缩回了太阳上。我起身,实在无法忍受,我一定要出去,倚在栏杆上。
为什么要这样。那一头短发走向我(长发中的短发,你的青丝从两鬓垂向双肩。如春之瀑,如泉之歌。你不属于前门与后门。)今天阳光真好,干嘛要这样趴在栏杆上(你的言语,你的言语。)这样有什么问题吗?小姐。朱栏谁欲倚,背月望秋思。栏杆是留给月亮的(月亮,月牙。你的月牙,弯弯的月上投下的目光。深邃的池影。成群结队的梦,为寻求解脱而投入你的秋波深处。)是留给晚上的吗?我说。只是夜晚的消解正是留给白日剩下的悒郁的。将栏杆留给月亮,实在可惜啊。不过白天靠在栏杆上总归是不好的,请陪我下楼吧。她说。
他发现了这个女孩的不同,这样的不同是天生的。在他跟随于她身后的时候,目光也紧紧地跟随着她的脚步。她的步态很特殊,每一次前行都同秋千一样微微摇摆,这是一种天然的率真。脚尖的轻跳以某种独有的节奏进行。她的生命打着拍子,令生活在内外的人都听得无比清晰。对于他而言,即使在许久之后的栏杆旁,他也将突然想起这个下午。那是一个秋天。
待在后面干什么?她停下来,她看着我,而我却忘记移开目光。快下来呀(惊喜吗?恼怒吗?嗔骂吗?诧异吗?)我从楼道的拐角走向她,淡黄色的花折射到她的脸上,眼角沾着点点花粉(星光洒在月牙泉边,我骑着骆驼,四蹄在沙上发出棉被的摩擦声)。我把视线挪开。我们要去哪里?我的视线在远远的高楼,棕褐色的砖瓦指向无云的蓝天,太阳在玻板上隐隐浮现。一束目光突然飞向我,我用余光接住。下楼有目的,下楼有目的吗?她突然笑起来,拍拍我的肩。你啊,这么个人呐。便从一旁走去,嘴角似乎还留着刚说完的句子。一瞬间,我隐隐感觉她还在看着我,但她没有扭头,她在等我跟着走。
我缓缓移向她,却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凡事都有目的的话的确无聊。我试图告诉她什么。若是都有目的则意味着必有始终。只是她似乎知道我要说什么。你说得对呐。她也缓下步子。不如就这样漫无目的地走吧。那曾是我要说的话。这样就没有始终了。她望向我的眼睛,似乎在等待什么,但她却告诉我,我的眼眶红了。
暮色浮在她的脸上。
夜晚比风还要深。在你犹豫的片刻中,他们站在门口的路灯下。我先走了。嗯。她斜着头,似乎在打量我。怎么了?没什么。
她笑得更灿烂了。
路旁被黑色裹着的树或是灯统一地躬着身子,如果仔细察看便可以发现个中缘由。事实是,即使它们在白昼的太阳底下多么笔直,它们也无法承受上面的黑色或是地上的黑与白色。因此,它们不停地颤抖以保持一种相对固定的姿态来证明其合理性与确定性。这对于夜晚是件麻烦事。在它尝试使之解构、消逝或者放开的东西中,都有上述这般类似的耐力——属于事物天然本性的抵抗而又在我的世界里困惑着、欺骗着、隔离着、提防着、潜在着,出露于水面、池面、湖面、海面、江面、河面、盆面、碗面、杯面,然后在一段漫长的窒息里继续存在。
杯子,倒扣在整个世界的头上,以便各种黑色的液体连带各处在头顶在边缘的白雾流往地面——我置身其中,脚也深陷其中,如果说得更彻底的话,我简直即将成为它了。四处交融的乳汁。无处干涸,无处逃逸。栏杆在道路一旁无限向远方延伸。无数棵梧桐在身后跟着我,枯掉的叶子在翻飞,我在栏杆上,听着,倚着,摇摆着,挣脱着,我也成了梧桐叶。我被卷向你。翻滚的铁栏与折叠闪动的光在远处,在上空,在地面。我回到面前。一个人走在前面。他在正前方,盲道上。四周漆黑一片。但引起我兴趣的不是他的姿态或是他沿盲道行进,而是他的模样。那个方形的背影。四段笔直而彼此垂直的线条构成后脑的头像。换一个角度,便可以这么说。他的脑袋就是一个长方体,或者一个箱子。每一个棱角密封得如此完美。没有弧度的,标准的九十度。在这个箱子底下,有一个称得上是圆柱体的躯干并在某一部位分岔形成前后摆动的双腿。他左手拄着盲杖,似乎在前进。他在向深深处,向深深处。不过十分遗憾的是——即使他应当无法意识到——在这条通往夜或是东方黎明的路上,一根电线桩被置在盲道中央。此时,他离这根石桩仅有约十米的距离。在他的拐杖触及这杆子的前一刹那,他顿时停了下来,这兴许是出于本能——一个盲人对前方未知而正在凝结固化的空气的天然恐惧。他抬起盲杖向前试探,感知到物体的存在。不过这般知悉无足轻重——他依旧无法判断。你甚至能看到摇晃的方形脑袋与拐杖上晶亮的汗渍。他在思考、揣摩、分析、判断、总结。他有无数种选择。事实上,无数种选择面对着他。他可以选择往左、往右,或者后退或者绕道来摆脱他的窘境,以某种代价。另外,他的拐杖也能替他探寻更多的选择。比如他举起盲杖,以自己为中心转一个圈来检测除了他面前之物是否还有其他障碍。或者,他干脆就顺着这道往前走,以他自己本身来感知,然后让诸多未知塌缩、塌缩,在一个个世界里。但是,事实上,他什么也无法知道。你看到他的面前,感知的、看到的都比他多,却依旧什么也不知道。我在那里,是什么让我想起了抑或是看到了这些?我的眼里感官里。垂下的黑云即将无法承受不可言说的重量,它向下拉长、延伸,成了钟乳石的结构。有些已经触及高楼,有些离地面很远,有些停留在高远的穹顶上。清一色的墨滴,清一色的黏稠,清一色的冰冷——液体滴在我的脸上,开始是一滴,很快就无数滴。雨云不可遏制地向下塌陷。整个世界只留下它的声音。我奔向那个方脑袋,想让他走。可他却比我更加有所迷惘,有所希冀,有所徘徊。在他无数次思考中,似乎已经得出了那曾在我经行的无数个夜晚所擦肩而过的结论——他不应该离开。他无法脱身。当他一旦离开那条指引后,便甚至无从下足。对于他而言,风的深不如夜晚的深,前者让他不知所踪,后者却令他无从前行。夜晚的深更不及他的深,前者令他无从前行,后者却令他未曾前行。你先走吧,他说。他停在那根柱子面前,似乎已同它相依为命,甚至融为一体。快走吧。我扭头便跑,以超越言语的速度。我奔向她,我奔向你。以超越言语的速度,仿佛整个世界都跟在我的身后。我跑进风里、夜里,甚至快比我还要深。我奔向你。而那个人已在遥远的某处,似乎从未存在过。可是无论他是否存在于世界的某处,曾经、未来,他都不会再出现在我明早的路上。
因为他会被冲走,被黑色液体,或是被夜晚剥噬。总而言之,就这样说吧。他,永远也不会再出现在那条路上了。
天空一碧如洗。如果极目远眺的话,便能望见最远端高楼上的瑰色红晕。整个天空倒映下来,地面也沾上澄澈的颜色。空气很清新,没有一点味道。世界的喧嚣,仿佛被什么禁锢了。
他飞快地跑着,一边观察周围是否有异样的痕迹,在那条通往白色铁门的路上。(磅礴的大雨在昨夜,滴下碧梧桐。滴答滴答。)他喘着的气,同阳光的芬芳糅在一起而成了奇妙的颜色。红蓝金的光圈交替闪烁,飞逝。不可名状的旋律于眼前起伏。我目视天空,大概它也听到了远处的海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