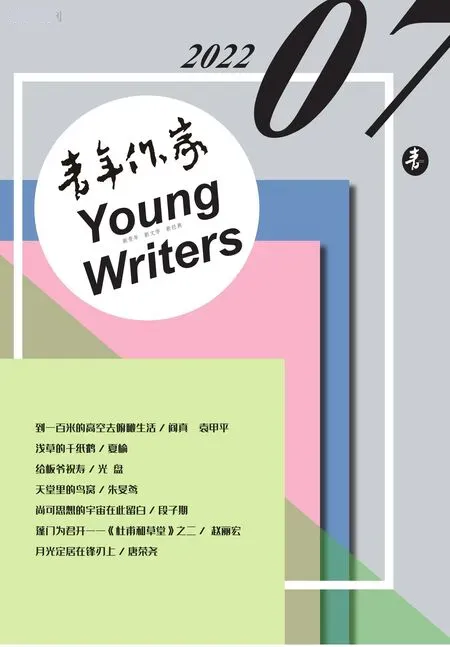火
李晓愚
狗
六十岁一过,老黄发现自己不再是个男人。确切地说,只能算半人,男人这个词语里的半边,即“男”字,不知不觉被切了。一想到这,不免下身一紧,脑子里都是劁猪时血淋淋的惨叫。
他感到很憋屈,觉得世人对老人太残酷,尤其对年老的男人。妻子得了宫颈癌后,他自动或半自动地被划到无性人那里。有时,他在村口见到一对毫不知耻交配的狗,他的这种半人感觉就更加强烈了……他愤愤地掐灭了手里的烟,骂了句他妈的,活得还不如一条狗!
他骂得好,骂得该。那两条没羞没臊的狗,正是他家的小黄和前庄寡妇赵如兰家的小花。他不禁替赵如兰也摇了摇头——唉,咱俩啊,都命贱如蚁。
赵如兰的丈夫两年前走的,咳咳喘喘了大半辈子。
人走了两年,人心如水中捕鱼的网标浮动,有些好心人劝她再找一个,反正岁数也不大,才五十多岁。她模样小巧,颇爱打扮,好好收拾一下挺像那么回事。搁农村可惜了,他想。可是,这世上谁又不是被浪费的呢?都是可怜人。
但赵如兰似乎铁了心守寡,不再动那找男人的念头。
她放出话来,老头子躺床上三年,她伺候够了,不想再给自己找个人伺候,还想再过两年清净日子呢。
既然她有这个话,那些丧偶的、离婚的、光棍的男人,也就熄灭了那个火。唯独老黄没有。
老黄完全明白赵如兰的心思。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何况夫妻呢?伺候个一天两天、一月两月还行,上个一年半载可就要了人的老命。
就说他老黄吧,老婆丁霞现在的脾气那叫一个怪。她要了一辈子的强,事事都要比人强,至少不落人后。即便是在外面落人家后头了,这不回家还有老黄吗?老黄这一生,在话头上就没占过便宜,尽是让着她护着她,丁霞人送外号“常有理”。
“常有理”吃饭挑剔,年轻的时候跟江南一个跑船的好过。跑船的跑了,她学了一身的毛病,老黄老说她,你一个农村人就老老实实种地,本本分分过日子就得了,一天到晚学那秀气劲儿,没用。
“常有理”一辈子在什么事情上都占理,唯独在这件事上她觉得理亏。老黄一旦使出这撒手锏,她就只有吃瘪的份儿。“常有理”和赵如兰是死对头。两个人抬头不见低头见,可见到了就当没看见。“常有理”高高大大,大鼻大眼,村里人说这叫大气;赵如兰小小巧巧,细眉细眼,村里人说她长得像江南人,秀气。“常有理”听了就赌气。
如今,她得了这宫颈癌,整日唉声叹气。脾气阴晴不定,动不动就骂人,谁都骂。一盘菜烧得不合胃口了,她眉头一皱,拖长了音儿说一句——哎哟!
家里人谁都怕她的哎哟。老黄尤其如此。两个儿子已经成家了。一个在苏州,一个在南京。在南京的是小儿子,大学毕业就留在那里,刚成家没几年,手里的钱又都送进了医院。但他没什么怨言。倒是在苏州的大儿子,人没本事,脾气还不小——这脾气也就对着兄弟和父母,对他自己老婆那是一点辙儿也没有。大儿媳妇精明强干,处处辖制着他。老黄有时看不下去,觉得儿子太窝囊了,没得用,连他妈“常有理”病了,要拿钱都不给。还不都是大儿媳妇的主意?
“常有理”没病之前,年年让他们去苏州带孙子。“常有理”病倒,再不提这个话。“常有理”想去苏州看看孙子都不行。人家的话说得可好听了。“妈,你病了不用来苏州,来回折腾。我们带宝宝回去看看你。”回是回来了,一家三口,周末开着车回家,像走亲戚一样。
倒是让老黄做一桌子好菜,好吃好喝招待一番,星期天一早,吃了饭,小汽车呜呜一响,绝尘而去。
“常有理”就气,气得抹眼泪,气儿子不争气。老黄也气,但老黄没那么气,因为他自己不也是这么过来的吗?想到这些,老黄就想笑,可是他不会说出来。
他如今不怕她了,但是他怕她骂人,搅得左邻右舍不得安宁。
他就这样漫无目的地想着,迈着悠哉游哉的步子往庄子里走。已经是三月底了。昨夜刚下过雨,空气里甜湿的味道通过鼻腔,进入身体,真是通体舒畅。不像家里,总是一股腐烂的气味。
杨树发芽了。水塘边的一株桃花也开了。他立在桃花前,左看右看,真是喜欢。“哟,大男人也这样看花呢?!”冷不丁一个女人的声音闯进来,他认出那是赵如兰的声音。
他扭头,面向她,带着笑。“就是男人才爱花呢。”她听了一笑,不搭。
“你家里的怎样了?”她问。
“哦,老样子。”他答。
他又说,“哎,你这是从上海回来了呀!年前不是说你去儿子家带孙子了吗?”
“是啊,昨晚才到家。”她顿了顿,“这不快到清明了嘛。”算是一种解释。
“刚才我看见我家小黄和你家小花……”不知怎么竟想起这话来。
“哦,我说呢,转眼就找不到了。”
人
他推开院门,咳嗽了两声,意思是我回来了。“常有理”从卧室走出来,头上戴着顶红色绒线帽,她眯缝着眼,望着他似笑非笑。“叫你割一把韭菜,没叫你去杀人,要这么长时间?!”
“哦,路上遇见人说两句话。”
“哪个?我还以为你被人短路上去了!”
老黄不吱声。“常有理”这两年遭了罪,化疗后人的皮肤暗黄无光,像老树皮剥离树干后的模样。她从前一头乌溜溜的头发,如今大把大把地往下掉,后来索性剪了个光头。
还是老黄亲自动的手。
老黄到厨房生火做饭。这两年练就了一手好厨艺,煲汤烧菜无所不能。只要“常有理”说想吃,就是再贵他也下得去手。钱,都是小儿子的。
可是,有时不免为小儿子抱屈。
自打“常有理”检查出病,小儿子第一时间联系南京那边的医院,求爷爷告奶奶,在省人民医院求到了病床。
老家人都以为小儿子有通天本事。那是在南京读大学,在南京买房子的人。这算不上什么,要说厉害,那还是他一个农村人,娶了个南京城里的媳妇。
村里人都这样说。老黄听了笑笑,点个头也就过去了。
其实,“常有理”曾经有大半年时间,几乎每个月都去南京化疗,他们连小儿子的家门都没进去过。“常有理”说他们不叫,我们不去。不请自来算什么?我们差他们那两口饭啊?
嘴上是这样说。住院看病吃饭,哪一样少得了小儿子的钱呢?
幸亏他赚钱上有些脑子。儿媳妇也来看过他们,在医院的时候,没带小孙子。她说医院里到处都是病菌,孩子太小,怕传染。老黄点点头说就这样好,不能带孩子来。“常有理”默不作声,用眼睛扫了一眼儿子、媳妇,最后又看了看老黄。
小儿子也是难,老黄心想。他也是不容易哦,那么要强的个性,这是在人家屋檐下讨生活呢。小的像他妈“常有理”,大的像老黄。听说,为了接他们去南京住这件事,小两口子没少打架。
最后,老黄都是一口回绝了。“你妈,我一个人就能伺候,用不了那么多人。再说,我们在乡下住惯了。”小儿子听了也就不再坚持,钱头上再苦再难不说个不字,只告诉老黄别委屈了。
“今早我看见我们家小黄和别的狗在打架。”老黄说。
“两只狗打仗有什么稀奇的?”“常有理”说。
“不是那种打仗。”老黄说着,用眼睛瞟了下她。她马上明白了。
“都几十岁人了——好看吗?”
“好看。”老黄突然窜过来,抱住她说,“要不我们也学学那条狗吧。”
“常有理”一把推开老黄,“你疯了啊?大白天的。哎哟,你是不是想让我早点死,你好跟那赵寡妇好啊!”
老黄本来兴致盎然的,忽然间似离了藤的黄瓜,蔫了。
“不做就不做嘛,一天天说这些阴阳怪气的话,你不活,我还要活呢。”“常有理”听了先是一愣,继而坐在那儿凄苦地哭了起来。
2018年7月初,首个中国—中东欧国家农业合作示范区在保加利亚揭牌,合作示范区以天津农垦保加利亚公司为依托,全力打造中国与中东欧16国及欧盟农业合作的典范。
见她落泪,老黄慌了。病人最是受不得气,他马上赔不是赔笑脸。“霞,别气。我这不是两年多憋的吗?再说了,你说我要是真的有赵寡妇王寡妇的,我哪还用来求你啊。”“常有理”一听不哭了,笑笑站起身,往卧室走。
老黄三步并作两步跟了进去。
猪
“哎,你还能记得以前我们家养的猪吗?”老黄心满意足地抽着烟,扭头问身边的妻子。“常有理”眉头微蹙,答道:“又是哪只猪啊?养过的猪多了。”
“所有的猪。”老黄兴奋地继续说道。“你说,过去养这么多猪,却只有劁猪这件事印在我脑子里,就像我教了这么多年书,能记住的学生没几个。不是尖子生,就是当年调皮捣蛋最让人头疼最让人厌烦的。”
“大白天说什么劁猪!我就该把你劁了!省得我半条命了,还受罪!”“常有理”白了他一眼。“哈!把我也骗了?!你舍不得!再说,那不是生不如死吗?”他猛吸了一口烟,然后像身边没有任何人那样低语道,“那还是个男人吗?那还是人吗?”
“你今天说这些疯话做什么呢?”
“我跟你说,我也是这两年才觉得不该劁猪。”
他没有继续说下去,再多说就会引起“常有理”的厌恶。
“常有理”起身去厕所了。独自一人的时候,他感到无比畅快轻松,甚至比刚才久违的性事还令他满足。他吐了口烟圈,过去爱胡思乱想的毛病也跟着那烟雾腾腾地涌起了。
“人活着难道就为了这一刻的快活?显然不是。可是,要没有这一刻的快活,人就不像人。”他默默地想着这些有的没的。听说出家人就没有房事,老黄心想,他们的牺牲未免太大了。换他的话,怎么也不会跑去当和尚的。那是一个人走投无路时的路。
不到万不得已,谁去走那断头路呢?
因此,他听到这种事就莫名起疑。奈何,自打“常有理”检查出病以来,她便莫名其妙地信起了佛。家里供了菩萨,日日敬香。老黄将信将疑,见她从此诚心诚意信佛,便只好随她去了。
好在赵如兰不信这些。猛然间他又笑着敲敲自己的脑袋——关人家什么事?!莫不是你想你老婆早点死?这样的念头一闪而过,愧疚如一条冰冷的蛇,嘶嘶地咬啮他的心。
快三年了!这些日子真不知自己怎么过来的,简直不能想,一想头皮就发麻,用旁人说他的话,那真是罪漫到头发梢上。过去,丁霞健壮的身体总令他充满生活的希望。如今,她病了。病了以后,她的脾气变了,就连身体也变了,就像刚才吧,他感到太多的勉强和陌生。不知是他还是她,或者是他们俩的缘故。
老黄对自己年过六十还想着这档子事感到好玩。这一把小火什么时候才灭呢?听人说人到死的时候,那团看不见的火才熄。老黄想,人这一辈子,全靠这团火支撑着啊。
正胡思乱想间,见到消瘦的“常有理”脸色难看地站在门口。
“都是你这死不要脸的!”
“我又怎么了?”
“下身出血了!刚才我就喊疼,你非要这样。你如愿了!”
老黄慌了神。抓上衣服,三下两下套上去。
“你先躺着歇歇。我喊人送你到县医院!”
梦
老黄走在前头,赵如兰跟在后面。两人距离有两米远。天渐渐地暗了下来。村头的地里没有别的人,不知怎么突然间下起了大雨。地,裂开了一道只能一人容身的沟壑。雨水灌进来,一会儿就漫到小腿肚子处。老黄头也不回地在前面走,赵如兰有些害怕,喊他也不应,转眼就没了踪影。天色暗了下来,只有微光。
她越走越快。独自走在水越来越深的沟壑里。突然,右手边的土地微微隆起。一个巨大的人形躺在那里。她认出那是死人!啊呀,躺倒都那么大,那是丁霞啊!
赵如兰从噩梦中醒来。才三月底,她出了一身冷汗。
睡不着了,她起身站到窗前,小雨淅淅沥沥地下,路灯发着暗黄的光,像一个老年人对人世最后的爱。垂首、安静、沉默,人一旦上了岁数,也和这路灯一样。只求不发出惹人厌烦的声响,顺便发点热,留点用处。就像她赵如兰,每年都要来上海住上几个月,帮着带孙子。原以为人老了,苦了一辈子的人了,牛马似的,总该休息一下了。不曾想,牛马到了不能劳动的时候,等待它们的只能是宰杀。
人,又何尝比那牛马高贵呢?还不是辛苦一辈子、操劳一辈子,说不上是为什么,甚至都不知道是为了谁。
小孙子跟着她睡,这样儿子媳妇才能再生一胎。孩子睡得香甜,孩子的梦里再大的苦不过是为了一个玩具一件衣服,或者一顿好吃的。
想想,大人又何尝不是如此?
儿子媳妇也在酣睡。儿子打鼾的声音,在寂静的雨夜,竟然传了过来。夜,太静了,那是一个孤独老人的世界。幸亏他们没有弄出别的动静来,不然听到了多么尴尬。
清明,又到了。
她该回去了。
她听到了死者的呼唤。
死
强了一辈子的“常有理”,现在躺在床上,再也站不起来了。过去,她那动辄因不满而高声斥责家人的嘴,也紧紧闭着。
老黄的两个儿子媳妇都在家,他们围着老黄问:“爸,现在怎么办?”老黄沉默不语。他抽根烟,然后说:“准备给她穿送老衣服吧。那个,老大老二家媳妇过来帮个忙。”
两个媳妇互相看了看,抿着嘴,跟了进去。
送老衣服是提前就买好的。两个媳妇一起在县城挑的。红色外套,知道婆婆一辈子钟爱大红。黑裤子,黑布鞋。到那个世界去,不能穿皮鞋。不知道哪里来的规矩。
她已经瘦成一把骨头了。疾病,这些年,一点一点,如蝼蚁啃噬一块骨头。它比人有耐心。世上最有耐心的怕是死亡了。不论你走多远,它总在路的前方,微笑着等着你。不慌不忙。那自信和从容,正是人类所缺乏的。
“轻点,轻点。”老黄急忙喊着。看着两个儿媳妇不知疼惜地动她,他眼眶里蓄满了泪。这个辖制了他一辈子的女人,终于松开了绳索,留他独自在人间自由。
这是他最后一次看她的身体。这是两个儿媳妇第一次看她的身体。身体是一个人最后的秘密。人的一生,只对自己信任的人敞开秘密。唯有到死的时候,人们才身不由己地将自己交给别人。
“常有理”忽然睁开了眼睛,她扫了一眼面前的人,哼哼着说:“穿好就把我放到门板上吧。撑不过今晚了。”老黄听了这话,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
“你们都出去吧,我想跟你爸说两句话。”她的声音很轻,又很含混,如同含了一口水说话。媳妇们没听懂,靠在她嘴边的老黄明白了。他点点头,然后将她们支走。
他握住她那双鸡爪似的手,俯身对她说:“有什么要交代的,我听着呢。”“常有理”吃力地喘着气,每吐一个字都像用了全身的劲儿。
“我知道你欢喜赵如兰。”老黄身体不自觉地直了下。
“我死了,你们一起过日子吧。”老黄说:“别胡说了。你歇歇。”
“常有理”摇摇头。一滴泪落在她枯黄凹陷的眼眶里,久久停在那里,像一个小型人工湖。
“赵如兰,她不说人,就是在等你呢。等我死呢……”
老黄摇摇头。
“女人才知道女人。她欢喜你几十年了……”老黄吓一跳。这是他想也不敢想的事情。怪不得“常有理”只肯趁老黄寒暑假回乡下老家住,原来怕的是赵如兰抢人。这几年住到乡下倒是“常有理”的主意,老黄自然也是愿意的。乡下空气好,空间大,吃点自己种的菜,胃口好。
老黄摇摇头,像是要把此刻不合时宜的念头摇出去。
可是,妻子那一句“她欢喜你几十年了”如同魔咒,钻进他的心里再也出不来了。哪怕,是在这样的时刻。
人啊,承担不起另一个人的爱。尤其是长久而沉默的爱。
怕
送走了妻子,老黄如释重负。老黄更老了,鬓角的白发越来越多。毕竟六十来岁的人了。这几年过的日子用妻子生前骂人的话来说,真是猪狗不如。他终于可以长长久久地休息一下了。
儿子们问父亲将来的打算。老黄说:“黄土都埋半截的人了!我还能有什么打算?活着呗。”小儿子说:“爸,你跟我们去南京住段时间吧。”
大儿子说:“苏州也行。爸,看你自己意思。就是两个地方来回换着住也便利。”
“我哪儿也不去。我就一个人守着这老屋。”老黄说。
“哎呀,爸,你怎么这么固执呢?妈妈走了,只剩下你一个人,你叫我们怎么放心呢?”任他们怎么说,老黄始终坚持住在老屋。
“实在不愿意跟我们走,也行。你住县城家里也比住这里好。便利。”儿子们没法子了。“不去。哪里都没有这里好。金窝银窝不如这里的狗窝。”儿子们第一次感到父亲的固执超出他们印象里的形象。
“爸,我听村里书记说,这里要拆迁了啊!大家要住集体农庄了!”小儿子像突然想起什么重大事件似的,如此说道。
老黄接过话说:“这都唱了多少年了!也没见拆!”
“爸,人都说我们庄子风水不好——”大儿子神神秘秘地说。
“什么?!”
“你看啊,这几年庄子里就死了好几个,都癌症。寿相也不大。”大儿子继续说。“瞎说八道!”老黄怒斥一句。“哪里都有死人的。哪年不死人?哪个不生病?生老病死,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这道理都不懂?”
儿子们不吭声了。
隔日,儿子们带上媳妇孙子们,一前一后,车子一开,走了。老黄送走了死人,又送走了活人,独个面对偌大的院子时,这才感到点空旷和寂寞。
“常有理”好像还没走。总是一不小心就听到她喊他:“黄良!”她喜欢说:“你大你妈没得本事,一辈子就干一件好事,给你起了个好名字。你看你兄弟几个,就你吃上皇粮了!”
老黄就笑,哪里就吃上皇粮了,代了大半辈子的课,四十多才转正。
一个人住最怕的是晚上。墙上贴的白纸,夜里风一吹呼呼响。头七那天晚上,他做了个梦,梦见他老婆说:“她欢喜你几十年了。”
他惊出一身冷汗,醒来后眼睛也不敢睁开。总感觉枕头边有微弱的呼吸声。他一动不动,就连呼吸也轻到不能再轻,仿佛猛然间睁开眼就能看到妻子的脸。
恐惧将他团团围住。都说不怕鬼,也说亲人之间没有害怕,都是假的,他只感到慌乱。有些后悔没回到县城的家里。可是,到了那边难道丁霞就不回来了吗?恐怕也未必。
还不如跟着儿子们过,像一件尚能御寒的破大衣,让兄弟俩来回地换着穿。然而,却是不能。至于为什么,他说不清。
此后,一到晚间,他就感到一双莫名其妙的眼睛在黑夜里望着他。整夜整夜地望着他。
后来,恐惧渐渐少了。思念盖过了恐惧。
他对丁霞的思念是从吃饭开始的。独自做饭独自吃饭,滋味实在不好过。从前想要的自由,如今却无力承担。哪怕有人吵吵嘴也是好的。寂寞,像蛇一样阴冷静默。
人真是害怕寂寞的动物呀,雄性动物尤其如此。他渴望一个女人,一个活生生的女人,一起说话做饭,晚上一起睡觉。如此,后半生也就没有遗憾了。
孤单,实在难以忍受。
赵如兰这些年一个人是怎么过的呢?哦,她有条狗。他也有条狗。丁霞刚走的那一个月,晚上他将小黄带到自己屋里,就在那次奇怪的梦境之后。
他们的狗都“打架”了,他什么时候能和赵如兰“打一架”呢?
他早就想单独去找她了。怕的是村里人的闲言闲语,老婆才死半年就等不及要讨个新老婆了。再说,儿子们肯定也反对,这是毋庸置疑的。
赵如兰什么心思他大概摸得出来了。但这个女人好面子,原本还会隔三岔五来“偶遇”他一趟,装作问问丁霞的病情。现在倒好,丁霞死了,她反而不来了。
她是怕人指着脊梁骨骂呀。
得激一激她才行。
寻
村里有人来给老黄说媒,对象是隔壁村一个离异的,还有个上高中的孩子,比他年轻不少。来人把这情况一说,老黄心里就跟明镜似的,人家比自己小上个十来岁,图他个啥?不就是图他一起养个孩子?
月月拿工资,不多,但饿不死。再一想,他都这么大岁数了,还去替人家养儿子?这不是没事找事干嘛?轻松日子才过几天啊!
老黄就想推了算了。再一想,他就觉得非去不可了。
照例是穿上最好的衣服,用小儿子买的刮胡刀好好收拾了一番。甚至,清早的那次刷牙都格外用心。他正照着镜子的时候,一眼瞥见丁霞的遗像,她望着他,似笑非笑。
似乎一切都被她看在眼里,他有些窘迫又有些恼火。一辈子管着他,死了还管着他!突如其来的一阵怒火,令他心烦意乱,随口骂了一句去他妈的。
人,见到了。他请的客,他觉得成不成都该男人花钱。他甚至还给她买了点心和水果。人是不错的,虽没有赵如兰好看,但胜在年轻。人只要年轻就好看。
再好看的人,老了都是一张揉皱了的纸。
傍晚回家在村口和赵如兰狭路相逢。他笑嘻嘻地说:“多少天没看见你了!”赵如兰只是鼻子嗯了一声,说了句“人逢喜事精神爽啊”,然后快步走了。老黄立在原地,一头雾水,转而笑出了声。
老黄去看人的消息不胫而走。在乡下,没有什么秘密能够躲得过夜晚看门的狗。老黄决定晚饭后去看看赵如兰。这个时间点很好,既能避开白天人的耳目,又不至于太晚,将来被人知道了不免说三道四。
他人还没到她家门口,就听见小花在里头汪汪地叫唤。它挨了一声训斥,犬吠声消失了,就像知道来人是来找她似的,她打开了院门的灯,灯光照在老黄的身上,一个夜色中归来的男人总是动人的。
随后才是开门声。哐啷一声,动静很大,像是故意让左邻右舍听见似的。老黄下意识地向周围张望了一下,倒是赵如兰很镇定。在这种事情上,男人总是比女人怯懦。
老黄进门,在靠门边的一个小板凳上坐了下来。两个人都不说话,也不看对方,就是沉默地坐着。约过了几分钟,老黄咳嗽一声,清了清嗓子,赵如兰抬头看了他一眼。他这才一惊,看出她刚哭过。
“怎么了?”他急忙问。
“啊?什么怎么了?”赵如兰答非所问。
“你不是哭了吗?”老黄一开口就想骂自己蠢。
“没有的事。”
“想你家老王啦?”他想挽救一下令人尴尬的氛围。
“提他做什么!”赵如兰气鼓鼓的。
老黄恨不得拧自己两下,一错再错。又是一阵沉默。
“这么晚你来我家有什么事?”赵如兰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事情一样,对他发问。老黄愣了愣,对呀,他是来干什么的呢。来之前心里潮涌着什么要鼓出来,此刻都烟消云散了。他犹豫了半天,双手来回搓着,然后微笑着说:“那个,明天晌饭来我家吃吧。”“就为了这?”赵如兰失笑。“你家明天晌饭要请客呀?是不是白天你看的那个女人?”
“不是不是!”老黄连连摆手。
“那是哪个亲戚来?”
“也不是。就,就我和你。”
“这我就不懂了。人都说无功不受禄,好好的,我自家的锅底又没掉!”不知怎么说着说着,心里就有气。
“我记得你烧鱼好吃。多长时间没吃到了。明天起早我去买两条鱼。”
赵如兰说:“烧鱼好吃的人多了,非要叫我去?!”
老黄被她一说,忽然感到一阵从未有过的快乐和放松。他笑着说:“哎呀,你这个人呀——”
“我这个人怎么了?”赵如兰不依不饶。
“非要我这样说才好——以后,我俩一起过吧。”
赵如兰没料到他能这样痛快把话讲出来,她一步步地“逼着”他,就是因为知道他生性软弱。他不说明白,她坚决不能过去跟他过。那叫什么呢?没名没分的,罪名都她赵如兰一个人担着了。
现在,他这样和她讲,她只觉得自己刚才白哭了一场。
“你不和白天见的那个年轻的一起过吗?我这都老太婆了。”老黄听了哈哈大笑。“你呀,一辈子一张嘴不饶人。”
“那你还来找我?没人求你来。”
“好好好,是我自己请我来的。我黄良啊,这一辈子都被强女人管着了。”
“周瑜打黄盖呗。”
两人高兴之余都有些悔恨,浪费了多少时间?!
何苦兜那么大的一个圈子呢?然而世间事就是这样。急不得。在男女事情上尤其如此。一切只讲究个相宜,而非早晚。
老
老黄承诺要给她个名分。他说要和两个儿子讲一声,他还说从前有人给他算命,说他命中注定有两个老婆,当时他还不信呢。
赵如兰就说:“你又说鬼话。什么时候算的命?这么些年也没听人讲过。”老黄说:“你们哪里能听过呢?两个老婆这种话,我要是说出来不是自寻死路吗?”说罢,两人相视一笑。
两个人边说边收拾屋子。自打丁霞死了后,这个家第一次有了生气。老黄看着她,心里说不出的满足。他望向妻子的遗像,仿佛对她说:“你料事如神。”
赵如兰手里拿着一个病历本在细细地翻看。老黄伸手想去夺过来已经晚了。“你看这个干嘛?丁霞病历本,你也要看。”
她站起身,指着其中一页说:“你都多大岁数了,她那时病了,你还像个吃不饱的狗一样!”老黄知道她看到了。那是丁霞患病三四年间唯一一次同房,她阴道出血去看了医生。
老黄像条犯了错的狗一样,垂着头不吭声。
“现在还饿吗?”赵如兰斜着眼瞟他。老黄顿时如获特赦,点点头,“这不一直想吃没吃上嘛。”
“那就让你吃个够。”
“这哪有够的时候?除非死了。”老黄嘴硬说道。
老黄搂着她,有点难为情地说:“男人老了,就没用了。”赵如兰说:“这不错嘛。”“你今天就搬过来住吧。”老黄动情地说。
“我现在搬过来住算什么?人家要怎么说我呢?”
“不怕的。我肯定会娶你的。过段时间就去领证。”老黄拍着胸脯保证。
“什么时候?”
“等我先和两个儿子说好的。”
“那要是他们反对呢?”
“不会。我有你照顾他们还省心,盼着都来不及。再说,丁霞走之前都同意了的,他们有什么好反对的?”老黄觉得这样说了似乎还不够,又说道,“以后,这个老屋都是你的。”
“我不要你东西。你这话说得就像我图你钱一样。你看你多有钱哦。”赵如兰半开玩笑地说。
“不是。我知道你不图什么,但我要安排好的。”
“房子不是说要拆迁吗?”她问。
“没准的事情。我要说的就是这个,就算将来拆迁了,钱都给你。我一分不拿。那两家也别想拿一分。”
“说得就像你能当家做主似的。”赵如兰取笑他说,“一辈子都没见你当过家,这么大的事你倒是能耐了。”
老黄嘿嘿一笑,有种被自己女人看穿后的熨帖和安心。“正因为我一辈子没当过家,在这件事上才要自己做主。你放心吧。我回头就跟他们讲。”
难
大儿子两口子全都反对。小儿子一时难以接受,说没想到这几十年的邻居变成自己后妈,总觉得怪怪的。大儿子说,再说了妈才走半年多,你就这样耐不住,你让我们怎么想?你让大家怎么看?最主要,你让妈妈怎么想?
老黄一听就火了。“我不管你们怎么想,我只是告诉你们一下!旁人怎么想那是旁人的事!你妈怎么想?你妈在临死前特别交代过。她不像你们这样没良心!”
儿子们一听老黄把话说得这样难听,简直怒不可遏。大儿媳妇说:“爸,你要是这样说,那将来可不能怪我们不给你养老送终!”
老黄咬牙切齿地回答:“你放心,我暂时还死不了!如不了你的愿!你不就是怕人来分你那点拆迁款吗?!今天,我明白把话告诉你们,你们几个一个子儿都没有!”
只有老二家那个南京媳妇同意。她乐得有人照顾公公,他们省却多少闲心。平时老大家就不肯照顾老人,重担都落在他们两口子身上,为这个事儿,他们夫妻没少吵架。现在一口苏北乡下老房子就能叫一个女人心甘情愿死心塌地地跟着他,她真是高兴都来不及。
那老房子说白了,真拆掉了,补贴的钱连十万都不到。这点钱买一个女人任劳任怨地伺候小半生,值了!
老黄没敢把小辈们的意思说给赵如兰听。他只是从此不提这个事情了。
闲言碎语伴随赵如兰进了黄家门那天开始,如缕不绝。人家当着他们的面不好讲什么。每次他们或他们中的一个靠近人群的时候,大家立刻收声,一脸尴尬,然后没话找话地来一句:“你来啦。”
久了,赵如兰不免受气。
她说:“你从前讲的话还算不算数?”
“什么话?”老黄被她突如其来的一问给问住了。
“你自己都忘了?”她更来气了。
“哦——那个事啊。”老黄拖长了腔调。“算话。当然算话。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那什么时候去领证?”
老黄一下子没了底气。毕竟,他不能把事做绝,将来总要靠着儿子们的。活着的时候,手脚能动的时候,她能料理一下家务,和他做个伴儿。
万一将来他瘫了呢?什么事都怕个万一。老黄一生谨慎。万一不能动了,她还能像今天这样贴心照顾他吗?他想起妻子丁霞病重的时候,他怎样厌烦,不到万不得已谁愿意伺候病人呢?
那还是少年夫妻呢。何况他们这样的半路夫妻?再说了,这还没领证,只能叫名义上的半路夫妻。儿子们的话也不能不考虑。半路夫妻有几个不是钱买来的?
老黄想着这样的心事,却难以对她言明。只能沉默以对。
赵如兰坐在床沿抹眼泪。“到了,我还是不如她吧?!”老黄没法解释,女人的想法真是难以理解。
“你有难处,我也不为难你。”她哽咽着说:“真的假不得,假的真不得!”老黄知道她是生自己的气了。见她这样他也难过。
“是我自己没长眼!相信一个一辈子没得主心骨的男人!”她突然不哭了,站起身,往自己身上拍了拍,似乎要把一身的尘埃抖落尽。
“我忘了告诉你了。今天我家老大来电话,说他媳妇怀上了。要我去上海伺候一段时间。”她二话不说就开始收拾自己的衣物,也简单,毕竟不是过了几十年的家。
到底是个过路的。
她打心眼里瞧不上老黄,更瞧不上自己。
病
赵如兰走一个来月了。
老黄的肠子都悔青了。他恨自己软弱,也恨自己当时为何不拦住她。
赵如兰的心真狠呀,说走就走。他当时还以为她说着玩的,顶多回她家住一晚就消气了。第二天一早,他不见她过来做饭,心里有些慌。他自己也憋了一肚子气,决心不去喊她。
晌饭时间都过了,她还是人影也没有一个。他憋不住了,装作没事人一样,往她家走。快到的时候,他在邻居家看到了她的狗。他的心咯噔一下,预感不好。小花只有她不在家的时候才会托付给邻居。
也许她上街了吧?走亲戚去了?小花自己跑过来的吧?他这样安慰着自己。然而,赵如兰家紧锁的大门给他沉闷一击。
后来,他听说赵如兰天不亮就起来了。赶了最早一班去上海的车。
她走了。她真的走了。她竟然走了!
他感到一阵难以言说的胸闷,剧烈的咳嗽袭来,眼泪都咳了出来!
她走了这么久,杳无音信。关于她的只言片语都是邻居传来的。每次,他都很想听到她的消息,但又要装作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人家问起他来,他也就一个咳字作答。
人们看出他们黄了。老黄也黄了。
过去那些茶余饭后评论他们的左邻右舍,突然间变了个人似的,对老黄格外同情起来。
老黄很多次想给她打个电话或去个信息。信息写了又删,删了再写,然后再删。如此,反复几次。他一赌气,将手机朝床上一扔,依旧是骂了句去他妈的!
人家一家团团圆圆的,我老黄干嘛要下贱去求她回来呢?再说了,她又不是不知道我一个人孤苦,既然她连这个都不在乎了,我就是求回来又有什么用?
他反反复复地跟自己这样说。晚上,他抱着小黄亲了一口,叹息道:“人还不如狗呢。人说走就走,狗,你撵多少回都不走。”
然后他对着虚空说:“丁霞,这下你称心如意了吧?都说你‘常有理’,还真是。”
说完这话,他又是好一阵咳嗽。
近来,他咳嗽得越来越厉害。伴随着咳嗽起伏的是令人难忍的疼痛胸闷。起先,他没当一回事,只当是感冒咳嗽。连村卫生室都省了,他给自己抓了药,买了点感冒药和止咳糖浆。
这样对付了半个来月,还是不见好。咳嗽胸闷等症状倒是越来越严重了。这时,他才意识到可能不是什么好事。小儿子给他来电话的时候,听他咳嗽得厉害,说:“爸,要不你来南京吧?我带你去医院看看。”
“多大点事,就往南京跑?”他抽了一口烟,咳得猛烈了。小儿子说:“没事当然最好。我们就当体检一下嘛。”
“不去。”老黄还是那么倔强。
“不来南京也行。那你自己去医院看看。明天就去,我等你电话。”小儿子下了任务,老黄答应了。
他去了县医院,正好顺道回县城的家里看看。按理说,赵如兰也走了,乡下没什么可值得他留恋的了。可是,他也说不上为了什么。他现在压根儿就不愿住到城里。在乡下,在他从小长大的村子里生活,他感到安心,像一株植物,移走多年又回来了。
医院照例是抽血、拍CT,医生看着CT眉头一皱,摇摇头说:“不太好啊。就你一个人啊?”老黄点点头。
“明天做个核磁吧。”医生建议道。
“怎么还要做核磁?”老黄紧张了。
“为了确诊。”
“确诊什么?”
“你家人呢?”医生并不回答。
“你有话直说吧。”老黄说。
医生犹豫了几秒钟,然后指着他的片子说:“你的肺部啊不太好。你是不是有吸烟史?”
老黄点头。“几十年了。”
“我们目前怀疑是肺癌。”这句话瞬间如一记响雷炸在他的头顶。他的第一反应是怎么可能?医生是不是搞错了。
医生看出他的震惊和怀疑。“所以我们才要你明天再来做个核磁看看。”
老黄机械地走出县医院的大门,又失魂落魄地回到了家。一个他许久没住过的家。他倒在床上,晚饭也不吃。他想起儿子还在等他的电话。他什么都不想说,将手机一关。
怎么会这样呢?我这一生并未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啊!老黄这样想着。这也太快了吧?!他原来想,自己怎么也能活到七十多。说不准,八九十也有可能呢。
也许CT错了呢。这不是常有的事情吗?等明天核磁结果出来再说吧。先睡个觉要紧。然而,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核磁共振并没有为他带来想要的结果。
突如其来的疾病击垮了他。医生让他住院,他不肯。他不信。小地方的医生水平很差,他这样想。他们诊断错了的时候多着呢,那谁还有那谁谁,从前就是被县里医院给耽误的。
他要去南京一趟。
他说去就去,一刻也不耽误。
悔
南京检查的结果也没给他希望。他一下子衰老许多。
医生说已经扩散,没有手术的必要了,化疗吧。和几年前妻子一样,他要把她走过的路再走一遍。
小儿子说什么也要他留在南京。他不肯。他比任何时候都盼着回到老家,他在这一刻才明白丁霞当初为什么非要回老屋。
儿子拗不过他。他说:“我又不是一下子就死的!医生不也说了吗?这个病,治疗得当的话,我还能活个三两年呢!你该上你的班要紧。我能照顾自己。等我不行的时候,自然会跟你说。”
这样,老黄又回到了老屋。
他慢慢接受了自己的病,接受了属于他的命运。他甚至把自己养得不错,还胖了两斤。
邻居都知道了他的病情,大家见到他的时候总是说:“黄老师,我们家菜地里的菜你自己去薅啊。”
他再也不用操心这个操心那个了,一辈子小心翼翼的,向这个赔小心向那个赔不是。现在,他不用了。他问心无愧,一生没有对不起的人。
他站在院门口,望着刚发芽的杨树,这样想着。然而,赵如兰的影子跳了进来。对,要说有对不起的人,就是这个女人吧。他答应人家的事儿没做到。
他让她灰头土脸地走了。
这些天,他格外想她。他想赵如兰就是狠,还说欢喜他几十年呢。几十年又怎样呢?还不是说走就走?
汪汪汪,一阵狗吠。来人了。村里通知说房子国庆前全部拆掉。送信的人并不停留,说了就走,留下一张纸。然后继续下一家。
真的说拆就拆了?
唱了多少年的戏,而今来真格的了。
这几间老屋都是他当年请人一砖一瓦盖起来的。比起县城那个家,这个家更像他自己。
想不到他得了绝症,房子也得了“绝症”。看样子,他们要前后脚消失了。他抚摸着门框,眼泪落了下来。自打他查出肺癌以来,这还是他第一次难过到掉眼泪。
手机响了。是她!
他赶紧接了。“喂。”对方不说话。再听,是她在哭。
“你哭什么?遇到什么难事了?”她哭得更凶了。
“我回来了。”
“什么时候的事?我没看到你啊。”老黄生怕再也见不到她了。
“我还没到家。车子才到县城。”
“我去接你!”
“不要!我自己回去。风吹了受凉的话,你受不住。”赵如兰说着又哭了起来。“你这个人真是死心眼。这么大的事也不跟我讲一声。”
老黄也抹了眼泪。这一回他没听她的。
一辈子听女人话的老黄,决心走到镇上去接她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