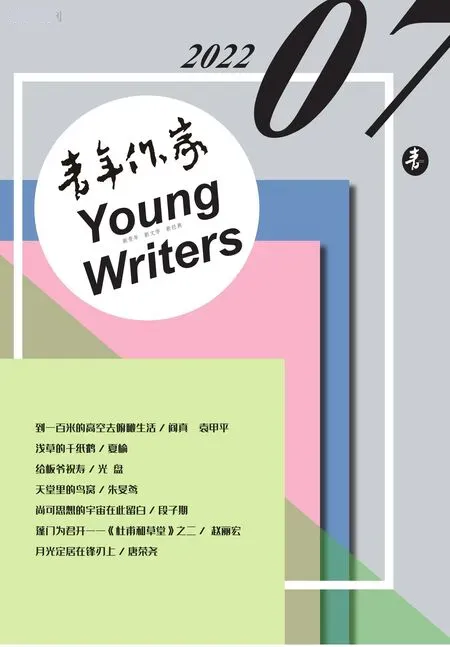隐匿
阿 茶
一
沈青坐在沙发上盯着外面的光影,阳光被割裂了般落在阳台上,逼迫着她想起往日时光。她在山泉边长大,春天山谷里的老树发新芽,地面上开始散落时光的影子,夏天空中的云层增厚,太阳把云朵投射在山谷里,那些影子随着白云流转穿梭于大地——孩童时的沈青踩着那些影子奔跑,那时候未经人事,有很多的快乐,等她略微长大,浸入尘世,便不再如此。
沈青起身走向卧室,她的男人正仰躺在床上。从窗帘缝隙中偷溜进来的光线,穿过男人的脸落在淡蓝色床单上。
空调散发着令人厌恶的寒意。
沈青打量男人的脸,一张饱满的嘴唇和一张满是皱纹的脸。她坐下来,把手摊开,光线落进她的手心,她蜷起手指,光线便从指间漏了去。
远处山林的风声透过窗户传进来,还有鸟叫声。屋子深处有更细微的燃烧声。钟点工离开前,煲上了骨汤,此刻蓝色火焰正安详地舔舐着砂锅底部,汤汁翻滚,沈青笑起来,闭上眼睛。
花圈巷的一侧是两米高的灰色围墙,一侧是商住两用的旧宅铺,宣纸扎成的花圈摆在宅铺外——从巷头至巷尾——一片白花之中夹杂着五光十色的塑料拉花,不过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城管来了,花圈不再被允许摆上街面,而廉价的宣纸或塑料拉花也逐渐被需要预订的鲜花花圈取代,就更不说店内的寿衣孝服了,从前全靠店家的手艺,现在交给了工厂和流水线。
走进花圈店,穿堂而过是三十米见方的院子,院子四周砌两层高的房子,除去南面临街的铺面,全做起居之用。王盛义的事务所就开在南面二楼的铺面上,取名“盛世事务”,却没有挂招牌,不过广告单放在一楼的铺面上,客人进来,不论买不买物什,总是先递去一张。
事务所的摆设相当简单。墙上挂旧空调,靠窗一把旋转椅,椅前一张办公桌。进门处摆着墨绿色旧沙发,沙发显然不是为访客准备的,散发着头油臭味的枕头和皱皱巴巴的薄毯堆在上面。唯一的书架也变成了衣橱,干净的衣服和穿过的衣服塞在里面。王盛义的卧室原本在北楼二楼,但自从搬回来后不再住进去,大概是因为那个叫爸爸的男人也住北二楼,尽管这个男人已经在监狱里待了好阵子了。
男人起初只是赌,上门讨债的人头几次还算客气,不久拳脚相待,妈妈拿出所有的积蓄,连利息都不够,只好跪下来发誓下次一定能拿出钱来,但男人有了钱又去赌……这是王盛义童年时的事情,后来他考了警校,毕业后进入市公安局,起初在办公室,两年后调至禁毒大队,又几年升任副队长,王盛义一心要做与男人截然不同的人。出乎意料的是,男人也变了,通宵值勤时为他送夜宵,雨天送伞,就连外出办案时也是如此。一次,王盛义对男人说,你与其来讨好我,不如在家多陪陪妈妈。男人答应着,递过棉衣就要去赶凌晨回家的车。一旁的大队长拍着王盛义的肩膀道,“父爱如山”。又把车钥匙递过来,“这穷乡僻壤,又这么晚了,送你爸回吧。”
王盛义难堪地低下头。等男人上了车,他劈头就问:“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你妈说的。天冷,你妈说你穿得薄!”
“她怎么晓得我在这里?”
“你有一次提过,你大概忘了。”
王盛义以为男人的讨好是在弥补年轻时的过错,直到在一次缉毒行动中王盛义抓住了男人,他当时愣住了,大队长赶过来,对着逃跑的男人扣动扳机,子弹贴着男人的大腿打过去,划破皮肉,在门上射出一个窟窿。男人跌倒在地,大队长掏出手铐扑过去,当他看到男人的脸,惊诧极了,扭头看向王盛义。
王盛义遭到局里的调查,所有人都在议论,是他向男人透露了行踪才导致多次抓捕失败。局里给王盛义休了假。王盛义质问妈妈,知不知道男人的所作所为,妈妈却说,你不能这样对你爸,你曾经的一切都是他给的,警校的学费、生活费……两个月后,王盛义回到局里,从缉毒一线调至文档管理处。整整一年,他消沉落魄,事事抱怨,索性辞了职,又与女友分了手,等到无处可去只好回到了花圈巷。
起初他帮妈妈守花圈铺,花圈铺的生意并不好,他们就坐在玻璃柜台后面盯着老式电脑里的电影。一回,他们看《影子杀人》,片尾戴高礼帽的神秘男人说:“我听说过在西方有像你这样的人,他们称为侦探。”妈妈看向王盛义道:“不如你也当个侦探,像电影里这样,先抓些男女出轨的事赚钱?”妈妈说完,笑了起来。不过电影里男主角最终成了一名真正的侦探,而盛世事务始终做的都是揪抓男女出轨的龌龊事情,老板与员工也都只有王盛义一人而已。
无所事事的时候,王盛义常站在事务所的窗前,打望趴在围墙阴影里慵懒地打着瞌睡的土狗,想着自己如果是条狗就好了。每当他这样想时,就拿起桌上的空啤酒罐,捏扁,朝土狗身后的围墙砸去。易拉罐击中围墙,哐当落地,又发出一连串滚动声。土狗受了惊,对着墙壁和易拉罐大叫。妈妈走出来,对着二楼喊:“王盛义,叫你不要惹狗,你又不听!”然后把土狗赶到别处。
三十年了,除了沥青路取代了水泥路,除了流水线代替了手工制作,除了居民家电换了一批又一批、墙壁粉刷了两次,花圈巷同王盛义出生时没有两样。他在这条巷子里出生、长大,离开过又回来,如今他三十岁了,巷子外已高楼林立,立交桥一层绕着一层。他家门口从前有两棵石榴树,石榴酸涩的味道他至今记得,后来铺沥青路,石榴树被推倒,花圈也是在那个时候不再被允许摆上街面……
二
沈青出现在盛世事务所,她穿着绸缎质地的粉色长裤和白色纯棉短袖,没有化妆,暴露无遗的黑眼圈使她显得憔悴。
“我先生外遇了。”她忧心忡忡地说,但更像是自言自语。
她递去一张折好的纸,王盛义接过来打开,上面写着一个名字和一串手机号。
“从先生的手机里抄下来的。”沈青道。
妈妈端着茶水上来了。
“喝点吧。”妈妈说。
“不用了,阿姨,我得走了。”
王盛义看着沈青下楼,木楼梯咯吱咯吱地响,妈妈叹了口气。
日历上的夏天已经结束了,但一切仍是夏天的景致。太阳带着令人不安的热浪,阴影闪闪发光。在太阳穿过枝叶投射下来的斑驳里,铺满掉落的金桂、银桂,香气袭人。蝉鸣此起彼伏。
林雅站在大学门口的蓝色禁停标志下,中分的直发,露出年轻的五官。王盛义坐在老式雪铁龙轿车里,朝她挥了挥手。等林雅上了车,他问:“想好了?”林雅点头,不说话。王盛义打开音响,车内传出老掉牙的时代金曲。
王盛义带着林雅来到医院大厅时,林凌已经等在那里,由于刚洗过澡的缘故,她的头发有些潮湿,身上还有淡淡的香味。
“沈青怎么样?我很久没见过她了。”林雅问王盛义。
“还能怎样?”王盛义不耐烦地说。
林凌的视线越过王盛义落在林雅身上,林雅低下头。
“我走了,沈青只是让我把她交给你。”王盛义道。
三
花圈巷的夜晚和别处没有两样,只不过少有人愿意在晚上经过这里。太阳下山后,居民们拉上卷帘门停止营业,他们从厨房端出饭菜,一家人围坐在院子里或饭厅里,饭厅里的电视总是开着,即使没人看也不会有人想把它关上。小孩满院子打闹,大人讨论着无关紧要的琐事。高大的护院犬也在这个时候被放出来,直到第二天花圈铺开张前才再次被拴上。
王盛义的家不这样热闹了,如今只住着他和妈妈两个人,从前乡下亲戚一来就住上很久,农忙才肯回去,这几年却一个都不来了,连电话也不打来。王盛义和妈妈就在厨房吃饭,但常常谁也没有胃口,王盛义把做好的菜原封不动地放进冰箱,然后点上一支烟。等他抽完烟,走进院子,抬头看向北二楼中间的房间,灯光从窗户里透出来,窗户上映出电视节目的光影和隐约的说话声。院子里停放的雪铁龙,已经生了一层灰。
夜里,王盛义做了一个梦——他驾驶着雪铁龙上了高速公路,路的近处明晃晃的,远处漆黑一片——他想起一件童年小事,他和朋友打赌跳入水中,险些淹死,一个青年将他救起,那个叫爸爸的男人赶来后不停地向青年道谢,转身却给了他一个大嘴巴。那一嘴巴打得真疼,王盛义至今都记得脸上的肉跳动着的痛感——王盛义不由自主地捂住脸,把雪铁龙停在了应急车道上。他打开车窗,夜风吹进来,他下了车,蹲坐在轮胎旁点燃一支烟……
王盛义不记得自己是如何进入监狱的内部,只记得一个狱警对他说:“还是别进去吧。”他看着狱警的脸,陌生又熟悉。他穿过狭小的屋子到达浴室,一排铁喷头下躺着男人的尸体。王盛义掀开尸体上的白布,看见脖子至耳根处的勒痕,以及淤青的腹部和身下残留着屎尿,有了一种快感,罪有应得。王盛义又去看男人的脸,肿胀成青紫色,舌尖吐出来,而浴室角落的铁窗上,一截尼龙绳还挂在那儿,王盛义捂住脸大叫。
“盛义!盛义!”是妈妈的声音。
王盛义放下手,妈妈出现在眼前。
“你哭什么?”妈妈问。
王盛义看看四周,原来是梦。
妈妈拉开窗帘,楼下来了客人:“老板在吗?”
“来了!”妈妈下楼。
王盛义也跟着走了下去,一个神情沮丧的男子站在门口。
“要些纸花圈。”
“要多少个?”妈妈问。
“六个吧。”
妈妈嘱咐王盛义去杂物间取花圈。杂物间入口处堆满有些发黄的纸房子、纸车、纸做的童男童女,四周桌上摆放着的纸灯笼、纸寿桃、纸元宝同样旧了,墙上挂着的金元宝寿衣寿袍也生了厚厚的一层灰。王盛义走到花圈前,提着花圈抖了抖,灰尘扬起来,吸进喉咙,王盛义不停地咳嗽。花圈上用毛笔写着“奠”,男人写的,周遭的一切物件也都是男人的手艺。
王盛义把花圈搬上客人开来的皮卡,等皮卡开走,王盛义问:“谁死了?”
“爸爸。”妈妈回答。
“你是不是觉得是我对不起他?”王盛义突然问道。
妈妈转身走进花圈店。
“是他对不起我!”王盛义大声喊道。
一辆黑色轿车开了过来,车窗降下来,露出沈青的脸。
“好久不见。”沈青下了车,径直往花圈店里走,看见妈妈,叫了一声“阿姨”。
王盛义跟着沈青上了二楼的事务所。
“我打算离开这里了。”关上事务所的门,沈青将身体压在了王盛义的身上。
“去哪?”
“回家——老家——我是说,我长大的地方。”
四
林雅和其他受术者在大门外等候,手术区的大门时不时被推开,一个粉色小护士走出来叫号。
“3号家属!”
一个男孩站起来,护士朝他招手,把他让进手术区大门内。
“4号家属!”护士接着喊。
一个中年男人快步走进大门。
“5号!6号!”护士又喊。
林雅站了起来,一个年龄与她相当的姑娘也起了身。
原来手术区大门后有一间看护室,刚刚进去的家属正坐在里面。
林雅按照护士的要求,换上墨绿色棉布手术袍和拖鞋,她的眼前是一条长长的走廊,护士让她和年轻姑娘一同坐在长椅上等待。长椅靠着窗户,太阳晒得她们后背滚烫。
很快,走廊尽头走出一个穿绿色手术袍的护士,推着轮椅,轮椅里坐着一个女人,驼着背,有气无力。
粉色护士打开手术区大门,唤进女人家属,家属大吃一惊,慌忙询问——麻药还没完全醒,绿衣护士解释。家属把女人扶上病床,绿衣护士推着空轮椅返回,经过长椅时,对林雅和年轻姑娘道:“你们跟我来。”
她们跟着护士走,走廊尽头转角处还连着一条走廊,走廊上还摆着一张长椅。护士让年轻姑娘跟着她走,把林雅留在了长椅上。
等到林雅进入手术室时,年轻姑娘已昏迷在手术台上。手术室很大,并排放着两张手术台,手术台之间没有遮挡。医生将扩宫器插入年轻姑娘的阴道,把一些血肉刮出来,那些还来不及变成婴孩的胚胎掉进姑娘两腿下方的铁桶里,铁桶套着卫生袋,咝啦啦、咚咚咚地响。
护士拿来了手术同意书和麻醉风险提示书,林雅看也没看,签上自己的名字。
“躺上去吧。”护士道。
一个同样穿着绿色手术袍的医生,坐着旋转椅滑到了林雅的两腿间,轻声道:“别紧张。”
林雅听出了声音,是那个叫林凌的医生。
林凌用湿漉漉的棉纱擦拭她的外阴,又深入进去,转了几圈。
麻醉医师走了过来,道:“麻药对血管有一些刺激,可能有一点点痛。”
林雅点头,眼泪不由自主地流出来。
麻醉液流进血管,冰冷,林雅睡了过去……
机场路口有一家名为安维塔的英式下午茶茶屋,前厅摆着巨大的月季花花束,花束由两千朵粉色月季组成。每日上午,店内的服务生要逐一检查花朵,剔除掉有衰败迹象的鲜花。
穿过前厅,茶屋大厅的中央被布置成十九世纪欧洲宴会厅的模样——巨大的水晶吊灯垂吊下来,七八张小圆桌配金丝绒高背扶手椅,四周立朱漆圆柱,挂红褐色帷幔。大厅南侧是透明橱窗,北侧砌书架墙,临着橱窗和书架墙设沙发卡座,卡座上摆两个杯盏,一个盛一浅碗清水,清水里插粉色月季,另一个放粉色香薰蜡,若是有客人来,便将它点燃。大厅东侧与前厅相连,西侧连接走廊。走廊北面是厨房、卫生间,西面是一大一小的包间。
林凌坐在小包内喝着玫瑰水,敲门声响了三下,服务生推开门,沈青走了进来。
“一杯红粉佳人。”沈青对服务生说。
服务生退了出去。
“这是你第一次来这里吧?”沈青问林凌。
“我没想到你把茶屋开在了这里,从前这一带是花圈巷,你带我来过——这里不正是盛义的老宅?”
沈青笑起来。
“那时候你差点……”林凌顿了顿,不想说下去。
“我差点和他结婚了。”
“我以为你回老家后就不回来了。”
“我离婚了。”
“恭喜。”林凌毫不惊讶地说,“不知道你的下个男人又会是什么样子?”
沈青耸肩:“听说你就要升副主任了。”
“我打算出国了。”林凌道。
敲门又响了三下,服务生托着茶具走进来。
“我自己来吧。”沈青对服务生道。
服务生退出去,屋子里又只剩下林凌和沈青。
沈青端起茶壶——茶壶是白底月季花花纹,淡粉色的茶水冲入茶杯,将杯子里的玫瑰花瓣托起来,不知是头顶的水晶灯还是茶杯镶金边的缘故,茶水里泛出隐约的金色。
沈青把茶杯递到林凌面前:“尝尝,酸甜。”
林凌抿下一口,酸味最重,隐匿淡淡的涩味,最后却是甜味。林凌又喝下一口,甜味愈加清晰,附在味蕾上不散。
沈青端回茶杯,也喝下一口。
“这里的变化太快了。”林凌感慨。
“精品馆、会所、酒店,谁会想到这里会变成这样?”沈青道。
“我出国后就不回来了……有些事我想忘记。你想过那女孩吗?如果没了子宫……你后悔过吗?”
“我以为你已经忘记了。那时候作为回报,我给了你想要的东西。”
“那时候我缺钱,我……”
“你缺钱的原因,我并不想知道。”沈青揶揄道。
“我真后悔!”林凌起身往外走,她走得太急,撞到了走廊上端茶水的服务生,茶水泼在她身上,她只好往卫生间走。
她擦干衣服上的茶渍,从洗手台镜子里看见倚墙而放的暗红色单人沙发,真是古怪。她洗完手,又抽出一张纸巾,再抬头,看见沈青坐在沙发上盯着自己,她几乎就要叫出声来,再看时什么也没看见。
林凌慌忙走出卫生间,瞟见走廊尽头挂着的老照片,她认了出来,是花圈巷,王盛义的老宅正在照片的中间位置。照片上没有行人,临街铺面的影子东斜,影子里立着两个人,一男一女,林凌细看,像沈青与王盛义,又不像。
沈青走了过来。
“这是什么时候拍的照片?”林凌问。
“你再看。”沈青贴着林凌的脸道。
林凌不寒而栗:“这是画的!”
“那时候你和盛义有没有背叛过我?”沈青抚摸着相框下方的月季花。
“沈青,你疯了!”
“你看见前厅的月季花没有?你知道月季花也可以寄托哀思?”
五
王盛义走出医院大门时病房的灯已经熄了,路灯亮着,一个蹬三轮车的小贩骑过来,又骑走了。几小时前,沈青发来短信,说林雅的手术出了点意外,希望他去看看,王盛义觉得麻烦,但还是去了。
“别担心,她会醒过来的。”林凌告诉他。
“王盛义,”林凌又喊,“发什么愣?”
“我觉得……”王盛义看向窗外,茂盛的树冠、炫目的阳光、回荡着的蝉鸣,让他觉得有些不真实,“她原本是想生下来的。”
“怎么能生下来?”林凌道,“她是瞒着父母、学校来做的手术,她的朋友也不知道。而且你知道沈青生不出孩子,如果那时候你不和沈青分手、你不要她打掉孩子——真该死,那时候还是我做的手术,大出血,天啦!”
“别说了!”
“我们都得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林凌低声说。
天花板上横着两根长长的白炽灯管,细小的蛾虫围在周围,林雅一睁开眼睛就看到了它们。这里不像是手术区内的看护室。透明的输液包挂在输液架上,连接着她的身体。
“你醒啦!”一个粉色小护士出现在她眼前,“你是觉得没有力气吗?是正常的,放心吧,好好休养就可以出院了。”
林雅不记得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了,等她再次醒来,四周一片漆黑,窗帘缝隙中透进来的微弱光亮划破地板、床单与墙壁,让她看清浓淡交错的阴影里的物件,依次是电视机、茶柜、微波炉、电水壶。床头柜上放着不知谁提来的面包、牛奶和香蕉。林雅寻找手机,凌晨四点五十二分,手机里有几条未读消息,林雅点开,是弟弟白天发来的照片:家中前场空地上,爸爸正拿着木钉耙翻晒谷子。
“爸的腰好多了,能下床晒谷子了。”弟弟告诉她。
但是她发给男人的消息始终没有回复。自从沈青来找她,那个男人就躲了起来。林雅吃力地下床,拉开窗帘,天空没有星星,连月亮也看不见,但远近的人造灯光使城市弥漫在一种氤氲之中。
六
“为什么背叛我?你对别人留情,却没有对我留过情!”王盛义又做了一个梦,梦里沈青这样质问他。
“对不起……”王盛义把沈青抱在怀里。
“我和林凌是同学,她的技术我清楚,一个简单的手术为什么会大出血?是你和林凌背叛了我吗?”
“你说什么?”王盛义困惑。
“来不及了。”沈青的声音。
血从王盛义的身体里流出,但他一点也不觉得疼。
妈妈又在喊他:“盛义!盛义!”
王盛义睁开眼睛,并不见妈妈。王盛义去开灯,灯不亮,黑暗中他走出事务所,看见北二楼妈妈的房间有光照出来,他往北二楼走。
“妈妈。”他站在房门口喊。
无人回应。
他又喊,门缝里的光灭了。
他拧开门,热浪与灰尘扑面而来,更深的黑暗笼罩他,等他适应黑暗,看清屋内床上只有一张裸露的床垫。
林雅拉开窗帘,阳光照在她的身上。
林凌走了进来:“这是你的病历。”
“可是医院的记录……”
“交给我吧,她不会知道。”
“为什么帮我?”林雅疑惑地问。
“大概因为……”林凌思索着,没有说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