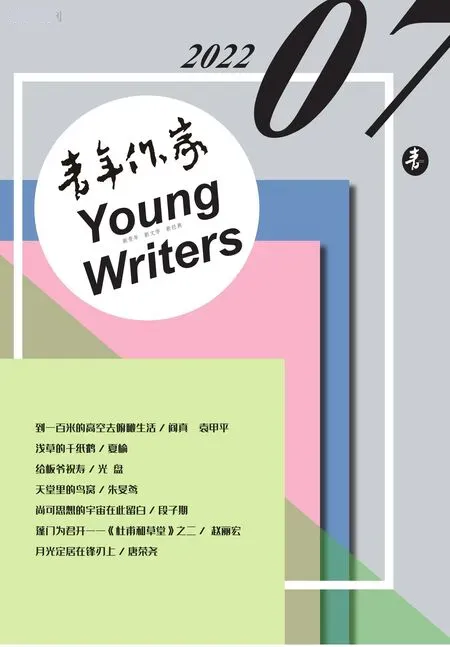到一百米的高空去俯瞰生活
——阎真访谈录
阎 真/袁甲平
阎 真/袁甲平
内心的呼唤会为你的人生找到正确的道路
袁甲平:阎老师,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发表文学作品的?
阎真:我第一次发表小说是在1979年,我记不太清那个杂志是叫《湖南文艺》还是《湘江文艺》了。杂志上登了一则广告,是新中国成立三十周年全省青年文学竞赛。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只能说感谢命运的眷顾,居然让我看到了这个青年文学竞赛启事。我也不知道怎么我心里就动了一下,花了两个晚上的时间写了一个三千字的短篇小说叫做《菊妹子》,这是我这辈子发表的唯一一篇短篇小说。
袁甲平:是爱情故事吗?
阎真:那不是。我写了一个小女孩,被当地流氓欺负,带着弟弟走了。结尾的那句话我还记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还去找她没有找到,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还活在人间。有一点感伤。
袁甲平:您的长篇小说延续了这种语言语感。
阎真:谢谢。《菊妹子》这个小说后来推荐到省作协,获得三等奖。这样一个奖对我今天来说是非常微不足道的,但对当时的我,一个拖拉机厂的工人,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巨大的刺激。那时候我正在准备高考,一直准备的是理科,但就因为这个奖,我临时决定改考文科。这是命运对我的眷顾。我也跟你说过,内心的呼唤会为你的人生找到正确的道路。
袁甲平:但我有的时候会怀疑,内心的呼唤是不是正确的,会不会我愿意做的事情刚好就是我不擅长的呢?我们这一代人经常受到来自学校、父母等方面的人生指导,他们的指导也不尽相同。
阎真:你愿意做什么事,就要往哪个方向发展,你的这个愿意爱好可能就是你的潜能。我的家庭从来没有指导过我,我是自己发现自己在这方面还有一点潜能的。1978年的时候,我记得我给妈妈写过一封信,问她大学还考不考。我妈妈给我回了一封信说,哎呀,你已经二十多岁了,别人在你这个年龄都大学毕业了,你就算了,在那边安心当一个工人吧。我当时接到妈妈这封信,痛哭一场,但痛哭一场之后还准备考。最开始我准备考理科,有语文、数学、物理、化学、英语、政治六门,准备了一年多,参加1980年的高考。到1979年下半年,《菊妹子》得了三等奖,我决定改考文科,语文、数学、英语、政治还是一样的,但要从头学历史和地理。我只有半年的时间,因为1980年4月就是全省预考,只有预考合格才能参加全国的统考。我历史一堂课没上过,地理一堂课没上过,没有成套的教材,临时找教材是不全的,而且是过时的,也没有任何一个老师,全凭自学。
袁甲平:您好有勇气,这是个很冒险的事。
阎真:是的。那时候,我每个星期上六天班,下了班再到附近的图书馆去看书,只有这么多时间。半年后,我就参加了预考。我的考场在株洲市一中,拖拉机厂在郊区,一中在市中心,我就在一中旁边找了一家小旅馆,4毛钱一晚。我跟服务员说,明天早上7点钟一定要叫醒我,我要参加高考。但是我晚上还是不敢睡着,我怕她万一没叫我。而且4毛钱是一个床位,那个房间里还有另一个客人,晚上打鼾,我想睡也睡不着。当时不知道为什么连闹钟都舍不得买一个,我家里也没来个人守一下,我也没舍得多花4毛钱单独住一个房间。第二天,我起来洗一个冷水澡就参加预考。
袁甲平:您成绩受到影响了吗?
阎真:没有,预考我考了株洲地区第一名,比第二名高了34分,呵呵。不过我当时并不知道,考试结束一个多月也没人告诉我成绩。我等不下去了就打电话给株洲市教育局,说我是株洲市拖拉机厂的。那边的人马上说,你是阎真吗?我当时很吃惊,觉得教育局的人怎么这么负责,几万人考试他竟然能记住拖拉机厂的考生叫阎真。但他只告诉我,我通过了考试,没说是第一名,具体成绩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袁甲平:然后您就决定报北大中文系了?
阎真:是,预考成绩一下把我的野心激发了。我原来是想考湖南师范大学的,预考我居然比第二名多34分,那我要填一个好一点的学校,就填了北京大学第一志愿,武汉大学第二志愿,湖南大学第三志愿,都是填的中文系。
袁甲平:从北大毕业之后,您回到了湖南师范大学教书,为什么不留在北京?
阎真:其实这又是一次人生选择。毕业的时候,我其实可以选择去中纪委,但我想都没想就拒绝了,唯一的理由就是,不符合内心的召唤。我对行政当官没有热情、没有激情,既然没有激情,我为什么往那个路上走?是吧?内心的热情激情没有在那个方向上,可能奋不顾身投入工作,那种激情根本就激发不起来,所以中纪委我没有去。
袁甲平:这个岗位在现在看起来是非常抢手的,去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的平均竞争比已经达到了61:1,一百五十多万人考试,录取两万五千多。
阎真:现在年轻人成长确实不容易,我那个时候竞争相对小些。中纪委当然很好,中央机关,但我的选择不是从概念出发的,是从内心出发的。当时我们班主任问我去不去,我说中纪委可能要求比较严格,我是一个自由散漫的人,怕做事做得不标准,我也不愿意穿西装。为什么?西装太正规了,我一辈子没穿过西装,不自在,不符合我内心那种需求。所以,那时候我完全可以留北京的但我没留,回湖南了。回到湖南,好单位也有很多,像湖南省社科院、湖南文艺出版社、湖南师范大学等等,我选择了湖南师范大学。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不要坐班。这符合我内心的需求,符合我内心的呼唤,就是这么简单,人生的选择其实没有那么复杂,你的心灵会告诉你应该往什么方向走,正确地引导。
八十年代是文学非常兴盛的时代
袁甲平:您到北大中文系的时候,刚好是中国文学和诗歌狂飙突进的年代,您还当了北大五四文学社的社长,我能不能认为,到北大以后,您的文学创作就真正起步了?
阎真:当时的确是一个文学非常兴盛的时代,尤其是诗歌。不但文科的同学,理科的同学也很喜欢诗,文学在我们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是非常高的。我举一个例子,我们那一届北大文学班有两个班,六十个人,文一班三十个人,文二班三十个人,我是文二班的,当了三年半的班长。我们班三十个人里面高考考了全省文科第一名的有四个,你看看那时候中文系热到什么程度?当然,我还是有点遗憾地说,我这些同学最后大部分都没有在文学这个领域沉淀下来,像我这样一辈子在文学圈子里面的可能只有一两个,而且还一辈子坚持写作的,还写出一点小小成绩的,我们班恐怕好像还只有我一个人,他们最后都改变了这种人生的轨迹。当年,很多校园诗人非常有才华,但是后来都消失了,埋汰在这样一种历史的长河之中了。我现在回忆他们的时候我都有一点感伤。
北大确实有一种文学的氛围、诗歌的氛围,这种氛围可能跟当时那样一种青春浪漫的时代氛围也有关系。但到了北大,其实我也不是很努力,成绩还马马虎虎,算中上水平。而且中文系是一个研究文学的专业,我读了很多文学作品,但跟文学创作并不是很相关,学校主要还是培养文学研究者。
袁甲平:对我们中文系的人来说,北大至今都是一座精神殿堂。八十年代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年轻、蓬勃,通过阅读文学回忆录,我感觉那个时代的文艺是灿若星河的,尤其是诗歌。
阎真:是这样的。我们这个时代的确是一个在市场经济背景的世俗生活时代,跟当年那样一种离世俗生活比较远的时代可能还是有一定的距离。为什么说八十年代是一个离世俗生活比较远的时代呢?在当年,我们反正也没有房子,反正也没有车,没有那么多功利主义考虑,不像现在考北大、清华都非常功利,意味着可以找好的工作或者多少年薪。当时的人不是这样想的,也没有这种机会,因为毕业都是分在体制内。所以说人们的思想可能相对来说单纯一点,这种单纯性就构成了诗歌兴盛一个比较重要的条件。我能不能这样理解?
袁甲平:到了九十年代以后,文学的主流体裁从诗歌转向了小说,乃至到21世纪之后的长篇小说,这是不是社会发展对文学书写的要求,甚至是规定?王国维先生说过“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在我的理解中,这是文学样式对时代内容自觉的跟进和回应。与上世纪八十年代相比,我们当下的生活是更加丰富,也更加复杂了,所以我们好像更需要一种客观的体裁、更长的篇幅去表现生活。我感觉到诗歌可能是有年龄,诗人永远年轻,富有激情,一个全民读诗、全民写诗的社会是不是也处在一个发展的青春期?
阎真:那肯定是的。你想一下,八十年代的时候,最有名的小说基本上都是短篇小说、中篇小说,但是在我们今天,中短篇小说,我不敢说退出历史舞台了,但是这二十年来中国文坛有哪一个作家是凭着写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在文坛崭露头角?我是研究现当代文学的,我举不出一个这样的例子。但是八十年代有很多,比如蒋子龙、莫言,还有王安忆,还有当时的很多人。
原来我们的思维有简单性,给一个事物的判断就是好的、坏的,这种简单的判断用一个比较短的篇幅可以完成,但是我们今天的人的多样性、立体性、复杂性,不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判断了。做了简单判断,我们会觉得这个小说写得很肤浅。比如当时有名的小说,我说实话,八十年代有名的小说真的写得很肤浅,那些获奖的小说,全国有影响的小说,他们那种非常简单的善恶二分法,我是觉得很难接受的。当年的著名作家对事物的看法就是这么单纯,善恶二分是典型的思维方式。所以说那种立体的、复杂的思维方式,多样性的人物,需要更长的篇幅来塑造、来描写,这也是长篇小说兴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袁甲平: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诗歌形式创新走到了瓶颈,而且就目前还看不到彻底打破这个瓶颈的希望。
阎真:大概十五年以前,我在湖南大学搞了一个讲座,当时有一个学生,是个年轻的诗歌爱好者。他说,阎老师,请你判断一下诗歌在当代的发展前景怎么样。当时我说,诗歌在当代没有什么更大的发展前景。我为什么会做出这样一种比较悲观的预见?我觉得十五年后的今天,我这种判断还是能够站住脚的。当下中国文坛写诗的人数以万计,甚至十万计,但是就在万计、十万计这种巨量的写作群体背景下,没有堪称当代大诗人的诗人出现。
袁甲平:诗歌还是非常热闹的,从省到市,到区县,甚至大一点的乡村,都有诗社,很多大型单位也成立诗歌社团。每年的诗歌节、诗歌日、诗歌奖可以说是数不胜数的,即便这样,我也没有感觉到诗歌的兴盛。当下诗歌只有总体的热闹,但没有举得起来的诗歌旗帜,也没有大诗人。
阎真:诗歌毕竟是一个形式的艺术,非常讲究这种形式感。八十年代,我读过非常多的诗歌,奇奇怪怪的诗都有,我个人的体验就是诗歌艺术形式的创新已经走向了极致,那种为创新而创新的都有。艺术形式走向了极致以后,后来的诗人还能够成为艺术的创造者吗?像朦胧诗,它一个最大形式就是意境,这种意境和意象在八十年代朦胧诗人那里已经被挖掘殆尽了。舒婷和北岛他们还活着,但连他们自己都不能创作出更多的生活意象和意境了。这就是为什么朦胧诗必然会衰落,不衰落它就得重复自己。八十年代已经过去三十年了。我希望能够有一个大家都公认的诗人突破这种局面,给中国诗坛带来一种欣喜。就像当年李白、杜甫建构了唐诗的高峰之后,至少后面还有一群诗人,他们没有那么高的程度,比李杜低一点,如杜牧、白居易等等,这些诗人还是构成了一个新的平台。这种状态在我们当代诗歌也还没有出现,类似当年李白、杜甫之后的那种新的平台,低一个层次的平台,在我们当代诗人这里没有出现,我觉得还是有点遗憾。
一旦意识到时间,就和痛苦结下不解之缘
袁甲平:从北大毕业后,您成了一个文学专业研究者,似乎再次远离了文学写作。
阎真:1984年,我毕业到了湖南师大,1988年就出国了。当时一个同学天天鼓动我。因为那时候中国还很穷,不像今天,我同学说,出了国就等于多活几十年。他认为,中国起码要几十年以后才有当时西方的生活水平。你提前进入西方生活水平,不就是多活几十年吗?所以,我申请了一个社会学的博士研究生,也出国了。
袁甲平:这段经历后来写成了《曾在天涯》?
阎真:是,《曾在天涯》写的是我自己在海外三年半的经历,但不是在加拿大写的。
袁甲平:我不知道这样说合不合适?听您讲您在加拿大的故事,我觉得您当时主要还是为了谋生,为了追求一个更好的物质生活。
阎真:加拿大确实比中国发达,我在那里打工,做厨师,一天大概可以拿一百多块钱人民币。我当时大学毕业在湖南师大教书只有54块钱一个月,这是巨大的经济差异。但你想一下,我在中国是一个大学老师,是北京大学毕业的,还算一个知识分子,社会起码的尊重和自己展开的空间还是有的。但在加拿大,你什么都不是,甚至连到一个餐馆里洗碗炒菜的机会都没有。我记得有一个冬天,零下30摄氏度,我骑单车出去找工作。出去打工赚钱,我还打个的去吗?零下30摄氏度,整个城市在找工作的骑单车的就只有一个人,一个中国人。这就是我为什么拿了绿卡要回国,我拿到绿卡的第二天我就订飞机票回国了,觉得自己在这个地方太没有展开的空间了。
袁甲平:所以,《曾在天涯》的故事是您真实的经历吗?
阎真:《曾在天涯》基本是爱情故事为展开空间的,细节写得非常细腻,但其实是我虚构的。加拿大那个地方太现实了,你一个打工的人虽然在报纸上发过一篇什么文章,但你想依据这一点展开一个情感是没有的,情感空间是没有的。加拿大真的是不相信眼泪,女孩子现实也要理解她的现实,她要活要生存,她希望在加拿大活得好一点、生存得好一点,希望将来有房子,要找到一个明确的前途归宿,是吧?
袁甲平:但小说所呈现出来的思维方式是您个人的,尤其是那种对文化身份的焦虑感。这个思想空间,您是充分展开了的。您笔下的留学生活有很鲜明的形而上的精神气质,这与当年出国潮外在的激情似乎是不相契合的。
阎真:当然我刚才说的是故事层面,故事是虚构的。但我肯定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上面去思考人生,“曾在”是时间的感觉,“天涯”是空间的感觉,也就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在一个时空完全不同的国家去考虑自己的存在、价值和意义。这个小说里面有一些关于时空的句子,二十多年以后的今天我看了,依然觉得非常准确。“一个人一旦意识到了时间,他就和痛苦结下了不解之缘。”这句子还可以吧?意识到了时间就知道自己生命的短暂了,只有人有空间和时间的感觉,动物是没有的。时间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人类才几十万年,最多一百多万年的历史,地球是什么历史?几十亿年的历史,宇宙更不用说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闪电一样,一辈子就过去了。空间就更加惊人了,地球在宇宙当中的位置可以说是渺小到没办法计算。太阳是地球的30万倍,你知道有的天体比太阳还大得多吗?大犬座VY星,我们已知的最大星球,已经出银河系了,它是太阳的80亿倍,什么概念?你可以说如果那个星球是一个地球,那我们的地球就是一个沙子,这样的比例。有了这种宇宙感觉、时间感觉,就会觉得人生特别渺小,但是反过来也可以说人生特别的珍贵,居然在这种无限的时空中间有了一个你。这就是《曾在天涯》除了故事层面之外的一种精神价值,就是对自己生命的反思、对自己存在的反思、对时间和空间的反思。
袁甲平:您对时空非常敏感。
阎真:可以说,我个人对时间和空间是比较敏感的,但是回过头来说,反思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只是一种认识而已,该吃饭还要吃饭,该买菜还要去买菜,该洗碗还要洗碗。我原来住在湖南师范大学,楼下是一个天文学家,物理系的教授,我好几次看到他提一包小菜回来就非常有感受。他研究的事业是多么大的事业,应该不屑于做这些事,居然也提了一把小菜和肉回到家里来,他也一样回到这样一个最低层次的人生,一个天文学家提着一包小菜回来了,这就是说人生是具体的,对我们具体个人来说是非常具体的,不能脱离这种具体性去看生命,如果要脱离个体存在的具体性去看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什么都不是,你说它是一颗微尘都是夸大的。
袁甲平:您的四部小说都传递了这样一种价值观,要在生活的具体性上去讨论超越性、考虑人生的价值。但这具体的生活和人生理想之间,似乎总是不可调和,没有那么容易和谐统一。
阎真:《沧浪之水》是讲一个什么感受?就是说外在世界对人的改造。外在世界要你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不管你内心有什么样的想法,你最后都要去适应这种角色的需要,这就是所谓生存法则,角色就是生存法则。《沧浪之水》这样一种核心表达到今天依然成立,它很具体、很现实地揭示了很多人存在的方式。为什么《沧浪之水》到今天还可以有这么多的读者,二十年了。我写的第三本小说《因为女人》讲的也是生存。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开放的时代,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欲望化的时代,道德压力减小了,我们每个人,特别是女性,她面临什么样的情感挑战和生存挑战?《因为女人》就是探讨这样一个问题。
袁甲平:老师,我觉得这些问题在80后、90后身上似乎有所改变,比如说物质的焦虑,在我们这代人身上已经很大程度缓解,或者叫转移了。
阎真:这个问题我是这样想的,这个时代生存的压力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物质条件的改善而得到很大程度缓解,甚至我反过来认为,这种焦虑可能在我们这个时代还加强了。我为什么这么讲?从我个人体验来说,当时我从工厂要考到大学的时候很焦虑,但是大学毕业以后,本科毕业就可以到高校工作,当时分了一间房子,觉得可以了。现在的焦虑是什么?现在的要求比以前对个人发展、生活空间的要求,包括对情感的要求,要高很多很多了,不是高一点点,高很多很多了。以前我们只是要吃饱饭,到食堂吃一份肉菜就觉得非常幸福和满足,但是现在的生活要求已经不是在这个层次了。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分到一间房子,心里有很大的满足感。大概二十年前我住了一个小的三室一厅,90平方米,我拿到钥匙把门打开,跪在地上,亲吻了一下地板,我觉得自己能够获得这样一种生活,简直是非常非常了不起了、非常非常满足了,觉得一辈子这样已经是心满意足了,但是现在回过头去看,要我再住那个房子,也不算很小,90平方米,我觉得我可能几天都住不下去,因为这个生活水平提高了,眼界提高了。所以,作为我个人体验来说,现在的焦虑是因为对自己的要求高了,每个人都只有一辈子,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也是一个没有第二次的过程,这一辈子想生活得更好一点,所以说追求完美,包括个人情感、个人生活的每个方面追求完美,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何况我们身边有很多人的确生活得非常好,成为我们的偶像、目标。所以说,现在的焦虑在我看来没有缓解,甚至还加强了。
袁甲平:您刚才也说到,当年从拖拉机厂参加高考是非常困难的,从您个人来说,时间精力都是局限,从整个社会来说,也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我会觉得,父辈祖辈的焦虑更多来自生存,但我的焦虑更多来自不知道这辈子到底要干嘛,因为我不愁吃饭了。真的,我觉得这个好像更麻烦了,吃饱了,然后呢,这个问题我更不知道怎么办。
阎真:作为我个人来说,作为一个作家对现实生活体验来说,你这个同学我觉得可能有点特别,还比较形而上一点。我写的每一部小说都是天地而齐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我就按照什么样子去描写生活,贴着生活的地面走。如果我们的眼光还和很多年前一样,你吃饭不是问题了,一间房子就可以了,厕所可能在40米以外,这个目标当然是非常容易实现的。但是现在眼光已经高很多了,当然我也可以说这种焦虑是一个人前进的动力。我有一个新小说即将出版了,是我人生最后一部小说。这个小说就是表达的这个主题——年轻人的成长。
袁甲平:用现在时髦的说法叫年轻人的内卷。
阎真:你看我当时一路非常顺利,大学毕业以后到高校,学文学的到中文系教书,不要坐班,把谋生和专业知识、人生幸福结合起来,一路都非常顺利。现在达到这个目标是何等的艰难,现在年轻人的成长是何等艰难!他们在生存空间、事业空间上开拓,我可以说比我们那个时代还更加艰难了,正因为如此,我也认为这种焦虑没有随着物质生活的进步而缓解,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还加强了。
到一百米的高空去俯瞰生活
袁甲平:人们的思维方式、情感体验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被市场所左右了,我们可以追问这是不是有点不对?为什么不对?
阎真:我觉得市场经济掌握了绝对话语权,理想就会节节败退,我特别不喜欢一个说法叫,得到就是实惠。
市场经济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巨型话语,就意味着它无孔不入,无形中左右你的思想。市场经济就是一个功利主义,我可以理解,但是作为我们每个具体的人来说,是不是要完全屈服于这种功利主义,我们是不是还有一点生存空间、有一点精神空间可以从功利主义当中拔出来?我们也许翅膀飞不到那么高,但是我们是否也可以稍微飞起来一点?我们不能到一万米的高空,但是能不能到一百米的高空去俯瞰一下生活,超越一下世俗的物质性?这很大程度上也是文学的价值和意义。就是说,我们从世俗生活当中也许暂时解脱出来,进入一种超越的境界,读小说和诗歌不是为了赚钱,不是图别的,而是为了精神的愉悦,是为了审美的快感。这也是为什么小说一定要写得很好很精彩很吸引人,这是一个作家基本的公理和使命所在。
袁甲平:所以,您认为应该给活着之上的东西留有余地。
阎真:我们每个人都没有办法逃脱生存的压力,这种生存的压力在今天,直接的结果就是现实的功利主义,活着就是一切,活着之上是不存在的。但活着之上是不是多少也有一定的价值?是不是还有一点除了活着之外的价值供我们今天的人来选择?如果不是知识分子,也许这些我们可以不做要求,如果是知识分子,这些命题还是要思考一下,在我们这个社会中还有没有精神的空间?巨大的市场、巨大的背景、巨型话语几乎左右我们的所有行为,一个人,一个知识分子还有没有那种展翅飞翔的空间和可能性?除了活着,还是不是有一定的、活着之上的空间意义,我也没有结论,我只能说我的主人公还是想去争取这样一个意义,不想做一个彻底庸俗的人,不想对生活完全随波逐流,也不想被功利主义引导一切。但是即使如此,这样一个非常低的心灵追求也是非常艰难的,有时候觉得生存中间这样一个底线都保不住。
袁甲平:对这个问题,我的出路一直很理想主义,我觉得读书、读文学能够让人短暂地从具体生活脱离出来。当然,我的前提是,得坐得下来、读得进去,我经常觉得享有文学是这个时代里难得的福气。
阎真:在这个市场经济时代,每个人有很大的生存压力,这些压力能不能用文学来解决,或者缓解,在很大程度上,我可以说这是一种理想,这种理想要得到实现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袁甲平:那老师您觉得在当下文学对我们还意味着什么?
阎真:这个时代文学还有存在的空间没有?我觉得还是有的,文学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情感交流。文学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不是用来讲道理的,是用来触动情感的,道理我们都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讲,不一定要用文学的方式,但是情感就一定要用文学方式表达,我们的前辈杜甫也好或者曹雪芹也好,如果他给我们讲的只是一些他的人物有什么思想内涵,那文学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就是可疑的。在我们这个时代,文学在强大的市场压力之下没有像以前处于我们生命的核心地位,但还是很有价值,它是我们情感交流的一种方式,看看别人是怎么生存的,别人对生活是怎么想的,这些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对我有什么意义和启发。这个意义和启发要通过审美的方式、情感交流的方式来实现,这对作者来说也是很严峻的挑战。
袁甲平:浅层次的情感交流可以看手机。
阎真:是的。你的作品凭什么去征服读者?文学必须有手机达不到的、更深层次的情感交流和思想交流,而且这种精神愉悦、情感沟通我觉得不但在我们这个时代,在任何时代都是非常需要的,这就是文学的生命力所在,文学的生存空间所在,也是文学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袁甲平:但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各种移动终端,确实对图书造成了冲击,许多人都不看书了,并且对生活似乎也没什么影响。您觉得文学阅读在当下人们生活中还占有多大分量?
阎真:我觉得文学阅读因人而异,很多人一辈子都不接触文学,他也可以生活得很好。文学是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必需品,我说因人而异。在我们生活中,阅读文学是不是已经成为一个小众事件,这种判断能不能成立?毕竟每天看抖音的有多少人,阅读文学作品的有多少人?我们统计一下,这个数字可能是很悬殊,比如几十比一。但这个并不要紧,还有一部分读者,我们就已经非常欣慰了。作为我个人来说,我写《沧浪之水》,已经过去二十年了,还可以得到读者的这样一种持续关注,我也感到非常欣慰,就是自己的小说在二十年中间一定程度上还是站住脚了。
另外一个判断我不知道对不对,从我个人的体会,我觉得该看小说的人他还是看小说,比如我自己的小说,十五年以前,每年大概是五万本。现在手机阅读是如此普及,《沧浪之水》每年发行还是五万本。五万本是一年的发行量,非常的均衡,也非常稳定。我不知道这种现象是怎么形成的,但是这是一个事实。
袁甲平:您是怎么看待碎片化阅读的?
阎真:我们这个时代,读图的时代,或者碎片化阅读的时代,每天晚上可能只有上床之前的二十分钟可以沉下心来读一点书。但是我个人觉得一个人要追求精神的深度还是要去阅读纸质的读物,你在手机上读和拿本书在手里读,那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个体验的境界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手机上你不可以说重点是什么东西,不可能。手机上阅读有它的好处,它的情节一下子就吸引你了等等。但是手机上阅读从情感的层次来说就是浅程度的阅读。既然时间在我们这个时代是最宝贵的东西,你既然愿意投入这么多时间去阅读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花一点时间去阅读一本纸质书,回过头来还可以把你自己的阅读感想写在旁边。因为你投入了最宝贵的时间,你就不要在乎那点小小的几十块钱的一本书了。我个人感觉是这样的。
我的文学观念就是艺术本位
袁甲平:老师,除了写作,文学研究也是您的主业,作家和教授的双重身份在您身上似乎并不存在冲突,比如感性思维和理性思维的冲突。
阎真:我是一个大学教授,在高校执教已近30年。别人了解我,主要是通过我的小说,但大学老师是我的职业,因为职业的需要,我在小说创作之外,还要从事理论研究,对象主要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我认为作家和教授两种身份是不冲突的,不但没有冲突,两种不同思维还可以相互启发、相互促进的。这种启发和促进的结果,使我的小说创作有着理论思考的特征,而理论研究也有着强烈的艺术本位倾向。
袁甲平:您的文学批评始终强调艺术本位。
阎真:我的文学观念用四个字来表达就是艺术本位,在我看来,文学史就是“经典性”的沉淀史,而艺术本位,则是这种沉淀的基本选择标准。我教中国当代文学,给本科生研究生开“小说艺术”“小说理论”课程。对于任何作品,我首先关注的不是它是否触及了敏感而重大的社会问题,是否有精神创意性和思想深刻性,而是它是否具有较高的艺术品位。因为,我分析的对象是文学,既然是文学,我的第一眼光、第一标准必须是从文学本身派生出来的,即艺术性的眼光和标准。偏离了文学的眼光,直接面对作品的社会性、思想性、时代性,那不是文学批评。艺术标准是本体性标准,这是文学的尊严所在。有些作品由于时代的社会的原因,在非文学的意义上获得成功,获得读者,获得市场,我也承认它的成功。但对这种成功我会保持冷静、保持距离,坚信艺术的力量将在时间之中选择自己的经典。
袁甲平:按照我们一般的理解,文学强调审美性、艺术性不是理所当然的吗?您为什么那么强调艺术本位?
阎真:不是这样的。其实我们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结构是非常稳定的,什么是好的艺术,什么是不好的,不是按意识形态、社会意义来选择的,而是按照艺术来选择的。“一行白鹭上青天”,有什么意识形态意义?“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有什么意识形态意义?有什么社会意义?都是片刻人生的感受。所以说,我们的古人做文学史的选择是非常精确的,比如说《唐诗三百首》,我不能说它选择的都是最好的,但是比如说杜甫的“三吏三别”之类比较有社会意义的它没有选,白居易的《卖炭翁》也没有选,这是体验民间疾苦的,更不用说什么“锄禾日当午”什么的,都没有选。《唐诗三百首》按照艺术标准来选择,我也不能说它的标准就是绝对正确的,但是它的基本框架是对的。《唐诗三百首》为什么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就是按照艺术的标准来选择的,这就是古人的刚性原则。
袁甲平:现当代文学批评没有很好地延续这个原则。
阎真:你自己学中文的,应该知道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史的选择方式和古代文学完全不一样,不是站在艺术的角度选择的。
袁甲平:比如郭沫若的诗歌。
阎真:你们用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基本是现代文学史一统天下的版本,每个学校都用这个教材,郭沫若在这个教材上有专章。郭沫若在当年确实影响很大,但是你说他的诗是很好的诗吗?不能。《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也说他在艺术上并非十分成熟。其实,现代的文学史上比郭沫若写得好的多了去了,比如说徐志摩这些诗人。但徐志摩这样的诗人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一节都没有,这是全国性的教材,就是这种比例关系。他的选择标准是什么?是社会历史、社会影响。郭沫若影响大吗?大。但是这种社会影响是时过境迁的,在这个历史背景下影响大,换一个历史背景就没有那么大,没有那么重要的意义了。40年前,我读大学的时候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三卷本,七十多万字,张爱玲、钱钟书连名字都没有,沈从文有名字,但不是因为《边城》等,《边城》等有很好的艺术品位的作品根本没有提到,文学史有他是因为他是“第三种力量”的代表人物。这样看来,关于中国新文学历史描述的错误到今天已经有了很大改变,但依然很不彻底,距离历史稳定性的目标,仍有相当遥远的距离。强大的社会意义是瞬间的存在,但是艺术性是超越时空的存在。所以编现当代文学史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标准来选择?我觉得起码现有的教材几乎每一本都是有问题的,选择的眼光都是有问题的,现当代文学史什么时候能够重新按照我们古人的那种标准、艺术本位的标准来写,是不是有那么一天?
袁甲平:但是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艺术性不那么高但发行量巨大的作品,您怎么看这一类作品?
阎真:这个太多了,每年都有。二十年前有一部作品《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当时发行量巨大,上百万册。我也去买了一本,但读了这部作品,我无论如何都兴奋不起来。原因很简单,就是艺术品位缺乏。艺术性并不好的小说能够获得这么多读者,一度我都怀疑,艺术性是不是真的那么重要?后来的情况证明,我的判断还是对的,这个书确实只是风靡一时。社会历史意义上的成功,只有建构在艺术性的基础之上,才是真实可靠的、长久的。一部作品,无论它怎么轰动,怎么好评如潮,如果它不具备艺术的标高,我宁愿保持沉默,也不会加入歌颂的大合唱。我不能脱离文学的标准谈文学,艺术的标高是经典性的标高,这是一种很高的甚至可以说超高的标准,同时也是一种不可超越的没有例外的标准。
所以,至少我可以说,一个写文学史的教授永远不可以忘记你是在写文学史,不是社会学、历史学,文学史有它的学科主权。文学学科的主权是什么?就是艺术性、审美性。它也有它的学科规范,学科的规范是什么?也是艺术性标准,审美性。它不要依附于什么社会学、历史学、意识形态等,这是学科规范,也是学科尊严。审美就是刚性的原则,是它的起点,文学的所有意义都要建构在审美上。我们还是以唐诗为例,一首诗我们可以说它有多方面的意义,社会历史意义、文化意义,以诗正史这些意义都确实存在,但所有这些意义的基础是什么?是审美性,你没有这个审美性和艺术性,所有的意义都不能成立。我们不能脱离审美性谈其他的意义,为什么?你是在谈文学,要按照文学的规范、文学的学科尊严和文学的主权来谈。这就是我的文学观念——艺术本位,我不是说我做得很好,但是我是往这个方向努力。
语言对作家而言具有身份界定的意义
袁甲平:老师,您认为我们现当代文学史研究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偏差?
阎真:这样一种实用理性文学观念的形成,有着历史的必然性。在几乎整个20世纪,中国社会都处于社会革命社会改造的进程之中,这一进程向文学提出了强烈召唤,文学也给予了这种召唤以积极的回应。通过对一百年来的中国新文学的宏观透视,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实用理性精神,也就是说,这一百年来,文学的基本价值和意义并不在于审美,而在于完成某种社会使命。在20世纪之初,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开篇就提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把小说的社会实践意义作为了其核心价值。这种关于文学意义和功能的价值观念,在整个20世纪,直到今天,占有了绝对主导的地位。作家总是试图通过自己的作品影响读者,引导读者对生活做出与自己相一致的判断,从而转化为实践性的力量,推动社会改造。在这种文学观念中,社会实践意义成了文学的终极目标。反过来说,作品的价值和意义,要放到这个评价体系中接受检验。所以,现当代文学的核心价值观与古代传统有着极大差异。
袁甲平:鲁迅先生也强调文学对社会大众的启蒙意义,认为文学要“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
阎真:鲁迅这话没有错,文学也应该承担“为人生”的社会使命。但我认为,这种承担应该是以艺术方式实现的承担,也就是说,“为人生”并不意味着可以因此将作品的艺术品格在价值上边缘化。鲁迅自己在这一点上就是一个榜样,《孔乙己》《祝福》等小说,是中国新文学的精品,放到我读过的所有中外短篇中,也是艺术极品,是艺术呈现与社会意义完美结合的典范。我们视野中的鲁迅,既是思想家鲁迅,更是文学家鲁迅,首先得是文学家鲁迅。艺术性是文学作品一切意义的前提,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个前提,抽离了艺术性基础,直接把“为人生”拿来作为评价作品价值的核心依据,特别是文学史选择的核心依据,那就错了。
袁甲平:我觉得,如果作家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指导社会实践,那大概率得主题先行,而且人物关系、人物的思想都得处理得比较简单,才能对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斩钉截铁。
阎真: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是巴金的《家》。《家》是新文化运动时期第一部表现新一代年轻人反抗家族制度、争取爱情自由的长篇小说。这是它在社会历史意义上的地位,但从思想上来说,《家》用一种绝对的姿态批判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且仍有强大生命力的家族制度,显然是太简单化了。而且,在人物关系的构筑上,巴金把中老年两代人划为思想僵化道德败坏的一类,把年轻一代划为心地纯洁道德高尚的一类,这种绝对的、按年龄简单划分道德高下的处理方式,截然的善恶二分,也显然是太简单化了。你可以对比一下《红楼梦》,它写的也是大家族,但曹雪芹塑造了几个系列的人物形象,都非常鲜活。比如小姐系列的黛玉、宝钗、湘云、探春,太太系列的王熙凤、贾母、王夫人、赵姨娘,丫鬟系列的袭人、晴雯、鸳鸯、平儿、傻大姐等等。同是小姐,同是太太丫鬟,各有各的个性。几百个人物,几乎个个面目鲜明,不雷同、不重复。这种人物塑造的能力,古今中外,绝无仅有。我认为这是《红楼梦》处于巅峰地位的最基本原因。《红楼梦》有没有社会历史意义?也有。比如色空观念的表达,对女性的尊重,虽然也很重要,但相对于艺术性,终究是第二位的。巴金的《家》很有激情,但显然把复杂的生活简单化了。这种简单化可以表现爱憎分明的激情,但说到底,他无法表现历史和文化的深刻。
袁甲平:也就是说,他为了社会意义把生活简单化,反倒无法到达社会意义的深层?
阎真:可以这么说。
袁甲平:除了人物,《家》的语言也不是特别好。现代文学史上享有盛名的许多作品,似乎也都有这个问题。这是不是因为当时的现代汉语还不够规范?
阎真:《家》的语言不是不够规范,是过于规范。过于规范,所以缺乏个性色彩,几十万字,看不出作者的才情和心血,没有语言创造性。作为一个在文学史上有如此地位的大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明显的遗憾。
袁甲平:您认为语言在文学评价中,占有什么地位?
阎真:我认为,语言是文学作品的核心指标之一。对一个作家来说,这个指标具有身份界定的意义。汪曾祺说:“往往有这样的说法:这篇小说写得不错,就是语言差一点。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我们不能说这首曲子不错,就是旋律和节奏差一点;这幅画画得不错,就是色彩和线条差一点。我们也不能说:这篇小说不错,就是语言差一点。语言是小说的主体,不是附加的,可有可无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语言的粗糙就是内容的粗糙。”我非常认同他的观点。
袁甲平:我读了您今年出版的《小说艺术讲稿》,虽然听过您的“小说理论”课程,但还是觉得受益匪浅。对读者,我觉得这部讲稿可以帮读者判断一部作品的好坏,对写作者,可以在里面学到很多技巧。
阎真:一个中文专业的大学生,在文学院修炼了四年,你敢不敢说自己有了纯正的文学价值观,敢不敢说自己是一个专业读者?我跟文学纠缠了一辈子,一晃五十年就过去了,到了退休年龄,一辈子就是如此。我最后的野心,就是希望这部小说艺术讲稿能够帮助那些对小说创作有兴趣的朋友进入艺术境界,也希望我的文学价值观能够有更多的理解者。
要为爱好找一个生存基础
袁甲平:老师,您支持自己的学生从事文学创作吗?您怎么看待这个时代的文学青年?
阎真:文学和青年,能不能这样说,不管你是学中文的或者不是学中文的,你首先还是要找一个生存的基础,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去从事你的爱好,不要把命运全部赌在这里。因为把命运赌在这里,成功的机会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大。今天还有很多人在写,其中当然也包括青年。十多年前,我收到过这么厚一本打印稿,起码四十万字,是一个女裁缝写的。我读了,文字也还不错,但到现在过去十多年了,这个女裁缝今天在哪里?为什么没有崭露头角?她真的写得还可以,但是就这样被时间埋没了。我们有多少中学生小作家,他们也写得不错,表现出相当的才华,但是后来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都被时间所埋没了。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容易被埋没的地方,要拱出来,突破这个地平线是相当不容易的,这是我的感受,我不能说作为你的人生指导,我只是说我的一点感受。
袁甲平:我们今天一开始就谈论了文学阅读的意义,我觉得如果说坚持文学阅读有点理想主义的意味,那从事文学写作可以说有点浪漫了,尤其是纯文学写作。
阎真:在一个非常现实的时代,文学多少是一个浪漫主义的事情。现实生活中这么强大的压力,非常具体,你还要从具体性当中超脱出来,这是需要一点点超越功利心的。我可以说,我们的文学也不要寄托太多的希望,我们更多的行为是被现实所制约、被现实所引导。我作为一个作家,我也承认这一点,我自己不能说不敢说我有多大的超越性。但我一辈子对权利和钱不是那么的敏感。而且,文学的确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从青年时代开始的事业,或者说一种兴趣爱好,我们暂时不谈事业,如果能够成为事业当然更好,如果没有成为事业,成为业余爱好也不错。当然这个既然是事业就越早越好,像我这样的是比较晚的,张爱玲的名言说,成名要趁早,她确实成名是趁早,二十三四岁的时候就写出她人生最经典的作品《金锁记》《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等等。后来她写的小说都没有达到这样的水平。
袁甲平:那您觉得,有志于文学事业的青年,应该如何坚守理想?
阎真:是这样的,这种矛盾对很多人来说,甚至可以说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存在的,我内心向往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状态,我内心觉得什么是对的,什么是美好的,和我的现实生活往往不协调,现实对我有一种制约,我要跟现实妥协。有时候我想一下我们中国古代的文化英雄,我用的是“文化英雄”四个字,这些文化英雄比如说屈原,他就是不向现实妥协的,但是他个人的命运怎么样?投江而死。比如说后面的陶渊明,也是不跟现实妥协的,如果跟现实妥协就没有屈原了,就没有陶渊明了,对不对?放着官不当去当一个农民,生活非常艰苦,这是文化英雄。特别是我个人是写小说的,我最崇拜的就是曹雪芹,不论是他的艺术才情还是他这样一种人格标杆都到了极致,《红楼梦》写出来没有拿一分钱稿费,曹雪芹生前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小人物,说起他,我现在都感到非常激动。他有很多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家也有达官贵人,他背向功利主义,面向自己的心灵,但是他的现实境遇是非常凄凉的,这么伟大的一个人物埋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他是一个太小太小的人物了,没有人知道他埋在什么地方,如果他生前有一定的名声,不要说后世这么大的名声,有一点,都不至于埋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连墓碑都没有。
当然我也说,文化英雄是供我们瞻仰的,我们普通人学不到,这些文化英雄每一个人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从屈原到曹雪芹,每个人都付出了沉重代价,我们是凡人、俗人,没有必要像文化英雄那样活着。而且我可以说,这些文化英雄不是个别人,是一批人,他们是有气节的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还有很多人因为没有这么高的才华,默默被时间所淹没了。但是我个人觉得,包括我自己的选择,我觉得他们那种精神标高太高了,我们可以瞻仰他,像仰望星空一样地仰望他们,但是如果说去成为他们,这种挑战太严峻了,而且成为他们,他们是非常有才华,才在历史上留下名声的,如果我们是普通人,根本默默无闻,会被时间淹没,连痕迹都没有一点,当然心也有不甘。
袁甲平:所以说,现实和理想之间还是要有一个平衡。
阎真:当然要找一个平衡。仰望这些文化英雄,我的人格不会太低,我的精神境界不会太低,我不会成为一个唯利是图、察言观色的小人,但是生活在召唤,是不是?现实在召唤,我还要想提拔,我还想买房子多赚点钱,我还要养家糊口,很多沉重的、现实的压力和要求,我必须去完成。这中间需要平衡,我不能因为现实需要就成为一个察言观色的人,一个小人,不能在每一个地方委曲求全,完全没有人格。
袁甲平:那您觉得可以如何找到平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