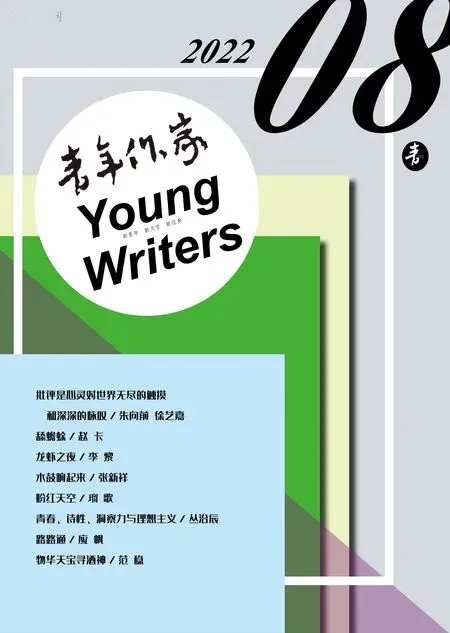粉红天空
瑠 歌
一
他要寻找月租低于三百美元的地方,过去六年,他尝试在布鲁克林某间被雨淋湿的阁楼里,成为伟大的诗人;实际上,即便他成功了,也无法逃避维持生活而必要的枯燥劳动,与他人的漠视。
临走时,他将许多诗稿留在地板上。
他来到车站,不知去往哪里。任何在日光下被遗忘的便宜小镇都是好的。
我们的主角,随意挑选了一趟列车,走了上去。车厢里,一个肥胖的老女人躺在椅子上喘息,她的皮肤布满太阳斑,足以证明一个人躺在摇椅下孤独的时间。她的膝盖支撑不了多久,睡觉的时候,好像随时会在睡梦中逝去。
一个金发少年坐在前面,用耳机将自己与世界封闭起来,他背着一把吉他,看上去是从家里逃出来的。
三个人坐在一个车厢里,习惯了旅途的彷徨。
健壮的黑人列车员穿过走廊,他的黑色风衣像是从战场上穿回来的。
车门关上了,景色开始流动,夕阳对城市施了一个魔法,让所有人都消失了。主角看着窗外,闭上了眼睛。
他醒来时,列车停在了一个陌生的夜晚,新月下的树林遮住了站台,戴耳机的男孩背着吉他下车了。十年后,他的名字也不会出现在某张海报上,他会继续弹奏吉他,默默流浪。
列车继续开动,肥胖的老女人从噩梦中惊醒,朝四周张望,车厢内的黑暗令她茫然。主角从后面窥视着她,想象着她的生活——对着深夜电视,暴饮暴食。
老女人回过头,与主角对视了两秒钟,她的眼神充满偏见,对穷人的偏见,对世界的偏见,主角早习惯了这样的目光。
“小伙子,要不要来点?”
说着,她从紫色的书包里取出一大包巧克力威化饼干。
主角只是腼腆地笑着,没有说话。
“来点吧,小伙子。”她嘶哑地叫道。
主角走了过去,坐在与她隔着走廊的位置。甜腻的玉米糖精在他的舌头上融化,啃下第三块之后,他感觉到胃在犯恶心。
“怎么样,再来点吧?“女人露出圆形的牙齿,大笑道。
“不了。谢谢您。”老女人还是硬塞给他一块儿。他勉强自己咽了下去,这样可以省去一顿饭的费用。
“你从哪里来?”老女人问。
“我出生在罗德岛,之后搬到了纽约市,现在又要上路了。”
“去哪里?“老女人吮着指尖的巧克力。
“不知道。”主角腼腆地一笑。
“你在流浪吗?没有工作?”
“算是。”
老女人用油腻的手拍了下主角的肩膀:“这不怪你,孩子,这个国家要完蛋了。”
“为什么?”
“太多的移民、亚洲人、黑人,和老鼠一样,到处都是。”
“如果我是黑人,您还会给我巧克力饼干吗?”主角笑着说。
“不会,不过……”老女人认真地看着他。
“不过什么?”
“不过我们都是可怜的人类,并非自己选择来到这个世界上的。”
“我明白了。”
主角转头望去窗外,密林中掠过一条踪影。此时,黑皮肤的列车员,又一次穿过走廊,他似乎躲在后面偷喝了酒,眼神麻木。
“您要去哪里?”主角问。
“我吗?”老女人又从包装里抓出一块巧克力饼干。
“迎接我的死亡。”
“在哪里?”
“佛罗里达。”
“从这过去要两天两夜。”
“我知道。这是我最后一次旅行了,我要好好看看周围的风景。”
“你觉得风景怎么样?”
“很普通。”
列车的轨道在郊外的工厂、森林的白房子间穿梭,如果没有地图,你永远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每个地方看上去都一样。
“到了那儿你有什么打算?”主角问。
“我找了一间不错的汽车旅馆,在一棵大树下,走路到海滩五分钟,没什么人。”
“之后呢?”
“我会在那里迎接死亡。”
主角仿佛看见了她肥胖的尸体腐烂在床单上,被苍蝇环绕。
“你有家人么?“
“有过。”
“他们现在怎样?”
“我不知道,你呢,小伙子?”
“他们住在马萨诸塞州的多切斯特。”
“你们不联系么?”
“不常联系。”
他们意识到这个话题无法进行下去,便沉默地别过脸,看着车窗上跳动的光影。
五分钟后,黑皮肤的列车员又茫然地穿过走廊。
“嘿!”老女人喊道。
他转过头,表情像杀过人,并且习以为常:
“怎么了?”
“你在喝酒!”她指着他笑道。
“所以呢?”他继续麻木地看着她。
“分给我一口,不然我就举报你。”
他面无表情地说:“你不如花钱买。”
“给我一口。”老女人又叫道,伸出了手。
“见鬼。”他叹了口气,从黑色夹克内侧取出一个银罐子。
“别喝太多。”
“放心。”
老女人将琥珀色液体,倒入了蛤蟆般的嘴巴里。
“哈!”
“带劲儿!”
她用粗短的手指掠过嘴角的威士忌,“好了,我想你应该再分给年轻人,他很眼馋。”
主角含蓄地摇头,“没有,我没有,谢谢您,不用了。”
列车员打量着他,“你多大了,孩子?“
“二十五岁。”
他看着这个年轻人,一件松垮的绿色外套裹着他瘦弱的肩膀,鼻子很高,棕色头发蒙上了蓝色的眼睛,一个萎靡的白人青少年,大概十七八岁。
“真的?”
“是的。”
“来吧。”说着,老女人将瓶子递给了主角。
“喝一大口。”
“一小口就好。”
“喝一大口!”老女人突然怒目而视。
主角刚举起瓶子,老女人一把按住他的胳膊,酒止不住地灌进他的喉咙,他咳嗽着,酒顺下巴流到脖子,老女人才松开了手,他朝着地板干呕了好几声。
“天哪。”
他抬起头来,感觉到燃烧的内脏,咳嗽到眼泪出来了,眯眼望着老女人。她在大笑,高大的列车员原本面无表情,也笑了两声。
“这才对嘛。”老女人说,“感觉怎么样?”
主角靠在椅子背上,全身松软下来。一阵能量从生命深处涌了出来,使他感觉到自己能毫发无损地穿过生活的火焰。
“还不错。”他扬起嘴角。
列车员收起瓶子,背对他们说:“好好享受这个夜晚。”之后进入了阴影中。
“谢谢你,黑人小伙子!”老女人朝他挥手。
随后,老女人对主角说道:“你知道吗?孩子,在你出生之前,我们可以自由地使用黑鬼这个词,我们可以辱骂任何人。”她仿佛从车厢尽头的黑暗中望见了过去,叹息道:“我们可以辱骂任何人,现在不行了,如果你对着一个脏兮兮的清洁员说‘黑鬼’,他们会曝光你,你会丢掉饭碗,你是一个白人,却在这个国家一无所有……”
主角平静地看着她,他的内脏燃起熊熊大火。
老女人接着说道:“这里是美国,我们应该有言论自由,不是吗?”
主角没有说话,过了十四秒钟,问道:“如果你刚才对他使用了黑鬼,会怎么样?”
老女人意味深长地看着那片黑暗,“我不知道,也许我该说出来,我已经老到要腐烂了,我应该行使我的自由,不是吗?”
主角望着那片黑暗,缓缓地说:“我觉得他会取出一把刺刀,捅死你。”
“为什么?他没那胆子。”
“我觉得他可能干得出来。”
“哈,好吧,你们这些左派的小子,你的父母也投票给了奥巴马么?”她摆手笑道。
“不,他们是资深共和党人,与酒鬼。”
“哈,替我向他们问好。”老女人又用油腻的左手拍了拍他的肩。
“你呢?”
“我不投票。”主角说。
老女人的神情又严肃起来,她下巴与脸颊上的肥肉,使她在黑夜像一名深沉的思想者。
“但是孩子,我们是一样的。”
“我们是指?”
“所有人,除了有钱人。”
“为什么。”
“我们只有靠更多的酒精与糖,让自己腐烂,才可以活下去。”
“为什么。”
她又用油腻的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因为生活永远是痛苦的,只有短暂的快乐能短暂地战胜痛苦,明天,又将回归黑暗。”她好像从空中抓起一把粉末,散落在面前,闭着眼睛,将痛苦吸进了鼻腔里。
“我不知道。”主角说。
老女人笑了笑:“别担心,孩子,总有一天,你也会和我们一样。”说着从包装袋里抓出三块巧克力华夫,一口塞进了嘴巴里。
“你的父母只是两个爱酗酒的白人,你一无所有,你没有希望……”
列车驶入了隧道,黑暗降临了,一阵阵风吹过。
“我不知道。”主角说。
之后,她昏睡过去,眉头微皱,张着嘴,在与睡魔抗争。
早上六点钟,主角睁开眼睛,在车窗外看见了平凡的海滩,一个小女孩从沙子里捡起什么东西——什么都没有。她父母潮湿的蓝色木屋就在旁边。一片树林,接着是大桥,寂静的工厂立在大海边上。
之后,白日又出现了,它映在了深蓝色的椅子上,白日永远会出现,因此你也不用期待它。
昏睡的老女人醒了过来,拖着肥硕的身躯,走向洗手间。她在座椅之间的走廊摇晃着,每走一步,像腿断了的人,在医院做康复训练那么艰难。
过了三分钟,她皱着眉头从洗手间走出来,好像经历了极大的痛苦,回到座位上,闭上双眼,面朝天花板喘息着。
“上帝啊。”
“列车员!”她大叫。
一个白皮肤的列车员,面带小镇男孩的憨厚微笑,走了出来。
“怎么了,女士?”
“还有多久到德克夏尔?”
小伙子看看表,抬起头,又示意她憨厚的微笑,“还有四十分钟。”
“好的……”她松了口气。
“妈的,我快要坐死在车上了。”她的脸颊流下虚汗。
“您要在那里下车吗?”主角问道。
“是的。”
“去干嘛?”
“看望我的儿子。”她艰难地揉着后腰。
“我要去见他最后一面,之后独自迎接自己的死亡。”
之后,主角没有再问她别的事情。周围的景色在教堂、白色的房子和草坪之间重复,随后抵达德克夏尔。”
她站了起来,拉开拐棍,背上紫色书包,用潮湿的手拍了拍主角的肩。
“再见,小伙子。”
“再见。”
她走到车厢前面,找出自己的银色行李箱,临走前,主角叫住了她:
“你叫什么名字?”
“什么?”
“你叫什么名字?”
“琳达。”
“再见,琳达。”
“再见,孩子。”
车厢里又走上来几个单身男子,典型的小镇居民,穿着图案已被洗掉的短袖,列车继续出发。
主角拿出手机,点开记事本,他想写一首诗,而很多思绪卡在了内脏里,好像随着昨夜的那瓶烈酒一起燃烧了。
二
主角决定下车了,没有特别的理由。
车厢里只剩下一个昏睡的白人,灰色帽衫套着瘦弱的四肢,手臂上的青色文身已褪色,他没有行李,也不知要去往哪里。
主角在心里与他告别后,下了车。站台位于车站二楼,列车离开后,天空露了出来。灰色的城市,被撒上了和煦的阳光。不远处,五座高楼错落分布,那里大概是市中心。
他走下台阶,没有人,推开大门,一个黑人站在马路旁打哈欠,他似乎是唯一的工作人员。
“你好。”主角说。
黑人神色诡异地看他一眼,不理解为什么眼前出现了一个白人孩子,将他从白日梦中拽了出来。
“你需要什么吗,孩子?”他的嗓音有些滑稽、嘶哑。
“我刚来到这里,我想找一个房屋中介,最好便宜点的。”
“房屋中介?”
“对。”
“你要搬到这里?”
“差不多。”
“哇哦。”他吐了口气,好像生活又有了乐趣。“房屋中介,让我想想。”他指着一座红白色的塔楼。
“看见那座塔楼了吗。”
“嗯。”
“那是最棒的公寓。”
“对我来说太贵了。”
“孩子。”他平和地面朝主角,“你大概是几年来的第一个新居民。” 他指着被阳光染成粉红色的塔楼说:“去吧。”
“这地方很久没有人来了么?”主角环顾四周,街上空无一人,洗衣店的牌子上只剩下一半字母,两辆三十年前的汽车停在路边。
黑人浪漫地叹了口气,仿佛听见了一首过去的情歌:“我们被遗忘了很久。”
“你需要顺风车么?孩子。”
“不了,我走过去。”
“一路顺风!”
“这里叫什么名字?”穿过十字路口,主角回头喊道。
“拉尔夫特!”黑人喊道,随后又踱起步来,回归他的白日梦。
主角走到拉尔夫特的街上,五分钟没有看见人,这里貌似与美国上万个平淡小镇没有区别,又不太一样。他不知道自己在地图上哪个位置,甚至一度怀疑,这里是否存在,而他还在列车上做着梦。
两个穿短裤的黑人孩子,骑着成年人的自行车,从街道上飞驰而过。主角在陌生的街道继续走着。他来到一片棕色的联排公寓前,院子的草坪很干净,一个红褐色皮肤的女人在烧烤,透过烤肉的烟雾,迷迷糊糊地望着过路人。
城市中心的路是斜的,一辆1972款的黑色道奇跑车,闯过了停滞的红绿灯。街边的长方形大楼是希尔顿酒店,墙壁上的窗户像是用打字机印上去的黑色方块——一座巨大的幽灵。
他仿佛看见,灰色透明的雨点,落在空荡的城市间。
红白色的公寓在太阳要落下的方向,不同于整个城市的灰冷色调,散发着四十年前曾经富饶的白人中产阶级情调。暗淡的金色门牌上,印着斜体的字母:幸福塔。推门走进去,红地毯有些褶皱,两边摆着白色花瓶,插着腐败的假花。
电梯缓缓上升,如同衰老的人爬上楼梯那样。到了三楼,他走向红地毯的尽头,玻璃木门上挂着金色牌子:管理员办公室。
他推开门,办公桌后,一个黑人老头在阅读一本小册子,他的西服很考究,尽管他每天的管理工作,只是一个人面对寂寞的大楼阅读。
“你需要什么,年轻人。”他抬起头瞥了一眼,目光又回到黄色的书页上。
“您好,先生,我想要租一间公寓,越小越好。”
“不好意思。”管理员轻快地说,“我必须把这一页看完。”
大概又过了十秒钟。
“好了,小伙子,你想要租一间公寓?”
“越小越好。”主角笑着补充道。
管理员上下打量着他,“是什么风把你吹到这儿了?”
“我只是来到这里了,我坐在列车上到了某一站,我决定下车,便来到了这里。”
“外面的生活太痛苦了,所以你逃避了,找到了这里?”
“一点也不错。”
“孩子,你或许来错地方了,拉尔夫特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是黑人。”
“我不介意。”
“你不介意?你只是不知道。你们这些长在白人区的孩子,从小听了太多种族平等的谎言,你不知道我们是什么样子的,你没有和我们生活过……”
“我不知道,但是我不介意。”主角淡淡一笑。
管理员用上扬、敌意的视线,审视着他,眼白透着红色的血丝,那大概是他对抗世界的姿态,“黑人有体臭,又懒惰、自私,如果没有钱赚,他们只会躺在沙发上吸毒。”
主角有些羞涩地别过头,“您是不想让我住在这里么?”
“不。”他否认道,“这栋公寓,本来就是给白人开发的,只是他们遗弃了这里,一场骗局。”
“一场骗局?”
“对。”
管理员便讲述了拉尔夫特的历史,大约四十年前,在里根时代,一些开发商决定大肆开发这里,他们修建公寓、商场、酒店,将拉尔夫特塑造成中产阶级的理想养老城市。那个时代,一个普通白人家庭,靠着父亲的一份工作,便能养活全家,购买新的彩电。增长似乎是无限的。中产阶级抱着投机的念头,将他们的钱植入这里的地产。可好景不长,89年股灾后,开发商的资金链断了,留下修建到一半的商场;房子变得一文不值,人们将房子以一半价格抛售,仍然没有人接盘。就这样,从没有来过的人,将他们的度假屋遗弃在这里,来了的人陆续离开,最后城里只剩下黑人,这里成了黑人的社区,便不会有新的人来了,也不会有新的商业。
“但是,这里很适合你这样的穷小子,不是吗?受不了处在大都市里的恐慌,便想躲在这样偏僻的角落。”管理员一边说着,从抽屉里寻找一些文件。
主角说:“我对商业、繁荣和思想进步感到厌倦了,我只想在这里。”
“你以前生活在哪里?”管理员问。
“布鲁克林、纽约。我靠打零工生活,付不起房租。”
“为什么不回到你爸妈那里?他们会毒打你吗?”
“他们生活也不如意。”主角苦笑。
管理员迸发出一阵轻快的笑声:“我十八岁的时候,被父母强行赶出了家门,我只能在朋友仓库里的旧沙发上躺了一个星期,再出去找工作。”
“他们为什么赶走你?”
“赶走?”他笑道,“如果你是一个黑人,你会天然地将子女视作负担。”
“这可真糟糕。”
“糟糕?也许吧,生活迟早会击垮我们,也许我太主观了,别人家的孩子或许获得了幸福。”他若有所思地望着窗外的斜阳,仿佛回到了一个美好、从未发生过的从前。
“不管怎样。”管理员从文件夹里抽出一张纸。“十二楼的顶层公寓,朝南,两居室,最棒的位置。”
“这对我来说一定太贵了。”
管理员平淡地说:“房子的主人大概已经死了,他七年前来过这里,短暂地住过三个月,之后委托我将房子出租出去,可想而知,一直没有人来看房。电话几年前就占线了,没人来过或提起遗产继承与变卖的事情。他们大概已经忘记了这座城市。”
“所以,”管理员狡猾一笑,“我们可以假装他没有死,以极低的价格租给你。”
“那钱给谁呢?”
“当然暂时由我保管,除非哪天出来一个人要认领它。”管理员将厚实的手掌击在一起,“怎么样?四百美元一个月?”
“三百五十美元吧。”
“成交,你这个穷小子。我们只需要伪造一些签字。”
“您知道哪里可以找到工作么?”主角轻轻地问,“我身上的钱只能付不到三个月的房租。”
“我不清楚,你可以在人多的地方卖柠檬汁和热狗。”
“但这里没什么人。”
“没错,孩子。”他用黑色签字笔在表格上快速画过。
“不管怎样,我决定留在这里了。”主角对自己笑道。
三分钟后,管理员递给他一串铜钥匙,“去看看你的新家吧。”接着,他们用一场葬礼的时间乘坐电梯上到十二楼;走廊两边的门紧闭着,1205是最尽头的房间,管理员将钥匙插了进去,好像要将门撞破了才打开。
客厅里,沙发上的毛线球在光线下浮动着,在没有人的岁月里,阳光一直在造访这里。
斜阳照在管理员苍老的脸上,他望着阳台上两把白色的椅子,上面的灰尘在光柱下熠熠生辉。
“曾经的主人还住在这时,我们两个人有时坐在阳台上喝啤酒。”
“他是什么样的人。”主角问。
“推销员,干了一辈子的老实人,离过婚,有一个儿子。”
“他的儿子呢?”
“不知道,在某个地方吧。”
主角想起了列车上的老女人,他不禁设想推销员曾是她的丈夫,在离婚后,她把自己吃成了那样,他们有一个孩子,住在德克夏尔,尽管这之间绝不会有巧合。
“谢谢你。”主角淡淡一笑。
“好了,年轻人,我要下楼看书了。”说着,他推开房门。
“如今看书的人不多。”主角说。
“我看书,只为了避免忘却,这是对抗死亡的一种方式,尽管你无法阻止它……”
“你看的是什么书?”
“大卫·冈萨雷斯,一个不入流的西班牙裔诗人,你听说过吗?”
“我也写诗。”主角说。
“如果你写诗,你就要以诗人的身份面对这个世界。”说完,他合上了门。
主角靠在阳台上,黄昏将公园的草坪染成了暗金色,现在是四点十五分。
他冲洗了浴缸里的灰,放满热水躺了进去,看着天花板上的光——天使从上空掠过,他感到一阵困倦。
三
他从昏沉的噩梦中醒了过来。在梦里,他不断逃离阳光,而阳光无处不在,最后吞噬了他。他从浴缸站了起来,眼冒金星,摇晃地走到客厅,湿着身子,瘫倒在沙发上。
“差点要死了……”
他觉得这是离死亡最近的一次,这似乎没有道理,尤其是一切朝着美好的一面发展时。
他光着身子走入阳台上的晚霞,街对面的公园里出现了许多黑人,草地上传来杂乱的旋律。他听见了萨克斯管、架子鼓,好像淘气的孩子不听家长的话,胡乱弹酒店大堂的钢琴。毫无疑问,这些错落的声音融合在一起,是成立的。
“这是爵士乐么?”
曾经在布鲁克林时,身无分文的主角喜欢在街上闲逛;有时路过小酒馆会停下来,里面常有两三个音乐家,对着情侣们忘情吹奏。但是他与他们之间,隔了一层玻璃;他更钟爱那些隐蔽的废弃仓库:其中一面墙上印着哭泣的圣母玛利亚,有人用粉笔在她的怀里,画了一个火柴人,他有时站在那里一整个下午,直到无法抵御寒冷,回到他窄小的公寓里。
眼前的派对没有那层玻璃,尽管他会是人群中唯一的白人。他穿上最棒的衣服:一件买大了号的粉色衬衣、青色破洞牛仔裤、运动鞋,走下了楼。
草丛边没有围栏,没有售票处,他径直走了进去。一群高大的黑人女子在排队等待购买香肠,魁梧的身躯使主角想起希腊神话中丰满的裸体女神。她们的神态代表了爱、力量与嫉妒。她们随意交谈着,她们轻易爱上的糟糕男人有多么糟糕,她们为这些男人大打出手。她们的身体很美,又无比丑陋,因过多的酒精、炸肉与汽水而畸形。她们勇于展现畸形的乳房与屁股,好像那是一切爱的源头。
主角也闻到了香肠的味道,感到难以遏制的饥饿;他想起火车上的胖女人琳达,她会赶走所有黑人,一个人把所有香肠吞下去。他要了一大份炸薯条圈配香肠,以及一大杯柠檬水。
主角捧着食物,穿过了人群,仿佛朝着森林的中央走了一百年。他坐在草地上,屁股上传来潮湿的触感。
他的双眼突然模糊了,随后发现,这不是主观上的变化,而是世界在被红色的雨溶解。台上浮现出一个臃肿的女人,裹着红裙子,一个瘦弱的男人手持贝斯,他的两个伙伴负责架子鼓与小号。他们的职业大概是离异妇女、酒保、江湖骗子与无业游民。这里没有真正的音乐家,因为音乐无法养活自己,就像诗歌无法养活诗人。
为首的女人开始歌唱,对她而言,唱歌像说话一样容易。主角确信她说的是英文,可是却听不懂一个单词,或者说,那些音节本身就没有语义,但是他确信,那是有诗意的。台上的每个人,随性演奏着自己的作品,他们在讲述不同的故事:臃肿的女人献给不可能的爱情,贝斯手献给月夜下的孤独,鼓手献给在死亡中体验到的快感,小号献给了迷惑人心的技巧——它们完美融合在一起,没有规则,没有谱子,而一切是成立的。
一切都是美的,因此世上一切的丑也是成立的——苟且偷生的日子、巷子里的垃圾、永远不被承认的艺术。
主角抬起头,人群在欢呼,老头儿站了起来,女人发出高潮般的尖叫,胖子掀起衣服,冲了出去。他只得再低下头,掩盖自己的泪水,所有人在笑,只有他哭了。他为自己幸福的泪水感到羞愧。
一个遮着灰色帽衫的男人坐在了主角左边,过了很久,他开口道:“你知道这是什么音乐吗?”
主角未来得及回应,男人便自问自答道:
“这是融合爵士。”
“融合爵士。”主角默念了一遍。
“融合了世界上最好的东西,不是吗?”男人笑道。
“是啊。”
“我叫麦克。”说着他伸出白色的手。
主角也说出了自己的名字。
“我们是这里唯二的两个白人,不是吗?“
“呵呵,是啊。”主角笑道。
“你为什么来到这里?”麦克问。
“我今天刚搬过来,我只是在路上随意漂泊着,便找到了这里。”
“这样很好,不是吗?不受任何人的指引、不听从老人的话,不听从社会,只凭着内心的指引。”
“是啊。”
“不过说是那么回事,这里最大的好处是便宜,不是吗?”麦克咧嘴一笑,他看上去三十出头,脸上还有青春痘。
“是啊。这里很便宜。”他们相视一笑。
“所以某种程度上,我们都是因为钱来到这里的。”麦克说。
“不错。”
“告诉我,你之前是做什么的?”
“我写诗。”
“你写诗,在哪里写,写在纸上么。”
“对,写在纸上。”
“你把那些纸拿来卖钱?”
“我尝试过,可是它们的价值比厕纸还便宜。”
“你在街上读过诗么?你知道的,我有时候走在街上,会看见一些人读诗,有人往他们的帽子里扔铜板,或者买上一两本书。”
“我尝试过一次,可这让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傻逼。”
他们便乐得合不拢嘴。
“抱歉,伙计。”麦克拍了拍主角的肩。
“没事儿。”
“可以给我来一根香肠么。”他指了指草地上的餐盒。
“请便。”
“所以靠艺术无法生存,不是吗?”麦克嘟囔道。
“靠艺术可以成为富翁,但是你得会贩卖有钱人喜欢的东西,或者让中产阶级觉得自己在精神上也很富有。”
“我理解。”麦克自信地点头,他看上去不太理解。
“所以你打算在这里干什么?”
“先好好放松一下,房租不贵,之后再打算干什么,反正我要留在这里了。”
“你住哪儿,兄弟?”麦克问。
主角指着身后的天空,他温馨的公寓被晚霞染成了暗红色。
“哇,真不错,晚上可以去你阳台上喝啤酒吗?”
“当然可以。”
“真不错。”他又说了一遍。
“那你是做什么的?”主角问道。
“我?”麦克得意地一笑,“我什么也不做。”
“什么也不做。”主角也重复了一遍,他们相视一笑。
“嗯,说实话吧,我告诉你一个秘密。”麦克凑到他耳边。
“你说吧。”
“你保证不会告诉别人?”
“这儿没有别人。”
“其实我是骗取养老金的。”麦克神色诡异看着他,好像说出了天大的秘密。
“骗取养老金?”
“对。”麦克组织着语言说道,“事实上,我的母亲已经死了,但是我还在偷偷领她的养老金,没有人发现。”
“那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所以我现在活得很轻松,我搬到这个地方,不会引起注意,他们发现不了。”他捂着嘴巴,用电视上联邦探员的语气说道。
主角用塑料杯里的柠檬水,碰了下他的啤酒瓶,“敬你死去的母亲。”
“敬我死去的母亲。”他说。
“我应该拿这笔钱,不是么,否则的话,这些钱就白白进入资本家口袋了。”
“一点也不错。”主角回应道,事实上,他不在乎这件事的善恶,仅仅出于友谊,表达对同伴的认同。
“你母亲的尸体在哪里?”
“她在弗吉尼亚海滩的一座白房子里,安静地躺在摇椅上。”
“邻居们没有发现么?”
“她不喜欢活在人群中,没有人打扰她。”
“真是幸福的死法。”
“幸福的死法。”麦克同意道。
“你有去看过她么?”主角问。
“没有,她不喜欢被打扰。”麦克说。
“你写什么样的诗?”麦克问。
“什么样的诗?”主角仰望着不透明的天空,此刻它与数光年之外某个星球上的晚霞是一样的。
过了十秒钟,他缓缓说道:“真实的诗。”
“真实的诗是什么?”
“任何我们内心触摸得到,又被他人忽视的存在。”
“比如现在。”他温和地看着麦克。
空酒瓶子被丢在草坪上,音乐在进行着。
“你会成为伟大的诗人。”麦克伸出抓过香肠的手,拥抱了他。显然麦克对诗一无所知,但这是他一生中听过的最有力量的赞扬。
主角露出童年留下的不整齐牙齿,笑道:“谢谢你。”
第二首歌开始了。
“朋友们,让我们有请失真迪斯科舞会。”
烟雾中出现了一个年轻女人,她的翘屁股对着观众;后面是一个戴着眼镜的矮子,操纵着一台布满电线的合成器,通过他贝雷帽下深沉的鼻梁,你可以得知,他将生命献给了音乐,未得到母亲的理解。
翘屁股女人右耳朵上挂着一个新月耳环,好像今晚的月亮就在这里。她拿起话筒,开始歌唱。
我每一份工作不会超过三个月
我在麦当劳里拿最低的薪水
我经常请假
或者宿醉翘班
我喜欢偷喝草莓奶昔
尽管每个在里面干活的人明白
天知道那是什么垃圾制成的
但是甜蜜的味道
没有任何人能抗拒
不是么?
她一定是世界上最懒惰的歌手,她的每一个音节都懒得发完全,被下句话吞下去;像她的人生一样,永远追求短暂的快乐,从不去抵抗。她轻快的舞步在粉红色的光下变幻,戴眼镜的矮子十分沉醉,闻得见每一个音符的气味,传递出粗糙的钢琴声、贝斯及古怪的铃铛声。
女人朝观众扭动屁股,耳环随之摇曳,所有的爱聚合在她的月亮上。她接着唱道:
我喜欢与顾客调情
他们大多肥胖,令人
厌恶的黑鬼与白鬼
偶尔出现一个
健壮、温柔的男孩
开着偷来的克尔维特跑车
来购买薯条
我便放下眼前的一切
随他而去
直到一切破灭
我回到我的沙发上
寻找下一份
奴隶的差事
她的红唇通过歌声施了一个咒语,使天空定格成粉红色,久久不能褪去。
许多肥胖的男人站起来,为她欢呼,麦克也站起来,以白人的方式喊叫着。之后,舞会变得越加混乱,空气中弥漫着甜味,不知混合了什么的饮料杯子,被传了过来,每个人都毫不犹豫地喝下去——黑人的口水混合着白人的,老人的混合着孩子的,病人的混合着健康的人的。
主角平缓地坐在草地上,麦克在前面撒野,他撞到了别人,被人踹了一脚。他揉着屁股回到主角身边。
“这帮疯子。”他骂道。
“你喜欢黑人么?”主角问道。
“喜欢黑人?”
“对。”
麦克以飞快的语速说道:“没有人喜欢别人,我们讨厌每一个人,因为他们占用了我们的空间,占用了我们的自由。但是……”
“但是?”主角纯真地望着他。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傻逼。”
“所有人都是傻逼。”他强调了一遍。
接着他朝天空大喊着,“所有人都是傻瓜。”拖动笨拙的大腿,冲向了啤酒吧。
主角注视着奔跑的麦克,没有批判任何一件事情——自己渺小可怜的人生,拥有杀人犯目光的酗酒列车员,肥胖、痛苦、垂死的种族主义者琳达,梦游的门卫,阅读诗歌却要压榨他的公寓管理员,靠着母亲的幽灵过活的麦克。我们为什么活着?美国究竟是什么?这些问题在酒精的催化下,使他的大脑爆炸。
这些问题显然没有清晰答案。从此以后,我们的主角可以深信一点,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存在于诗歌与音乐,与驱使它们前进的爱中。他拥有过它们,并且从此以后一直有。
漫长的夜晚刚刚开始,更疯狂、混乱的爵士乐在人群中爆发,主角拖着麦克沉重的身躯,回到他位于幸福公寓十二层的房间,他们站在阳台上,继续目睹人们的堕落。麦克将马尿色的啤酒灌入喉咙,开始发表他的政治观点——所有政客都是华尔街的走狗(显而易见),美国被狠狠操了一下,他仍然不相信犹太人,他可以与性感的黑女人上床。他说起了童年:很早便开着货车逃离的父亲、独自抚养他的母亲、他最爱吃的苹果派。夜深了,天上的星星躲在城市的幻光后,继续偷听他们的故事。到最后,麦克昏倒在脏兮兮的沙发上,主角躺在被单的螨虫上。
第二天下午,主角睁开了眼睛,感到口干舌燥,从水龙头接了一大口水,昨晚他做了梦,大概对过去二十六年的人生做了总结,醒来时又好似没发生过。他走到客厅,麦克倒在沙发上,阳光钻进了他牛仔裤下的屁股缝。
现在是四点十三分。主角来到阳台上,草地上还留着昨夜狂欢后的狼藉,他望着粉蓝色的天空,写完了一首诗,并朗读了它:
一个午后
如柏拉图说
“让哲学家统治”
最好的哲学家是诗人
一个伟大诗人
精通修辞学
终于在八十岁
入住白宫
他坐在总统办公椅上
望着阳台外的小花园
感到一阵哆嗦
热血从内脏涌出来
像他年轻时那样兴奋
世界
就在你的手心
一个无人的
午后
我走进白宫
坐在他的椅子上
水蜜桃般的
女秘书
在抽屉下
舔食我的阳具
口水浸入方糖
将爱融化
我打开阳台的门
播放一张
迪斯科唱片
好像
地球上
所有人
从浑噩的阳光中
睁开眼睛
听懂了
它的声音
属于
人类的午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