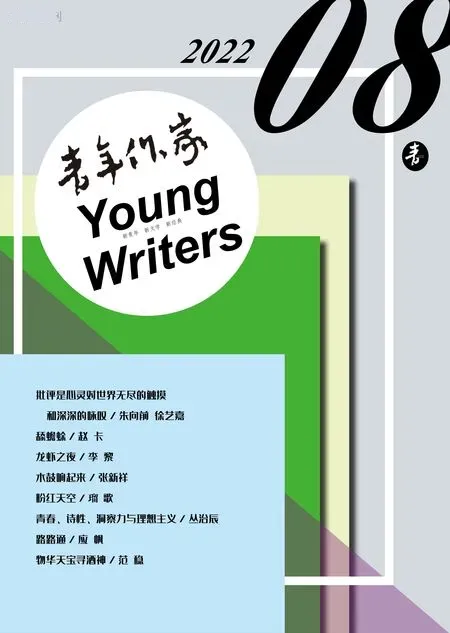小说观 文本有它自我的想象方式
赵卡
一篇需要解释的小说或许不是什么好小说,至少对建立作者的世俗声誉来说没多大用处,所以,我这篇小文不是解释这篇小说的,我也不打算多解释。
这篇小说用了一个“舔蟾蜍”的名,我不确定我是否在揶揄人类的理性,反正我想在绝大多数人的脑补画面里,想不恶心都难。我一开始也有这种感觉,平生第一次感到有些文字竟会如此引起人的糟糕生理反应,如果文字在纸上有知,估计悔恨自己被发明出来。但请注意,“舔蟾蜍”有一种奇特的聚焦作用,它灼伤既不是地狱也不是天堂,而是读者的眼球(开个玩笑)。
我平时写小说,不缺乏散性思维,也不缺文体意识,但缺整体性思维,缺结构意识,往往脑子里有了一个念头后就可以动笔了,没有规划,信马由缰,想到哪就写到哪。这块儿的气质有点像谁呢?像写《万里长城建造时》的卡夫卡,首先得有个“方式”或“内容”的发现,也就是说,我这个小说的内容建构方式用我的一种独特视角去完成的,文本有它自我的想象方式。
表面上看,《舔蟾蜍》像个寓言,窥测另一端世界的秘密,因为在叙事的展开上作者似乎想搞出一个深刻的洞察,或者是象征主义,其实这就是个障眼法。作者真正的意图——我这么说吧,我写的是一个小说的语言装置作品(梅洛庞蒂意义上的“一种语言能够指示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东西”)。这个说法对别人来说可能无所谓,但对我的读者朋友来说应该多少有点耸人听闻。
那什么是小说的语言装置作品呢?我个人的理解很简单,不外乎一个观念性的作品,就是将(爱伦·坡意义上的)细心设计出效果的词语释放出来,这是词语的世俗性荣誉;当然,我已经注意到了,就像我们现在再读十九世纪的那些老派作品时,还是有点不得劲儿。
这篇小说的内容我就不在这里说了。前段时间,爱奇艺的一个项目小组讨论我的一个长篇小说时,谈到我小说的特点:奇观+公路。这个我还真没考虑到,但被他们总结出来了,感觉就是。至少你们会看到,我在这篇小说里还仿雷平阳的一首诗《澜沧江在云南兰坪县境内的三十三条支流》写了一段呢。
对了,我需要说明一下,这篇小说的灵感来自公路商店公众号上一篇猎奇性质的文章,标题我忘了,那篇文章说,在澳大利亚某地,有一种叫甘蔗蟾蜍的动物,像一只行走的致幻剂,喜欢什么东西都要舔一舔的狗子,误舔了它以后,会神情呆滞、四蹄朝天… …我就此设置了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