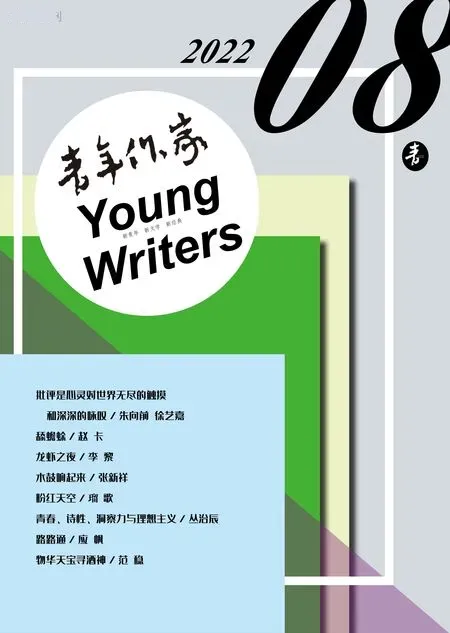谈炯程
2022-05-26 12:05:58
青年作家 2022年8期
琵琶湖
勾芡着一叶蛛丝的坡度等级,蚂蚁
窥见放大镜下的山脉,如焯水的鱼骨般
展开。湖面,用骨瓷式的莲叶告诉我
塘鹅的逗点曾拨响那簇倒影。“入夏的
树,搁浅于琴盒的抹香鲸,他们凿开
唇上结痂的海水,进去。”在我的暗室,
牛奶从未将那个手势冲洗:太规整,
以致冰箱中的偷渡客正变成务虚的牙膏……
然而,树荫下环卫工人铲平光的
味蕾。太迟钝,但夜晚会在一块冰里留下
它的蝉蜕。于是风退潮,露出街灯的
龋齿,寄居蟹迁进这团濡湿的像素。我的
一生被这堵坍塌的空气归纳:“偶尔泡在
生意里,用拔了牙的老虎机践行阶级。”
恐龙园,2008年
车载广播里皱巴巴的噪音是一截病号服
滚动着。他尚未冲制这夏日茂盛的
苦意,滋生于墨镜的游乐场;旋转木马
与摩天轮如锡纸的外焰皱成几粒缩写。
那年表哥刚学会抽烟,打方向盘时,
就像一台宿醉的滚筒洗衣机。穿过省道,
平原豁开的拉链敛迹于后视镜,松树
正结出毛球,在你唇的锈色上他触到生活
如跨过禁飞区触到恐龙的尾椎骨。
“我熟悉你,八音盒里一腋斑白的蘑菇,
带我去到市区,拉环式的聚落摇曳沿途;
当然,你诚如开水壶内胆那般禁欲,
碎裂时渣土路正化作那枚扃闭的石榴……
被铺开,茎生的旅游业,红砖间浆着枿芽。”
猜你喜欢
作文小学高年级(2022年5期)2022-06-16 06:22:42
小星星·阅读100分(低年级)(2018年7期)2018-09-04 03:16:36
婚姻与家庭·性情读本(2017年9期)2017-09-21 21:32:58
小康(2017年19期)2017-07-07 16:58:54
娃娃乐园·综合智能(2017年5期)2017-06-15 20:29:23
学苑创造·A版(2016年1期)2016-03-10 18:16:35
中华手工(2014年11期)2014-12-03 03:55:20
汉语世界(2014年6期)2014-02-27 11:56: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