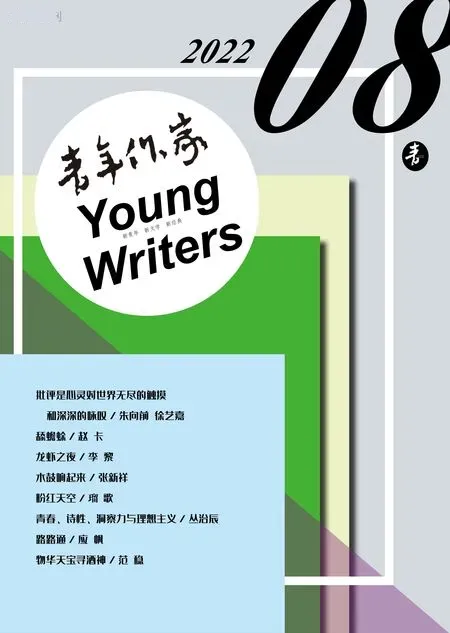老兵遁走山林
高满航
我不得不交出半张白卷,内心悲壮如即将开启多舛的命运之门。
那是新兵训练结束后的第一次选拔考试,如果成绩优异,我就能如愿成为发射营的兵。带我们的班长经常讲,你们要真有本事,就考到发射营去打导弹,打得好就能立功,提干指标也多,考军校还有加分政策。
当兵前,我是一所非985和211大学的大三学生。家里忧虑我毕业后的出路,听取曾在部队当过营长的舅舅建议,让我从所在大学报名入伍,到部队当兵去。我之所以同意,并不是受了他们说的退伍回校后有国家资助学费、研究生考试加分等等看得见的好处诱惑,而是打心底里对一成不变的大学生活厌倦透顶,决定顺水推舟,离开学校换个活法。
刚到新兵连那会儿,我觉得带我们的下士班长威风得很,打定主意将来像他那样转士官。后来见了排长连长和营长,就又立志成为军官。
听到选拔考试消息时,我认作机会,摩拳擦掌欲作一搏。遗憾的是,那些机会都归了我同批新兵里那些貌不惊人却出类拔萃的学有所成者。
那年十二月底,我不得不去导弹旅最东北角的哨所报到。
山里刚下了一场大雪,到处白茫茫一片。风从宽阔的河道滚来,一阵又一阵,卷起冰冷的雪片抽打在我脸上。我无处躲藏,面冷如心,扛着背囊,拎着行军包,垂头丧气跟在警卫营文书身后。走到一处岔路口,风又来,雪也起,他在风雪中抬手指着通往山里的方向,说他还有紧急的事要提前回去,让我顺着山脚一直往前走,无路可走时就能看到哨所。他已走出十几米,又转身大喊着让我到了给他说一声。我还没来得及问怎么给他说,他就转过山的拐角不见了踪影,只留下雪地上一串脚印。
我不得不独自去哨所。
藏在雪下的山路可真不好走。左边是长满杂木枯枝的陡峭山坡,稍不留神就戳到头,右边是被山洪冲毁护堤的河道,时时得提防着不滑下去。冰冻的河面看似平静,冰层下的流水却哗哗作响,听得人心里发毛。
我一边谨慎踩着脚下的路,又不得不时时朝山上张望。
我在新兵连听那些待过哨所的班长讲,走山路遇到野猪是常有的事。他们还说,那些膘肥体壮的野猪寻仇似的,专在隐蔽处等落单的官兵袭击。他们给我比画见过的野猪有一搂粗的脖子、一尺长的拱嘴,冲着人来时哼哼叫着,就像射过来啸叫着的炮弹。班长们还说,山林里动物的战斗力排名顺序是一猪二熊三豹子,野猪能把胳膊粗的树一口咬断,更不要说咬人了。班长们的本事倒是一点儿也不比野猪差,他们都完美躲过了野猪袭击,有的是爬到树上,有的是跳进河里,还有的是躺平装死。
我愈加强烈的恐惧不只是遇上野猪,更是弄不清到底哪种方法管用。
行走在寒冷的冰天雪地里,我很快就大汗淋漓,全身湿透。
我的脚疼到即将麻木。前面没了路,果真就看到了哨所。
我毕生难忘那一抬头所见的情景。
二十几个兵在哨所门口分两排站立,军犬也在队列尾部蹲得笔直。我踏上乱石拼铺的台阶时,就已看见了他们喷薄而发的激动。我刚站上哨所前的水泥广场,掌声就哗哗响起,我心头一热,眼泪止不住涌出来。
我站上广场的同时,朦胧看见老兵昂首走出哨所大门。
整齐列队的哨所官兵不是欢迎我,而是欢送老兵。
老兵神情肃穆,眼含热泪,他情深意切地和每个人握手、拥抱。他们说等他回来,他也答应他们一定回来。老兵最后也和我握了手,并且和我拥抱。他的脸上绽出笑来,夸我能来哨所了不起,让我也等他回来。
老兵向大家挥手告别后,背着他的背囊向山下走去。
我喊住老兵,让他小心野猪。那一刻,我就如同把充斥大脑的恐惧传递给了老兵。他却没有丝毫紧张,只是冲我咧嘴一笑,然后潇洒而去。
我后来才知道,我对老兵的提醒完全多余。
老兵是刚卸任的代理哨长,他那天是去哨所的上级单位警卫营报到。
关于老兵的更多故事,我是后来断断续续听哨所的战友们讲的。他们说,老兵就像钟情自己的初恋一样热爱哨所巡守的三十里山林。他们说他的身手比山林里的猕猴更加矫健,他的嗅觉比德国血统的军犬更加灵敏。他们还说老兵曾徒手擒获一头偷袭他的野猪,不过他倒没有伤害它,而是放归山林。老兵就像对待自己的家人一样宠爱山林里的飞禽和走兽。哨所每一个战友都无数次对我讲,与其说老兵是哨所的兵王,莫若说,他天生就是哨所巡守的三十里山林禁区的一部分。在这三十里山林,他是太阳,是月亮,也是风和雨,是白天的雄鹰和晚上的猫头鹰。
我不理解他们的比喻,更疑惑天生属于山林的老兵为何离开哨所?
他们说,老兵不会离开哨所。他们还说这些年里,老兵固守哨所的信念从来都是坚若磐石。他通过了发射营选拔考试,却没去报到。他军事比武拿了多个第一,却放弃提干培训。他符合预考军校的苗子班条件,也是一次没去。老兵坚守哨所七年,从列兵到中士代理哨长,继续前进的道路却不通了。哨长是排长编制,要么少尉或者中尉军官担任,要么士官代理,但哨所的士官编制最高到中士,老兵明年就中士届满,再没法留下来。老兵倒是符合士兵提干的所有条件,所以他不得不踩着二十五岁的年龄门槛,晋升培训后转换士兵身份为军官,然后再回山林来。
哨所的每名士兵都知道,老兵一年后就会归来。那时,老兵将从中士代理哨长成为名正言顺的少尉哨长,又和以前一样,携枪带犬巡守山林。
谁也没想到,才过半年,老兵就回来了。
老兵没带任何行李,同他一起回来的还有旅里的保卫科长。
那天,哨所每个人都忧心忡忡,只有我不清楚发生了什么。我又一次见到老兵格外兴奋,向他问好时,看到他脸上绽出笑容。我问他是不是已经成为少尉军官,这次回来就再不走了。老兵点头说不走了。保卫科长满脸愁容,我听见了他一根接一根抽烟间隙里的沉重叹息。除此之外,他还一遍遍重复地问老兵:“你怎么可以这样,你不应该这样呀?”
老兵更多的时候并不答话,只是陷在心事重重的沉默里。
老兵向接替他的代理哨长借值班哨一用,说要到山林里走一遭。保卫科长警觉起来,他让代理哨长跟老兵一起去,老兵却点了我。他说我是哨所唯一没跟他巡守过山林的兵。保卫科长显得为难,但还是答应了。
老兵得到应允后,欢快地将哨子衔在唇间。他冲出哨所院外的篱笆门后,一个大跨步就轻松越过河道,然后敏捷地攀上陡峭山坡。我气喘吁吁跟在他身后,不知道他要去哪里,也不清楚保卫科长给我使的眼色是什么意思。老兵冲上山脊后,倒是慢下来,他衔在唇间的哨子却响个不停。他长吹一声说,这是找你,短促吹两声说,这是有危险,悠扬吹三声说,这是平安无事。他问我记住没有,我点头说记住了。为了让他相信我的记忆力,我又复述了一遍。老兵高兴极了,欢快地向着山脊更远处跑去,他在中途停下,转过身来向我挥手,夸我能来哨所了不起。老兵再转过身去后,就迅即隐于密林,没了踪影。我沿着他奔跑的方向追去,却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见。他就像是一阵风,从无处归于无处。
我正犹豫要不要独自回去,这时,在弧形山脊的另一头,传来三声悠扬的哨声,紧接着,在山脊弧顶的树上和山脚的泄洪河沟,同样传来三声哨响。我确定了老兵还在山林,他并没有走远。我独自返回哨所。
老兵到晚上也没有回来。保卫科长一根接一根抽烟,不断重复说:“想尽办法,必须找到。”上山去寻老兵的战友陆续归队,他们没能发现关于老兵的任何一点线索。每个人都替老兵忧虑,他们怀疑老兵坠入山崖,遇到猛兽,或者迷了路,但这些臆测又被提出者之外的其他人推翻。
哨兵失踪是哨所几十年从没有过的事,现在却发生了。
每个人都眉头紧锁,哨所持续发酵着关于老兵去向的种种推测。
保卫科长又抽完一包烟后,小心翼翼给上级打了几通电话,然后在哨所住下。他也带着士兵和军犬上山寻过几次,同样没有任何结果。他回来后倒是再没说必须找到的话,却愁眉不展,又开始一根接一根抽烟。
有士兵窃窃私语讨论,听说老兵大概是在警卫营犯了严重错误。我也是那时才知道,老兵已经办理完退伍手续,这次回来本是和哨所战友作最后的告别。有战友推测,老兵是不服从组织对他的处理决定才以隐身山林作为抗争,也有一种说法,老兵是在兑现之前对于某个人的诺言。
没人知道某个人是谁。也没人知道诺言的内容。
时间一天天消融于日月的光芒。久不见老兵,有战友推测他有可能穿过山林回了老家,也或者去了其他地方,重新开始退伍后的崭新生活。
各显神通的战友们在山林那些必经之处拉上细线、撒上排列整齐的米粒,或者布设标记号码的纸质粘板。他们希望获得老兵的踪迹,但一切的精心设计都未见成效。老兵踪迹全无。大家认定老兵早已离开山林。
保卫科长离开后又很快回来。他已不信任我们哨所的军犬,不知从什么地方带来八条军犬和八个驯犬员。保卫科长和他的队伍午饭后上山,到晚上才回来。他们筋疲力尽,垂头丧气,仍旧没有找到老兵。又过了几天,保卫科长带来一架装有微型摄像头的小型无人飞机。无人飞机一次次飞走,又一次次飞回,却连老兵的半个影子都没有拍到。保卫科长终于认定老兵已经离开山林。他在哨所给上级打电话时也是这么说的。
我最清楚他们做出了错误判断。
每天早上的起床号前和熄灯号后,我都能听见三声悠扬的哨响。有时在山巅,有时在河沟,有时就近在哨所门前广场的台阶下。我知道老兵游走在哨声响起之处。我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对老兵的行踪秘而不宣。
直到有一天我正站哨,接连几次听到一声长长的哨音。我下哨后循着哨声,在我们上次分别的地方找到老兵。老兵虚弱地靠着一棵树皮已经斑驳脱落的老树,一只腿蜷着。他见我来,脸上绽出灿烂笑容。他小腿胫骨处受了伤,虽用揉烂的刺蓟敷裹,却不断渗血。我跑回哨所拿药时,代理哨长不但准备好了止血药,还有纱布、酒精、雨衣、蚊帐和衣服。老兵只收下了止血药。他笑着和我告别后,一瘸一拐地走向密林深处。
哨所战友都知道老兵游走在山林。我们谁也不说,就像每个人都密密实实地捂着一个人尽皆知的秘密。我们有时觉得老兵就在哨所,事实上他一次也没有回来过。我们不知道他怎么吃饭、怎么喝水、怎么睡觉,大雨之夜何处避雨,烈日之昼哪里避荫。我也不知道他的腿伤是否痊愈。我确定的是老兵还在山林。三声悠扬哨响一早一晚准时传来,有时很近,近在眼前,有时很远,远在天边。哨所寂静,我每次都听得一清二楚。
老兵隐身山林,断绝了和我们的联系,但我们忍不住又常提起他。一班长说起老兵训哭他的事时,又哭了。我之前听说,误哨事件后,他脱胎换骨像完全变了个人。二班的贾大壮打小怕狗,因为军犬在,他几次闹着要离开哨所。贾大壮从没透露老兵教他和军犬相处的绝招是什么。他动不动就搂着军犬问:“想老哨长不?”我们知道是他想老哨长。不止他,我们都想。老兵似乎一点也不想我们这些想他的兄弟。我更想不通,老兵已经办完退伍手续,他为什么不远走高飞,而是游走于三十里山林?
老兵成了哨所待解开谜底的谜面。因为他,我们巡守禁区时不再走固定路线,有时穿越嶙峋乱石,有时钻过密布藤蔓,也有时从山巅直插河沟,却仍旧没发现他在山林里的蛛丝马迹。就在不抱希望时,我们循着他的哨音扑灭了一起山火,抓住一个形迹可疑的闯入者。慢慢的,我们习惯了一早一晚的三声悠扬哨响,也期待揭晓藏在他身上的无尽秘密。
接替老兵的代理哨长考取了军校。他在我们为他举办的欢送会上尽力克制着情绪。他回忆了和我们每个人相处的点滴往事,也谈到自己这几年的成长进步,最后提到要感谢的人时却号啕大哭。他哽咽得几乎说不出话,但我们都知道他最感谢老兵。老兵治愈了他的自大和自卑。代理哨长的大哭也引燃了我们的悲伤。我们在夏天的空调房里不知道老兵如何对抗酷暑,在冬天的暖气室里不知道老兵如何忍受严寒,他怎么洗澡、怎么刮胡子、怎么剪指甲、有没有换洗衣服?我脑中的老兵浑似一条被水浇过的苍老瘦狗。他虽然直挺挺站立,却随时有可能一倒不起。
我们巡守禁区时,在老兵受了腿伤的地方放下压缩饼干、简易帐篷、薄厚衣服和能够简单处理外伤的纱布、药物。我们再次经过时,偶尔会发现少了一些纱布和药物,那些饼干、帐篷和衣服却原封不动。
老兵隐身山林半年之后的年底,与他同年入伍的一班长即将退伍。一班长坚持和老兵告别。他穿着卸了军衔的军装面向山林。一班长大喊老兵的名字,没有应答。他一张张拿起和老兵的合影,说起以前的往事。他说完一张,新任哨长就给他换一张。他呼唤老兵应为每件事大醉一回。情深意重的一班长被前尘往事感动得哽咽不能言,山林里却没有一丝回应。一班长伤心得瘫坐在地上,我们扶他回哨所,所有人一路走一路哭。
一班长走后一年,三班长也退伍,紧接着就是二班长。时间就像滴落在流水里的墨汁,瞬间便踪迹全无。哨所每年都有情同手足的战友陆续离开,也有新兵源源不断补入。待我无人可喊班长时,才发现自己成了哨所最老的兵。这些年里,我再没参加发射营的选拔考试,退出了旅里军校苗子班的预选,也放弃去士官学校进修。我拒绝所有改变命运的机会,心甘情愿坚守高山哨所,似乎就是为了解开老兵这个谜面的谜底。
无所不能的老兵,笑容暖人的老兵,他何以错失了提干而突然退伍?他又为何年复一年隐身山林?我这些年见人就问是否认识老兵,又不遗余力在认识他的人里打探关于他的一切。有一年,来哨所维修电缆的上士技师在我送他一对山核桃后告诉我,老兵重返哨所前一晚喝了很多酒,对同饮的营部文书说了很多话,营部文书应该知道我想了解老兵的秘密。我高兴极了,以为一切都将有答案,并且知道技师所说的文书正是当年送我到哨所山口之人。可是自那之后,我再打探不到文书的任何消息。他退伍多年,没人知道在什么地方,也打听不到任何联系方式。
每当新闻上播报世界各地的间谍案件,哨所的战友都会自信满满地说,连我们自己人都不知道消失的老兵隐身何处,哪个外人又敢擅入三十里山林?也有人说,外国间谍早就谋划从三十里山林进入我们的导弹旅禁区,老兵是领受了上级布置的秘密任务才潜伏山林,只等抓谍立功。
不管真相是什么,我都相信老兵不会有错。
八年后,我中士第三年。也到了士兵在哨所服役的最高年限。
加之我的所有过往就像一场半睡半醒的梦,我常在梦里委屈得泪流满面。老兵一去不回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他出走山林席卷了我的整个军旅生涯?我遇老兵时是哨所最新的兵,和他只不过相见三面。
四季轮回里的风霜雨雪更新着三十里山林,一切如故,一切又都是新的。我的头发被山风吹掉了大半,容颜苍老。我的腿巡山时被落石砸断,皮肉虽痊愈,骨头却落下残疾。严重的颈椎变形让我整日头昏脑涨心烦意乱。我厌倦日复一日重复巡守山林,我极度渴望换一种新的活法。
可是老兵呢?我常记不起他的容貌,不得不到哨所的荣誉室里紧盯着他的戎装照片,才能在脑中缓慢还原那个脸上绽着笑容的陌生故人。老兵一年又一年就像山林里的野兽一般独自生存,却又没有野兽那样强壮的身体。我有时残忍地想,老兵是不是早已暴死山林。哨声依旧一早一晚响起,他还活着吗?我有时宁可相信哨音是我头昏脑涨产生的幻觉。我自己和自己掐架,激烈争论老兵的生死。他在我半睡时死去,又在我半醒时活了过来。我不知道哪一个我是对的,也不确定他是死还是活。
我长久地痴望山林自言自语,才不到三十岁的年纪,却颓丧得像个病入膏肓的老人。新到任的中尉哨长温和地劝我最好不要夜晚独自上山。我惊讶地望着他,知道他知道我半夜梦游。他维护着一个哨所老兵最后的尊严,并没有那样说。哨所没有梦游者,或许每个人都有梦游的夜晚,但没有人说别人梦游。我也闹不清那是白天还是黑夜,睡去还是醒来。我还不到三十岁,耳朵灵敏,在月光击打玻璃的嘈杂声中捕捉到那一声长长的哨音。我知道老兵找我。我披衣起床,循着哨音步入山林。我在老兵受伤的地方看到一个黑影,我走近,黑影却跑开。那黑影就像另一个我,我动他也动,我停他也停。我知道我是我,黑影是黑影,那是老兵在我面前的投射。我急于知道他长久隐身山林的谜底,更想劝他走出山林。我还像八年前那样称他哨长,我说:“不管您在这里坚守什么,都已经太久了,离开吧,您还没有老到埋骨山林。我和您当年一样,现在是哨所最老的兵,我来接替您吧,您去重新开启自己的生活。”黑影定在那里一动不动。我继续说:“放心吧,您能做到的,我都能做到。”我说出这些话的同时就后悔了。我只想劝服老兵,他在这片山林待得太久了,也到了该离开的时候。我也不再年轻,即将卸下军衔失去军人的身份。
我没动。黑影动了。
我看见老兵走近我。他苍老的脸上绽出欢快的笑容。
我没想到老兵会相向而来,更没想到他同意了我的建议。我站在丛林之中,看到老兵向着哨所的方向走去,他跨过河沟到了哨所门前的广场,哨兵没有发觉,军犬也没有吠叫。老兵朝着哨所敬了个军礼。他下了台阶走向唯一的出山小道。我看见他在月光的照耀下越走越远,直到踪影全无。我突然沉陷在无边无际的绝望里。我即将三十岁了,到了中士第三年,我马上就要退伍离开哨所,开始新的生活。我在山林里狂奔,我相信老兵只是出现在我的梦里。我故意撞向树干和石头,我知道梦里没有疼痛。就算明知是在梦里,我也急于收回我对老兵说过的每一句话。
新任的中尉哨长默默地给我拿来了治疗外伤的药物,又一次劝我最好不要夜晚独自上山。嘹亮的起床号响起,我却没有在此之前听到悠扬的三声哨响,我在漫长的白昼里急躁等待,夜晚降临,熄灯的军号声止住后,我仍没有等到悠扬的三声哨响。老兵走了。我冲出哨所,站在广场望向山林。风止林静,月光如洒,就像万千将士屏息等待我的统领。
老兵走后,再没人见过他,就连曾经随风飘荡的关于他的传说也踪迹全无。老兵在哨所荣誉室留下一张戎装照片,那是他真实存在的见证。
我患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夜不能寐,昼则浑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