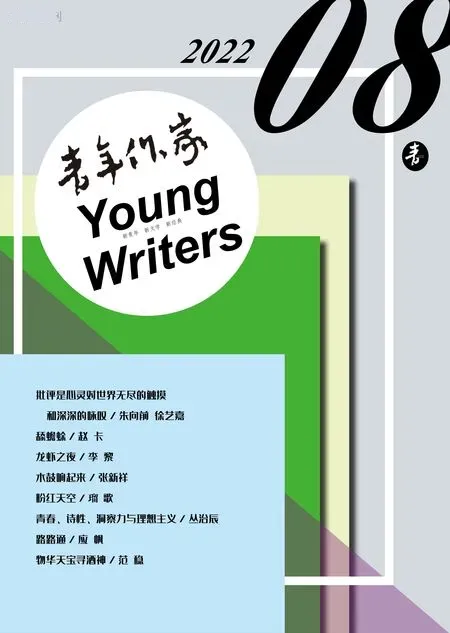半个月亮升上来
黄金
当王亮决定要回去一趟后,已不犹豫、不担心,但情绪仍像波浪一样,起伏不定。他和山梅说了想回老家一趟之后,在不到十天的时间里,山梅已经不止十次问,你还会回来吗?他笑着说,你在这里,我怎么会不回来?他看着山梅,山梅老了,头上有了不少白发,两鬓尤其严重,其实她才刚四十岁,生活艰苦,她已经成了小老太,他知道自己也不显年轻,又黑又瘦,这段时间不刮胡子、不剪头发,整个人和她比起来,也成了小老头。他身份证上的年龄是三十八岁,比她小两岁,只有他自己知道,他的实际年龄是三十二岁。离开故乡整整十五年了,这期间他无数次怀念故乡、思念父母,但从不敢动回去一趟的念头。
其实当决定以后,他可以立即动身了的,但他迟迟没有动身,一天又一天,他想尽量和山梅再待一待,他自己也不知道,这一趟回去,他人生的终点最终会停在哪里。他已经犹豫好几年了,最终下定决心回去一趟,哪怕是远远看上父母一眼,哪怕只为亲近故乡一次。
第十五天,他决定动身,再不动身,怕是来不及了——特别是父亲,恐怕现在回去,都已经阴阳两隔了。
山梅默默地为他准备东西,腊肉、腊肠、糯米,腌好的咸蛋……他什么都不带,就带几件换洗衣物。山梅说,这么多年没有回去,不带点东西怎么成?他笑着说,路途远,带这些东西不方便,我回到老家县城买点礼物就成了。山梅让他多带点钱,他只拿了三千,家里有现金七八千,存折上也有点,山梅让他多带一点,回去给父母多买点礼物,他坚持只拿三千,说三千足够了,不能回去探亲一次,就把家里的钱都花了。
天刚蒙蒙亮,王亮出发了,汉威开摩托车送他到乡里,从平瑶屯到乡里有二十七公里。以前他刚到平瑶的时候,这里还没有通公路,他是走山路来的。现在通了乡村公路,虽然路面不宽,弯多坡陡,但铺了水泥,还算好走。汉威开车挺快,路小弯急,他提醒说慢点慢点,注意安全!汉威说知道,油门却继续拧大。年轻人开车都快,这条路就通到平瑶屯,平日里路上走的车很少,现在是清晨,路上没有见到什么车——不过也有出事的,前年寨子里的一个年轻人,开摩托车过弯的时候开得过快,迎面撞上拉木料的后推车,当场死亡。他刚到平瑶屯的时候,汉威不到五岁,现在二十出头了,身材瘦小,和他父亲老盘一样,初中毕业后去城市打过工,后来回来了,后来又出去了,又回来了,到城市里混不容易,哪那么容易扎根。
到乡里等车的时候,汉威掏出烟来递给他一根,他摆手,说不抽了,这段时间老咳。汉威自己抽,点燃后深吸了一口,缓缓吐出来,说叔,你这次回去,还回来吗?他微笑着看他。汉威犹豫了一会儿说,我爹不在了,你可以给我当爹吗……双眼直勾勾看着他。他感动,鼻子一酸。这么多年,他对汉威一直小心翼翼,他不知道最终老盘知不知道他和山梅的关系,也不知道到现在汉威知不知道他和他母亲的关系。他说,等我回来,好吗?他每次和山梅发生关系,都是在上山劳动的时候,都是在太阳最大躲到树荫底下休息的时候,而且每次时间都尽量快,完事后马上分开,就算偶尔有人来到他们劳动的山地边,看到的都是山梅和他保持着距离——不管是休息还是劳动,他们都保持着距离。他知道寨子里不少人对他持有质疑的眼神,他一有机会就一再和人们说,他老家穷,全是石山,土地很少,生活艰难,他出来就是想找一个山地多土地肥沃的地方落脚,他不求回报,只要有饭吃有地方栖身就成,当然如果能遇到想招婿上门愿意招他为上门女婿的,那是他的福分!但是这么多年来,自从和山梅有了关系,他从来没有刻意去投石问路寻过姻缘,老盘也从没有提过要给他介绍女人,他知道老盘的心思,如果他真的有门路了,离开了这个家,老盘的家庭会重陷困境。他自己也乐得这么过下去,如果真的找到了一门亲事,结了婚,是要办结婚证的,他的身份证是捡来的,到时候就会露馅了。
平瑶屯是个地处偏僻的深山瑶寨,附近没有什么寨子,他刚来的时候寨子只有十三户,现在二十二户,这里的人们过着近乎与世隔绝的生活——这是他当初选择来这里落脚的主要原因。十五年来,他几乎没有离开过平瑶,特别是头几年,他没有离开过平瑶半步,乡上的集市也没有去过,后来过了好些年,山梅把种出来的生姜、薏米、玉米驮运到乡上的集市售卖需要帮手,他才跟着去了几次,去了办完事马上回来,从不停留。
登上开往县城的班车,找了座位坐下来,他打开车窗朝汉威说,你回去吧。汉威不走,一直站在车边。他的头发原来烫过,现在长长了,像一个鸡窝,年轻人都这样,不是烫发就是染黄染红,总想和别人不一样。他对汉威说,你回去吧,我过几天就回来了。说完,内心一股悲凉涌上来,他真的还会回来么?他还能回来么?
十几年了,刚开始的时候他常常做噩梦,梦见警察把他抓住了,手上、脚上被铐上冰冷的手铐和脚镣;有时候梦见他在前面拼命跑,警察在后面追,他跑啊跑,警察追啊追,后来枪响了,他扑倒地上……每次醒来,他浑身冷汗。
他原来的名字叫李杰,老家是桂西北一个叫那坪的小山村,王亮这个名字,是他在逃跑的途中捡到一张身份证上的名字,身份证上的人和他长得乍一看有几分形似,年龄比他大六岁,就一直用到现在。这么多年过去,就算在梦中,他也从不恍惚,他知道自己不是王亮,他是李杰,他杀了人,是个在逃的杀人犯!
十几年了,在那坪时候的生活场景会时不时进入他脑海,或闯进他梦中,特别是近段时间来,那些记忆像汹涌的河水,朝他涌来,越来越清晰。
那天发生事情之前,李杰本来脆弱的神经又经受了一次强烈刺激。下午,母亲让他去看水田,水田隔三岔五需要察看一次。寨子的水田都是梯田,插上秧苗后,需要经常察看,不然田埂有开裂或坍塌的可能,如果那样,水就跑光了——刚刚撒了尿素,肥水都流到别人家了;还有一种可能,贪小便宜的人知道你家刚撒了尿素,偷偷开了田埂,再从上面放水进来,把你家的肥水都偷走了。
李杰准备走到田边时,听到渠坎下有人说话,驻足细听,是寨子里的卜曼腾和阿如。他们在谈论他母亲的事情。阿如说:“你说她还跟不跟李杰爸睡?”卜曼腾说:“李杰爸腰断了,不睡了吧。”阿如说:“难说,李杰爸腰断,其他又没有断……”两个人笑起来。
李杰的头涨起来,内心像被砸进一块大石头,激起了剧烈的震荡。他不去看水田了,转身回家,回到家蹬蹬蹬直接进了房间,关上房门蒙头睡觉,内心阴郁。那天是农历六月六,母亲杀了一只鸡,晚上吃饭的时候,母亲叫了好几次,他才起来吃饭。
坐到桌边,李杰主动给自己倒了一碗酒。
龅牙见了咧嘴一笑。
几年了,自从意识到龅牙在这个家是什么角色,李杰再也不跟他说话,也不愿跟母亲说话。他变得沉默寡言。读到初二的时候他就辍学了,他自己不愿读,不愿再花龅牙挣的钱。
龅牙有力气,人也勤快,在寨子里,人们种香菇他种香菇,人们种生姜他种生姜,人们种杉木他种杉木。他还多了一门手艺,会砌砖建房,会刮墙灰搞装修——这个家因为龅牙的到来,从困境中走了出来,过上了和寨子里人们一样的日子。龅牙把挣到的每一笔钱都交给母亲掌管,过年过节人们打牌赌钱,他在旁边笑眯眯看,从不参赌。他唯一的爱好是喝酒,每餐必喝两碗酒,但不嗜酒,寨子里有红白喜事,没见过他醉烂如泥。
父亲偶尔喝一两碗,一般是在过年过节有好菜的时候,平日里不喝。家里的酒,都是母亲自己酿的。
李杰主动倒酒喝,在龅牙看来他长大了,变成男人了。两个男人一起喝酒,就有了沟通的渠道,所以龅牙咧嘴一笑。
李杰喝得很快,很快把一碗酒喝完了。碗蛮大,一碗酒差不多半斤。李杰之前没有喝过酒,不胜酒力,半斤酒下肚,整个人晕晕乎乎起来,他的脸喝成了猪肝色,眼睛里也有了血丝。
龅牙讨好地问他,要不要再倒一碗?李杰不应声。
龅牙从桌子底下抽出酒瓶,拧开瓶盖,伸过来给他倒酒。李杰并不领情,他把碗挪开,酒洒到了桌面上。
李杰的举动令龅牙生气,他脾气急,极易暴怒,他牛眼一瞪,用白话骂了一句:“丢那腥,比面不要面!(×你妈,给脸不要脸!)”
李杰怒视着他,他早就想跟他干一架了,把他撵出这个家。但他知道自己不是他的对手,龅牙身体强壮,打不过他!但现在酒壮怂人胆,李杰血脉偾张,气粗如牛,他冲动地起身,抢过龅牙手上的酒瓶,猛地朝他头上砸去。啪,装有大半酒水的酒瓶猛地砸在龅牙头上,玻璃瓶碴和酒水迸溅。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所有人都惊呆了。
龅牙瞬间像一根木桩,脸色惨白,摇晃着向后倒去。母亲惊叫了一声,过去推搡呼唤龅牙,龅牙毫无反应。血水从他头上汩汩冒出来。母亲哭了起来,不断地推搡龅牙,呼喊他的名字:“老罗!老罗!……”
父亲从震惊中反应过来,朝母亲低吼:“别哭了,快去把门关上!”
母亲扭脸看他,停止哭泣,惊慌地去把大门关上。
李杰呆呆地站着,手上还攥着断裂的瓶颈。
父亲思索了一会儿,对李杰说:“赶紧的,收拾几件衣服,马上离开家,走得越远越好!”又对母亲说,“家里有多少钱,都拿给他!”
母亲说:“李杰走了,他怎么办?”指着地上的龅牙。
父亲说:“我们后面处理!”
母亲看着躺在地上的龅牙,他们都认为龅牙被他打死了,害怕和慌张令她浑身颤抖。她捂住自己的嘴巴,尽量让呜咽压在胸腔里。
母亲抖抖索索地把家里所有的钱都拿了出来,两千多。
父亲催促他快走,不要让寨子里的人知道了!
面对自己一手造成的突发事件,李杰一时不知所措,慌慌张张地进房间收拾几件衣服,塞进一个双肩包,然后接过母亲手上的钱,趁着夜色,急匆匆离开了家。
李杰的父亲李杠原来是个强壮的男人,一个冬天,李杠去山上砍柴,不慎脚底一滑,滚了坡,捡回了一条命,腰却摔断了,从此成了一个废人。1995年,寨子里许多人家房上的茅草换成了瓦片,李杠自己不能打瓦,他每天被老婆兰瑛背到门口的躺椅上,不断地对从门口经过的人重复一句话:“看到有打瓦的,帮我领到我家来。”一天,终于有人领来了一个男人,此人印堂黑红,身板强壮,上颌前突畸形——是个龅牙。他挑着两个蛇皮袋,一边是几件衣物,一边是一张薄被。有一张薄被,看样子他随时可以就地过夜。男人说他是钦州人——他的母语是白话,普通话很蹩脚。李杠的普通话也很蹩脚——那坪的人们讲壮话,普通话都很蹩脚。两个蹩脚的普通话对讲,就像鸡同鸭讲,交流很困难。比画了半天,总算弄明白:男人姓罗,叫罗里宁,会打瓦,不讲价,主家看着给,有口饭吃有个地方落脚就成。这正合李杠的意。
龅牙在李家落下脚来,他每天起来牵着水牛到寨子对面的黄土坡上打瓦,那里的黄土黏性好,杂质少,取水也方便,生产队的时候人们在那里挖了两个瓦窑,建了两排晾晒瓦片的草棚子。龅牙上午挖泥、踩泥,下午打瓦,中午不回来,兰瑛给他送饭。地里农活忙的时候,兰瑛送完饭就转去地里干活,农活不忙的时候,兰瑛去送饭时就留下来一起干活,端送踩好的黄泥,收集晾晒干的瓦片。李杰经常跟着去耍,看龅牙打瓦——龅牙光着身子,只穿短裤,皮肤黝黑,虽身上黄泥斑驳,但胸肌和腹肌时隐时现。那时候龅牙爱逗他,问他想不想学打瓦?
以前人家请人打瓦,打完瓦结账走人,家里人自己上山砍柴烧瓦。李杰家的瓦打够后,李杠让兰瑛杀了一只鸡,他请龅牙喝酒。两碗酒下肚,李杠问龅牙接下来有什么打算?龅牙说不知道,走到哪里算哪里。李杠说不回老家吗?龅牙摇头,说老家都是石山,土地少,家里也没有什么人,不回去了。李杠问,想不想在这里找个媳妇?龅牙眼睛一亮,说想啊,我出来闯荡,就是想找个落脚的地方!李杠说,你看我这个样子,成了废人,烧一窑瓦需要很多柴火,李杰妈一个女人,得砍到什么时候才够烧一窑瓦?你如果继续留下来,我想办法帮你介绍一个女人!
龅牙就这么留了下来,他和兰瑛一起天天上山砍柴。晚上回到家,兰瑛忙着烧火做饭,龅牙挑猪潲去喂猪。以前龅牙没有来的时候,兰瑛收工回到家,一边烧火做饭,一边火急火燎地去喂猪,猪圈里的猪饿了一天,转着圈嗷嗷地叫。又累又饿又愁苦的兰瑛,常常会拿着猪潲瓢打猪头,一面打一面骂,老娘又累又饿,老娘还没得吃呢,叫什么叫!叫什么叫!常常打着打着,兰瑛哭了起来。
到了冬天,龅牙和兰瑛像蚂蚁搬家一样,把砍下来的柴火扛到了瓦窑口,码起来的柴垛像一节小长城。开始烧窑后,龅牙住到瓦窑,兰瑛每天给他送饭。天冷,草棚子四面透风,兰瑛上街买来彩布,帮龅牙围了一个小间。一个月后,终于烧好了两窑瓦。龅牙又和兰瑛一起,操持着把房上的茅草换成瓦片。房屋修缮是大事,寨子里的人都来帮忙,龅牙和兰瑛上街买来酒菜,杀鸡宰鸭,忙前忙后。李杠被抬到邻居家的廊檐下,他看着龅牙和老婆忙碌,一点帮不上忙。
给龅牙介绍女人的事却一直没有进展。先后介绍了几个附近村寨想招婿上门的人家,不是嫌他年纪大,就是嫌他长相难看,还是个外地人,不知根知底!
一年又一年,虽没有给他介绍到女人,龅牙却没有离开的迹象,他把李家当家,扎下根来。这正合李杠的意,自己一个废人,白捡了个壮劳力!
自从李杠成了废人后,兰瑛愁苦又劳累,整个人又瘦又黑,龅牙来了以后,帮了她很多忙,兰瑛的脸上渐渐有了红润。
十二岁那年,有一天晚上,李杰正睡得迷迷糊糊的,突然被一阵打砸声和叫喊声惊醒。侧耳细听,打砸声和叫喊声是从父亲的房间传出来的。父亲拿着拐棍一面打砸床边的衣柜,一面喊:“李杰,家里进贼了!李杰啊,家里进贼了!……”李杰懵懵懂懂地爬起来,趿鞋出得房间,手电筒照见龅牙站在堂屋里,他身上只穿着裤衩,母亲的房间门虚掩着。龅牙说:“我察看了,家里门窗好好的,没有进贼!”父亲双手拍打自己萎缩的双腿,唔唔地放声悲鸣。
一次,李杰和寨子里的几个伙伴玩扑克,因为阿伦偷牌,被李杰发现了,两人发生了争执。阿伦恼羞成怒,打了李杰一巴掌,李杰冲上去,两人扭打起来。阿伦的鼻子被打出了血。阿伦的母亲来了,她指着阿伦的额头破口大骂:“你这个衰仔,你去惹他做什么?你惹得起吗?人家有两个爹你有吗?挨打了没有?你活该!”骂着扯过阿伦,拽回家去了。
晚上吃饭的时候,李杰问母亲:“妈,阿伦的妈为什么说我有两个爹?”李杠一听,手上的筷子“啪”地砸到桌面,怒目圆瞪,吼道:“你是嫌我还没有被气死吗?!”李杰被吓住了。兰瑛低着头吃饭,不吭声。龅牙镇定自若,甚至霸气地喝了一大口酒,响亮地咳了一声。
帮李杰家修缮了房屋后,龅牙什么都干,种田种地,上山找土特产,帮人起房子,赶马驮运杉木,什么挣钱干什么。他也从开始的小心翼翼、谨小慎微变得自若起来,该吃吃,该喝喝,该干嘛干嘛,俨然把自己当成了这个家庭的一分子。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龅牙强硬、霸道、暴躁的一面暴露出来。李杰不听话,他动辄训斥,甚至动手打他;李杠和他顶嘴,他就不给他饭吃,不让兰瑛帮他端屎送尿。
李杠躺在床上,因为腰椎以下不能动弹,双腿越来越萎缩,人越来越枯瘦,李杠憋着一口气,骂:“滚!你这个外来的流浪汉,这个家不需要你,你给我滚出去!”
龅牙冲进房间,指着李杠破口大骂:“我为什么要滚?……昂……没有我,房上的茅草能换成瓦片?没有我,这个家能撑到今天?……要我滚,你问问李杰妈同不同意?……你现在才是这个家的累赘,该死的人是你!”龅牙已经学会了讲壮话,虽然很蹩脚,但不影响交流,更不影响骂人。
李杠气得脸色发青,双唇颤抖。但李杠无可奈何。
最后,李杠不得不妥协,不得不屈服。他哀求龅牙不要把家丑外扬,他想要和李杰妈公开过,等他死了以后吧,给他留一点男人的尊严!
这个家就这么畸形地过了下来。
龅牙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他过得更自然了。虽然没有公开和兰瑛睡到一个房间,但晚上进兰瑛的房间不再避讳了,不再偷偷摸摸了。
一个女人,两个男人!这是个公开的秘密,寨子里的人都知道!
刚开始的时候,人们当面称龅牙老罗,背地里叫他“龅牙”。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称他“杰叔”——阿杰的叔叔之意。小时候李杰觉得人们称龅牙“杰叔”没什么不妥,渐渐长大后,知道了一些事情,他明白了“杰叔”背后隐含的所指是什么,他感到了被羞辱、被中伤!
渐渐长大,十七岁了,李杰曾无数次想过要和龅牙打架,把他撵出家门。可是他知道自己不是他的对手,龅牙身体强壮,打不过他。
整个少年时期,李杰郁郁寡欢,他内心充满了耻辱、悲愤和孤独!
那天晚上逃离家门后,李杰不走大路,专走小路。天黑了下来,人们都收工回家了,大多数人正在家里吃饭,没有人碰到背着背包神色慌张急匆匆离开村庄的李杰。出得村口,李杰没有选择公路,他选择了上山的小路。也许龅牙被他打死,现在村庄里已经有人知道了,如果有人报警,派出所的警车会很快在公路上搜寻。
李杰朝山上走,他走得很快,没有目标,只想往深山里钻。过去李杰胆小,害怕妖魔鬼怪,害怕野兽,现在顾不上怕了,也不能怕了,只有往深山里钻,才是不被警察快速搜寻到的唯一途径。在路上,李杰把身上的身份证掏出来,埋到了路边树下的土里,他知道,从今以后,他不是李杰了,他要变成一个来路不明的人、没有身份的人!
在逃离的过程中,李杰想到了父亲那句话“我们后面处理”,他们会怎么处理呢?说父亲因为愤怒失手打死了龅牙?人们会相信吗?人们可能会同情,龅牙霸占了他的女人,或者说共享了他的女人,他因为耻辱和愤怒,持酒瓶失手将龅牙打死是有可能的。但是,一个腰断失去双腿的人,人们会相信他能把龅牙打死吗?说母亲失手将龅牙打死?不,不可能,龅牙是她的另一个男人,人们不会相信她会持物器将龅牙打死!那么,剩下的,只能是他李杰。李杰突然想到,父亲根本没有想要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不然他不会让自己逃跑!如果父亲能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一家三口口径一致,又没有证据,没有其他目击者……他老了,而且腰断了,双腿残废了,是个废人了……李杰伤心起来,父亲为什么就不能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呢?他打龅牙,为的什么呢?还不是从他的角度出发?还不是替他出气?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后悔已经来不及了。李杰伤心、懊悔、恐惧!
李杰连续疾走了几个小时,又累又困,在一片深山老林里,他找到了一个树洞,树洞能容下一个人,他用一根木棍在树洞里乱掏,用手电筒仔细检查,看有没有蛇或者其他动物,在确认没有后,才采摘来一堆树枝,垫在洞内,猫腰进去蜷缩在里面。因为累和困,他很快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他从噩梦中醒来,他梦见一个披头散发的恶鬼,正在朝树洞摸来,他惊悚得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果然,他听到黑暗中传来呜的一声,他屏声敛气,又听到呜的一声,像病入膏肓的老人临终前的呻吟,他毛发尽竖,颤抖着摸出随身带的折叠刀,另一只手紧攥着手电筒,瞪大眼睛紧盯黑暗中的树洞口。呜叫声持续不断,每隔几分钟响一次,后来他突然想起有一次听寨子里经常夜间上山打鸟的卜红雨说过,有一种鸟在夜里睡觉的时候会发出“呜——呜”的声音,这种鸟在睡觉时用嘴巴插进土里,随着呼吸时不时“呜——呜”地哼,就像人睡觉时打呼噜。他迫使自己恐惧的心慢慢放松下来,但他再也睡不着,黑暗中山野里的每一点风吹草动,都令他肌紧。
天际线刚刚露出了点鱼肚白,他又出发了。走的时候他把树洞里的树枝带走了,走了蛮远,才把树枝藏到一处草丛里,他尽量不留下什么痕迹。昨天晚上匆匆逃离村庄,他并没有方向,只想往深山里钻。现在他想了想,往西走,也就是太阳落山的方向,走五六个小时山路,会到达一个叫卡白的村庄,那个村庄不属于达县,属于新州县,他有个姨妈在那里,小时候他跟随母亲去那里走过亲戚。他打算先到那里,但不会停留,接着他会搭车往云南方向走,到达云南边境,找个地方落脚,再想办法越过边境,进入越南。
由于没有身份证,也害怕警察张贴通缉令而被人认出,李杰在往云南边境行进的过程中,从不在县城或乡镇的宾馆留宿,他选择农村投宿,越小的村庄越好。每到一个村庄,他主动给人家干活,不求回报,只求给一口饭吃,给一个地方睡觉。有时候找不到愿意收留他的人家,他只好乞讨,甚至捡拾垃圾果腹,然后找一个角落蜷缩过夜。后来,他在云南师宗县高良乡一个村庄的村道上捡拾到一张身份证,身份证上的人跟他长得乍一看有几分形似,年龄偏差也不算大,他偷偷藏了起来。离开那个村庄后,他有了新名字:王亮。
三个月后,王亮辗转来到云南马关县猛硐瑶族乡,经过打听和了解,他决定选择平瑶屯落脚。平瑶屯是个地处偏僻的深山瑶寨,附近没有什么寨子,距离乡政府驻地远,翻过两道山梁,对面就是越南。那天从猛硐出发,他顺着山路走了四个小时,然后爬一个陡峭的山坡,爬上山坳,远眺过去,一个小村落静卧在对面山的缓坡上,十几座房子掩映在绿树丛中。他观察了一会儿,发现平瑶屯的人们住得挺分散,像羊拉屎一样撒在一片缓坡上。他思索了一会儿,决定到住在最顶端的那家去试试,只要有一口饭吃,有一个地方睡觉,要他干什么都可以。
他抽了一支烟,身上的汗收了,才沿着山路下山,朝村子走去。走到村口,路坎的上方是一座泥墙瓦房,看样子已有些年头了,一个枯瘦的男子坐在门口的门礅上,看到他,热情地打招呼:“来了?来家里坐啊!”他心里一惊,他知道他要来?难道警察的通缉令已经贴到了这里?但他脸上微笑着,稍一犹豫,朝男子走去。他递烟给男子,男子接过去,指了指另一边的门礅,让他坐。后来他在平瑶待久了,才知道这里太偏僻,极少有外人来,偶有外人来,这里的人都很热情,尽己所能地接待。这里的人常说的一句话是:“出门在外,谁也不能把家背在身上!”
两个人坐在门口抽烟,男子看上去年纪并不大,但枯瘦、黝黑,病恹恹的样子。男子问他从哪里来?他说师宗。男子噢了一声,不知道他知不知道师宗在什么地方。男子问:“是来耍,还是想过那边去?”指了指山的背面,那边是越南。王亮本来想说是,但犹豫了一会儿说不是。“老家都是石山,土地少,生活艰难,所以出来闯荡,想找一个能讨生活的地方落脚!”他说。男子眼睛一亮,说:“你来对地方了!我们这里山地多得很,土地肥得很,插一根扁担都能发芽!”他突然咳喘起来,咳喘了一阵,继续说:“我们这里有好几家想招上门女婿,你年轻,将来在这里落脚,讨生活肯定没得问题的!”
他微笑着,做出认真倾听的样子。他在心里决定,不上住在最顶端的那家去试了,就在这家留下来。这个男子病恹恹的,家里肯定需要劳动力。
男子说他姓盘,“就叫我老盘好了。”
老盘站起身,进屋去舀出一瓢玉米粒,撒到屋场,嘴里“咕咕咕”地叫唤,不一会儿,从屋后的草丛里窜出一群土鸡,争先恐后地抢食。老盘瞄准了其中一只,突然弯腰出手,抓住了鸡的脖子。鸡“喔——喔——喔——”地惨叫,扑棱挣扎。群鸡散去,远远地踱步观望。听到抓鸡声,一个四五岁的男孩从里屋跑出来,用瑶语叽哩咕噜对着老盘说什么,老盘微笑点头,指着坐在门礅上的王亮说:“叔叔来家,今晚我们杀鸡!”男孩高兴得手舞足蹈。男孩叫汉威,是老盘的儿子。
暮色下来的时候,老盘的老婆收工回来了,她戴着竹篾编的尖顶遮阳帽,穿着瑶族服饰,挑着一担芭蕉芋回来。进屋后撂下担子,摘下遮阳帽,王亮惊异于女人的容貌,女人虽然脸色蜡黄,偏黑,但她的脸形很好,瓜子脸,眼睛大,鼻梁挺,牙齿很整齐,白。
女人刚开始对突然而至的客人有些腼腆,说上话后,就放开了,很热情,吃饭的时候积极劝酒,还陪着喝了两碗。他们很纯朴,对突然到来的陌生人并没有提防心理,也许他们早就渴望家里来一个陌生人——确切地说,是来一个能帮助他们家庭解决劳力困境的人,这人当然是陌生的,熟人没人会到你家里来做长工——只提供食宿不付酬劳的长工!
后来在老盘家待久了,王亮发现平瑶寨子里的人都很纯朴、热情,初次见到他,都主动打招呼:“来啊?有空到家里耍!”再次见到,也主动打招呼:“你好啊!今天去做什么工啊?”这个村子,外人来得太少了。
一段时间后,王亮发现女人不仅勤劳,还心灵手巧,家里的酒都是她自己用玉米酿的。老盘叫她山梅,他叫她嫂子。
那天晚上,山梅为他铺了干净的床铺,他进去插上房间门,上床掖好蚊帐,几个月来第一次躺在完全属于自己的空间,惊惧不安的心渐渐平静下来。将来怎么样,他不知道,但他决定暂时就在老盘家扎下根来,只要有一口饭吃,有一个地方栖身,该干什么干什么,不惜力气,隐藏自己的脾性和心思,暂时就这么过下去吧。以后要是有什么变故,再说!
躺在床上,王亮的眼泪流了下来,他不知道自己怎么就走到了今天,父亲的腰断他无法控制,母亲的悲苦和孤独他无法解决,龅牙的到来,他去干预了!他想到了那坪寨子里的其他人家,各家都有各家不同的境遇。脸面真的那么重要吗?耻辱真的那么重要吗?和现在的境遇相比,他当时真的应该那么悲愤吗?不知道!不知道!
他和山梅之间,具体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好像是他来到老盘家四五年后,那年春天,两个人在溪流边清洗盖秧苗的薄膜,他的手无意间碰到了她的手,他看见她的脸红了,他的心突然狂跳起来,二十多岁了,他的荷尔蒙早已分泌,但他的处境,哪还敢有欲望?刚到平瑶的时候,他还经常思谋着如何越过边境,进入越南,那样他就彻底不用担心警察对他的追捕了。随着时间推移,他从村民口中了解到,想偷偷越过边境并不容易,而一旦真的进入了越南,那边是一个截然不同的国度,语言不通,一个外来偷渡者很容易被那边的执法人员抓住,那他的命运将走向何处?平瑶是一个地处偏僻的小村落,外人极少进来,他隐匿在这里,应该也相对安全。当处境渐渐平稳下来,随着年龄渐长,他对女人的欲望越来越强烈,但他从不敢跟老盘提出给他介绍个人家,他害怕他的身份因此露馅。荷尔蒙的瞬间激发,令他无法遏制内心的火焰,他突然伸出手抓住她的手,她看了他一眼,并没有抽回手去,而是脸更红了。他的心跳像万马狂奔。来到老盘家几年,他已经知道老盘有严重的疾病,身体瘦弱,经常咳喘,那个功能应该是没有了,老盘独住一个房间,山梅自己睡另外一个房间,许多个夜晚,他刻意注意过,没见老盘进过山梅的房间。山梅还年轻,她身体健康,应该有需求的。
不久后的一天,他和山梅到山上的地里劳作,中午休息的时候,他对山梅说:“我们到那边去休息好不好?”指了指一处隐蔽的丛林。他刻意不叫她嫂子,往常他跟她说话,前面都先称呼嫂子。说完他就径自先往丛林走去,他不知道她会不会跟上来,他现在心里像鹿撞,突跳不已。如果她不跟过来,那么他就在丛林里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继续劳作,以后不敢再有奢望了。
没想到,她跟了过来!
那天,是他最幸福的一天,他人生第一次体验到了女人的滋味。而她,也许因为很久没有体验男人的滋味了,激动得满脸绯红!那时候她因为生了汉威,已经响应政策号召做了避孕手术,并不担心意外怀孕。
从那以后,王亮的干劲更足了,他把老盘家当成了自己的家,把山梅当成了自己的女人,一心一意地和山梅一起经营着这个家。但他吸取龅牙的前车之鉴,处处小心翼翼,对汉威疼爱,对老盘和山梅客气,他时刻提醒自己,不能让老盘察觉到自己和山梅关系的任何蛛丝马迹。后来,政府有危房改造政策,他和山梅一起,张罗着把泥瓦房倒掉,建了两层的砖混楼房,老盘对他更好了,从友好,到感激,到依赖,他已经感觉到,在老盘心里,这个家已经离不开他了。
两年前,老盘病逝了,他按乡俗给老盘操办了隆重的葬礼。老盘死后,山梅多次跟他提出,办几桌酒席,把寨子里的人请来,明确他们的关系。他说,不急,等汉威从心里接受他,等汉威自己提出来,那样更水到渠成。
现在的交通条件比过去好了很多,当天王亮就到了砚山县,第二天转到达县,第三天就到了老家那龙乡。十几年前他从那坪出发,辗转了三个月才到达平瑶,现在他从平瑶出发,回到家乡,才三天。这十几年他隐匿在边远的村落,外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道路宽敞,路边村寨的楼房,像雨后春笋。
下车后他进了一家小炒店吃快餐。店里没有其他客人,老板娘忙完后坐在店门口。他向老板娘打听那坪屯的情况。老板娘回头看了看他,问:“你从哪里来?想了解那坪什么情况?”他说:“那坪有我一个亲戚,很久没联系了,想了解一下情况。”老板娘笑了,说:“你算问对人了,我就是那坪的!”他心里一阵欣喜,认真看了看她,老板娘二十出头的样子,长得小巧玲珑。他在脑海里苦苦搜索,她的样子是谁家的孩子呢?一点也想不出来。他离开十五年了,他离开的时候她还是个小孩子,时间让她和他都发生了变化。他问:“李杰家现在情况怎么样?”“李杰家?”老板娘想了一会儿,噢了一声说:“是有这么一家,李杰离家好多年了,不知是生是死,从没见回来过。”“他父母现在还好吗?”“他父亲前几年过世了。”王亮心里一沉,鼻子一酸,眼睛红了。“剩他母亲一个人,生活很艰难吧?”老板娘说:“没有啊,还有龅牙叔。”他心里一惊,脱口而出:“龅牙叔没死吗?”老板娘看了看他,问:“你知道龅牙叔?”他赶紧解释:“我小时候去过他们家,看到有一个龅牙叔,外面来的。”老板娘说:“我听我爹说过,以前李杰用酒瓶砸龅牙叔脑袋,龅牙叔昏死过去,后来又活过来了,李杰就是为这事跑的,后来家里想找他回来,一直联系不上。”
太意外了,压在心头十几年的东西,现在突然烟消云散,王亮瞬间感觉浑身轻松——噢,不,他不是王亮,王亮是另外一个人,龅牙没有死,他现在可以做回李杰了!
李杰还从老板娘那里了解到,父亲死后,龅牙和母亲正式结为夫妇,近两年母亲也病了,癫痫病,时不时会突然倒地,口吐白沫,全身抽搐,是龅牙一直在照顾她。父亲在死前,也是龅牙一直照顾,父亲死后,是他操办的葬礼。龅牙还把老屋推倒,起了两屋的砖混楼房,里外装修漂亮。老板娘说:“龅牙叔能干,什么都会做,建房和装修都是他自己干的。”
李杰心情复杂,看来他们家需要龅牙,母亲需要,父亲也需要,就像老盘家需要自己,山梅需要,老盘也需要!他突然想到,这么长时间了,老盘和汉威,其实应该知道或者感觉到他和山梅关系的,他们不吭声,不代表他们不知道,而是他们明白了境遇,理解了生活!他突然明白,他打龅牙那天,母亲的眼睛里除了慌张和害怕,还有深深的哀伤和疼痛!
吃完饭,已近傍晚,到那坪屯的乡村客运已停运,李杰走路回村。路上遇到几辆过路车,他抬手拦车,没有哪辆停下。一个多小时后,李杰回到阔别十五年的村庄,他没有直接进村,而是爬上村庄对面的山坡,当年他逃离,就是从这里逃走的。他在一棵树下坐下来,眺望对面的村庄,心里百感交集。这里的一草一木他太熟悉了,好像昨天刚刚离开。村庄里的建筑倒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的泥墙屋全部变成了楼房,他搜寻自己家的位置,找到了,现在那里是一栋两层的白色小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