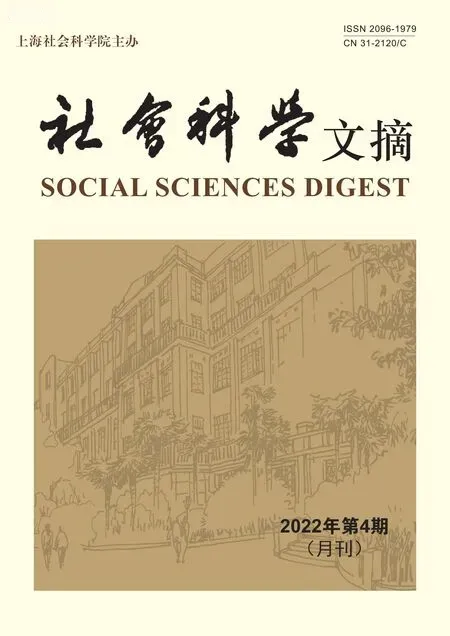再谈走向“活”的制度史
文/邓小南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摘自《史学月刊》2022年第1期)
“走向‘活’的制度史”这个说法,是2001年在包伟民老师组织的“近百年宋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研讨会上提出来的。本文涉及的内容,是对该文的一些补充。
下“死”功夫,做“活”历史
“活”有两层基本含义:首先,制度本身是“活”的,有活动,制度才有效能、有作用;其次,制度史研究不能只重视文本规定,还应该关注其实际表现,关注影响其“活动”的诸多因素。研究中所谓“死”与“活”,并非相互排他:研究对象是“活”的,我们的观察思路也要活;而就研究的基础而言,只有下足“死”功夫,才能让研究真正“活”起来。
(一)“史有定法”与“史无定法”
“史有定法”还是“史无定法”?事实上,二者相通而非相互排斥。
史有定法,通常是指历史学科有自身“压舱底”的基本功夫,学者也有个人的学术定位与研究方式。“定法”从实证开始。实证是一种硬功夫,是历史学的看家本领。台湾史语所柳立言先生训练学生的基本方式,是“史有定法”的一种代表。柳先生和一些老师、研究生一起研读五代墓志,结合传世文献辨析史实,为趋近历史实相提供了可行的路径。如柳先生所说,所有研究的本质都是回答问题。要关注“谁的问题”“如何发现问题”“如何回答问题”;在阅读史料的基础上,找出问题并且予以回答。他把切入点概括为“史学六问”和“五鬼搬运”。所谓“五鬼搬运”,就是五个“W”(when、where、who、what、why);除了这五个“W”之外,还有如何、怎样“H”(how),综合在一起,就是“史学六问”。这样的“死”功夫也是一种硬功夫,是大致有方法可循、有问题意识、有相对明确的路径可走的入手方式。
史无定法,不表示不需要方法或没有较好的办法。吴承明先生指出:“我国早有‘史无定法’之说。我赞成此说……在方法论上不应抱有倾向性,而是根据所论问题的需要和资料等条件的可能,做出选择。”也就是说,研究中应该有针对性,实事求是,不宜固守某一种特定的研究方法。“史无定法”正是历史研究这种包容性和创新性的体现。
历史学的活力来自不断地求真求新。这样的活力,其来源、其力度恰恰是从死功夫、硬功夫里生发出来的。所谓的“活”,是产生于沃土的生命力。“活”,绝非浮泛飘忽,只有肯下“死”功夫,像树木把根基深扎在泥土中,才能枝繁叶茂地“活”起来。新视角往往来自长期积累的激活,新思路常常来自线索的缀连想象,这些都离不开往日功夫。新议题可能导致动态鲜活,传统议题也可能贡献出通贯深入的新颖见解。新材料的牵动,能使研究“预流”;深读“坊间通行本”,也可能发人所未发。
(二)制度史的“生命”所在
对于“制度”,学界有不同的概括和理解。大致上讲,可以说制度是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法令礼俗和基本规范,是制约政治活动、社会活动的行为框架。
有学者强调,制度的最基本要素就是结构、功能和形式,所以形式排比和结构分析,是制度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也有学者指出:制度分为“无意中逐步形成”和“有意建构”的两种类型,我们都生活在多种秩序形成的交叉网络之中,而不是在某种单一秩序里。制度所维系的正是特定的秩序。如果放在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进程的更大背景中看,制度就是政治文明的底色,是政治文明的支撑与映衬。
我们知道,制度本身是有生命的,有它的节奏、韵律,历经形成、生长、发展,可能不断完善,也可能走向衰亡。追踪、观察、多维度反思这一过程,正是制度史的“生命”所在。
说到制度、规则,我们首先想到的是相对稳定恒常的标准,但是,制度必须应对多变、流动的现实。制度本身追求的“可预期”,跟它应对的现实情况的复杂起伏,本身就构成有张力的两端。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一些折中的方式,出现非正式的制度运作。
所谓“非正式”,就是不见于书面规定,“令式之外”但经常为人们使用的一些做法。一方面可能是无奈情况下的灵活处置,或是应对制度“形式目标”的要求;另一方面对制度的规定与初衷势必带来某些调适甚或扭曲。欧阳修在《新唐书·百官志》中说到官制的两类情形,一种是“其纲目条理可为后法”,另一种则是“事虽非正,后世遵用,因仍而不能改”。这些“事虽非正”的运作,对于正式制度的施行可能有补充——或者说是润滑——的作用;在某些情况下,缺乏灵活弹性的制度借由非正式制度的“因仍”“调和”才得以推行。如果我们专注于观察制度运行的实践进程,那么几乎可以说,“正式”与“非正式”制度交错混糅、互为所用,甚至是相辅相成的。相对静态的制度规定与动态的现实需求之间,存在一定的空间,空间里面有变形,有扭曲;这种空间中的活动,往往决定着制度的走向。
制度本身是“规范”和“人事”折中的结果。制度本为“设范立制”,既是引导保障,也是对某些利益关系的限定,对某些行为方式的制约。这样的引导、限定与制约,在历史上究竟是不是曾经生效?与制度运行相关的“人事”起到什么作用?都需要通过制度的运行过程来观察。
制度的活力与生命是“人”赋予的,研究制度史必须关注人的活动。制度史研究的活力和持久生命力,取决于对制度活力的认识深度。所谓“活”的制度史,不仅是指生动活泼的写作方式,更重要的是指从现实出发、注重发展变迁、注重相互关系的研究范式。
从运作“路径”看制度
我们研究古代制度的意义,要点不在于重现;而在于观察当时如何回应问题,规定如何调整,制度如何执行,也就是要观察制度演变的“路径”。历史研究讨论“变迁”,就是讨论过程,路径是实际过程的载体,是走过来的方式。目前的探讨,通常注意到制度的起讫两端:规定与结果。但对于研究者来说,我们需要注意连结两端的路径。
路径是完成“过程”的经历与步骤。过程中会有若干节点,所谓“契机”,正是由特定历史节点上的事件所引发。观察节点之间如何连结,就要关注“路径”。历史过程是由涉及多方面、起讫点不一、内容性质不一的多种演变进程交错汇聚而成。这样的动态过程像转动的链条,是由不同的环节、阶段连续构成,不追寻环节就看不清演进。例如王朝实施的法律制度、赋役制度,民间的家族制度等,各有其内在的发展轨迹,有起讫不同的历史阶段性。这些节点往往不与王朝起讫同步。一个朝代的制度可能并非开天辟地,所以才有多轨过渡,才显得复杂丛脞。
观察路径,事件与人物往往是其抓手。制度中的“人事”,有人有事。“重返人/事关系的历史世界”是制度史研究的现实取向。事件、人物都是行为的组合。从突变到潜移默化,从非常到日常,这些因素都可能影响制度设计与实施。学界讨论“什么是日常统治史”,研究的就是一些基底性的制度及其形成演进的路径。
制度的台前幕后都是“人”,是“人”在“事”中的行为使得制度“活”起来。制度的鲜活,是由于行为带来的活力;制度的原则,也是产生于并运行于现实行为之中。即便在同样的基本体制之下,面对大体类似的情形,不同成长背景、利益关系与认知框架下,不同决策者、执行者的行为准则也可能有所不同。
面对层叠纷杂的事件与群体利益诉求,制度所着眼维护、限制的,主要是看似无形的特定“关系”。这是协调维系机构、程序、仪式的“神经”系统。某种意义上,制度实态、路径选择是由“关系”牵动、决定的。君相权力、中央与地方、文武之间、体制内外……都是讲关系。制度运行过程中的公开规则与潜在规则看似对立,实则关联。关系并非虚缈,其渗透在方方面面行为之中,实在而又强韧,左右着路径选择及实施过程。国家体制内诸多制度并非并列,是由制度的统辖组合关系决定其根本属性。
对于这一切,都要放到制度运行的现实中去观察。换个角度说,事件节点与人物活动,是我们观察制度演进过程的入手处;而节点之间的过渡方式、行为活动导致的趋势方向,都与运作路径相关。
制度与制度文化
(一)制度:“有制有度”
古人心目中的“制度”,其实是有“制”有“度”。“制”通常指规定,而“度”则是对于规定的把握幅度。中国古代对于“制度”有很多不同的表述,较早的如对《周易》“节”卦的解释:
《彖》曰: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
孔颖达《正义》曰:
王者以制度为节,使用之有道,役之有
时,则不伤财,不害民也。
彖辞中“节以制度”四字,点明了“制度”的意义。古人所谓“制度”,是指规矩;“节”“数”“度”,都是指节制、边界,指对于限度的把握。
“制”与“度”的关联,提醒我们注意规定与尺度之间的关联;“使”“为”“用”之类表述,让我们注意到制度背后“人”的作用。
(二)“初衷”与“折中”
王充《论衡》中说:“礼乐之制,存见于今”,而“法制张设,未必奉行”。“张设”与“奉行”间的差距值得思考。例如宋代的选任制度,关系到每个官员的仕途生涯,众目睽睽之下,有一套套细密的规则。正如苏轼所说:“一命以上,皆付之定法。”正因其有条可循,人事部门才得以实施除授。《宋会要辑稿》《吏部条法》等,到处都是强调严密的例子,但执行起来,不可能那么拘泥。首先可能是破例破格(或许声明“下不为例”);如果可行,这些套路就渐渐变成“故事”;积累整理之后,就纳入“成例”。在此过程中,有些先例也许过了一段被废除,有些就成为条文的补充,有些甚至通过修订格目被编进铨选条法。应该说,承先启后的“故事”在此过程中起着突出的作用。
规定与调整让我们看到“初衷”与“折中”的关系。“循名责实”与“岁月序迁”,是贯穿于考课黜陟之法中截然不同的两种原则。前一原则为宋代的有识之士所崇尚,原本是政策制定的初衷;后一原则却在多数场合下悄然起着调谐作用,并由于其便利易行而为多数人所接受。二者看似冰火不容,却共同蕃衍出复杂波折的折中式运作,体现出宋代制度的务实特色。
执行制度的安排,也会带来问题。宋代监察官员会去地方查究文档,号称“刷牒”。要清查的事项前期通知,被按察的官员预先准备应付。这样的做法,显然违悖“觉察”之初衷,却是常态习熟的运作方式。此类制度貌似运转带来的弊端,内在严重性可能更甚于制度停摆。
制度的“具文”与“空转”,可能是与某些制度“俱来”的存在方式。我们既不能仅依据文献记载的条目规定,就认为某一制度实施有效;也不能只看到运作现实与我们心目中的制度不符,就简单认定为“具文”。相同的制度规定,不同场合下把握方式各异,实际功用不同,要透过制度运行的实态去探究当时政治局面的实态。对于某些制度“空转”,观察者批评其“空”,体制内注重其“转”;今天的研究者批评其似是而非,当年的操控者在意这系统格套俱在,各层级可供驱使,奉上尽忠。
非正式制度、潜规则中,会有官吏上下其手;但有些看似被制度“防范”的做法,事实上可能是体制惯用且不可或缺的运行类型。制度经由现实折中,可能“塑造”出不同的行为方式,“开发”出多变的解决问题途径,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限定了国家的治理轨迹。
(三)关于“制度文化”
制度并非天然合理。中国古代的国家制度、官方制度,尽管考虑到现实因素,归根结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而这些“意志”能否不折不扣地被贯彻,受到综合文化环境的制约。
制度设计是系列运作的结果;制度变迁可能以特定观念为其先导,更可能来自现实的挑战。设计规范有内在罅隙,具体实施则面临诸多不测。制度的节点都留有层级式的阀门,掌握其开关者,既有不肯尽职甚至刻意阻碍者,也有忠于体制小心行事者。即便是在体制内正常作为者,深层的考虑也往往在于预期的政治秩序及政治前景的风险。这种看似制度规范之外的权衡,却是决定制度执行曲线的重要逻辑。而这些判断与抉择,显然与抉择者身处的制度文化环境相关。
所谓“制度文化”,不仅是制度设计层面体现出的意识,亦应包括环绕制度运行的政治文化氛围;既包括刚性的制度条款和规范,也包括延伸笼罩着条规、无固定形式踪迹又无处不在的整体环境,是多种因素互动积淀产生的综合状态。这种弥漫性的制度生态,浸润渗透于制度之中,影响着制度的生成及其活动方式;既包括对于制度轻重缓急的认知,也包括制度设计者、执行者、漠视者、扭曲者、抵制者的态度、行为与周旋互动。制度的施行状态势必呈现出“万象”图景。
制度推行的动力在人。我们希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权力显然不会主动进入笼子,谁能够把这些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什么动力赋予人们“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决心?这就与整体的制度文化氛围有关。
制度运行的真实逻辑需要在现实中观察把握。规则的确定性和实践中的不确定性,永远是一组绕不过的张力。在其“空间”中,充溢着官场文化的影响,也有多方强劲的现实拉力。凡此种种,透视洞察不易。这可能是制度史研究最富挑战性也最有魅力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