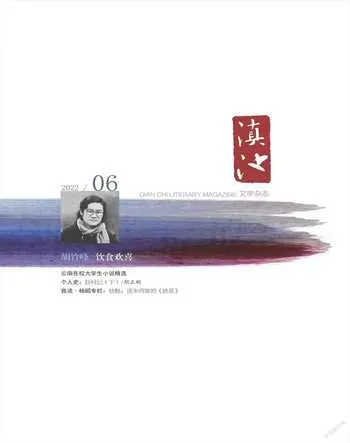陈年旧食
魏振强
山芋干
现在还记得外婆家的村庄叫大司村,位处皖东,属于丘陵地带。村子里的水田不多,但山地不少,除了种蔬菜,大多种的是山芋。越冬时节,山芋容易冻伤、腐烂,有的人家便挖了地窖藏山芋。这些山芋基本上不用作口粮,而是做来年的种子——埋在土里,等它们发芽,长出苗,然后移栽到山地里。
我去外婆家之前,外公和大舅早就死了,外婆家的那座房子里只有她一个人。一个人,也就只能分到一个人的田地。田地少,种的菜少,种的山芋也少。外婆家没有太多的山芋,也就没挖地窖,山芋都放在灶膛后面的柴火池里。土砖砌成的柴火池,堆了草和松树枝,下面还铺了层糠,山芋埋在糠里。因为有柴草和糠的双层保护,那些山芋所受的待遇不比地窖里的山芋差。
我坐在灶膛口烧饭,偶爾会动糊涂心思——掀开柴草,把手插进糠里,在里面摸出一根山芋来。熬过了夏秋两个季节,山芋到了冬日,生吃起来格外甜;要是埋在灶膛的柴火里烤着吃,又香又甜。外婆家的山芋本来就剩得不多,除了我吃掉的,还有烂掉的,来年的时候基本上所剩无几,外婆不知道我做了手脚,嘀咕:那么多山芋怎么都烂掉了?
好在别人家有山芋苗,外婆东家要一点西家要一点。村东村西两头都有外婆家的地,在山坡上,除了留着一小块种茄子、辣椒、冬瓜、南瓜,全都种上山芋。山芋长大了,挖出来,堆在堂屋的拐角。老鼠经常会在夜间或白天没人时跑出来,啃几口;有时在屋外吃食的猪没被及时关进圈里,也会跑进屋子,直奔那堆山芋,我一见就很生气,狠狠地朝它的屁股上踹一脚,它“嗷”一声,撒开腿,逃了。
并不是舍不得给猪吃山芋。一般来说,我会把山芋煮烂,和糠掺在一起,放在食盆里给猪吃,但猪和贪婪的人一样,总是吃不饱,逮着能吃的就会张着嘴,它在屋子里呼哧呼哧地大口嚼着山芋,满地都是碎碴子和它留下的涎水。我那时正是喜欢打架的年纪,却又打不过别人,猪正好可以拿来撒气的。
外婆种了那么多山芋,主要还是为了给我的父母和兄弟用作口粮。我老家在圩区,种的是水稻,但家里人口多,挣工分的少,分到的口粮总是不够吃,“缺口基本上都是靠外婆种的山芋填补的。
山芋刚从地里挖上来的时候,放在锅里加水煮,或者切成薄片放在锅沿上蒸熟,很香、很粉。山芋还可以放在灶膛里烤着吃,这当然是孩子们经常干的事,大人们是没有那个闲工夫的。最常见的吃法则是煮稀饭。山芋“上市”时,我父亲会准时来到大司村,他正在壮年,挑一担一百来斤的山芋,翻山越岭,走过四五十里的路,当然很辛苦,但傍晚时还是能赶回家的。山芋挑到家,父母还会客气,当成稀罕物给左右隔壁送去几根——那玩意在圩区确实还是稀罕的。
保存山芋最好的办法还是做成山芋干。
通常是立冬前后,先把山芋洗干净,放在筐子或者桶里,人坐在一条前端装着刨刀的长板凳上,戴着手套,把山芋刨成片。刨刀很锋利,不小心的话,就会把手指或手心刨得鲜血淋漓。我也刨过山芋,但从来没有受过伤,外婆也没有。
山芋片要拎到村后面的山坡上晾晒,每隔一两天,就要翻一下,不然另一面吸入草地里的湿气,很容易生霉。如果一直不下雨,经过十来个日头,就会晒得很干很脆。但老天常常不讲理,会突然从空中往地上倒下大滴大滴的雨。雨从天而降,人影就像变戏法似的,从屋子、学校、地头冲出来,发疯一样往山坡上跑,拼着命,把仰晒在坡地上的山芋干扒拢到一起。原本白净净的山芋干,连泥沙、杂草和雨水被装进筐子或袋子,要是老天接连几天不开眼,山芋片基本上就会发霉,不能吃了。遇到这种情况,不光我外婆,换成任何人家,都会心疼得要命。有一回,小河子家晾晒在一大片山坡上的山芋片被雨水淋透了,他的妈妈哭得很伤心,小河子站在雨中,指着广播骂:他妈的!做天气预报的人哪有本事啊?他们就是看看屋里的墙根和屋外晒的腊肉,要是没回潮,就说不会下雨,回潮了,就说要下雨,他们尽瞎扯,嘴巴不烂掉才怪!
山芋片顺利晒成山芋干后,就要往家收。大人们弯着腰收山芋干,小孩子扎在一起,在山坡上打滚,玩跳房子游戏,还有的在石头边挖个洞,架起柴草,把山芋干放在上面烤。山芋干不好烤,边沿很容易烤焦,需要不停地翻动,火候把握好的话,烤好的山芋干特别香,也很脆。收山芋干大多在傍晚,夕阳照在山坡上,照着枯黄、柔软的草,一缕缕烟在山坡上飘,小孩子的尖叫声和大人的斥骂声交织,山芋干的香味和糊味在山坡上飘浮。那也是除了双抢之外大司村最热闹的一个场景。
山芋干要比山芋片轻得多,我十来岁的时候就能把两筐山芋干从山坡挑到家中,先倒进一个大缸里,盖上一个大的簸箕,再压上一块石头。但可恶的老鼠总会有办法咬穿簸箕,跳进缸里,啃啮山芋干。有一次刚搬开石头,掀开簸箕,发现两只老鼠正在缸里贼眉鼠眼地盯着我,我想把它们吓走,但这两个东西怎么使劲,也无法从光滑的缸壁上爬出来,后来还是隔壁的小铁头聪明,他用一把长长的大扫帚将这两只可恶的家伙从缸里挑了出来。
山芋干可以放在饭头上蒸,也可以用来煮稀饭。稀饭里的山芋干,既软又有些咬劲,吃起来很香很糯。冬日的早晨,大人们上了头遍工,回来吃早饭,他们端着饭碗,聚在门口的日光下,热气腾腾的碗里盛着的都是山芋干稀饭,一碗山芋干稀饭吃不饱,就再吃一碗,两碗山芋干稀饭下了肚,人的头上有热气冒,脸也红扑扑的。一般的人家,基本上是早上吃山芋干稀饭,晚上也吃山芋干稀饭,只有中餐才会煮干饭,说是干饭,其实饭头上还是要蒸点山芋干当饭的。我们家的稀饭有时没吃完,外婆一定会留着第二餐吃的,我让她倒给猪吃,她舍不得,说:“你家公、大舅他们那时要有一碗山芋干粥,就不会把命丢了。”
父亲一般在年前都要来外婆家挑一两回山芋干,每次两大麻布袋。冬季正是青黄不接的关口,我老家那里的很多人家常常只吃两顿。我有一次跟着父亲回去,路过老家边上的一个村庄,很多人跟我父亲打招呼,他们似乎都知道他从我外婆那里挑来了山芋干,一位老人站在路边,咂着嘴:“声传有个好丈母娘,多有福气!”
父亲把山芋干挑回家,山芋干的香气也会飘进其他人家,有几个人就上门央求我母亲带他们到大司村借山芋干,母亲不好拒绝,那几家的男劳力低着头,挑着空空的稻箩,跟着我母亲,走过四五十里山路,赶到大司村。母亲挑了几户孩子少的人家说明情况,那些人家尽管口粮不多,但没有人说二话,总是匀出一些山芋干来,那几个男人第二天都挑着装满白白的山芋干的稻箩,昂着头回去了。
第二年夏天,我老家的人割了稻子,碾成米,首先想到的就是归还大司村的口粮债。当时借的不过是区区的几十斤山芋干,却是救命的粮食,虽然谁也没有打欠条,但按照事先的约定,都会给足斤两,有的人还会顺带用木桶装一些他们在水田里捉来的泥鳅送给人家,算是额外的感谢。
时隔很多年,大司村还和我老家的大庄村还有来往。都是因山芋干而结缘的人,如今都老了,他们见面时,还会说到往事。大庄的人说:“我们那时真是困难,你们的山芋干帮了我们大忙!”大司村的人这样答:“哪家不会有难处呢?你们给我们带了好多泥鳅,那时的泥鳅真是好吃啊!”
熬糖稀
进入腊月,大司村的人家就准备熬糖稀了。
熬糖稀用的不是米,而是山芋。山里的水田不似圩区的多,田里长出的稻子填饱一家人的肚子本来就很难,哪能像圩区人那么大方,舍得用米熬糖呢!但山里有山场,每家都有几亩地,种大豆,种高粱,也种山芋。
山芋从地里全部刨起来后,就碼在堂屋里。早上蒸满一大锅,人吃一半,猪吃一半;晚上家里煮稀饭,山芋也是锅里的主角,这样的“硬食”,可以耐肚子也可以省米。临近冬天的时候,剩下的山芋就要放在地窖里,留作腊月里熬糖稀了。
在我去外婆家之前,外婆是不熬糖稀的。一个人熬什么糖呢——别人问她时,她总是这么答。我去了她家之后,她就把山芋省下来,到了冬天就放在柴火堆里,用草盖好,隔个十天半月,又会掀开草和柴火,看看山芋们有没有被冻伤。山芋的伤是会传染的,有了伤的山芋要赶紧取出来,轻伤的,剜去伤处,用来煮稀饭;全身烂得差不多的,只好扔掉了。
熬糖稀的前一天早上,外婆将所有的山芋从草窠里摸出来,一一洗净。鸡叫的时候,她就起床了。先把山芋煮烂,然后在屋梁上悬上一只纱布袋子,将煮烂的山芋和汁水一齐倒进去,此时的袋子鼓囊囊的,像饱满的帆,汁水先是哗哗地往袋子下面的桶里流,越流越细,外婆的双手不停地晃动着袋子里的山芋渣,最后用双手使劲地拧,直到渣子里再也没了汁水。
熬糖稀就是熬汁水。汁水倒进锅里,天已大亮,我也起床了。我要做的就是给灶塘添火。添火是门技巧活。刚开始的汁水很稀薄,有些绿,需要旺火烧煮,这时可以用松毛或者枯树枝,但烧了几个小时之后,汁水慢慢浓了,颜色也渐渐泛红,有气泡不停地冒,此时则需用小火,否则沸腾的汁水很容易溢出锅外。失误当然难免,外婆一边“扬汁止沸”,一边呵斥我赶紧用柴灰盖住火,这么一做,汁水果然不再往外溢了。
熬糖稀是个苦差事。人不能分神,更无法跑出门外跟别人闹,时间坐长了,脸上滚烫,腰和腿都酸胀得很。外婆为了让我耐住性子,就用锅铲在锅边铲一下,此时铲下的是汁水的结晶,我咬下来含在嘴里,虽然硬硬的,还有些粘牙,但一股甜味却是直逼心底。
汁水熬成糖稀,一般都是次日的鸡叫时分,虽然眼皮发紧,全身麻木,但还是强“熬”着,因为锅边及锅底的最后“结晶”是最有诱惑力的。灶塘里不再添火了,外婆将糖稀慢慢地往坛子里舀,这时火烬还在发挥余热,烘烤着锅边的结晶,待糖稀全部被舀尽之后,锅的四周已结满了厚厚的一层,铲起来,咬一口,甜得嗓子直发干。
糖稀虽有了,但并不意味着就会去做米糖。村西头,几个外地来的汉子早已搭起了锅灶,小铁头和六三家的米糖已做了好几天,但外婆似乎一点儿也不急。我不好意思向别人要米糖吃,但耐不住嘴馋,不时掀开坛子盖,用筷子蘸一点儿糖稀尝尝,坛子边沿因而满是筷子上滴下的糖稀。外婆决定做米糖的那天早上,双手刚摸上坛子沿,就发现手上沾满了糖稀,她气呼呼地骂了一句:“哪有你这么好吃的伢!你大舅小时候多乖!”
大舅我从来没有见过,我还没出生他就死去很多年了,但每到过年做米糖的时候,外婆总会有意无意地提到大舅。我知道她心里一定想着大舅,虽然她从来不说。我也默不做声,只是悄悄地搬着一只箩筐,跟着她往村西头的作坊走去……
芝麻粉
那几天,哥哥去放牛,我也跟着去,他先把我托到牛背上,然后牵着牛,往圩埂那边走。
往圩埂那边是开阔的田野。圩埂脚下是大片的芦苇荡,密密实实的,各种颜色的大大小小的鸟不知躲在哪丛芦苇里,会突然飞起来,在空中发出或凄厉或激越的叫声。与芦苇荡相连的是一望无边的稻田,风过的时候,青青的禾苗翻卷着绿色的浪,一波一波的,一直滚到眼睛追不上的地方。圩埂的另一边是条河,叫“老西河”,清清的水里能看到游动的鱼和晃动的水草,还有一些挂着帆的船在里面来来往往,有的靠人在岸上背着缆绳往前拉,有的开着发动机,突突突地在水面划行。那些船在很长的时间内让我着迷:它们往哪开?能一直开到海里去吗?有时太阳落山的时候,背船的人还没停下来,我就想着他们真是太可怜了——晚上在哪睡觉呢?
大司村地处山区,我老家则是在圩区,夏季是圩区最美的季节,纵横交叉的河道和沟汊里开满了荷花,白色的、粉红的、紫红的荷花们像在共赴一年一度的盛大聚会,热闹得不得了。水里有藕,有莲蓬,有菱角,有鸡头果。摘菱角的大多是姑娘和妇女们,她们坐在腰子盆里,用两只棒槌一样的小划子在水中划动。嫩的菱角可以生吃,既脆也甜;老的,可以烀熟了吃,又粉又香。哥哥和那帮放牛的孩子对莲蓬和嫩藕更感兴趣,他们一个猛子扎进水里,就会踹出来一截嫩藕。但鸡头果就不好惹了。它们藏在淤泥里,需要用脚踹,但它们的外壳上长满了刺,一不小心,脚就会被刺着。剥开时,需要用指尖顺着它们张开的小小的嘴巴,慢慢地扯。剥开了壳,是一粒粒圆圆的果子,老的呈黑色,嫩的粉红,再咬开就是白色的米。那些天,看着哥哥他们在水里游来游去,我的心很痒,但还是忍住了,我前几天往河里跳的时候,撞伤了腿,掉了一块皮,伤口没有好,不敢下水,好在哥哥他们谁也没拿那些果实当稀罕物,不时地把几个莲蓬和几截藕扔到岸上来,让我在岸上坐享其成。
我的腿快好的时候,地震的传言越来越多。有一天,大队的广播里播出了一个通知:可能要地震,家家户户都要在空旷的地方搭个防震棚,白天在里面吃饭,晚上在里面睡觉。
我们家的防震棚就搭在屋子前面的一块空地上,用树棍和竹竿作支撑,顶上盖着稻草。棚子不大也不高,仅够放两张床,人要进去的话,必须弯着腰。天太热,棚子就像罐头盒,我们弟兄三个晚上都不进去睡觉,而是把凉床和门板抬到外面当作床。
父亲和母亲带着小妹妹还是在棚子里睡。除了他们三个人,村中的一位独居的六七十岁的老太太也住进了我们家的防震棚。老太太有两个儿子,各自的家都搭了防震棚,但两个儿子都不大孝敬,老人就跑来跟我母亲商量,问能不能住在我们家的棚子里,我母亲说,怎么不照(行)呢?照啊!
按照大队的通知,家家户户还要准备些干粮。母亲炒了一些小麦,还炒了些米泡,放在一个铁桶里,准备在地震发生时作为全家的口粮。天快黑的时候,老太太来了,还端来一个搪瓷缸。她把搪瓷缸放在桌子上,对我母亲说,先梅,这些粉是我今天磨的,有芝麻,还有熟糯米,给伢子们吃。她边说边揭开盖子,一股香气马上就冒了出来。
七岁的弟弟当时正立在旁边看母亲洗碗,他的鼻子立马被香气擒住了,他二话没说,伸手就抓了一把粉塞进了嘴里,可能是塞得太多,那些干粉在他的嘴巴里裹着,吞不下去,也吐不出来,他的嗓子就那样被阻隔着,没办法吸气,他仰着头,翻着白眼珠子,脸霎时就开始发青,母亲虽然没见过世面,但她向来遇事不慌,她顺手掬起洗碗盆里的水,倒进弟弟的嘴巴里,然后不停地拍打着他的后背,弟弟终于将米粉吐了出来。
老太太那天晚上吓得不轻,不停地跟我母亲赔罪,说差点闯了大祸,我母亲哈哈大笑,说,这个屁伢子真好吃,这回没吃到好东西,倒是喝了不少脏水。
弟弟是1969年生的,他刚满月的时候发大水,风雨交加,我和哥哥被父亲抱进一只大腰子盆里之后,母亲把尚在襁褓里的弟弟递给父亲,没想手一滑,母亲下意识地曲着双腿,正好夹住了他,他这才没被洪水卷走。
大水退了以后,父亲便给弟弟取了个名字:正水。也算是和“水”有缘分。
责任编辑 包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