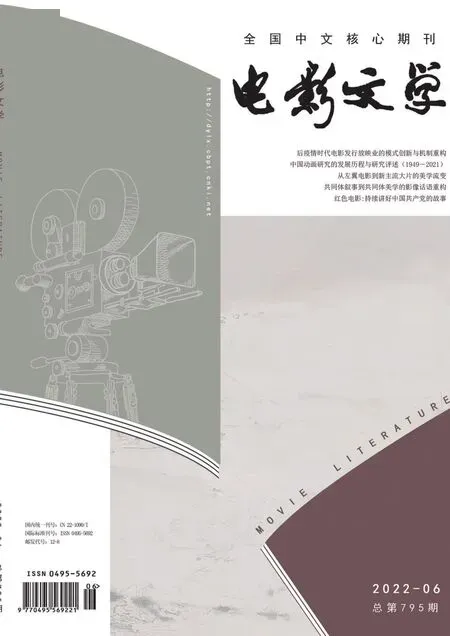《兰心大剧院》从文学到电影的表达策略探析
胡 伟
(辽东学院,辽宁 丹东 118001)
文学作品与影视作品的联系一直非常密切,很多知名的影视作品都是在文学作品的基础上进行改编的,文学作品不仅能为影视作品带来已成体系的故事框架、丰富的人物形象等,让影视作品在二次创作中带来很多便利,如果是拥有高人气的文学作品还会为影视作品带来一定数量的观众,对于影视作品的推广起着一定的助推作用。近年来,我国很多影视创作者都选择对文学作品进行改变,将文字视觉化呈现,赋予作品新的生命,电影《兰心大剧院》便是其中的代表之一。与很多影视作品不同,《兰心大剧院》所选择的文学作品《上海之死》并不是拥有非常深厚读者基础的小说,原著作家虹影虽是享誉世界文坛的华人作家,但《上海之死》并不是其代表作,这为电影工作者带来了更多二次创作的空间。导演娄烨是中国第六代导演的代表之一,是一位极具个人风格的导演,其创作的《浮城谜事》《推拿》等都是有口皆碑的作品,电影不同程度地表达出爱情、犯罪、悬疑等内容,让影片呈现出明确的类型倾向。在《兰心大剧院》中,娄烨运用了极具其代表性的黑白画面、交叉的叙事方式等,为观影者带来视觉冲击和心理体验,将原著小说用全新的方式进行呈现。本文将从叙事策略和影响策略两个方面阐述《兰心大剧院》从文学到电影的表达策略,以期为今后文学作品影视化的改编提供思路。
一、丰富多样的叙事策略
文学作品以文字为表达方式,影视作品将文学作品进行改变,需要将文字的内容转化为视觉符号,在这个过程中就需要将叙事策略进行改变。《兰心大剧院》建立在原著《上海之死》故事框架的基础上,对很多细节内容进行了改编,让整部作品从叙事视角、叙事空间等方面呈现出丰富、立体的效果,从而用更加视觉化的方式表现出原著文字的主旨。
(一)多样化的叙事视角与内容表达相结合
涉及历史题材的电影,很多都会选择几条故事线交织推进、对比进行的叙事方式,这样的方式不仅能为观众留有一丝悬念,同时从整部电影的呈现上也更为立体,逐渐推进的几条故事线索最后交织到一起,让观众在影片的后半部分将之前的线索进行组合,让电影的结局更具新意。《兰心大剧院》的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上海的法租界是为数不多没有被日本人占领的地区,这就决定了在这样一个并不大的区域中,会有代表多方利益的人出现,因此,从不同的角度叙述故事就成为这部电影的关键。女主角于堇最广为人知的身份是女演员,但除此之外,她还是接受过专业训练的间谍。在原著《上海之死》中,对于于堇的个人背景阐述得更为全面:从小父母去世,被法国人收养,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嫁给了多金的倪泽仁,后因信仰不同而分道扬镳,后接受养父的安排前往香港,接受专业的间谍训练。如此丰富的经历决定了于堇一定是一个很难猜测她究竟代表哪方利益的人,原著小说中复杂的人物关系为电影的从多种视角进行叙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让观众在观影的过程中不断猜测:于堇返回上海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不同的视角能带给人不同的视野,它们在某一层面上极大地影响了叙事的客观性、真实性和完整性。《兰心大剧院》整部影片从始至终都将多样化的叙事视角与内容表达相结合,故事不是从某个单一角色的视角呈现,让故事更为立体、生动。影片开始部分,将于堇召唤回国的养父代表美国的利益,在他看来,于堇是能为自己利用的一个高素质的间谍,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紧盯着于堇的白云裳和莫之因代表了国内不同利益集团,他们迫切想知道于堇回国的目的是不是营救身陷囹圄的前夫,加之后来出现的因于堇像去世的妻子而被于堇利用的日本人,不同的利益代表者不仅表达出在当时那样一个纷繁复杂的时代背景下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也让观众在观影的过程中站在不同角度了解到了原著文字中表达出的人物属性,从而更客观、全面地展现出了叙事的对象,将文字转化为影像的功能最大化满足了观众的观影需求。
(二)更具层次性的叙事空间与内容表达相结合
叙事学研究是存在着两个维度的,一个是时间维度,一个是空间维度,空间维度可以体现在影视剧的创作中。从《兰心大剧院》的影片名就得知:戏剧是这部电影的重要符号,女主角于堇是一位知名演员,男主角谭呐是一位导演,两人之间的故事因戏而生,整部影片都围绕着戏剧进行,最终故事的高潮也是发生在兰心大剧院中。戏剧本身就有强烈的冲突,借助戏剧,《兰心大剧院》设计出了“戏中戏”,将现实与戏剧相联系,成为影片最吸引观众的部分之一,这也是电影与文学作品最大的优势之一。
戏中戏设计得最为巧妙的一点是将兰心大剧院的舞台与于堇、谭呐约会的船坞酒吧这两个戏剧与现实的不同空间联系在了一起,看似是从两个空间讲述故事,实则两个空间是相互联系,推动观众不断思考的。兰心大剧院的舞台布景复制了船坞酒吧的空间布局,加之来来往往的群众演员和酒吧中的客人,让观众在观影中不断地思考:这究竟是戏剧还是现实。不同的叙事空间与丰富内容表达相结合让这部电影充满了层次性。
《兰心大剧院》的“戏中戏”中,男女主角在不同空间中别无二致,唯一能进行区分的是谭呐的眼镜:摘下眼镜时是导演谭呐,戴上眼镜时是戏剧中的谭呐。对于细节的观察与反思增加了观众在观影过程中的趣味,这样有趣的设计也是文字很难呈现出来的。剧院舞台与现实中酒吧的相似设计成为“戏中戏”的关键,加之故事内容的加持,让“戏中戏”的效果更为出彩。影片中的第一个场景,男女主角邂逅的戏码被暴力打断,穿过走廊和楼梯,二人牵手进入了另一栋黑暗的建筑。影片的结尾,二人从剧院的大舞台逃出,穿过重重的现实阻碍,退回到他们在第一场戏里跑出的地方,与影片的开头相互辉映,不仅表达出了二人对于演员和爱情的承诺,更是用这种首尾呼应的方式将戏剧与现实相连接,让影片更具连续性。
影片的高潮是日本特工前往兰心大剧院追杀于堇,台上的演员还沉浸在剧本和表演之中,破门而入的追杀者已开始朝演员开枪,此刻台下的观众误以为开枪的同样是演员,这些因于堇慕名而来的观众还在感叹戏剧的真实性,直到看到慌忙逃下台的演员和台下被误伤的观众时,才反应过来:这并不是戏,而是现实,也纷纷落荒而逃。此刻的观影者和影片中的观众一样,同样经历着赞叹、疑惑、慌乱的过程,沉浸式的体验带给观众更好的观影体验。
二、影音结合的影像策略
文学与电影的最大区别就是对于画面的呈现,画面语言既包括画面的构图、光效、色彩、影调、运动、节奏等,又包括画面与画面之间的主题架构,具有信息传递、故事叙述、感情流露、思想阐述等功能。《兰心大剧院》的导演娄烨是一位拥有个人风格的导演,不同于其他导演四平八稳、中规中矩的拍摄画面,娄烨导演的电影经常使用手持摄影机拍摄,电影画面的色彩也以黑白等暗色系为主,让其作品极具个人特色。
(一)创新性影片构图的运用
色调是一部电影带给观众最初、最直观的感受,色调的呈现强化了电影的主题和基调,娄烨电影中常见的元素:低饱和度的冷色调也出现在了《兰心大剧院》中。基于原著小说的故事背景,整部电影都是充满矛盾、紧张的,因此,以黑白为主的色调更能凸显出电影的整体基调。无论是人们所穿的服装,还是他们所处的环境,都是以冷色调为主,彰显了特殊年代下人们的压抑和不安。当故事情节进入到紧张激烈的阶段时,雨的出现更渲染了故事的萧瑟,突出了人们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的内心的寒意,让整部电影充满了忧郁的气质。
娄烨作品中的另一个特点便是手持摄影机拍摄,与机械辅助拍摄出的效果不同,手持摄像机拍摄出的效果会让一些观众在观影的过程中感觉到没有那么的四平八稳,因此,很多人对这样的拍摄手法持反对意见,但不可否认的是,手持摄影机拍摄出的效果是符合《兰心大剧院》的故事主题的。娄烨认为手持摄影的更大意义在于它给出了更真实的生命体验。在动荡不安的时局下,人们不知道未来将面对什么,电影中人物的表情、内心、情感等细节在手持摄影机的拍摄下一览无余,让观众感觉好像一切都发生在眼前,观众如果能体会到这一点,便会沉浸在这样拍摄手法下呈现出的视觉效果中,对当时人们的感受更能感同身受,会获得更好的观影体验,而这样由视觉带来的沉浸式体验是电影相较于文学作品的优势之一。
(二)衬托性影视音乐的呈现
电影从来不仅是视觉的艺术,声音作为电影中必不可少的元素之一,好的音乐在电影中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如何选取适合电影主题的音乐,对于电影创作者来说是一个非常有难度的任务,因为它不是简单地堆砌在影片之中,而是要与影片内容融为一体。《兰心大剧院》的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上海法租界,当时生活在此处的人来自很多国家,加之故事的主要场所是剧院,其观众是追求生活品质的人们,两种因素相加使得爵士乐成为电影中出现频率最高的音乐。当于堇与谭呐在剧场彩排时、二人在酒吧约会时,都出现了符合当时时代特点和品位的爵士乐。而轻松、悠扬的爵士乐与以黑白为主的电影色调搭配在一起时,更是突出了当时上海法租界与外界的格格不入,人们貌似生活在一个稳定的环境实则未来会有更多未知的矛盾境地,看似轻松的爵士音乐的呈现,实则衬托了整部电影紧张、矛盾的氛围。
一直以来,文学作品与影视作品的结合都是人们所探讨的话题之一,文学作品为影视作品带来了已经初具体系的内容框架、丰富立体的人物形象,但在影视化的过程中,很多读者却对影视作品不满意,究其原因是在将以文字为代表的文学作品转化为以声音影像为主的影视作品的过程中出现了偏差。娄烨作为中国第六代导演的代表之一,电影画面、拍摄手法等成为他的标签和名片,《兰心大剧院》在将原著小说改编的过程中,将画面、拍摄手法、“戏中戏”这些他本就擅长的手法运用其中,加之原著故事中丰富的故事人物促成的多样化的叙事视角、导演巧妙的音乐上的选择,都让这部作品呈现出了故事性、丰富感官体验等特点,让观众在观影的过程中,不仅能够身临其境地体会到电影中人物的经历,也促使他们不断地思考故事将朝着什么方向发展。无论是从叙事策略,还是从影像策略方面,《兰心大剧院》对于今后文学作品影视化的改编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