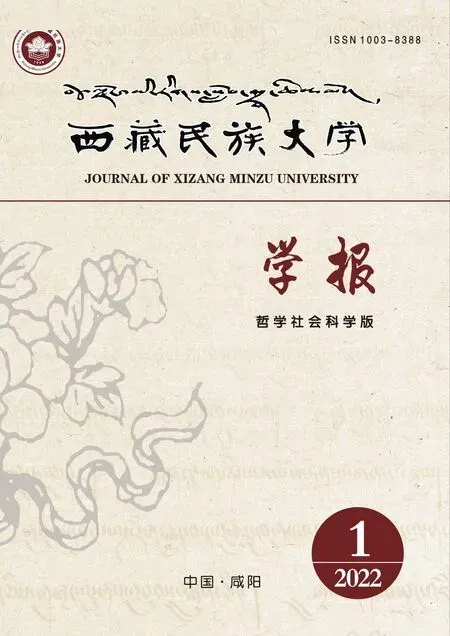炕与灶:青藏高原烟火味生活技术中的文化交融
郝世亮,范琳俐
(1.西藏民族大学法学院 陕西咸阳 712082;2.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北京 100872.;3.西藏民族大学教育学院 陕西咸阳 712082)
中华民族是在中国大地上生息的不同民族群体在历史长河中不断交往交流交融形成的民族共同体,在广袤的国土上处处留存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印记。千百年来,青藏高原及其周边区域各族人民在山峦、河流与绿洲构造的交通廊道中通过政治、经济、军事、技术的和文化的碰撞交流形塑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民族社会共同体,涵育了多民族文化交相辉映、互嵌融合的日常生活文化形态。一般而言,承载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印记的载体有两种,一是包括文字史料、墓葬、建筑、碑刻等在内的各种物质性文化遗存,二是俗民的日常生活文化。学者们通常在讨论中国西部地区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历史线索时多关注前者,而后者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从历史和现实看,中国不同民族群体在日常生活领域中的技术与文化的相互采借、吸收、转化和融合的历史源远流长。特别是在“民族走廊”地带,俗民“烟火味”生活技术与文化流变的地理文化现象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程际遇和历史进程密切相关,其投射的丰富文化意涵和社会意义有待我们进一步深入理解和分析。“烟火味”生活技术是指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掌握与应用的用于炊饮、取暖和寝卧一套民间技术,它是俗民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组成。
文化是历史的建构。[1]文化功能论认为,人类群体在不同地域空间上的区隔化生存涵育了形态各异的生产生活技术和文化类型。文化传播论则认为,文化与技术的传播是社会得以形成的工具,人类发展的历史就是文化与技术传播的历史,是人类关系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机制。[2](P10)综合论则认为,技术与文化的地方性创造机制和跨区域传播机制同时发挥作用。当行走在广袤的西北地区和青藏高原时,我们发现与炕、灶有关的烟火味生活技术与文化的多样化形态中既渗透着不同民族人民的独特生存智慧与审美情趣,也透射着各民族人民技术文化互借交融的印记。在青藏高原不同区域,烟火味生活技术演化出了不同形态和组合。如在青藏高原与西北高原交界地区,火炕和灶炕结合技术早已融入各族农户的日常生活;在青海省游牧民安居点,我们既可以看到牧户对火炕和灶炕结合技术的广泛应用,也可以看到有的牧户依然沿用着牧区传统的烟火味生活技术;而在西藏自治区则少见火炕和灶炕结合技术的踪迹。
那么,该如何解释青藏高原两省区藏族农牧区居民烟火味生活技术流变的差异性和复杂性呢?火炕、灶炕结合技术在青藏高原地区的传播与分布背后又有怎样的源流与历史线索呢?在不同地域、不同历史时段,各民族人民烟火味生活技术与文化的多形态演化背后的动力机制是什么呢?本文尝试走近青藏高原多个区域的居民日常生活文化场景,结合人类学与区域社会史的“草野历史”分析视角,在空间中理解时间,以火炕、灶以及灶炕结合技术的变迁、传播为线索来搜寻和理解青藏高原农牧区居民日常生活文化变化历史脉络中的多元文化交融印记,并尝试讨论推动这种日常生活文化交融的动力机制。
一、行走的火炕:灶、炕及灶炕结合技术的源流与传播
考古研究发现,人类的制灶技术应远早于造炕技术,在灶炕结合技术出现之前灶与炕的演变经历了漫长过程。从中国境内不同时期人类活动的考古证据可以推断,史前人类对火的控制技术与制灶技术应是同步出现的。如在半坡遗址中,考古发现了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聚落在茅屋内挖掘浅坑作灶的实物证据。考古发现,火炕技术的历史也很悠久,在中国北方地区和东北亚国家均发现古人使用火炕的实物遗迹证据,在古罗马文明遗址中亦发现“热炕取暖系统”遗迹。[3]从目前考古成果看,中国火炕技术遗迹大多分布在北方地区,尤其是在东北地区发现了反映火炕形态演化完整链条的系列考古证据。考古研究表明,中国境内的单烟道火炕雏形最早于新石器时代出现在绥芬河流域和辽河平原,华北等其他各地区的单烟道火炕至迟在秦汉时才出现,北方草原地区则出现较晚。西北地区“自史前至秦汉时期,在建筑遗迹中发现的取暖设施除了地面上的灶坑外,以壁炉为主”。[4]研究者结合现有考古证据和文献推断,火炕技术可能源于生活于中国东北地区的古人类聚落,该技术向中原地区、西北地区的传播是金元以来北方民族南下、西渐的产物。考古研究为中国境内火炕的起源与传播提供了线索,但没有足够证据精确地描绘火炕传播的时间节点和具体路线。就目前考古发现看,青藏高原前现代人类活动遗迹中还没有火炕技术应用与传播的明确实物证据。
现存中国汉文文献中亦有反映火炕技术分布和传播情况的诸多记载。如汉代班固所著《汉书》之《苏武传》中记载了匈奴医者在苏武自刺后拯救其生命的场景:“凿地为坎,置煴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5](P178)据此推断,匈奴医者用到的施救设施应为一种古老原始的火炕。据笔者了解,此种原始火炕技术在当代中国北方寒冷地区依然有传承印记,一些牧人或猎人在秋冬季野外露营时会制作这种简易火炕来御寒取暖。唐代释慧琳在其所著《一切经音义》中写道:“炕,乾也,考声云上榻安火曰炕,从火,亢声,或作亢”。[6]经求教专家,笔者推测“上榻安火曰炕”一句中“炕”应是与北方农村“火盆上炕”取暖设施以及西南地区彝族聚居区的“火炕床”形制相似的设施,在这些区域的传统民居中,人们常在房屋内土炕或木床之上设置火盆来取暖或烹饪。晋代刘昫在其编著的《旧唐书·东夷高丽传》中记录了高丽人“其俗贫窶者多冬月皆作长坑,下燃煴火以取暖”。[7]宋、辽、金、西夏等政权并立时期,汉文文献中关于炕的记载明显增加。关于灶和烟囱的修建制度的最早汉文记载则出现于北宋土木建筑师李诫所著的《营造法式·卷第十三·泥作制度》。[8]《大金国志·熙宗纪》记载:“金初,尚无城郭,星散而居,太宗尝浴于河、牧于野,屋舍车马衣服饮食之类与其下属无异,所独享者惟一殿,名曰乾元,所居四外栽柳以作禁围而已,其殿宇(绕)璧尽置火坑(按:此即今之火炕也,此字出于俗语本无正字,故或从火,或从土),平居无事则锁之,或时开钥,则与臣下杂坐于炕”。[9]《大金国志·初兴风土》篇记载金人“穿土为床,煴火其下,而饮食起居其上”,其《婚姻篇》记载“妇家五大小皆坐炕上”。[9]南宋范成大在其诗作《丙午新正书怀十首》中写道:“厉风翻海雪漫天,百计逃寒息万缘。稳作被炉如卧炕,厚裁棉旋胜披毡”。范成大既有南方为官的经历,也有北上处理金国与南宋王朝政治事务的经历,此诗对炉、炕、棉、毡的描述也是现知少有的对南北方烟火味生活技术差异进行呈现的文献。据以上文献可以推断,至少在宋、辽、金时期,排烟道与灶、炕结合的泥作建造技术已经发展定型,并在中国北方地区广为应用。
元、明、清三代各类史书、方志、碑记、诗文、戏曲、小说等中涉及火炕的文字纪录数量非常多,对炕的称谓包括“北地煗牀“”土炕“”火炕“”炕”等。如至元十年(1273)所立的山西大同“下华严寺”碑记中有“庆寿三年炕未氈(毡),叶落归根来不言”之语。[10]耶律楚材所撰《湛然居士集》中有“牛粪火熟石炕煖,蛾连纸破瓦明”之语,[11]王实甫所撰《破窑记》已有关于炕的描述,等等。明代胡谧撰《山西通志》、涂山辑《明政统宗》、徐光启撰《农政全书》,万历年间编撰的《定襄县志》,以及《金瓶梅》等各类流传于民间的笔记、小说中也多有关于火炕的文字。
清代文献中关于炕以及灶炕结合技术的记录则更为翔实。如清代山西《河曲县志》对河曲地区炕灶结合技术有详细记载:“河邑乡村依山而穴土为窑亦有砌石成者,诗所谓陶复陶穴是也,穴居者夏不畏暑,冬不畏寒,凡窑屋有火炕、地炉,烧炭炉中,火气传土炕而过有烟洞引之达于户外。炉之妙,不扇而风,不呼而吸,竈(灶)则前后二炉相通,前炉爨,而后炉炊,便于日用,然宜用炭火,若柴火,则其势立烬,不能炊之”。[12]民国时期编撰的大量地方志中关于炕的记载内容比以往更为丰富。根据这一时期地方志中反映信息可以看到,中国东北、华北、华中、西北以及四川、安徽等地均有火炕与灶炕结合技术分布。当代中国,包括东北地区、黄河流域农牧业区与农牧业混合经济带、西北五省等地域在内的广大农村,一种兼具烹饪、取暖、寝卧等功能的“锅头连炕”灶炕结合技术设施是大多数农村地区家庭的必备设施。[13]结合已有考古发现和汉文文献材料,我们可以大致推断中国境内火炕与灶炕结合技术源起与传播的一个粗略线索,即在数千年历史进程中,伴随着大大小小政权的碰撞与交流及不同地域各族人民的流动与迁徙,火炕与灶炕结合技术从北至南,从东到西,逐渐传播开来。
粗览现存文献,笔者发现鲜有汉文文献记载了青藏高原地区火炕与灶炕结合技术的分布与传播情况,在当代学术研究中也鲜有专题研究关注这一现象。事实上,青藏高原特别是青海省内黄河及其支流湟水流域农业区与农牧结合经济带,火炕与灶炕结合技术分布广泛。关于青海省灶炕结合技术的文字描述多在文学作品中出现,也有文化研究者对此进行过简单描述。如蒲文成曾描述过青海河湟地区被冠以“家西番”称谓的藏族农民家中的“锅头连炕”,文中写道:“在家西番人家……厨房与卧室相连,用矮墙相隔,锅头连炕,既能煮饭,又能取暖”。[14]传统卫藏地区即拉萨、日喀则、山南等地极少见到火炕,在各类留存文献中也鲜有相关记载。张荫棠曾在其撰译的《藏俗改良》关于西藏地区移风易俗论述中谈到过炕,文中有“兄妹姐弟叔嫂婶妇不得同炕夜卧”语句。[15]结合其他文献,笔者推断张荫棠在文中所提到的“炕”应是关于卧具的泛指性概念,而不是专指土炕或火炕。当然,我们不能武断地推论说西藏地区在历史上就从来没有土炕或者火炕。如在地处拉萨市八廓街的“更敦群培纪念馆”中就能看到在他的起居场所还原场景中就有土炕的存在。
时间指针滑向21 世纪,随着国家推动游牧民定居工程的实施,火炕与灶炕结合技术也走进了青海地区藏族、蒙古族等游牧民群众的定居点。笔者实地调研发现,西藏自治区境内亦有零星的火炕与灶炕结合技术分布,分布地域多处西藏自治区与四川省、青海省的交界地带的昌都市东北部农牧区。如笔者发现昌都市江达县邓柯乡沙嘎村很多居民家中就有火炕与灶炕结合设施。另据报道,西藏也有政府技术部门推动的实验性太阳能热炕技术的零星分布。但就整个地区而言,该区大部分农牧业地区人民的烟火味生活技术形态带有明显地域色彩,人们用于取暖、炊饮与寝卧的设施大多分开建造火设置,火炕或灶炕结合技术并没有在西藏得到规模性应用。显然,青藏高原不同地域的烟火味生活技术的变迁与发展存在差异。
二、区域特质与技术传统:青藏高原农牧区传统的烟火味生活技术
在中国广袤国土上,居于不同气候带、不同地域的人们发展出了丰富多样的生产方式与烟火味生活技术。据最新考古研究发现,青藏高原东部距今至少16 万年前便有丹尼索瓦古老型智人活动,曾在这里生活的古人类聚落的用火与制灶技术历史也应非常久远。[15]在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共同影响下,生活在高原不同地域的藏族人民逐渐创造形成了体现独特生存智慧、审美品位的日常生活技术,涵育了一种具有内在一致性与外在类同性特征的烟火味生活技术传统与人文共识。[15]同时我们注意到,青藏高原独特的自然条件同时孕育了游牧生活文化和定居生活文化,在两种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下人们的烟火味生活技术各有特点。
(一)定居生活与烟火味生活技术
农业生产与定居文化有机统一。青藏高原种植业历史久远,距今有五千多年历史的昌都卡若遗址中就发现了谷物种子。另据《吐蕃王朝世系明鉴》记载,吐蕃时代的青藏高原腹地农业大约始于布袋巩夹(当于公元2-3世纪)时期。[17]今青海河湟地区,西藏自治区拉萨、日喀则、山南、阿里、昌都等地的河谷地带均有悠久的农业发展史。种植业的发展孕育了定居文化,青藏高原先民们因地制宜地创造了多样化的定居建筑技术和烟火味生活技术。如林木资源丰富地区的人民多建造木作房屋,少林木地区居民则多选择以泥、石、木等混合材料来修筑房屋。在旧社会,贵族阶层和其他富裕阶层家庭多在家中安置“三围靠背式”坐卧两用落地木床(文化学者多习惯称之为“藏床”),农奴和其他贫苦人家多用石、木、兽皮、卡垫等搭建简易矮床用于寝卧。从传统藏式木床的彩绘装饰和形制看,其彩绘装饰中融入了中原文化与高原文化交融的各类符号,如龙、凤、花、鸟及宝瓶等图案;但其形制与内地常见木床有较大差异。在取暖和烹饪器物方面,藏族人民在房舍内、外用泥、石、砖混合材料修造炉灶,修造工艺多样。其中在青藏高原地区最为流行的炉灶是如图1所示的长方体造型炉灶,其燃料箱与火塘相连,便于牛羊粪等生物燃料的添加,火塘上方设立炊具支架,下设一小出灰口。在昌都、林芝等一些多林木地区,人们则习惯在木房地板上架设石、铜或铁质火盆做灶,以牛粪、木柴或木炭为燃料,在房顶开孔作烟道,烹饪和取暖皆赖于此。近年来,随着青藏高原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速和人民增收,群众对于烟火味生活技术的选择也更加多样化,农业定居区有的藏族家庭用铁制或钢制炉替代了传统泥灶,燃气炉、电炉等炉灶也逐渐进入普通百姓家庭。

图1
(二)游牧生活与烟火味生活技术
游牧民群众逐水草而牧形成了适应于游牧生产的烟火味生活技术。在青藏高原牧区,牧民群众多以牦牛毛织造的“黑帐篷”为居所,选迎阳近水处安扎帐篷。在帐篷内的炉灶设置上,有的牧户就地取材选用石块或草皮搭建简易灶,有的采用石制、铜制或生铁带足落地火盆作炉灶,有的则修建泥灶,帐篷上方留有排烟孔。在卧具设置上,牧户会选用结实的干草皮、牛羊毛毡和各式卡垫等来作“床”,以藏被(或藏毯)、羊皮大衣以及各式棉芯或羊、驼毛芯被裹身保暖。20世纪80年代前后,随着交通改善与商品贸易便利化,牧户在居住、取暖、炊饮和寝卧生活物料上的选择也更加多样化。各类轻便的新式帐篷,铁质长条炉、便携太阳能灶、煤油炉、液化气炉以及便携钢丝床等逐渐走进牧人的日常生活。
在自然经济时代,自然条件决定生产方式,不同生产方式又孕育了不同烟火味生活技术。通过简要考察青藏高原游牧与定居两种生产生活模式下藏族群众烟火味生活技术的传统形态及当代变迁,我们发现如同其他文化类型一样,青藏高原农牧区人民逐渐形成了既契合于生产生活实际需要,又彰显民族性人文共识的一种相对稳定的烟火味生活技术与民俗文化形态。
任何形态的烟火味生活技术与文化都是依附于特定地理空间、历史际遇与人们生产生活的实践而存在的。“日常生活的空间性和实践性在本体上是一体的,空间关系并不是固定的实体,它是实践的不确定的关系。它不仅是历史性的关系,同时还向历史的变革敞开”。[18]历史变革始终是形塑不同族群生存空间、影响族际交往互动机会以及驱动技术与文化传播的强大力量。
三、族际交往与技术采借:青藏高原农牧交界地带烟火味生活技术变迁
文化传播论认为文化传播的范围决定于不同文化形态群体之间交往的持续时间和密切程度,不同族群聚落在地理上的连接必然有族际间的人口流动与技术、文化交流。从古至今,陇、川、陕、藏、青等地区交界区域一直以来就是多民族文化、技术交流与融合的地带。如甘肃临夏地区、天祝藏族自治县、甘南藏族自治州,青海河湟流域,四川省北部和西部等地区的农牧区交界带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混居的地带,各民族人口在地理空间上的接近性为火炕与灶炕结合技术的民间传播提供了条件。依据目前各类证据我们无法获知火炕与灶炕结合技术究竟何时传播到青藏高原。但是,结合西北地区与青藏高原地区的人口迁移史可以看到,至迟自汉代以来,特别是在元、明、清以及民国时期,传统农业区人口通过“民族走廊”自东向西、自北向南的自发迁徙以及由中原王朝组织推动的人口迁移过程中,火炕与灶炕结合技术也随之传入青藏高原地区。
调研发现,青海省湟水流域的民和县、乐都县、平安县、互助县、西宁市、大通县、湟中县、湟源县、海晏县,黄河流域的循化县、化隆县、尖扎县、贵德县,火炕与灶炕结合设施早已成为在这些区域生活的汉、藏、回、土、蒙古族等各族人民传统民居内的标配。有一首“青海花儿”唱词中道:“尕房里盘下个打泥炕,我俩儿,热热火火地睡上;尕阿哥活像是抹蜜,把蜜糖,甜甜蜜蜜地喂上”。[19]流传于民国时期的青海民间故事《占炕》记载:“有一天,几个不同地方的人来住店,店里只有一个热炕,他们都想睡。其中一个人提出条件说:‘谁说个自己家乡的啥好东西,谁就炕上睡。’甘肃(指今兰州辖区一带)人说:‘我们兰州有个木塔,离天丈八。’青海人接着说:‘我们青海有个老爷山,仰天躺下揣着天。’凉州人说:‘我们凉州有个钟鼓楼,半截钻在天里头。’河州人说:‘我们河州没有啥,这个尕炕我占下。’说完就睡在炕上了”。[20](P165)这些材料生动记录了在新中国建立之前陇、青多民族混居地区火炕融入各族百姓日常生活之中的民俗现象。
笔者调查发现,青藏高原地区农户的火炕与灶炕结合设施的结构形态、功用基本一致,但不同地域在建造工艺与材料选用上有一定差别。如多产青石板岩的青海省民和、乐都两地居民习惯将板岩加工成石板来作炕面;少石地区居民则多采用“打泥炕”技术来夯筑火炕,也有农户自制方块状土坯和长条状水泥板来作炕面。烧炕则多用农作物秸秆、羊粪等生物燃料。自20 世纪90 年代以来,以煤、电替代生物燃料的各类新式节能吊炕逐渐流行起来。笔者发现,西宁和格尔木两地的一些城居民他们虽住在楼房但依然对热炕情有独钟,很多人家在楼房中建造水暖炕和电暖炕。
在火炕和灶炕结合技术传入青藏高原的同时,各族人民的日常饮食习惯也相互影响融合。有研究者观察指出,青海“川水地区的农民称山地农民住的是锅头连炕,吃的是青稞面干粮,更多的是指受藏族影响的汉族农民”。[14]结合其他资料,我们发现在很长的时间内,青稞面干粮不仅是藏族人民最为喜爱的粮食食品,它也是甘、青、宁、新等省区汉、回、土、蒙等各个民族群体传统饮食结构中的重要构成。就这些区域居民的日常食物种类的易获取性和品类数量而言,农业区或农牧业交界地带的食物来源多样性要高于牧区,这就造成了青稞食品在不同地域人民日常食谱中所占分量的不同,对农业区群众而言它是“副食”,对牧区群众而言它则是“主食”。概而言之,从青稞炒面在西北地区与青藏高原的流行可以看到,饮食选择主动适应了气候、地理、生产方式和物产结构。
四、国家工程与技术引入:安居工程与青藏高原牧区烟火味技术变革
在一定意义上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国家推动的一系列经济社会改革与建设是国家牵引的影响国土全域、每个民族、每个家庭甚至是每个个人生活际遇的现代化进程。在此进程中,青藏高原的俗民日常生活方式和生活文化受到巨大影响,在青藏高原的游牧区群众的烟火味生活技术与文化的变迁中,我们更能清晰地感受到这一点。结合现有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资料看,火炕与灶炕结合技术“规模性”进入青藏高原腹地牧区的历史起点应是国家规划实施的游牧民安居工程。同时,我们注意到安居工程的实施对青海省和西藏自治区两省区牧区群众烟火味生活技术变迁所带来的影响并不相同。
(一)青海省牧区安居工程与牧区群众烟火味生活技术变迁
2005年底,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五中全会作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决定。随后几年,青海省、四川省、甘肃省、西藏自治区等省区陆续实施牧民安居工程,自此青藏高原牧区群众的日常生活方式开始加速转变。从2009年起,青海省以国家财政补贴与村民自筹相结合的方式为全省11.3万户共计53万人建设了安居房,部分州县安居房建设采用了节能炕、太阳能暖廊等技术。如在青海省刚擦县的藏族牧民安居点,安居房房屋主体结构为单排双坡屋顶平房,房屋迎阳侧建有贯通式附加阳光间,部分家庭卧室内建有节能炕。在工程推进过程中,当地政府在房屋设计和实际建设中综合考虑了青海农牧业区人民生产生活的实际需求、地方性技术传统及农牧民群众对新事物的接受度,将火炕技术带到了牧区安居点,受到了牧区群众的欢迎。
刚擦县沙柳河镇藏族牧民多吉向笔者谈到了他家修火炕的故事,他说:“我们的房子是政府组织工程队建造的,我们周边几个州的房屋样式都不一样,我们是这种有暖房的砖房。政府只负责盖房子,盖起来的时候没有炕。我到我亲戚家睡过他们的炕,舒服的很。后来我亲戚帮我请了好像是海北那边来的师傅们来给我们砌的炕,厨房里的灶和炕连在一起,我们这不确牛羊粪,烧起来方便的很”①。同时,也有很多群众在家中自建了实心炕,没有建造火炕或灶炕相连的设施,秋冬季取暖和平日烧水做饭多用室内独立架设的金属火炉。可见,青海牧区人们对火炕与灶炕结合技术的接纳是一个自主选择的过程。同时,随着居住方式的变化,定居点牧户的饮食习惯也发生了变化。在刚察县沙柳河镇潘保村安居点村民措毛家,她家的日常食谱与青海一般农区家庭几乎没什么区别,如早饭食谱中包括大米粥、奶渣、酥油茶、鲜奶和糌粑;午饭和晚饭则多吃各种荤素面条、揪面片或炒菜米饭;节庆或待客时会做油炸果子、人参果(蕨麻)米饭等。牧区传统食物与农区食物在牧区定居家庭中自然而然地融合到了一起。

图2:青海省刚察县沙柳河镇牧民安居点的黑帐篷与阳光安居房②
(二)西藏安居工程与农牧区群众烟火味生活技术变迁
2006年,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相应国家政策研究决定在“十一五”期间加快实施以“牧民定居、农房改造和扶贫搬迁工程为重点的农牧民安居工程”。[21]西藏有关部门通过广泛研究讨论确定了安居房设计的基本原则,即“提高农牧民住宅建筑水平,引导农牧民建设实用、经济、美观、安全且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风格的新型住宅”。[22]西藏自治区建设厅在“拉贡”(拉萨贡嘎机场沿线地段)民房改造工作经验的基础上,会同自治区农牧民安居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自治区建筑勘察设计院和拉萨、日喀则等七个地市建筑设计院统筹负责设计了全区各地的安居工程。在设计过程中,不同地区安居工程房屋在外观、结构、装饰和空间功能布局上充分考虑了当地传统建筑特色和人民生活实际需求。其中,在部分地区安居房建造中采用了玻璃阳光暖房热能辐射采暖技术。房屋内采暖、炊饮设施和家居陈设不在统一规划建设范畴之内,由农牧民自主安排,藏族农牧民群众多采购金属火炉用于取暖、烧水和做饭,寝具则选用自造或采购的藏式木床。概而言之,无论是政府主导的房屋建造,还是群众自主安排的室内生活设施的选用都在本土化经验与习惯范畴之内。
当然,西藏自治区也有数量极少的节能炕技术分布。如2009年,在自治区有关部门的主导下,定日县扎西宗乡拉隆村建设了一批实验性“节能建筑”,该建筑在主体房屋南侧建造了被动式阳光间,同时配套建造了卵石蓄热太阳能炕。但这种实验性节能炕并没有在西藏得到规模性推广。
农牧民安居工程的成功实施极大地改善了青海与西藏两省区农牧民群众的生活条件和生活品质,尤其对游牧民而言,安居工程的实施对于他们生活方式转变的影响是革命性的。同时我们发现安居工程实施后,青海、西藏两地牧民群众的烟火味生活技术变化则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样态,受到青海定居牧民欢迎的火炕与灶炕结合技术并没有在西藏自治区安居工程中得到应用。笔者通过访谈当时参与两省区安居工程建设的有关人员,总结了造成上述差异的原因。一是党和政府在推进安居工程时充分考虑到了各地人民的主体性意愿,充分考量了人民日常生活的功能性需求、生活习惯、审美偏好以及群众对引进性技术的接受度。青海省人口的民族构成多样,是典型的多民族杂居区,在长期的族际互动交往中,牧区群众对农区流行的火炕及灶炕结合技术有一定的认知,在思想上易于接受这种新技术。一些青海籍游牧民在过上定居生活后,他们经过观察对比,发现火炕有效利用了当地生物燃料,有效解决了屋冷床凉的实际问题,越来越多的牧户便主动选择引进了火炕技术。二是不同省区在安居工程建设中有很强的自主性,地方文化、知识和技术传统决定了决策者和设计者的设计理念和技术认知。长期以来,西藏地区与邻近省份的交流因受自然环境与交通条件的限制,绝大部分西藏籍藏族群众对火炕技术的认知近乎空白,更谈不上对此技术的接纳、引入和使用了。因此,在青海省各地常见的火炕及灶炕结合技术没有进入西藏自治区安居工程推动者与普通群众的视野就在情理之中了。
结 语
通过粗略观察青藏高原不同时期、不同区域藏族农牧民人民烟火味生活技术的变化历程,我们可以看到青藏高原人民的生活智慧以及民俗偏好,也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国家、现代化、族际交往以及技术传播等结构性要素构造的历史际遇中多元文化交融对人民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巨大影响。综合前文分析,我们发现青藏高原地区灶炕技术以及灶炕结合技术的传播大致有两条路径。一是民间族际交往推动的技术采借式传播。其多发生在青藏高原多民族杂居的农业经济带、农牧业混合经济带和农牧业交界地带。从千百年青藏高原与内地互动关系的总体趋势看,它是大大小小的聚居族群共同体的生存生活空间在地理上由相互连接逐步替代彼此隔离的过程,各民族人民大大接触交往为烟火味生活技术和文化的传播与交融提供了历史机缘。正如萨林斯指出:“复制社会文化体系的不是社会化和仪式,而是日常生活的实践”。[23](P117)青藏高原地区民间烟火味技术的传播是各族人民在生活技术的“工具箱”里自愿选择的结果。二是国家工程牵引的技术引入式传播。如果说农牧业经济交界杂糅地带的不同民族群体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的自发性联结为各民族团结涵养了文化心理条件的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持续推动的国家一体化现代化进程则为各民族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开启了全新篇章。国家牵引的现代化进程特别是牧民安居工程的实施,烟火味生活技术的传播为青藏高原人民日常生活的历史性变革注入了新的动力。但是,国家在安居工程实施中并没有搞一套标准、一套方案,充分尊重了雪域高原不同地域人民的习俗、习惯和审美偏好,同时充分发挥了各个地区在工程实施中的自主性。无论是民间自发的技术采借还是国家推动的技术引入,在青藏高原不同地区人民烟火味生活的传承与变化中,我们都能深切地感受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带给各族人民日常生活体验的实实在在的好处、便利和多元化的技术选择。
[注 释]
①访谈地点:青海省刚察县;时间:2019 年 7 月 18 日;受访者:多吉,刚察县人,男,藏族,48岁。
②图片为作者在青海省调研时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