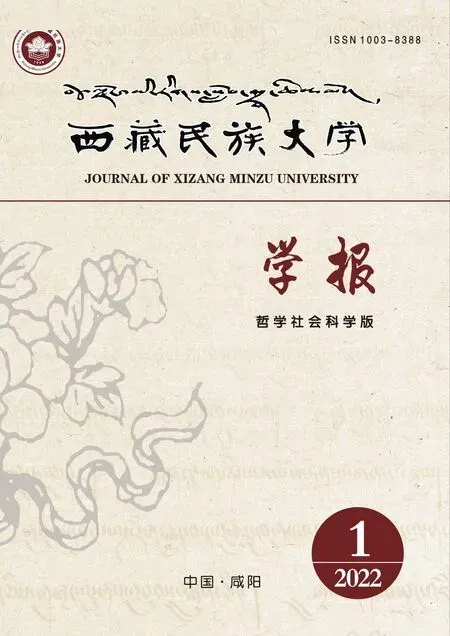谢灵运自“乌衣之游”至外放永嘉前的心态变化
孙习阳,王军涛
(1.西藏大学文学院 西藏拉萨 850000;2.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 陕西咸阳 712082)
一、青少年时期的孤傲任性与好奇豪奢
谢灵运出生并成长于晋末宋初,这一时期政治混乱、讨伐不断,正所谓“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1](P177)这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思想的整体状况及变迁,对谢灵运性格、心态和思想的形成及变化无不具有深刻的影响。与此同时,他的家庭出身、士族特权与贵族生活,也导致了他自幼便形成了孤傲任性与好奇豪奢的性格特征和生活习性。
谢灵运出身于东晋权势显赫的世家大族,其从曾祖父谢安曾立下赫赫战功,被追封为庐陵郡公,同时封安弟谢石南康公、子谢琰望蔡公、侄谢玄康乐公。同日一门封四公,历代所未有,荣耀至极,谢家一跃而为甲族之冠,如张溥所言:“谢氏在晋,世居公爵,凌忽一代,无其等匹。”[2](P169)灵运自幼就聪慧过人,所以深得其祖父谢玄的宠爱。《宋书·谢灵运传》中记载:“灵运幼便颖悟,玄甚异之,谓亲知曰:‘我乃生瑍,瑍那得生灵运!’。”[3](P1743)然而,谢灵运的出生对谢家来说却是喜忧参半,他出生十天其从曾祖父谢安去世,又数月后其伯祖父谢靖、父谢瑍去世,所以灵运被家族称之为“子孙难得”①。所以,在谢玄去世后,四岁的谢灵运便被送至钱塘著名的道教徒杜明师家中,接受的仍然是贵族式教育。“隆安三年(399),十五岁的谢灵运由钱塘杜明师处至京师建康。袭封康乐公②,授员外散骑侍郎”[4](P389),此后,直至元兴三年(404),即谢灵运16岁至20 岁,一直居住在谢氏家族旧宅“乌衣巷”③,享受着士族特权。这种与生俱来的社会地位和殊荣,也使得他性格中自然而然就滋生了一份孤傲与任性,“据《宋书·谢灵运传》的记载,谢氏是从少年时代就被世袭的贵族生活宠惯坏了的一个骄奢子弟。”[5](P246)灵运为人极其狂傲、素少交游,所以与其交游者亦多为谢家同宗弟子。《宋书·谢弘微传》有载:“混风格高峻,少所交纳,唯与族子灵运、瞻、曜、弘微并以文义赏会。尝共宴处,居在乌衣巷,故谓之‘乌衣之游’④,混五言诗所云‘昔为乌衣游,戚戚皆亲侄’者也。”[3](P1591)在乌衣巷交游走动的皆是高人一等的士人名流,这是因为在当时的门阀制度下,士族与非士族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莫说士人与庶民之间有天壤之别,即便是做了高官,倘若非士族出身亦不敢和士人一起并坐。如若想成为士人,哪怕亲得皇帝的圣谕,也需要得到士族的认可与首肯。如《宋书·蔡兴宗传》中记载:“元嘉初,中书舍人秋当诣太子詹事王昙首,不敢坐。其后中书舍人王弘为太祖所爱遇,上谓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当判耳,殷刘并杂,无所知也。若往诣球,可称旨就席。’球举扇曰:‘若不得而。’”[3](P1584)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唐代诗人刘禹锡所咏诗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深刻内涵了。
谢灵运的孤傲任性还通常表现在他的为人处世上。如他与人论辩锋芒太露,“(王惠)素不与谢灵运相识,尝得交言,灵运辩博,辞义锋起,惠时然后言。时荀伯子在坐,退而告人曰:‘灵运固自萧散直上,王郎有如万顷陂焉’。”[6](P630)事实上,谢灵运与不纳访客、“印封如初”的王惠素不相识,初次见面论辩,灵运这种“辞义锋起”“萧然直上”而不留一点情面的表现,充分显示了他孤傲任性的性格特征。谢灵运的孤傲任性还表现在他喜好任意褒贬人物上,“灵运好臧否人物,混患之,欲加裁折,未有方也,谓瞻曰:‘非汝莫能。’乃与晦、曜、弘微等共游戏,使瞻与灵运共车,灵运登车,便商较人物,瞻谓之曰:‘秘书早亡,谈者亦互有同异。’灵运默然,言论自此衰止。”[3](P1558)另外,谢混还时常提醒灵运要克服“博而无检”的缺点,如谢混所评“阿远刚躁负气,阿客博而无检,曜仗才而持操不笃;晦自知而纳善不周,设复功济三才,终亦以此为恨!至如微子,吾无间然。”[3](P1591)作为叔父的谢混正是因为对灵运关爱有加,所以他的教诲往往对灵运既恳切又重要。谢混还曾为韵语以奖劝和警戒灵运、瞻等:“康乐诞通度,实有名家韵,若加绳染功,剖莹乃琼瑾。……数子勉之哉,风流由尔振,如不犯所知,此外无所慎。”[3](P1591)
除了孤傲任性以外,灵运还时常表现出好奇豪奢的一面。事实上,谢家作为当时的世族,其子弟的衣着、吃喝、行为举止等无一不是绮襦纨绔、“钟鸣鼎食”⑤、铺排讲究过度。首先是着装的妖冶,从谢玄开始就“好著紫罗香囊。”[6](P863)其次是吃喝的豪奢,堪称挥金如土,如谢安与子侄辈往来游集时一餐的酒菜每每都要花费上百金。《晋书·谢安传》中这样描述:“每携中外子侄,往来游集,肴馔亦屡费百金。”[7](P2075)又《南史·谢弘微传》中所载:“上以弘微能膳羞,每就求食。”[8](P552)再者就是举手投足的夸张,如谢裕为了保持自己居室的整洁,他的痰唾不吐到痰盂而吐到左右的衣服上。《南史·谢裕传》:“景仁性矜严整洁,居宇净丽,每唾辄唾左右人衣。”[8](P529)显而易见,谢灵运的好奇豪奢是有家族渊源的。同家族成员相比,他的豪奢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性奢豪,车服鲜丽,衣裳器物,多改旧制,世共宗之”,不仅喜欢在车上装饰一番,而且穿衣装扮上亦甚是讲究,乃至引领当时的风尚潮流。再如他每次出游尤其讲究排场,“四人挈衣裙,三人捉坐席。”[3](P884)灵运的这些做法还被时人编成歌谣传唱,又被沈约作为咎徵写入了《宋书》的《五行志》。
通过对谢灵运青少年时期孤傲任性与好奇豪奢性格因素形成的分析,不难看出他深受当时的社会风气、门阀政治、家庭出身和贵族教育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这种性格在他以后的人生经历和处世方式上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如“自谓才能宜参权要,既不见知,常怀愤愤”[3](P1753)的孤傲;“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游遨,遍历诸县,动逾旬朔,民间听讼,不复关怀。所至辄为诗咏,以致其意焉。在郡一周,称疾去职,从弟晦、曜、弘微等并与书止之,不从”[3](P1753-1754)的任性;“灵运因父祖之资,生业甚厚。奴僮既众,义故门生数百,凿山浚湖,功役无已。寻山陟岭,必造幽峻,岩嶂千重,莫不备尽”[3](P1775)的豪奢好奇。这种性格亦直接影响了谢灵运以后的人生命运、诗文创作及心态。
二、“风流由尔振”的积极用世心态
“元兴年间,桓玄篡晋,政局动荡不安。元兴三年(404),刘裕、刘毅、何无忌、刘道规等相与合谋起兵反桓玄,众推刘裕为盟主。……安帝回建康,以琅琊王司马德文为大司马,刘裕为侍中、车骑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徐、青二州刺史如故。……安帝又以刘毅为左将军、都督淮南等五郡军事、豫州刺史,何无忌为右将军,其他讨逆功臣也各有封赏。”[7](P256-259)缘于此,可知饱经祸乱忧患的东晋王朝,总算暂时安定下来。在此情形下,作为谢氏家族这样的名门望族是不可能缺席的。其实,“晋末以来,几家最高的门阀士族,以谢氏影响最深,潜力最大,所以谢氏人物参与政治的机会,也较其他家族为多。”[9](P189)此时作为谢氏家族代表人物的谢混可谓是洞若观火,他瞅准了安帝复位后诸事一任由司马德文调理的绝佳时机,便不失时机地将谢灵运、谢瞻以及谢弘微一并送入琅琊王府中任职,以期晚辈能够乘势而起,这就是前文中谢混所说的“风流由尔振”的真实用意所在。这样一来,21 岁的谢灵运于义熙元年(405)任琅琊王大司马行参军,始入仕途。
其实,谢混将谢灵运引入仕途是带有很强的政治目的和家族意识的,是与谢氏家族重视儒学的传统分不开的。“作为一个在两晋南朝传承十数代的世家大族,陈郡谢氏虽表现出了鲜明的名士色彩,并以此形成了其家风的显著特征,但在宗族内部,谢氏与其他大家族一样,仍然有着坚实的儒家礼法传统。”[10](P153)灵运自“乌衣之游”时就受到叔父谢混的关爱和提携,在乌衣巷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从小也就濡染着浓重的家族文化,被强化着以重振家族为己任的意识。所以,谢灵运也是带着“芝兰玉树生阶庭”的人生理想和家族观念步入仕途的,他在后来所作的《答中书》诗中也曾提到:“伊昔昆弟,敦好闾里。……仰仪前修,绸缪儒史。”⑥这也恰恰验证了灵运自“乌衣之游”时便与族人一起接受了儒家经典的教育和熏陶。
灵运初入仕途第二年,遭遇了重大的家族变故和政局动荡,即“义熙二年(406),灵运追随豫州刺史刘毅,任记室参军。灵运在刘毅帐下一待就是六、七年,他仕于刘毅的几年间是政情最不安定的时期。……义熙八年(412)九月,因刘毅和刘裕的斗争,谢混以‘扇动内外,连谋万里’的罪名被诛。十月,刘毅被刘裕先遣军王镇恶、蒯恩部打败,自缢死。”[4](P403)谢混和刘毅的失败,使得谢灵运无论是在家族中还是在仕途上都失去了靠山,这对他的打击之大不言而喻。回过头来看,不管当初灵运改投刘毅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抑或是出于其族叔谢混的举荐,但事实上都证明了他改投刘毅的选择是错误的,并且由此埋下了祸根,对灵运一生的仕途发展和心态变化都有极大的负面影响,可谓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对此李雁先生认为:“如果说刘毅的死使灵运在仕途上失去了政治上的靠山,那么谢混的死更使他失去了心理上的凭依,此后灵运进退失据,时常任性而为,再无人能对他有所节制或指点。这也是热衷与追求权力的谢灵运却不能与当政者很好地合作的重要原因之一。”[11](P30)
由此看来,谢灵运初入仕途便深陷政治斗争的漩涡而不能自拔。原本他是怀着重振家族的美好愿景步入仕途的,然而政治上的错误选择和失败导致事与愿违,甚至还使其陷入险境。尽管事实上刘裕也并没有问罪于他,义熙八年(412)十一月,太尉刘裕入镇江陵后,还是听从申永“除其素衅,倍其惠泽,惯叙门次,显擢才能”[3](P2278)的建议,为了安抚受到伤害的谢氏家族,改授谢灵运为太尉参军,以示宽宏大量,不计前嫌。此时灵运的处境着实令人堪忧,他最终不得不面对现实,做出顺从刘裕的选择,毕竟“谢灵运之所以没有归隐而又转主而侍,是因为他并没有放弃现实中的政治追求,没有放弃重振家族的希望。”[12](P187)
三、入刘裕帐下到外放永嘉前的失意矛盾心态
东晋义熙八年(412)到南朝宋永初三年(422),这期间是谢灵运在江陵、建康等地为官时期。灵运28 岁入刘裕帐下为太尉参军。义熙九年(413)二月底随刘裕归京,出任秘书丞,但不久即被就地免职,这是灵运仕途上第一次去职。《宋书·谢灵运传》中记载:“毅伏诛,高祖版为太尉参军,入为秘书丞,坐事免。”[3](P1743)义熙十一年(415)正月灵运复出,任刘道怜咨议参军,后转为中书侍郎。次年(416)八月,改任世子刘义符中军谘议。义熙十三年(417)正月,刘裕亲引水军发彭城西讨,灭后秦。这年冬天,灵运“奉使慰劳高祖于彭城,作《撰征赋》”[3](P1743)。赋中对刘裕不乏溢美之辞,“相国宋公,得一居贞,回乾运轴,内匡寰表,外清遐陬……宏功懋德,独绝古今。”(《撰征赋》)义熙十四年(418),刘裕为相国、进封宋国公后,便任命灵运为宋国黄门侍郎,迁相国从事郎中。元熙元年(419),灵运由彭城回建康,充任世子刘义符左卫率,因擅杀门生桂兴,被免官。永初元年(420),再次复出降公爵为候,任散骑常侍,后转任太子左卫率。永初三年(422),被权臣徐羡之和傅亮诬为“非毁执政”而贬官至永嘉。
纵观谢灵运追随刘裕以来官职的不断变迁,虽然也曾被免官两次,但也不曾被刘裕刻意排挤。可是,按常理来推测,谢灵运追随刘毅多年,当然不可能再受到刘裕的信任和重用。而且灵运孤傲任性的性格让他始终以谢安、谢玄作为自己崇拜的门阀政治家,始终希望以自然超脱的姿态出现在政治的高位上。可是,出身寒门的刘裕执政以后,便转而对门阀士族采取了打压的政策,所用人物委以实权者都是有实干能力且绝对服从者。而像谢灵运这样仍坚持门阀士人从政风格的士人,对于以军功起家的寒素族的刘裕及其他出身低微的实权人物,是不可能从心底里认可的,所以灵运当然也就难以受到统治者的重用。更何况在刘裕心目中,谢灵运只不过是一空疏文人,“朝廷唯以文义处之,不以应实相许”[3](P1753)。这点他跟后世李白的遭遇颇为契合。然而,他作为高门贵族子弟尚有拉拢的价值。其实,“在晋宋皇权复兴之际,谢氏这样的家族,对于皇权说来,既最有利用的价值,又最具生事的危险。”[9](P189)所以,刘裕对灵运采取的策略便是仅以文人相待而不给予实权。刘裕的这种做法,灵运心中自然抱有不满。一方面他对刘裕仍抱有幻想,期盼能建功立业,一展抱负,并对刘裕大加赞赏,如“良辰感圣心,云旗兴暮节”(《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虞承唐命,周袭商艰。江之永矣,皇心惟眷”(《三月三日侍宴西池》)。另一方面,他又心怀忐忑,“惜图南之启运,恨鹏翼之未举”“身少长于乐土,实长叹于荒馀”“苦邯郸之难步,庶行迷之易痊”(《撰征赋》),都道出他虽常怀兼济天下之志,而不能施展抱负的焦虑。
通过对他这一时期大多数诗文的梳理分析,不难看出他的心态主要是失意和矛盾的,时常表现出仕与隐的矛盾心态和对生命的迁逝感,同时也抒发了内心有志不得伸的苦闷,这也与他“自谓才能宜参权要,既不见知,常怀愤愤”[3](P1753)的自诩和现实落差紧密相关。他的心情和境遇可以从他这时期的几首诗中流露出来,如《赠安成》中最后一章:“驽不逮骏,莸不间薰。三省朽质,再沾庆云。仰惭《蓼萧》,俯惕‘惟尘’。将拭旧褐,朅来虚汾。畴咨亮款,敬告在文。”此诗作于晋义熙十一年(415)夏,这是写给从兄谢瞻的,灵运在诗中对自己未能施展政治抱负而深感惭愧,也反映出了自己忧谗畏讥的心理,表白自己并不安心职守,准备挂冠隐遁。
《赠从弟弘元》中最后一章:“视听易狎,冲用难本。违真一差,顺性谁卷。颜子悔伤,蘧生化善。心愧虽厚,行迷未远。平生结诚,久要罔转。警掉候风,侧望双反。”此诗作于义熙十一年(415)冬,诗中表明自己违背本性而误入官场,内心感到惭愧。同时对自己的处境深感忧虑,对自己目前在京任职,流露出不满情绪,似有拂衣之意。
《岁暮》中写道:“殷忧不能寐,苦此夜难穨。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运往无淹物,逝年觉易催。”此诗大概作于义熙十二年岁末(416),其时刘裕屯兵彭城,即将西征收复洛阳,灵运奉诏前往彭城慰劳刘裕。诗中写作者长夜不寐,忧思难解,伤叹岁月如流,人生易老。诚然,“大谢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承袭了弥漫二百馀年具有时代意义的迁逝之悲的。”[13](P373)不过,结合当时的政治背景来看,这种消极情绪的产生,似与抱负不能完全实现有关。
《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中最后两句:“岂伊川途念,宿心愧将别。彼美丘园道,喟焉伤薄劣。”此诗是晋安帝义熙十四年(418)九月九日,刘裕在彭城戏马台为即将归隐的孔靖饯行,命群僚赋诗,灵运的诗才倚马可待,写下这首诗来赞羡孔靖已踏上归隐之道,伤叹自己薄劣不如。正是由于“自汉末魏晋以来,社会的动荡,政局的多变以及由此引致的政治迫害的频繁,使得尚隐的风气愈来愈浓,以至于社会普遍接受了隐高于仕的价值观……本来只是避祸全身的消极行为的归隐,便成了在精神境界上高出于仕进的一种选择,隐士当然也就是高士,而仕进者只能是俗人。由仕而隐,不仅有人生哲学上的理论支持,也为社会舆论所肯定;反之,外则为人讥责,内则愧疚于心”[14](P37-38),所以灵运才会发出如此感叹之语。
《彭城宫中直感岁暮》中写道:“草草眷徂物,契契矜岁殚。楚艳起行戚,《吴趋》绝归欢。修带缓旧裳,素鬓改朱颜。晚暮悲独坐,鸣鶗歇春兰。”此诗作于义熙十四年(418)岁末,是年,灵运担任宋国黄门侍郎,再转为相国从事中郎。元熙元年(419)八月,刘裕迁都寿阳。诗中显露了灵运极其低沉的情绪,这对于一个年龄尚不到35岁的人来说,正值人生壮年却感慨岁月易逝,人生将老,似乎显得太过于消沉和低落了。而即便杜甫有诗言“人生七十古来稀”,但三十多岁的年龄亦绝非暮年。这种年龄与心态之间的极不匹配与强烈反差,反倒更加形象鲜明地折射出他有志不得伸的苦闷心情与孤独之感。
通过以上几首诗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这一时期谢灵运的失意矛盾心态占据着主导地位。他之所以对自己的处境表现出了种种不满和极端消极的情绪,是因为他远大的政治理想和抱负无法实现。纵观这一时期谢灵运在仕途上的不称意与现实中的百般无奈,主要是因为“朝廷唯以文义处之,不以应实相许”的缘故,才使得灵运有了如李白一样“明朝散发弄扁舟”的归隐之心,或者说是作出了归隐的姿态,然而这一切并非出于其本意。假如归隐真是出于其本心,入世是“违真一差”,他又何苦两次被免官又两次复出呢?这说明灵运始终不能真正做到弃官归隐,只是发出“彼美丘园道,喟焉伤薄劣”的感叹遮人耳目罢了。再加之其生发出对岁月迁逝、人生易老的极度感伤,这种心理感受与其人生芳华形成的强烈反差,显得尤其不符合常理。所以,谢灵运这种对人生过度的焦虑显然不是出世的心态,反而印证了他强烈的入世心态。
[注 释]
①我国东南一带往往有寄子于人以求消灾避难的习俗,唯恐孩童不易成活而使之拜和尚、道士为师,或送入寺院、道观养育。
②晋末宋初,正是门阀之风极盛、士庶之别极严的时代。朝廷中的高级职位均由士族独占,王、谢二姓当时是数一数二的高门望族,其子弟不仅享有士族的世袭特权,而且有着与生俱来的爵禄。据《宋书·谢灵运传》的记述,谢灵运是晋朝车骑将军谢玄的孙子,谢玄曾经因为淝水之战大败苻坚,以勋封为康乐公。当他去世的时候,因为他的儿子谢瑍早卒,所以就由谢瑍的儿子谢灵运继承了康乐公的爵位,食邑有二千户之多。《宋书·谢灵运传》中描述他:“性奢豪,车服鲜丽,衣裳器物,多改旧制,世共宗之,咸称谢康乐也。”
③因其地位于都城东南,即三国时东吴乌衣营旧址处,故名。东晋时这里是陈郡谢氏的聚居之处。
④所谓的“乌衣之游”,就是以灵运族叔谢混为领袖人物的谢氏宗亲子弟之间的交游活动,他们在京城乌衣巷清谈玄理、商较人物、吟诗作文、宴饮歌咏,颇类今之“学术沙龙”。
⑤古代豪门贵族吃饭时要奏乐击钟,用鼎盛着各种珍贵食品。故用“钟鸣鼎食”形容权贵的豪奢排场。汉张衡《西京赋》:“击钟鼎食,连骑相过。”唐王勃《滕王阁序》:“阎闾扑地,钟鸣鼎食之家。”鼎:古代的炊具。
⑥以下所引谢灵运诗文均出自顾绍柏的《谢灵运集校注》,下文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