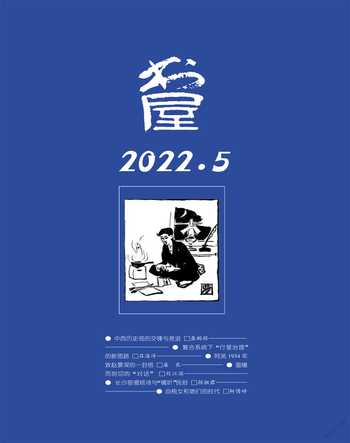苏轼与月
汤伏祥
月,情也;月,光也。在文人笔下,月无处不在。皓月如银,笛声弄舞;残月茫茫,寂静寥寥。在苏轼笔下,月也自然有一番情愫。月诱发了他的思想、他的诗情,也成了他情思的表达符号、再现符号,在“无意于佳乃佳”的境界里,留下了千古绝唱。
月,穿行于苏轼的词境,有如明月穿行于云朵。是月点亮了诗词,还是诗词给月增添了色彩,增添了情愫呢?当月与诗词交融后,苏轼的诗情、才情、思境、情境,以及跌宕人生旅程就跃然纸上了。在苏轼留存的词中,月一直相随左右。苏轼的词究竟有多少首呢,这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今以谭新红等人编著的《苏轼词全集》为准,谈谈“苏轼与月”。在《苏轼词全集》中,有词三百四十八首,其中点题“月”的有七十三首,约占百分之二十一。透过这些词作,苏轼把月写尽,月在苏轼笔下,是“思念之情”,是“孤寂之魂”,是“高远之境”,更是“希望之光”,是他人生的真实再现。
一
嘉祐元年(1056),二十岁的苏轼出川赴京,参加科举。自偏僻的西蜀沿江东下,路途跋涉了几个月,次年才得以进京。苏轼以《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正当名动京师、大展身手时,其母在四川病故。苏轼只好与苏辙随父苏洵回乡奔丧,守丧期满后又折返汴京。《浣溪沙》(山色横侵蘸晕霞)是苏轼为母守孝期满从眉州返回汴京“路过荆州北行出陆之时”而作,一般认为是苏轼最早的词作。“梦到故园多少路,酒醒南望隔天涯。月明千里照平沙。”每个远行的人,都注定会思乡,这是流淌在中华儿女血液中最活跃的基因。故土的滋养,亲人的嘱盼,沉淀在游子的内心深处,当触景生情后,就會一泻千里,这正像“明月千里照”一样,饱满的思乡之情跃然纸上。
月,或在云间穿梭,或高悬照射千里。地上之人与嫦娥遥遥相望,那嫦娥已然是亲人的化身。望月向来都是望亲人,望故园的。人与月这种遥不可及的距离,恰恰填满了苏轼的思念。治平三年(1066),苏洵病逝,苏轼、苏辙兄弟扶柩还乡。守孝期满,苏轼还朝,入京。时,王安石变法,苏轼与之政见不同,被迫离京,于熙宁四年(1071)改任浙江杭州通判。越三年,苏轼任山东密州知州。熙宁七年(1074)十二月,苏轼来到密州,一路旅途劳顿,次年正月十五作《蝶恋花》(密州上元),“灯火钱塘三五夜。明月如霜,照见人如画”,感怀在杭州时的生活。初到密州,思念故土、亲人之情感更是强烈异常。正月二十日,苏轼作《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明月幽静,千里孤坟,悼亡妻子,无处话凄凉,“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谁人不思亲,谁人不梦故呢?明月孤坟,思亲悲恸,读来情真真、心切切。
颠沛流离,是苏轼的人生写照。在不断变迁、动荡的人生际遇中,苏轼虽也任事一方,但大半时间漂泊颠簸在路途中。人,在得意之时也许会忘却故土,在喧闹中也许会忽略亲人、故友,但在孤月中,过往、亲人、故土、旧友就涌上心头。不管哪段旅途,月仿佛一直追随苏轼左右,诱发、催生他的思念,也寄托着他浓烈的人生情感。哪怕到了他人生的后半期,面对春事阑珊,感慨是“客里风光”,思念之情油然而生。夜静五更时,梅花梢上月亮仿佛都要被吹落了。作于元祐六年(1091)春三月的《定风波》(月满苕溪照夜堂)也是把月与思念写尽:“余昔与张子野、刘孝叔、李公择、陈令举、杨元素会于吴兴。时子野作《六客词》……凡十五年,再过吴兴,而五人者皆已亡矣。”人事沧桑,虽新作《六客词》,但思念旧友之情如同“长庚对月独凄凉”。
思念之情,把月写尽,不管是圆月还是残月、初月,苏轼俨然把月化作思念的音符,让才华在词中流淌,让月光在词中倾泻。我们读来,仿佛也走近他的人生羁旅。
二
于漂泊的诗人来说,月,自然是其永恒的歌咏对象。我以为,苏轼不仅把他的思念寄情于月,更是描绘了月的孤寂之魂,这魂恰如苏轼自身。孤独寂寞月影随,了无寒凉夜相伴。《华清引》(感旧)是苏轼由京城汴梁去凤翔途经骊山所作。当年唐玄宗与杨贵妃游览骊山,可谓盛极一时,“玉甃琼梁。五家车马如水,珠玑满路旁”。但一切都注定要成为过往,在苏轼笔下,曾经的辉煌也只剩下了垣墙,“独留烟树苍苍。至今清夜月,依前过缭墙”。或许孤寂原本就是一切的本真,一切的繁花终究凋零,留下的只有那冷清的月色。
苏轼确实有过得意的时光,当年他意气风发来到汴京参加科举,并受到追捧,春风得意,人世风华不过如此。但胜利的欢悅犹如一阵清风,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倒是因为母亲程氏去世,他在丁忧期间,得以与妻子王弗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或陌上游春,或登山揽云,或读书煮茶,或临溪对月。但苏轼绝非能如此平静生活一生的人,他注定属于远方,属于孤寂,正如那皎月一样,定是要高高悬空、照射四方的。于是,丁忧期满,苏轼与父亲、弟弟又沿途跋涉,再次抵京。时逢制科考试,苏轼“才识兼茂”,所著《留侯论》更是“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至其浑浩流转、曲折变化之妙,则无复可以名状”。
或许才气横溢者注定是孤独的,这有如天上之星,只能自己闪耀、自己旋转,不能与他人交集。尤其是处于高位,处于掌声后,一旦跌落,那跌入深渊般的感觉,其孤寂是无法名状的。“乌台诗案”后,已经过了不惑之年、在官场浸染二十余年的苏轼来到黄州“闭门却扫,收召魂魄”,他“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从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翛然,无所附丽”。但是,这般自省与清宁,大抵是因为“不可得”,是繁花凋尽的孤寂。苏轼初到黄州,曾寄宿定惠院,与山僧参悟宁静悠远,于是填下《卜算子》(缺月挂疏桐)。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残月挂梧桐,稀稀疏疏,苏轼悠然而过,有如那不肯归栖的孤鸿。月夜清冷,正如苏轼的心境。人生几何,谁不想成就一番事业呢?但事事难以遂心愿,几经劫毁,出仕时的意气风发早已磨灭,换来的是月的孤寂,以及这孤寂中的一点坚守、坦荡。这为后人所敬重,所追寻,后来文人墨客也常在不如意时望月感怀,以寄岁月苍茫、人生孤寂。
三
孤寂也许是人的本真、归宿。有限时光的生命,在面对无限的死亡,不管如何鲜艳,如何强盛,终将落尽,终将凋零,人生只是一段行程,最后都将化为尘土与孤寂的山川为伴。苏轼仰望星空的月,月就把孤寂洒向大地。不过,我以为在他的孤寂中,却寄托了他的高洁、高远。他高洁致远的心境、志趣、理想,有如明月当空,是许多没有经历苦难的文人所无法抵达的。
贬居黄州,苏轼虽为清贫,但安定无扰,也算怡然自乐,“寓居去江无十步,风涛烟雨,晓夕百变。江南诸山在几席,此幸未始有也”。这般山水,让苏轼多了几分惬意与诗情。“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临皋闲题》)苏轼不问圆缺,心中自有江月,自有一番天地。功名利禄也罢,尔虞我诈也罢,不过是奔忙不歇、岁月匆匆罢了。元丰五年(1082),苏轼作《满庭芳》(蜗角虚名):“蜗角虚名,蝇头微利……思量、能几许?忧愁风雨,一半相妨。又何须抵死,说短论长。幸对清风皓月,苔茵展、云幕高张。”不管繁花吹落,还是诗情画意,一切都是长短不等罢了。庆幸的是,有皓月相伴,清净而高洁、高远。清风皓月,就是他高远的情操、高远的天空。
同年七月,一轮素月起,清风拂面,水色连天,苏轼泛舟赤壁,作《赤壁赋》,又怀古作《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这气魄何等壮观,但“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煙灭……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江月依然是他高远的心境写照。他寄情于山水,寄情于江月,也似乎只有这浩瀚的江月能寄托他的心情,能映衬他的高远。
人生渺小,风雨常在,江月永恒。在面对浩瀚的星河,在面对高洁的江月。一切都显得苍白无力,“似花还似非花”,许多事情就是这样道不明、说不来的。但苏轼知道,万物皆有他的造化,只有把日子过出新意,才能与明月遥相映照,才能有诗和远方,也才能抵达自己的内心世界。江水悠悠,明月朗朗,一切都是身外物,“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前赤壁赋》)。高远、阔达、通透,明月如此,苏轼亦如此。
四
黄州几载,苏轼倒也豁达,闲情自乐。原本想“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但一朝入仕,宦海沉浮,许多事情就由不得自己了。元丰七年(1084),苏轼奉诏赴河南汝州就任。但一生都在赶路的苏轼无心前往,先是去筠州与弟弟苏辙相聚,而后至九江、往江宁、转泗州、去宿州。时神宗驾崩,太后摄政,苏轼不得不重新被推到了浪潮中,在宿州,他得令擢升,知登州。经过几个月的跋涉,到了登州,接着又接诏书,还朝任礼部郎中。到元祐元年(1086),苏轼更是仕途一片光明,在短短的几个月内连升几级,从起居舍人,到中书舍人,再到翰林学士、知制诰。对于这些,苏轼虽也知道风光,但他内心深处依然是清风明月。苦难时能屈能伸,得意时不恋不贪,都能坦然面对,此乃圣人。苏轼为什么能被后人所敬仰、所追寻,大抵也是因为如此。穷困潦倒也罢,富贵无边也好,不都是一段修行吗?
已经过了知天命之年的苏轼在元祐四年(1089)二度知杭州。我们后来人说苏轼豁达,是因为苏轼能笑对坎坷,能挺拔人生,高洁而致远。但就苏轼的为官履之道看,他所到之处皆受到百姓的爱戴,在百姓中享有声望,可谓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元祐五年(1090)四月,苏轼上书《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陂湖河渠之类,久废复开,事关兴运。虽天道难知,而民心所欲,天必从之。”五月复上《申三省起请开湖六条状》,言:“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盖不可废也。”端午时节,苏轼作《南歌子》(湖景),更是想象西湖之景色:“佳节连梅雨,余生寄叶舟。只将菱角与鸡头。更有月明千顷、一时留。”明月千顷,就是最为美好的。三分明月夜,月是美的象征,是希望的象征。
苏轼心系黎民百姓,千顷明月给杭州西湖以新的生机、新的诗情画意,也照亮了希望之光。这给我们今人留下了“苏堤春晓”的美景和佳话。不过,苏轼的一生都是颠沛流离的,他在漂泊中催老了岁月。知杭州才两年,他又被召回朝。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调任安徽颍州。元祐七年(1092)改任江苏扬州知州,一年半后,再改任河北定州知州。绍圣元年(1094),再被贬为(广东惠州)宁远军节度副使。绍圣四年(1097),年已过六旬的苏轼被一叶孤舟送到了荒凉之地海南儋州。宋徽宗即位后,苏轼相继被调为广东廉州安置、安徽舒州团练副使、湖南永州安置。元符三年(1100),苏轼复任朝奉郎。这年六月,在他北归的路上,他在云散月明的深夜,眺望江海,思绪涌上心头,写下了诗作《六月二十日夜渡海》:“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希望之光照万里,九死南荒都不值得记恨,明月仿佛照亮了前程,照亮了未来。深夜里,万千心事付诸江流,明月与希望同在,与无悔、倨傲、豪情、未来同在,也与苏轼同在。
月光如水,岁月静好,澄明如月,高洁辽远。月,生活在苏轼的时光里,贯穿着苏轼人生旅程的全部。皓月高远,遥不可及,月有圆缺,但永不停歇。或许正是因为月的遥远、永恒,在许多文人笔下,月是情的化身,是思念的化身,也是孤独的化身。但似乎没有谁能像苏轼那样,让月伴随左右,伴随人生起伏,伴随人生颠簸,伴随人生高远,伴随人生洒脱。月有多远,情便有多深,志便有多坚。“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月永在,苏轼便永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