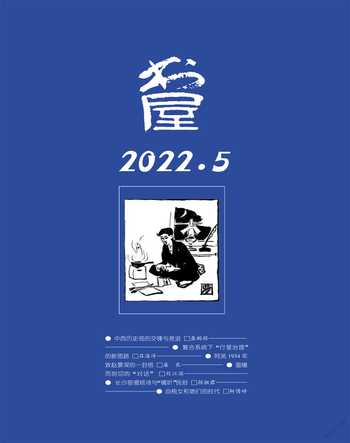中西历史观的交锋与竞进
龚鹏程
芸芸众生,各个不同,你的未来不是我的梦。
各族群也一样。中国人自古喜欢谈历史,有强烈的历史意识,故天然地以为每个民族都有历史。其实,古印度人就无历史意识、无历史观、也无史著,就像我们相信人都是父母生的,可是古印度人更常说是他自己轮回来的。
因为时间观不一样,生命观也就不同。
观念创造未来。因此大家分道扬镳,各走各路,各成风景。
一、无历史的社会
早期印度文化被称为吠陀文化(约公元前3000年到前600年),大致与两河流域文化及古埃及文化同时。
吠陀,意思是“知识”,但只是宗教的知识,中国古代曾将这个词译为“明”或“圣明”。此时传下不少文献,但其历史完全无从考查。
《娑摩吠陀》《耶柔吠陀》《阿闼婆吠陀》产生较晚,被称为“后期吠陀”,种姓制度大概此时已出现。崇拜梵天、毗湿奴、湿婆三大神的婆罗门教,代替了敬奉自然神灵的早期吠陀信仰。战事频仍,最终形成了二十多个早期印度国家。
公元前六—前二世纪,从吠陀时代末期到摩揭陀国孔雀王朝,释迦牟尼创立了佛教,也称为佛陀时期。
公元前二世纪—公元二世纪,大夏希腊人、塞人和安息人先后侵入印度。大月氏人更在北印度建立贵霜帝国,传入中国的大乘佛教和犍陀罗艺术,都由它来。
贵霜分裂后,笈多王朝兴起,这是印度人建立的最后一个帝国了。
啊,你看,古印度的历史不也很清楚吗?
哈哈,其实这只为了让现代读者(例如你)理解,姑且如此说说而已。马克思早就讲过:“印度人没有历史。”它的过去,都是十九世纪以后西方考古学和史学一点点建构起来的。
是否瞎编呢?当然也不是,但终究只是一则现代人说的印度故事。
1997年,我去北印度菩提迦耶弘法。那是佛陀成道处,圣地,仍保留着当年开悟时的菩提树及金刚座,旁边有嵯峨的佛塔群,十分壮观。全世界来朝圣的人环绕着佛塔跪之、拜之、打坐、游走,一波接着一波。
但它不建在山顶,而是在高坡上往下一块凹地里。
原来当年菩提迦耶遭到进攻,佛教徒无力防守,又担心圣地被破坏,所以大家纷纷担土来把塔院埋了。英国殖民后,探险家才根据玄奘《大唐西域记》找到它,挖开小土丘,恢复埋着的塔院,叙说它的身世。
印度人自己知不知道这类西方替他们重建的历史?
至少他们不会这样说历史。实际上,他们根本就没有用来编织过去各种事件的时间链条。
所以你若跟印度人相处,千万别惊讶他们“毫无时间观念”。
他们有,但那全是另一回事。
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时间链条是年、月、日、时(中国还有旬、辰、更),时下再分刻、分、秒。印度的“年”却完全是另一概念。在印度人看来,时空是循环的,每次循环称作一次“劫波”,每劫波又分为十四个“期”,每一期终了,宇宙再生(当今处于第七个期)。每一期划成七十一个“大间歇”,每次大歇间分为四个“时期”,各时期分别包括四千八百个、三千六百个、二千四百个和一千二百个“神年”,每一神年相当于人世三百六十年。
在如此长时间、大循环中,人的一生不过是一个神年的四分之一左右,谁会那么在意这几个小时呢?那么久,就连杀父之仇怕都忘了吧,更别说谁借了你的钱。
过往那些琐事,在长时间中,不仅根本不值一提,更无法编织、记录。人世间的一千年也不过是几个神年,记录或记忆的对错,意义有多大?《沙恭达罗》的作者出生年月就是差上一千个人世年,也不过三个神年而已。
时间的计量单位不是那么那么长,就是极短极短。短到什么地步呢?《仁王经》说“一弹指六十刹那,一刹那九百生灭”,也就是一秒钟事相生灭二十一万六千次。
所以,整个印度人的时间观,正如白居易《和梦游春》所说:“愁恨僧祇长,欢荣刹那促。”
这在外部空间上说,固然还有难以把握之处,但从内在心理时间上看,却再确实不过了。梵语“阿僧祇”,意为“无数、无量”。失恋时,时间难挨,一日如同几世纪;欢乐则如冰激凌,舔舔就没了。
印度的“神时观”就是这样,使印度人的时间观念极为恒久漫长,而“自省的空间观”又使其特别注重具体的细节和思考,过于注重微觀,一念三千。
二、反历史的文化
希腊文化属于另外一型。它是反历史的。
柏拉图在《泰米阿斯篇》中说,梭伦在埃及祭司们提问时,发现他自己或任何其他希腊人谁也不知道他们自己的古代史。所以埃及祭司耻笑道:“你们希腊人仍处在幼年时期,你们没有从你们祖先那里得到任何古老的教诲,也没有得到任何一门古老的学问。”
希腊人都不知道历史,也不关心。历史,在其教育中没地位,他们也不喜欢写历史,这些都很像印度人。
但被现代人塑造成非常理性的希腊人,其实很八卦,对过去事情的细节很感兴趣。所以,古希腊并无整体历史的叙述,只喜欢谈古代的事,如酒宴、景色、阿喀琉斯的盾牌等。
被誉为“历史学之父”的希罗多德,真是过誉了,实际比现今一般记者还不如。记了许多读之令人失笑的鸡毛蒜皮琐事:漂亮的伊利里亚姑娘如何选择丈夫,湖区的居民怎么防止儿童失足落水,埃及人驱除蚊子的办法以及蚊帐形状,波斯国王在旅途中只喝煮沸的开水,塞西亚人怎样挤马奶等。
对民族的起源、国家的形成、制度的演变、文化的传播与发展,他都很少涉及。换言之,关注的并非历史,只是一些事件,犹如一位熟悉王菲和周迅恋爱史的人不能冒充为一位摇滚音乐史家。
至于《伊利亚特》等史诗不是史,则不用强调。木马屠城、特洛伊大战是“一颗苹果引发的血案”,独目巨人吃掉奥德修斯同伴,神女喀耳刻把他的同伴变成猪等,都和海伦之美一样,让人难以捉摸。
因此,虽然古埃及鳄鱼木乃伊肚子里已发现了写有荷马史诗片段的莎草纸,但这种民间扬抑格六音步短歌集,就跟唱着蔡伯喈负心的戏曲《琵琶记》一样,不但非史,而且反历史。
热衷琐事、关心“杂”的另一面,就是追求“一”。追求永恒、确定性和事物的有序性,是希腊人的思维特征与生活方式(他们闲着没事,喜欢躺着与男朋友聊这些,作为风雅的社交活动,爱男子也爱智)。
他们认为,哲学和科学的使命就是寻求世界的秩序和确定性。不管是泰勒斯、毕达哥拉斯,还是德谟克利特,哲学家们都在寻找世界的本原。这种寻找世界本原的哲学活动,与历史学意义上的“寻根”完全是两回事,强调的是永恒、是“一”,而不是多、不是变化。
三、科学的历史学
所以,西方从来没有史学。现在声势浩大的史学家、史学学科,都是十九世纪才模仿自然科学建立的。
十九世纪,出现了一些有影响的历史哲学家,注意,仍是哲学。是哲学地想历史是怎么回事,而非从历史出发的史学。这是文艺复兴以后,学习希腊文化的一种成果,并一直争论着:历史是科学吗?理性和逻辑在历史学科中起什么作用?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的关系是怎样的等。
这些又都围绕着一个根本问题:历史是个必然过程吗?如何看待历史必然性?十九世纪三大历史哲学(黑格尔历史哲学、唯物史观、批判的历史哲学)对此,看法完全不同。
但基于“事实”的历史研究(如中世纪德国财政史,不列颠棉纺史、毛纺业史,乃至古代艺术史之类),因缘际会,却也展开了。
这是因为各国忽然大力开放和整理官方档案。法国大革命后,贵族的传统势力日衰,新兴资产阶级力量日盛,拿破仑征战所引发的民族利益之争也强化了社会矛盾。因而十九世纪初,各国都希望学者使用档案文献材料,以证明政权的合法性。
政府和书生一样,其困境都是:要通过叙事来打破困境。所以各国都热衷于档案文献的整理,或资助研究者整理史料。如德国出了大部头《德意志史料集成》,法国也出了《法兰西历史未刊文献汇编》三百卷,包含手稿、特许状、执照、编年史、回忆录、通信以及各种著作。
这原是古来扒粪揭秘、偷窥八卦之遗风的扩大,但评价变了。档案史料,被认为是客观的记录;对之进行类似科学方法的考证,即能达成如科学知识一般可靠的历史知识。
“科学史学”即形成于这种“历史是一门科学,不多也不少”的气氛中。
他们强调掌握第一手史料,否则不能说明历史真相。兰克的《教皇史》《宗教改革时期的德国史》等均以史料考证著称,促使历史研究建立在档案的基础上,用以强化国家意识,体现史学是近乎科学的客观知识。
科学,马克思随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强调: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这是一次重要的历史转折,反历史、不重视历史的西方文明,竟走到了它的对面,变生出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在这时代,历史就渐渐取代了哲学。
许多人搞不清楚情况,仍把哲学当作西方文化的核心。或说它只是重心有了点转移,从形而上学转到认识论,再到语言学,所以,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有个“语言学的转向”,哲学仍然颇有发展。
其实,语言学的转向只是哲学内部的事,是分化了而不是扩大。此后分之又分,语言哲学、艺术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社会哲学、经济哲学、教育哲学……不断应用化、琐细化,事实上也就越来越不重要,距离从前所谓的哲学也越远。
亚里士多德曾把人类的知识分为三部分:最基础的部分是树根,是形而上学,它是一切知识的基础(所以笛卡儿《形而上学的沉思》又称为《第一哲学沉思录》);第二部分是物理学,好比树干;第三部分是其他自然科学,如树枝。如今First Philosophy(第一哲学)早已没人谈了;第二级的物理学又移出了哲学领域,甚至连人文学都不是了,剩下来的全是第三级的东西。
故二十世纪以来,哲学虽尚未死,实是衰微日甚。哲学家,谈来谈去,仍是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后面皆其绪余、补充或不成对手的挑战,并未有足以另开一代的人物。
史学就不一样了。
史学(研究不可见的过去)虽与形而上学(研究看不见摸不着的上帝)同样在谈不可知的东西,但因性质相同,又宣称能通过史学方法让人可知可见,当然很快就取代了形而上学。
学科的正当性及教学研究体制又迅速建立完成。历史系比哲学系更多、更好招生、更好就业,也加速了哲學的边缘化。被重建的历史,又如小说或新兴的电影艺术,可把过去演示于观众面前。在大众传播市场上,遂亦远比哲学受欢迎。名人轶事、绯闻八卦、秘闻奇谈、明暗斗争,更都可附丽于史考史述之中,谁不喜欢?故从此以后,史学就在科学化、客观化、如实重现历史场景的路子上不断前进。且随着殖民扩张,欧洲人在全世界建了无数历史系,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学士、硕士、博士。每个系,入门就在讲科学的史学方法。
中国当然也是如此,但略显曲折。
1902年,新设的现代学堂才开始设置“史学”课,次年改称“历史课”,这是我国最早出现的“历史”一词及“史学”课程。
在此之前,“历史”的含义仅用“史”字代表。许慎《说文解字》说:“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谓史即记事者,也就是史官。换句话说,被文字记录的事情才叫史。历史一词,虽然《三国志·吴书·吴主传》注引《吴书》提到吴主孙权“博览书传历史,藉采奇异”,但史前加的“历”字是指历法,跟近人说的“历史”不是同一个概念。
近代日本学者才用“历史”一词翻译英文“history”,并以进化、文明、近世、国家、社会、国民等具有一般思想史意义的史学术语来叙述中国史事,建构出仿拟西方史学的东洋史学。夏曾佑于1902至1906年参考其论述,编出第一部新式中国通史教科书《中国古代史》,也就是说,当时国人皆取径日本,接上洋流。
其后胡适的“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傅斯年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没有材料就不说话”,也都是向西方取经的痕迹。而且,熟悉近代思潮的人都知道:新建构的西式史学,乃是五四运动以来推动新思潮和社会发展的发动机。
四、后史学的钟声
你也许要说:我国自有悠久的史学传统,何至于此?
是的,我们有不同的史学。可惜近代是个打倒传统的时代,所以由清末引进新式学堂之后,所有史学及历史系都是学西方的。
面对西方史学,我们本来可以形成对抗或挑战。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想保卫自家传统都很困难,哪还有力气、资格反省西方?敢稍微回回嘴,就马上要被群嘲群殴了!
质疑、批判、反省的力量主要还生成于西方内部,大体脉络有三:
一是从事实层面质疑“客观研究”这回事。
例如,兰克本身就被证明是代表德意志帝国的利益而考史,所谓科学的纯学术研究只是一则神话。而后来史学界内部主要也就靠揭发别人的研究不客观、不严谨来运作,考来考去、骂来骂去。
二是把这种质疑,从个人、史实层面,提到方法论层次。说人文学绝不可能客观,跟科学不同。因为历史不能重演、不能实验,已消失的史事与人物也不可能再生,保存的史料更是绝对不可能完整,历史知识既有缺漏又常会被新证据推翻(“历史知识的不完整性”和“历史知识的不确定性”),故史学有与科学不同的方法论与目标。卡西尔的人文科学、狄尔泰的精神科学,都属于这一路。
三是与此异曲同工的雷蒙·阿隆、柯林伍德、克罗齐等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的历史”“历史是历史学家心目中的历史”。强调历史研究不是服务于过去,而是与研究者当下的思维意识、存在情境息息相关的。
当然,这些质疑并未停止史学建制化的大潮流,史学之科学化(包括量化、社会科学化)愈来愈畅旺、愈来愈理所当然。
因为学科建设成了体制,就如泥水成了碉堡,甚难摧毁,只能等,等里面的人老、死。可是质疑也终不可能无效,否则怎么能符合历史“变”的规律呢?
碉堡无论如何坚固,都有愿意出来透透气的人,二十世纪中期以后发展出的“后现代史学”就坚决反对历史学的科学性。认为历史研究中不可能排除主体价值的介入,因而无法实现客观性。
同时,史学也不能进行理论模式建构的宏大叙事,跟科学研究有根本差别。史学若有“元叙事”,也是纯粹的主观建构,且是握有权力的团体在建构,它会随权力主体的变化而变化,根本不存在可对它们证实的客观标准。像对法国大革命、拿破仑之评价和天主教历史作用等问题,永远吵成一团,去哪找客观叙述与评价标准?
因此,后现代史学认为不必去妄想重建史实、进行历史解释和理论建构,能复兴“叙事史学”、讲讲故事就万幸了。
历史认识论和历史编纂学乃因此产生了重大颠覆,史学出现了合法性危机。
五、史学的合法性
其实,把“历史学合法性的证明”当作史学本己的任务,早在尼采那里已开始了。现代史学,打它诞生起,就一直处在证明其合法性的焦虑中。
史学,不论是纪念的、好古的、裁判与毁灭过去的,尼采都认为它得服务人生。故“历史被认作纯粹的科学,成为至上的,也许对于人类是一种人生的终结与清算”,服务于人生的历史“永久不能,也不应该成为例如像数学那样的纯粹科学”。
海德格尔进一步提出“此在的历史性”,说人这样的存在者,就具有“本真的历史性”。本真的历史性不一定需要历史学,无历史学的时代本身并非也就是无历史的。
此在,讲的是人生在世就处于操心之中。操心是人的现实感性活动,人不得不为自身生存有感性的筹划,唯有这种真正的存在感,才能从“将来”来到自己本身。
时间性则是在生存中把所有当前化的将来统一起来的本真现象,它乃是操心得以可能的本真源始的条件。
他说,本真的时间性根本不是随着过去、现在、将来的流俗时间之“流”而积累拼凑起来的,而是将来、曾在、当前等“绽出”样式的同等“到时”。而在诸种样式中,将来又居于优先地位。时间性之于此在的操心筹划,首要的意义在于“将来”,“源始而本真的时间性是从本真的将来到时的,其情况是:源始的时间性曾在将来而最先唤醒当前”。
既然如此,此在的历史性,当然就不是思想家通过逻辑、概念、反思做出来的。历史性源出于此在在世的时间性,而时间性又是此在在世整体能在之不可或缺的基础,故历史性就是此在在世之本真,“我们越是具体、合乎人性地把握了人的存在的时间性的根基,就越能清楚地看到这一存在本身是彻头彻尾的历史性的”。
反之,历史主义以追寻某种“普遍的东西”为对象,或以陈列“个体性的”事件为对象,从根基上就错了,因为它们“使此在异化于其本真的历史性”。
六、史法解梦占
西方哲学家的论述魅力,正在于它的晦涩迂曲,一个简单的道理,扯得似乎十分深刻。
海德格尔写过一本《时间概念史导论》,却五分之二在谈现象学,另外谈存在与时间。时间概念史呢?喔,只谈了时间和对时间的界定。
此处也类似,迂曲晦涩,绕来绕去,大意只是说:历史就存在于人在时间中的操心处,而操心主要是对未来的烦虑。
但这个讲法是有意义的。他以为历史学应该要回到这本真的历史性,并揭示了未来才是历史真正的根源。
也就是说,真相有时恰好与所谓常识相反,一如人都以为地是平的,其实却是圆的。
历史,大家都以为是真的:过去之事,记錄下来就是历史。殊不知,五岁以前的事你根本不记得,晚年即使不痴呆,也糊涂得很。中间三分之二时段,又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睡觉,没知觉;或在做梦,意识纷乱;自认为是醒着的时候,又泰半无集中意识,只是吃着动着而已,跟猫狗没啥两样;而自以为是有意识的行为与思虑,绝大多数又都忘了;勉强记得的,其实却多模糊、错乱或张冠李戴,如旧日照片般斑驳褪色,不辨眉目。因此,人并不能天然地拥有属于他的历史。
个人尚且如此,他人、家庭、宗族、国家,乃至异族、他邦、世界,其历史如何说起?要说,就需要一个历史以外的网,网罗破碎、零乱、片段的记忆,以想象力、创造力、叙述力、编织的技巧、同情的理解、设身处地Cosplay等方法,去描述已消失的物事。
已消失,便是无,是“事如春梦了无痕”的无。可能曾有,但现在已无。
所以无是真的,曾有者是否真有,反倒值得怀疑了。因为即使真曾梦过,梦能当真吗?梦之有,尚且不是真有,则史书所述,一春梦雨常飘瓦,尽日灵风不满旗,比梦还不实在,何可当真?
解梦需要技术,古代有《周公解梦书》,近代则有弗洛伊德。
这些技术真能解梦吗?当然不能,但只要当事人相信就好。所以,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会有不同的解梦术。一时或相信因果,一时或相信鬼神,一时或相信潜意识,一时或相信科学。
历史之编织与理解同样需要方法,故古有巫、有史官,近代便发展出了史学,方法也是随时代变化的。
大家都想抓住梦中缥缈的风铃声。
巫,用神话思维作为绳索来编织,近代史学用科学技术来编织,传统史学界乎神话与理性之间,占梦师则只注目人本来就不能有理性意识之处。
占梦师游心于阴,巫半阴半阳,史阳渐盛,近代史学更是虚阳亢进,然其为编织则一也。所谓科学史学研究方法,与夜行人吹的口哨相似,响亮着心虚。
现代人当然以为科学理性思维远比神话思维高明。实则非也,因为内里交织难分。
例如历史本无所谓分期,流水光阴,分也无从分,抽刀岂能断水?故中国就从来没分,通史以编年为主、朝代史以纪传为主。
西方中世纪基督教基于所有人类皆上帝之子民之概念,讲跨国别、跨种族的“普世史”,才有了分期法。
以耶稣生命为线索,把历史分为耶稣出生前和出生后,称为纪元前、纪元后。纪元前是上古;纪元后,以上帝旨意或教会文化发展之线索看,又可分为中古和近代。
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曾痛骂它不顾世界各文化之殊相,强用一个框架去套,是狭隘偏私的。何况,其说本于犹太宗教天启感念之传统,代表着基督教思想对历史的支配,在时间的暗示中其实预含了许多宗教态度,并不是历史本身就有的规律,只是一套神学。
历史分期不只是静态地分,还指明着历史动态的方向与进程。
梁朝大名士陶弘景就有《梦记》一卷,自记所梦。他弟子周子良,从梁武帝天监十四年五月二十三日至次年十月二十七日之间,连续与神冥通(入梦或现身),最后解化升仙(其实就是自杀)。陶弘景也把他的日记编成《周氏冥通记》四卷。又编了上清派祖师们的梦神录为《真诰》七篇。以梦为史,蔚为典型。
你说这不是史?
其一,记梦者自己未必觉得是梦。其中一位通灵者杨羲甚至觉得整个过程太清醒了,不相信是在做梦(紫微夫人和清灵真人则答复说:“此实着至之象,事显幽冥,非虚构也。”意思是:梦就不实吗?梦也是实的,你真的是在做梦)。
其二,史本来就与巫颇有交集。陶弘景所记之事,便往往与《左传》《史记》相涉。而“《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早有定评。《史记》呢?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亦自报家门说他们太史公这种官:“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他掌天官,不治民,工作是观察天象、奏定历法,凡祭祀、丧、娶、瑞应、灾祥、时节禁忌诸事,皆要由他管理,不是巫,是什么?
所以,其三,记史原即与神怪脱不了干系。《汉书·艺文志》之所以认为“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原因即在于此。
如春秋时就有一种《训语》,说夏朝衰时,褒人之神化为二龙,出现王庭,或后羿寒浞斗争等荒怪的故事。《国语》,柳宗元也批评它“不顾事实,而益之以诬怪、张之以阔诞”。《左传》多巫怪、《春秋》言灾异,本即是史之传统。
西晋时,汲冢发现《汲冢琐语》一种,体例类似《国语》,史事传说,颇涉妖怪。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说它是“诸国梦卜妖怪相书”,略如后世《夷坚志》《齐谐记》,又说它是“古今纪异之祖”“古今小说之祖”。
近人论文学史,从鲁迅以来即喜欢说“六朝志怪”,好像志怪是六朝的特产,或志怪到了六朝才陡然兴盛起来,然后再去替六朝之所以多志怪找這个那个原因。不晓得讲这些卜梦妖祥及琐事,正是古代“庶人传语”(《吕氏春秋·达郁》)而被小史采录的传统。
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指的就是史多浮诞夸饰这一特点。
不仅《汲冢琐语》如此,汲冢所出《竹书纪年》里面也多是黄帝仙去、三苗将亡天雨血、青龙生于庙、柏杼子得九尾狐、十日并出、宣王时马化为狐等故事。司马迁撰《史记》时说百家述黄帝,其言多不雅驯,即指此。直到《新唐书·艺文志》还把一些志怪书归入史传类,可见其原委。
我这里不是替巫史争正统,或说科学理性思维其实本是神话、神怪幻梦却常被当成真史实事。
我只是说:过去的事,春梦无痕,难以记忆、无法还原。近代史学界的先生们,自称可以科学方法复原之、重建之,实无异于痴心汉艳说佳人梦中情事。又好似胡应麟形容的唐人传奇,“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只能当故事看看。其记梦之法,貌若新颖,实亦与巫史占梦之编织测度无大区别,且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也难说谁就胜过谁。
在现代史学自矜新潮、瞧不起巫史传统时,自己倒是跌了许多跤。
1890年,英国人霍恩雷曾获得一批来自新疆、抄写在桦树皮上的古抄本。研究发现,那竟是古印度笈多时代婆罗米字母拼写,此前从未发现过、已失传千余年的阿育吠陀医学典籍。这消息,立刻引起了一阵国际骚动,引发中亚探险热。英国、法国、俄国、日本探险队纷纷到新疆和中亚地区考古调查,收集到各种汉文、婆罗米文、突厥文、阿拉伯文、吐火罗文、于阗文写成的文书,洋洋大观。这些抄品,不但被大英博物馆、俄罗斯皇家科学院等机构收藏研究,也被斯文·赫定当作真品记载在了他的《穿过亚洲》中。
那真是个丰收期,使“东方学热”高度升温。
可惜抄本多是伪造的。造伪健将之一名叫斯拉木·阿洪,他是个文盲。文盲先生用杨柳枝泡了水,将纸染成黄色或浅棕色,之后再在上面胡乱写一堆他自己也不认识的符号。有些则放在火上熏烤,进一步做旧。然后在装订起来的纸页间随意撒些沙漠中的细沙,源源不绝地生产各种“古文书”,后来由于销量太大,更干脆用雕版印刷加速制造。他的勾当后来被斯坦因(也就是去敦煌“盗宝”那位)识破了,伪造才告一段落。
然而仍不断有人被骗。1929年,北京大学黄文弼参加中国和瑞典合组的西北科学考察团,买到一些活字雕版印刷古文书,大喜,因为这显示古代西域雕版印刷发展的时间很早,甚至可能将中国发明活字版的时间大大提前。
为了慎重,黄文弼还专门请了季羡林鉴定,季先生判断是古和阗文。黄相信季的权威,故将这些古文书都收录到他的《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中。
直到1959年,季羡林的老师、德国印度学家瓦尔德施密特才在给黄文弼写的书评中揭露,他买到的一千多个字符的文书,都是由斯拉木·阿洪他们用四个不断重复的“词组”组成,没有任何意义,只是拿几块像印章一样的“活字雕版”反复在纸上印出来。
一个文盲居然让那么多大牌教授、学者、研究机构都摔了跟头。
这是特例吗?当然不是,我爱惜篇幅,也想替学界留面子,不愿多说而已,这种事是“古已有之,于今为烈”的呀!近三十年,忽然数量暴增、海外买回的简牍和字画,轰动华夏,蔚为显学,内中其实就多有此类物事。
当年史学新浪潮,即曾以“疑古辨伪”为大旗,从1926年至1941年,推出了《古史辨》三百二十五万余字。认为中国史必须拦腰砍去一半,春秋以前的事都只是传说的层层叠加。老子没这个人、孔子没见过老聃这回事、《老子》这本书是战国以后造的,《尧典》更是后人所造,没孙武这人、《孙子兵法》只能是孙膑所作……
现在,大家不这么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