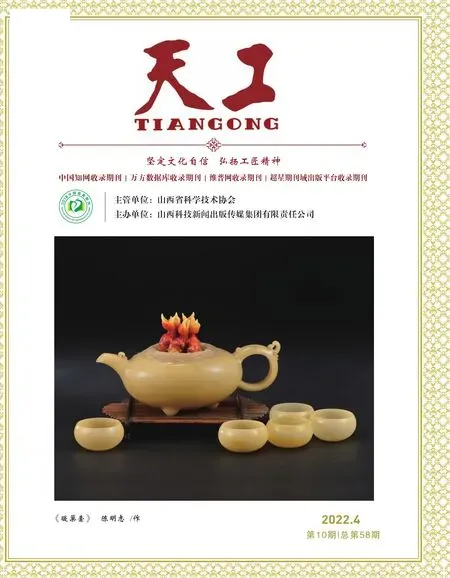山西晋祠水镜台清代建筑木雕纹样研究
刘子真 太原师范学院
一、晋祠水镜台建筑木雕背景概况
晋祠水镜台木雕装饰的风格形成具有独特的地域性。木雕装饰依附于建筑,在建筑发展的过程中,地区的自然因素、人文因素、经济因素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晋祠建筑群是不同时期逐步建成的,后建的建筑受到了前朝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在建造水镜台前台的清朝时期,经过前面几个朝代的推动和影响水镜台建筑木雕发展到了顶峰。晋祠水镜台建筑木雕装饰在满足戏台基本功能的同时,将建筑木雕发挥到了极致,充分地体现出地域特色。
(一)水镜台地理环境概况
太原地处山西中部、晋中盆地以北区域,整体地形北高南低,呈簸箕状。群山环绕中的太原从地理位置上就形成了独有的建筑特点和装饰特征。建筑与周围山形一样,体量敦厚,雕饰精美,规模宏大。这一特点在晋祠水镜台的建筑雕饰上也得以体现。由于山西省境内地貌结构复杂,受山地阻隔等多种因素制约,建筑结构与装饰大都因地制宜。从水镜台建筑装饰性来看,其装饰题材和寓意也极大地受到了地理环境因素的影响。如花鸟、人物、动物等题材也是自然地理条件的转译。
(二)水镜台历史文化背景
在历史发展长河中,太原是北方地区游牧民族文明与中原地区农业民族文明互相碰撞、互动融合最为密集的地方,由此形成了山西区域文明发展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山西传统文化内涵丰富,沉淀深厚,作为古代神话传说的发祥地之一,众多古代传说和圣贤故事都能在山西找到流传的历史遗迹。建筑装饰成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现实载体,山西特有的文化传统也丰富了水镜台木雕装饰的题材和内容。
二、晋祠水镜台建筑木雕装饰艺术形式
(一)明清时期水镜台的装饰形式沿革
以晋祠水镜台为代表的山西传统戏台建筑,创造了自身的装修理念与装修风格。明中期之前,山西戏台的装修格调简朴雄浑,但明中期以后,戏台进入了一次全面革新的时期,相比于元代的简洁有力,更加重视外部的雕饰和装潢,追求高大艳丽,内部装潢也更加考究。
晋祠水镜台明代所建的后台注重装饰,与同属晋祠的宋代建筑圣母殿的木雕装饰大不相同。明代时期,水镜台的装饰设计风格应该算是元代和清代的中和体,既不似元代戏台的朴实雄浑,基本无室内装饰,又不似清代戏台的纤巧烦琐,也不再依附于建筑物结构上。它更具有自身的气质和格调,在简朴中扩散装点,在装点中而不弥散,高大艳丽,散发着属于这个时代独特的艺术气息。到了建造水镜台前台的清代,戏台的形状和装潢艺术都已经比较完备和成熟。戏台的总体平面形状也不仅仅拘泥于传统的方形或矩形,而是更多地使用了组合式平面,设计师因人制宜地创造了多样的戏台形状,将中国传统建筑雕饰艺术发挥到了极致。戏台的梁架、额枋、斗拱、雀替、柱基等建筑物结构上都充满了雕饰与彩画,这也与清代繁荣的戏剧演出分不开,说明了戏台已经由“娱神”过渡到“娱人”。而水镜台上檐下的建筑物装潢也堪称华美之极,以明艳的彩画及精致的雕饰填充了全部的建筑构件,无一遗漏。而水镜台前台的清代建筑物木雕装潢艺术特色突出,凡是能装点之处均以装饰,已经不再依附于建筑物结构自身,甚至于有些斗拱与雀替也已经没有自身功用,而成为纯装饰构件。
(二)水镜台建筑木雕纹样的形式与种类
1.水镜台斗拱木雕装饰纹样
斗拱,作为我国木构建筑的主要标志,是由榫卯结构相互交叉或重叠而成的支撑结构,通常置于梁帽、额枋、顶板中间,为立柱与梁架中间的重要关节部位。斗拱上的结构密集、交错、层层叠叠,构成了我国木构古建的一个奇观。而斗拱也是中国木构古建的重要结构件,其用材的大小决定了木构古建筑出檐的大小,而出檐的大小又是木构古建筑规制级别的重要标志。
晋祠水镜台前台的清代斗拱,已经演变成了一种兼具装饰的建筑结构,较唐宋时期的斗拱变得短小秀丽、十分繁密。雕工的精细与造型的反复排列形成韵律,这是此时期建筑木雕的特点。工匠将它雕塑为龙头、凤首、长鼻等不同形体并进行了彩绘(如图1)。

图1 水镜台斗拱
水镜台前台建造于清代,从建筑斗拱的木雕来看有着典型的清代建筑装饰特征。龙头雕刻繁杂细密。水镜台斗拱具有完全的装饰性质,其功能性较弱,斗拱龙形向外延伸,龙鳞、龙鳍、龙首雕刻丰富而错落有致(如图2)。大龙吐小龙、小龙吐珠,也有着深刻的教育寓意,意为上一代教育下一代,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和教育。这种寓意也暗含着戏曲和戏台建筑的功能——高台教化。

图2 水镜台斗拱雕刻纹样(笔者手绘)
仅次于龙的主要装饰形式为象,象与狮同属佛教之物。调研中发现,水镜台等神庙戏台则把大象和龙融合为另外的形体,成为雀替斗拱而存在着。从装饰上来看,斗拱木雕龙上的象头昂装饰比较古朴,少装饰。从美学上用少装饰的象头衬托复杂的龙纹,使之形成一种独特的美感。
2.水镜台梁枋木雕装饰纹样
梁枋类构件是中国传统建筑中最重要的构件之一,晋祠水镜台后台为明代建造,前台是清代补建,其梁架部分的繁花似锦正是雕梁画栋的写照。
水镜台的雀替是戏台建筑装饰的重头戏,在建筑上用得很普遍,且多集中用在外檐柱子上,屋内比较少见。当雀替逐渐丧失了结构作用而作为一种纯装饰构件的时候,形式就不受限制地夸张变形,而且越是边远地区越明显,小小的雀替也可以有万千的装饰效果。水镜台的龙形雀替体量较大,常常出现在骑门梁与建筑正立面中央两根柱子的相交处,简单的装饰有夔龙、草龙等装饰意味浓厚的龙的变体,一些比较讲究的戏台则用一整条具象的、蜿蜒活跃的龙体作为雀替装饰,雕刻细腻且形态逼真。水镜台龙形雀替中龙身盘曲有力,龙首上昂,虽然色彩略显陈旧,却依稀可见当时的繁华。同时雕刻工艺更加出神入化,采用高浮雕和透雕的技术将龙的形象和周围卷云的形状融为一体,飘逸洒脱,充满灵性(如图3、图4)。

图3 水镜台龙形雀替

图4 水镜台龙形雀替雕刻纹样(笔者手绘)
梁枋和雀替的功能一样,但表面的雕刻装饰并不简单,细细的边框内有用植物枝叶、花果组成装饰图案的,有用回纹、万字纹满布装饰的,也有复杂一点的动物和人物雕刻,造型自由随意。水镜台的梁枋共分为四层,从结构上由精细变得简单(如图5)。第一层多为动物与植物结合,动物以瑞兽为主体而植物分布在四周作为衬托。第二层为植物雕刻,偏向于平面曲线化的植物(如图6)。第三层由二维变为三维,出现了一些三维的场景,描述了一些圣贤故事、神话故事等。第四层由简单的几何图形组成二方连续的纹样。这样繁杂和简单的结合形成了建筑木雕的强烈的美感。

图5 水镜台梁枋

图6 水镜台梁枋植物纹样
3.水镜台垂花门木雕装饰纹样
垂花门是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的一种独特装饰部位,是一种半悬式檐柱结构,悬挂在屋檐下或院墙上。下面是经常雕刻成花瓣状的半柱,称为垂花柱。
山西木构古建筑,垂花门分布极为广泛,其结构精巧,构件众多,可谓精雕细琢、不厌其烦。在晋祠水镜台建筑中,垂花柱的雕刻也十分繁复。受佛教的影响,垂花柱雕刻题材多为不同的佛教素材,垂花门有着佛教宝座的雕刻形态。水镜台前台正面两侧雕刻的垂花柱,多为佛教莲花形态。上端类似花朵包裹,下端结一垂珠,中部利用镂空的手段,雕刻出复杂的装饰图形。
三、水镜台建筑木雕装饰纹样的题材
山西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与历史文化造就了晋祠的恢宏与精美。在历史悠久的三晋大地,当地人们在与自然共生的过程中流传着非常神奇的神话传说、圣人故事、诗词歌赋。这些共同为晋祠水镜台的木雕提供了丰富的装饰题材,赋予其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晋祠水镜台是山西劳动人民用无穷的智慧与想象力创造出来的艺术精品,饱含着人们对文化和自然的深度思考。
传统戏台建筑雕刻的题材十分广泛,大体可分中国传统龙凤、瑞兽、花木、器物等。龙从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中国的吉祥文化,因此龙的形象是传统建筑雕刻图案中常用到的元素。在晋祠水镜台上,龙的元素主要出现在柱头雀替和斗拱上。常用的瑞兽包括麒麟、狮、虎等,这些动物往往成为祥瑞的标志,也寄托着对人类美好的希望,如“麒麟送子”“狮子滚绣球”“镇宅神虎”等。这些素材出现在晋祠水镜台的梁枋之上,组成错落有致的纹样装饰。常见的吉祥灵禽有鹤、喜鹊、燕子等。喜鹊登枝、松鹤同春、白头长春等以花草树木为题材的吉祥图案在晋祠前台中最为常见。人们常常根据它们自身的特点,赋予了花草很多吉祥的意义,寄托了人们的思想。
传统建筑中寓意吉祥的器物最常用的是如意,头像灵芝或云形,形态优美。道教和佛教中的重要器物,八仙手持的标志性法器等组成的八仙纹等也是常见的吉祥图案元素。
传统戏台的雕刻题材多种多样,不同的图案和造型蕴含着不同的文化内涵,寄托着人们美好的愿望。在山西,儒家、道教、佛教文化在传统戏台的雕刻中均有反映。首先,山西的传统戏曲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特别是“二十四孝”在山西的众多建筑装饰中多有体现。再者,佛教在山西的广泛传播,也给传统戏台的雕刻提供了不同的题材。佛教中的菩萨、罗汉等人物形象,狮子、大象等动物形象,以及宝塔、香炉、法轮、木鱼等器物形象,都可成为雕刻题材。
四、总结
山西晋祠水镜台以精美的木雕装饰,承载了千百年来人们对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水镜台作为我国戏台建筑的突出代表,其建筑装饰具有我国戏台建筑装饰的基本特征,同时水镜台又包含了其独特的地域性艺术审美特征。山西晋祠水镜台承载了中国建筑雕刻的手法与记忆,实现了审美性与实用性的高度统一。通过对水镜台建筑木雕纹样的梳理研究,可以相对真实地解读历史建筑信息,描绘出当地的人文景观与历史文化内涵。水镜台建筑屹立于晋祠之中,精美绝伦的建筑木雕纹样与台上表演的晋剧戏曲艺术交相辉映,其艺术思想、装饰手法、文化底蕴为当前艺术设计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来源与文化支撑,不断推动着中国艺术设计走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