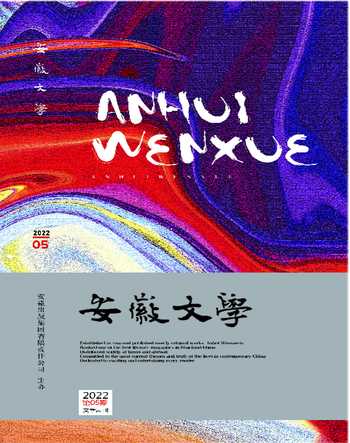在大兴安岭山脊或山脚(组诗)
蒋林
向 北
从皖东向北,经淮河、运河和黄河
干流、支流和桥梁,横陈于乾坤。
村镇的田地与房舍,所说与所唱
皆为大河腔调。在预设的导航中
我把自己定位成一粒北斗下的蝼蚁
抑或吊挂在线谱上的音符。众河流
与斜拉索被季风弹拨,我周身轰鸣
多年的向往,与涡轮发动机共振。
向北,高端有星斗,远处有极光
我被蝼蚁的沉默控制着,时不待我。
地理分界线,犹如必须过的一道坎
从极高处看,只需一个垂直的信念。
山与原的交界处
河北平原,出天津与唐山的口音之外
燕山接管方言。其字正腔圓,区别于
淮河以南江淮官话洪巢片合肥小片。
像负有使命的钦差,用横亘的山脉
对来自方言区的吉普,宣读北方诏书。
群山威仪,树木铁青,交通标志线
引领柏油路,蜿蜒在秩序和目标中。
山与原的交界处,面对突兀或流畅
回头是不可能的,继续是唯一的方向。
中年发动机在路上的动力依然强劲
它已跨越沙漠和戈壁,年轻和迷信。
赤 峰
被黄金海岸弹射,空间上落地于赤峰
时间上落在肇始于新石器时期的红山。
在博物馆,相遇玉器“中华第一龙”
缓缓旋转的全息投影,也是时光回旋。
仅仅凝望三秒,灯光、玻璃橱窗
壁上文字和图片,竟如泥胎纷纷剥离
浮升出五千年前的幽深……乃上溯
及至七千年前,吾乡的侯家寨遗址
夯土堆上的母系氏族,其陶器、骨器
也怀抱红山玉龙这般净润,清晰可见。
真是意外!我的方言,难道交集了
出土的睡眠?抑或是闭关中的文物
在古旧的乡音里,发生了穿越和际会?
大兴安岭的一个鞭梢
大兴安岭山脉自东北向西南,卧成一条
休憩的鞭影。大地的神迹,如果来自
上苍,也非一日之功。那些林莽和禽兽
是歇息下来的呼吸和脉动,巍巍石阵
落座于黄岗山梁,是一记有力的鞭梢
被克什克腾的牛羊舔舐,被西拉木伦河
少女的裙裾裹围。阿斯哈图冰石林
冰是冰川的冰,周围的白桦林,是浴火
重生的白、抱团成丛的林。承蒙神启:
诗,需要凝成峻峭的石头;我需要
石头的蛮荒和苍劲,凝成血液里的鞭响。
用一场大雨宣示草原的性情
从科尔沁草原入城,一场大雨落下来
就像朋友察罕不花敬上的一碗马奶酒。
如果不能一饮而尽,那我就不配接受
天意和洗礼,也无颜挑开蒙古包垂帘
说出我对草芒和露珠的欢喜。这取决于
我能否一口炸一个罍子,低吼的吉普
能否与滚雷和闪电形成诚挚的互动。
乌兰浩特年降水440毫米,此番豪爽
跟游牧的性情相匹配,恰好我也很喜欢。
光线特意指出海拉尔的傍晚和清晨
强光和铅云是一对恰当的神仙。羊脂
般的云,被海拉尔的日光晒得乌青
又像在乌青的袍子上染一层铅粉。
这是错觉。在纯粹的蓝和青草之间
城池就像垛在色彩里的积木。光线下
我看傍晚或清晨,柔和得就像民谣。
城市的灯光和广场,是鄂温克小女子
身佩的串珠和圆环;她的连衣裙上
镶着花边,叫作芬芳的街道和阳台。
除此之外,上午、下午和剩下的词语
都齐刷刷站在柔和民谣的对面了——
匈奴、突厥、狼毒花;烧烤的汉子
他听我描述南方,翻转烧烤显得焦急。
大草原的最小计量单位是一株草
无边的草原,往往视而不见一株草。
进一步忽视的是草芒上的一缕光,是
落在草根的雨滴,拂过草叶的风丝
举起草茎的撮土,以及它的细微气息。
都看见呼伦贝尔跟天一般大,我却
先看最小的计量单位,一株草,由它
生发的广阔和辽远。最纤细的呼吸
和最微弱的蝴蝶翅膀、和其后的风暴。
其余的土,长其他草,其余的光芒
各找各的草叶,蜿蜒的河流梳理长风
长风捋一捋马鬃、揪一揪绵羊的毛。
天穹下的美妙让人难言,人间啊——
我相信这一定是上面的神仙安排好的。
责任编辑 老 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