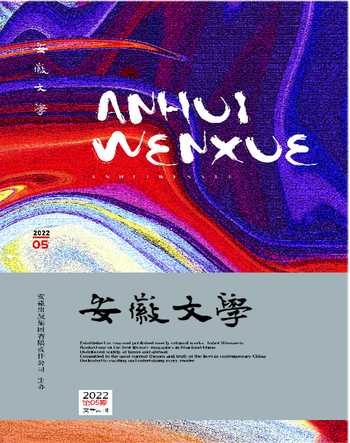东京铁塔
周亭
它并不是一个适合做梦的城市,我却不时地做着这样一个梦:
轻淡而深远的雨幕遮蔽了喧嚣。她轻便地逃离。跟随身后的是凶残如噩梦的追剿令。她反而逃入繁华的东京。穿过苍莽的槐林,会入往来如潮的人群,再又淋着桃花开后的雨雪,孤单,凄寂。没有生意的布店固执地不肯打烊,到薄暮时分迎来一个只为避雨的路人。店伙想要劝她买一双雨天行路的木屐,她却摇摇头,开了口问,请教,去铁塔往哪边走?
略为相关的一个事实是,有个人曾对我说,东京的铁塔是很美的,你来,你来吧。
我对一座真的铁的塔没有兴趣,何况他的意思是要我留在东京生活,一起经营中餐馆。从宋朝的东京东行,到东瀛的东京,原因就在于他认为,这座废掉了的古都并不是一个适合做梦的城市。梦者,本来就应该在飘渺的远方,须千万里去追寻。而且既做梦,何妨是一场春秋大梦,小城市是装不下的。
七八年间,所有的朋友和恋人飘零四散。使我愈发觉得,应该在一地根植下去,在今日的地表生长,在昨天的地下深扎,直至触及地核里的火或天空中的云。
我费了不小的力气买了一处小房子。在金钱有限的基础上,选择虽不多,但也颇有困难。在东或在西,全新或半旧,安静或喧闹,在考虑中取舍不下,被舌灿莲花的经纪人搅得左右为难。但有一次,我在一间落地窗的阳台上看到晴空下的铁塔。巍巍沉默的琉璃砖深色塔体,由明媚得有点朦胧的天光映衬着,仿佛笼罩了一层淡淡烟霭。在没有高楼大厦的开阔低空中,有种众鸟飞尽孤云去闲的寂寞和安详。
有什么东西从我身体里飞了出去,导致我半天无法动弹。铁塔在等我。这一厢情愿的想法,让我和铁塔这样式的相逢变得意味深长。站在毛坯空间里,我的心脏一阵跳腾,似有绳索牵出,任意飞绕,将我拴牢在大地之上,或者任何事物上。
就是这里了。
决定好之后,我变得身无分文。除了通过上班挣的工资,我加倍努力写文章,不惜把之前所鄙视的烂梗套路都用上。意外并没有得到差评,也许是人气低迷的缘故吧。呕心沥血双目眍䁖,这部言情小说进展到十分激烈的阶段,以我的能力,只勉强能够接续下去,不敢说高潮迭出无懈可击,不被找出逻辑错误已经算是我的上限了。天可怜见,有几天我居然收到几位读者高额的打赏。等了几天,确定这些钱不会从我账户中溜走,我痛快地下单,购买了橡木地板和灯具。也许这是我这辈子成绩最好的小说了,之后我兴奋而无望地这么想着。并且,我再也没有勇气重回作家的正途,而只能是个写网络小说的。
但我的梦继续做下去。
铁塔?那店伙说,城中塔是多的,有瓦的有砖的,有木头的有石头的,并没有一座铁的塔。可是,她抹了抹鬓边的雨水说,我就是要找铁塔,最高的那座塔。布店柜台里瞌睡的掌柜这时醒了过来,沙哑了声音说,就是开宝寺塔嘛,人人都传说是铁塔,真怪了。
她便又问,开宝寺塔,向哪边走才是?
尚未落成呢。八角的至高之塔,基座就够高的,所用琉璃砖不知有多少块,其上又不知有几十样图案,又要百年不坏,三年五载怎么建得成?
然而……她望着那蒙蒙烟雨沉吟。她的思绪被时骤时缓的雨声打乱,成为一片浮萍田田的水塘,被满溢流泻的护城河水冲得荡漾不已,所有的倒影扭曲交融,模模糊糊。
我的梦亦乱了。
夏天就这样过去。之后是霖霖脉脉的秋雨,在月亮隐藏了最圆样貌的那天,我被召到郊区舅家,参加大家庭的聚会。虽然传统里很重要的一项是赏月,但好像并没有人在乎月亮。在开饭的前夕我来到客厅的阳台,向东方的夜空张望许多时一无所获,才接受这是个阴天的事实。
话题围绕前几天刚刚定下的悦颜的婚事展开。舅家和四个姨家——包括三个表哥家,所有人好像瞎了眼睛,对着舅舅手机里那个既秃且肥的半老男人称叹不已,说他帅气、成熟、年轻有为,说打着灯笼也找不到这样好的婆家。
也许是打着灯笼撞见了鬼吧。
我不懂悦颜。这一年我们互相没有联系,不晓得为什么。
后来,在黑夜初至的社区广场,一片包含着未知内容的昏黑里,隐约觉察到三两个人有男也有女,循着逆时针方向跑圈。又隐约听见两条长椅的位置上有些喁喁语声,是那群在白日下午也可见到的退休老者隨意聚集了的闲谈。这里是他们的社交场所,是他们追忆往昔和谈论时政的露天沙龙。一涉时间,往往是三四十年前。
我一边慢慢散步,一边滋生起枯寂的无聊,便塞了耳机播放一首半听得懂的英文歌。
这歌唱的是少女对意中人的仰慕和靠近,心心念念,亦痴亦醒。美好的爱情啊,只存在艺术作品里。在现实中多半就是不堪。现实的秩序是万分复杂而无法掌控的。一架飞机从很近的低低的夜空飞过,巨大的声响持续了十几秒,吞没了歌声。在这十几秒里,我由着一颗孱弱的心孱弱下去。等到歌声在耳中清晰起来,世界也一下子恢复安稳,我长长地抽一口气,把一切杂念都摒除了。
工作和写文让我坐着的时间太久,腰椎疼痛难解,每天步行半个多小时就成了我唯一的运动项目。此时的广场,稍亮了些,我看得见每一个人所在的位置和他们的大致体形。夜空没有月亮,广场上所有的灯光都在相当远的地方,只映照了它们上方的一点夜空。可整片夜空终究不是黑魆魆的,还有一些灰灰的清白,隐含着光,正是这些不太光明的光,和广场浅色的瓷砖地面相互反射,成为足够眼睛辨物认路的浅浅夜色。
原来,在一个黑暗的地方久了,就可以看到它的光明。
是否适应了一个地方的黑暗也就不以为怪了呢?我想。
不,不是这样的。至少滕薇就不是。她永远有最狠的眼神和语言,对不管亲疏的任何人,对不论得失的任何事。比如今天,中秋节的团圆家宴,她就可以毫无心理负担地不参加,甚至根本都不回来。而我每次都过不了自己这一关,自觉考虑父母的处境和感受,去参加大概率要过问我的工作和婚姻的家族聚会。所以我把滕薇奉为半个偶像。但今天是万万没想到,在大团圆的中秋夜把一桌饭菜都掀了的人,是悦颜。
舅舅是过于兴奋了,和明哥两个人一杯接一杯地自己灌自己,还时不时撺掇大家都来干杯。即将与豪门联姻,空前拔高了他的自尊,团圆饭变成了由他即兴生成新规则的酒桌。我端着一杯椰汁,想跟悦颜碰一下,却只见她呆着一张毫无表情的脸,好似什么都看不见听不见。
八点半,窗外爆出朵朵欢喜的烟花时,悦颜起身夺了父亲和哥哥手里的酒杯,掷在地上,随后是酒壶、酒瓶,然后是歇斯底里的喊叫,满桌杯盘佳肴从扬起的桌布上哐啷滑了下去。
所有人都吃了一惊。如果不是舅妈示意我把悦颜带出去,接下来的场面恐怕会演变成一场混乱的斥骂。今晚除了饭菜美味,其他都不对劲,悦颜最不对劲,我一直问她怎么了,她却只用“没事”两个字打发我。我不能不生她的气。但这就像遂了她的心一样,来到街道上,她拦下一辆出租车自顾自走掉了。
我在广场上茫然地晃荡了好一会儿,才想到打电话给滕薇,告诉她今晚发生的一切。我们三个表姊妹,从小一起长大,滕薇比我大三岁,我又比悦颜大两岁,但几乎不以姐妹相称。也许是血缘的原因,我们天然能够毫无阻碍地相处相知。但我不明白,悦颜为什么变成了这样。我就很自然地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也许我写的网文档次太低,即使还不算文字垃圾,也可以说是文字做成的一次性用品,比如包装纸,到人跟前就是用来撕开扔掉的,跟悦颜专一从事的学术研究是云泥之别,通过网文,她窥见了我的一些底细,大约如此。
“我知道是怎么回事。”滕薇犹豫了一下说,“节后我们见面说吧。”
滕薇长居上海,时常到各地出差,去绿城的话偶尔会在古都停一下,跟我见上一面。我们都知道她从事IT行业,但隔行如隔山,想不通她为什么收入那么高,高得和我们好像不在一个世界。
有一天她告诉我,她要移民到大洋彼岸某国。应该是很快就办好了,但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突然暴发,她迟迟没能动身。也就是在这时候,她遇到了未来的丈夫,那个只存在于家长们的传说中而无人见过的残疾男人。
滕薇向我讲述过这个故事。那是寒冷的早春,疫情最为严峻的时期,她走在一条狭窄而冷清的老街上,对面远远走来一个有点瘸的男人,在他们交错而过的时候,他忽然轻轻地说了句:“你好漂亮。”这是不太说得通的,滕薇以为。因为她除了戴着口罩还围着围巾戴了帽子,一身黑色羽绒衣,整个人严严实实,就是一堆行走的衣物,为什么会说她漂亮呢?并且她不觉得他正眼直视了她,像那些会不错眼珠地盯着她甚至会对她吹口哨的男人那样,甚至在说那句话时他也并未看她,只是向前走。她走出很远,快转弯的时候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却见那个男人在路的那端也停住了。她犹疑着,不知该走掉还是待着。按照她平常那种超强而奇特的自尊,她是要走掉的,但疫情期间,每次出门见城市冷清,门户关闭,她就觉得为数不多的路人之间存在着一种不需表现出来的温情。她没有马上走掉,然后那个跛脚男人就走过来了。
在悬铃木新叶成荫的初夏,他们结了婚。那张背景是上海老街绿树的婚纱照,我羡慕了很久。可是叶子还没黄时,他们就离了婚。
滕薇的高学历和高收入给我们这些表妹表弟造成了不小的压力。这桩被家族人视为失败或胡来的婚姻,成为她唯一而致命的缺点。这一年,滕薇从我们的榜样跌落成引以为戒的对象。女孩们差不多都受到了家里的训诫,婚姻大事假如跟滕薇学的话,以后就不要进这个家门,云云。我想,这对滕薇来说其实是无关紧要的,在我和悦颜看来也是。当时在我们三人组成的小群里,我俩用极可爱的表情送了滕薇一朵小花花。
可惜我一直是个废物,努力也追不上滕薇十分之一,何况根本就不想努力。悦颜却是刻苦,一心扑在专业上,而今在读名校博士,前方已有几所高校可任她屈就。
儿子成为公司老板,女儿成为大学教授,是舅舅一生的梦想。他年轻时在同龄人中算得有文化,后来做小生意,长年累月下来他明白一个道理,凭自己这辈子是不会露脸了,只有依靠儿女来光耀门楣。儿子当老板,然后找个知识分子家庭结亲,女儿当教授,然后找个亿万富翁来嫁,如此,便是名利双收,四角俱全,十全十美。
把滕薇迎进我简陋的新房里,首先得到她封的一个厚厚的红包。我开心极了,当场打开,查看有几千。滕薇笑说:“看你这样,当初就问要不要借点给你,还嘴硬。”“本来就是没多少钱嘛。”我说,“还比不上上海房价零头的零头。这还要向人借,一点面子也没啦。”
滕薇原本很瘦,现在长了些肉,整个人由内而外显得有点松弛。和以前一样化着妆,这是刚刚结束了公务。起初她是不喜欢化妆这件麻烦事的,后来全盘接受。她说,那些衣冠楚楚内心脏臭的货色,只配她以假面目相对。而且,凭此假面,凡事都充分自信,有如顶了一面盾牌。
时间是午后,我们吃过饭,懒懒地歪在阳台的椅子上,说话喝茶。说起小时候进城来玩,看到这铁塔,总是被它的阴森威严所震慑,不知道它到底包含了什么样的过去,藏了些什么事情。也没有登上去过。铁塔下的那座大学校园,百年里也饱受风雨和屈辱,这几年是有明显的壮大趋势。也是悦颜未来工作的选择之一。
“悦颜会爱那个豪门丑男未来总裁吗?”这是个我绝对不想听到肯定答案的问题。
“她到现在都没和那男的牵过手。”滕薇叹气,“她自己什么道理都知道。但是呀,不是光知道就可以,知行合一才是真知道。”
“为什么偏偏选了个这,极限挑战吗?”与其说我是不解,不如说是气愤,“她虽然一直很听舅舅的话,但现在长大了呀,读研都没问家里要过一分钱。当然舅舅也不给。中秋那天吃饭,她都敢掀桌子甩脸子了,多棒啊。”
好一会儿滕薇才说:“她那是恨极了。要是那时候她能这么做,就好了。”她把那时候三个字说得很重。
她確实有话要说,可就像说不出来似的。然后,她拿出手机,划了几下,给我看上面的内容。
那是悦颜向滕薇求助的信息。
事情发生在悦颜大学所在的城市,周末的惯例安排,父母亲友安排的相亲。这次是同学介绍的男人,约了见面吃饭,这人一身簇新西装,眉眼挺有精神,很是健谈。过程中不时劝酒,使悦颜平生第一次醉倒。之后这人把她带到酒店房间,强奸了她。悦颜清醒过来,先告诉介绍人同学,同学说,这事是不好,不过还是算了吧,闹出去对谁都不利。悦颜便回去洗了澡换了衣服。某个时刻,不甘和痛苦像针扎着她。
“然后,她就发信息给我。”滕薇说,“我马上回电话,告诉她,一定要报警。现在就去医院做伤情鉴定,然后去最近的派出所报案。如果她不去的话,我马上开车过去和她一起。还好,她照做了。那个男的也承认了。”
我赶紧问:“判刑了吗?”
“判了。”
“判了多久?”
“不清楚。我没有具体问她。”
我站起来,急得跺脚。我一定要知道那个罪犯判了多久。
所以,之后悦颜那么讨厌酒,讨厌男人借着酒逞脸,即使是父兄也一样丑恶无法忍受。可是,她也无法正视自己,索性将自己随意对付了,换得一时清净。
“不。我想她是不愿意再受相亲的折辱。”滕薇说,“现在,我们只能劝她不要着急结婚。”
“是,即使做个坏蛋也要极力劝阻她。即使在她穿上婚纱就要走上红地毯了,我也要再劝她一次。”
“可以,很好。”滕薇微笑着,“可惜我看不到那时候,春节之前我就得走了。”
我揉了一下眼睛,远处的铁塔在视野中清晰起来。滕薇端起咖啡杯,和我一同把目光投向那老而又老的建筑物,美轮美奂的艺术品。
我们对铁塔有着不一样的感受。总的来说,铁塔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字,美。而滕薇却说,看到铁塔,会感到心痛。
“记得以前看过一种说法,说是太美的事物会让人绝望。”
“也许吧,”滕薇说,“一种孤独的美。”
夜晚,滕薇眉间的笑多了起来。我们靠在床头,在温暖的灯光下说了许久的话。最后她说:“你要当作家,不管是写网络小说还是什么,我都觉得特别棒。我觉得你的心里有把火一直烧着,从小到大都是。我呢,我的火只烧在外面,内里都是灰烬了。好在那是还没凉透的灰烬,还有点热乎劲儿,够我用了。”
滕薇又说:“我特意来你这里一下,不专为悦颜的事,也有我的事。有一件事,我從来没有对人说过,除了我爸妈,也没别人知道。”她笑了一下,把手遮住了眼睛,“我说给你,不是要传递给你负能量,你可以当小说素材写出来。就是,是这样——发生在悦颜身上的事,我也遭遇过。小时候,十二岁的时候,那是晚自习回家的路上,碰到那个人,他说送我回家,我几乎没坐过汽车,就很开心地上车了。可是车开到了我不认识的地方。我回到家的时候已经半夜了,我很害怕,告诉了爸妈。那个人是咱们的亲戚,对我家很好,帮了很多忙。我爸妈不想把这件事传扬出去,我爸揣着把刀,找到那个人,要杀了他。可我爸下不了那个狠手,只捅了他两刀。那个人也不敢声张。你想知道那个人是谁?很好知道,我家再不来往的那家,过年聚会也是有我家没他家。那之后,我爸就觉得对不起我,后悔没有杀了那个人,每天上学送我,放学接我,从不让我单独出门。没事的时候,他就揣着刀到处转悠,看谁像罪犯想干坏事。我们家,没人再提那件事,当那一切没有发生过……这几年妈妈去世了,爸爸也去世了,对于人世间我已经没有留恋。可是不行啊,还得好好活着,想来想去,移民算了。那种幸福的生活场景,小男孩小女孩在屋子里跑来跑去,小猫小狗铃儿响叮当,面包烤好出炉了,外面开始下雪,我想象过,可我永远不能是这样的人。我只能是一个人。”
我抱住滕薇的一只胳膊,一时说不出话来。我的脑子大概是轰鸣了一阵,以至于中间有些话我不曾听进去。天气真的转冷了,我感到双足冰凉,冷得恶心,身体止不住地瑟缩颤抖。
那个人,我差不多已经猜到了。奇怪的是,我在心里忍不住把亲戚里所有的男性过了一遍。我想,等到那个人死了,我去他坟上送一副庆贺的喜联。不,这没有什么用,我要——我希望在他有生之年以一个小辈的张狂,当面狠狠地唾骂他诅咒他。
滕薇说,那一年,她有一本英文教辅书,封面是被灯光映照得璀璨无比的一座塔桥,桥下的河水波光潋滟油画一般。她对我说,我们将来一定要去这个地方。我说,好。而那时候,我们生活的全部世界是小镇和村庄。
我隐约记得这回事,记得那个灿烂而深沉的古老建筑,代表了外面世界的温暖辉煌似的。可是又绝没有作为一个承诺记着。
寒潮如期降临,一夜是北风凄厉的呼啸,几次把我从浅睡中惊醒。蒙眬中我不断地想到下一部网文零零碎碎的情节,又有点替铁塔担忧。它经受过几次洪水,泥沙埋了基座,也受过贼寇的炮火,躯体多年残缺。在它漫长的注视下,许多生命湮灭于水里火里。今日这样迅猛的风中,它不会颤动,它果真支持得住吗?我披衣起来,去把窗户关紧,然后特意到阳台望它。黑魆魆的身影,在夜的粗犷线条里像是金刚法身,泰然憩息。
我知道天快亮了,滕薇就要起身离开。在许多因素造成的泪眼蒙眬中,我有一点明白。对我而言有些事物就像铁塔,我并不住在铁塔里,我实在需要住在一个现代化的新房子里,最好是大平层,甚或是别墅,但我无法满足于此,我需要时不时看到铁塔,巍峨安详地耸立在晴空之下,宛如一个含义模糊的梦。
快到元旦时,游人涌入,这座废掉了的古都焕发起旅游城市的神采。黄昏下班路上,有个人向我问路,问去铁塔怎么走。我说,铁塔公园这时都关门了。
“没关系,我就是看看铁塔。”她说。
我给她指明了方向路线,包括如何乘坐公交车。
她白了大半的卷发在围巾上显得亮亮的,笑着对我道谢,然后就向北一直走去。
我们的路线是重合的,但我故意避开她,离远一些。一路上,我看到她不紧不慢地迈着步子,时不时向前方张望一回,好像不及时望见就会错失似的。
责任编辑 张 琳
创作谈
为她们而写
她们并不是完全虚构的人物,即便你不认识她们,你认识的人也很可能认识。在幽暗的角落或者堂皇的场所,她们遭受了严重的身心伤害,却无法诉说和排解。实际上,不少女性都或轻或重地遇到过性侵犯,甚至,那已经成为一种必须忍受而不能介怀的正常现象。到底是为什么呢?
每次听闻这样的事情,我都非常非常难过,超出年轻些的时候会感到的愤怒。多了一些思考,就多了沉重。对于这篇小说里所写的伤害,我无法做到感同身受,可也不能纯以局外人的眼光来审视。我和她们应该而且确实有着最亲近的关系。因为有着同样好的品质,同样美的追求,同样艰难而顽强地生活着。就如古老的铁塔,历经沧桑而依然屹立。也许我把铁塔当作了女性的化身,至少只要我愿意,就可以让两者之间有共通的精神。
也不是所有女性都适合或需要婚姻。直至今天,婚姻的决定在许多情况下仍是含混的,随意的,被动的,荒谬的,总归就是错误的。在父权的管控和重男轻女的环境下,很多女孩的自尊被大大降低,潜意识里委屈自我,顺从他人意志,即使成长为一个看起来很优秀的女性,也未必能获得幸福的人生。
女孩的人格其来有自,主要就是赖以长大的家庭。出于血缘关系,家族是个联合的整体。出于家庭之间的互相独立和竞争,家族又是个深藏龃龉的存在,其中也产生了各种权力关系。
在旷野中感到的孤独胜过在喧嚣洪流中的无助。即便都是痛苦的,也因为自由或不自由而大不相同。但愿我们有自由的孤独。
我所想到的一些问题,也许无法在这个短篇小说里完整体现。有意无意地体现了一点吧。近乎本能的出发点在于美和同情,借以抵抗痛苦,安慰“我”和她们的心灵——作为写作者,其实并没有这样想,但就是这么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