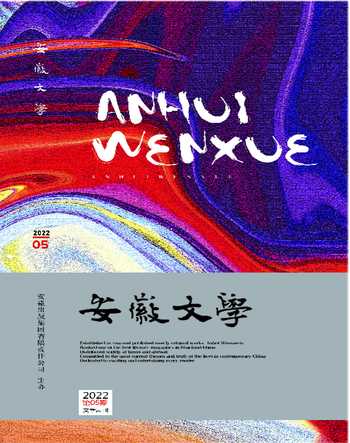游牧
王闷闷
一、我们去哪里?
我们是在做什么?!妻子愤怒地扔掉手中拿着将要放进收纳箱的碗,碗与地板砖猛烈撞击发出的清脆声划破房子里这几日混浊黏腻的空气,他知晓这刻迟早会到来,发生了也好,不然老积压着,厚到一定程度,谁也无法控制。地上除了碗的碎片,还有收拾好的大包小包和将要装进纸箱带走的物件。遇上这种情况,他说不上是习惯,心有余悸应为最好的表达,这时语言也最是苍白软沓,应运而生出的支支吾吾会助长潜在火苗的燃烧。他不说话,她不说话,在这个房间他们制造的只有静默无趣冷寂。他拿起门口拐角放着的扫帚簸箕清扫碗的碎片,寻找坚硬气流中柔软的间隙,当然,这个只是自我感觉下的判断,清扫到离她稍远的位置,说,你不要多想,这只是暂时。她冷笑,说,你告诉我,我们如此这般重复了多少次?或者说,这是第多少次?他陷入沉思,具体的次数能数见也数不见,想着过几分钟就会忘却这个话题。
几分钟过后,他说,一直忙于收拾整理,还没来得及吃饭,我给咱叫个外卖,你想吃什么?此时的灯光异常明亮,像是刻意要赤裸他隐藏的用意。见她不说话,痴痴地看着对面空荡荡的墙壁,他试探着说,好赖吃点儿东西,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她眼睛从墙壁挪移到他身上,像是初次见面,上下打量,说,收起你那点儿鬼心思,别想绕开问题。他依旧抱有侥幸心理,明知故问,什么问题?她拿起桌子上的杯子,举起,说,要是再打马虎眼我就再让你听一遍。他说,非要说出多少次?她举杯子的手升高,说,你以为我是在和你开玩笑?他连忙说,不不不,我说。她等待着他口中说出的数字,这种执着倔强里包裹了太多无奈和愤懑,说不上完全是在和他较量,也不是在和她自己,所以不能说出无理取闹这几个字。一切没有这么简单,就像他们这次搬家。
他回忆细数从他们认识到现在搬家的次数,不自禁地自言自语起来,我们到今天认识有九年多,刚毕业那阵儿和你去看房子是在东郊,在那里住了十个月左右,随后搬到几公里外的老旧小区,因为那里房租便宜……她呵斥道,不要说出声,在心里数。他照做,心里依着时间想,伸展手指头记录次数,七八分钟后,说,这是第七次。她举着杯子的手慢慢落下,以为会息事宁人,没想到杯子还是掉落在地上。他满脸迷惑地看着地上形状各异的碎片,说,不是这次搬家没有这么简单,是每次。她说,别说得那么高深,少用你那套无用且走火入魔胡思乱想的所谓的哲学思想解读,生活中用不到,怎么就不简单,有什么不简单,我们搬家无非是没有钱买不起房和工作摇摆不定。他欲言又止,不想争吵,在手机软件上叫了饭菜。
饭菜摆上桌子已是十点多,他在橱柜里拿出碗筷,舀好米饭,放在她面前,说,这些都是你平时爱吃的菜,多少吃点儿,一切终会好起来的。她眨巴着眼睛,硕大的眼泪啪嗒啪嗒落在桌子上手上裤子上,说,我们这种日子何时才是头?这次去的那里,你要知道,我们已经投降给现实,去了市区边缘。他不能再说类似于前面的大话空话,给她夹菜,随即自己端起碗埋头吃饭。她没再多说,饭吃毕洗刷过碗筷,躺在床上盯着房顶的灯和白墙看,说,我们到底要去哪里?他回答不上来,长叹口气,看时间在这间房子里流逝,时间会洗刷掉人生命里所有的难题,包括她问出的问题。
他起身去关敞开着的窗户,看到楼下的小区,深浓的夜色中,站立的路灯清晰可见,静寂再现,不自主地坐在飘窗上,回想她这几天问过的那些问题,在这个城市他们到底有没有留下痕迹,从现实层面看,南郊北郊东郊西郊都住过或长或短的时间,比如说现在这里,算起來住了有一年半,每日的来来往往中自然生长出了记忆情感,尽管心知肚明这里不会住太久。按理说移动会让人愉悦,怎么就会这么苦大仇深,总想着落地生根,从而延伸出记忆由何而来?记忆是否真实?刚才想过,这种短暂的居住也会生发记忆情感,还有,流水不才是最为鲜活吗?死水一潭什么时候发展出了这种令人向往的魅力?拉上窗帘,看安静下来的她进入了睡眠。她最后说的,我们要去哪里?是呀,这次搬家后多久又会搬家?从这里到那里,之间到底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到了那里,是否刚休整差不多又要搬离?
二、身体·匈奴
每次看镜子里的自己,不,应该是镜子里的人,他就有想和镜中人交流认识的冲动,他觉得他不是这种容貌,是否存在着意识里认同的那种容貌,尽管现有的身体容貌与之相差甚远或有些差别。他说不清,假若说,镜子里的人不是自己,那为什么又在身心思想上有些相似呢?在一些场合,经常有人会惊叹他的身形,说,这种高大宽厚魁梧的身材,不像是汉人。这时他有几分羞惭,脸泛红,红色会在脸上堆积,直至燃烧起熊熊火焰,这是个恶性循环,越是担心害怕什么就越会出现什么。有人说,就是就是,你看这肤色,红黑红黑,像是外国人。他用挤压出的微笑回应,以化解尴尬。到这里没有结束,因为他有新的举动,手不由自主地摸脸颊的胡子,这样做实则是想给脸颊降温,好尽快恢复到正常温度下的肤色。有人接着说,对呀,这么旺盛的胡子,蒙古人和欧洲人最多,咱这里的人少数。他无言以对,借着生硬的理由狼狈走开。
走在路上,他恨不得用衣服将自己的脸蒙住,可是不能,这样更会引起路人的注意。如果有个口罩就好了,想着去路过的药店买一个,没承想,经常一路遇到最多的就是药店,此时像是和他作对,一个都遇不到,心中纳闷,怪事一件,是不是在他这种情绪爆裂中产生了虚无的幻象。胡思乱想中忘却了此事,脚步没有了方向,漫无目的地走,到家快餐店,进去坐下,服务员过来问想吃什么?他看着桌上的菜单随意点了两个。服务员不大会儿将饭菜端上来,说,要不要来个酸奶?他说,为什么喝酸奶?你们店里的特色?服务员说,不是,你看起来像喝酒了,听说酸奶解酒。他说,你是看我脸红?服务员点点头。他说,不要靠单一的表面现象去做判断,我没有喝酒,脸一直都是这样。服务员说声对不起不好意思,迅速走开。
他边慢条斯理心不在焉地吃饭,边用眼睛偷看自己的脸,看到的多是鼻子尖,红色还在,装作看其他实则扫视周围的人,尤其那个服务员,是否注意着他,是否跟同事在说他。他拿起手机,打开相机设置到自拍,看自己的脸,确实不像周围其他人的肤色,他的脸为什么这么红?以前,他为此专门去医院的皮肤科看过,医生说是角质层薄,容易受外界冷热的影响,换句话说,脸上的皮肤过于敏感,给开了些药让回家按时服用。药服用完,脸上的红色没有任何消退,一切照旧。再去医院医生再看再开药,服用后依旧无用,反反复复几次,他放弃了。想来不是医生说的那些原因,医学是建立在理论实验科学的基础上,但毕竟还是有所限制,就他这个脸容易红的症状,事实证明医学难以医治或难以很好地医治。
从而说来,或许经常被人说起是蒙古人不像汉人这些是对的,每次照镜子就能得知,只是不敢承认心中的猜想,觉得没有依据,会被说神神叨叨。他从饭馆出来,急匆匆回到家里,进到洗手间对着镜子看,今天定要问出个究竟,说,我到底是谁?镜子里的人说,你想成为谁?他说,对,就是这样,我们说的不一样,说明我们真的不是一个人。镜子里的人笑着说,我不是你,你不是我,我们自然不是一个人。他说,说得好,不要觉得我身材魁梧爱脸红胡子多就觉得我是你。镜子里的人说,我从来没觉得,你是谁你自己心里比谁都清楚。他说,我是谁我还真不清楚,但有一个可以肯定,绝对不是你。镜子里的人点着头,大笑。他说,你笑就说明我说得有些不对,那么,我是两个人,现有的这个人和意识里的那个人,不,我要说得宽阔些,给我自己留够空间,让你无话可说。他专心致志地看,想起凝视可以看到许多时候看不到的疆域,眼睛酸痛时,他脱口而出两个字,匈奴。
对的,原先到现在面对的好多问题只要遇到这两个字一切就迎刃而解了,他身体里有一种远古的记忆,这种记忆不会在时间长河里的身体变更中丢失,一直内核样保留,匈奴的表述不敢说是最精确,但总是有了开端。有哲人说,一个人不能同时踏进两条河流,这句话的对立面最能解释他这个奇妙的想法,要知道,反过来说,两条河流也不能同时被一个人踏入。不管怎么说,以后的日子里,他可以在此基础上深入辽远地思考许多问题,最主要的是可以应对那些人说的让他听起来比较难堪的话语。无论他们说什么,他只要冷静地说句,我是匈奴人,他们便再难有对他外表相异引发出简单粗鲁的猜测和质疑。
三、停留·语言·构建
这天下班,妻子做饭,他坐在卧室的桌子前整理工作中用到的资料。饭摆上桌子,妻子叫他过去吃,他看完剩下的两页过去,坐定后环视客厅里还没有熟悉的一切,算起来搬到这里还不到两个月,再住段时间就会有感情。妻子说,不吃饭看什么?他说,我们也会对这里熟悉起来。妻子说,熟悉了又能怎么样?还是要离开,前面住过的几个地方难道没有熟悉?只是陌生得更快,离开就是陌生。他说,整个世界的万事万物运转就是这样。妻子说,你意思是经过多人断断续续经验情感链接形成的世界?他说,差不多,任何一个地方,就算是我们买下来,如今的城市建设,房子产权七十年,正儿八经能住到七十年吗?现在那些老房子,最多时间的也不过五十年,无限逼近拆迁,拆迁后新盖起来格局不同或用处不同的房子场所,谁能说这里的熟悉就能保留?妻子说,假如按你说的,谁都无法停留,居住的记忆终究抵挡不住形而下物事的变化。他说,不然呢?妻子说,吃饭吧,别再自我安慰,即使如你说的,那人家搬移的速度也是缓慢的,停留的时间长。他夹起菜吃几口,扒拉些碗里的米饭,那会儿的饥饿不知去了哪里。
妻子见他食欲不佳,说,因为我们刚才的争论?他惊诧地说,什么?妻子说,对房子熟悉停留这些的争论。他说,你说我因为我们争论而吃不下饭?妻子点点头,他笑着说,不至于,你把我想成什么了?妻子说,谁知道你自己是怎么想的,今天同事们闲聊,说起买房子,趁着这边房价不高,赶紧买。他说,我说几句你不爱听的。妻子说,既然是我不爱听,那就不要说。他说,我仔细想了,我们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不仅仅是表象看到的那么简单,比如像你说的工作生活贫穷这些。妻子语气里充满了厌恶,说,不是这些是什么?是一些神秘的看不到的力量,还是我们这些人从出生起就注定奔波就应该不停搬移?他说,你看我的肤色身材脸上的胡子像什么?妻子细细打量,说,像什么?他说,我觉得我是匈奴人,身体里有着他们生存基因或者是远古记忆的留存,刚好在这个时代被唤起,其实前两天我还是矛盾的,因为我意识深处拥有着另一种生存方式和样貌,是那种闲情逸致飘逸无比清雅清秀,昨天我明白过来,意识深处是接受了书籍和现有生存方式摇摆渺茫混乱交织影响下产生的模糊渴望。妻子说,你的胡言乱语留着你自己享用,说来说去不就是想说你愿意搬移,你的本性就是这样,你是匈奴人吗,骑着马四处游荡,对不?但我要说的是,我不是匈奴人,我没有你这种远古的记忆和呼唤。
他无以反驳,家里待着烦闷,出门在小区里走走。这里的环境比市区好很多,人也不多,生活节奏自然就慢,走在小区里能听到人家里的炒菜声,抬头看天空,有月亮有星星,若有所思往前走的路上,听到有人说,这是月亮,看。循声看去,一个老人带着四五岁的孩子,站在谁家装修拉来的沙子边,孩子手里拿着玩具铲子和翻斗汽车,认真听着看着。老人说,给爷爷指下,哪个是月亮?孩子聪明地抬起胳膊,伸出手指指着天空。老人说,不错,爷爷再告诉你,那些是星星,咱那里方言是星宿。孩子点着头,眼睛不时瞥看沙堆上修建半拉的建筑,说,星星和星宿不一样?老人说,一样,是两种不同的叫法,比如,回到咱家乡那里,大家都叫你猴娃娃,这里的话不是叫你小朋友就是小孩子。他走过去,站在旁边近距离观看他们,老人明晓他的意思,说,也有同一種叫法的,比如这位叔叔,到哪里都称呼叔叔。他说,这个说不好,我能问问小朋友修建的是什么建筑吗?孩子看眼老人,征得老人同意,兴致勃勃地说,这是个城堡。他说,童话里的城堡?谁住在里面?孩子说,我住在里面,这是我的地盘。他说,如果这堆沙子被搬运走,你的城堡不就没有了?孩子说,没了可以再找个地方修建,我的城堡我的地盘一定会有。他说,为什么非要有你的地盘,跑动飞翔着不好吗?孩子说,我要有自己的地盘,不然在哪里落下,鸟儿都有巢穴,不对吗?老人说,孩子就是在沙堆上刨挖着玩,游戏而已。他笑着说,我们哪个人不是一辈子在做这样的游戏?
出了小区去不远处的广场转悠,接到朋友发来的信息,是几张图片,他发文字过去,这是哪里?怎么看着这么熟悉。你真认不出了?认不出,你说下。这里是你刚毕业那会儿上班的地方。四区?对呀,你辞职后,这里进行了拆迁,修建成现在这样。现在叫什么?环形艺术中心。四区到环形艺术中心,两个天壤之别的名字,四区几十年形成的概念内涵是个城中村,里面有迷宫样的巷道,巷道里有能满足人们生活上所有需求的店铺,还记得我们那次入夜进去后闲逛不?数不清的霓虹灯闪烁不止,映照着夜色与本身就黑漆麻乌的地面墙壁,你说这里的人也黑漆麻乌,我说我们也黑漆麻乌。对呀,但现在就是变了,环形艺术中心是整个省城最大的艺术区,里面有各式各样的场馆,往后这里会给人们形成这样的概念内涵。四区里住的人去哪里了?拆迁有安置房,搬到其他地方,还是叫四区,一个新的地方会被叫作四区。四区之前这里叫什么?之前的之前是什么?这种追问看似没意义,但我们一代人在用文字语言构建一代人的记忆。再大胆些,文明文化是否也是这般构建的?最难的悖论出现了,就像哲学里思想的思想怎么说,这里文明文化之前的构建又是谁构建的?毫无新意的变化流动是变化是流动吗?我说不上来,回答不了你的问题。
四、逐机械虚无而居
第八次搬家在两年后到来,这次不同的是,妻子收拾东西时没有以往无奈无望下的气愤,而是很有兴致地设想搬过去后如何布局摆放,他心情也放松,对于他们来说,可以退而求其次甚至最少,不敢有太多奢求。这次是他想办法争取的人才公租房,与政府签订租赁合同,只要不超出规定的条件就不会被清退,减少缓和了搬家带来的惆怅。夜里躺在床上无眠,妻子说,我们在城市努力十年了,依旧没有自己的房子,是不是我们太没有本事?他说,我们是完全靠自己的本事在拼搏,没有任何人帮扶,也许真是你说的我们没本事,但我们也真的尽力了。妻子说,搬吧,十年都搬了,还怕再来个十年?只是希望我们的孩子不要再重复我们这种没意义的搬移。他说,你说得对,没意义的搬移,看似忙忙碌碌,实则不知在为何搬移,我还是坚持原先的想法,促使一次次的搬移没有那么简单。妻子说,是没有那么简单,其中的复杂难以说清,你说你是匈奴人,那我就是匈奴人的妻子。他说,现在不是匈奴人了,是包容所有类似于匈奴人生存方式的人。妻子没好气地看一眼他,调转头自顾自睡去。
第二天搬家公司的车过来,大小不等的包和家具一件件搬到陌生且远离的房子,最后由于司機催促,没来得及多看搬空的房间和两年里走了上千遍的小区,他和妻子坐在驾驶室里,搬运工人坐在车厢里。出了小区,进到宽阔通畅的路上,司机说,不是我故意催你们,是每日搬家的人太多,我们跑不过来,如果去得晚了,要搬家的人不开心,公司也要扣我们的钱。他说,能理解,我有个问题想问你,你每天都在为各种家庭搬家,你感觉我们是为什么搬家?司机皱起眉头,说,别说,我真想过这个问题,我问过一些搬家的人,没有答案,我也没有在这里买房,租房住,隔三差五也要搬家,比如上次搬家,原因是妻子怀孕,需要个宽大些的空间,原先租的地方太小,我知道这不是根本的缘由,我想有内在深刻的某种神秘动力在驱使。妻子看一眼他,嘴角上扬起,装作看他衣服上有什么凑过来,很低声地说,没想到这里遇到知音,你开心坏了吧?他看一眼妻子,眨巴眼睛示意不要胡说八道。
司机在等红绿灯时,拿起车座上放的矿泉水喝几口,说,我们年纪相仿吧,我大学学的是哲学,毕业找不到合适的工作,逛荡了几年,读硕读博深造的机会错过,考编这些也没有心力,结婚加上有了孩子,着实不能再有空幻的想法,不是不能,是没有时间精力,孩子成天叫爸爸,我能怎么办?你说的搬家,好像是我们这个时代注定的,在偌大的城市里飘移来飘移去,不知道为了什么,现实中的理由看似特别正当,等夜里躺下细细琢磨,这些理由都不值一提,太瓷实了,没有空隙,你明白我的意思?他说,好像能明白,你是说我们像游牧民族,哪里有草地水源就去哪里,一个地方待一阵接着去下一个地方,对不?司机说,通常意义上的游牧民族是逐水而居逐草而居,我们是在逐什么?他说,你在这个城市生活了几年?搬了几次家?司机说,生活了八年,搬了六次家,有时候朋友相聚,经常会说到谁谁买了房,这下落住了脚,现在,固定下来成了一种骄傲和荣誉,就像我们现在用的导航,必须有从哪里走和去哪里的地点,没有地点怎么定位,不,不是没有地点,是没有属于自己的地点。他说,你说的有意思,是的,我们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定位地点,想拥有个属于自己的定位地点,不然就会迷失在这个漂浮无趣的城市里,有一个问题出现,我们真能找到和拼搏到属于自己的定位地点吗?日新月异的变化里谁不是新的谁不是旧的?司机耸耸肩膀,表现出无助,说,我们连自己每天在做什么都不知道,好像是为搬家而搬家、为活着而活着、为吃饭而吃饭……丝毫没有延展,有相对的解决办法也没有相对的解决办法,我们在这里追逐什么生活,追逐什么?
追逐什么?他跟着说了一句。汽车过了收费站就进到市区,路上车辆当即密麻起来,不敢再和司机说话,专心开车成了正事。司机也收起话语,面无表情,双眼无神地开着车,在车流中穿梭,不时看眼手机上导航的地图,地图上移动的蓝色三角形代表的是他们,正在靠近要去的地点。有段路很是拥堵,车子小脚老太太样移动,妻子看着望不到头的汽车,说,现代社会现代城市现代生活真是无解,大家每日在奔波移动,却不仅在现实中留不下痕迹,而且精神记忆里也空无一物,经常出现在脑海里的问题便是,这是哪里,我在哪里,我要去向哪里,我是我吗,我不是我我是谁……
责任编辑 张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