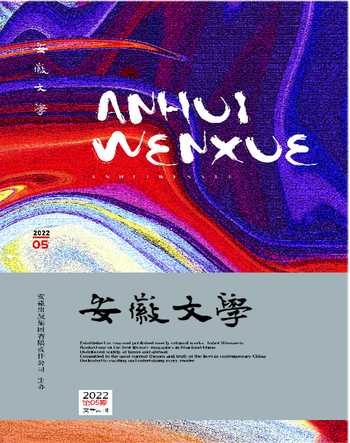游民
黄大鹏
我一星期三次经过天桥都见到那个男人,或许他一直在天桥上,只是我以前没注意到。那时候不像现在这样悠闲,从上午散步到中午,从下午散步到黄昏。我不太愿意回忆啃着面包踢踢踏踏快速通过天桥去乘坐早班地铁的日子。过去和现在时常会形成对照,总会在彼时或此时滋生失落之情,日子就是日子,不该是旧日的延续或对照。我这样想,但不确定能做到。
男人五六十岁,穿一套皱巴巴的黑西服,脚上穿着白色运动鞋,鞋帮已经发黑。他坐在地上,屁股底下铺了一张报纸,头发灰白稀疏,梳得很服帖,三七开,眼睛灰蒙蒙的,像患了白内障,嘴上的八字胡轻飘飘的。他噗噗抽烟,不去理睬掉落在西服上的烟灰,他从边上的黄色旅行包里拿出一本没有封面的厚书,读了几页,放回去,仰望天空。阴天,远处有雾气,城市像是海市蜃楼。他看了一会过往的行人,站起身,把报纸往边上挪了挪,睡到地上,枕在旅行包上,哼起含混的小调。
我对他没有好感,这样的人往往懒惰,不学无术,擅长行骗,他们会算卦,表演街头魔术,推销延年益寿的产品,鼓吹一个一本万利的项目。父亲被骗过,到城里做工,走在路上,几个中年男人在争吵,都想买对面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手里的方鼎。方鼎被铜绿包裹,男人说这可是商代的青铜器,两千你们都不肯出,我不卖了。父亲花了两千买下了,电话里很激动,说给我买了件传家宝。我特地找到一個做珠宝鉴定的同学,同学戴着白手套,拿仪器照了照,把铜绿铲下一片,露出灰色的水泥。
地铁进站语音播报的声音把他唤醒了,他看到了我,我立刻把视线转移到手表上。他开口了,声音浑厚,时间对我来说不重要了。对我也一样,我说。确实,我一度效仿学生时代的生活,挥霍不以为意的时光,看电影,上网,踢足球,在图书馆发呆。但我知道我在刻意复制青春,不敢正视江河日下的岁月,从我坐在大学图书馆招来一群大学情侣好奇的目光起,就明白我是“滥竽充数”的那位,我的青春早就翻篇了。他说,你失业了还是失恋了?我笑了笑,递给他一支烟。都是,我心里说。老板两年前就公布了“换血”计划,我这四十岁的大龄“码农”能苟延残喘两年,已是老板格外开恩。老板开导我,说他自己也后悔入错了行,靠科技吃饭的一不小心就会被时代淘汰,诺基亚、柯达就是血的教训。他说他应该去干房地产,房地产经久不衰,不会被时代淘汰。我并不悲观,其实在裁员大潮伊始,我就为自己的未来做了诸多规划,比较实际的是开一家电脑维修店,一个唱衰IT行业的同事五年前就辞职了,他靠翻新电脑和手机,在上海郊区买了一套房。父亲把水泥方鼎抱回家后,成了村里的笑料,他一蹶不振,没日没夜地喝酒,六十三岁那年脑溢血死在镇上手套厂的保安室里。我没有把失业的状况告诉母亲,虽然她对IT一无所知。父亲出事后,她信了佛教,吃斋念佛,在家里敲木鱼,在菩萨面前为我祈福。相比母亲为我失业后的生计担心,我更忧虑母亲听闻我窘境后质疑起偶像的神力,菩萨都不可信,她还能信谁?
失恋对我来说是一件久远的事了,最后一次失恋让我对婚姻失去了兴趣。那是三年前,我靠一己之力在城里买了一套一百二十平方米的公寓,女朋友杏子在私立银行上班,到处打电话推销银行的金融产品。恋爱半年,我们同居了,我把母亲接过来,初衷是照顾她,结果反之,母亲为我们干起了洗衣做饭的活。杏子的爆发是在一顿晚餐上,我和母亲把饭菜端上桌后,她没有坐到桌子前,而是点了一份外卖,我说菜都做好了,你怎么点外卖了。她冷冷地说,天天吃辣椒,每个菜都放辣椒,叫我怎么吃?我们母子俩享受着家乡口味,疏忽了杏子的感受,她的家乡吃的是淮扬菜系。打那以后,母亲像是魂不守舍,坚决不碰灶台,杏子掌厨,母亲小心地咀嚼,问她好吃吗,她不敢看我们,直点头,像是犯错的小学生。过了一个多星期,母亲要回去,说得忙秋收,我知道离秋收还有个把月时间,再说那点薄田,收不收无关痛痒。母亲是急着要逃离我们的生活。母亲的离开给我对婚姻的向往蒙上了阴影,我想象起婚后的场景:杏子掀翻了桌子,大发雷霆,母亲瑟缩在沙发上。我和杏子开启了无止境的争吵,为各种琐事,我承认大多的争吵是源自我的挑衅找茬,想通过争吵去撕开甜蜜生活的伪装,检验爱情的可信度,如胶似漆变成了水火不容。事后证明这种检验是可笑的,可怕的,好比一场酷刑,非要拷打出人性暴戾消极的一面。母亲听说我和杏子不欢而散,暗自流泪,后悔打扰我们的生活,挑起了我们的争端,又批评我意气用事。傻儿子,你妈能跟你们住几天,日子是你们自己过啊!我坦白,我卑鄙地以孝心为导火索,使得这场本被看好的恋情分崩离析,杏子收拾好行李离开的那天,一针见血地指出我的私心。你根本就没打算挽救我们的感情吧?要是这样,何必要大动干戈,你说一声不就行了吗?我无言以对,她关门之前,留下一句,没人受得了你。
我说,看见你好几次了,你是做什么的?他懒懒地说,无业游民。果真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人,他有手有脚的为什么不去找一份工作。他像是看出了我的困惑,说,一辈子都在工作,想歇一会。他坐起来,理一理头发,谈他自己。二十几年前,他和一个合伙人在武汉做建筑工程,钱包鼓起来,人也就不安分了,包养了一个二奶。我说,饱暖思淫欲。他接着说下去,工程临近竣工,老婆跟着合伙人私奔了,把工程款全卷走了。我笑了笑,心想一报还一报。他说,从那以后,我只有一件事可做,还钱,还银行的钱,还工人的钱,我不分昼夜地干活,有一次钻下水道替人找一枚贵重的戒指,差点被沼气炸死。我说,你境界还挺高。境界?他说,我是赎罪。有几次都想一死了之,农药瓶子都拧开了,想到老婆和合伙人在床上光着屁股嘲笑我,我就想,不能让他们看扁,要死也把钱还清再死。我说,钱还清了吗?他说,十年前就还清了,也不想死了,还没享福呢,死了不值。我说,没想过去找你老婆?他说,找到又能怎么样?她不嫌弃我,我还嫌弃她呢,破鞋。他咧着嘴笑了,露出焦黄的碎牙,现在多好,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他说,你结婚了吗?我摇摇头,跟你一样,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他说,想不到我们还是同道中人,晚上跟我吃喜酒去。我说,喜酒?是你什么人?我想不到他这孤家寡人在城市里还有亲友。他说,走吧,说了你也不认识。我有点犹豫,一方面觉得去参加一个陌生人的喜宴十分造次,更多的是对他不信任,生怕他是一个杀人越货的家伙,把我灌醉或者迷晕,要么把我卖到哪里干黑工,要么割去我的器官。我说,在哪个酒店?他说,哪个酒店?皇家花园吧。皇家花园是本市的顶级酒店,我前老板在那给儿子举办过十岁生日宴。我更好奇了,哪个权贵会邀请这么一个灰头土脸的大叔。出于成熟男人对诱惑和好奇心的本能警惕,我拒绝了他,不去了,晚上有约。
我回到家,从冰箱里拿出中午吃剩的酸菜鱼,放在微波炉热一热,撕开一包花生米,打开一瓶冰啤,边吃边喝,没有胃口。我洗了头,换上白衬衫牛仔裤和皮鞋,决定去皇家花园看一看。做一个窥伺者总比被人牵着鼻子走有安全感。况且,独居生活太乏味了。
皇家花园金碧辉煌,广场上有一座喷泉,立着一个张开翅膀的天使雕像,两个穿着制服的迎宾向每一个客人鞠躬问好。大厅里环立着罗马柱,正中间放着一排指引牌,有婚宴,有生日宴,共八家,我望着层层叠叠的楼梯,像陷入了浩大的迷宫。我找到第五家,找到了他,是婚宴,司仪在台上声情并茂地介绍新郎新娘,他坐在靠门口的一桌,喝得红光满面,这桌应该是备用桌,只坐了六个人。他看到我并不惊讶,招呼我坐在他旁边,替我倒了一杯白酒,我看了一眼酒瓶,五粮液。我说,你是新郎的亲友,还是新娘的亲友?他说,你别这么拘束,吃菜,喝酒。吃了一会,新郎新娘过来敬酒,两人很般配,新娘脸上星光点点,我担心他们会问起我这个不速之客的身份,我多虑了,他们象征性地敬酒,匆匆去了下一桌。这么多人,他们未必每个都认识。
我说,要不要出份子?他说,随便你。我说,你出了吗?他说,出了两百。我说,那我也出两百。吃完婚宴,夜空月朗星稀,清风拂面,我喝得不多,他步履阑珊,我说,你还没回答我,你到底是主家什么人呢?他说,我不认识他们。我说,不认识?不认识你来吃什么酒?他说,你不是也不认识他们吗?我说,我以为你是他们亲友,跟着你来的。他说,你可是自己找来的。我不说话,我没办法和他进行推心置腹的对话,从在天桥上遇到他起,就不知道他哪一句话是真,哪一句话是假。
第二天下午,我在天桥上又遇到了他,他在地上摆了一盘象棋残局,自己跟自己下。他说,来两盘?我说,来一盘,赢了你告诉我真相,输了我赔你一包“中华”。他说,行。我上中学那会,在老家下象棋小有名气,拿过市里少年组二等奖。他走了几步,我看出他的棋艺很一般,中规中矩,不懂得留后手和欲擒故纵。走到十几步,他就大势已去,我并不着急“杀”死他,甚至还用缓兵之计,让他误以为困局已破,走到三十几步,他把手中一颗“马”一扔,说,你玩我呢,看不出来,你还是个高手。我说,谁让你先玩我的,不说真话。他说,我说的就是真话,新郎新娘我都不认识,告诉你,我吃了几十场陌生人的喜酒了。我说,你专业蹭吃蹭喝。他说,这么说也没错。我说,就图个饱腹?他说,不知道,没想那么多。
大概是经受不住他的蛊惑,我循规蹈矩半生,对特立独行有着补偿性质的迷恋,生活如一潭死水,需要泛起一丝涟漪。我说,我跟你去。他说,欢迎,有空教教我下棋。我说,好。我们互留了电话,他手机是杂牌的老人机,没有微信。他说,哪天想去打电话给我。我说,好。
我去了一趟上海,找那个靠翻新电脑手机发家的同事取经,他带我在上海玩了几天,我问起他的生意,他也是只言片语,遮遮掩掩。他带着我去了好几个公园的相亲角,说,壮观不,像选妃一样,你不看看?我在他那待了三天,临走时送了他女儿一个正版迪士尼娃娃。我打了天桥上的男人的电话,我在通讯录里给他备注成“游民”,我说晚上跟你去吃喜酒。地点还在皇家花园,他还是穿着那套黑西服,说,这两天没看你来天桥。我说,有点事。他说,今天给你选。我说,选什么?他说,选在哪一家吃饭。我在指引牌上打量一番,选了一家婚宴,新郎新娘不太般配,新郎矮胖,看上去年纪不小,新娘高挑,正值妙龄。我们还坐在门口的备用桌,同桌有个戴眼镜的男人问我们,李总这边的还是新娘这边的?游民说,李总的远亲,你怎么称呼?眼镜男拆开酒桌上的中华烟,散给我们,说,免贵姓马,李总的司机。他说,马师傅好。我担心眼镜再问下去,我们会露馅,眼镜男接了个电话,出去了,没再进来。新郎上台,比照片上老很多,抬头纹重,秃顶,单膝下跪有点费劲。司仪介绍了新郎的成就,说李总打拼多年,成了享誉海内外的企业家,和新娘郎才女貌。新娘父母上台,看上去和李总年龄相仿,司仪开玩笑说,叔叔,新郎该叫您爸还是哥,要不有人的时候叫您爸,没人的时候叫您哥。台下哄笑,游民说,你准备红包了吗?我说,准备了,两百。他说,今天不出。我说,为什么?他说,这李总不缺钱。
这一夜辗转反侧,我没有出份子,白吃白喝了一顿,心有愧疚,游民没心没肺,吃了大半只澳龙,半盘蓝鳍金枪鱼片,喝了一整瓶茅台,临走还拎了伴手礼——一盒包装精美的白茶。我觉得他有一套吃酒的原则,简而言之,“杀富济贫”。
接下来半个月,我参加了三场相亲,女方是婚恋网站上的会员。我去相亲更多是为了消磨时间,另外不想浪费我在婚恋网站上缴纳的几千块会费。我无一例外地临阵脱逃,我怕她们失望,更怕她们对我抱有希望,我不相信自己能藏起棱角,心甘情愿地向一个女人妥协一生,让一个女人向我妥协一生,更是痴心妄想。试探,真性显露,磨合,龃龉,剑拔弩张,一拍而散。我厌倦了。
我带了一副银质的象棋来到天桥,这是我参加市里象棋比赛的奖品。游民躺在旅行包上打盹,拿小手指掏耳朵。我说,喂,教你下棋。他一骨碌坐了起来,说,年纪大了,不想学了,来两盘消遣吧,让我一边车马炮。我说,那不行,我没那么高水平,再说,这么下你赢了也没意思。他说,那好,让一个车。我说,行,给你先走。下了三盘,一胜一负一平。他说,你放水了,哄我开心。我说,没放水,少一个车,就像少一条腿,残疾。他说,找我有事?我说,找你能有什么事?无非是去蹭饭。他笑了笑,那个李总,靠他老婆家资助发了家,发达后把他老婆踹了,新娘是小三。我说,你怎么知道的?他说,猜的。我说,李总说不定是钻石王老五呢。他说,你观察不仔细,主桌上坐着一个小男孩,胖胖的,跟李总长得很像。我说,讲讲你混吃混喝的故事吧。他说,摆棋,不要你让,边下边讲。我摆好棋,他还是老路子,架起当头炮,说,我主要参加婚礼,大部分婚礼都一个样,喜气洋洋的。我说,说几个不一样的。他一个车跟我的车对脸了,我没吃它,把车移走了,他说,五年前的冬天,雪下得很大,把汽车都埋了,那天晚上,我在小饭馆吃砂锅,桌子碗筷都是油腻腻的,几个民工在另一桌猜拳喝酒,闹哄哄的。我看到进来一男一女,都很年轻,像高中生,穿着臃肿的羽绒服,脸上红扑扑的。他们坐下后,脱下羽绒服,男的里面穿的是西服,女的里面穿的是婚纱。我们都看着他们,他们点了几道菜,要了两瓶啤酒,男的在西服口袋里摸出一枚戒指,戴在女的手上,說老婆嫁给我吧。女的在羽绒服口袋里也摸出一枚戒指戴在男的手上,说老公娶我吧。两个人抱在一起,说着说着就哭起来。一个年纪大的民工穿着沾满泥点的劳动服,说,你们两个哭啥?你们跑这来结婚?男的哭哭啼啼,说他是孤儿,女的要跟他结婚,父母不同意,一气之下跟她断绝关系。民工说,没事,我们做你亲人,我做你爸。他在饭馆扫视一圈,指着我,老兄,你做新娘的爸。那是我第一次参加陌生人的婚礼。
我一走神,露了破绽,被他吃了一个马,我要悔棋,他打了我的手,说,落子无悔。他说,前年还是大前年,十月份,在威尼斯酒店,新郎叫游子豪,新娘叫朱雅婷,新娘家有权势,来了一百多号亲友,新郎家只来了一桌人,都是缩头缩脑的,像没见过世面。新娘家轮番向新郎爸爸敬酒,新郎的爸爸喝了几杯就趴桌上了,新娘一个肥头大耳的舅舅硬要把他扶起来,跟他喝酒,说不喝就是不给面子。我看不过去,走过去,对新娘舅舅说,你们这么喝有点欺负人了,来跟我喝,咱们一口一壶。他问我是谁,我说你别管我是谁,肯定陪你喝好。我将军,双炮连环将,他说,你什么时候把炮藏这的。我说,有几步了,没法悔了,新娘舅舅跟你喝了吗?他说,没喝,他不清楚我底细,这种人就是看人下菜。
我又摆了一盘,他抽走了我一个车,说,给你费点脑筋。我说,你一次都没被识破过?他改变策略,飞起马,说,有过两次,他们问我是谁,我说这不是徐东勇的婚礼吗?他们说什么徐东勇,你走错了,我说不好意思,徐东勇跟我说是这里。他的应对真是万无一失,谁会在喜庆的婚礼上迁怒一个走错宴席的陌生人呢。我吃了他的炮,他非要悔棋,说炮被吃了这一盘就玩完了。我说,悔棋行,徐东勇是谁?他说,瞎编的。我又把他的炮拿走,他急了,说,我那王八蛋合伙人。我心不在焉,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偷奸耍滑,我连失一车一马,被他兵临城下,我说,你恨徐东勇吗?他说,不恨了,他死了。我说,死了?他说,吸毒吸死了,他婚礼我没去,葬礼去了,本来是一个大胖子,吸毒吸成了一具干尸。我说,你是不是幸灾乐祸?他说,说不清楚,我在想,要是当初卷款跑路的是我,会不会也是他这结局。我说,落子无悔。他笑笑说,对,落子无悔。
我继续跟着他,参加各式各样的喜宴,地点都在大酒店,淹没在人海中比较保险。新郎新娘般配的,我们就出两百块份子;老牛吃嫩草的,小白脸傍富婆的,我们就不出份子,大吃大喝,走了还要拎一份伴手礼;男女方有一方明显是弱势群体,我们就前去助威。我看着带回来的几十盒伴手礼,像一堆战利品,我发现自己离不开这种猎奇的活动了,它让我获得不可名状的充盈感。直到有一天,一个朋友给我转了一条朋友圈消息,标题写着:警惕,本市出现职业蹭饭党。配图是几个婚礼现场,我和游民被红笔圈了出来。朋友问是我不,我说怎么可能,是挺像的。当天我去染了个黄毛,站在客厅里自拍一张,发给朋友,说我是宅男。
我低调了一段时间,没有再跟着游民去蹭饭,倒不是害怕事情败露,影响声誉,这件事本身像行为艺术,我无法向别人解释这诡谲的行径。我自己也没有答案。
到了腊月,母亲问我什么时候放假,我说不知道,等通知。我不想回到家乡,空荡荡的村落,几个衰朽的躯体坐在门口晒太阳,谈论陈芝麻烂谷子,从城里回来的年轻人更像是游荡在异乡,舟车劳顿,只为在几天里释放他们积攒了一年的亲情。
游民打电话给我,约我喝酒。我突然发觉,他是第一次打电话给我,我对他依然知之甚少,他晚上睡哪?白天一直在天桥上吗?他的家乡在哪,过年会回去吗?我说,我不想去蹭吃蹭喝了。他说,不去吃酒席,在小饭馆吃羊肉。我不说话,他说,我请客。风很大,刮断了不少树枝,路边停着的车此起彼伏地发出警报声,一群男孩追着一个被风刮跑的足球。游民戴着雷锋帽,穿着军大衣,脚上还是那双运动鞋,我们进入饭馆坐下,他脱下雷锋帽,左边耳根有一道血红的伤疤,像一条蜈蚣,延伸到下巴。我说,被人发现了?这话白问,徐东勇是他的“免死金牌”。他摇摇头,我说,那谁干的?他苦笑说,同行。他说一个月前参加了一场婚礼,他坐在备用桌上,同桌一个四五十岁的男人闷头吃饭,趁着全场灭灯,搬起墙角一箱五粮液,大摇大摆走出门。我说,你见义勇为了?他说,我喊有人偷酒了,我跟着七八个人冲出去,那人搬着酒,跑得不快,见我们追过来,就把酒砸向我们,横穿了马路。我说,后来你就被报复了。他说,三天后,我在天桥上打盹,脸上突然火辣辣的,行人尖叫起来,我一摸脸,黏糊糊的,天桥下有个人在撒腿跑。
羊肉汤翻滚了,我舀去浮沫,他在塑料杯里倒了两杯二锅头。他说,你父母呢?我说,我爸死了,我妈在老家。他说,我有个儿子。我说,多大?他说,三十五了,要是没出车祸的话。我没说话,他也没说话。我说,还是在小饭馆自掏腰包放得开。他说,吃吧,肉不捞就老了。他耳根上的“蜈蚣”在雾气中若隐若现,我说,你过年回家吗?他说,家?我哪有家?他说,别光顾说话,喝酒,干杯。他一口喝掉半杯,哈着嘴,从怀里掏出钱包,在票夹里找出一张泛黄的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十几岁的男孩,眉清目秀,穿着白T恤,站在学校门口。我说,你儿子很帅。他说,聪明,动手能力强,八岁就造出航模,拿过省奥赛一等奖。我说,好苗子,能上清华北大。他说,十七岁那年暑假,高二,来我工地这度假,想让我开车带他去长江大桥逛逛,我说等过阵子不忙了带他去。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我,没打通,就借了工人的摩托车,骑上街,在一个路口被渣土车撞了,就穿的照片上这件T恤。尸体,是铲起来的。他眼圈红红的,我抓着他的手说,节哀。他说,儿子打我电话的时候,我手机关机,和二奶在一起。他抓了一把蒜头塞在嘴里,顿时泪眼婆娑。外面下起了雪,白茫茫一片,雪粒噼里啪啦击打窗户。他说,我在找一个人。我说,谁?他说,徐东勇。我吃了一惊,说,徐东勇不是死了吗?他说,我希望他死,我听说他来到了这里,还过得很滋润,外面养着三四个女人呢。我说,要是哪一天你参加婚礼,发现新郎是徐东勇,你会怎么办?他喝了一碗羊肉汤,脸上浮现出笑容,说,那我就把这王八蛋的好酒全喝光。我不知道是希望他尽快找到徐东勇,还是永远找不到,找到徐东勇之后,他又何去何从?
我说,你在这里有没有参加过熟人的喜宴?他想了想,说,没有。我说,来参加我的婚礼吧。他瞪大眼睛说,你要结婚了?我说,我妈催了,說她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我再不结婚,她怕等不起了。他说,恭喜,什么时候办?我说,开春吧。他说,新娘子干吗的?我说,保持点神秘感,就当参加陌生人的婚礼。他抹着眼睛说,好,到时候一定叫我。
三月份,春暖花开,婚礼定在周末,小范围,总共八桌。我妈激动不已,紧紧拉着新娘的手,把一个大红包递给她,她把红包转交给我,司仪插科打诨,看来新郎主导经济大权啊,新娘子可要小心,男人有钱就学坏。他说,新郎,你有几张卡?我支支吾吾,说有两张卡。他说,新娘子,我刚才问新郎有几张门禁卡,他说有两张,你问问他有几个家。我配合司仪,挤出笑容,我和游民在陌生人的婚礼上听过各种各样的桥段,对司仪的调侃早就无动于衷。
游民不愿意和我的朋友坐一桌,我理解他,他怕在我朋友面前演砸了给我丢脸。他坐在尾桌,和几个小孩坐在一起,小孩们在玩手机,他自斟自饮。
我关照司仪一切从简,婚礼两个小时就进行完了,我厌倦连篇累牍的仪式。没有闹洞房环节,我一个朋友把我远道而来的亲友送到旅馆,我妈对新娘恋恋不舍,我说,妈,回去歇歇吧。她上了出租车,向我们挥手。游民最后走的,拎了一份伴手礼,我说,两盒坚果,档次低了点。他拥抱了我,和新娘握握手,说,祝你们白头偕老。我说,谢谢,电话联系。他说,看吧。
没用完的烟酒退给了酒店,剩菜由一帮亲友打包走了,酒店服务员熟练地拆除舞台,收拾桌子,热闹的婚礼现场转瞬之间就变得冷冷清清。
新娘和我一同坐在轿车后座,她望着窗外,远处一片绚烂,不知道是烟花还是流星雨。我在想什么时候和她分道扬镳,也许不必想,人生终归分道扬镳。月亮高悬,灯火阑珊,黑夜渐渐柔软,晚风吹进车厢,夹着玫瑰的香味。
责任编辑 夏 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