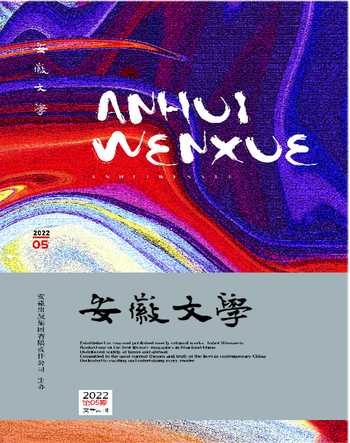遥远的牵手
司玉笙
初秋的阳光下,那个老男人已在村外的小河边徜徉许久。
河边有几行桑树,其中两棵最粗壮。那人就在林间出出进进,而后站在河堤上来回端详,掏出手机换着角度拍照,好像在考察什么。有路人经过,他就问,你是乐桑村的吗?
路人看看他,用当地方言回了一句,就过去了。他听得懂,就轻叹一声,再往村里望一眼……
几十年前,一个男孩作为下乡知青,插队落户到这个村。这男孩会唱歌会谱曲,大队文艺宣传队就把他作为骨干使用。每到农闲,宣传队就到各生产队巡演。演出结束往往都过了午夜。知道男孩一个人住在牛屋旁的仓房里,大队专门安排生产队指定一户社员负责男孩的夜饭。
那户社员家与牛屋就一路之隔。夜间演出回来,院门总是虚掩着的,轻轻一推就开了——这是事先约定好的。
摸进厨房,饭菜就盖在地锅里,端起来还热。每吃到嘴里,耳畔就想起这户女主人的声音,别嫌糙米粗豆,要得管你个饱!除了女主人,还有一个女孩脆亮的声音飘过来,小王哥,得空了也教教俺唱歌。
那时候,女孩正上初中,放学回来就帮女主人做饭洗衣喂猪,采桑养蚕也是一把好手,村里人都喊她佃妹子。
那天夜里回来后,男孩依旧去那院里取饭,当掀开锅盖时,一股热气带着异香直扑鼻面,端起来一看,除了两个米团,还有大半碗炕好的蚕蛹子!
男孩捧着碗正在发愣,忽听得院子里有什么响动,抬头一看,一个熟悉的身影一闪,消失在正屋门内。
几天后,他遇见佃妹子,说,那天的蚕蛹子真好吃。
对方笑笑,看看四周低头不语。
他又问,你喜欢唱歌?
娘说了,想唱歌到桑树底下去,风一吹,那就是最好的歌。
哦,我明白了。
第二年开春,男孩从城里带回来一棵桑树苗,栽到小河边。有人问起,他就说,这是新品种,长大了,风一吹就唱歌。
不过两年,那桑树已拳头粗,枝条蓬散,形似妙伞;叶子宽阔,如同神掌。而最先采摘这桑的就是佃妹子。她边采边唱,声如暖风拂耳。
就在这年冬天,男孩穿上了绿军装,戴上大红花去部队了。
上高中的佃妹子放寒假回来方知此事,就问娘,小王哥走时谁送他哩?娘说,能去的都去了。咱家没给他送个啥?送了,一捧蚕蛹子。热的凉的?凉的,放心窝里焐焐就热了。
佃妹子听了,扭脸跑回屋里。
次年春,那棵桑树旁又多了一棵同品种的树苗。一高一矮,迎风含首相揖,枝头触碰犹如大手牵小手……
佃妹子,你还好吗?
屏蔽回忆,老男人突然对着桑林大喊一声,好像要唤回那个远去的岁月。
你这一喊怪吓人的!一个声音在背后说。
扭头一瞧,是一位老农,骑坐在一辆老旧的三轮车上,也在看树。俩人眼光一碰,同时发问,你是?
相互一抖身份,老农惊讶得上眼皮都斜了,急急地跳下车。哦,你就是那个会唱会弹的小王!
你就是会计毛蛋哥!
四只手紧紧地搦在一起,道道青筋蚯蚓似的鼓动。
老了哩,要不报出名儿,就是脸碰脸也不敢认。退休了,你才有空儿来?
是晚了些……佃妹子她现在怎么样?
哦,她现在是个大医生,奔武汉抗过疫哩……那时候,她就知道怎么防病,生产队的蚕房让她把得可严咧……你夜里回来能吃上热饭热菜,都是她不断锅底火,怕凉了伤胃……
真不知道,真不知道……
我也是后來听她娘说的。她娘还说,你要是个女娃多好,吃住都可在她家。
老人家现在哪儿?
早被佃妹子接省城去了。
她家、还有那牛屋呢?
哪还有啥的牛屋土房?你瞧瞧,一码色的红砖楼房和蚕房,哦,这树还在……第一棵是你栽的,第二棵是她上大学那年栽的——不得了,高考复来第一年她就考上了医学院。
不是复来,是恢复。
反正就是那意思——恁这一开头,谁家只要有当兵走的,考上大中专的,都要在这儿植一棵桑。没事儿我就过来看看,摸摸树心里就暖畅。
明年我定带孩子来多栽几棵。
好,好哇。
说话间,两个老男人已身入桑林。走到佃妹子那棵桑树前,当年的男孩张开双臂紧箍树干,花白的头颅抵在上面蹭磨,簌簌有声。呜咽中,吐出一句谁也听不清的话。
兄弟,你说啥哩?
我,我一次也没牵过她的手,不敢……
老会计长叹一声,拉起他手引向那第一棵树,俩人伸展的手臂顷刻将两棵树牵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