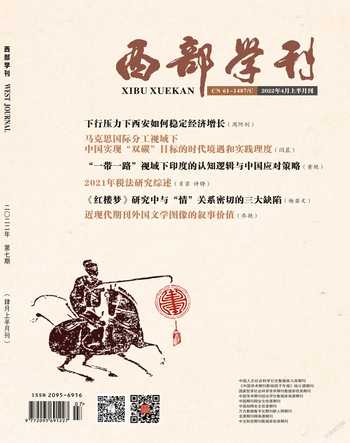晚清滇黔边岸川盐官运商销制度施行背景探析
摘要:官运商销制度是通过宏观调控对市场的整顿,有效控制私盐和运输途中的非法手段,减少不经过盐引控制的销售行为,实现了销引数量的大幅度增加。其施行背景是,在太平天国运动的冲击下,清廷财政供支捉襟见肘,不得不依赖地方的力量平息戰乱。彼时的四川作为受战乱波及较小的省份,靠川盐济楚政策增加的盐税收入承担着协济各省的任务。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为规复淮盐销区,川盐济楚被叫停,川省失去了一笔重要的财政来源。为了弥补这一财政缺口,川省开始致力于整顿滇黔边岸,川盐官运商销制度由此应运而生。它既是当时中央财权下移、地方财政兴起这样一种复杂历史条件的产物,也通过能保障地方财政稳定来源的内生优势实现了对其的一种呼应,二者呈现出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关键词:禁川复淮;官运商销制度;地方财政
中图分类号:K2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2)07-0009-05
光绪初年,丁宝桢①就任四川总督,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盐政改革。盐政改革措施主要集中在滇黔边岸的整顿上,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丁宝桢上奏整顿滇黔边岸,开办官运商销,于泸州设置盐务总局,综理滇黔盐务事宜。这一措施的施行,极大地改变了川滇黔边岸废弛的现状,为川盐行销滇黔边岸提供了保障。丁公的官运商销措施一直是学界的重要研究对象,围绕这一制度产生了一部分优秀的学术性文章,但有关探讨目前看来更集中于关注其措施或成效, 对相关背景的探究虽有涉及,却并不深入。鲁子健在《试论丁宝桢的盐政改革》[1]一文中涉及对官运商销制度施行背景的探讨,提出丁宝桢的盐政改革背景是由于复淮情势之迫以及川盐行销制度本身的腐败性。但笔者认为,禁川复淮的情势之迫是刺激川盐开辟新的市场,从而引发整顿滇黔边岸盐业事务的导火索,而官运商销体制能成为整顿滇黔边岸唯一的良方,更有其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的内在原因值得深入剖析。
黄国信在其著作《国家与市场:明清食盐贸易研究》[2]中,将川盐济楚及后来的禁川复淮争议归结为特殊背景下市场运行的结果,提出传统时期政治权力运作的根本目的在于财政收入。受此启发,本文从地方财政的角度出发,结合太平天国运动后清政府在政治、经济上出现的一系列变化,分析川盐官运商销制度形塑的背景,以探明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动因。
一、晚清地方财政的兴起
在中央权力高度集中的统治下,清政府财政资源的调拨采纳中央集权的方式,而地方的财政收入无论是直接收归中央的部分还是留供地方政府支取的部分,都由户部直接调控,严格遵循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总前提。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撼动了这一总前提,清代财政关系在战争的冲击下出现了变动。随着太平军的兴起,长江以南的大片区域或由于战争打击陷入生产停滞或为太平军所控制,清政府财政收入在这样的现实情况下被一再压缩,而军需的持续增长使得财政开支成为一笔巨额数字。收支不平衡的局面使得清政府不得不变通旧制,另寻他法以稳定战时局面。当时清政府面临的局面是仅靠国家财力已经无法完成镇压太平军叛乱的任务,于是将中央的财政责任转嫁到了地方政府的身上,要求他们贯彻以“本省之钱粮,作为本省之军需”原则,实行就地筹饷。在财政责任转嫁的同时,清政府相应地下放了一部分的财政权力,一元中央集权财政体制有了部分变动。
四川作为太平天国战乱中受波及较小的省份,在东南各省接连陷入战火,本地财赋化为乌有之时,不得不承担起协济各省的任务。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在广西桂平金田村首先爆发,户部指拨川省接济广西,以备不时之需。五月十三日,时任四川总督的徐泽醇筹银七万两解赴广西,三个月后,又筹银二十五万余两接济广西。除广西外,湖南、湖北、贵州、云南、陕西、山西等省份,也或多或少提出了请求四川协济的要求,如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署理湖北巡抚胡林翼奏请川省协济楚省军饷,川省遂起解十数万两赴湖北支援。此外,湖南防堵经费银五万两,也由四川筹集拨解。据统计,仅从咸丰元年至咸丰四年底,四川协济各省饷银三百三十二万四千余两[3]。协济军饷的增加,使得四川财政呈现出罗掘俱穷的态势,为满足省内各项开支需求,同时承担起清政府施加的财税负担压力,四川总督不得不挖掘省内潜力,以达到财赋增收效果。这一时期,四川地区的加税主要有田赋附加及厘金两种形式。
(一)田赋附加
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清政府宣布固定丁粮税额,定下了“后世滋生人口,永不加赋”的政策,可见清代定制不得随意增加田赋税率。但作为传统农业大国,国家财政收入主要靠田赋税收补给,要想扩张财政收入,亦不得不从田赋着手。虽不能直接增加田赋税率,但可以通过各种手段增加田赋附加收入进行转圜,在四川地区的田赋附加有按粮津贴和捐输之名目。
按粮津贴在嘉庆年间就已有施行,是为筹措镇压白莲教起义的军费而设置的。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在天平天国运动的压力下,清政府再次下令陕西、山西、四川三省施行按粮津贴,定于本年春季征完本年应收田赋,秋季则借征次年钱粮,并以此为定制,直到战事平息。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四川首先开征按粮津贴,拟定税制为在田赋正税之外,每两加征津贴一两,边远贫瘠地区免征,由地方官选派公正绅耆,设立公局经理相关事宜,每年征完后随同地丁银一同解省。
除按粮津贴外,四川还设置了极具特色的税种——捐输。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四川总督依据清政府的要求开始在省内筹办捐输,用以填补各项开支需要。捐输的征收原则是以当年正赋税额为参照,每年捐输所摊派的额度不固定,由藩司根据当年收成情况确立捐输额度,除边远贫瘠州县外,其余州县按收成丰歉等级摊派,由地方官督促当地绅耆征收,当捐输达到一定数额时,总督会奏请朝廷扩张该地本年度文人科举中额、学额等,以资鼓励。捐输每年征收额度不定,大约一年可得一百八十余万两[4],作本省军需及各省协饷之用。
(二)厘金
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四川总督黄宗汉在富荣、犍为等产盐大厂设局,开始抽收盐厘,由此建立了四川的厘金抽收制度,并于次年开办货厘征收。川省厘金征收,大抵以这两项为主,其中又以盐厘为大宗。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为完善川省厘金征收制度,四川總督骆秉章在省城设立捐输厘金总局(后改称厘金总局),综理全省厘务,并在各地置厘金分局,就地抽收厘金,其办理方法同当时的湘省一致,采用官绅合办的方法,总局由四川督抚委任或藩司推荐,重要的分局委员则由当地绅士担任。户部在厘金局所的人员任免上没有发言权,相关人员薪俸由地方督抚裁定发放,实际上形成了完全独立的地方财政机构。
除以上各项外,川省加税还包括关税及各项杂税加征,但其项目琐碎、征收混乱,所入款项有限,其扩张财政收入的作用与田赋附加及厘金相比相形见绌。总的来说,在四川总督、盐茶道及各地地方官员的共同努力下,四川省实现了这一时期地方财政的扩张,在中央财政一再衰败的情势下,承担起了协济各省的重任。
二、川盐济楚与地方财政
(一)川盐济楚对地方财政的增收作用
清代盐政历来施行专商引岸制度,每个盐场都配有固定的销岸,破岸流通即被视为私盐,会受到严厉打击。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打破了这样的专商引岸制度,原为淮盐引地的楚地,由于长江水道被太平军占领而无法到岸行销,在这一特殊情形下,清政府决定转引川盐入楚,破岸行销,以解决楚地居民无盐可食的困境,川盐济楚方案由此开始施行。
在入楚之初,川盐行销并不十分顺畅,由于淮盐运输的停滞,楚地成为滋养私贩的摇篮,占据着地理优势的川私乘虚而入,充斥了大半楚地市场,且以其价格优势独占鳌头。为了保证盐税的征收,四川在宜昌府设置了盐局,对过往盐斤统一按四川厘金征收标准抽收盐厘,此法在当时取得了一定成效,一年共计可抽收盐厘银二十余万两。此后又在沙市设立了抽收盐厘分局,同样以化私为公的方法阻截入楚川私,每月征收盐厘七八万串左右。此后随着战事的加急,所需军费不断增加,川省遂提高了宜昌、沙市的盐厘局税率,每年征银总数增加至八十万两上下。咸丰四年(公元1855年),川盐境内销售也沿路设局,开始抽收盐厘,每年征银约十二万余两。在各项加赋重压下,川盐销售仍旧畅旺,四川当局遂于同年对盐厂开征厂厘,每年征银约三十万余两。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以后,各地动荡不断,川饷支出浩繁,于是在原有厂厘税率之上做了酌量增加调整,每年抽银增加到七十五六万两。咸丰十年(公元1864年),重庆开始设立盐厘总局,对过往盐斤按固定标准统一抽收盐厘,一年收银共计二十五万两有余。根据以上数据可以得知,川盐济楚施行以后,川省每年抽收盐厘总计八十万两左右,加之省内的盐厘、厂厘以及重庆盐厘局的收入,川省财政增收额每年计一百万两有余[5]。川盐济楚的施行对四川省地方财政的增收作用是巨大的,在战争动摇着农业帝国基础的飘摇时代,一定程度上为四川及其周边省份的稳定、发展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
(二)川盐济楚的支付项目
川盐济楚带来的巨额盐厘收入一度成为川省地方财政供给的主要来源,不仅为本省提供军事、行政、民生上的各项经费,更为重要的是为供给各省协饷提供了稳固来源。
首先是湖广协饷。湖广地区作为太平天国的主战场之一,其军费需求是巨大的,尽管川盐济楚的收入为其提供了一笔不菲的收入,但并不能满足战争的高额消耗,四川作为经济状况较好的邻省,自然而然地承担起了协济湖广的重任。这笔协济款项最初是由四川总督派人押送至湖北,是以现金的形式支付,后来逐渐演变成为楚地官运购盐资本。其运作方式是由川省司库从济楚协饷账下划拨固定金额银两,由湖北购盐官员按额在指定厂地领盐后运回楚地销售,在运输途中需照旧向川省盐厘局缴纳盐厘。这样一来,川盐济楚实际上已经以非现金支付的形式完成了川省对湖广的协济。
其次是云贵协饷。云贵之乱历时更久,在太平天国运动平息之后,又有黔东南苗民起义,而云贵地区即使在和平时期,每年都必须接受大量的协济款项,随着战争的愈演愈烈、生产的停滞以及军费的激增都给财政带来了更大的负担。在协助的各省中,作为邻省的四川尤为重要。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云南巡抚岑毓英在呈上的奏折中将川省协济的具体情况做了简要说明:“臣伏查四川省历次奉拨协滇军饷,咸丰十年闰三月间,奉拨月饷银八千两,同治三年八月间,奉拨由盐厘项下每年协济银二万两,每月应摊银一千六百六十六两零,又六年十月间,奉拨月饷银四万两,在重庆、泸州厘金项下拨给,七年二月间,奉拨月饷银三万两,共计每月应拨银七万九千六百六十六两零。”②可以看出,川省云贵协饷的支付主要依靠的是盐厘收入,其中又以泸州、重庆夔关等川盐济楚沿途厘金为大宗。
至此,川盐济楚的施行已经逐步演变成为川省地方财政扩张的重要来源,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承担着支付诸如协饷等大宗财政开支的重要任务。可以想象,在川盐济楚方案被宣告终止,川盐在楚地销售的市场份额一再被打压时,对川省地方财政造成了怎样的打击?在这样的情形下,川省不得不为填补失去的这一部分收入来源而为川盐寻找新的出路,由此,滇黔边岸的川盐官运商销制度应运而生。
三、川盐官运商销制度的诞生
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丁宝桢督川,开始着手整顿川省盐务,其时正面临户部和两江总督对在楚地市场流通的川盐处处打压,以致其无路可退的两难境况。当川盐丧失楚地市场后,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八十余万两的盐厘收入消失殆尽,此前赖以作为支付保障的湖广协饷、云贵协饷以及部分本省开支都失去了固定来源。如何整顿如今川省的盐务现状,弥补这一巨额的财政缺口,成为丁宝桢盐政改革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官运商销制度恰好具有为地方财政提供稳定来源的内生优势,要佐证这一点就需要从官运商销制度的组织架构及其运作手段去分析。下面,我们可以从丁宝桢拟请开办官运商销的奏稿中看出官运商销体制的大体构造。
“臣现拟于泸州设立办理黔边盐务总局,委唐炯前往驻扎,督办官运商销黔盐事宜,并刊发木质关防以昭信守,所有永、綦、合、涪、江、南六岸及本行边引之酉、秀、黔、彭、纳、谿暨近边州县计引悉提归总局转发配运以一事权。并于产盐之富顺、犍为两厂,每厂设立购盐分局,綦江、涪州、合江、永甯、江津、南川六岸每岸设立售盐分局,凡给票、配引,收盐、发商,验票、缉私等事,各委干员分司其事,并将局办各岸奏销由局自行专办,俾专责成其从前各州县积欠改归局办,各边计之,引张及羡截税课,各银两均应随时会商司道核办,由臣饬盐道详细查明引数银数,分年分成带还,以示清晰,其一切应办事宜,统由唐炯调度。”③
可以看出,官运商销制度是通过官运局的统筹把握,来综理滇黔边岸盐务全部事宜,通过官方设置的购盐分局、售盐分局以及专理运输的各个分机构,完成从产地购盐到运输至岸的整个过程,然后在场岸交由当地商人分销,其中产生的购盐费用、运费以及应征税课等构成的整个成本由官运局暂行承担,在分配给场岸商人行销时再将成本分摊到每斤盐包。这样一来,官运局通过预先征收的办法解决了盐税收入无法保证的问题,实际上也行之有效地杜绝了商贩在运输途中的掺杂混卖、重照影射等问题。除此之外,官运局通过控制盐斤成本的手段把盐价维持在合理区间,同私盐相比,官运盐则不会由于价格失去市场优势,私贩会逐步因为无利可图而销声敛迹。官运商销制度就是通过宏观调控对市场的整顿,有效控制了私盐和运输途中的非法手段,减少了不经过盐引控制的销售行为,实现了销引数量的大幅度增加。而食盐的税收来源就是以盐引为凭证,销引数量增加,财政收入自然会随之增加。
在官运商销制度实行以后,滇黔边岸盐税总收入就一直趋于稳步上涨的狀态,一百数十万两的盐税收入,几乎与司库的地丁、税羡、津贴三项相等,其对地方财政的裨益,无疑是巨大的。据统计,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川省财政支出中的防营一切支出总计不过十四余万两,京协各款项总计在两百万两左右,而该年滇黔边岸官运局盐税总收入达到了一百三十余万两,已经占了这笔大额支出的半数以上[6]。这说明官运商销制度的确立,的确满足了当时地方财政兴起的要求,在户部可以调拨的经费无法满足地方开支需求时,承担起了稳定川省财政收支平衡的重任。
四、结语
在官运商销制度施行一年以后,作为禁川复淮争议中主要一方的四川总督丁宝桢在对禁川复淮的态度上有了明显的转变,从此前的据理力争变成了一定程度上的极力配合,同时主动提出罢除两江总督沈葆桢承诺的规复淮岸后每年协济川饷银六十万两,但保留鄂省的协济一百万两仍然应该支付的意见。禁川复淮的争议牵扯出的是几个省地方财政之间的利益纠葛,这样复杂的纠葛使得两湖地区的川盐在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自发选择的相互作用下且进且退,最终点燃了滇黔边岸川盐整顿的引星,成为官运商销制度诞生的温床。由此可以看出,官运商销制度是在地方财政兴起的背景下,以禁川复淮争议这样的剧烈冲突为契机出现的。它既是当时中央财权下移、地方财政兴起这样一种复杂历史条件的产物,也通过自身能保障地方财政稳定来源的内生优势实现了对其的一种呼应,二者呈现出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注释:
①丁宝桢(1820—1886年),字稚璜,贵州平远(今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牛场镇人,晚清名臣。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中进士,此后历任翰林院庶吉士、编修,岳州知府、长沙知府,山东巡抚、四川总督。他勇于担当、清廉刚正,一生致力于报国爱民,任山东巡抚期间,两治黄河水患,创办山东首家官办工业企业山东机器制造局,成立尚志书院和山东首家官书局;任四川总督十年间,改革盐政、整饬吏治、修理都江堰水利工程、兴办洋务抵御外侮,政绩卓著、造福桑梓、深得民心。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丁宝桢去世,朝廷追赠太子太保,谥号“文诚”,入祀贤良祠,并在山东、四川、贵州建祠祭祀。
②岑毓英《岑襄勤公奏稿》卷2《滇饷请拨邻省厘金折》,第362-385页。
③丁宝桢《筹办黔岸盐务官运商销折》,见《丁文诚公奏稿》卷15。参考文献:
[1]鲁子健.试论丁宝桢的盐政改革[J].盐业史研究,2000(2).
[2]黄国信.国家与市场:明清食盐贸易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19:140.
[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十六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348.
[4]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资料编辑组.四川款目说明书[M]//近代史资料:第64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89.
[5]张学君,冉光荣.明清四川井盐史稿[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120.
[6]鲁子健.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下册[M].成都: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105.
作者简介:蒲雅兰(1996—),女,汉族,四川南充人,单位为苏州科技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研究方向为中国专门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