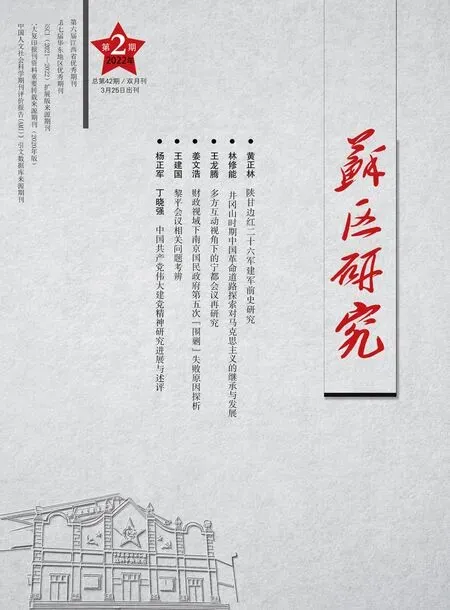多方互动视角下的宁都会议再研究
提要:宁都会议的起因既有前后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关于前方军事部署的分歧,也有前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组织领导的问题,而1932年9月26日朱德、毛泽东发布的《敌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则是促成宁都会议召开的直接因素。会上及会后,前后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互有批评,但主要批评毛泽东的所谓“右倾”和周恩来的所谓“调和”,并通过毛泽东暂时回后方的决定。中共临时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起初是不同意公开批评和召回毛泽东的,不过临时中央出于前方领导一致地执行进攻路线的考虑,后来同意此决定,以至撤销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
1932年10月3日至8日在江西宁都小源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通称宁都会议),集中批评了毛泽东的正确军事主张,决定毛泽东暂时回后方主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工作,随后他所担任的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被撤销,这实际上“改变了正确的党的领导和军事领导”,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中央红军长征初期的严重挫折产生深远影响。目前学术界在宁都会议的背景、起因、经过等方面已取得不少研究成果,但是对宁都会议所牵扯的多方互动关注不足,尚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和必要。因此,本文将从多方互动的视角切入,从会前、会上及会后、会外三个方面对宁都会议再作一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会前:苏区中央局内部的分歧
宁都会议召开的目的是“解决前线与中央局之间的争论问题以及前线在组织问题上的争执”。这说明在宁都会议前,分歧与争论不仅存在于前方与后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之间,也存在于前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之间。前者体现在前方的军事部署及军事原则上,后者体现在前方的组织领导上,而1932年9月26日朱德、毛泽东发布的《敌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则是促成宁都会议召开的直接因素。
第一,前后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关于前方军事部署存在分歧。1932年9月,在国民党军队“围剿”和中共临时中央“左”倾方针的影响下,鄂豫皖苏区、湘鄂西苏区的军事斗争形势日益严峻,临时中央、中共苏区中央局要求红一方面军立即北上作战,以减轻两苏区的压力及配合作战。9月23日,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苏区中央局并转临时中央,认为红军目前的行动能给鄂豫皖、湘鄂西以直接援助是最好的,但在目前敌军固守据点,红军又难以围城打增援部队的条件下,“应以夺取南丰,赤化南丰河两岸尤其南丰至乐安一片地区”,以促起敌情变化,进而在运动战中打击和消灭敌人,故这“虽不是立即出击敌人,但仍是积极进攻的策略”。25日,苏区中央局复电反对前方分兵赤化的军事布置,并不认可“解释这为积极进攻策略的具体布置与精神”,“这在实现上将要延缓作战时间一个月以上。将于鄂豫皖、湘鄂西,……不是呼应配合的”,并提出打击乐安之敌或攻击南城以调动敌人消灭之的意见。同日,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复电苏区中央局,再次陈说目前敌我形势不宜立即北上作战,攻城打增援部队也是没有把握的,“若因求战心切,鲁莽从事,结果反会费时无功,徒劳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局面”,仍坚持赤化北面地区,逼近宜黄、乐安、南丰,争取消灭敌人的有利条件,“这样才能胜利地配合全国红军的进攻,这自然是积极进攻的。”26日,苏区中央局复电前方坚持前电意见,强调“如在轻敌之下分散布置赤化工作,则不但将失去运动战中各个击破敌人稍缓即逝的时机,而且有反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同日,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复电苏区中央局,表示驻守乐安的敌军第九十师实力较强,且联系不上地方部队第八军而无法配合行动,故不宜攻打乐安,若宜黄敌人较弱,则进攻宜黄,反之则不攻,“只有执行原定计划,布置宜、乐中间一带战场,争取群众以调动敌人”。也是在这一天,朱德、毛泽东发布《敌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决定战备的在这一向北地区做一时期(十天为一期)争取群众推广苏区以及本身的教育训练工作”,具体是在宜黄、乐安、南丰一带地区以战备姿态布置战场,消灭这一地区敌人的反动武装和游击力量,争取群众和建立游击队,随时打击和消灭敌人的出击部队,以创造有利于与敌人主力决战并取得胜利的条件。
前方和后方的军事部署都是为了配合和支援鄂豫皖、湘鄂西苏区的军事斗争,分歧在于是立即北上作战,还是赤化一定区域,等待有利时机作战。这体现的是前后方对进攻路线的不同理解。后方机械地执行临时中央的进攻路线,不顾实际地要求进攻敌人和攻打城市;前方则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适当和有利的方案,其目的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毛泽东在1932年5月3日复电临时中央时即指出:“我们的任务是夺取中心城市实现一省胜利,似要以消灭敌人做前提。”前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1932年9月在给湘鄂西苏区、鄂豫皖苏区打破敌人“围剿”的建议中表达了同样的意见,“红三军应集结全军力量,机动地选择敌之弱点,先打击并消灭他这一面”,“红军尚须力求避免过大的牺牲,争取便利于消灭敌人一部,以各个击破敌人”。即选择敌人的弱点,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聂荣臻后来通过对比1932年上半年红军攻打赣州和漳州的不同结果,生动地总结了这一军事原则:攻赣州而未克,吃了“大苦头”,顺利攻占漳州,吃了“甜头”,因为赣州有重兵,而漳州是弱敌,故“选择敌人的弱点打,应该是我们处于劣势的部队绝对要遵守的一个军事原则”。
第二,前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的组织领导难以机断专行。这集中反映在周恩来9月24日给苏区中央局的电报中:“前方组织既不是集权于个人负责制,各人能力又均有长有短,许多事件既不能决之于个人,……因许多不同意见且均系负责者的意见,自然要加以考虑。”这就对前方军事部署的迅速决策和执行产生消极影响,因此,周恩来视其为“目前最中心而亟须解决的问题”。那么,前方何以出现“均系负责者”的情况呢?1932年6月中旬,中共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仍辖红一、红三、红五军团,朱德兼总司令,王稼祥兼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仍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份随红一方面军总部行动。7月21日,周恩来以苏区中央局代表身份赶赴前方,随后后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两次提议由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7月29日,周恩来致电苏区中央局,提议在前方组织以周恩来为主席,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为成员的最高军事会议,并再次提议由毛泽东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说明“其权限于指挥作战战术方面为多”。这既尽量发挥毛泽东的“经验与长处”,又“督促他改正错误”,否则,毛泽东“以政府主席名义在前方,实在不便之至,且只能主持大计,这又与中局代表或军事会议主席权限相同”。即以这样的组织设计和职权限制来说服后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同意毛泽东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8月上旬,苏区中央局通过周恩来的提议,在前方组织最高军事会议,毛泽东也被委任为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至此,前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除兼任前方的职务外,还均有另外一种身份,即周恩来为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朱德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王稼祥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这就形成了“均系负责者”的局面。
尽管周恩来说明“遇关重要或犹疑不定时,我便可以最高军事会议主席或中局代表名义来纠正或解决”,但最高军事会议的组织形式并没有完全解决“均系负责者”的问题。因为各人的责任与权限不够明晰,以致前方的机断专行只“可用之于日常事务上,而无法用之于临时紧急处置上”,尤其是毛泽东鲜明的个性和风格加剧了这种情况的严重化,“前方每遇商榷之事,动辄离开一定原则谈话。有时海阔天空,不知‘伊于胡底’,而实际问题反为搁下。……尤其是军事战略,更可以随意恣谈,不值定则”。为了解决此问题,周恩来提出自己回后方的想法或者用其他办法解决。
第三,后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对到前方召开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的态度,有一个从消极到积极的转变过程。周恩来在9月24日给苏区中央局的电报中指出,王稼祥提出后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来一人到前方开会,毛泽东则提出项英、任弼时来前方开会,周恩来在吸纳王稼祥、毛泽东意见的基础上,首先提出在前方召开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在周恩来看来,前后方以及前方内部的各种分歧和争论已经严重到必须召开中央局全体会议,以“彻底地解决一切原则上的问题”,“否则前方工作无法进行得好”。前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取得一致意见后,在9月25日共同致电苏区中央局,“我们提议即刻在前方开一中局全体会,并且要全体都到”,并且详细地说明召开中央局全体会议要解决的各种问题,包括“目前行动问题,并要讨论接受中央指示、红军行动总方针与发展方向、地方群众动员与白区工作,特别是扩大红军苏区与争取中心城市之具体进行等”。然而,后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以前后方的客观困难为由,在9月26日复电中表示拒绝:“项英、邓发已去闽西参加会议,而且你们亦须随军前进,中央局全体会议不可能开。”同日,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再电苏区中央局,坚持“中央局全体会以项、邓两同志回后,仍以到前方开为妥”,强调前电提出的各种问题,必须在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上讨论解决。
在前方的一再要求下,以及恰逢中共临时中央电示红军行动方针,为迅速讨论临时中央指示及前方问题,苏区中央局9月27日提出折中方案,“我们提议恩来同志即回瑞开会,前方有毛、朱、王同志主持,无甚妨碍。若将来到前方开会,路程过远,费时太多,对工作影响甚大”。可见苏区中央局认为到前方开会太耗费时间,会影响苏区中央局的日常工作。这表明苏区中央局此时对前后方的分歧还没有足够的认识和重视,以致于在优先性上将苏区中央局日常工作置于解决前后方的分歧之上,对到前方召开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并不积极。不过,苏区中央局在9月29日收到朱德、毛泽东签发的《敌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以下简称“《训令》”),得知《训令》坚持在南丰河两岸地区做赤化工作、准备战场的军事布置,并进入实施阶段。至此,他们的态度才迅速转变,开始认识到前后方分歧的严重性,“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同时认识到解决前后方分歧的紧迫性,“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遂改变要周恩来回后方开会的决定,提前召回原本10月1日才能回到瑞金的项英、邓发。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于9月30日下午日夜兼程地赶赴前方,召开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苏区中央局9月30日又特意致电周恩来,指出分散赤化的意见是对形势估计不足,要予以无情的打击,苏区中央局在10月1日再次致电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表示“我们坚决不同意九月二十六日训令的军事布置”。可见《训令》对苏区中央局的刺激之大,后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即使在赶赴前方的途中,仍频频去电表达对《训令》的反对意见。可以看出,《训令》是促成后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同意到前方召开中央局全体会议的直接因素。
二、会上及会后:苏区中央局前后方成员的争论
上述分歧与争论全部集聚到宁都会议,引发了“中央局内部从未有过的两条战线斗争,打破过去迁就和平的状态”,前后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尤其是毛泽东、周恩来与后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之间发生争论。此外,苏区中央局在9月30日转发中共临时中央电报给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电称国民党军即将全力进攻中央苏区,要求“以最积极迅速之行动,择敌人弱点,击破一面,勿待其合围,反失机动,望即定军事动员计划”。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同日回电表示“已提议在前方召开中央局全体会议,……军事行动计划亦将在这一会议上决定”。因此讨论第四次反“围剿”的军事计划亦是宁都会议的重要议题。
一是,前后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在会上相互批评
后方是从政治路线的高度批评前方的,指责前方分散赤化的军事布置是以准备为中心的主张,是对革命胜利和红军力量估计不足,是“专准备为中心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因此,周恩来不得不检讨前方“确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肯定后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集中火力反对等待倾向是对的”。在这种政治压力下,前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主张结合前方实际情况贯彻中央指示的意见也被打压下去,会议最终接受临时中央关于行动方针的指示电,决定采取积极迅速的行动,在国民党军完成合围前,主力红军首先北向出击,选择敌人弱点各个击破。同时,前方批评后方对敌人大举进攻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和群众动员工作做得不够。相较于后方对前方的批评上升到政治路线的高度,前方对后方的这一批评是切合实际情况的。在会前的前后方争论中,前方在9月25日就向后方指出“特别要认识敌人正在布置更大规模的进攻中区,残酷的战争很快就要到来”,但后方并未重视起来,造成后方的群众动员等工作落后于形势的发展。因此,周恩来在会议结论中同时“指出前方同志以准备为中心的错误,以及我们(指后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引者注)对(敌)大举进攻认识不足的错误”,但后方对此结论不太认可,认为这是“调和结论”。这让周恩来难以接受和释怀。所以,周恩来在10月17日致电苏区中央局,以江西省委违反宁都会议的决定,拖延把省委迁到宁都一事为契机,批评这仍是对目前敌人大举进攻的忽视与估量不足,“证明我提出以主要火力反对等待主义同时要反对松懈动员工作的右倾的绝对正确,绝对不是调和结论”。
二是,后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错误地集中批评毛泽东
后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认为毛泽东“对扩大中央苏区、占领中心城市和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斗争表现动摇”,“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而且毛泽东在会上坚持《训令》的观点,不同意红军无条件地离开苏区出击强敌,以至公开反对临时中央关于行动方针的指示电,因此后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集中火力批评毛泽东。他们一方面批评毛泽东犯有所谓“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另一方面把毛泽东反对攻打赣州等中心城市和向赣东北发展的意见批评为“纯粹防御路线”,指责南雄战役、宜乐战役都犯了分兵筹款的错误,认为《训令》确定的分兵赤化的计划也是错误的,甚至批评毛泽东领导的漳州战役的胜利“延缓了北上任务之实现”。后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对毛泽东的批评可谓苛刻。他们在会后也承认对毛泽东的批评“有过分的地方”。周恩来指正了他们对毛泽东的过分批评,但他们只是承认在批评的程度上“过分”,在方向上是没有错误的。因此,他们不认可周恩来在会议结论中“不给泽东错误以明确的批评,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释掩护”的做法,指责周恩来没有坚定地集中火力反对以准备为中心的右倾错误,甚至将此上纲为“是调和,是模糊了斗争战线”。
三是,解决前方的组织领导问题
后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在会上提出由周恩来负领导战争的责任,毛泽东回后方主持临时中央政府的工作,以保证前方领导的统一和机断专行。他们在9月30日给中共临时中央的电报中就提出了这个想法:“我们坚决而公开地批评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并想把他召回到后方[中央]苏维埃政府中工作。”并且在会前把“即将召回泽东的意见告诉恩来,他亦不表示一定的意见”。可能是由于时间仓促的原因,周恩来没来得及表示意见。所以,当后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在会上提出召回毛泽东时,因“事先并未商量好,致会议中提出后,解决颇为困难”。周恩来在会上对此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案,即取消前方最高军事会议制度,以“集权于个人负责制”取代之,“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核心是留毛泽东在前方参与军事指挥,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对他个人亦能因局势的展开而更彻底转变”。朱德、王稼祥也支持毛泽东留在前方。毛泽东则因不能取得苏区中央局的全权信任,坚决不同意后一种方案。在支持毛泽东回后方和留前方的意见平分秋色的情况下,后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一方面认为毛泽东“对他自己错误的认识即在会议上也还不深刻,由他在前方负责,正确行动方针的执行是没有保证的”,因此不宜留在前方,另一方面称“后方的动员和领导亦需要他回中央政府工作”。这其实更多的是让毛泽东回后方的托词。毛泽东因病回到后方后,相当一段时间在长汀福音医院休养,并未立刻领导起临时中央政府的工作。会议争论的结果是变通地采纳周恩来提出的第一种方案,即同意毛泽东留前方助理,同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假回后方养病,必要时到前方。这在一定程度上优先满足了后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的要求。
三、会外:中共临时中央、共产国际的介入
宁都会议最终确定的军事路线和组织调整总体上倾向于后方中央局成员的意见,但他们在组织调整上的“先斩后奏”,有违中国共产党及共产国际的组织纪律,尤其引起共产国际代表的不满和批评。不过,由于他们所坚持的进攻路线符合中共临时中央、共产国际的要求,也就未加以追究和纠正,而为保证前方领导一致地执行进攻路线,临时中央甚至比他们走得更远。
正当宁都会议召开期间,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10月6日开会讨论苏区中央局的问题。博古在会上指责毛泽东的观点“是保守、退却”,一贯的“分散工作的观点”,批评周恩来不能与之作坚决斗争,“又暴露一次调和以至投降的弱点”,张闻天表示同意博古的上述意见。博古进而提出要与毛泽东的观点作坚决斗争,“但不一定指出泽东名字”,“因为要估计到泽东在苏区红军中的威信”,张闻天则提出“泽东可调回后方做苏维埃工作”。为此,博古还提出自己代表中央赴中央苏区指导工作,张闻天表示“须与△△(指共产国际——引者注)相商”。会议决定,立即致电苏区中央局。
10月7日,中共临时中央致电苏区中央局,批评毛泽东“没有充分看到国内力量对比有利于革命的巨大变化,以及南京政府的进一步削弱”的有利形势的同时,要求苏区中央局“尝试用同志式的态度争取他赞成积极斗争的路线”。对于后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9月30日电报中提出的公开批评和召回毛泽东的建议,临时中央表示“不进行反对毛泽东的公开讨论”,“现在我们反对将他从军队中召回”,以“保证领导的一致”。显然,这封电报主要体现了博古在会上表达的意见,而未采纳张闻天调毛泽东回后方工作的意见。
尽管临时中央在电报中要求苏区中央局“速发给我们补充信息,不要等到[一切]事实既成之后”,可能是电报收发时间差的原因或其他原因,苏区中央局还是在“撤销毛泽东前线总指挥的职务,对他进行公开批评并谴责他的错误立场”的决定通过之后,才告知临时中央。共产国际代表埃韦特10月8日在给皮亚特尼茨基的报告中,说明此情况并表达不满。他承认苏区中央局采取进攻路线是正确的,而毛泽东主张防御策略是错误的,但认为应该“尽可能地采取和善的方式”说服毛泽东接受进攻路线,因为“毛泽东迄今还是有声望的领袖,因此为实行正确路线而与他进行斗争时必须谨慎行事”。这与博古的意见是一致的。在他看来,苏区中央局既没有进行这种努力,又在“未告知我们的情况下”,“是不能作出这种决定的”,这不符合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的组织纪律。因此,埃韦特表示“反对目前撤销毛泽东的职务”,而“要使他改变观点”。
与埃韦特的不满态度不同,临时中央看到既然木已成舟,便顺水推舟,在10月10日致电苏区中央局,表示“我们可同意现在召回泽东同志与公开批评他的错误观点,批评的方法应该说服教育,并继续吸引他参加领导机关的工作”,并要求采取进攻路线,具体方向由苏区中央局讨论,“并能与泽东同志取得一致意见”。10月12日,中革军委根据宁都会议的决定,发布通令:“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兼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同志,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同志代理。”10月26日,临时中央正式任命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回后方工作,本是宁都会议决定的临时性举措,即保留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由周恩来在前方代理,毛泽东必要时可回到前方,但在临时中央的介入下,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被撤销。毛泽东后来批评说这“是缺席裁判,并且不通知”,完全是一种“高慢的宗派主义”。
从反对到同意召回和公开批评毛泽东,再到撤销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中共临时中央的态度为何如坐“过山车”般大起大落?这只能从这前后的电报中寻找蛛丝马迹。11月12日,临时中央在收到周恩来和后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关于宁都会议争论情况的电报后,复电苏区中央局,首先肯定宁都会议的路线是正确的,接着指出“泽东同志在会议上已承认自己的错误,必须帮助泽东迅速彻底的改正自己的观点与吸引他参加积极的工作”,并强调“领导一致是目前最重要的”。和10月10日给苏区中央局的电报相比,这里有一个微妙的变化,即对毛泽东从“继续吸引他参加领导机关的工作”到“吸引他参加积极的工作”。一个“领导机关”之差,体现了临时中央的心路历程——它在这些指示电报中,一直在强调进攻路线和领导一致这两点,而说服和争取毛泽东是服务于这两点的,即说服毛泽东赞成进攻路线,以保证领导一致地执行进攻路线。因此,临时中央在10月10日电报中指示苏区中央局,在执行进攻路线上“与泽东同志取得一致意见”。不过,临时中央后来意识到,毛泽东虽然“已承认自己的错误”,但并未“迅速彻底的改正自己的观点”,这样的话,吸纳毛泽东“参加领导机关的工作”,既不能保证领导一致,又不能执行进攻路线,所以临时中央最终同意召回和公开批评毛泽东,以至撤销他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可见,进攻路线和领导一致是临时中央的核心关切,因此,临时中央在11月23日致电苏区中央局询问:宁都会议后进攻路线执行如何,有否反对和抵抗?中央局领导在策略上目前有所分歧否?11月26日,苏区中央局复电临时中央,指出“现在对进攻路线除毛同志最近来信仍表现有以准备为中心的意见外,并无其他反对与抵抗”,中央局领导是团结一致的,无任何分歧与争执。由此可知,毛泽东坚持自己的正确观点、不赞成进攻路线,成为影响临时中央处理毛泽东相关问题的关键因素,这也为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后进一步冷落和排挤毛泽东埋下了伏笔。
共产国际对苏区中央局内部的分歧及临时中央的处理意见更是后知后觉。根据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临时中央在10月16日致电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就派一名中央政治局委员去“中央苏区贯彻[中共]中央的方针并消除那里的冲突”一事征询共产国际的意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10月27日复电临时中央,要求“详细告知中央苏区的意见分歧”,表示对此“一无所知”,共产国际至此才间接了解到中央苏区有意见分歧的情况,但仍未掌握其中的具体情形。临时中央在11月11日致电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只有寥寥几语,说明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已召开及会议结果:“莫斯克文(即周恩来——引者注)负责前线的一切军事问题,毛泽东因病已回到后方。”共产国际在11月以后收到上文提到的埃韦特报告以及王明的汇报,了解到中央苏区意见分歧的情况后,也就不再继续向临时中央询问,但对毛泽东的政治境遇是持续关注的。最具代表性的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在1933年3月致电临时中央,强调继续加强军政领导力量,并提出“对于毛泽东,必须采取最大限度的克制态度和施加同志式的影响,为他提供充分的机会在中央或中央局领导下担任当负责工作”,试图改善毛泽东被边缘化的地位,使毛泽东做“负责工作”。
宁都会议最直接的互动是前方和后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围绕前方的军事部署和组织领导问题展开的,背后也有苏区中央局与临时中央、共产国际代表以及临时中央与共产国际之间的互动。在这互动过程中,始终隐潜着一条保证中央苏区领导一致地执行进攻路线的主线。会前,前后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对进攻路线的不同理解,前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因“均系负责者”造成的领导不一致,这都是宁都会议致力于解决的问题。会上及会后,前后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虽互有批评,但由于后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自恃站在进攻路线的“正确”立场,集中批评前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的所谓“右倾主要危险”,并在会上通过毛泽东暂时回后方的决定,以保证前方的领导一致。会外,后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因擅作主张而受到共产国际代表的批评,同样是由于他们坚持进攻路线而未予追究,反而由于毛泽东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使得临时中央不顾共产国际代表的反对意见而进一步撤销他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以保证前方领导一致地执行进攻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