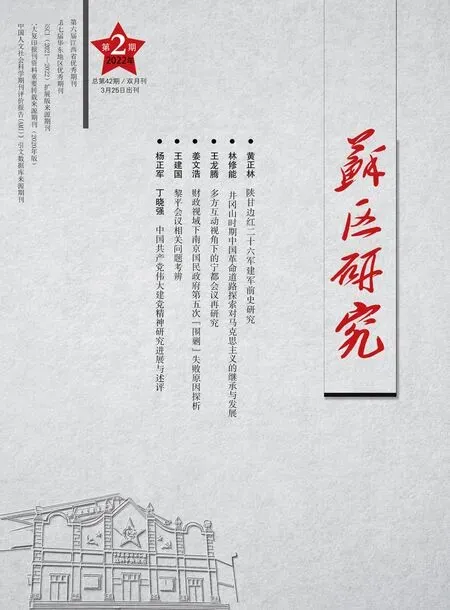井冈山时期中国革命道路探索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
提要:井冈山时期中国革命道路探索承载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历程的“开端”价值。这一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道路探索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并根据对中国具体实际的把握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革命”层面,在坚持理论指导革命、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的基础上提出“工农武装割据”,深化了对“工农联盟”“物质斗争”“渐进改造”等问题的理解;“中国”层面,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理论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并在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中加强了对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的要求;“道路”层面,在坚持实践认识论的基础上初步展现出成熟“实践论”的萌芽,蕴含着“实事求是”“实践检验真理”的真理观,显示出道路的科学性。回溯这段历史,有助于理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历程中一以贯之的指导作用,更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发展。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井冈山时期提出并发展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初步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1945年,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在这一时期……在理论上更具体地和更完满地给了中国革命的方向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依据”。《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也指出,“从进攻大城市转为向农村进军,是中国革命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学界对于井冈山时期中国革命道路探索的重要历史定位与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状态存在着一定的共识,许多学者将井冈山时期中国革命道路探索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
然而与实践史的高度认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内外学界关于这一时期中国革命道路探索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关系问题存在一定的争议。当前学者们对这一问题主要存在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无关论”,认为井冈山时期的中国革命道路探索是毛泽东的独创,并且背离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持这一观点的有斯图尔特·施拉姆(Stuart Schram)、本杰明·史华慈等。第二种观点是“阴谋论”,认为所谓的“中国道路”只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严格指导下的产物,是苏俄向外扩展的“阴谋”。持这一观点的主要学者有范德克鲁伊夫(Justus M. Van der Kroef)等。第三种观点是“结合论”。越来越多中西方学者提出了更为中立的看法,也就是把中国革命道路看成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结合。罗伯特·派恩(Robert Payne)等学者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特雷弗·苏达马(Trevor Sudama)、尼克·奈特(Nick Knight)等人则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将马克思主义的作用归结为方法论、认识论指导。这种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方法,将中国革命道路探索作为具体实践的研究也成为了国内研究的主流,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让理论适合本国国情的方法论强调也成为了国内学界的共识。
当前研究存在三点问题:首先,井冈山时期毛泽东虽然经历革命低潮,但仍然坚信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当面临着“红旗到底打多久”的信仰考验时,他毅然决然坚持站在马克思主义一边,因此“无关论”是难以成立的;其次,中国道路展现出了不同于苏联的创造性,冷战结束后中国的党和国家仍然展现出强大生命力,“阴谋论”不攻自破;最后,如果马克思主义仅以方法的形式呈现在中国面前,那么就很难理解中国革命与中国建设、改革的区别,而从另一方面来看,过度强调中国的实践独创性又很容易滑向“无关论”的思潮,并容易陷入毛泽东一再批判的“经验主义”错误之中。
整体上现有研究没有很好地触及“中国革命道路”的根本所在。中国的革命道路归根到底是一条革命道路,因此有必要着重探究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思想在其中起的作用与得到的发展;同时,中国的革命道路归根到底是中国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因此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现实延展也是绕不开的研究议题;最后,我们需要用更宏大的视角来理解中国革命道路的创新性问题,需要思考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在中国实践中的理论演进,从而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真谛与中国革命的“道路”独特性。井冈山时期承载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实践的“开端”意义,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明确了“无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的使命,因此可以从这些问题的探讨中透视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的基本逻辑,更有助于理解马克思主义以何种方式介入到中国革命、中国革命又以何种方式发展马克思主义。
一、“工农武装割据”对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正如雷蒙德·怀利(Raymond Wylie)所指出,“随着共产党人在1925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中的失败,许多左翼知识分子转而根据中国具体的历史背景和社会体制,重新思考革命的理论”,当国共合作破裂、共产党人遭到屠杀的时候,现实的需要使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重新思考“中国的革命依靠什么人、怎样实行”的问题。杨奎松指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道路探索经历了从群众起义、城市中心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过程。张静如也指出,“农村包围城市”这一道路的形成和确立经历了艰难的探索,而井冈山时期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与实践是这一道路的第一阶段。因此,井冈山时期无疑是中国革命道路探索中最重要的转折点,蕴含着深刻的道路转向与启新意义,我们可以从中清晰地看出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的理论演进与现实延展。
井冈山时期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首先是对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的继承,因为这一道路归根到底是服务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使命。马克思主义作为在革命年代诞生并指导革命的学说,对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中国革命的方式、革命的主体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在这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方法,还提供了更宏大的真理指导。首先,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强调在理论掌握群众的基础上开展物质力量斗争,“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思想对物质的领导作用是现代革命的共性,而马克思主义革命的独特性就在于对无产阶级思想领导权的强调。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井冈山时期恰恰就将这种思想发挥到了极致。毛泽东十分重视用无产阶级的“理论”掌握群众。他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提出:“我们感到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这种对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强调贯穿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道路探索历程,是中国共产党人自觉践行马克思主义的最好体现。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毛泽东并非“农民革命家”,而是当之无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其次,井冈山时期革命道路探索蕴含着一以贯之的“物质斗争”原则。这种“物质斗争”的延展就是对“武装割据”的强调。“所谓割据,必须是武装的”,毛泽东这一思路是“对马克思暴力革命学说的最好验证”。在这一历史时期,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归根到底是为了服务于生产关系的改造,而不仅仅是抽象政治权利的争取。因此可以判定,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时期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历程中,基本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物质革命、理论掌握群众等革命观点的相当一致的认可。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深刻吸取斗争教训得出的正确结论,更是在对马克思主义深入把握的基础上提出的科学判断。中国革命道路对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的这种显著的继承性应当得到重视。
除此之外,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还包含着对人民群众的主体认同和对革命渐进性的把握。井冈山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还根据中国现实情况发扬、发展了经典理论。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指出,“(巴黎)公社不仅代表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还代表除了资产阶级以外的全体中等阶级的利益,首先代表的是法国农民的利益”,并阐述了保卫巴黎公社时全体人民的共同奋斗。这其实已经强调了无产阶级革命与农民利益的一致性,并隐含着对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的可行性与必要性的思考。而他在反思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原因时也指出,“工人阶级为了谋求自己的解放,并同时创造出现代社会在本身经济因素作用下不可遏制地向其趋归的那种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蕴含着的渐进改造的思路。革命历程的渐进性并不妨碍革命的巨大变革性,也不妨碍革命的向前发展趋势,而只是说明了斗争的长期性与改造历程的阶段性。但是,马克思在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下并没能进一步提出作为革命主体的“工农”如何具体开展联合行动的问题,也没有阐明如何将这种革命渐进性在现实中加以具体实现。
井冈山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与之俱进的发展。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初期,就初步回答了中国革命的主体、手段与战略问题,给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答案。这是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显著发展。
首先,中国革命的主体是“工农”,也就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工人阶级革命”理论的进一步深化,并结合中国实际对理论进行了具体发展。当时“全国工农贫民以至资产阶级,仍然在反革命的通知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这种处境决定了中国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利益在根本上一致,而农民遭受的压迫十分严重、反抗的力量也更为巨大,因此强调无产阶级动员农民、引导农民进行革命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一种创造性尝试,并为历史证明是正确的。毛泽东在大革命失败前就做出了准确的判断:“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然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军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中国革命道路对农民的强调,是在坚持无产阶级领导基础上对具体国情的把握,并不是背离马克思主义,而是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之上的创新。
其次,中国革命的成功需要依靠“武装”,这是革命手段的探索。毛泽东意识到,“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这无疑是对“物质斗争”理论的深化认识。在此基础上,党中央也达成了共识。1929年2月7日《中央通告第二十九号——关于党员军事化》在引用列宁的理论的基础上指出:“我们可以明白暴力的使用,在被压迫阶级革命的意义上,成为一种推翻现存政权建立革命政权的唯一手段”。这是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基础上,总结中国此前革命失败教训得出的宝贵经验,推动中国共产党走向独立自主、武装革命。同时,武装必须是工农的武装。陈毅指出,红军与普通军队的主要区别就在于“红军是阶级的军队,是工农阶级的学校,是由工农斗争中产出,不能脱离工农群众”。因此“工农武装”一词的提出,同时回答了革命主体与斗争方式的问题。
在此基础上,“割据”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革命渐进改造的具体行动的探索。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后,中国共产党得以开展持续的土地革命,变革生产关系,同时对群众进行思想教育、进行革命宣传,这大大增强了革命的优势。毛泽东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政权的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的观点,充分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中的渐进改造理论,并提供了现实的实践支撑。这既是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果,也是对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的创新发展。
总结来看,井冈山时期的中国革命道路探索的成果以“工农武装割据”为核心,不仅坚持了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中“理论掌握群众以开展物质斗争”的重要指向,坚持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无产阶级领导权,而且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回答了中国革命的主体、手段与战略问题,深化了对“工农联盟”“物质斗争”“渐进改造”等问题的理解,是在继承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的创造性发展。
二、“党的领导”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井冈山时期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归根到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探索,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道路的领导者。这一阶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的领导形式与党的建设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在1929年6月14日给林彪的信中,毛泽东指出:“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这是四军党的主要问题……如果少数同志作的个人主义领导胜利了,那末必至你的来信所说有一种破坏党的团结一致和不利于革命的前途会要到来”。同时毛泽东也一再强调“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问题,指出“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可以看到,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党要不要领导中国革命”“什么样的党可以领导中国革命”“党要怎么领导中国革命”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如果说“工农武装割据”对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的继承与发展突出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建设、改革的区别,体现了井冈山时期中国革命道路探索的纵向独特性,那么“党的领导”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则体现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道路与同一时期国民党探索的“革命道路”的根本区别,展示了井冈山时期中国革命道路探索的横向独特性。
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时期深化了对党领导革命的认识,创造性地提出了“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民主革命”,并在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中加强了对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的要求,最终得以领导全国人民走向革命的胜利。
王奇生指出,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组织形态上最大的差别就就在于“国民党是一个弱势独裁党……但它所面对的恰恰是一个具有高度社会动员能力和组织内聚功能的中国共产党”。国民党一度陷入党争与内耗之中,无法承担起中国革命的重担,而中国共产党则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在中国革命中锻炼自身、担当大任。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核心指向就是以无产阶级政党领导革命。《共产党宣言》指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发展到资本主义时期,无产阶级受到的压迫最为深重,因此革命也将最为彻底,而这一革命的领导者将是“共产党”,因为“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恩格斯也一再强调:“无产阶级要在决定关头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就必须(马克思和我从1847年以来就坚持这种立场)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地阶级政党”。因此,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是建立在阶级分析、革命思想基础上的政党理论,强调的是共产党对革命的代表与领导,同时也隐含着对共产党自身先进性的要求。毛泽东在大革命失败之前已经根据自己对巴黎公社运动的理解,提出“其实四千多年的中国史,何尝不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呢?”的重要观点,在大革命失败后更是意识到“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井冈山时期坚持无产阶级政党对革命的领导,并自觉地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指明政党的阶级性与革命领导权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的这一思考曾经受到很大的阻力。当时党内存在“两次革命”与“一次革命”的争议,但这两种观点归根到底都陷入了对革命性质与革命领导权的教条理解,认为民主革命只能由资产阶级领导。毛泽东恰恰在这一点上实现了理论创新,一方面承认革命的渐进性与现阶段的民主革命性质,另一方面又坚定地提出以无产阶级来领导民主革命。这是由无产阶级的先进性、中国国情的独特性决定的,于是他从理论上解决了党领导中国革命的正当性问题。正如毛泽东在1929年4月5日代表红军第四军前委写给中央的信中指出的那样,“在将来形势之下,什么党都不能和共产党争群众的……无产阶级领导是革命的唯一关键,党的无产阶级之基础,大区域产业支部之创造,正是目前党在组织方面的最大任务”。这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领导革命”立场的贯彻与发展。
进一步地,毛泽东等人还意识到共产党内部必须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领导革命。这是继承并发展列宁提出的“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思想。这最初是针对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具体问题而提出的,但对于党的建设问题的持续关注又使得这些思考日渐成熟,进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发展。1928年12月16日的《红军第四军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已经指出,苏维埃政权能继续存在的首要条件是“能坚决斗争的共产党”。1929年12月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对关于如何实现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有了进一步思考。在决议案中,“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被具体、充分地提了出来。毛泽东对党内存在的单纯军事的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的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党内存在的一系列错误认识进行批评,并提出党的组织问题、如何使党员到会有兴趣等具体问题;强调党内教育,在此基础上阐述具体的红军宣传策略、士兵训练等治理军队的具体措施。这一决议案充分体现了党的无产阶级先进性的自我要求与对军队的严格管理,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的具体深化,指明党的纯洁性、先进性对于党的领导的重要作用,尤其注重对党员的思想引导作用。
同时,这一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还认识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不是天然巩固的”这个十分现实的挑战。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领导革命的立场,但是并没有深入到“如何领导”的具体问题之中。1928年12月《中央通告第二十号》指出:“农民劳苦群众不是天然就跟着无产阶级跑的,这要靠正确的政策和不断的斗争来决定”。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广大农民的动员都面临着这一问题,而中国共产党人积极寻求解决办法。毛泽东等人在井冈山时期提出了较为实际的土地政策,强调对群众进行政治训练和宣传动员,并在教育群众的基础上武装群众,保卫土地革命的成果。这些探索都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基础上对政党领导革命的具体实践过程的深化探讨,是结合中国革命实际进行的创造性发展。
总结来看,井冈山时期中国革命道路探索蕴含着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继承与发展,继承了无产阶级政党领导革命的基本立场和对政党组织建设的重视,又在具体的革命实践中探索出适合中国共产党政党建设的具体思路与党领导革命的行动指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这一时期创造性地提出了“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民主革命”,初步回答了“什么样的党可以领导中国革命”“党要怎样领导中国革命”的问题,对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革命行动做出了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研究,是实践与理论共同发展的结果。
三、作为认识论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在这一时期的继承与发展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井冈山时期进行的革命道路探索构成了中国革命道路的起点,“工农武割据”具有的开端启新意义是巨大的,初步展现了中国革命道路的创新性。在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得到了继承与发展,构成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建设、改革的纵向独特性;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也进一步深化,成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道路与其他革命道路选择的横向独特性;而从更宏大的视角来看,马克思实践哲学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发展,这恰恰是整个中国革命道路的科学性所在。
现有研究对于这一时期体现的实践哲学往往采取了方法论的描述方式,认为马克思主义对实践的强调被作为一种方法吸纳进中国革命道路探索中,通过在现实场域内得到发挥而实现了对于方法的科学性验证。但是中国革命道路的创新除了在现实场域得到运作之外,还包含着对全新思想场域的开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实践不仅仅作为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得到了发展,更作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得到了突破。在这一道路探索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初步回答了“要以何种方式认识中国革命”“要以什么思想指导中国革命”等一系列哲学层面的认识论问题。
实践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与旧唯物主义最大的区别。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绝不仅仅是一种方法论,更是一种主体认识世界的认识论,实践哲学带来的最根本的革命是认识论革命。如果以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话来表述,那就是“把传统的思与行、沉思与劳动、哲学与政治的关系彻底颠倒过来”。这样的一种认识论转向意味着我们不再应该在寻求完备的真理之后才去行动,因为真理隐藏于行动之中,因此应该在行动中、在主体的对象化实现过程中去发现真理。其最大的特征就是反对教条主义。
井冈山时期中国革命道路探索恰恰是在这种认识论下面开展的行动。城市中心的教条主义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存在着。1927年11月中共中央通过的《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在支持农村割据的同时仍然体现出了以城市为中心的思路,认为“城市工人的暴动是革命的胜利在巨大暴动内得以巩固和发展的先决条件”;1928年11月8日《中央通告第十五号》也提出“群众工作的对象,最主要的当然是城市的广大劳苦群众——尤其是产业工人。没有城市的领导,乡村斗争很少胜利的可能”。这种思路很大程度上建立在苏俄革命经验的教条主义总结之上,提出理论的时候缺乏对实际情况的透彻了解,并没有给予有力的事实证据支撑。在这种以城市为中心的思维指导下,许多党内同志认为工作重心仍然要往城市偏移,企图通过全国城市暴动的方式一举赢得革命胜利。毛泽东很早就重视乡村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在大革命失败之前就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据亲历者回忆,在向井冈山进军、开辟革命根据地之前,毛泽东也一路调查党的和武装的情况,并在井冈山的斗争实践中十分注重了解周边情况,发展和检验了“群众路线”。当他于井冈山奋斗两年多之后,便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开始质疑城市群众起义的路线问题:“他们这种理论的来源,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件事认清楚”,认为中国的这一国情一旦被认清,必然会“明白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因而,也就会明白农村起义何以有现在这样的全国规模的发展”。另一方面,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判断也是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在《井冈山的斗争》中,他总结了一年多的革命经历,指出“我们一年来转战各地,深感全国革命潮流的低落……红军每到一处,群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地起来。和敌军打仗,不论哪一军都要硬打,没有什么敌军内部的倒戈或暴动……我们深深感到寂寞”。正是这种革命实践使毛泽东认识到,寄希望于全国性城市群众起义实现胜利是不可靠的革命道路,必须开辟出全新的实践场域。因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这一时期开辟的井冈山道路其实是建立在自身革命实践的基础上的深刻认识,井冈山时期中国革命道路的开辟其实蕴含着对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真正认同,将实践经验而不是教条作为道路选择的出发点。
除此之外,井冈山时期的中国革命道路探索对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也存在着发展意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一时期是毛泽东“实践论”的理论探索开端,更是“实践检验真理”的最好明证。许全兴指出,毛泽东1937年的《实践论》是以20年代末期到30年代初期的中国革命经验教训为基础的创作,尤其注重对党内教条主义的批判。事实上,毛泽东在《实践论》中也多次提到“战争”“革命”,并着重指出“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他在井冈山时期总结出了游击战术的“法门”: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等等。这一策略在现实中的运用使国民党方面的“围剿”均失败。据亲历者回忆,当时毛泽东领导下的红军已经熟练掌握了游击战术,使得国民党方面困扰不堪。而“这些都是在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中提出来的”。如果进一步分析,会发现对教条主义的突破、根据现实情况进行经验总结其实蕴含着“实事求是”思想的萌芽,即所有的决策和判断都要从客观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教条或者从以往的片面经验出发。因此,这一时期革命道路探索更深层次的哲学意义是“实践检验真理”的正确认识的确立。无论是对宏观革命道路的选择,还是对微观战术的总结,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都是在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基础上做出的科学判断。反观同一时期的左倾路线,他们缺乏对客观实际的承认,忽视了敌强我弱的情况,总以为革命高潮已经到来,于是轻易放弃根据地、一心想攻打大城市,最终的失败恰恰从反面上检验了井冈山革命道路的真理性。
总结来看,井冈山时期的中国革命道路探索不仅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尝试,而且还是毛泽东实践哲学的重要来源,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真理认识论的初步发展。毛泽东在此时一方面突破了教条主义的束缚,勇于实事求是地分析中央的决策失误根源、提出不同意见并给予强力证据支撑,另一方面初步展现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上升的认识论,在游击战争、开辟农村根据地等方面逐渐形成了完善的策略,为之后的革命斗争打下了牢固的基础。这种认识论深化无疑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不仅为中国革命树立了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观,而且强调在发现真理基础上对真理进行运用及检验。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进一步发展,确立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对中国革命的指导。
结语
井冈山时期中国革命道路探索展现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力图将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政党理论、实践哲学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尝试,在坚持实事求是、进行充分革命经验总结的基础上开辟出了中国独特的革命道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初步回答了中国革命要如何进行、中国共产党要如何领导中国革命、要以什么思想指导中国革命、要以什么标准探索正确道路等一系列重要问题,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民主革命”等一系列重要的战略指向和战术方针,为中国革命最终的胜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当前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经开始挖掘井冈山时期中国革命道路探索的马克思主义内涵,突破方法论视角,直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关系。比如,奈特强调“在1927—1937年的毛泽东的文献中,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毛泽东并没有‘背弃’工人阶级,并且他的思想也没有受到‘强烈的反城市偏见’的驱使”;石劲松提出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思想、马克思主义群众观、马克思主义独立自主理论在这一时期的应用与发展;陈桂香关注那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性质、无产阶级领导思想的延续与发展等等。此类研究大多关注阶级、社会性质、城乡中心的理论问题,提供了一种颇具潜力的“萌芽—发展”型思考范式,将马克思主义视作一种萌芽状态,移植到中国大地上后,它通过自身的逻辑演进与外部环境的刺激成长成独特的植株。因此这一模式既强调继承,又强调创新。本文即是在延续着这种思路的基础上进行研究,选取井冈山时期中国革命道路探索中的“革命”战略思想、“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理论与“道路”科学性三个核心层面来分析,推动对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仅是实践上的议题,而且在实践中也伴随着理论的发展与真理的检验。中国给予马克思主义以实践土壤,马克思主义给予中国以真理力量。正是真理与实践的结合,才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能够取得一次又一次伟大的飞跃。
回首这段艰辛历程,我们既能理解中国共产党人筚路蓝缕、开创大业的艰辛,又能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时期一以贯之的指导作用以及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发展。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没有辜负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也没有辜负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