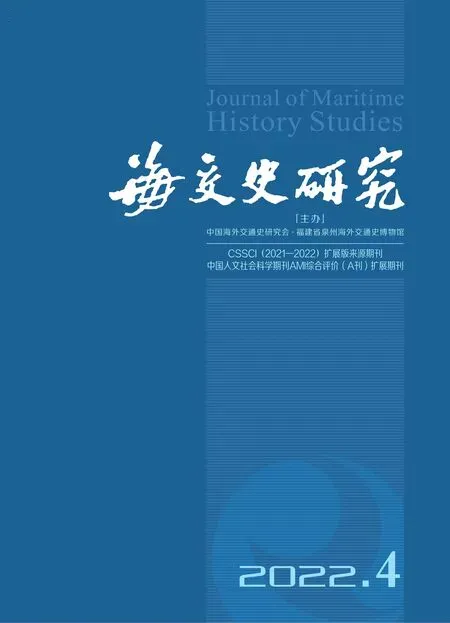江户时代日本俵物“出血输出”中国的历史逻辑*
安艺舟
*本文系2017年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青年项目“15—18世纪朝贡贸易体系下东亚海域城市交流圈的形成与发展研究”(项目编号:17CZS042)阶段性研究成果。
俵物,指日本江户时代专门用于出口的干海参、干鲍鱼和鱼翅。日语中“俵”有稻草包之意,这些脱水加工后的海产物用稻草包裹出口,故称为“俵物”,亦常将三者统称为“俵物三品”,出口的主要目的地是中国市场。为与其它出口品加以区分,日本又将除了铜和俵物以外的其它出口品统称为“诸色物”。在同时期清廷奏疏中,有“查商船回棹货物,向例四分铜斤、六分系彼处海菜等货,名曰‘包头’”“将各船所带回货减为二分半铜斤,余悉尽搭包头货物”的说法(1)《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卷177,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24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6页。,可知清朝方面有时也将俵物习称为“包头”。关于中日之间的俵物贸易,日本史学界已有一定研究,多从国际贸易角度出发,探讨日本国内管理和运输相关海产品的机制、收购方式与出口量,关注点集中在俵物的经济价值,认为日本出口俵物的目的,是为缓解长期大量出口铜导致的资源流失。同时,亦有研究者认为俵物大量投入中国市场,“深刻影响了中国菜的食材”(2)[日]日比野丈夫:《図説世界文化史大系》卷18,《中国IV》,东京:角川书店,1960年,第101页。“中国菜中才盛行使用海参、鲍鱼和鱼翅”(3)[日]大庭修:《日清贸易概观》,李秀石译,载《社会科学集刊》1980年第1期,第94页。。对于俵物出口背后的政治意图,以及俵物“出血输出”的缘由鲜少涉及。(4)相关成果主要有[日]小川国治:《江戸幕府輸出海産物の研究——俵物の生産と集合機構》,东京:吉川弘文馆,1973年;[日]荒居英次:《近世海産物貿易史の研究——中国向け輸出貿易と海産物》,东京:吉川弘文馆,1975年;[日]松浦章:《江戸時代に長崎から中国へ輸出された乾物海産物》,载《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紀要》45,2012年第4期;[日]松浦章:《清代海外贸易史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主要围绕日本国内管理和运输相关海产品的机制、地区以及收购情况进行研究。对于俵物出口的政治意图、“出血输出”的缘由以及俵物之于日本整体外贸战略的意义,至今并无涉及。国内学者对于此类进口品的研究集中在东南亚进口渠道,对日本渠道关注较少。国内学界对这一问题至今关注甚微。江户时代日本集全国之力推进俵物向清朝出口,为此构建起纵贯全国的生产、收购和运输网络,甚至不惜以民间禁食为代价经营,却始终未曾获得明显的贸易利润,反而在收益上呈现赤字状态长达百年之久,“出血(亏本)输出品”因之而得名。这种在政府统一管理下持续亏本经营的做法,势必带有鲜明的政治意图。“出血输出”的现实也不能不引人反思,以往研究中提出的俵物出口是为弥补铜资源流失、换取外贸利润的观点是否成立?俵物大量出口中国,又是否真正影响到当时中国菜式的食材选择?本文拟通过对中日双方原始文献的整理研究,在重新探讨这些问题的基础上,分析江户时代日本俵物“出血输出”中国的真实意图和历史逻辑。
一、日本俵物出口政策与“出血输出”
1698年,日本在继续强化定额贸易制度的同时,正式出台俵物出口政策,向前来贸易的中国商船发布新规定,将每年允许进入长崎港贸易的船数从70艘增加到80艘,条件是每艘船收购的日本货物价值定额8000贯,其中必须包括价值2000贯的俵物和诸色物。(5)《長崎会所五册物》,载《長崎県史·史料編第四》,东京:吉川弘文馆,1965年,第29页。1715年又颁布《海舶互市新例》,进一步向中国商人提出俵物收购要求,规定允许来航的唐船数额缩减为每年30艘,凭信牌抵达长崎后,购铜总上限定为150万斤,贸易额度定额6000贯,其中2025贯用于购买铜,2388贯购买俵物和莳绘道具、伊万里烧、长崎纸等诸色物,110贯用作工人费用,剩余1477贯为“唐人遣拾”费用,包括鱼、蔬菜、唐船的日常用度、预算以及“八朔之银”等交给日本外贸部门的礼金。此外还特意要求,在2388贯用于购买俵物和诸色物的额度中,俵物应占据大多数。如果在6000贯的交易之外,唐船还携带有多余商品,也可以用来交换俵物,除此以外其它商品一律禁止。(6)《通航一览》第4,卷166,《商法》,东京:泰山社,1940年,第399页。此后,俵物在日本出口中国的商品结构中所占比例急速上升,直至幕末,始终致力于不断增加俵物份额。为确保俵物供货来源稳定与运输渠道畅通,更是陆续做了以下专门性工作:
一是鼓励生产。为提高俵物产量,1763年幕府向九州地区、中国地区以及东北地区陆续派遣专门的俵物承办人,贷给渔民渔具,以求捕获更多俵物用于加工出口。(7)《外国商法沿革志》,载《長崎叢書·增補長崎略史》下卷,长崎:长崎市役所,1926年,第462页。次年又向全国下令,“奖励干海参与干鲍的制造和加工”(8)《外国商法沿革志》,第463页。。18世纪中期以后,俵物出口中国量迅速增多,幕府又相继于1764、1765和1778年多次下令,奖励各地干海参、干鲍和鱼翅生产(9)《外国商法沿革志》,第463、465页。,由政府统一收购。1786年因国产海参供货不足,幕府甚至临时从朝鲜调货海参1万斤,以补出口中国之用。(10)《外国商法沿革志》,第467页。
二是突出俵物权威性。1754年规定,除承包人之外,禁止一切干海参和干鲍的买卖,以供出口之急务(11)《外国商法沿革志》,第461页。,1765年禁止用作国内民间消费和买卖。此外,要求运载俵物的货船上都必须书写“御用”二字。长崎俵物会所以及各地俵物收购事务所,也要在门上张贴“长崎御用俵物会所”标签,以示权威。(12)《長崎県史·対外交渉編》,东京:吉川弘文馆,1986年,第574页。1831年,幕府又专门重申禁止国民食用和买卖干海参、干鲍鱼,并派遣专门的工作人员在九州各海岸巡回(13)《外国商法沿革志》,第477页。,确保无虞。
三是鼓励甚至强迫中国商人收购。俵物出口政策出台之初,由于中国尚未形成市场需求,销售渠道狭窄,清朝商人收购俵物回国后往往会遭遇亏损。《华夷变态》记载了日本俵物输出政策制定的第一年——1698年商人采买俵物的一些情况,首先是“三番南京船之唐人共申口”提到“在当地购买铜和俵物等”(14)[日]林春胜、林信笃:《華夷変態》卷26,东京:东方书店,1958年,第2031页。,随后4号、26号南京船采购俵物遭到亏损,同年5号、6号南京船,8号、10号宁波船和9号普陀山船都不同程度亏损,有的商船亏损大到无财力再次出海的地步。(15)[日]林春胜、林信笃:《華夷変態》卷26,第2032—2054页。加之中国商人赴日首要使命是“奉命采办洋铜”(16)[清]徐珂:《清稗类钞》,“农商类·范芝岩商于张北”,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304页。,出发前已从内务府支取本金,对俵物难以产生兴趣。为此,幕府采取强制销售措施。为避免长期滞留和空船回国,商人亦不得不进行妥协。俵物出口成为常态后,幕府甚至经常贷给中国商人银两,专门用来交换俵物,如1841年,一次性贷给一位唐船船主455贯银,用作购买俵物的经费,(17)《外国商法沿革志》,第479页。出口之迫切需求可见一斑。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幕府对与清朝的俵物贸易从一开始就寄予厚望,在生产、运输、消费各个环节都进行了充分战略部署,重视程度甚至超越当时仍占出口量第一位的铜资源。然而,付出如此代价经营的“战略性商品”,出口量虽在波动中上持续上升,却从经营第一年起就遭受巨大亏损,之后一直处在赔本经营状态,未给日本带来经济收益。为此,幕府一度推测中国人并不喜爱俵物(18)《長崎市史·通交貿易編東洋諸国部》,大阪:清文堂出版株式会社,1981年,第273页。,却没有丧失继续推动其出口的信心。1757年开始,日本对俵物实行“定值段”,即固定价格,售卖给清朝商人的干海参定价平均一斤2钱8分5厘7毛,干鲍鱼定价平均1斤2钱3分3厘3毛3弗(19)《長崎県史·対外交渉編》,第576页。,鱼翅平均一斤为2钱。此定价维持了一个世纪左右,一直到幕末不曾变化。在这一百多年的俵物经营中,俵物产量和市场物价都有诸多波动,经营越久,势必亏损越大。因此,固定价格反而促使亏损程度进一步加剧。《长崎县史》收录了1771年日本出口中国俵物的价格数据,涉及干海参和干鲍鱼两项。这一年,干海参出口量达到365630斤,长崎会所从渔民处收购的进价平均1斤为3钱6分9厘2毛2弗,干鲍鱼出口量49989斤,进价平均1斤2钱4分5弗,都远远超过上述幕府规定的出口价格。可见,俵物三品中,已有两种是确凿无疑的赔钱出售。而纵观从1744年到1784年共41年间的情况,俵物出口平均每年都会给长崎会所带来价值2000贯的外贸亏损。(20)《長崎県史·対外交渉編》,第575—576页。因此,俵物也随之而得名为“出血输出品”。
面对亏损,幕府的处理仅仅是压低商品进货价格和推进规模化生产,亏损部分由长崎会所补偿给生产者,始终未曾涨价,甚至明确表示,中国也好荷兰也好,想要的无非是日本铜,对于干鱼盐鱼等所谓俵物兴趣并不大,长崎会所要做好亏损的准备。(21)《長崎市史·通交貿易編東洋諸国部》,第309页。而俵物出口政策从18世纪延续至幕末始终未曾停止的现实也充分表明,幕府的首要目标不是为换取外贸利润。那么,到底是何种因素促成幕府不惜以长期亏损,甚至民间禁食为代价,持久推广和扶持俵物出口的决心?
二、出口俵物的真实意图
以往研究大多认为,18世纪以前铜矿过度开发和出口,使日本陷入铜枯竭危机。幕府引入俵物的主要意图,就是试图通过推进海产品贸易,在减少铜资源流失的同时,最大限度维持对清贸易利润。然而,如若俵物出口的直接目的是为追求经济利益,则难以解释面对长达一个世纪的亏损,仍坚持不懈的现实。在推动海外贸易大宗产品从铜到俵物转换的表象之下,尚存更深层次的目的有待解读。
(一)俵物并非专为避免铜资源流失而选择的代替物。
1659年,日本曾尝试增大铜出口量来避免银过度流失,产生过一定成效,却无形中造成铜资源过量出口,以至于“宝货流入外国已及大半”(22)[日]新井白石:《折焚柴记》112,《限制长崎贸易之建议》,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34页。,幕府对此也甚为担忧。然而,在18世纪的中日贸易环境下,铜是清朝商人络绎不绝前往贸易的直接目的,尤其清前期许多商人是内务府“招殷实商人采买洋铜”(23)《乾隆九年三月初四日山西巡抚阿里衮奏报监生刘光晟呈请采买洋铜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档案号04-01-35-1234-010。的号召下,从官府支取本金前往长崎购铜。幕府非常清楚,如若禁止铜出口,双方贸易实难继续维系。为吸引中国商船前来,保证中国生丝、端物(织物)、砂糖、药材等需求品的进口,铜贸易不得不继续维持。即使1715年《海舶互市新例》出台,明确限制中国商船购铜额度,增加要求中国商人必须收购俵物的内容,铜依然以2025贯的标准在贸易品分成中占据高比重。与此同时,《海舶互市新例》虽然将出口中国的铜量限定为每年150万斤,但依然会根据每年产铜量波动予以调整。《长崎实录大成》收录了1742年和1746年幕府关于铜出口量的两条诏令,其中1742年严格履行了“一年分铜量限于一百五十万斤”(24)《長崎實錄大成》卷11,载《長崎志》,长崎:长崎文库刊行会,1928年,第406页。的标准,至1746年却下令“以后唐船定数十艘,发予其古牌十枚作为凭证,一年可出口铜二百万斤”(25)《長崎實錄大成》卷11,第408页。,并未严格执行新例。
从实际事例来看也是如此,琉球《历代宝案》中记载了1741年一艘唐船在长崎收购货物后,返航途中因风暴漂至琉球的情况。根据琉球方面统计,船上搭载货物有“条铜七万七千四百九十九斤,共计一千五十九件。海参鲍鱼二万五千零八十斤,共计二百九件。红叶鰇鱼四千二百斤,共计三十五件。海带二万四千斤,共计四百三五件”(26)《历代宝案》第2集,卷25,台北:台湾大学影印本,1972年,第2377页。;1745年另一艘漂流至琉球的唐船搭载“条铜、海参、鲍鱼、海带等件”,累计条铜13万斤,参鲍10袋,鱼翅2小袋,(27)《历代宝案》第2集,卷27,第2445—2447页。铜占据绝对主体。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世纪。松浦章统计了1803—1804年间中国商船搭载铜和俵物的各自价值,合计铜值2300000贯目,俵物三品总计1940457贯目,(28)[日]松浦章:《江戸時代に長崎から中国へ輸出された乾物海産物》,第67页。铜的价值超过俵物三品总和。至于幕末日本铜出口量暴跌,是为铜山产铜量减少的客观现实决定的,也与俵物的存在与否没有直接关联,且俵物出口量虽在持续增加,占据日本出口商品总额的比例亦始终未曾超越铜。因此,幕府虽曾试图将清朝商人收购的关注点从铜引导至俵物,但俵物并不是,也根本无力成为日本为避免铜出口而选取的替代品。
(二)俵物“出血输出”是日本为打入中国海产品市场、带动其它相关产品出口中国做铺垫。
一般情况下,对某种商品的亏本销售目的无外乎有三,一是为提高产品知名度,打开市场;二是高价出售与亏本产品相配套的其它产品来获取利润;三是意图掀起抢购风潮。日本对俵物长达一个世纪的“出血输出”,在经济方面正是出于前两点的考虑。
清代中国进口海产品的主要来源有日本和东南亚两个渠道。对比之下,东南亚进口渠道仍维持传统商贸模式,日本则在规模化生产、运输、销售乃至专门针对消费者喜好经营等各方面都已遥遥领先。然而,俵物政策推行之初,中国并没有从日本大批量进口海产品的传统,仅仅是民间渔船有零星搭载回国贩卖的少许先例,如1656年清廷截获一艘民间走私船,搭载“番货如胡椒、苏木、铜锡、象牙、鱼皮、海味、药材等项,有数百担”(29)《顺治十三年正月初九日刑部尚书图海为汇报通洋接济巨奸请旨究拟以肃海禁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档案号02-01-02-1820-009。,1662年又查获一批“到东洋长崎”贸易的走私团伙,携带货物中包括有鲍鱼、鱼翅和海参,(30)《刑部等衙门尚书觉罗雅布口等残题本》,载《明清史料》丁编第3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51年,第528页。未形成有规律的收购模式。加之国产与东南亚进口海鲜渠道畅达,日本俵物占领中国市场的步伐势必相当艰难,前期为培养消费习惯、打开市场,赔本经营是必要的过渡阶段。而这一阶段恰逢清廷展海令推行前后,富庶官商对珍奇海味兴趣日增,甚至素来以本地海参为上品的山东,也出现“供不足以应求”的情况,不得不“多购自外舶”(31)[民国]宋宪章等修:《牟平县志》卷1,《地理志》,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1969年,第163页。。双方供需匹配,促使中国商人对俵物的态度由拒绝转向青睐,开始“用大量银来购买”(32)《長崎県史·対外交渉編》,第574页。。这同时也意味着日本在提高俵物知名度、培养消费习惯与打开中国市场方面取得一定成功。
以通航路线成熟、消费力强大的中国为目标,俵物只是日本带动整个渔业出口的第一步,对利润的漠视显然说明,俵物出口是一个长远的战略布局。这一布局的效果在18世纪末开始显现,俵物打开中国市场后,通过对环日本四岛海岸线俵物的大规模捕捞,附加获得的其它海产品也开始陆续出口中国。至乾隆年间中国就已形成日本“所产自铜而外,不过海参、海带、鳆鱼”的一般认识。(33)《乾隆元年正月十七日户部左侍郎李绂奏请停买洋铜以滇蜀之铜运京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档案号04-01-35-1226-027。史籍有收录的18世纪末出口中国的海产品包括昆布、乌贼、所天草、鲣节、切块海参、切块干鲍鱼、藤海参、刻昆布(海带丝)、干虾、干濑贝、寒天、干贝、獭皮等,(34)《長崎会所五册物》,第41页。其中又以昆布占据最大份额。18世纪,日本昆布向中国的出口量倍增,北海道出产的昆布经日本西海岸线一路南运,经下关和濑户内海辗转至琉球,再出口到中国,(35)[日]松本一男:《コンブロードと堺の昆布,第一部》,载《フォーラム堺学》,第5集,堺:堺都市政策研究所,1999年,第137页。所有载满货物的中国船只,空缺部分由昆布来补仓。(36)《長崎会所五册物》,第41页。主要口岸大阪、堺和萨摩甚至因此而出现大规模的昆布加工产业。与固定价格的俵物不同,其它海产物按市场规律定价,有利可图。据荒居英次对幕末各项海产品出口量及占比统计,至幕末,除俵物三品外的其它各项配套海产品总收益已超越俵物,为日本打开新的贸易局面。(37)参见[日]荒居英次:《近世海産物貿易史の研究——中国向け輸出貿易と海産物》,第558—561页统计表格。可以说,在俵物带动和幕府潜移默化的经营下,最终实现了对中国海产品贸易常态化的目标。
(三)通过俵物生产与贸易,进一步强化对地方资源的管控力度和统一调配能力,是幕府的重要意图。
日本在17世纪中期以后,对外政策从开放迅速走向封闭。从1635年正式推行海禁开始,(38)19世纪末至20世纪,日本“锁国史观”流行,学界多认为从宽永十年(1633)开始,幕府先后发布五次“锁国令”,并认为“锁国”是江户幕府的核心外交政策。这一理论也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日本史研究。事实上,日本历史上并未发布过明确标识“锁国令”或者“锁国”的公文,在同一时期,日本也始终在松前藩、对马藩、萨摩藩和长崎开放着“四个口”,来经营与朝鲜、琉球、虾夷、中国和荷兰的关系。因此,相对于“锁国”与“锁国令”来说,“海禁”用来概括这一时期日本情势更为恰当。就已规定“从前在九州各处往来的唐船,以后一概往长崎移动,一切向其它地方的渡海都停止”,次年“御奉书发布,日后从日本出发一切向外国出海都停止”(39)《長崎實錄大成》卷1,第11页。,将外贸对象限于中国和荷兰两国,贸易地点限于长崎一口,无论是铜还是俵物出口的权力和利润,全部由幕府直接掌控的长崎奉行统一管理,逐渐向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形态过渡。政治权力集中势必伴随着经济贸易权集中。然而,占据外贸收入来源主体地位的铜出口业经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机制已成熟甚至固化,17世纪铜出口利润几乎被大阪16人铜商团体垄断,幕府的收益来源主要是铜商上缴的“运上金”,具体发掘和出口过程难以全部控制。加之铜资源过度流失和产铜量逐年减少,国内收购铜的价格水涨船高,铜商自身亦日渐捉襟见肘。俵物政策的推行为幕府打开了新思路,经营之初,就采取严格管控、统一安排的做法,由政府选定专业承办人赴各地收购。收集来的俵物,集中到指定的采办机构——“大问屋”和“小问屋”管理。1699年又设置“俵物总问屋”,旨在强化对俵物在搜集、运输和出口各环节的统一调配,同时负责沟通中国商人和日本俵物采买商之间的关系。(40)《長崎県史·対外交渉編》,第569—570页。至1749年,管控更加严格化,明确规定,对于用来和中国贸易的重要海产品,除长崎俵物承办人之外,其它机构和人员一概不许介入。(41)《外国商法沿革志》,第460页。1799年又在长崎修建专门的俵物役所,(42)《長崎志続編》卷3,载《長崎文献叢書》第1集卷4,《続長崎實錄大成》,长崎:长崎文献社,1974年,第50页。所有俵物收购、聚集以及对外贩售,由长崎俵物役所一手包揽。同时,对于俵物的管理和控制始终处在不断收严过程中,尤其重视打击走私,使得俵物出口链条所有环节,都牢牢把握在幕府手中。
俵物出口的集中管理进一步强化了幕府对地方经济的直接管控,在两方面表现尤为明显。一方面,通过俵物生产运输,增强了各地区经济关联性,构建起纵贯全国的商贸网络。江户时代开采出的铜矿资源虽丰富,但大型铜山数量有限,在运输上能波及到的地区亦有限,主要集中在东京至长崎的运铜路线沿途,“专靠搬运货物铜斤往来交易、以资口食者,岂止十余万人”(43)《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卷174之17,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23册,第466页。,其余地区难以波及受益。俵物则不同,对于四面环海的岛国日本来说,大部分地区都可捕捞生产,俵物风干后耐储存耐运输,较之沉重且开采难度极大的铜,在促成全民参与生产和运输方面要容易的多。因此,鼓励俵物生产政策激发了各地参与积极性。《花蛮交市洽闻记》收录有1745年日本出口的俵物来源和各地所供应货物数量。其中干海参供货地有松前、津轻、南部、仙台、相州、尾张、三河、纪州、能登、越前、越中、丹后、备前、备中、丰后、平户、壹岐、唐津、筑前、安房、上总、武藏、伊势、志摩、播磨、阿波、淡路、讃岐、安艺、周防、长门、石见、出云、肥后、天草、岛原、萨摩和大村,干鲍鱼供货地有长门、筑前、佐渡、对马、平户、丰后、五岛、南部、天草、壹岐和松前。(44)《花蛮交市洽聞記》6,载《長崎県史》,史料编第四,第388—389页。这些地区遍布日本四岛乃至离岛,紧急缺货时还会从朝鲜调运。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各地大小问屋集中调度,幕府增强了对全国交通运输与人力资源的集中调配,以及对全国市场的统一监管。另一方面,俵物出口路径设置在长崎一处,并强行要求中国商人收购的做法,使得唐船除铜外,船舱几乎被俵物填满。加之1789年规定,无论金银铜钱还是杂货,只要私下贸易金额达到十两即算作走私,再犯者无论额度,均可判处死罪。俵物三品由俵物方役所直卖,与前者同等对待,买者与卖者同罪,(45)《長崎市史·通交貿易編東洋諸国部》,第460页。这种经济管控的集中化,进一步削弱了地方大名的实力。尤其是以经营海外贸易而发达一时的萨摩藩,外贸路径和利润被截断,在经济上受到严重打击,政治力量也随之削弱。在幕府经营下,通过铜和俵物出口换得的新式武器、商品、情报高度集中于长崎,对于下一步尝试经营以日本为核心的新型东亚贸易网络,起到至关重要的铺垫作用。
三、俵物出口中国的效果
日本学界多认为,日本向中国大规模输出俵物造成了中国市场上干鲍鱼、海参和鱼翅价格下跌,“变成了一种非常普及的食材”(46)[日]松浦章:《清代海外贸易史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第387页。“德川幕府俵物官方贸易开始的元禄十年(1697),即中国康熙三十六年左右,海产料理获得了在中国料理中不可动摇的地位”(47)[日]荒居英次:《近世海産物貿易史の研究——中国向け輸出貿易と海産物》引《青木正児全集》卷8,第38页。,以此来论证日本俵物大批量流入中国市场,深刻影响了中国菜的食材搭配。然而纵观中方史料可知,俵物对中国的影响并未达到这一程度。
首先,从俵物的进口量和供应区域来看,输入中国的俵物波及范围有限。18世纪俵物的贸易额,因现存数据资料多有缺失,很难对其进行精准的定量分析。现仅将可见的俵物贸易从开始到走向鼎盛阶段——1709—1815年间,明确记载有收购俵物的唐船数量和搭载情况分阶段进行统计(其中1715—1755年数据缺失)。

表1 1709—1815年间日本俵物出口中国数额统计表
从上述统计可以看出,俵物出口量除了在1715—1756年间因正德新例的强行推销政策而翻倍增加外,其他各时段波动都较大,总体并未呈现出持续上升态势,三种俵物各自出现出口量高峰的时段也并不相同。这很大程度上在于干货海产品捕捞和集约化生产仍处在起步阶段,产量受气候潮汐等自然因素影响较大。加之俵物不似铜一般属于迫切需求品,对中国来说甚至可有可无,难以实现每年定量出口、稳定增减的经营模式。1805年以后,随着出口至中国的其它海产品品种更加多样化,俵物的带动作用减弱,从表中可见,俵物三品中,干海参和干鲍鱼的出口量都开始显著回落。
日本俵物进口中国后,主要消费在江浙一带,并未造成普及全国的效应。赴长崎港贸易的清朝船只主要来自上海和乍浦,这两地同时也是清政府规定的赴日官民商船的启航与归航口岸。虽然日方统计,“宁波、舟山、普陀山、福州、厦门和广东亦有商船前来”,但依然是“上海和乍浦最多”(48)《長崎古今集覽》(下卷)卷13,载《長崎文献叢書》,第2集第3卷,长崎:长崎文献社,1976年,第369页。。乾隆时期闽海关亦报告“闽省商船俱系前往南洋、吕宋、葛喇吧等处地方贸易,并无往东洋日本长崎岛贸易者。其江浙有倭照商人,俱在江浙进口”(49)《乾隆五年八月初七日署理福州将军兼管闽海关事策楞奏请敕江浙二省仍招商办运洋铜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档案号04-01-35-1231-017。。由此可以推断,日本渠道进口的俵物首先供应于江浙一带,或是由官商带往北京。从表1中可以看出,江户时代俵物三品各自顶峰时段的出口值为海参33883.67斤,鲍鱼31216.61斤,鱼翅2768.59斤。根据李伯重的研究,江南8府从1400年到1850年,人口从900万增加到3600万左右。(50)李伯重:《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的低速增长及其原因》,载《清史研究》1996年第2期,第12页。以乾隆时期“东南各省风尚侈靡,普通宴会,必鱼翅席”(51)[清]徐珂:《清稗类钞》,“饮食类·豚蹄席”,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6268页。的奢靡程度来评测,从日本进口的俵物量尚难满足江南地区供应,更难以在中国的三种产品整体消费量上占据主体地位。即使标准化、针对性生产的俵物质量优于东南亚进口和中国本土海产品,江浙和北京作为清朝最大的消费中心就可以迅速消化这些日本俵物。
其次,清朝对日本俵物不构成路径依赖。中国沿海地区本可以自产鲍鱼、海参和鱼翅,民间也在明代就已形成对其品质默认的口碑和优劣之评。如海参,《清稗类钞》评价称“以产奉天者为最,色黑多刺,名辽参,俗称红旗参。产广东者次之,色黄,名广参。产宁波者为下,色白,名瓜皮参,皆无刺。别有一种,色白无刺,谓之光参,出福建”(52)[清]徐珂:《清稗类钞》,“动物类·海参”,第5709页。。加之鲍鱼、海参和鱼翅作为滋补品,在明清以来养生观念盛行的社会本就深受民间推崇,如鲍鱼,《医林纂要探源》称为“镜面鱼”,“可治骨蒸劳热,解妄热,疗痈疽,通五淋,治黄疸”(53)[清]汪绂:《医林纂要探源》卷3,“药性·介部”,丛书集成三编,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第316页。;海参“补心益肾,养血滋阴”(54)[清]汪绂:《医林纂要探源》卷3,“药性·介部”,第317页。,鱼翅则“味甘性平,补五脏,消鱼积,解蛊毒”(55)[清]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卷10,“鳞部·沙鱼翅”,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8年,第422页。,在东北至广东的广阔沿海地带都有出产。这种情况下,日本俵物即使打入中国市场,也难以占据主体地位。因此,从清朝文献的情况来看,亦疏于对日本俵物和其它干货海产品的专门记载。
再次,中国在明清以来消费鲍鱼、海参、鱼翅等高档海产品的习惯是潜移默化的过程,中国菜式的食材搭配并非因俵物进口而改变。在明代,三种海味均已成为豪奢之家宴席上的常备品。文人食谱中,多出现以海鲜占主体的“山水八珍”“海八珍”说法,甚至有以海参和鱼翅居于首位的“参翅八珍”和专门的“鱼翅席”“海参席”(56)[清]徐珂:《清稗类钞》,“饮食类·宴会之筵席”,第6265页。。尤其在经济富庶又尚豪奢之风的江南一带,消费这些高档海产品已成为日常,“大凡明日请客,须先一日煨之,方能融洽柔腻,若海参触鼻,鱼翅跳盘,便成笑语”(57)[清]梁章钜:《浪迹三谈》卷5,“海参鱼翅”,清代史料笔记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83页。。日本俵物大规模进驻中国市场的乾隆时期,中国三种海产品的消费量不仅并未出现突然增减,价格变化亦不明显。清代前期,海参和鲍鱼为珍贵难得的食材,时人评价“其贵而难致者,曰海参,曰鳆鱼(鲍鱼),曰西施舌,曰笔管蛏。四种为水族奇珍”(58)[清]李文藻:《诸城县志》卷12,“方物考第九”,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年,第353页。,到乾隆以后乃至晚清时期,俵物三品依然仍属于价格昂贵的食材。如汪康年所见地方官鱼翅宴,耗资三百金,依然被视作“古今食谱中之豪举”(59)[清]汪康年:《汪穰卿笔记》卷3,“杂记”,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91—92页。。如果日本俵物输入中国的量已达到深刻影响中国菜式构成的地步,势必会呈现出整体性价格降低、消费平民化趋势。而俵物三品在中国的消费局限于社会上层,加之另有国产和东南亚进口两种渠道,日本俵物对中国日常饮食的影响力是有限的。
四、俵物“出血输出”中国的历史逻辑
江户时代前中期的日本社会从动荡逐步迈向安定富庶。幕府一方面对国内集权要求愈发强烈,另一方面也存在扭转海外贸易被动局势、扩大本国在东亚国际经济和政治双方面影响力的野心。俵物的“出血输出”,正是提升其在东亚贸易网络中地位的重要一环。从推行效果来看,日本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预期。
首先,通过俵物“出血输出”,日本扭转了传统外贸模式中一味逢迎市场、追随他国喜好供应出口品的习惯。17—18世纪期间,日本频繁调整对外贸易规则,从相对贸易法、市法商法到御定高制,再到长崎会所设置和海舶互市新例的推行过程中,小规模政策变更亦时有发生,这种行为透露出幕府对现行贸易模式的不满态度,而这种不满的根源,正在于输出品大宗始终无法脱离资源类属性。这种状况从日明勘合贸易时期即已奠定,先后从硫磺过渡到金银,再过渡到铜,每种品类都曾红极一时,但囿于资源的有限性,无法长久维系。同时期荷兰商馆贸易则具有中继贸易性质,主要目的仍在以中国生丝、砂糖等商品换取日本白银运回欧洲。可见,两条主要外贸线路中,日本均处于被动地位。因此,“只有依靠本国土产的天然物进行加工制造,才能向外国无限供货,确保万无一失。何为可供无限出口的天然加工物?当属人参、海参、干鲍、鱼翅、干贝、乌贼、干海老、干濑贝、椎茸、寒天、昆布之类。”(60)[日]阳其二:《支那貿易說》,东京:制纸分社,1878年,第4—5页。而在以上诸类海产品中,俵物三品又最具利益前景,具有难以替代的优势:其一,产量稳定,四面环海的日本各地都可以产出,较之其它农产品来说产出受气候影响较小,较之重金属资源又不存在枯竭危机,可以长期大量经营;其二,价格昂贵,预估利润率高;其三,风干后干净卫生,可以长期储存,即使长时间漂流海上也不易腐坏;其四,重量轻,在船上占地小,可以大量搭载。而海产品若单靠一地产出来供应,成本高、收益低,只有各地配合共同供货才可能达到压低成本、大批量供货的目的,这无疑又与幕府调动各地资源集中调度、建立健全国家贸易体系的目的相一致。以此为原则,江户幕府除了继续积极主动推进干货海产物出口外,进口方面,对于赴日贸易商船的国别、船只数量、登陆口岸、时间、搭载商品等亦严格规定。急于扭转外贸被动地位,建立长期稳定的水产品出口链条这一意图表现明显。直至明治时期出口品种类持续增多,甚至生丝、茶等也开始变进口为出口时,日本仍在反复强调,此类产品不属本国自有之物,价格时有波动,收益不稳,只有质量上乘、供货稳定的海产品,才是日本最为理想的标杆性出口品。
其次,一定程度上促成日本的金银回流。俵物贸易虽长期维持在“出血输出”程度上,但从1763年中国商人王履阶“从中国带来元丝银三百贯目,希望换购铜三十万斤,其中正铜占七分,俵物三分”(61)《長崎實錄大成》卷11,第417页。开始,日本实现了银的回流。此后,中国商人逐渐开始用银购买俵物。1767年开始,中国商人开始又用金来购买,鼓舞了日本俵物大规模增产和集中收购。(62)《長崎県史·対外交渉編》,第574页。而幕府的致力经营又继续推动着金银回流。至19世纪30年代,产于云南的金开始大批量用作对日海产物贸易,所购商品大部分是昆布,甚至还有日本已流失海外的“和金”在双方海产品贸易中回流。(63)[日]内田银藏:《日本経済史の研究》卷上,东京:同文馆,1921年,第473页。中国商人也不像早期一般强烈要求购铜,而是专门前来购买海产品,购买重点也渐渐从俵物扩展至昆布,直至昆布占据双方贸易主流。这宣告着日本推行俵物出口真正显现出成效。(64)《長崎会所五册物》,第100页。内田银藏在《日本经济史》中统计了1791年到1840年间从中国实际输入的金银额,其中“足赤金843贯982钱9;其它各种金45贯906钱4;各种纹银等2929贯492钱7;各种银钱516贯299钱5;外加再输入的和金2358两”(65)[日]内田银藏:《日本経済史の研究》卷上,第475页。。然而,金银的回流程度依然远远少于日本战国时代以来的流失,也少于俵物输出的亏损速度,并未达到理想效果。
再次,在立足本国基础上,俵物“出血输出”的对象选定于中国,与日本立足东亚推进经济影响力提升的经营方向相一致。而中国巨大的市场又为日本提供了努力方向和想象空间。因此,日本对俵物的寄托,远远超出短时期内盈利的狭隘目的。在推进俵物贸易的过程中,日本联结起从朝鲜一直到琉球的商路,并试图以日本海产品作为整个东亚海产品优劣的衡量标杆,进一步规范各项海产物大小、品相、优劣、制法上的区分标准,宣称海产物“其南海所产者亦颇多,但我国品位价格都高人一筹”(66)日本水产局:《清国輸出日本水産図說》,“序言”,东京:农商务省,1886年。,以提高口碑,从而进一步拓宽中国市场。直至明治时期日本成立水产局,虽不再执行“出血输出”规则,在海产品产量、制法、商路方面,却仍在持续进行大规模开拓。1868年—1884年,干海参出口中国量从153612斤迅速增长到626882斤,(67)日本水产局:《清国輸出日本水産図說》,第16页。干鲍从1868—1882年从210240斤升至1071950斤,(68)日本水产局:《清国輸出日本水産図說》,第12页。鱼翅在1884年达到242029斤,(69)日本水产局:《清国輸出日本水産図說》,第13页。品相优者价格高昂。以干海参为例,明治时出口中国的海参细分为10个品种,品相最佳者称之为开片梅花参,卖价达到中国银每百斤140两。(70)日本水产局:《清国輸出日本水産図說》,第9—10页。但无论何种海产品,对于4亿人口的中国市场来说,只占中国需求的九牛之一毛,明治政府依然在继续改良制法、拓展商路。(71)日本水产局:《清国輸出日本水産図說》,第38页。而中国市场局面的打开,无疑是江户幕府对俵物百年来“出血输出”政策铺垫和经营的结果。
然而,幕府对俵物的布局和经营,以社会秩序稳定不变作为基本前提,从一开始就面临制度与实践的矛盾。18世纪中期,幕府选派的俵物承办人尚能够牢牢控制各地海产物收购和贩卖至长崎会所的专权,中期以后,各地商贩却都对此嗤之以鼻,“走私贸易丛生,运回长崎会所的俵物持续减少”(72)《外国商法沿革志》,第466页。。到1778年,幕府更加重视向各地下达奖励干海参、干鲍鱼和鱼翅生产的优惠政策,唐船商人搭载的俵物也一年比一年增多,但运往长崎的俵物却呈现出逐年减少趋势,迫使幕府继续加强管控,却始终未曾扭转走私泛滥之势,俵物出口已不再是统一调度资源的有效手段,主要受益群体也不再限于幕府自身。安政开海后(1854),东亚贸易格局急速变化,日本进出口政策亦发生巨大调整,对俵物出口品和出口对象国彻底无力控制,呈现出全新样态。
结论
总之,日本俵物出口政策,是为扭转海外贸易被动局势,提升在东亚贸易网络中地位做出的尝试,并非专为减少铜出口而设计的代替品。为此,幕府做了长远规划,不惜以长期“出血输出”为代价来培养消费习惯、打开市场,并一定程度上达到目的,刺激了中国市场对海产品的需求,中国商船对俵物的态度也逐渐从拒绝过渡到主动收购。但由于中国市场广大,俵物三品亦非日本独有,中国市场并不对日本俵物构成路径依赖,日本俵物对中国沿海地区菜式的食材构成、相关海产品的价格和消费习惯影响始终有限。明治政府建立后,放弃“出血输出”原则的同时进一步拓展对中国市场的俵物出口,虽因东亚海域国际局势变化而存在明显调整,但其贸易基础和经营理念,依然是在江户幕府俵物政策基础上的延伸和扩展。
——以青岛市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