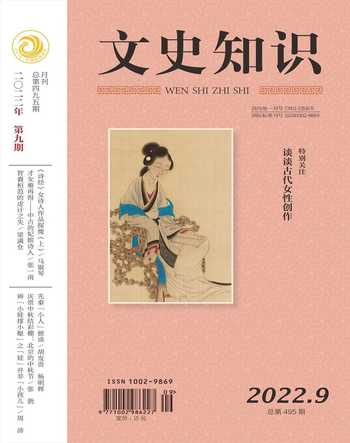《诗经》女诗人作品探微(上)
编者按:中国古代女性文学创作历史悠久,在《诗经》中就可以见到若干女子作品。古代女性作家的抒写有着比较浓重的人情味和现世性,她们关注的是与自身、现世相联系的人和事、情与景;艺术表达上,风格多是婉转蕴藉,时常伴随着节制、压抑的情感。本期特别关注诚邀四位专家,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角度,带我们领略古代女子创作的异彩纷呈。
西周时期的仪式乐歌《小雅·斯干》中有这样两章:“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无非无仪,唯酒食是议,无父母诒罹。”(孔祥军点校《毛诗传笺》,中华书局,2018,下同)由此可知,男女之间的尊卑差异,在当时被认为是与生俱来的存在。即使是贵族阶层,对于女子的整体要求也只有这么一句话:“无非无仪,唯酒食是议,无父母诒罹。”(不违背命令、不议论是非,只关心酒宴饭食,不要让父母忧惧)这是一个女子根本不享有基本权利的时代,女子需要接受的教育,唯有出嫁之前的“妇德、妇言、妇容、妇功”之教,而这项教育的实施目的,也仅仅是达到“无非无仪,唯酒食是议,无父母诒罹”。在这样一个被全面压制的时代,女性在创造与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往往会被历史的记录者刻意忽略或者弱化,如周室三母(尤其是公亶父之妻太姜),在《大雅·绵》诗的歌唱中,还曾与公亶父一起出现,“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但到史官的笔下,无论是《逸周书》还是《史记》,都不再有太姜的影子。而乱国、灭国之祸端,却往往会被追溯到某一位女子的身上。从西周初年周武王就以“牝鸡司晨,维家之索”谴责商纣王的罪过,到西周后期出现“哲夫成城,哲妇倾城”的警诫之语,都体现出对女性的警诫与不信任。于是,《小雅·正月》诗中原本是对褒姒乱政这一政治讹言进行质疑的“燎之方扬,宁或灭之,赫赫宗周,褒姒灭之”,在周平王最终胜出的大背景下,再经过“烽火戏诸侯”故事的铺垫,也最终变成了后世阐释者眼中“诗人知其必灭周也”的历史叙述,导致西周灭亡的罪魁祸首这口黑锅,也顺理成章地背在了褒姒的身上(相关讨论参马银琴《“褒姒灭周”故事与〈诗经·小雅·正月〉的性质》,《北京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
然而,只要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发生过的人与事,或多或少总是会留下一些痕迹。即使在等级森严的周代礼乐社会中,女性被有意识地排斥在社会政治生活之外,但不经意间,她们仍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在文化史、文学史上留下了印迹。《毛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作为周代礼乐制度的组成部分,“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的“采诗观风”,让《诗经》作品在应制之外,也保存了不少“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心灵之歌,其中不乏出自女性之口的作品。其中有作者身份明确的,如许穆夫人作《载驰》;有身份相对明确的,如“卫女思归”的《泉水》和《竹竿》;更多的作品则出自身份地位均已无从考知的女诗人之手。作为“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的情感表达的语言成果,这些歌辞借助“采诗观风”制度被记录和保存下来,为后人理解她们的情感世界以及文化思想背景提供了第一手材料。这一类作品虽然数量不多,但广泛分布于《小雅》与《国风》当中,尤其以郑、卫两国风诗中最为集中。本文拟以这些诗篇为基础,选择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几组作品,争取在准确理解诗意的基础上,探索《诗经》时代女性诗人丰富复杂的情感世界,以期进一步揭明不同的情感表达背后不同的思想背景与文化原因。
一 《鄘风·载驰》与《邶风·泉水》
第一组诗歌之所以选择《载驰》与《泉水》,一来因为它们是《诗经》中作者身份相对明确的作品,其中《鄘风·载驰》出自许穆夫人之手,而《邶风·泉水》自古被认为是出嫁他国的卫国公室女子的思乡之作,其身份及身世与许穆夫人有相似之处;二来则因为这两首作品相近的创作时代与背景。
先说《鄘风·载驰》:
载驰载驱,归唁卫侯。驱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则忧。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视尔不臧,我思不远。既不我嘉,不能旋济?视尔不臧,我思不!
陟彼阿丘,言采其虻。女子善怀,亦各有行。许人尤之,众稚且狂。
我行其野,芃芃其麦。控于大邦,谁因谁极?大夫君子,无我有尤。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
从诗歌的内容来看,这首诗作于卫戴公被拥立于漕邑时期。诗歌首章着重表达了许穆夫人听闻卫国大夫告难的消息之后忧心不已,想要驱车归返卫国漕邑以吊唁兄长卫戴公的心意。但是,返卫唁兄的想法因违背礼制而得不到许国君臣的支持,这让许穆夫人忧思不已,这是作者在第二章不断重复“不能旋反”“不能旋济”,“我思不远”“我思不”的主要原因。忧思不已,故有了陟丘、采虻之举,在这个过程中,作者在反思自己想法的合理性与许国大夫责难的幼稚与轻狂之后,进一步思考谁才是在卫国遭遇国难之后可以依托和指望的对象,并在诗歌的最后表明了采取实际行动的决心:“大夫君子,无我有尤。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许国大夫上百种的思虑筹谋,都不如我实际地走一遭。在这里,许穆夫人之“所之”中,不仅包含着“归唁卫侯”的因素,更重要的是“控于大邦,谁因谁极”一句所反映出来的求助于诸侯大国的意义。那么,这位许穆夫人又是谁呢?
许穆夫人是卫宣姜与卫宣公庶子昭伯所生之女,她出生在春秋中期卫国公室最为混乱的时期。卫宣公(前718年至前700年在位)曾为其太子伋娶齐女,但见到齐女美貌之后,强自娶之,这位齐女就是宣姜。宣姜为卫宣公生下子朔、子寿之后,进谗言致使太子伋与子寿被杀。于是,在卫宣公死后,宣姜之子朔继位,是为卫惠公。同时,在齐人的要求下,宣姜又嫁给了卫宣公的庶子昭伯,即《毛诗序》所说“公子顽”,生三子二女,除齐子早夭,二子相继为卫君(即卫戴公与卫文公),二女出嫁为宋桓夫人与许穆夫人。公元前668年卫惠公卒后,其子懿公继位。卫懿公好鹤荒政,导致卫国人心离散。前660年,狄人来袭,在有限的抵抗之后,卫懿公身死国灭,卫国遗民七百多人南渡黄河,宋桓公迎而置之于漕,立戴公。宋桓公能够出手相助,其中不可能没有宋桓夫人的积极推动。就在卫戴公接受宋桓公的救助在漕邑立足时,他的另一个妹妹许穆夫人也在闻知消息之后,开始了自己的救国行动。《鄘风·载驰》所表达出来的,就是许穆夫人当时的心声。许穆夫人思虑的主要问题就是“控于大邦,谁因谁极”,即向大国奔走求助,谁能够依托,谁是最后的指望?在当时的情况下,许穆夫人所能依托的,有谁呢?
按时间线索来说,卫国遭遇狄难在鲁闵公二年(前660),时值齐桓公二十六年。而从鲁庄公二十七年(前667)周王“使召伯廖赐齐侯命”开始,齐桓公就已经积极主动地承担起了诸侯之长的职责。前663年即发生了山戎伐燕而齐桓救之之事,齐桓公不但伐山戎至于孤竹,还“命燕君复修召公之政,纳贡于周,如成康之时。诸侯闻之,皆从齐”(《史记·齐太公世家》),齐桓公的霸业进入全盛时期。至前661年,在邢国遭遇狄人进犯时,齐桓公也听从了管仲的建议出兵救邢。因此,在时隔一年卫国再次遭遇狄人侵犯,君死军败之后,除了宋桓公,有能力救助卫国的,就只有当时的诸侯霸主齐桓公了。因此,许穆夫人“控于大邦,谁因谁极”这个问题的答案,只能是齐桓公。从历史的记载中,我们无法确认许穆夫人所说的“不如我所之”最终是否成行,《毛诗序》“许穆夫人闵卫之亡,伤许之小,力不能救;思归唁其兄,又义不得,故赋是诗也”这段说辞,表达出来的也是许穆夫人力不能救、义不得归的困境。但是,《左传·闵公二年》在记载卫国遭遇狄人之难后补叙的与卫国命运相关联的重要事件时,紧跟在“许穆夫人赋《载驰》”之后的,却是齐国的举动:
及败,宋桓公逆诸河,宵济。卫之遗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为五千人。立戴公以庐于曹。许穆夫人赋《载驰》。齐侯使公子无亏帅车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归公乘马,祭服五称,牛、羊、豕、鸡、狗皆三百与门材。归夫人鱼轩、重锦三十两。(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266—267页)
紧接在“许穆夫人赋《载驰》”之后的“齐侯使公子无亏帅车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似乎透露出了许穆夫人赋《载驰》与齐侯使公子无亏戍曹两件事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也因为《左传》的记载,许穆夫人之于《载驰》一诗的作者身份也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许穆夫人”由此成为文学史上一个闪光的名字而熠熠生辉。
再来看《邶风·泉水》:
毖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怀于卫,靡日不思。娈彼诸姬,聊与之谋。
出宿于泲,饮饯于祢。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问我诸姑,遂及伯姊。
出宿于干,饮饯于言。载脂载舝,还车言迈。遄臻于卫,不瑕有害。
我思肥泉,兹之永叹。思须与漕,我心悠悠。驾言出游,以写我忧!
《诗序》说:“《泉水》,卫女思归也。”从诗歌内容来看,这是一首卫国女子远嫁他国后思归不得而舒泄忧思、以诗写志的作品。全诗在叙述事由、表达感情时层次非常清晰。首章由故乡最具特征的泉水与淇水写起,直接叙写思念卫国,故向同嫁诸姬寻求帮助。第二章设想回归途径,想起当初因来嫁而远离父母兄弟,由此可知,卫女所思念者,就是此刻远在故乡的父母兄弟。第三章继续想象回家之路,想到了准备车驾时发现回归之路非常遥远,同时还想到了疾速归卫可能对礼法带来妨害以及由此心生忧疑。于是,在现实的困难面前,第四章重新回归“思归而不得”的现实,在一声声的叹息中,选择通过驾车出游的方式来宣泄心中的忧思。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在这首诗中得到了鲜明而直接的体现。
那么,这位思归的“卫女”究竟是何身份呢?诗中有云“问我诸姑,遂及伯姊”,而《春秋公羊传·庄公十九年》有云:“媵者何?诸侯娶一国,则二国往媵之,以姪娣从。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诸侯壹聘九女,诸侯不再娶。”该女所谋的对象既然是“诸姑”与“伯姊”,那么她就不可能具有诸侯夫人的身份,因此只能是卫国从嫁的媵者。这样的身份,与作为卫戴公亲妹妹的许穆夫人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除此之外,与《载驰》一样,该诗也提及了“漕”这个地名,与之同时出现的,还是泲、祢、干、言、须等从《毛传》开始就未能达成共识的地名。《毛传》以“地名”释“泲”与“祢”,以“所适国郊也”解“干”与“言”,而郑玄笺《诗》云“干、言,犹泲、祢,未闻远近同异”,亦是未知其地。而对于“须”,《毛传》以为是卫邑,郑玄笺《诗》则认为是“自卫而来所经邑”,至后世也一直未能达成共识。实际上,在这五个地名中,“泲”同“济”,或与济水关联。而“须”,在春秋时有须句国,为鲁之附庸;秦时置须昌县,后改为须城。而济水正好流经须句国。若诗中的“须”就是卫女所嫁之国,“漕”则是作为卫国的象征而出现的。诗中的“思须与漕”,正好代表着女诗人悠悠之思的两个端点。而对于卫国公室女子而言,“漕”所具有的代表卫国公室的意义,只能发生在卫人庐于漕时,而卫国在接受齐桓公的帮助之后不久,于僖公二年“封卫于楚丘”。也就是说,这首卫女思归的《泉水》,与《载驰》相似,其创作的背景也应该是卫国遭遇狄人之难后居国于漕的两年间。
这样一来,同样是出嫁他国的卫国女子,同样是在卫国遭遇狄人之难后思归而不得的抒情之作,《载驰》和《泉水》所表达出来的具有截然不同特点和趋向的思归之情就有了有迹可循的解释路径。《载驰》的作者许穆夫人与公室关系密切,她和宋桓夫人一样都是新立卫君卫戴公的亲妹妹,对卫国公室有着直接的关切,因此在卫戴公都于漕邑时才会有“归唁卫侯”的冲动,才会在卫人面临困境时急切地思考“控于大邦,谁因谁极”等紧要的问题。而《泉水》的作者不但是一名随嫁的媵者,而且在媵者队伍中,也位列诸姑、伯姊之后,她的身份与地位远不如许穆夫人尊贵,和卫国公室的关联也远不如许穆夫人密切。因此,她的思归,只是对淇水、肥泉等旧地故乡的寻常思念,并非基于对卫国公室的牵挂与担忧。因此,她在想到回归路途之遥远时,还想到了疾速归卫可能对礼法带来妨害的忧疑,“遄臻于卫,不瑕有害”。于是,在现实的困难面前,她很自然地放弃了归卫的打算,“思须与漕,我心悠悠。驾言出游,以写我忧”,选择通过驾车出游的方式来宣泄心中的忧思。《泉水》一诗“发乎情,止乎礼义”,甚至有些“闲愁”意味的思念,迥异于《载驰》的冲动与急切。这种不同,实际上表现了两位同样是远嫁他国,却因身份不同、地位不同、与卫国公室的关联程度也不同的卫国女子完全不同的情感世界。
二 《邶风·谷风》与《卫风·氓》
《小雅·斯干》把“无父母诒罹”作为对女子的最高要求,因此,女子出嫁而让父母安心的“归安父母”也就成为对女子最大的祝福。然而,在夫权至上的时代,女子没有任何自主权,即使出嫁在途的女子,也会因种种的不确定性而产生“未见君子,忧心忡忡。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降”(《召南·草虫》)的情感波动。如《草虫》毛传所云,“妇人虽适人,有归宗之义”,因各种理由被遣回娘家,是悬在女子头顶可随时落下的一柄剑,弃妇怨吟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常见的一个题材。这样的题材,也出现在《诗经》当中。兹拟以《邶风·谷风》与《卫风·氓》这两首分属于不同时代的弃妇诗为例,考察不同历史阶段上被弃女子不同的情感反应及其背后可能存在的文化原因。
先说《邶风·谷风》。其诗云:
习习谷风,以阴以雨。黾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无以下体。德音莫违,及尔同死。
行道迟迟,中心有违。不远伊尔,薄送我畿。谁谓荼苦?其甘如荠。宴尔新昏,如兄如弟。
泾以渭浊,湜湜其沚。宴尔新昏,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发我笱。我躬
不阅,遑恤我后。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浅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黾勉求之。凡民有丧,匍匐救之。
不我能慉,反以我为雠。既阻我德,贾用不售。昔育恐育鞠,及尔颠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尔新昏,以我御穷。有洸有溃,既诒我肄。不念
昔者,伊余来塈。
这首诗首章以“习习谷风,以阴以雨”发端,以采择葑、菲取其根茎的比喻,引出了“及尔同死”的夫妻约定,奠定了后面五章抒写被弃之后悲苦心情的基调:大归途中想起丈夫的喜新厌旧,无论是洁净的自己被认为浊恶的痛苦、顾念着家却又顾之不及的矛盾、操持家务时的辛苦劳作,还是今昔对比中丈夫的忘恩负义与薄情寡义,都让作者痛苦不已。从首章的“黾勉同心,不宜有怒”开始,“行道迟迟,中心有违”“我躬不阅,遑恤我后”“不我能慉,反以我为雠”,到最后一章的“不念昔者,伊余来塈”,着力表现的都是被弃之后的痛苦、彷徨以及不能断然割舍的复杂心理。《小雅》中也有一首名为《谷风》的弃妇诗,但是《邶风·谷风》和《小雅·谷风》相对简单的叙述相比,其以更为具体的细节,把被弃女子哀怨、凄恻、悲苦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从创作时代来说,《邶风·谷风》应该是西周后期宣王、幽王时代的作品(参马银琴《两周诗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276页),这也正是《斯干》一诗所提出的“无非无仪,唯酒食是议,无父母诒罹”最通行的时代。与此相对应,《邶风·谷风》所表达的情感当中,有痛苦,有哀怨,有对男子忘恩负义与薄情寡义的陈述,但是,在充分表达了自己的痛苦与哀怨之后,仍然是不能割舍的留恋,到诗歌的最后,作者仍然把情感停留在了“不念昔者,伊余来塈”的怀思之上。强烈而痛苦的情感体验让该女子突破了“无仪(议)”的限制,她不厌其烦地述说着自己的不幸遭遇,但是,从头到尾,她都没有对抛弃自己的丈夫有任何的谴责或批评。也就是说,她始终都没有突破“无非”的要求,在顺从接受被弃的命运时,仍然表现着缱绻与不舍。与之相比,《卫风·氓》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情感选择。
《卫风·氓》诗云:
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送子涉淇,至于顿丘。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将子无怒,秋以为期。
乘彼垝垣,以望复关。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尔卜尔筮,体无咎言?以尔车来,以我贿迁。
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于嗟鸠兮,无食桑葚。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
桑之落矣,其黄而陨。自我徂尔,三岁食贫。淇水汤汤,渐车帷裳。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
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静言思之,躬自悼矣。
及尔偕老,老使我怨?淇则有岸,隰则有泮。总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诗歌从男子借口贸丝来接近并谋娶自己叙起,二人未经媒妁之言而自主订下婚期,经过了忧心与喜悦交织的等待之后,在龟卜筮占均无不祥之言的前提下带着彩礼出嫁为妇。俗话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该女子的不幸人生就从嫁入男子之家开始了。诗人的自叙充满了反思与自省的味道,因此,在自叙婚后生活的不幸之前,首先以鸠鸟之食桑葚为喻,指出了男子与女子对待感情的不同态度,“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因此向女子发出了“无与士耽”的诫语。女子容颜的衰老就像桑叶“其黄而陨”一样不可抗拒,出嫁之后的贫苦生活就像淇河水沾湿车旁的帷幔一样改变着女子的容颜。尽管女子的行为没有任何差错,却不断地受到丈夫怀疑,根本原因只是在于其丈夫本来就没有原则、心意反复。女子在多年辛苦任劳任怨只换来暴虐伤害,不幸的遭遇也得不到兄弟的理解,甚至招致嘲笑时,只能静下心来自我感伤。想起“及尔偕老”的誓言,“偕老”之誓不由得让诗人心生哀怨。淇水有河岸,隰田有界畔,独独自己失去拱持,心无所依。没有想过未娶未嫁之前欢乐和悦时立下的恳切誓言会被违背,可誓言既然已经被违背了,那就不想了,“反是不思,亦已焉哉”的结语中,包含着自伤自悼之后的自决。
这首诗所传达的情感,与《邶风·谷风》的优柔寡断完全不同。前儒在说解这首诗时,多据《毛诗》续序“宣公之时,礼义消亡,淫风大行,男女无别,遂相奔诱,华落色衰,复相弃背。或乃困而自悔,丧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风焉”的说法,因诗中“子无良媒”等语,便认为这是一首未经媒妁之言而私订终身最终色衰被弃的女子的自悔之词。就诗意而言,诗歌第一章的叙述表现出了自由恋爱、未经媒妁之言约定婚期的意味,但第二章的等待以及“尔卜尔筮,体无咎言?以尔车来,以我贿迁”的卜筮与亲迎,都表现出了亲迎成婚的特征。而且,《周礼·地官·媒氏》有云:“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周礼注疏》,《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中华书局,2009,1580页]既然礼制的规定中都有“奔者不禁”的条目,那么“媒妁之言”就未必是当时婚姻的必备条件。更进一步而言,春秋时期本来就进入了一个礼制松散的时代,卫宣公可以娶其子之妻,卫宣公死后,宣姜又能遵从齐人的安排嫁给卫宣公庶子昭伯。这些现象的出现,都说明了“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齐风·南山》)的传统观念在这一时期并不具有多么强大的约束力。而且,在交代了“无良媒”却欢天喜地自愿出嫁的前情之后,从第三章开始的感叹、反思,一直到最后一章的“反是不思,亦已焉哉”,诗歌抒写的重心都在两人相处的问题上。出现在第三章的“于嗟女兮,无与士耽”,恰恰点明了问题之所在。为什么诗人要警诫女子“无与士耽”?从后文的叙述来说,这个问题与有无良媒无涉,却直接关系着女子婚姻生活的走向。对于该女子而言,这明明是你情我愿的一桩婚事,是龟卜筮占都没有显示出任何不吉兆象的婚事,为何自己会遭遇被弃的不幸呢?紧接在“无与士耽”之后的“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说明对于这个问题,作者已经有了清晰的答案,其答案就表现在“士也罔极,二三其德”上。对于一个没有原则、心意反复的男子而言,什么样的感情会是他放不下的呢?于是,当女子容颜老去,行事没有任何差错(“女也不爽”),却始终得不到男子倾心相待(“士贰其行”),甚至被粗暴对待,也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然而,更让人难受的是,自家兄弟不仅不理解女子的不幸遭遇,还肆意嘲笑。因此,在反躬自省的感伤之后,诗人清醒地认识到年少时立下的誓言已遭到未曾预料到的背叛。在这个时候,她没有像《邶风·谷风》的咏叹者一样沉溺于痛苦难以自拔,而是决绝地做出选择:“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同为弃妇诗,《卫风·氓》与《邶风·谷风》产生于不同的时代,自然而然也表现出了因时代差异所带来的思想观念、文化认知等方面的不同特点。但是造成诗歌截然不同的情感表达方式的原因,还与诗人自身的性格直接相关。很有意思的是,这两首诗歌都提到了初时的誓言,却表现出了完全不同的态度。《邶风·谷风》在首章就说“及尔同死”,与之同时出现的“德音莫违”,表现了作者心中暗存的期望。这种期望与诗歌最后的“不念昔者,伊余来塈”首尾呼应,成为贯穿全诗的痛苦、彷徨又不能割舍的优柔寡断的情感基础。而《卫风·氓》则在诗歌的最后才说到“及尔偕老”的誓言,同时出现的除了“怨”之外,还有对誓言会被违背的出乎意料与随之而来的决然。“亦已焉哉”作为全诗结语,不但可以理解为对被弃一事的决然态度,也可视为与过往生活的诀别。这样的情感态度,与其早年“送子涉淇”“泣涕涟涟”“载笑载言”“以我贿迁”等行为一样,都表现出了敢爱敢恨、果断刚强、拿得起放得下的性格态度。
三 《郑风·山有扶苏》《褰裳》与《遵大路》
《礼记·乐记》记载魏文侯与子夏论乐时说过一句话:“吾端冕而听古乐,则惟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自此“郑卫之音”作为专称为后人所熟知。《汉书·地理志》在叙及郑国地理环境与风俗文化之间的关系时,曾说:“幽王败,桓公死,其子武公与平王东迁,卒定虢、会之地,右雒左泲,食溱、洧焉。土陿而险,山居谷汲,男女亟聚会,故其俗淫。”《地理志》又言及“郑卫之音”:“卫地有桑间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会,声色生焉,故俗称郑卫之音。”除“郑卫之音”的说法之外,因为孔子明确说过“郑声淫”,又说过“恶郑声之乱雅乐也”,“郑声”也作为“雅乐”的对立面,成为“郑卫之音”之外另一个指向新声靡乐的代名词。经过战国秦汉时代的发展演变,人们开始把“郑卫之音”“郑声”,与《诗经·郑风》关联起来。等到宋代,狭义的“郑卫之音”“郑声”与《诗经》中的郑卫之诗、《郑风》之间的界限似乎进一步模糊起来。朱熹《诗经集注》更是在“郑、卫之乐,皆为淫声”的前提下,通过对郑卫两国诗歌的比较分析,提出“郑声之淫,有甚于卫”的说法,以进一步证成孔子“郑声淫”的判断:
郑、卫之乐,皆为淫声。然以诗考之,卫诗三十有九,而淫奔之诗才四之一,郑诗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诗已不翅七之五。卫犹为男悦女之辞,而郑皆为女惑男之语。卫人犹多刺讥惩创之意,而郑人几于荡然无复羞愧悔悟之萌。是则郑声之淫,有甚于卫矣。故夫子论为邦,独以郑声为戒而不及卫,盖举重而言,固自有次第也。《诗》可以观,岂不信哉!(朱熹《诗经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6,39页)
从朱熹的论述中可知,他得出“郑声之淫,有甚于卫”的理由有二,一是《郑风》中“淫奔”之诗的数量多于卫诗,二是卫诗“犹为男悦女之辞,而郑皆为女惑男之语”。所谓“男悦女”,应如《卫风·氓》“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所呈现出来的男方掌握着主动权的两性关系。那么《郑风》的“女惑男”,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特征呢?兹拟以被朱熹判为“淫女之词”的《山有扶苏》与《褰裳》为例,在理解诗义的基础上,进一步追寻《郑风》“女惑男”特征形成的文化原因。
先说《山有扶苏》。其诗云:
山有扶苏,隰有荷华。不见子都,乃见狂且!
山有桥松,隰有游龙。不见子充,乃见狡童。
扶苏、桥松为木名,荷华(荷花)、游龙则为泽中草名。子都、子充皆为美男子的代称。“狂且”与“狡童”,前者指行动轻狂之人,后者指狡猾多诈的少年。朱熹《诗经集注》于诗首章下云:“淫女戏其所私者曰:‘山则有扶苏矣,隰则有荷华矣,今乃不见子都,而见此狂人,何哉?”(《诗经集注》,36页)忽略朱熹对“淫女”的判断,他对于此诗之义的解读,无疑揭明了该诗的情感指向,这是一位女子对所遇男子的戏谑之词。
再来看《褰裳》: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岂无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所谓“惠思”,即爱而思念,“褰裳”,即撩起下裳。如此,诗之义可解为:你若真的爱我想我,就会撩起下裳涉过溱水、洧水来见我了;你不想我,难道就没有别人吗?你这轻狂的少年也太过分了。而朱熹《诗经集注》于首章下则云:“淫女语其所私者曰:‘子惠然而思我,则将褰裳而涉溱以从子。子不我思,则岂无他人之可从,而必于子哉?‘狂童之狂也且,亦谑之之辞。”(《诗经集注》,39页)无论是来见“我”还是“从子”,在情感的表达中,这首《褰裳》和《山有扶苏》一样,都表现出了两性关系中女子掌握着一定的主动权的特点。而这样的特点,除了这两首诗之外,在《狡童》《萚兮》,以及具有弃妇诗特征的《遵大路》中,都有一定的体现。《遵大路》诗云:
遵大路兮,掺执子之袪兮。无我恶兮,不寁故也。
遵大路兮,掺执子之手兮。无我魗兮,不寁好也。
“掺执”即执持、抓着;“恶”与“魗”,均指厌恶、丑恶;“寁”有速弃之义;“故”与“好”,指故旧之情好。就诗义而言,这应是一位被弃女子在男子离去之时,在道边牵其衣袖极力挽留之词:顺着那大路,抓着你的衣?;你不要厌恶我啊,不要这么快拋弃旧情。这里通过“掺执”表现出来的主动性,与《邶风·谷风》《卫风·氓》中女子被弃时逆来顺受的反应表现出了完全不同的意味。所谓的“女惑男”,应该就是指《郑风》中常见的这种由女子主动表达情感的方式与特点。
在此认识的基础上重新审视朱熹对于郑、卫两国诗歌特征的比较分析,可知这段文字比较准确地总结了郑、卫两国诗歌的总体差异:卫国的诗歌在相对自由的情感抒发中仍然表现出了比较浓厚的政教色彩,即朱熹所说的“多刺讥惩创之意”;而在涉及男女情思的作品中,女子多是两性关系的被动承受者,鲜少出现主动选择的情况;而郑国的诗歌,绝大部分是男女之间的情思歌唱,出自女性的主动表达在其中占据了很大的比重;即使是被认为“美武公”的《缁衣》当中,也能读出基于亲密关系的恩爱之情,如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就认为《缁衣》的作者“可能是一个贵族妇女,也可能就是这位穿缁衣者的妻妾”(中华书局,1991,219页)。由此而言,《郑风》多男女情爱之词,且情爱的表达多出自女性之口的特征是朱熹得出“女惑男”结论的主要依据。(未完待续)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