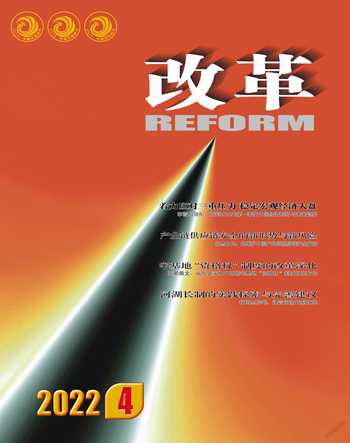数字经济的就业创造效应与就业替代效应探究
胡拥军 关乐宁



摘 要:数字经济深刻影响着就业市场的变革,使得就业载体、就业形态、就业技能要求发生重大变化,既存在巨大的就业创造效应,又面临显著的就业替代效应,其背后有着深刻的内在机理,对不同时期、不同区域、不同群体产生着结构性的影响。从就业创造效应来看,数字经济提供新型就业岗位对稳就业作出了突出贡献,但数字经济蕴含的扩就业总量的巨大潜力仍未充分激活,在劳动制度、权益保障等方面存在一些短板弱项。从就业替代效应来看,数字经济对优化就业结构的成效明显,但需要警惕就业替代效应带来的结构性失业冲击等风险苗头。数字经济是未来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的重要基石,要破除就业壁垒、加强风险应对,积极优化数字经济就业创造效应与替代效应的政策设计。
关键词:数字经济;就业创造效应;就业替代效应
中图分类号:F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43(2022)04-0042-13
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就业促进规划》提出,“以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为主要目标,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健全有利于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的促进机制”。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对就业市场产生着持续而深远的影响。与历次产业变革相比,以数字技术变革为基础的数字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就业创造效应和就业替代效应更加激烈、深化、长久。如何因应数字经济的就业创造效应与就业替代效应,统筹就业长期总量扩容与短期结构风险,加快就业政策制度体系调适,是我国稳就业、保就业的关键课题。
一、数字经济正在引发就业市场质与量的变革
以数字技术创新应用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发展推动了劳动力市场的质变与量变,一方面引发了就业载体、就业形态、就业技能要求的显著变化,另一方面对就业数量产生了双重影响,形成了带有明显数字经济时代特征的就业创造效应与就业替代效应。
(一)就业载体发生巨大变化
数字经济的发展改变了组织的架构形态与管理模式,工业时代的静态、线型、边界清晰的组织形态得以重构。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各类资源要素快速流动、各类市场主体加速融合,企业边界被不断突破。我们能够基于网络化的链接构建起包含产学研用等在内的创新生态系统,构建起动态、网络型、无边界的新型组织,网络和平台越来越成为重要的就业载体。一方面,用工无需局限于组织内部的劳动力,而是能借助数字化网络或平台向各个社会节点寻求联结,“经营方式从传统的等级化的集中经营向分散经营转变,它的特征是合作、社会网络和行业专家、技术劳动力”[1]13。与此同时,个体生产者、创业者也能依托网络实现更高质量的自主就业,能够更为广泛高效地从其他社会节点获取订单、接受培训、对接资源等,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拥有了更为坚实的基础与更具活力的动能。
(二)就业形态产生深刻调整
一方面,数字经济打通了劳动的情景区隔。在工业化时代,空间的边界构成了当班(on duty)和不当班(off duty)的区分,工作需要劳动者聚集在一定的物理空间内才可进行。但数字经济泛在连接的特性,打通了工作与非工作的情境边界,既使得传统工作可借由远程办公、在线会议等手段得以在更多时空形态下得以展开,促进了企业降本增效,并由此催生了一批依托网络的新岗位新职业,为不同群体提供了更为多元包容的劳动机会。另一方面,数字经济打破了人与岗位的固定联结。在工业化时代,某一岗位往往对应于特定职责、特定个体,但数字经济时代,“工作计量单位从‘牛顿力学迈向量子力学”[2],岗位可被解构为由不同单一技能所组成的“技能集”,再通过网络平台向社会发包,寻找不同适配技能的劳动者。一个岗位可由多个个体共同完成,一个个体也可同时适配多个岗位。新的劳动方式也产生了新的就业形态,在签订劳动合同、建立固定劳动关系的标准就业形态之外,产生了“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网签加盟‘合作合营‘利益分成‘众包模式等新型模式”[3],劳动关系认定及建立在其之上的劳动者权益、用工责任等也都产生了重要变化。
(三)劳动要求发生重要变化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发展为自动化过程的劳动资料的生产力要以自然力服从于社会智力为前提”,社会生产方式的转换也需要新的劳动技能与新的社会生产相匹配。一方面,数字技术和智能机器正在成为重要的生产工具,使得“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当事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4]218,这也就意味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劳动输出将更多以脑力为主,标准化、流水线式的体力劳动将交由智能机器所承担,这将极大地促进人力的解放,“在必要劳动时间以外,为整个社会和社会的每个成员创造大量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即为个人发展充分的生产力,因而也为社会发展充分的生产力创造广阔的余地)”[4]221。另一方面,数据成为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资源。这意味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大量工作将以“数据”为核心展开,对劳动者的数字技能和数字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数字人才的社会重要性和市场需求度不断提升。尤其是在跨界融合、交叉渗透的创新环境下,掌握多类知识、拥有多种技能的复合型人才会更受青睐。
(四)数字经济对就业数量形成创造效应与替代效应
数字经济不仅会改变就业载体、就业形态、劳动要求,而且会形成对就业数量影响的创造效应与替代效应。创造效应与替代效应的来源是由于数字经济引致了宏观经济和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变化。从宏观经济方面来看,其对社会生产率、产业、技术的影响会作用于劳动力就业部门的规模;从劳动力市场内部来看,就业载体的变化、就业形态的调整、劳动要求的改变会引起就业岗位及需求的变化。创造效应意味着数字经济将创造大量新型的就业岗位,比如芯片產业发展带动了大量高技术人才进入芯片设计、芯片代工、芯片封装等领域;替代效应意味着部分就业岗位将会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中逐渐消失,比如“机器换人”使得大量制造车间的流水线工人失去饭碗。创造效应与替代效应的对冲形成的最终情形,即数字经济对就业的综合效应,数字经济到底是扩大了就业还是减少了就业,难以一概而论,需要从不同时期、不同群体、不同区域进行结构性分析。
二、数字经济对就业市场变革影响的内在机理
从历次技术变革对就业影响的长周期来看,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是一柄“双刃剑”,而数字经济对就业相互对冲的双重影响更加明显,既有就业创造效应,又有就业替代效应。两种效应的力量对比,即数字经济对于就业的综合效应,在不同维度具有显著的结构性差异。
(一)数字经济就业创造效应的内在机理
一是生产率提升引致劳动力需求增加。数字经济发展将会带动整个社会生产率提升,进而通过作用于产出、需求等带动就业(见图1)。2018年2月,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发展中心对1993—2007年17个国家的数据研究发现,增加机器人使用会使年度劳动生产率提高 0.36 个百分点。相比之下,1850—1910年,蒸汽技术对英国年度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为 0.35 个百分点。Paolo Pini将数字技术进步带来的就业创造效果分为价格效应和收入效应。价格效应是指技术进步提升了劳动力生产效率,导致产品生产成本降低、价格下降,在名义收入不变的情况下,市场会增加对产品的需求,继而带动产业规模扩大、产业工人增加。收入效应是指技术运用带来的产出增加将会提升劳动者的收入,从而激发劳动者的需求,进而刺激企业扩大生产规模与用工规模。普华永道分析认为,人工智能在提升劳动生产率的同时,将对产品价格产生显著影响,提高消费者福利和实际收入水平,从而扩大消费需求;企业为了满足新增需求则需要雇用更多劳动力,从而创造新就业。除降低物价之外,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还能提升现有产品质量、创造更多新产品,这同样创造了更多就业需求[5]。
二是产业部门创新引致劳动力需求增加。技术进步将通过创造新产品、新机器、新产业部门等促进就业增長。Harrison等研究发现,产品创新引致新产品需求的增加极大地促进了就业。在由产品创新带来的就业中,至多有1/3来自同行的工人的转移,最少有1/3来自新产品的生产带来的市场扩张[6]。一方面,数字技术的研发管理本身就需要高技能劳动力的大量投入,根据德勤的研究报告,在过去的35年里,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的信息技术管理人员增加了6.5倍,编程和软件开发人员增加了近3倍。计算机的使用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导致市场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显著增加。另一方面,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由此诞生的新模式、新业态也创造了大量的新就业岗位。Moretti E.指出,2001—2011年,互联网行业的工作岗位数量增长了634%,是同一时期其他国家/地区经济总体工作岗位数量增长率的200倍以上。全球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McKinsey)估计,仅互联网部门就构成了2004—2008年美国经济增长的五分之一。
三是技术扩散的补偿机制引致劳动力需求增加。马克思指出,“虽然机器在应用它的劳动部门必然排挤工人,但是它能引起其他劳动部门就业的增加。”[7]509如投资银行高盛(Goldman Sachs)纽约总部的美国现金股票交易柜台,因自动交易程序对工作的接管,股票交易员由原来的600名减少至2名,但同时雇用了200名计算机工程师[8]。此外,数字经济的融合性特征还能对其他行业起到关联带动作用,美国有研究显示,城市中每增加1个高技能岗位,就会带来5个消费型服务业岗位,包括技术性职业(如律师、教师、护士)和非技术性职业(如服务员、美发师、木匠)。如苹果公司在库比蒂诺地区拥有12 000名员工,同时也在当地创造了60 000多个额外服务工作岗位,包括36 000个非技术人员岗位和24 000个技术人员岗位[9]。
(二)数字经济就业替代效应的内在机理
一是生产率提高引致劳动力需求减少(见图2)。Aghion & Hoowitt指出,技术进步从两方面对就业产生“创造性破坏”作用:一方面,技术进步降低了当前工作岗位价值、缩短了工作岗位的生命周期,从而可能减少劳动力需求;另一方面,技术进步促进人力资本价格的提升,导致企业利润降低,进而影响企业进入市场以及创造工作岗位的积极性[10]。龚玉泉等提出,技术进步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导致单位产品所需的劳动力投入降低,在产出给定的情况下,会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11]。
二是智能技术创新应用引致“机器换人”。智能化、自动化技术的发展不仅会大幅降低机器设备的价格,使得原本相同的资本投资可以购买更多能够替代人力的设备,而且机器设备效能的提升也会降低对机器管理、运营、维护人员的需求,双重效应导致人工岗位减少。Daron Acemoglu等研究发现,1990—2007年,每千名美国工人中增加1个机器人,全美就业人口比下降0.2%,工人的工资降低0.42%。这意味着美国制造业中每增加1个机器人,平均会取代3.3名工人[12]。
三是产业结构变革引致技术性失业。弗里曼和佩雷斯的技术范式理论认为,在新技术扩散导致社会发生结构性变革的时期,会出现失业率上升的现象,当社会经济制度逐渐适应新技术经济模式以后,经济会再次繁荣,伴随着劳动力结构的调整,失业率也会下降。在新业态冲击、取代传统业态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使部分职业大量减少甚至消失。在历次工业革命演进过程中,包括人力车夫、卖报员、电梯员、电话接线员、底片冲洗工等岗位已经消失。1900年,41%的美国人在农业部门工作,而到2000年这一比例仅为2%。2015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与1999版相比,包括“话务员”“制版工”等在内的894个职业被取消。
(三)数字经济对就业影响的综合效应研究
从长周期来看,技术与产业变革带来的就业创造效应大于替代效应,新技术、新产业的涌现是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的根本动力。以第一次工业革命为例,以蒸汽机为动力的发明和广泛应用造成英国大批手工业工人失业,但机械化应用推动了矿山、冶金、化工、石油、运输等新兴产业部门的发展,带来了大量新型就业岗位,提高了全社会的就业量和就业率[13]。不容忽视的是,技术与产业变革对不同时期、不同区域、不同群体的影响具有结构性的差异。
从时序影响来看,根据新古典劳动力需求理论,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主要取决于总需求的技术弹性。从短期来看,技术进步率对需求的影响可能较小,长期内弹性较大。因此,技术进步在短期内可能降低就业,在长期内可能增加就业[14]。数字技术在发展之初可能伴随着阶段性的失业率上升,但随着社会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生产效率的持续提升、产业门类的日益增多、社会投资和需求不断增大,会创造出更多的工作岗位;加之人力资本的逐渐提升,劳动者的技能与工作岗位的匹配度也会不断提高,劳动者能在长期内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从区域影响来看,技术对就业的影响因各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状况、人才结构、教育培训、社会保障、就业政策等因素的不同而呈现较大的差异。从整体来看,发达国家的就业受技术进步的影响相对较小,据世界银行2016年的发展报告估计,未来20年OECD国家57%的工作将被人工智能替代。发展中国家由于以中低成本劳动力为竞争优势、处于产业价值链中低端、人才体系尚不健全,其就业受到的技术冲击会更加明显。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数据(2017),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将有超过85%的零售工人被自动化销售替代。
从群体影响来看,数字经济对不同类型的劳动者产生的冲击具有显著差异。根据劳动内容,可分为程式化工作和非程式化工作;根据劳动技能,可分为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数字经济对程式化工作冲击最大,且其替代作用正从体力劳动向脑力劳动延伸扩大,这对部分白领和蓝领工人会产生较大冲击。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6全球人力资本报告》,随着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的持续渗透,全球对劳动力的需求尤其是是对白领和蓝领技工的需求将减少700万人。
三、数字经济就业创造效应的表征及其制约因素
数字经济作为集聚创新要素最多、应用前景最广、辐射带动作用最强的经濟形态,能够有力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激发社会创新动能,但其创造大规模就业机会的巨大潜力释放面临种种现实壁垒。
(一)数字经济就业创造效应的表征
1.数字经济直接创造新岗位
数字经济发展能有力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新动能发展壮大,释放出更多新兴岗位,成为我国就业的新增长点。一方面,新技术催生新岗位。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对于软硬件开发、技术架构、实施运维等多种技术密集型岗位的需求不断增长。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岗位数量从2010年的185.8万增长到2019年的455.3万,增长率达145.0%。另一方面,新业态孵化新职业。随着数字化向各个行业的全面渗透,一些新型岗位被创造出来,既包括传统职业在数字经济时代的再创新,如无人机驾驶员等,又包括数字经济新业态催生的全新岗位,如网约配送员、全媒体运营等。2019年以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先后发布了4批共56种新职业,大量职业与数字经济相关。
2.数字经济间接创造新就业
数字经济发展创造出覆盖广泛、开放协同的数字生态,有力带动了产业上下游就业增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数据显示,我国灵活就业从业人员规模已经达到2亿人,约有8 400万劳动者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约占全国就业人数的11%。如滴滴平台2018年共带动就业机会1 826万个,其中包括网约车、代驾等直接就业机会1 194.3万个,还间接带动了汽车生产、销售、加油及维保等产业链上下游就业机会631.7万个[15]。微信平台上,由公众号、小程序、视频号、微信支付、企业微信等共同构成的微信生态,2020年衍生就业机会3 684万个,同比增长24.4%[16]。
(二)数字经济就业创造效应的制约因素
1.数字经济时代的劳动制度亟待创新
新就业形态难以简单纳入传统的劳动雇佣关系。现有劳动法是在工业经济的大生产背景下制定的,针对的是科层制的组织用工模式,在平台化、网络化组织大量涌现的数字经济时代表现出了明显的不适应性。以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具有区别于传统雇佣形式的创新特征,在二元分割的法律体系下遇到了身份认定与社会保障的巨大挑战。一方面,这部分灵活从业者具有从业年限拉长、工作时间剧增、经济依赖程度提升、因“平台积分”而受制于平台规则等特点,具有明显的劳动关系特征;另一方面,灵活就业群体又具有能够自主决定是否工作、何时工作以及何地工作,不同于劳动关系下受拘束给付劳务的灵活属性,且存在“多平台同时就业”的情况,与劳动关系并不完全相符,劳动者与企业的关系难以界定。而我国包括劳动基准、社会保险、离职补偿等在内的福利保障都是基于劳动关系之上的,这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
新就业形态难以简单纳入既有的劳动保障体系。若简单地将平台企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灵活就业人员之间认定为劳动关系,纳入现行劳动保障法律调整范围,将大幅增加平台企业责任与成本,既不利于新经济新业态发展,又不利于吸纳劳动者就业。以社保缴纳为例,若是要求平台企业完全比照劳动关系承担费用,由于平台灵活从业群体规模庞大,这将会形成一笔“天文数字”,为企业带来巨大的财务压力。除经济性考量之外,在正当性层面也有商榷之处。以工伤保险为例,由于劳动者工作时间、工作场所的灵活性特征,工伤保险的主体责任、保障范围边界难以判断,工伤认定将面临种种障碍。强行适用劳动关系为企业带来的负担必将拖累平台经济的发展,这会反过来限制企业用工的积极性,导致缩招、减薪、裁员等情况,向社会输出失业压力。因此,亟需加快推进制度创新,在保障劳动者权益、促进新业态发展、扩大就业规模三项重要公共利益之间取得平衡。
2.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权益保障不足
一是劳动基准缺失,劳动者缺乏加班限制、休息休假、安全卫生的保护。在生存和竞争压力、平台严苛考评体系下,劳动者不得不超负荷工作。就外卖领域而言,39.40%的骑手每天工作时长超过12个小时,37.32%的骑手表示自己每月基本不休息;88.28%的骑手因为担心订单超时、不能按时送到而选择违反交通安全规则;24.78%的骑手患有胃病、腰肌劳损、颈椎病等慢性疾病[17]。就快递领域而言,我国快递从业人员每天工作10—12小时的占33.69%,近20%的从业人员工作12小时以上,末端揽投人员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的比例更高[18]。就网约车领域而言,大部分网约车司机一周出车7天,占比约74.76%,出车在5天以下的司机群体比例不足10%[19]。
二是社会保险缺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参保率偏低,以货运行业为例,仅有22.5%的货车司机投保了交通意外险、7.7%参与医疗保险、7.6%投保养老保险,参与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的比例更小,还有20%的货车司机没有投保或缴纳保险费用[20]。这主要是由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不属于标准化的劳动关系,难以满足现行社会保险体系的参保条件。尽管当前法律为灵活从业群体提供了个人身份参保的通道,但范围有限(往往仅包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且存在缴费偏高、户籍限制、申报手续复杂、异地转移接续困难等问题,保障范围和力度明显不足。在工伤保险方面,骑手、快递员等劳动者工作环境复杂、强度大、工伤高发,但缺乏参与社会工伤保险的制度通道,实践中往往以商业保险替代,但存在保障范围窄、理赔难、保障水平低等问题。
3.数字平台的不规范用工问题突出
一是利用垄断优势盘剥用工。一方面,公平性存疑。部分平台在获得市场优势地位后,调整计价规则等经营策略,设置过高抽成比例,且抽成规则具有任意性、不透明性。这种平台单方制定、与劳动者地位及利益不对等的分配机制违背了公平公开、透明规范的市场准则。另一方面,正当性缺失。部分平台在利益最大化导向下实施“最严算法”考核机制,迫使劳动者不断提升劳动强度,甚至引发人身健康风险。如为了缩短时间,外卖平台系统有时会给骑手输出包括逆行、人行道行使电动车等违反交通规则的指令,导致外卖骑手工伤高发。
二是利用制度空白转嫁风险。由于现有劳动者保障机制是基于传统用工形式下的劳动关系而制定的,出于降低用工成本、规避劳动责任的动机,部分平台会通过用工关系层层转包、将劳动者注册为个体工商户等方式,将本应由平台承担的责任转嫁给劳动者个体与社会。数据显示,外卖平台将骑手配送业务转包至外部公司后,其承担用人单位责任、与骑手认定劳动关系的概率,从100%降到了1%以内[21]。劳动关系的认定困难将导致劳动者社会保障不足、职业伤害维权困难等诸多问题。
三是资本无序扩张冲击就业。超大平台依靠垄断优势持续跨界扩张,并通过不公平价格、限定交易、差别待遇等不正当竞争行为谋取市场优势地位,大大降低了创业者的市场进入动力,加大了中小企业的社会融资难度,对传统行业从业者产生了较大冲击。尤其是近年来超大平台纷纷进入社区团购等民生领域,以资本优势低价倾销,对线下小商贩、农民等形成巨大冲击,对“稳就业”带来了较大挑战。
四、数字经济就业替代效应的表征及其制约因素
马克思提出,机器不仅仅是工人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而且总是置工人于失业的边缘。在就业创造效应持续释放的同时,数字经济的替代效应也不断深化。这种替代效应既带来了结构性失业的风险,又推动了更高质量的就业转化升级。
(一)数字经济就业替代效应的表征
1.“机器换人”持续深化
出于应对人口老龄化、劳动力成本提升、用工短缺的现实考量,以及智能机器水平不断提高降低人力比较优势的社会背景,越来越多领域运用机器人取代人工劳动力。我国已经连续8年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消费国,工业机器人应用领域已经覆盖汽车、电子、冶金、轻工、石化、医药等52个行业大类、143个行业中类,服务机器人、特种机器人在仓储物流、教育娱乐、清洁服务、安防巡检、医疗康复等领域实现了规模化应用[22],“机器换人”进程也在不断推进。未来随着技术智能化水平的提升,“替代效应”将从低端、体力工作向中高端、智力工作岗位蔓延。
2.新老业态交替加速岗位淘汰
随着各个行业数字化转型的广度和深度加速拓展,部分劳动密集型行业将会由于产业的创新升级受到严重冲击,继而引发较大规模失业现象。如电子商务行业的发展引发了传统商品交易市场的衰落,传统商品交易市场就业人数占批发零售业就业总人数比重从2007年的33.0%逐年下降,到2018年已不足18.0%[23]。隨着智能技术影响的进一步深化与泛化,其对我国居民就业的影响将会持续强化。据麦肯锡预测,到2030年,中国将至少有1.18亿人被人工智能或机器人替代,另外有700万~1200万人转换职业[24]。
3.数字经济加速更高质量的就业转化升级
一是推动向更高技能要求转化。智能技术首先替代的是那些高重复性、高风险性的工作,能够让人去从事更有创造性、更有价值性的工作。这将会提高劳动者技能和收入水平,进而提升企业产业中高技能劳动力的比例,从而推动社会就业结构优化升级。这对于推动我国产业转型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应对人口老龄化、低生育率与用工成本攀升等不利影响的关键之举。
二是促进向更高质量岗位转移。数字经济创造了更为多元包容的就业形态,吸纳了大量劳动力的就业转移,成为调剂劳动力市场的重要“蓄水池”。尤其是为社会重点群体的就业创造了更具新兴发展潜力、更高岗位附加值的广阔就业空间。数据显示,滴滴平台上20.4%的专职司机由于下岗、失业等而从事网约车工作,41.1%来自制造业,13.6%来自交通运输业,4.9%来自钢铁、煤炭等去产能行业。
三是推动向更高收入就业转变。数字经济就业具有明显的薪酬优势。2015—2019年,数字经济产业的年人均收入分别为11.20万元、12.24万元、13.32万元、14.76万元、16.14万元,非数字经济产业的年人均收入分别为6.35万元、6.83万元、7.44万元、8.17万元、8.79万元(见图3)。数字经济的薪酬优势不仅体现在技能密集型、知识密集型群体之中,而且体现在门槛较低的包容型岗位上。据美团数据显示,平台骑手中50%的月收入为4 000~8 000元,近10%的骑手月收入超过1万元[25]。而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农民工月均收入水平仅为4 072元。
(二)数字经济就业替代效应的问题透视
1.就业替代引发的结构性失业风险亟需关注
一方面,数字经济虽然带来了生产力与经济总量的快速提升,但劳动者不能在短时间内提升收入、甚至出现失业,出现“恩格斯停顿”效应,自动化投资的回报率往往需要经历较长时间才能以更高的工资和更为优越的工作环境回报给当代劳动者。另一方面,尽管数字经济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但劳动力的转岗再就业不可能无缝衔接,被替代群体很可能并不能胜任新创造岗位。就我国而言,当前劳动力人口结构明显不适配数字经济发展需要。我国就业群体受教育程度整体偏低且老龄化程度持续加大,与市场需求并不吻合。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在我国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构成之中,占比最高的是初中文化程度人员(超过40%),大学专科、本科、研究生比例加总后仅为约20%,反观英、美等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劳动人口比例往往能达到30%~40%。不仅如此,我国老龄化程度在持续加深。2011年,我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为100 283万人,占比为74.4%,首次出现下降,2019年这一年龄段人口下降为98 910万人,占比下滑至70.6%。
结构性失业风险的加大不仅会加剧劳动者的生存压力,而且会对社会管理带来巨大挑战。如工业革命时期英国掀起的以“捣毁机器,抵制新技术”为诉求的卢德运动,就是因为机器生产逐渐排斥手工劳动使大批手工业者破产,致使工人失业、工资下跌,工人将机器视为贫困的根源,由此引发集体行动、影响了社会秩序。这要求政府不仅应投入相当的社会成本来进行人力技能和素质教育,为低收入群体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而且要加强社会稳定性的管理。
2.就业替代风险的根源是就业市场供需不匹配
就业创造与就业替代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应当顺势而为,其关键在于新兴的岗位能否吸引足够适配的人才,被替代的劳动者自身能否适应新兴岗位。数字经济具有显著的“知识经济”特征,这对劳动力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现有劳动力市场的供给与需求并不完全相配,既加剧了就业替代效应的可能,又制约了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从而对稳就业带来了不利影响。
就我国而言,由于教育体系仍然具有浓厚的工业时代特点,无论是教育体系、学科设置,还是课程内容、教学方式方面都较为落后,不能适应数字经济发展所急需的高技术型、跨学科型、复合型人才培养需要。2020年数字化人才缺口接近1 100万人[26],无论是高素质数字人才,还是技能型数字工人都普遍短缺。据相关统计显示,目前我国人工智能人才缺口达30万人[27]。集成电路行业2023年前后全行业人才需求将达到76.65万人左右,或存在20多万人的缺口[28]。相较于发达国家,我国数字人才短板明显。根据《全球数字经济竞争力报告(2020)》,全球30个主要城市中,北京竞争力排名第八,是中国唯一进入前十的城市,但是其数字人才竞争力排在第23位(得分48.22,是纽约的71%)。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需要推动形成劳动力市场更高水平的供需动态平衡,在多措并举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的同时,必须着力解决持续凸显的结构性就业矛盾。
五、加快优化数字经济就业创造效应与替代效应的政策设计
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就业作为“六稳、六保”之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未来亟需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强化就业优先导向,加快释放数字经济就业的巨大潜力,充分激活创造效应、防范化解替代冲击,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一)破除就业壁垒,充分激活数字经济的就业创造效应
数字经济的就业创造效应潜力巨大,要创造更优的发展环境,加强政府、企业、社会多方协同,以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带动高质量就业,以高质量就业支撑高质量发展。
1.建立符合数字经济规律的就业政策体系
第一,推动劳动立法创新。一是对标国际、突破创新,借鉴英国、德国、加拿大等国家的立法思路,突破传统“劳动二分法”立法思路,基于经济从属性认定,探索完善“第三类劳动者”的身份认定机制,将灵活就业者与平台之间的关系纳入立法体系中,为保护灵活就业者提供基本依据。为了避免倾斜保护“一刀切”的问题,应从灵活从業者之于平台的从属性、持续性、协同性等方面对劳动者及保护程度进行分类。二是宽严并济、有紧有松,切实加强对劳动者公平就业、最低工资、最长工时、安全与卫生、隐私和个人数据等方面的保护,在标准工时、社会保险缴费比例、解雇保护等方面探索更为弹性灵活的管理方式。
第二,扩大社会保险覆盖范围。一是急用先行、重点突破。以社会各界关注度较高、灵活从业群体需求急迫的工伤保障为切入口,建立用工单位缴纳和政府补贴相结合的新型职业伤害保险,参照工伤保险以支定收的原则,实行独立核算,不与劳动关系挂钩,在涉及面广、风险较大的出行、外卖、即时配送、同城货运等领域优先推进。二是分级分类、精准施策。根据用工平台类型、用工特点等确定平台企业的责任份额,如在职业伤害保障机制中,对于外卖、网约车、代驾等风险更高、平台与劳动者联结程度更为紧密的领域,要求平台承担主要缴费责任,而对于家政服务等平台仅发挥信息提供作用、不直接参与交易的领域,由灵活从业者承担主要缴费责任。
2.建立多元协同的劳动者保障机制
第一,积极吸纳新职业从业者加入各级工会组织。突破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或者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限制,充分吸纳灵活从业者等新就业劳动者加入工会组织。集中推动重点行业依法普遍建立工会组织,积极探索适应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不同职业特点的建会入会方式。通过单独建会、联合建会、行业建会、区域建会等多种方式扩大工会组织覆盖面,最大限度吸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加入工会。紧扣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依托互联网平台开展工作的特点,大力推行网上入会方式,创新服务内容和服务模式。
第二,推动建立新职业从业者集体协商机制。鼓励不同数字平台企业选出新职业从业者职工代表,与工会、行业协会、头部企业或企业代表组织就行业计件单价、订单分配、抽成比例、劳动定额、报酬支付办法、进入退出平台规则、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保护、奖惩制度等开展协商,签订行业集体合同或协议,推动制定行业劳动标准,不断提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刚性和水平。行业协会应对本行业服务质量、竞争手段、技术标准、工资指导等问题进行严格监督,维护行业信誉,鼓励公平竞争,打击违规行为,保障从业者收入水平。
第三,健全法律援助和争议调解处置机制。加强各级法院和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机构对于新就业形态劳动争议的办案指导,畅通裁审衔接,根据用工事实认定企业和劳动者的关系。发挥各类法律援助机构、调解组织及其他专业社会组织的作用,向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法律咨询、法律援助、纠纷调解等服务。探索将互联网平台的灵活就业问题纳入公益诉讼制度,采取国家诉讼和私人诉讼并行的双重机制。
3.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平台的就业创造效应
第一,规范平台灵活用工机制。加快修订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无论平台与劳动者之间是否属于劳动关系,平台均有劳动者权益保障责任。压实平台对外包公司等合作用工单位的审核、监督、管理责任,劳动者权益受到损害的,平台应承担其过错范围内的相应责任。加强劳动监察,将落实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情况纳入行业诚信体系建设范畴。组织开展数字经济平台的劳动者权益保障满意度调查并定期发布。
第二,健全平台收入分配机制。要求平台建立与工作任务、劳动强度相匹配的收入分配机制,确保其向正常劳动从业者提供的报酬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引导建立劳动报酬合理增长机制,推进带薪休假制度,保障劳动者休息休假权利。完善平台订单分派与考核机制,遏制“以罚代管”,实行“算法取中”,加强对于平台在进入退出、订单分配、计件单价、抽成比例、报酬支付、工作时间、奖惩、职业安全等方面的算法审计,建立算法投诉审评机制。
第三,落实平台社会保险责任。督促企业依法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费,依法规范使用劳务派遣。推动企业引导劳动者参加社会保险,积极参加国家新型职业伤害保障试点。鼓励并支持平台为灵活就业群体设计灵活化、个性化的商业保险,对以商业保险方式为新就业形态和灵活就业人群提供多层次保障的平台企业予以合理支持。
第四,深入推进平台反垄断。突出竞争政策基础地位,强化“两个毫不动摇”“三个没有变”的市场预期管理,健全市场准入制度、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公平竞争监管制度,建立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监管体系[29]。加强对平台经济领域的IPO融资和增发、可转债、并购重组等再融资行为的监管,纠正平台不顾成本约束抢占市场、以补贴等不正当竞争方式压低行业边际价格的行为。推动行业自律机制的建立,以整体自律氛围引导企业走出无序扩张的怪圈。
(二)加强风险应对,防范化解数字经济的就业替代冲击
缓解数字经济的就业替代效应,一方面应加强劳动市场的供需匹配,促进劳动者转岗再就业;另一方面,应优化劳动力供给,增强与数字经济发展的适配性。
1.打造供需匹配效率更高的劳动力市场
第一,强化就业供需匹配。加强就业形势统计分析及动态监测体系建设,强化对劳动用工和失业的风险预警。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监测调度平台,打通省际劳务协作渠道,实现对劳动力资源的精準及时调配。充分发挥“互联网+”就业服务作用,强化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对接。
第二,加强失业或面临失业风险劳动者的技能培训。鼓励和支持大型企业通过“干中学”、转岗再就业等方式内部消化“机器换人”问题,引导失业工人通过社会培训进入数据采集、内容审核、云客服等就业门槛较低的数字经济岗位。
第三,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与劳动力技能结构适配互促。推进农业全产业链延伸和升级,开展高素质农民培育和家庭农场培育行动,在乡村振兴中带领农民共同致富。促进传统制造业数智化转型,加快智能制造人才培养,在提升国际竞争力中打造制造业就业新增长点。加快构建现代服务业体系,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鼓励发展新个体经济,在高品质和多样化升级中进一步强化服务业就业吸纳潜力。
2.推动劳动者技能结构数字化升级
第一,深化高等教育改革。突破工业时代界限分明、相对孤立的学科分类体系,以推动数字经济创新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为导向,构建跨领域、跨学科、跨平台的学科格局;促进计算机科学、数据分析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扩大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数字人才培养规模;建立专业退出机制,加强对高校专业课程的动态评估,及时停招、缩招不适应技术和经济发展要求的专业。
第二,推动职业教育创新。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引导行业企业同步制定与产业发展规划配套的人力资源开发方案,并与职业院校相对接,提升院校布局、专业安排与产业发展的契合度。依托数字平台建立线上线下课时衔接、直播点播课程互补、知识技能跨界学习的灵活培训模式,针对不同工作类型设置职业技能、创业指导、法律知识、职业道德、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教育等培训内容,对开展灵活从业者职业培训的平台企业给予一定职业培训补贴。
第三,建立终身教育体系。打造面向公众的智能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平台,开发“数字通识课程”,提供大规模、个性化定制学习服务。探索建立终身学习学分银行,提供学习成果积累与转化服务,以全民数字素养的有效提升支撑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1]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安德鲁·麦卡菲.第二次机器革命[M].蒋永军,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
[2]杨伟国,张成刚,辛茜莉.数字经济范式与工作关系变革[J].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18(5):56-60.
[3]秦国荣.网络用工与劳动法的理论革新及实践应对[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4):54-61.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5]PWC. Will robots really steal our jobs?[EB/OL].(2018-02-08)[2021-12-15].https://www.pwc.com/hu/hu/kiadvanyok/assets/pdf/impact_of_automation_on_jobs.
[6]HARRISON R, JAUMANDREU J, MAIRESSE J, et al. Does innovation stimulate employment? A firm-level analysis using comparable micro-data from four European countri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2014, 35(8): 29-43.
[7]资本论:第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509.
[8]NANETTE B. Goldman sachs embraces automation, leaving many behind[J]. MIT Technology Review, 2017, 120(3): 22-25.
[9]陆铭.大城市不需要低端劳动力吗?[J].上海国资,2016(6):17.
[10]AGHION P, HOWITT P. Growth and unemployment[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94, 61(3): 477-494.
[11]龚玉泉,袁志刚.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非一致性及其形成机理[J].经济学动态,2002(10):35-39.
[12]ACEMOGLU D, RESTREPO P. Robots and jobs: Evidence from US labor markets[Z]. NBER Working Papers, 2017.
[13]高德步.英国的工业革命与工业化———制度变迁与劳动力转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14]苏剑,陈阳.技术进步减少了劳动力需求吗?[J].开放导报,2018(3):28-32.
[15]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课题组.滴滴平台就业体系与就业数量测算报告[R/OL].(2019-09-12)[2021-12-20].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44455755786553904
&wfr=spider&for=pc.
[16]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数字化就业新职业新岗位报告[R/OL].(2021-04)[2021-12-20].https://xw.qq.com/cmsid/20210423A07CT600.
[17]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骑手生存与发展需求报告[R/OL].(2021-05-19)[2021-12-20].https://xw.qq.com/cmsid/20210520A0
DEFB00.
[18]中国邮政快递报社. 2019年全国快递从业人员职业调查报告[R/OL].(2020-01-02)[2021-12-20].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546
18717255670050&wfr=spider&for=pc.
[19]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企业责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2021年中国一线城市出行平台调研报告[R/OL].(2021-05-17)[2021-12-20].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9985867
144188043&wfr=spider&for=pc.
[20]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2021年货车司机从业状况调查报告[R/OL].(2021-06-29)[2021-12-10].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03
891798118464185&wfr=spider&for=pc.
[21]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外卖平台用工模式法律研究报告[R/OL].(2021-09-18)[2021-12-20].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11203695662679680&wfr=spider&for=pc.
[22]工业和信息化部.《“十四五”机器人产业发展规划》新闻发布会实录[EB/OL].(2021-12-28)[2022-01-21].http://wenku.baidu.com/view/47e4f206b52acfc789ebc92f.html.
[23]杨飞虎,张玉雯,吕佳璇.数字经济时代中国稳就业的挑战及政策建议[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21(5):78-85.
[24]黄浩.数字经济带来的就业挑战与应对措施[J].人民論坛,2021(1):16-18.
[25]美团研究院.2020年上半年骑手就业报告[R/OL].(2020-07-20)[2021-12-20].https://wenhui.whb.cn/third/baidu/202007/20/361780.html.
[26]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数字经济就业影响研究报告[R/OL].(2021-09-30)[2021-12-20].https://m.gmw.cn/baijia/2021-09/30/35204035.
html.html.
[27]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人工智能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白皮书2020[R/OL].(2020-11-21)[2021-12-20].https://www.baidu.com/link?url=y3G0Y8IdcNnRxT835TuU
9mPUr9_G23Num5wZnGfXjhC1fNaXO3tDR
6hGnFIBObViTqu4LspDXC-9-nCuCZQ4k6d
xfj0ulk6djdDFmOv3Vi&wd=&eqid=abc41d3
8002a7387000000026223618e.
[28]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中国集成电路产业人才发展报告(2020—2021年版)[R/OL](2021-11-03)[2021-12-20].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15367105563601917&wfr=spider&for=pc.
[29]许荻迪.平台势力的生成、异化与事前事后二元融合治理[J].改革,2022(3):24-38.
Research on Employment Creation Effect and Employment Substitution Effect of Digital Economy
HU Yong-jun GUAN Le-ning
Abstract: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brought about great changes in the employment market, which has led to significant changes in work organization, working methods and workers' skill requirements. It has not only created more jobs, but also replaced many jobs. It has had different effects on different periods, regions and group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ployment creation effect,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created new jobs,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stabilizing employment. However, the ability of the digital economy to create jobs has not been brought into full play, and the labor system and labor security need to be improv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ployment substitution effect, digital economy plays a role in optimizing the structure of the employment market, but we need to guard against the resulting structural unemployment and other risks. Digital economy i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achieving fuller and higher quality employment in the future. We should solve current problems, strengthen risk response and strengthen the formulation of policy system for digital economy.
Key words: digital economy; employment creation effect; employment substitution effect
作者簡介:胡拥军,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和产业发展部研究员;关乐宁,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和产业发展部分享经济政策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