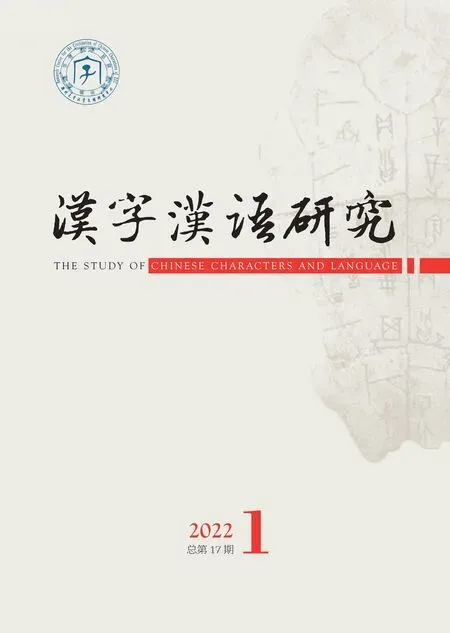从整体上看“龙山时代”前后中原和周边的“文字萌芽”*
黄 亚 平
(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提 要 中国文明有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作为中国文明符号标识的汉字,理应具有同样悠久的历史。但由于种种原因,尤其是受西方语言学理论对文字定义的限制,文字史家们在讨论汉字起源和形成问题时,总习惯于从甲骨文、金文开始,而罔顾汉字前文字阶段实际发生的事实,或者仅作为讨论汉字体系形成问题的附缀,这是不应该的。跟世界上的其他文字一样,汉字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汉字发生发展与演变的全过程始终与中国文明的发展趋势存在高度的一致性。在“龙山时代”前后中国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同时,出现在中原和周边地区的“文字萌芽”应从整体上看作汉字的原始文字。
“龙山时代”前后,随着中国文明“多元一体”大格局在中原腹地酝酿成型的发展进程,出现在中原和周边地区的“文字萌芽”,应从整体上看作汉字的原始文字,纳入汉字发展史的前文字阶段加以研究。理由如下:
其一,跟世界上的其他文字一样,汉字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汉字发生发展与演变的全过程与中国文明的发展趋势存在高度的一致性①有关汉字与中国文明的关系的讨论,另参黄亚平(2022)。。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二期(距今4900-4800年左右)算起,至“龙山时代”(距今4600-4000年左右)结束的这一段时期,中国境内各地域性史前文化出现了加速汇聚中原的态势,随着史前文化的大碰撞与大融合,“汉字萌芽”在以中原为核心的广大地域范围内涌现出来,史前中国地域文化汇聚趋势与汉字原始文字的出现相互一致,相得益彰。
其二,汉字是属于“表意”性质的视觉符号系统,文字具有明确的表意性,部分文字能够直接表达思想观念,记录语言的程度不应该是对表意文字,尤其是早期表意文字的全部要求。汉字的言文关系有一定的脱节现象是可以允许的,不能拿表音文字的“记语性”作为衡量表意文字是否成熟的唯一标准,而对汉字发展史早期的事实视而不见。
其三,汉字发展史研究应首先明确区分不同的发展阶段,既充分揭示不同发展阶段的重要特征,又牢牢把握整个汉字发展史的总趋势,正确处理各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与整个发展趋势之间的矛盾。一部汉字发展史可区分为前文字阶段、古文字阶段和隶楷阶段等三个发展阶段,每个阶段各有特点,但又统一于整个汉字发展史总趋势之中。缺乏汉字前文字阶段的中国文字发展史是不完善的,应明确将汉字的前文字阶段纳入汉字发展史研究的范畴之中。
在“龙山时代”前后的汉字前文字阶段,汉字原始文字在形体样貌方面大致可区分为“象形”与“记号”两大类;从字符功能方面观察,应有“记数”与“记名”等功能。由于尚处在“文字萌芽”状态,无论字符的样貌、数量,还是文字的功能,都还比较草率宽泛,记语能力有限,符合后代成熟文字标准的字符数量不足,文字的表达方式也比较多样化,并没有形成完全统一的格式。即便如此,也不妨碍我们从整体上把这个发展阶段归入汉字的前文字阶段,把这个阶段的文字称为成熟汉字之前的“汉字原始文字”或“先行汉字”。
“龙山时代”前后的汉字原始文字,从其分布地域范围来看,大致可区分为中原系统、山东系统、江南系统等三大系统。三大系统中的一些图画、纹饰、记号及其记号组合,虽然仍带有一定的地域特色,但已经表现出史前文化融合汇聚的特征,并初步具备了汉字原始文字的属性,应从整体上归入汉字发展史的前文字阶段深入讨论。
1.中原系汉字原始文字
1.1 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
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出土的彩陶“太阳鸟”纹饰或图像是汉字原始文字象形类的典型代表之一。其中不但有侧面的太阳鸟纹(图1.1-2),也有正面的太阳鸟纹(图2.3-4),而且不论正面还是侧面纹饰,都有较为明显的演变痕迹。

图1 庙底沟类型二期侧面、正面太阳鸟纹汉字原始文字

图2 庙底沟类型侧、正面鸟纹演变图[采自张朋川(2005:158-159)]
庙底沟类型太阳鸟纹饰或图像不但出现在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范围之内,而且出现在相邻的山东大汶口-龙山系文化、江南崧泽-良渚系文化、江汉平原石家河文化,甚至还出现在西北地区的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中。从时间早晚来看,河姆渡文化中出现的太阳鸟纹饰应是中国东南地区该类纹饰的祖型,太阳鸟纹饰从河姆渡文化向北、向西传播进入山东、河南境内,逐渐汇聚中原,并传入西北地区,成为史前时期中国境内代表东南部庞大鸟崇拜集团的符号标识。此类鸟崇拜图像与大汶口图像文字的性质大体相似,应是古汉字象形文字的滥觞之一。
1.2 中原龙山文化
约距今4600-4000年的中原龙山文化,从地域上还可再区分为河南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客省庄二期)、龙山文化陶寺类型等。无论从地望、时代,还是从社会发展程度考虑,中原系龙山文化相较山东系龙山文化、江南系龙山文化都应该更加贴近古汉字的成熟文字,它是理所当然的古汉字的直根系。中原系龙山文化发现的汉字原始文字与那个剧变的时代文化交流频繁发生而多变的特色息息相关,并在符号层面呈现出来源多样化、符号借鉴现象频仍发生、符号记语性尚不充分的特点。
约距今4600-4000年的河南龙山文化出土的陶器以灰黑陶为主,陶器上发现的刻划符号和原始文字的数量都较少,而且绝大多数是单个符号。其中部分符号在不同史前文化中都有发现(图3)。

图3 河南龙山文化中发现的部分汉字原始文字
约距今4300-4000年的陕西龙山文化(客省庄二期)考古发现的陶符和汉字原始文字仅有数种,其中,在绥德小官道遗址出土的陶器比较接近庙底沟二期文化(图4)。这是因为,中原庙底沟二期文化在向西传播的过程中难免同时附带符号的传入,因此才有庙底沟二期的符号出现在陕西龙山文化,甚至出现在更西部的马家窑文化晚期的现象。而同类的符号传播现象不但出现在陕西龙山文化、西北马家窑文化,还出现在江南良渚文化、江汉平原石家河文化中。这一符号传播现象可以看成龙山时代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符号的激发扩散。

图4 陕西绥德小官道遗址发现的汉字原始文字
约距今4300-3900年的中原龙山文化陶寺遗址考古发现了1件残破泥质灰陶扁壶,其腹部右侧有一朱书符号,左侧另有两个朱书符号(图5.1)。李建民、罗琨、高炜、冯时、何弩等人将右侧的朱书释读为“文”字。张政烺先生指出:“这个字同大汶口文化陶文、殷墟甲骨文和现在通行的汉字属同一个系统。”(参看高炜,2007:175)图5.1左侧的两个朱书陶文,罗琨认为是“昜文”二字,记述尧的功绩;何弩认为应是“文尧”二字,“文”是尧的尊号。冯时认为朱书陶文应为“文命”二字,正好与文献记载里所说的夏禹的名字“文命”相应。2017年,何弩新发表了陶寺遗址ⅠM26墓底北侧壁龛中新发现的另1件骨耜文字(图5.2)。他认为该骨耜未见使用痕迹,可能是“与农事有关的礼器”,其上的人工刻划符号形态类似象形,或许标示了墓主农官的职位,应释读为“辰”字。何弩(2017)并指出,“辰”字的发现“不仅丰富了陶寺文化文字的字形数量,而且将汉字体系的出现年代再次提前,进一步证明陶寺文化文字是甲骨文、金文文字系统的先河”。同年,陈治军(2017)认为,陶寺遗址ⅡM26出土骨器不是骨耜,而是仿制玉圭或玉笏的骨礼器,其上刻辞不是一字,而是“家有”两字(图5.3),意思是“家国能大有”。

图5 中原龙山文化陶寺类型原始汉字
1.3 夏代与商早期文化
约距今3800-3500年的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考古发现了宏伟的宫殿建筑群、青铜器及其各类手工艺作坊,发现了普遍共存和成群出现的陶器以及墓葬中以成组陶制酒器陪葬的现象,充分说明二里头文化已具备最初的国家形态和礼文化特征。
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20余种刻划符号绝大多数刻在大口尊的内口沿上,许多文字学家都认可它们是原始汉字。曹定云指出,约当夏代晚期的二里头文化陶器刻符中的一部分是原始的数字,如等;另有一部分符号已经是夏代晚期的文字(见图6)。实际上,二里头陶文不但是夏代晚期的文字,而且是与殷商中、晚期的陶文有直接联系的中原系原始汉字,商代陶文则应是在二里头陶文基础之上的进一步发展(曹定云,2004)。

图6 二里头陶文原始文字[采自曹定云(2014)]
商代中期,中原系汉字原始文字首先发展出了“商代陶文”。有关其性质,照理应纳入汉字的古文字阶段之内加以讨论,但由于目前中国文字史尚未正式接受“商代陶文”为成熟汉字,尚未将其作为商代通行文字中最早使用的那一部分文字来看待,故我们在这里一并进行初步的探讨①有关商代陶文的性质及其在汉字发展史上的归属与地位,另参拙文《论“商代陶文”应单独列为一系——兼谈“陶文”与“陶符”的区别原则》的讨论。。
商代陶文可分为前、后两期。考古发现的商前期陶文(包括数字在内)即便按最保守的估计也有50余例。这些陶文主要发现在郑州商城遗址二里岗期、郑州小双桥、河北藁城台西等遗址。从总体上看,商前期各地陶文的书写风格既有抽象,又有象形,与甲骨文、金文一脉相承,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符号传承关系。对于商代陶文,许多文字学家都比较认可其与殷商甲骨文、金文之间存在一脉相承的联系,有人还对其中一部分陶文进行了释读(参看黄德宽,2006:11-25)。在商前期的陶文中,同一个陶文单字,在各地重复出现的情况也比较普遍,其中最常见的是“记数文字”和“记名文字”。当然,商代陶文中也有部分陶文和陶符之间较难区分,另有部分陶文具有地域风格。
商后期陶文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殷墟陶文,它们与甲骨文、金文同处一时、同出一地,字的结体和书写风格不但与甲骨文、金文基本一致,而且与商前期陶文异曲同工。若去除形体重复和基本相同的情况,商后期新增陶文的数量在40例以上。此外,在吴城陶文中,还发现了部分明显带有地域元素和南方风格的陶文,比如横写的“戈”字,箭镞的“镞”字,就有明显装饰风格;部分“多字陶文”还具有南方越人文化的地域风格。
无论从社会发展条件和社会需求的角度,还是从文字制度和书写习惯的形成与积累程度来看,商代都已然存在通行范围甚广的汉字系统,这其中当然应包括陶文在内。“商代陶文”应是一种体系性的存在,是商代通行汉字(何崝,2007)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较早出现的那一部分。
2.山东系汉字原始文字
从地望、社会发展程度、骨卜传统、史前符号的图像形态等诸多因素来综合判断,山东大汶口文化晚期-龙山文化各遗址出土的陶器和玉器上的图案,很有可能是古汉字象形文字的另一条直根系。与中原系不同,山东系图像类原始文字较多而记号类原始文字少见,同时伴随出土较多的“太阳鸟纹”,较多的实足与空足鸟形陶鬶,以及骨卜传统的遗物。
2.1 山东大汶口文化晚期
距今4800-4600年的大汶口文化晚期陶器上发现的部分图像文字是典型的汉字原始文字的代表(见图7)。其中图7.1唐兰释为“炅”字;图7.2唐兰释为“炅”的繁体,于省吾释为“旦”字,李学勤释为“炅山”;图7.3唐兰释为“斤”字;图7.4唐兰释为“戉”字。此类史前图像应是古汉字象形文字的滥觞之一(唐兰,1975;于省吾,1973;李学勤,1987)。

图7 大汶口文化大口尊上的汉字原始文字
2.2 山东龙山文化
山东龙山文化考古发掘中未见与大汶口文化晚期图像文字近似的汉字原始文字,但却出土了较多神奇的兽面纹、陶塑鸟和形制不同的鸟形鬶,而且在三足盘和盆形鼎中还首次出现了以鸟头作脚、鸟嘴着地、面如鹰隼一类的猛禽形足,或被称为“鬼脸式”足或“鸟喙式”足。这一文化现象被认为是山东古代东夷族鸟图腾崇拜的产物,而与中国上古文献中记载的有关鸟图腾部落集团的神话有关(参看安立华,1989)(图8)。

图8 山东大汶口-龙山文化鸟形器
据说殷商的祖先是东方夷人,以鸟为图腾。《诗经·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石兴邦(1989)指出:“商人的鸟图腾,在甲骨文中还有遗留,尤其在祭祀他们先公先王中最为显赫的高祖王亥时,头上总要冠以鸟形,以记其不忘祖源之义。”商周金文中有许多带鸟形的铭文及器名应是鸟图腾崇拜在商周铜器上的反映(图9.1-2)。

图9 鸟图形铭文[采自石兴邦(1989)]
2.3 岳石文化
山东岳石文化上承龙山文化,下接夏商文化。考古人员在该文化桓台史家和唐山两处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多处祭祀、占卜和人殉遗迹,以及专门的木结构祭祀器物窖藏。桓台史家遗址木结构祭祀器物坑内出土了2件岳石文化晚期的文字卜骨(图10)。2件卜骨皆为未经修治的羊肩胛骨,已残损,其上兆文大部分已失,但仍残留了一些人工刻划符号和文字。据考古报告,图10.1标本96HSF1H:226正面有明显的人工划痕,中间一字为“”,即“幸”字;图10.2-3标本96HSF1H:232两面均刻有文字,一面为“”“”,可释为“大”“卜”;另一面有“”“”和“”三字,未释读。桓台史家卜骨上的文字被认为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最早的甲骨文。它的发现,将甲骨文的历史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这对研究夏商时期东夷文字和甲骨的占卜契刻源流提供了重要线索”(参看淄博市文物局等,1977)。

图10 岳石文化晚期有字卜骨
综合考虑山东大汶口-龙山系考古学文化中发现的图像文字、兽面纹、鸟形塑、鬼脸式盆形鼎足、桓台史家的有字卜骨,这个地区广为流传的太阳鸟图像崇拜,以及殷商民族的族源出自东方的传说,应该承认,山东系汉字原始文字,尤其是东夷文化发达的图像叙事方式对甲骨文、金文同样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应是古汉字的另一个直根系。
3.江南系汉字原始文字
3.1 良渚文化汉字原始文字
江南良渚文化黑陶器上发现了总数600多个的原始文字或前文字,其中既有单个的象形类原始文字,又有抽象的记号类原始文字;既有单个象形类原始文字的组合,又有单个记号类原始文字的组合(张炳火,2015:32),此外,还发现了少量的刻划在史前“名牌”之上的“记名文字”。
单个的象形类原始文字如龟、鱼、猪、犬、鹿、飞鸟、燕子以及部分植物、农具、网、干栏式建筑的图形(图11.1-4),单个的记号类原始文字呈几何形状,有非常丰富的样貌(图11.5-10)。

图11 良渚文化黑陶器上出现的单个原始文字
伍淳发现有三块明显打磨加工痕迹的良渚文化黑陶片(参看伍淳,2019:8)。其中的标本T2⑪:11被特意磨成臂章形,其上有一“木”字状符号;标本G2②B:197被磨成了不规整的扁圆形,其上有一网格状符号;标本G1②:381被磨成了三角形,其上有一圆角“田”字形刻符,中间交叉点上有穿孔(见图12)。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发掘报告(2014)指出:“这个‘木’一定具有指事功能,所以它应该是最接近原始文字的一个符号。”如若此言不虚,则该圆陶片有可能是史前时代的“名牌”,其上的抽象陶符则很可能是良渚文化的原始“记名文字”了。类似的情况,在中原腹地的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墓葬以及其后的商文化遗址中同样有所发现,可为旁证(李志鹏,2008:28)。

图12 良渚文化黑陶片上的单个原始“记名文字”
良渚文化陶符还有较为丰富的符号组合形式,其中既包括单个象形类原始文字的组合,又包括单个记号类原始文字的组合。其中图13.1陶尊腹部有1个梅花鹿图案,1个石钺图案,宋建(2002:34-35)认为:“梅花鹿石钺图记录了一次大型的由氏族首领亲率的集体活动。石钺就是权杖,代表了权力和有组织的大规模行动,鹿为行动的对象。这可以是一次狩猎,以捕获鹿科动物为目的;也可以是一次祭祀,祭品就是梅花鹿。”图13.2在黑陶罐肩部发现了2个图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报告(2014:353)认为:“一个为家禽形,一个为栅栏形,似乎在表达一个事件。”图13.3李学勤(1994)释读为“巫、戉(钺)、五、俞(偶)”四字,意思是指“神巫所用的五对钺”。

图13 良渚文化黑陶器上的组合式原始文字
良渚文化黑陶器及其上出现的刻划符号性质,在总体上仍属于“龙山时代”考古学文化。在这一时期,中国境内各大史前文化迅速向中原地区汇拢,文明发展趋势已经为文字的出现准备了充足的社会条件,因此,良渚文化黑陶器上的符号与符号组合,虽然在地理范围上距离中原较远,文化交流也不如上述中原地区和山东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充分,但其整体性质也应该不同于龙山时代之前散见于中国各地的史前陶符,已经初步具备了“汉字先行形态”的性质,应作为汉字体系形成的源头活水之一来看待,加以深入挖掘。
3.2 石家河文化汉字原始文字
约距今4600-4200年,约当中原龙山文化王湾三期,山东龙山文化和江南良渚文化后期,在江汉平原地区的石家河文化中也发现了50多种陶器刻划符号。其中,绝大多数符号发现于泥质灰陶大口尊腹部(有意思的是,这种器皿并非石家河文化自产,而是来自周边相邻的大汶口文化),大口尊上的符号既有象形的,如图14.1-3;也有几何形的,如图14.4-6。绝大部分符号是单个出现的,如图14.1-6;也有个别组合形式的符号出现,如图14.7-8(参看郑中华,2000)。与龙山时代其他相邻的史前文化一样,石家河文化的陶器符号同样是一种具有一定地域特色的汉字原始文字。

图14 石家河文化陶器上的汉字原始文字
不但石家河文化的符号载具——陶大口尊来自相邻的考古学文化,而且大口尊上的部分符号也与相邻的考古学文化有所牵连,如符号“”与良渚文化玉器和陶器上出现的同类符号近似,符号“”“”“”“”“”则与大汶口文化陶大口尊上的同类符号近似。这种情况正好是龙山时代中国境内各地域性史前文化加速汇聚发展的符号证据。
总之,如果我们承认社会发展程度是文字系统形成的先决条件之一,那么,汉字系统的形成与建立最有可能是在距今4900—4000年左右中国境内的“龙山时代”,汉字最有可能的直根系应在中国境内中原地区和东南地区的中原龙山文化、良渚文化、山东龙山文化等史前考古学文化之中。针对汉字字符来源的研究,应该紧紧围绕广义的“龙山时代”以上几大考古学文化类型及其交流与互动情况展开,而不是漫无目标地四处寻找与无限系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