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对《周易》“时”思想的探究
叶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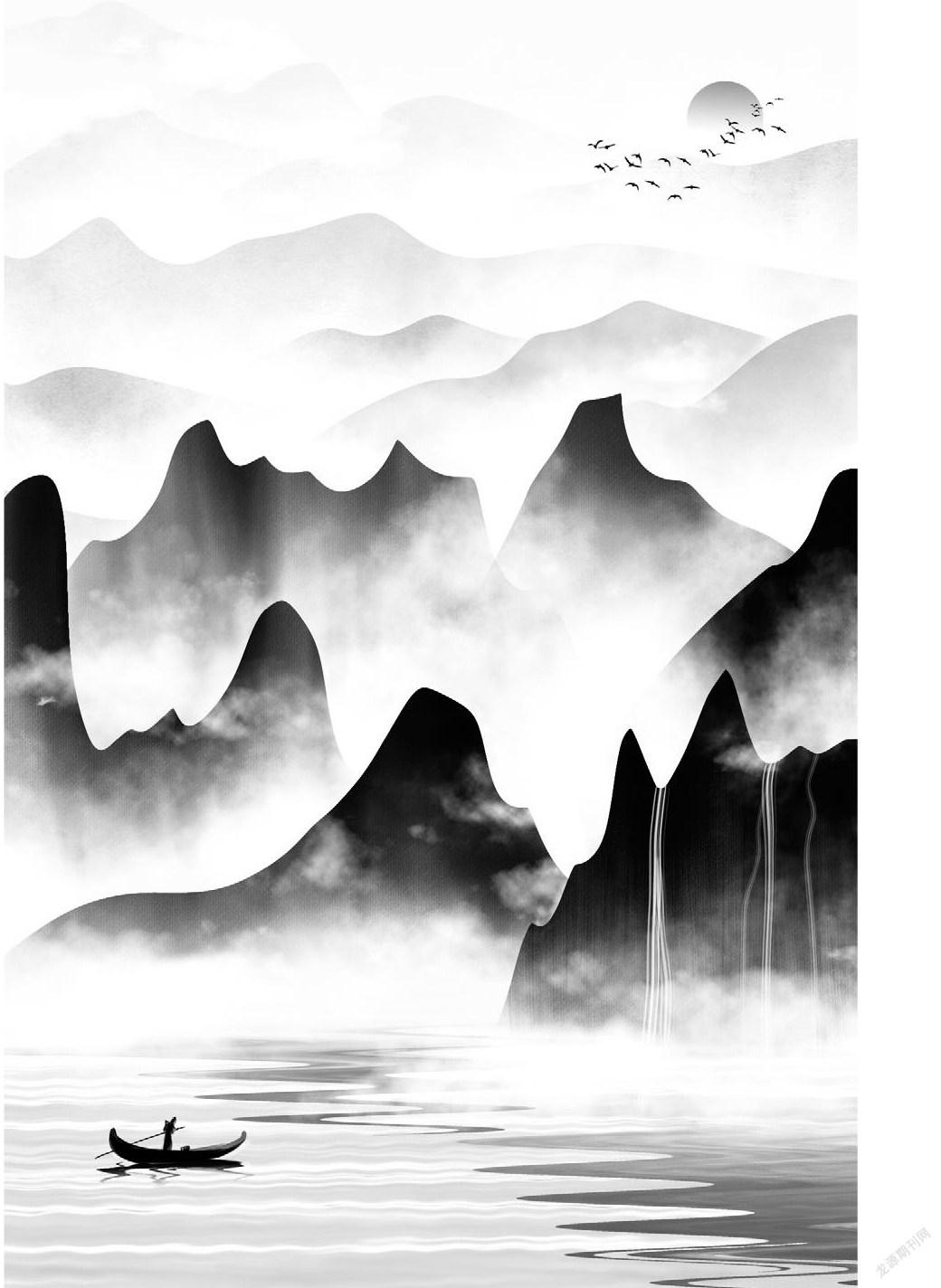
史不离“时”,司马迁著《史记》宗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皆在“时”中。他将“究天人之际”置于首位,可见“天”“人”观是解读司马迁思想之关键。司马迁继承《周易》重“时”的特点,“推天道以明人事”,在天“时”的基础上注入了其对人“时”的倚重,以人为重心,强调“人”才是历史盛衰“时”变的主要因素。《周易·系辞下》云:“《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时”是贯通《周易》天人思想的核心概念,天、地、人三才皆在卦爻辞之“时”中,与“时”变化,随“时”通变。史官历来重“时”,司马迁史学和易学思想意识源出于巫、史同源时期巫史卜筮、沟通天人之职,其著史宗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皆在“时”之经纬中,与《周易》“时”观如道器交织,殊途而同归。司马迁承巫、史、儒三种思想,“究天人”是由“天”至“人”重心转化的理性思想的建构,突出“人”在历史时势中所起之主导作用。司马迁以人为重心,为人列传,重视“人”在历史演变推动之作用,是对人在大一统时代背景中新的定位,是他究天人之“时”,通古今之“时”,与“时”变化背景下的易学思想之“时”观的解读。
一、司马迁对《周易》“时”思想的继承
中国历代史学家多对《周易》有精深的研究,以易学思想解读历史是中国古代史学的特点之一。史出于巫,巫史同源,巫史保管且精通《周易》,《周易》成为史学家解说历史和释意卦爻辞的思维依据。司马迁虽无专门的易学思想著作,但《史记》中却多有引用和化用《周易》哲思以《易》解“史”。溯源其易学思想,一是司马家族世典周史,典天官事,司马迁承继先祖史官之职;二是其父司马谈受《易》于杨何,孔子后传《易》至杨何是八传,乃儒家易学思想源流;三是师承于大儒董仲舒之学术思想渊源。
《周易》本卜筮之书,神秘之处往往在于借天道以明人事,天道被赋予了某种神格,合《易经》和《易传》为一体的易学思想,升华了原始巫术形态之精髓内涵,实现了人文理想之升华。《丰》卦彖辞云:“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显然,自然规律非人为所能驾驭。儒家思想中,社会之根基且能推动社会前行的就是人,《周易》不仅奠定了中华民族“天人”思想的思维方式,亦建构了后世学者对“天人”关系的理性思考。受《周易》思想之影响,司马迁更重视的是历史人物的道德色彩和“人”对历史进程的影响,而不是看重人物的出身和地位。《太史公自序》曰:“《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天官书》曰:“为天数者,必通三五。终始古今,深观时变,察其精粗,则天官备矣。”司马迁“时”的思想与史官记录历史,观测天时之职责相关,含自然之“天时”和时势之“人时”深意,其著史宗旨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含义逐层递进。司马迁将“究天人之际”置于首位,可见“天人”思想是解读其“时”观深意之关键。《系辞下》云:“《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天、地、人三才皆在卦、爻辞之“时”中,与“时”变化,随“时”通变,可见“时”是《周易》贯通天人思想的核心概念之一。《贲》云:“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系辞下》云:“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乾文言》云:“终日乾乾,与时偕行。”“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革》卦彖曰:“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事大矣哉!”皆强调应把握“顺乎天而应乎人”之“时”。司马迁“时”思想由“天时”至“人时”的理性思想建构,与《周易》对其影响息息相关,司马迁强调人时之深意,以天时推及人时,强调人的积极作用。“时”是人不可主动抉择的,需顺天应时,但并不意味着人在“时”面前完全被动,而应当主动把握驾驭“时”,与“时”变化而行。
史不离“时”,史在“时”中,时势皆随“时”变迁。史官之职与“时”息息相关,《史记》“时”观源出于巫、史同源时期史官沟通天人之职能。韩兆琦先生在《天官书》简评中述天官亦称为星官,经过薄树人先生研究,《天官书》的星官体系是司马氏的体系,也是汉代皇家机构所使用的体系。司马迁记载:“幽、厉之后,周室微,陪臣执政,史不记时,君不告朔……是以其禨祥废而不统。”史官记“时”是周室不微乃至后世王室朝代有序不微的重要象征之一,司马迁重“时”不仅是其承继先祖,世典周史职责所在,亦是其隐喻朝代式微与否的标志之一。他对“时”的重视不仅是先祖卜祝之职的延续,更是其自身理性思想的升华,是从巫祈天至史家究天,从顺承天时至驾驭人时的深层思考,这反映了西汉前期易学思想的史家特点。司马迁对“时”观的理性构建与巫史演化历史息息相关,是对“天人”关系在大一统时代背景下的理性思考和对“天”“人”重心重新定位的哲思解读,是以《易》解“史”的时代解答。
二、司马迁的“时”思想在《史记》中的展现
司马迁的“时”思想,与其所处时代的儒学思想密不可分。司马迁生活的时期,“天时”“天灾”等灾异的言论,引发了人们对“天人”思想的关注,作为典天官事的史官,司马迁对“时”的思考是必然的。经过“文景之治”的西汉王朝,至汉武帝时达到强盛阶段,此时的“无为”思想必然要被新的治世思想所更替,而儒学是最能符合武帝要求的,亦必将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学术思想。公元前134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天人三策》之谏“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作为董仲舒的学生,司马迁受到儒学思想的渗透与此背景不无关系。
然而司马迁的“天人”思想从本质上来看,和其师的“天人”思想是有差異的。董仲舒的“天人”思想,其重心落在“天”,由“天”统领一切;而司马迁的“天人”思想,其重心落在“人”,司马迁“究天人之际”,所言之“天人”,其核心和意欲表述之深意在“时”,是“天时”向“人时”重心的转变,人可以主导并决定历史演变的时势、时机。他的思想体系中剔除了董仲舒“天人感应”的神秘色彩,《太史公自序》中曰:“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可见,司马迁阐释的“天”和“人”之间并不存在神秘谶纬的“感应”关系,“天”是四时变化交替的自然存在,是以自然之“时”呈现的顺应规律。他亦指出:“星气之书,多杂禨祥,不经。”认为星气之书宣扬的思想是不符合逻辑的,人的福祸与星象的变换是没有必然关联性的,这点他与父亲司马谈的观点一致,司马谈认为:“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阴阳之术宣扬的吉凶之兆会让人有所忌讳,将导致人们拘束不安并感到恐慌、畏惧。
在《史记》中司马迁并没有引用、节录或阐释《天人三策》的相关理论或思想,虽师承于董仲舒,但司马迁并没有给老师专门立传,《儒林列传》中还认为董仲舒“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可以看出,对“天”“人”理念的差异,源于其二人观点立场的不同,董仲舒从政治角度出发,而司马迁从史官角度出发,以记录时事为主,对所记录的历史人物、事件和时事演化多从现实和理性的角度出发,强调时势、时机的主导性。而“天人感应论”强调的“天”是根据人事行为的好坏、良善而招致相应的福祸,对此司马迁是有质疑的,曰:“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作为好人的伯夷、叔齐并未得到好报,作为坏人的盗跖也并未得到相应的恶报,故以“天”作为衡量的标准,真的就能够赏善罚恶吗?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再次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人事的成功与失败,其内在根源一定是“人”之时势、时机的因素,并非“天”之主导命定。同样,在王朝更替的规律上,司马迁并不认同将王权的兴衰成败理解为带有命定色彩的“三统三正”“五德终始”之论,如《三代世表》中司马迁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他指出历史所记载的同一国世系,往往是自相矛盾的,社会的发展演化是有其自身变化规律的,一个王朝的兴衰成败不应该由“天”来命定,而应该由“人”来决定,如何把握人时、人势,利用时机,这就是对“人”的重新定位。可以看出司马迁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探究重心上采取了与其师董仲舒甚至是同时期思想家不同的理性思考方向,他从社会、时政以及人时、人势的角度展开对“天人”思想的研究分析,引申至对“时”的反思,可以看出这是探究司马迁“天人”思想的核心观点所在,他以“人”为重心的思想为后世传递了一种理性的思考方向,亦是解读其“时”思想的重心所在。
三、司马迁对易学“时”的反思
中国古代史学家探究“天”和“人”,通常都是将两者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思考,体现了中国古代史学“天人”观的整体思维模式。这一传统体系源于《周易》,从《周易》的卦画结构来看,就体现了天人合一的理念。《说卦传》云:“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將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易经》六十四卦每一卦六爻的符号呈现,都展示了天、地、人三才合于一体的模式。《系辞上》认为,在“天人”一体的模式中,“天地设位,圣人成能”,人可以顺应天道,发挥主观能动性,以成就天地生化万物的功能,促成事物的发展变化。《周易》之“天”是人可以效法之“天”时展现人的力量,阐发人的作用和价值,这种思维方式启发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对“天”“人”关系的重新探究。
先秦史官因职业缘由,保管且精通《周易》,史官从四时、天象的循环往复和古今通变中觉察出社会人事的演变,将天道与人事结合起来解说社会各种时事现象,司马迁就是其中典型的探究者之一。司马迁探究之“天人”,第一层有自然之“天”的含义,如《史记》中记录的天象变化、四时自然和与时变迁等等;第二层所指之“天”与人的关联密切相关,受人的推动和影响,历史时事发展之“势”,即一种必然发展的趋势,也是一种时机态势。首先,司马迁是肯定人事对历史发展作用的,他从“时”的角度而言,阐释为自然之时和时机、时势等与人相关之“时”的内涵。但同时,司马迁对“天命”是有质疑的,《蒙恬列传》云:“夫秦之初灭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伤者未瘳,而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强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脉哉?”他论述项羽为:“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司马迁从史家客观的角度评定其笔下的历史人物,从现实之时势出发,不信传统之“天命”,不以成败论英雄,可见其“天人”思想多是以儒家君子之“德”为行事标杆和入世标准的。
司马迁给世人展现了他所建构的历史世界,如五帝时期是司马迁希冀的理想时代,司马迁笔下唯独对五帝时期满是溢美之辞,他饱含理想去建构且陈述那个时代,创建了一个国人理想的太平盛世。《史记》对中国历史影响巨大,对后世影响极其深刻,了解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离不开对《史记》的解读。《史记》的历史思维方式对国人影响至深,司马迁在“独尊儒术”的大时代背景中接受儒学的洗礼,又以儒家易学思想反思其史学思想,《天官书》云:“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强调以修“德”为本。因此,我们今天读《史记》,不仅要了解历史时事,且要反思为什么司马迁要以这样幽隐的方式以《易》解“史”。

